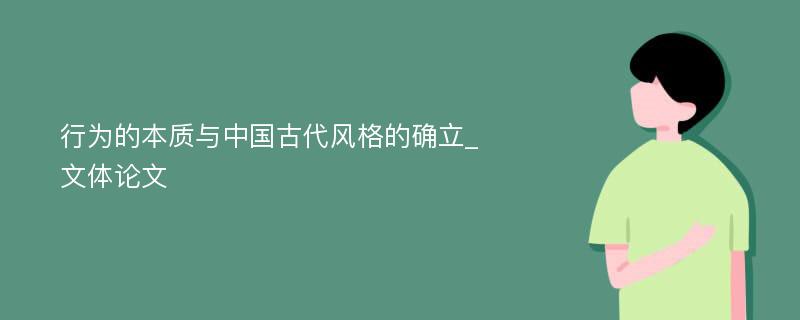
行为性质与中国古代文体的确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文体论文,性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文”学的行为经验本质,确立了中国“文”学文本为不同行为过程中“文字单元”的性质,也确立了中国“文”学文体的发生机制和文体区分的主要原则,即以不同的行为性质作为中国“文”学文体的区分标准。这一原则的确立,使中国古代一级文体形态摒弃了以西方语言形式来确定文体的原则,而且也是众多一级文体向二、三级文体发展的依据,散文、小说、戏曲也依然保持着这一特征。故中国的文体,大都有着一定的内容、风格的要求,而在语言形式上,各种文体却都可以相互兼容。这一点,形成了中国古代文体和文体学的基本特征。 在中国古代文体的研究中,中国文体依据什么确立、怎样发展和文体要素到底因何而产生这些根本问题,很少得到关注。解决这些问题,对认识中国古代文学的性质以及文学的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故本文不揣陋见,试加阐释。 一 行为性质与文体的发生 西方认为文学只是对现实生活的模仿,将文学文体分为史诗、抒情诗、戏剧,虽涉及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但核心是依据表现形式来区分文体。西方后来的文体理论也有多样化色彩,但以形式区分文学文体却是西方众多理论家的选择,故西方不少人将文体学列为语言学的分支,如徐复观所说: 西方的文学领域是纯文艺性的,很少含有人生实用上的目的,因之,其种类的区分,多是根据由语言文字所构成的形式之异。①中国“文”学的一定性质行为经验的本质,不仅确立了中国“文”学功能文体的性质,也确立了中国古代文体与西方文体不同的发生方式,为中国“文”学文体的分类确立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文体分类模式。 现实生活中任何一种性质的行为,都有一个过程。这种过程一般都由几个行为单元结构而成,诸如决策、准备、实施等。一个实施中的行为,也分为不同的步骤和单元。中国文学从本质上说,是人们的社会生活自身,而非西方所谓作家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因而,中国的“文”学作品,也就是社会生活不同性质的行为过程中的“文字单元”,即文本;每一文本的产生,都有一个“前因后果”的行为过程。“前因”,即驱使主体写作的事因行为过程,“后果”即文字言说过程。那些用于应酬如赠、和、答、应制、奉和、寄、酬、饯、问、送、别之类的诗歌,都具有典型的行为过程中的“文字单元”性质。 中国自古就有文因事而作的观念。《毛诗序》以为每一诗都是因事而发。班固认为,汉乐府“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②。其后,历代文人皆有类似表述。而所谓“缘事而发”“触事感物”“因事而发”,都表现出将文本的产生看作是一个行为过程结构单元的观念。既然每个一定性质过程中的文字单元就是一个文本,那么“一个行为过程中的文字单元,在诞生时就同时具备文体和文本的双重涵义,是一个具有文体意义的文本。这也就是说,每一个文本都是一定类别文体的文本,而每一文体的意义都必须以文本的形式表现出来”③。因而,在文体的发生时期,文体与文本就同是一定性质行为的产物。 考商代甲骨文、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的铜器铭文,还未见有文体的分类。《尚书》主要为行政公文之类的文献,亦是我国最早明确标明文体的文献。刘知几说《尚书》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④,这是指《尚书》的六种文体。据西周的铜器铭文,《尚书·周书》的那些文献应该是真实的。因而,根据《尚书》的“六体”,可以分析出那个时代人们对于文体的区分原则。《尚书》有些篇名并不标明其所属文体,但《尧典》《康诰》《文侯之命》《秦誓》《皋陶谟》等,却都是以行事主体之名结合行为性质名篇、行为性质为不同文体区分的核心。 “诰”由“告”发展而来。“告”原本是一种行为方式,即一方将自己的意见告诉另一方。如甲骨文“黎方来,告于父丁”“王于唐告”,其中的“告”都用于人际关系行为,即告知对方。周初,已出现“诰”字,如《尚书·大诰》:“王若曰:猷大诰尔多邦。”也有“诰”写作“告”的,如《多士》:“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召诰》:“旅王若公,诰告庶殷。”则“诰”“告”连用。从《召诰》这两句话看,前一“诰”字显然已经具有了文体的意义。“诰告庶殷”应理解为:以诰文训告殷遗民。而当诰成为古代的一种行政公文文体时,它就只能用于帝王对臣民进行政治、道德言说。 “训”,一般训为“教”。但作为一种文体,“训”也并不能用于任何关系的言说。从先秦的一些“训”来看,“训”多用于君臣之间的言说,既有君主对臣下之“训”,也有臣下对君主之“训”。如《史记·殷本纪》谓伊尹作《伊训》,言说对象当是太甲。《尚书·高宗肜日》说:“高宗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训诸王。”孔疏谓:《高宗肜日》与《高宗之训》“二篇俱是祖己之言,并是训王之事”⑤。所以,《高宗肜日》亦可以“训”视之。“训”这一行为言说的对象虽然有些为帝王,但“训”的主体几乎都是德高望重者。因而,是德高望重者以道理教导对方这一行为性质赋予了“训”这种文体的特性。 “誓”,源于人类社会活动人际之间的某些行为信约需求,主要表示一种决心、行为的不可改变。如《左传》昭公十六年谓:“世有盟誓,以相信也。”现存《尚书》的誓辞,主要用于战争的仪式行为,如《周礼·士师》云:“誓,用之于军旅。”《尚书》载有启伐有扈时在甘之野所作的《甘誓》,还有《汤誓》《牧誓》《费誓》也都是战前誓辞。后来的“誓”,虽可以用于其他信约行为,但必须使用于信约这一行为性质,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行为的实现途径和手段。 “命”当由“令”演变而来,原本指不可违背的上帝的旨意。甲骨文常有“帝令……”的卜辞。周人将不可违背的天意称之为“天命”,故周人将天子对臣下下达某些任务,或者任命某种职位等这种性质的行为都称之为“命”,取其意愿不可违背之意。《尚书》载有商代《肆命》和《说命》三篇。《肆命》已佚,《说命》见于晚出古文。《书序》说:“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三篇。”内容为高宗对傅说的任命和对群臣的告诫,与西周铜器铭文中的那些策命之铭相同,故“命”这种文体性质也由行为性质确立。 “谟”,唯见于《尚书》,今古文《尚书》都载有《皋陶谟》。《史记·夏本纪》说:“皋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与语帝前,皋陶述其谋曰……”说皋陶与舜、禹语而述其谋,亦意有“谟”即“谋”之意。《说文解字》称谟“议谋也”。《左传》载穆叔曰:“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咨难为谋。”⑥据穆叔所说,咨、询、度、诹、谋,皆为一种咨询性质的行为。“谟”当为记载君臣或上下级商讨某些政事的文体。不仅《尚书》的这些文体,颂、箴、祝、传、赋、论、诅等等原本也是生成于某种性质的行为。颂,产生于祭祀天地和宗庙祭祀这一性质的行为,如刘勰说:“颂主告神……斯乃宗庙之正歌,非宴飨之常咏也。”⑦箴,生成于臣下对君主规劝性质的行为,如韦昭注《国语·周语上》曰:“箴,箴刺王阙,以正得失也。”祝,生成于祝史向鬼神的祈祷行为,如《周礼》:“大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贞。”⑧“诅祝掌盟、诅、类、造、攻、说、禬、禜之祝号,作盟诅之载辞,以叙国之信用,以质邦国之剂信。”(《周礼注疏》卷二六《诅祝》,《十三经注疏》,第816页)赋,产生于祭祀仪式上祭祀主持人一一列举向神灵贡献祭祀物品和各地参加祭祀的人员,表示对神灵的恭敬。诗则产生于国家中央政治机构之“寺”的礼乐政治性质的行为。这些文体在其原生形态,都是行为过程中的文字单元,依于某种性质行为而产生。 “语”,也是由一种一定性质的行为演变而来。先秦言、语有很大区别。《周礼·大司乐》载:“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郑注云:“发端曰言,答述曰语。”孔疏谓:“许氏《说文》云:直言曰论,答难曰语。论者,语中之别,与言不同。故郑注《杂记》云:言,言己事,为人说为语。”(《周礼注疏》卷二二《杂记》,《十三经注疏》,第787页)《诗经·公刘》:“于时言言,于时语语。”孔疏:“直言曰言,谓一人自言。答难曰语,谓二人相对对文。”(《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第542页)知“语”原本是与他人进行论难的性质的行为。“传”和“辞”一样,也是一定性质行为的产物。“传”原本是一种对于典籍进行解释的性质的行为,如《左传》《穀梁传》《公羊传》都是对孔子《春秋》进行注释。《周易》的卦辞、爻辞,分别为卦象、爻象的解释文字。 可见,先秦的文体都因一定性质的行为发生,并用于一定性质的行为。后来的中国古代文体学著作对这些文体功用的分析,也说明在古代人们的观念中,行为的性质也大多与一定的文体对应。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将收录的文章分为十三类:其中除辞赋以形式来区分文体外,其余通过他对文体特点的说明,也可以看出他将行为的性质当作了区分文体、文类的标准。 二 从一级文体到二、三级文体 古代文体的发展,有一个种类由简到繁,即一级文体向二、三级文体分化的过程,这也是中国“文”学的功能、内容题材、言说方式方法、审美特征的发展历程。一级文体包含有原始文体和文类的双重涵义。所谓原始文体,是指那些最早产生,后来分化出不同性质行为的文体。因那些分化出来的文体都可归入原始文体一类,故原始文体具有文体分类的性质和作用,使一级文体具有文类的意义。二、三级文体即由原始文体分化出来的文体。如诗为原始文体,后分化出颂、雅、风、乐府、五言、七言等等。这诗即一级文体,颂、雅、风、乐府、五言、七言为二级文体。三级文体则是由二级文体分化出来的文体。 汉代以来,文体的数量越来越多。《汉书》《后汉书》以及刘熙《释名》所载文体已有五十多种。刘勰的《文心雕龙》论述的文体虽只有三十四类,而实际涉及的文体却将近九十种。明徐师曾作《文体明辨》,文体已达一百二十七种。清吴曾祺的《涵芬楼古今文钞》不收诗歌,将文章分为十三类,二百零二种文体。清张相的《古今文综》将文体分为四百多种。分析这些中国文体的名称,有助于认识一级文体向二、三级文体发展的内在规律。 《涵芬楼古今文钞》将文体分为十三类,在各类下面再分具体的文体。如论辩类下有:论、设论、续论、广论、驳、难、辨、义、说、策、程文、解、释、考、原、对问、书、喻、言、语、旨、诀。传状类下有:传、家传、小传、别传、外传、补传、行状、合状、述、事略、世家、实录。辞赋类下分:赋、辞、骚、操、七、连珠、偈。《涵芬楼古今文钞》讨论的不是中国古代文体的发展,很难从中看出文体的发展方式。但明代黄佐作《六艺流别》、谭浚作《言文》,效法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所提出的五经为文体本源的观念,对文体的发展进行了梳理。黄佐《六艺流别》认为文体都从六艺发展而来,如认为《诗》艺产生谣、歌和诗,由谣、歌分化出二级文体讴、诵、谚、语、咏、吟、叹、怨;诗分化出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和骚、赋(律赋)、词、颂、赞以及律诗、排律、绝等。《书》艺产生典、谟。典分化出命训、命、诰等。命训又分化出制、诏、问、答令、律等,命细化为册、敕、诫、教,诰则分化出三级文体谕、赐书(符)、书、告、判、遗命。谟分为训誓、誓、训。训誓下又有议、疏、状、表(章)、启、上书、封事、弹劾、启事、奏记(白事)等。誓又分化为盟、檄、移、露布、让、责、券、约等。训又细化为对、策、谏、规、讽、喻、发、势、设论、连珠等。谭浚的《言文》以《易》《书》《诗》《礼》《春秋》为一级文体。由《易》而产生了序、论、说、词,序又分化出原、引、题、跋;论又细化为辨、议、评、断、判,说又分化出难、言、语、问、对,词又细化出繇、集、略、篇、章。他如诗细化为赞、颂、赋、歌,赞细化出铭、箴、碑、碣,颂细化出诵、《封禅》《美新》《典引》,由赋发展出七词、客词、连珠、四六,由歌发展出谐、隐、谜、谚。 古代文体,确实存在着如褚斌杰所说的多种文体区分的标准:“文体(文学体裁)的构成本具有外在的形式和内容的规定性双重因素。它既具有语言、结构方面的特征,同时也有内容和题材方面的因素。”“我国的诗、赋作品,通常采取从语言节奏、韵律的角度分类,如四言、五言、七言、杂言、古诗、律诗、古赋、骈赋、律赋、文赋等,也可以从内容上着眼,如山水诗、咏史诗、咏怀诗、京都赋、江海赋等等。”⑨从《涵芬楼古今文钞》《六艺流别》《言文》对中国古代的文体进行分类涉及的文体看,褚斌杰说得没错。《涵芬楼古今文钞》没有涉及诗歌;其中的设论、续论、广论是以论述的方法进行区分,七、连珠等是以语言形式区分文体,序、跋等是以放置于文章的开头或结尾来区分文体。黄佐在诗区分二级文体时,采用了以语言形式的区分标准;如诗分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律诗、排律、绝句等,赋有律赋之体。确实,魏晋以来文人对语言文采之美的追求,导致了以语言形式来对诗词和赋进行二、三级文体区分的现象。但是,这种以语言来进行文体区分,只限于诗、赋,而且只限于二、三级文体。 黄佐和谭浚对文体及其源流的区分是不科学的。但他们的文体发展观念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黄佐将文体的产生归之于六艺而不是“六经”,充分地表现了文体源于一定性质行为的观念。二是两人都注意到了中国古代文体发展为逐级分化这一发展方式,即由产生一级文体的性质的行为细化为二、三级文体。黄佐在区分诗的二级文体时,以语言形式作为区分标准;但《言文》和《涵芬楼古今文钞》《六艺流别》一样,在散文的发展方面,都肯定着二、三级文体为一级文体所体现的一定性质的行为细化这一规律。如臣子向君主陈说政事这一行为所使用的文体,先秦名为“上书”或“书”,秦时名之为“奏”,而“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细分为疏、表、议、章、启等。表、议、章、奏,虽都用于向帝王陈说政事,但其功能却有着一定的差异,各用于不同的性质的行为。“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文心雕龙注》,第406页)根据行为性质的不同,这些文体又进一步细化,如表又分为贺表、谢表、降表、遗表。记、志为一级文体,因记、志的外延过于宽泛,一切言行的记载都可谓之为记、志,不便明确具体的行为性质,故记、志有了语、纪、传、说、世系等文体的细化。语主要用于记载言论,如《国语》《论语》。纪专门记载帝王的行事,如各史中的本纪。传则专门用于记载上至卿相下至百姓的事迹,如《史记》中的列传。说即对各种事情、包括街谈巷议进行记述,如《韩非子·说林》、刘向《说苑》。世系即对诸侯及著名重要官员一姓的世代传承进行记述,如《国语上》说“教之世”,韦昭注谓:“世,谓先王之世系也。”传后来分化为家传、内传、别传、外传、补传等。这些记载人物的文体虽都名传,但就行为性质而言,还是略有区别。家传,主要叙述家人事迹以传示其子孙的传记,如《孔子家传》。内传则多记载人物的逸闻轶事,如《汉武内传》。外传,是正史已有记载而别为作传,另记其遗闻轶事,如《赵飞燕外传》。至于小说,后有笔记、话本或通俗、文言小说的区分,但这其中多是当今的研究分类,古人似乎并不执着于这些概念。可见,在文体发展过程中,以行为的性质确定二、三级文体的区分,依然是主流。 中国文体发展的这一规律产生,由中国“文”学为社会生活自身这一本质而决定。中国“文”学为人们日常社会生活行为过程中的“文字单元”,众多的生活行为主体也就是“文”学的创作主体;而行为的性质是决定文章的分体的标准,因而,当人们的生活行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得日益丰富,行为性质日益多样化时,原有文体也就不能满足社会生活新的性质的行为表达的需要。这种矛盾的核心,实际上是原有文体功能不能适应社会生活需求的问题。于是,有了拓展文体功能的必要。从中国“文”学的历史看,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一是创造新的文体,二是“文体漂移”。 社会生活每一性质的行为,不可能都有一种相应的语言形式。故新文体的创造,也有以语言形式来表示新文体的情况,如五绝、七律等。但以语言形式区分文体,很难确立文体的具体功能。在先秦乃至汉代,有些不同的文体可以具有同一语言形式是常见的现象,如诗、箴、赞、冠辞、碑文等等,大都为四言韵文。所以,新文体的创造主要一是文体细化,以文体的细化来实现文体功能的细化;二为原有不同功能的文体相互交融,产生一种新的文体,如六朝的佛家转读和史传相结合产生的变文、话本,以史传和志怪笔记相融合而产生出的“传奇”。 “文体漂移”,是将原有表达某一种性质行为的文体移到其他性质的行为表达中。它不同于“文体融合”。“文体融合”是指不同的文体在功能及语言形式方面的交互影响,而“文体漂移”是改变原有文体用于某一行为性质的特有功能,用于新的性质的行为,主要表现为文体功能的拓展。如祭祀天地、祖先的颂,到屈原用于歌颂橘的品质。诗原本用于政治,歌功颂德,到魏晋南北朝用于抒写个人情感、用于说理、交际、纪行,再到杜甫用于评诗、写作家信等等。这种漂移即表示着诗的文体功能新的拓展。“文体漂移”,在诗、赋、戏曲、小说、散文的创作中都存在,尤以诗、赋更为突出。赋如由荀子的《赋篇》用于政治讽谏,到宋玉的《高唐赋》等用于娱乐君主,再到贾谊的用于抒写个人的不遇,到汉武帝时众多的赋家用于歌颂帝王的统治等。诗、赋的这一状况,是因为诗、赋在一级文体形成之时,行为的性质不是非常明确,也没有严格的限定,行为的主体存在着身份的多元性,有帝王、官员,也有百姓,如《诗经》中的诗。因而,这一类文体,在其创作的过程中,可以在较大程度上突破一级文体形成之时的行为性质的限制,用于现实生活不同性质的行为表达。但是,完全实用的文体,尤其是应用于行政的文体,却是比较严格地按行为的性质被使用而不能“漂移”的。 这其中的关键原因,是最早的实用文体源于中国古代的礼乐政治形态。礼乐制度是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这一制度不仅规定不同的身份等级具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宗教祭祀权力,而且就是服饰及其色彩图案、所用器皿的大小形制、乐的使用等各个方面,不同身份等级都有着极为严格的区别。这种等级观念表现在不同性质的行为方面,如《礼记·曲礼下》曰:“诸侯未及期相见,曰遇。相见于郤地,曰会。诸侯使大夫问于诸侯,曰聘。约信,曰誓。莅牲,曰盟。”(《十三经注疏》,第1266页)不同性质的行为,都有着不同的名称。这不同的名称,都是表示等级关系的符号,名称改变,即意味着等级关系的改变。诸侯相见曰“会同”,若将大夫相见也称之为“会同”,便违反了礼制。 先秦的文体是一定的礼乐政治行为的产物。这些文体不仅表示一定礼乐行为性质,也表示着特定的主体和行为对象的身份及其构成的行为关系。如果用于某一性质行为的文体用于其他性质的行为,则表示着特定的主体身份和行为对象的身份及其构成的行为关系的改变。故作为礼乐政治行为过程中的“文字单元”文本的文体,自然不能随意运用,如诰、命、策专门用于帝王向臣民进行政治、道德言说,奏、疏、书用于官吏向君主的言说。这些文体若是互用,文体体现的那种等级关系便会消解。礼乐制度所规定的严格的等级关系贯穿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这在导致中国古代君臣和官民之间的等级关系的稳定性的同时,自然会导致用于礼乐和行政的实用文体功用的“专一”性,文体发展更多的是以文体分化的形式进行。 此外,中国“文”学经验性本质所确立的以行为性质区分文体的原则,也对其采用语言形式为标准产生了影响。中国早期文体的生成过程中,文体的语言形式都没有太多的区别。诗一般为四言,但《尚书》如《微子之命》,诸子散文如《荀子·劝学》中的一些段落都是四言;《逸周书》的《常训》《程典》《小明武》《武称解》等全篇基本都是四言,而且大多押韵。诗一般押韵,但《诗经》的颂,如《清庙》《昊天有成命》《时迈》《噫嘻》《武》《酌》《桓》《般》都全章无韵,如《周颂》中的《我将》《臣工》《访落》《小毖》《良耜》,《豳风》中的《鸱鸮》,《大雅》中的《思齐》《常武》《召昊》等亦如此。两周的铜器铭文却有很多是韵文,故宋代陈骙说:“六经之道,既曰同归;六经之文,容无异体。故《易》文似《诗》,《诗》文似《书》,《书》文似礼。”⑩ 中国早期文体的生成过程中,文体之间缺少语言结构形式的差别性,说明以行为性质区分文体时,人们对于文体的语言形式不曾给予关注。这一原则的确立,也使得后来各种文体在发展过程中,除诗、词和律赋在语言形式上有一定的区分外,其他的各种文体在语言形式上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如赋既有骚体,也有散体和骈体,有些还杂有诗体,如萧纲《晚春赋》全用六言,庾信《春赋》的前一段和后一段都为五、七言的句式。书信有的采用骈文,有的则纯采用四言,如简文帝《与慧琰法师书》。箴和汉代的碑文多用四言,韩愈的碑文则散句与四言相兼,如《平淮西碑》;有的则纯用散句,如《柳州罗池庙碑》。古代的小说,有些则在叙事中杂用诗、词,形成一种多文体交叉的文体。 同时,中国“文”学行为都是社会生活行为,实用的价值取向相对于审美的价值取向占有绝对优势。即便是律诗、词,也在实际的生活过程中承担着实用的功能,如那些交际类诗歌中的律诗和词,虽然必须遵循语言形式的原则,但都没有摆脱它首先作为每一性质行为过程中文字单元的实用功能的制约,美的形式都是服务于用的。文学创作,一定的语言形式应该是为实现一定的目的和表现一定的内容服务的。从中国“文”学的发展看,虽然到六朝出现了骈文,唐代将声韵引入了文体的区分,出现了律诗、绝句,此后又出现了词,但自南朝注重语言形式以来,中国历代都出现过诗文革新运动,反对散文的骈化。诗歌则如白居易《新乐府序》,提倡“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主张“其体顺而肆”。可见,“文”学的实用与对语言形式的追求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虽然律诗、绝句、词也能用于实用,但正如李冶所说:“盖古人因事为文,不拘声病,而专以意为主。”(11)专注语言形式,对事与意都有一定的限制,与以用为主的中国“文”学整体价值取向是相违背的。可见中国“文”学的行为经验本质,决定了中国确立文体时对语言形式的忽视。 三 行为性质与中国文体体素 中国古代文体的行为本质,对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文体观念,即建立在这一观念的基础之上。语言形式类文体是以语言的结构形式包括音韵、句式等来确定文体的性质,故凡符合某一语言结构形式的文字便可以视之为某种文体。只要满足文体一定的语言结构形式这一关键的要素,某一文体的性质便可以得到确认。语言的结构形式本身就已满足了文体的内在要求,成为了确定文体的唯一条件,故以语言形式区分文体,语言形式便赋予了文体自足性。换言之,语言的结构形式即意味着文体的确立,便无须通过文本的内容、风格便可认定某一文本的文体性质。 相对于以语言形式区分文体,中国古代文体的体素则要复杂得多。如吴承学所说,中国文体学的“体”,“兼有作品的具体形式与抽象本体之意,是形而下与形而上的有机结合;既有体裁或文体类别之义,又有体性、体貌之义,既可指具体的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又可指文章与文学之本体”(12)。罗根泽认为,中国所谓的文体,一是指体派之体,如元和体、西昆体之类,一是指体类之体,如诗体、赋体、序体等,既包括体裁,也指风格(13)。童庆炳以为,中国古代的文体之“体”,其涵义最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体裁的规范”、“语体的创造”和“风格的追求”(14)。学者对中国古代文体确立的要素的认识虽稍有不同,但他们同时都注意到了中国古代所谓文体之体素:体裁、内容、语言形式、风格等。 中国古代有“文各有体”的观念。这一观念,虽到宋代才明确提出,但汉代就已形成。后汉蔡邕的《独断》将章、奏、表、驳议四种文体加以区分,说明它们功能、书写规范的差异: 章者,需头,称稽首,上书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云云。奏者,亦需头,其京师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闻,其中有所请,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台,公卿校尉送谒者台也。表者,不需头,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诚惶诚恐、稽首顿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日某官臣某甲上,文多用编两行,文少以五行,诣尚书通者也。(15)章、奏、表虽然都用于臣下对君主的言说,但所用场合不同,其功能也不相同,故章、奏、表的内容及写作程式都不相同。蔡邕这一段话,表明他已有“文各有体”的观念,故有意识去对章、奏、表这些文体进行分辨。而这对文体的区分及强调,正在于古人将文体也视为文章的体裁。因为文体体裁不同,其功能、内容、语言及其形式、风格有不同,在写作中不符合文体体裁的规范,会被认为不识文体。所以,文人强调写作应先“辨体”,如胡应麟说:“文章自有体裁,凡为某体,务须寻其本色,庶几当行。”(16)明陈洪谟说“文莫先于辩体”(17)。虽然像诗一类文体能无所不写,但众多的文体,尤其是那些实用性文体,大都有着一定的内容限定。一种文体具有的特定功能,决定了它抒写的内容,形成文体与内容的对应。《梁书》载简文帝作文“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18)。所谓宫体,不仅是在形式上追求词藻靡丽,更主要是内容“轻艳”。明贺复徵说:“咏宫体之辞,则志不出于奁匣。”(19)故中国古代的文体之“体”包含内容的涵义。 中国古代的文体观虽非形式文体观,但文以语言为表现形式,故中国古代说到文体,自然也离不开语言形式这一元素。萧子显说: 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20)萧子显所谓当时的文章“三体”,是针对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之作而言,既关涉内容、风格,也关涉语言的形式及表达方式。“虽存巧绮,终致迂回”“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崎岖牵引,直为偶说”“雕藻淫艳”,都是就语言形式及表达方式对文体所作的阐述。刘勰说:“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为乏,辞反正为奇。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耳。”(《文心雕龙注》,第531页)这是批评当时一些文人以改变文句结构以形成新巧之“体”的方法。 每一文体的内容、语言形式及表现方式所呈现的整体趋向,形成文学作品的风格,故古代论文体,风格也是重要内容之一。即便是同一体裁的作品,因主体不同而有着不同的风格,如李白的诗与杜甫的诗。那些实用性文体,为限于一定场所的言说,功能、言说主体的身份和言说对象的身份都基本相同,如章、奏、表,故不同主体的这类作品,不仅内容差异不大,所用语言及表现方式也相去不远,如陆机《文赋》谓: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21)陆机的这段话论文体,便是将语言与风格融为一体,来言说不同文体的不同风格要求。 众多的研究者讨论古代所谓文体之“体”时,大多不注重文体功能。其实,古人强调作文要先辨体,即主要是基于文体用于不同性质的行为,承担着不同的功能。《礼记·祭统》说:“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显扬先祖,所以崇孝也。”(《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606页)论铭之体,首先谈到的就是其功能。蔡邕的《独断》谈章、奏、表,也将文体的功能放在首要位置。陆机论“体”,虽少涉及功能,但到刘勰,论述各种文体,也是首先论其功能,如《诏策》:“誓以训戎,诰以敷政。”(《文心雕龙注》,第358页)《议对》:“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献说也。”(《文心雕龙注》,第439页)故说古代文体是一个融体裁、功能、内容题材、语言及表达方式、风格于一体的综合概念。西方将语言形式看成是文体区分的标准,是因为西方将文学看作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否认文学为社会生活本身。中国古代人们普遍将“文”学视为现实生活的产物,文体意识建立在“文”学为现实生活这一观念的基础上,故中国才产生古代视文体为体裁、功能、内容题材、语言及表达方式、风格于一体的文体意识。这可以从两方面理解: (一)文体与文本共生共存。每一文体在其产生之后,文体的体性就已经基本确立;因而,每种文体都有它的独立性,似乎可以不依赖文本而单独存在。正因如此,文体的研究往往大多脱离文本。这样的一种研究方法,使文体学从“文”学中独立出来,但却割断了文体与文本内在的血缘关系,阻碍着我们对文体本质的认识。从众多的中国一级文体的原生状态来看,文体与文本原本二位一体,同为一个行为过程中的“文字单元”。我们以荀子的《赋篇》为赋的原生文体,那么,《赋篇》就已同时具有赋体和作为赋体的文本的双重性质。作为赋这种文体之“体”和作为赋体的文本都同是荀子对君主进行讽喻行为过程中的“文字单元”,文本与文体是合而为一的。它既体现着赋这一文体的体性,也表现着《赋篇》这一文本的特色。而且,赋这一文体的体性因《赋篇》这一文本的特征而获得。所以说,文本是一定文体的文本,文体是一定文本的文体,文体以一定的文本为表现形式。离开文本,文体的体性特征就无法表现。文体与文本这种关系,形成了文本和文体要素的同构,使文体以文本的要素为要素,不然,文体的性质和功能就无从得以表现。如杂剧这一文体的特征,即通过诸如关汉卿《窦娥冤》、王实甫《西厢记》等具体的杂剧文本得以表现,而《窦娥冤》《西厢记》的文本也表现为杂剧这一文体的文本。《窦娥冤》《西厢记》的体裁、内容题材(包括故事情节、结构等)、语言形式(包括唱、白结构)、表现方法等,也必然表现为杂剧这一文体的要素。因而,文体在生成之后虽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意义只是在理论的阐述时才得以存在,而当它一旦用之于创作时,虽然主体根据行为的需要先决定采用某种文体,然后进行文本的写作,但文体依然以文本为表现形式,文体与文本融为一体,互不可分。故文体与文本是共生的。 (二)以行为性质确定文体的区分标准导致文体、文本同构。以语言的结构形式来区分文体,赋予了语言结构形式以本体的地位。语言结构形式的这一地位,使得在区分文体时,唯一注重的只是语言的结构形式,而毋须联系功能、内容题材、表达方式、风格等文本要素。从这一视角去考察一个文本的文体属性,也就毋须注意它的具体功能、内容题材、表达方式、风格;如一首七绝,我们只要看到它为四句、每句七字、且符合平仄要求,就可确定它为七绝。而内容、题材、表达方式、风格等,是我们进行文本分析的重要元素。以语言的结构形式来区分文体,可以忽略这些文本的要素。这样做虽然也要关注文本,但文体与文本的结构要素,并不同一。然而,以行为性质来区分文体则不同,它赋予了行为性质在文体生成过程中的本体意义。每一不同行为性质的行为都有着一定的目的,性质与目的规定着行为的场合、主体的当下身份、言说对象的身份。主体必须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是什么身份说什么话,是什么对象说什么话。如笔者在《先秦文学发生研究》中谈到柳永的几首著名的词作:《望海潮》“江南形胜”和《雨霖铃》“寒蝉凄切”、《醉蓬莱》“渐亭皋叶下”。据《本事词》说,《望海潮》为柳永欲见孙相不得通,作此词与歌妓,请她在孙相听曲时歌唱,告知自己欲见孙相,知《望海潮》本是一张投刺名牌,作者特定的身份和特定的言说对象决定了这首词的创作。词的特定言说场所是孙相的衙门,若不是衙门门禁甚严,柳永不是一个平民的身份,用不着词就可以见到孙相;如果言说的对象不是镇守杭州的孙相,柳永也不会极力去夸写杭州的繁华富丽,也不会有“千骑拥高牙”后面几句的言说。《雨霖铃》“寒蝉凄切”是他离开汴京,前往浙江时“留别所欢”而作。因其言说场所为别离之地,作者此时的身份是情人,言说的对象也是情人,所以才有不同于《望海潮》的无限凄凉的别情抒写,才有了“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诉说,有了“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凄美景致的描写。而《醉蓬莱》“渐亭皋叶下”的限定言说时空与前两首都不同。据《古今词话》上卷引《太平乐府》曰:柳永“后以登第冀进用,适奏老人星现,左右令永作《醉蓬莱》以献”。知《醉蓬莱》“渐亭皋叶下”作于宫廷之中,言说对象为宋仁宗,作者的身份为臣子,是君臣关系的言说。故全词不乏宋初宫廷诗华艳的谀美:“华阙中天,锁葱佳气。嫩菊黄深,拒霜红浅,近宝阶香砌。玉宇无尘,金风有露,碧天如水。正值升平,万机多暇,夜色澄鲜,漏声迢递。南极星中,有老人呈瑞。”全然不同于《望海潮》和《雨霖铃》。可见,在行为过程中,行为的性质始终规定着行为过程中的“文字单元”即用以达到行为目的的文本的言说内容、语言和言说方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风格。行为的性质与文本的每一要素都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在每一行为过程中,文本与文体是共生共存的,所以,文本的这些要素也就自然而然成为确定文体的要素,形成文本要素与文体要素的同一性。因而,文体和文本的结构要素的同构,否定着以语言形式作为区分文体的唯一标准,而将内容、题材、表达方式、风格等都纳入了文体区分的标准之中。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就是中国文体的发展史。古代对文体的行为性质的本质的体认,将“文”学的文体与文本融为一体,使文体的要素与文学文本的要素形成对应的同一结构,也使得文体、文本的发展与主体的行为产生密切关联。因而,文本某一要素的改变导致文体的体素产生相应的改变,也使得主体行为性质的转换必然产生“文体漂移”,进而导致文体功能的拓展。同时,由于每一性质的行为都是主体以某种身份实施的行为,故也使得主体的身份在文体的演化中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 ②班固《汉书》卷三○《艺文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二十五史》本,第1册,第168页。 ③赵辉《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内在机制》,《文学评论》2013年第6期。 ④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页。 ⑤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6页。 ⑥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13页。 ⑦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57页。 ⑧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五《大祝》,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08页。 ⑨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8页。 ⑩陈骙《文则》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80册,第685页。 (11)李冶《敬斋古今黈》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6册,第414页。 (12)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13)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页。 (14)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0页。 (15)蔡邕《独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0册,第78-79页。 (16)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1页。 (17)徐师曾著,罗根泽点校《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80页。 (18)姚思廉《梁书》卷四《简文帝纪》,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册,第109页。 (19)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卷二六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05册,第285页。 (20)萧子显《南齐书》卷五二《文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2册,第908页。 (21)严可均《全晋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0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