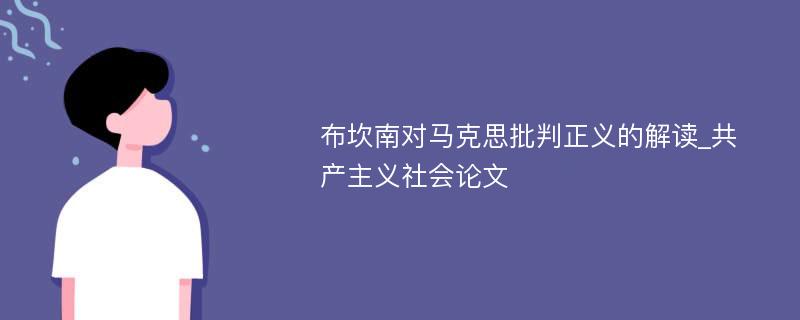
艾伦#183;布坎南对马克思批判正义的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艾伦论文,正义论文,布坎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7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660(2013)01-0016-10
在关于“马克思与正义”的关系的论争上,艾伦·伍德(Allen Wood)一方与齐雅德·胡萨米(Ziyad Husami)、南希·霍尔斯特姆(Nancy Holmstrom)一方有一个重要争论:马克思是否认为资本主义为不正义的?对于这一论题,伍德的观点是马克思不仅没有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甚至是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正义的。伍德的这一具有挑战性甚至不乏煽动性的观点自然引来了各方的批驳,在早期诸多批驳中,胡萨米、霍尔斯特姆一方称得上是“针锋相对”的一方,这一方认为,马克思以资本主义之后的分配正义原则(或无产阶级的正义观)批判资本主义为不正义的,但胡萨米、霍尔斯特姆这一方的观点却被伍德等人指认为缺乏文本依据。双方的争论似乎都各有其理,但又都难以令人信服,由此,如何基于文本事实而又令人信服地提出一种能够统摄双方的诠释方式,就成了诺曼·杰拉斯(Norman Geras)、凯·尼尔森(Kai Nielsen)和艾伦·布坎南(Allen Buchanan)的一个努力。而相较于杰拉斯和尼尔森来说,布坎南所做的工作更为成功,他不仅融通、综合了双方的见解,而且极富解释力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以至阿兰·桑德洛(Alan M.Shandro)指出:“在艾伦·布坎南(Allen E.Buchanan)的《马克思与正义——对自由主义的激进批判》(Marx and Justice)一书中,我们能够看到,他关于马克思的反法权(anti-juridical)的解释是一种最令人信服、最为透彻的说明”。①R.G.佩弗(R.G.Peffer)则把布坎南对马克思批判正义的诠释视为他一个无法绕过的学术成就。②甚至观点为布坎南所批评的学者艾伦·伍德也认为艾伦·布坎南的《马克思与正义——对自由主义的激进批判》称得上是第一本致力于将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与马克思对待道德的理论以可理解的方式结合起来的著作。③正是基于布坎南在诠释马克思批判正义上的学术成就,本文试图就他这一思想做一述评。
一、马克思不是诉诸某种外在的正义观念批判资本主义
在马克思是否以正义、权利等法权观念批判资本主义的问题上,艾伦·布坎南部分地认可了伍德、米勒等人的一种观点:马克思不是诉诸某种外在的正义观念批判资本主义。即马克思并不存在霍尔斯特姆和胡萨米等人所指认的,以一种资本主义之后的分配正义原则(或无产阶级的正义观)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
在布坎南看来,那种认为马克思曾以一种资本主义之后的分配正义原则(或无产阶级的正义观)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不仅缺乏文本事实的支撑,而且从马克思的理论自身来看也是难以得到有力辩护的。他指出,“霍尔斯特姆与其他学者认为,至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某些外在批判是从一种共产主义正义观——一种建立在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按需分配的基础上的正义观——的视角出发的。……至少就分配正义而言,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而且,看不到这种观点的错误也就看不到马克思对分配正义批判的激进所在”。④
布坎南指出,不仅我们无法找到支撑马克思以某种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正义原则(或无产阶级的正义观)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本,而且还碰到相反的文本事实:“马克思不仅嘲笑了那些谈论社会主义的正义的资本主义批判者,而且他自己也似乎有意地避免使用正义和权利的语词。”⑤
当然,理解马克思为何不以某种正义原则批判资本主义,关键还不在于文本事实上,而在于把握马克思理论的内在理路,一旦我们把握到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的彻底性,我们就不会以为马克思是以某种分配正义原则或正义观念去批判资本主义的分配不正义。
首先,就分配来看,马克思不断强调,任何社会的分配都是派生的现象:它的一般特性是由该社会的基本生产过程的特性所决定。“既然从总体上理解一个社会的关键是分析它基本的生产过程,那批判一个社会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揭示那些过程的缺陷。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试图揭示的。现在,正如资本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于它的基本生产过程,因此,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共产主义的根本优越性将存在于其独特的生产过程中,而不是存在于分配的安排上。为此,假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是从共产主义的分配正义观的视角来展开的,就将是奇怪的。”⑥
其次,承接伍德的观点,布坎南认为更具有决定性的反对理由是霍尔斯特姆和胡萨米等人的这种观点与马克思认为正义是意识形态的观点是相悖的。辩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依据共产主义的分配正义标准是无法与马克思将谈论分配正义和平等权利斥为“过时的语言垃圾”,以及社会主义者应该停止“意识形态的胡说”的成见相一致的。⑦“马克思相信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休谟和罗尔斯所说的(分配)正义环境业已消失,或者已经弱到在社会生活中不再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大致上说,分配正义的环境是那些稀缺的条件——且冲突是建立在稀有物品的争夺之上——使得运用分配正义的原则成为必要。马克思坚信,新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将减少稀缺和冲突的问题,以致分配正义原则不再成为必要。”⑧
最后,布坎南认为,不论是塔克、伍德,还是霍尔斯特姆、胡萨米、柯亨等人,他们在讨论“马克思和正义”的关系上,都过多地停留在分配正义的问题上,尚没有探测到马克思批判的理论深度和彻底性。在他看来,马克思对正义和权利的批判并不仅限于分配正义,而是直指“正义一般”。他的批判不仅包括分配性的权利,而且涵盖非分配性的权利;不仅指向资产阶级的正义和权利观念,而且指向权利和正义观念本身。⑨因此,正如对于意识形态的彻底批判,需要立足于一个非意识形态的阿基米德点一样,⑩马克思针对分配正义、正义、权利等法权观的彻底批判也需要有一个非法权的外在批判,而这一批判就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但在“马克思与正义”的这场争论中,这一根本的维度却没有得到充分地彰显。(11)
不过,布坎南虽然不认可马克思以某种资本主义之后的分配正义原则(或无产阶级的正义观)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但他却承认马克思存在着以共产主义为参照去批判资本主义。他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控诉是暗含‘比较的’,并且比较的标准是外在于资本主义的:仅有通过引入共产主义作为参照,资本主义的饥饿、死亡、耗竭和孤独才被看为可避免的,也才因之是非理性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点是在这个意义上为马克思提供了基本的或根本的评价视角:即如果不引入共产主义的生活,马克思的批判就失去了激进特征。正因为如此,那种断言马克思的主要兴趣在于批判资本主义而不在于提出一个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的论断就是难以令人置信”。(12)只不过布坎南不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共产主义是正义社会。(13)而且一旦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共产主义理解为正义社会,就会遮蔽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激进品格和批判的深度。因为,一旦我们理解了马克思分析的深度,我们就能够意识到,对于他来讲,也许对资本主义——和所有的阶级社会——最致命的控诉之一就是它们的生产方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以致使分配正义的原则成为必要。对马克思来说,对分配正义原则的这种特别的需要正是构成社会核心的生产过程存在缺陷的决定性症状。从正义讨论的要点来看,共产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并不在于它最终侥幸而又有效地实施了正确的分配正义原则,从而解决了分配正义的问题,而在于它使分配正义的整个争论成为多余。(14)他认为他的解释的优点是不仅吸收了霍尔斯特姆对塔克和伍德的明智的批判,而且说明了霍尔斯特姆的解释没能解释的三点:(1)马克思拒绝指认共产主义社会为正义社会;(2)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必将消除分配正义的环境(其言外之意是共产主义不需要正义原则);(3)马克思把关于正义和权利的谈论批为“过时的语言垃圾”和“意识形态的胡说”。(15)
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不正义的,但他却避免这样说
马克思既不以某种外在的正义观念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也避免使用法权话语批判资本主义,似乎有可能得出一种伍德式的结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无所谓正义或不正义,甚或资本主义剥削是正义的。(16)但布坎南却通过诠释他所认为的马克思的内在批判来避免得出这一伍德式的结论,其立论是:马克思并没有,像伍德等人所断言的,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正义的,而是相反,但马克思却避免指认资本主义剥削是不正义的。
在布坎南看来,像罗伯特·塔克、艾伦·伍德等人之所以会认为“马克思并没有斥责资本主义是侵犯了某一分配性正义准则的社会制度”,(17)断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合乎正义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他认为伍德等人在这一观点的主要失误就在于他们只是看到马克思有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外在批判,而没有看到马克思有基于法权的内在批判。
布坎南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既有内在批判,又有外在批判。内在批判是指以某一社会所固有的法权观念批判该社会本身,(18)如: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正义概念和权利概念反过来批判资本主义自身”,(19)即“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而外在批判,则有两类:基于某一外在的法权的外在批判;基于某一非法权观念(如历史唯物主义)的外在批判。(20)“在这两类中,批判的视角都是外在于处在批判之下的正义观念”,(21)即外在于该社会所固有的法权观念。在布坎南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只有基于法权的内在批判和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外在批判,而且在这两种批判中,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具有最为根本性的地位,(22)而“内在批判仅仅扮演次要的、破坏性的角色,只是用来驳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试图证明资本主义是正义的那些论辩”。(23)但是,内在批判尽管仅具有次要的地位,却不能忽视其作用和意义,他认为,伍德的失误,就在于他未能看到马克思的内在批判。(24)他把伍德的论证归结为如下两点:
(1)依据马克思,正义标准仅有运用在它赖以产生和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上才是富有意义的(每一生产模式都有它不同的正义标准)。
(2)依据马克思,工人和资本家的工资关系是正义的,这是依据适用于它的唯一的正义标准(即等价交换的标准)而得出的。(25)
对于第一点,布坎南认为伍德是设定了生产方式和正义标准之间的先定的和谐关系,(26)即伍德在《马克思论权利与正义——对胡萨米的回复》中所表述的,依据马克思的“正义标准应用于某个交易或制度的唯一合理基础,就是这种标准与该交易或制度所赖以建立的生产方式之间的相符合”的观点。(27)他认为,伍德这种关于正义与生产方式之间的先定和谐的观点无疑排除了任何内在批判的可能性,(28)没有充分地意识到,“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揭露那些在试图表明资本主义是正义上有着重要作用的虚假的经验信仰。资本主义的正义概念,像其它法权概念一样,都是预设了某种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实的归纳”。(29)
对于第二点,伍德曾援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一段话作为佐证:“这种情形”,“对于买者(即购买劳动力者)是一幸运,但对于卖者来说,一点也不是不公平”。(30)伍德的解释是,在工人和资本家的交易过程中,尽管资本家通过交易获取到了能够为他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力,但剩余价值却不是通过不平等交易的方式获得,而是遵循着平等交易,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尽管雇佣劳动属于剥削,且剥削是属于奴役的一种形式,但它却不是不正义的”。(31)
布坎南认为,对于伍德的这一观点,尽管可以像南希·霍尔斯特姆和胡萨米等人那样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伍德对马克思文本的理解存在“断章取义”和没有领悟马克思反讽的口吻。(32)但他认为伍德的这种观点主要是来自于他没有意识到马克思的内在批判所致,认为一旦意识到马克思的内在批判,我们就能认识到,即使“依据资本主义自身的正义标准,马克思也不认为资本主义是正义的”,(33)因我们一旦跳出交易本身来看待问题,就会发现这种交换并不自由,劳动者和资本家各自的地位中蕴含着深刻的不平等,劳资交易下的自由和平等也只是一种假象。(34)
在布坎南看来,要理解马克思视野中的资本主义剥削不可能是正义的,还可以从“剥削-异化”的关系入手,就此,布坎南对剥削、异化、人性提出了新解,并层层推演,彰显了他所说的隐含在马克思文本中的内在批判。出于简化起见,我将布坎南的论证概括为如下的推论:
(1)雇佣劳动存在剥削;
(2)剥削的内容是异化,异化是人性的扭曲;
(3)不合乎人性就是不合乎正义,雇佣劳动不合乎正义。
在这个推论当中,对于(1)和(3),布坎南似乎觉得不成问题,并没有着力解释;但对于(2),他却几乎用了一章的篇幅(《马克思与正义》一书的第二章)来阐释,毕竟他必须解释:剥削是如何与异化“对接”上的?在已有的学术成见中,异化与人性的思考并不贯穿至成熟期的马克思,又该作何解释?
在布坎南看来,对于马克思的“剥削”,我们不宜将它局限于劳动过程本身去理解,(35)也不能将剥削界定为对工人剩余产品的占有。(36)依据他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提到的剥削概念,他认为马克思的剥削概念包含着三个要素:“第一,剥削人就是像人利用工具和自然资源那样来利用他(或她);第二,这种利用对于被利用者来说是有害的;第三,这种利用的目的是为了自身的利益。”(37)而且,剥削“超越了劳动过程本身,不仅适用于一个阶级内部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38)“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剥削社会的基石,但不是整栋大厦。把马克思的剥削概念局限在劳动过程中的任何解释都忽视了马克思的根本论点:一个社会的劳动过程对该社会的所有人类关系都具有普遍的影响力。”(39)
通过对剥削提出新解,布坎南认为他实现了马克思的剥削与异化的对接,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通过对人类被利用的方式和这种利用对人类伤害的形式提出系统化的分类,为剥削概念提供了内容”。(40)
而对于那种认为异化与人性的思考并不贯穿至成熟期的马克思的观点,他则指出,异化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在马克思的中、后期消失,(41)而是一直贯穿马克思的整个《资本论》时期,马克思也不是拒斥人性观念,而是以一种马克思所理解的普洛透斯般(千变万化)的人性观念拒斥那种传统的不变的人性观念。(42)
通过引入“剥削-异化”的关系,布坎南再次认为伍德所说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正义的——观点是无法成立的,而应是,即使依据资本主义的正义观念,资本主义剥削也是不正义的。但布坎南认为,马克思一直不愿意说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因一旦指认资本主义剥削是不正义的,就会让人误以为剥削问题在本质上是分配问题,就会执迷于认为剥削只是违背了分配正义的某个标准,执迷于把消灭剥削的要求等同于“公正”的或“公平”的工资的要求。但根据马克思,这种执迷有双重的灾难。第一,把注意力集中在分配上就是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分配是生产的职能,没有生产方式上根本变革而谋求分配的改革是注定要失败的。第二,把剥削主要当作分配性问题会把注意力引向混乱抽象的正义理想,而远离具体的革命目标。(43)
三、马克思对正义的局限性的揭示
尽管布坎南肯定了内在批判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但他一直强调,内在批判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毕竟不是主要的、根本性的,要把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解释与批判,还是必须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入手,只有基于此,才能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为何是最为根本的、彻底的,(44)也才能把握马克思所揭示的正义的限度。
(一)正义是一种缺陷性的、补救性的价值,是一种意识形态
对一些人来说,正义是一种好东西,而马克思是一位好人。因此,马克思秉持正义似乎是不证自明的,而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自然就是一个美好的社会、正义的社会。但在布坎南看来,在马克思那里,正义更多的不是社会的首要价值或公民社会的最高美德,而是一种缺陷性的、补救性的价值。
(1)从正义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环境来看,在一个没有存在利益冲突甚或利益分化的环境之中,正义无从产生,也不需要正义。“正义只是起源于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以及自然为人类需要所准备的稀少的供应”。(45)而就社会生产来看,正义只是社会生产过程存在缺陷的症状和必然诉求。正义是有缺陷的社会生产的产物,也是对其缺陷的应对和补救。正义的追求是在一个使正义成为必要的环境的基础上的追求。在布坎南的诠释中,“正义的追求是无用的,因为正义的环境恰是正义的需求难以实现的因素”。(46)因而,正义追求似乎注定是一场难以实现的“夸父追日”。马克思既不愿以不正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也不会以正义界定共产主义,在他的理解中,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它消解了正义赖以产生的条件。
(2)虽然正义体现为对人的权利的维护和捍卫,但是一个依仗正义、权利来谋求对人的保护的社会,正说明其人际关系上存在着紧张的冲突和缺陷,而正义、权利也无非是这种冲突和缺陷的表现与复制。(47)他指出,“假如,像马克思所认为的,权利概念仅在一个对竞争、稀缺、人际冲突、人与人的分离无法控制和减少到最低限度,且如果有尊重的观念就要有人是权利主体的观念的社会中才有重要作用,那由此可推出的是,任何需要尊重的社会都是存在根本缺陷的社会。如果这确实是马克思的观点,那么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就不在于它没能实现权利和尊重的观念所追求的标准,而是社会的无序需要这些观念”。(48)
因此,似乎在马克思看来,正义、权利并不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佳准则,把人作为权利主体来尊重也并不是对人的尊重,正义、权利无不意味着某种划界,无不指向一种社会缺陷。
“任何需要法权概念的社会都是有缺陷的社会这个论题将会调和(temper)我们对法权原则的狂热以及我们的沮丧情绪,即我们所为之着迷的权利和正义意味着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存有深深的猜疑和普遍的冲突。”(49)“假如人际关系足够的和谐或者冲突能够得到自发地裁决,那么索取或者要求也就没有存在的机会,因而也就没有必要存在权利的观念。”(50)由此,也可以理解,对于身处共产主义社会的人来说,“环绕他们世界周围的是爱人、朋友或者同志,而不是值得尊重的权利主体”。(51)
还有,设若马克思批判正义、权利是因其“在广义上,是一种‘判决性’和‘对抗性’的观念”,(52)那马克思是否持有了一种更为宽泛的正义观念,或承认正义是一种自发的、和谐的秩序的问题,而不是在各种冲突的力量之间划界的问题?(53)
对此,布坎南指出,这样的一种理解是在极端地误导我们。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记得,马克思本人既没有在两种权利概念之间做出区分,也没有明确将他的批判限定在前者,更不曾使用正义的语言描述他称为共产主义社会的自发的和谐秩序。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应该或者可能提出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他眼中的共产主义可以作为另一种正义观的应用。但这样一来,就搁置了马克思坚决要从彻底批判社会的基本词汇中去除所有正义谈论的努力。(54)
(3)正义、权利是一种意识形态。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对人的尊重就表现为对人的权利的尊重。“对应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利的两个基本范畴,资本主义把对人之为人的承认降低到对法权观念的两种形式的承认。诸如尊重人被等同为对拥有私有财产权和平等的政治参与权的地位的承认。”(55)在这种权利的平等图景中,人与物之间的界分给抹杀了,人与人之间的天然的差异性给“平等化”了,不同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人在行使政治权利上的有效性的巨大不平等也给“忽视”了。(56)“贫困的工人和富裕的食利资本家,妓女和嫖客,高级政府官员和政治无能的‘公民’都在市场上有平等权利订立契约,在选举上有平等的投票权。”(57)
从总体上看,马克思认为对权利持有者地位的承认不仅没有将人与物区分开来,而且还抹杀了二者在作用上的重大差别。仅仅承认个人是有交换权利以及参政权利的存在只是一种抽象的表面的尊重人的观念,但这在把人仅仅当作物的制度中却起着非常具体的基础性作用。(58)
既然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权利在其根本上是把人当为物来看待,那是否意味着马克思认为真正的正义社会应该是一个“把人当人看”的社会?
布坎南认为,尽管马克思预期并认可了一种“把人当人看”的社会,但马克思并没有把这种社会归为正义的社会。因此,我们不能把他对资本主义法权的尊重观念的批判看作是在更为充分的权利观念的基础上,为更为充分的尊重的法权观念开拓路径的一种努力。相反,我们应该得出,马克思所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对人的尊重不是对权利持有者地位的承认,它在根本上是一种不同于我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像尊重人这样的观念已经没有任何意义。(59)
(二)正义不起主要的革命动机作用
在关于马克思为何不以正义批判资本主义上,伍德和米勒等人曾经指出,正义在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中不起主要的革命动机作用。(60)布坎南继续拓展了伍德、米勒的这一观点。
布坎南指出,马克思认为那些试图通过诉诸道德义愤来激起民众抗争的道德说教的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是肤浅的,马克思自己所做和所倡导的是对资本主义做非道德的、科学的分析,而这与他关于革命动机的论述是相一致的。(61)马克思革命动机理论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不依赖个人的正义感或权利的行使。(62)
对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的革命动机就是其自我利益或阶级利益,这一点也不夸大。很多时候,马克思甚至将其界定为诸多生存利益中最为基本的一种。(63)“依据马克思,自我利益或者阶级利益在革命斗争中总是主要动机。……一旦无产阶级在对抗极少数派中变为绝大多数,所有关于权利或正义的任何托辞就能够被抛弃。无产阶级在他们的正义感引导下去获取普选权也不是马克思的诉求。马克思诉求的是他们的战略的意义,无产阶级会逐渐地意识到,要粉碎他们的阶级敌人,就应该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道出了避开正义诉求的另一原因:正义诉求不仅不是必要的,而且是分歧和含混不清的,因为每个社会主义者派别都有他们自己的正义概念和权利概念。”(64)
但阶级利益是根本,是否排除了对于正义的诉求呢?或是否二者是冲突的,才导致马克思对正义诉求的拒斥呢?
在布坎南看来,马克思相信,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会变得如此极端,以致对无产者来说变得越来越明显。与有产者(资本家)的不断减少相对垒的是无产者(无产阶级)的不断增加。有产者——那些控制着生产工具的人——变得越来越富有,而那些仅仅拥有自己劳动力的无产者却变得越来越贫穷。社会面临着由生产过剩产生的矛盾:因为工人的生产超过了工人的购买力,因此经济危机产生了,工人失业了。每一无产者一旦认识到阶级斗争的这些基本事实,他就能意识到他自己的利益连同他的整个阶级利益的实现都要求推翻资本主义社会。(65)
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概念使得正义原则或者任何一种道德原则的激励作用成为多余。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是自身利益或者阶级利益的动力——并不需要诉诸正义感或者任何道德标准。事实上,马克思嘲笑了那些道德学家的社会主义者——如蒲鲁东,他热心地劝说大众诉诸他们的正义感来进行社会变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者“没有道德说教”,并清楚地说明,共产主义者的恰当角色是教育大众,以便他们更为清楚地看清他们自己的利益并将由此产生的革命努力引导到最有效的革命过程中去。共产主义者不是构想正义原则或者运用劝说技巧激发无产阶级的正义感的人。(66)
显而易见,马克思的革命动机概念使得寻求道德原则作为任何激励作用都是多余的。诉诸生存利益中的真实的自我利益已是足够,而没有必要诉诸正义感或者其他道德准则。(67)
布坎南认为我们至少要注意到这一点: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的正义与权利概念,无论对于激起或解释革命动机,还是作为寻求新社会的基本的规范准则来说,都是没必要的。要走向新社会,直接的方式是阶级斗争,而不是正义诉求。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讲,谈论正义和权利在所有这些意义上都是过时的。(68)
四、结语
总括布坎南对马克思批判正义的诠释,我们可能会发现,布坎南的诠释的得力之处是在尊重马克思文本事实的基础上,吸收、融通各方的理论优点,并深度挖掘马克思关于正义的局限性的看法。概要地说,布坎南诠释的理论优点主要在于:
(1)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上存在着基于法权的内在批判与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外在批判,既吸收了马克思不以外在的法权原则批判资本主义的观点,又认可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不正义的观点,较好地解决了塔克、伍德一方与霍尔斯特姆、胡萨米一方的理论分歧。(2)在批驳伍德断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正义的问题上,他创制性地引入了“剥削-异化”的关系进行阐释,给剥削注入了“新解”,并以之诠释马克思并没有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正义的,而是不正义的。其论证,相较于霍尔斯特姆、胡萨米等人只是简单地指认伍德在文本的引用上断章取义或没有注意到马克思的反讽的口吻,要来得深刻;也比柯亨从“剥削—掠夺—侵犯自我所有权”得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不正义的,(69)更具有理论的自洽性,因柯亨得出马克思隐蔽持有一个自我所有权的观念,既与马克思批判自我所有权,废除私有制不相符,也存在把马克思降低到他所批判的对象的水平上的嫌疑。(3)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较为完整而又不乏说服力地展示了马克思关于正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态度,揭示了马克思何以拒斥、批判正义的缘由。
从总体上来看,布坎南是试图立基于文本事实和遵循马克思内在的理论脉络的基础上,协调双方之间的理论冲突和紧张关系,因而布坎南的阐释不仅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而且具有“兼容并蓄”的特性。
然而,如果细加比较、辨析,我们也许会发现,布坎南在阐释“马克思与正义”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在相当程度上也得益于他试图破解争论双方的理论紧张和吸纳各方的理论优长,因此一来,也含蓄地隐含了争论双方的理论紧张。
首先,就布坎南与伍德一方的比较来看,布坎南与伍德的主要分歧是布坎南反对伍德断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正义的观点。从表面来看,双方的观点是冲突的,但是,一旦我们注意到伍德在断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正义时,还同时附注了“正义是意识形态”,那伍德所说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正义的观点,就不是对资本主义剥削的肯定,而是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否定。伍德在他这一“刺耳”的断言中,特别提醒了我们要透过“正义是意识形态”的这一前提性判断来理解“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正义的”说法。因此,一旦我们注意到伍德的这一前提性判断,那布坎南与伍德在表述上就虽有所不同,但基本思想却可以说是一致的。对于布坎南的这种相反的表述,伍德也许可以以他之前说的“承认资本主义剥削是正义的这一事实(假如是按照马克思理解这一事实的方式)并不是为资本主义辩护,而且,以正义为它辩护也是没有意义的”(70)来回应布坎南。当然也必须承认,布坎南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不正义的”提法,是比伍德更进了一层,即,即使以资本主义的正义标准来衡量,资本主义剥削也是不正义的。然而,布坎南通过阐发马克思的内在批判来揭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剥削)是不正义的,虽然迎合了人们的“常见”或“常识”,但也给自身增加了一些理论紧张和理论的难点。一是,如强化马克思基于法权的内在批判的作用,就会弱化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的作用;如强化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彻底的作用,就会淡化甚至忽略马克思基于法权的内在批判的作用(例如,像伍德那样)——在相当程度上,我甚至可以说,“马克思赞成正义一方”和“马克思反对正义一方”的理论紧张已经转换成了布坎南阐释中的内在批判和外在批判的紧张。二是,布坎南的内在批判的阐释还有赖于布坎南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人性理论的充分阐释,而且有必要指出在马克思的中、后期中(特别是在《资本论》时期),异化理论和人性理论是如何起到内在批判的作用的,但在这一方面,布坎南更多的是断言,而缺乏周详的论证。(71)
其次,就布坎南与霍尔斯特姆、胡萨米一方的比较来看,当布坎南认为马克思有以内在法权批判资本主义并且强调其必要性时,就意味着在批判资本主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并非能够独担重任,那历史唯物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上的不可替代性和根本性就会受到削弱,也因之,才需要内在批判来“帮衬”解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既已“借力于”内在批判,又何以不能“借力于”外在的法权批判呢?因一旦认可内在法权批判的必要性,也意味着基于某一外在的法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是可能的,其可能就在于对内在批判的需要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强烈到不需要任何基于正义视角的批判。
对此,我们也许会说,以某一外在的正义原则进行批判,是缺乏文本依据的;而内在的法权批判却能找到文本支持。但是,缺乏文本支持是否就没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呢?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设想来探问这种可能性:以资本主义的正义标准批判奴隶社会是否可行呢?或者说,依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以某种外在的法权观去进行批判是否可行呢?假如可行,我们就不能排除以一种资本主义之后的正义准则去批判资本主义的可能性。(72)当然,从文本上的确难以找到直接的理论依据。但是,没有直接的文本依据,是否就意味着理论上的不可能呢?在笔者看来,这未必。因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是能够推演出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依据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导:设若a)社会主义生产优于资本主义生产(即S[P]优于C[P]);b)社会生产决定正义,(73)那相应地,就有:社会主义的生产决定社会主义的正义,资本主义的生产决定资本主义的正义(即S[P]决定S[J],C[P]决定C[J]);那么我们根据a)和b)就可以得出:c)社会主义的正义优于资本主义的正义(即S[J]优于C[J])。既是如此,那这一与资本主义的正义有着发展的连续性且优于资本主义正义的社会主义正义,就可以用来评价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生产。
最后,从总体上看,尽管布坎南与伍德在马克思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剥削为不正义上,存在着分歧,但布坎南与伍德的观点还是存在着较多的相似性,其观点基本上可以视为对塔克—伍德一方的观点的发挥,尽管伍德认为布坎南的观点更多的是与塔克相近。(74)
(1)布坎南的内在批判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来自伍德的启示。伍德所断言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正义的刺耳的提法给人一种有悖常理的感觉,因此,为使提法合乎常理,就必须寻求另一种可能的自洽的解释,霍尔斯特姆和胡萨米等人从马克思的批判语境入手和布坎南从马克思的内在批判入手都可以说是来自于伍德这一有悖于常理的表述的回应。
(2)从布坎南排除霍尔斯特姆和胡萨米等人所认为的马克思不存在以资本主义之后的分配正义原则(或无产阶级的正义观)去批判资本主义的两点理由——没有文本依据和正义属于意识形态——来看,也不乏有伍德等人的启示。因就文本事实来看,伍德早在《马克思论正义与权利——对胡萨米的回复》一文中就已经论述“胡萨米严重误读了整个《哥达纲领批判》,他从中提取出他自己所偏好的无产阶级正义原则”。(75)至于正义属于意识形态,则是伍德一直强调的观点。
因此,如果将布坎南的诠释与伍德的诠释做一比较的话,我认为二者的理论分歧并不是很大,而是一脉相承,尽管伍德论辩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正义的,而布坎南则论辩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不正义的。因为,只要意识到,在伍德的诠释当中,伍德着力强调的是正义属于意识形态,而历史唯物主义在与正义此类的意识形态的对垒当中,则有弱化正义此类意识形态的作用,(76)以至将正义弱化到如同废物。(77)相比较而言,布坎南虽然也如伍德那样强调正义属于意识形态,却并没有认为马克思将正义“弃如敝屣”,而是让其在内在批判中发挥作用。如是观来,伍德与布坎南的一个理论分歧就可以视为是否将历史唯物主义推向极致的一个分歧。对于布坎南来说,马克思以法权观念的内在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外在批判共同批判了资本主义,其言下之意,似乎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无法独立地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对于伍德来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仅凭历史唯物主义就足以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无须一个“有意识形态问题”的正义的“帮衬”。这样一来,布坎南在对待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上就反而没有伍德那么彻底与“激进”了。这一点我觉得周凡博士对伍德就看得尤为透彻。(78)
也许,当我们试图从伍德的视角去审视布坎南在马克思与正义问题上的理论成就时,可能会抹杀布坎南的作用。对于伍德来说,他对马克思批判正义的诠释,其意也许不在于申明马克思如何对待正义,而在于试图借助对马克思批判正义的阐释来彰显历史唯物主义,正如马克思当年借助批判意识形态来彰显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与观点;但对于布坎南来说,他已不满足于仅仅阐释马克思在正义上的看法,而是试图在阐释马克思对正义的看法上,更进一步地与马克思对话(在他看来,毕竟在我们的当代以及可设想的共产主义还依然需要权利与正义),即如诺曼·杰拉斯所说的“把马克思带进正义”,并与马克思对话。而这样的一种对话,对于置身于当今正义论题的英美马克思主义者显有必要,对于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更有必要。
注释:
①阿兰·桑德洛:《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王贵贤译,载李惠斌、李义天主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8-349页。
②R.G.佩弗在其专著《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吕梁山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扉页的“鸣谢”中充满感激地说:“首先我要感谢桑福德·G.撒切尔、凯·尼尔森和艾伦·E.布坎南……在对待马克思的规范性观点的解释和评价问题上,我看待布坎南就如同诺齐克看待罗尔斯:要么接受他的分析,要么解释不接受。我深深地感谢他所做的一切。”
③Allen W.Wood."Review of Marx and Justice:The Radical Critique of Liberalism,by Allen E.Buchanan".Law and Philosophy,Vol.3,No.1(1984),pp.147-153.
④Allen E.Buchanan,Marx and Justice:The Radical Critique of Liberalism,London:Methuen,1982,p.56.
⑤Ibid.,pp.56-57.
⑥Ibid.,pp.57、59.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第488-489页。
⑧Allen E.Buchanan,Marx and Justice:The Radical Critique of Liberalism,London :Methuen,1982,p.57.
⑨Ibid.,pp.50、162.
⑩戴维·麦克里兰:《意识形态》,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页。
(11)Allen E.Buchanan,Marx and Justice:The Radical Critique of Liberalism,London:Methuen,1982,p.50.
(12)Ibid.,p.26.
(13)Ibid.,p.57.
(14)Ibid.,pp.58-59.
(15)Ibid.,p.59.
(16)艾伦·伍德:《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林进平译,载李惠斌、李义天主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34页。
(17)Allen E.Buchanan,Marx and Justice:The Radical Critique of Liberalism,London:Methuen,1982,p.52.
(18)Ibid.,pp.xii、51、54.
(19)Ibid.,p.75.
(20)Ibid.,pp.14-15.
(21)Allen E.Buchanan,Marx and Justice:The Radical Critique of Liberalism,London:Methuen,1982,p.56.
(22)Ibid.,p.75.
(23)Ibid.,p.75.
(24)Ibid.,pp.55、187.
(25)Ibid.,p.53.
(26)Ibid.,p.53.
(27)艾伦·伍德:《马克思论权利与正义——对胡萨米的回复》,林进平译,载李惠斌、李义天主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0-81页。
(28)Allen E.Buchanan,Marx and Justice:The Radical Critique of Liberalism,London:Methuen,1982,p.54.
(29)Ibid.,p.55.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第219页。
(31)Allen E.Buchanan,Marx and Justice:The Radical Critique of Liberalism,London:Methuen,1982,pp.53-54
(32)Ibid.,p.54.
(33)Ibid.,p.56.
(34)Ibid.,p.54.
(35)Allen E.Buchanan,Marx and Justice:The Radical Critique of Liberalism,London:Methuen,1982,p.53.
(36)Ibid.,p.60.
(37)Ibid.,p.38.
(38)Ibid.,p.40.
(39)Ibid.,p.42.
(40)Ibid.,p.42.
(41)Ibid.,p.15.
(42)Ibid.,p.27.
(43)Ibid.,p.45.
(44)Ibid.,pp.50-51、75、97.
(45)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36页。
(46)Allen E.Buchanan,Marx and Justice:The Radical Critique of Liberalism,London :Methuen,1982,p.69.
(47)Ibid.,p.80.
(48)Ibid.,p.77.
(49)Ibid.,p.178.
(50)Ibid.,p.76.
(51)Ibid.,p.76.
(52)Ibid.,p.83.
(53)Ibid.,p.83.
(54)Ibid.,p.84.
(55)Ibid.,p.80.
(56)Ibid.,p.80.
(57)Ibid.,p.80.
(58)Allen E.Buchanan,Marx and Justice:The Radical Critique of Liberalism,London:Methuen,1982,p.80.
(59)Ibid.,pp.80-81.
(60)R.G.佩弗:《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吕梁山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04-208页。
(61)Allen E.Buchanan,Marx and Justice:The Radical Critique of Liberalism,London:Methuen,1982,p.86.
(62)Ibid.,p.73.
(63)Ibid.,p.87.
(64)Ibid.,p.74.
(65)Ibid.,p.74.
(66)Ibid.,p.74.
(67)Allen E.Buchanan,Marx and Justice:The Radical Critique of Liberalism,London:Methuen,1982,p.87.
(68)Ibid.,p.75.
(69)见G.A.柯亨的《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G.A.Cohen,Self-Ownership,Freedom,and Equal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一书的第5、6、8章。也参见Allen E.Buchanan,Marx and Justice:The Radical Critique of Liberalism,London:Methuen,1982,pp.185-186.
(70)艾伦·伍德:《马克思论权利与正义——对胡萨米的回复》,林进平译,载李惠斌、李义天主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0页。
(71)具体参见布坎南的《马克思与正义》一书第二章的“马克思的评价视角”。
(72)事实上,象诺曼·杰拉斯就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了这种努力。诺曼·杰拉斯:《将马克思带向正义:补充与反驳》,曹春丽译,李惠斌、李义天主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4-245页。
(73)参见林进平:《马克思的“正义”解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18-136页。
(74)Allen W.Wood."Review of Marx and Justice:The Radical Critique of Liberalism,by Allen E.Buchanan".Law and Philosophy,Vol.3,No.1(1984),pp.147-153.
(75)艾伦·伍德:《马克思论权利与正义——对胡萨米的回复》,林进平译,载李惠斌、李义天主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4页。
(76)Allen W.Wood.Karl Marx.2nd Edition.Routledge.2004,p.155.
(77)伍德指出:我们不妨认为,资本主义是否应被称为“不正义的”,这仅仅是语词之争。毕竟,马克思确实谴责资本主义,而且,他的谴责至少部分是因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剥削制度,它会依靠资本而占有工人的无偿劳动。如果马克思在称呼资本主义的这种罪恶时用的不是“不正义”而是其他词语,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它们听起来仍然像是“不正义”;而且只要我们喜欢,就尽可以用“不正义”这个词来替换它们。艾伦·伍德:《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林进平译,载李惠斌、李义天主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页。
(78)周凡:《历史漩涡中的正义能指——关于“塔克尔—伍德命题”的若干断想》,《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3期。
标签: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道德批判论文; 资本论论文; 共产主义论文; 伍德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