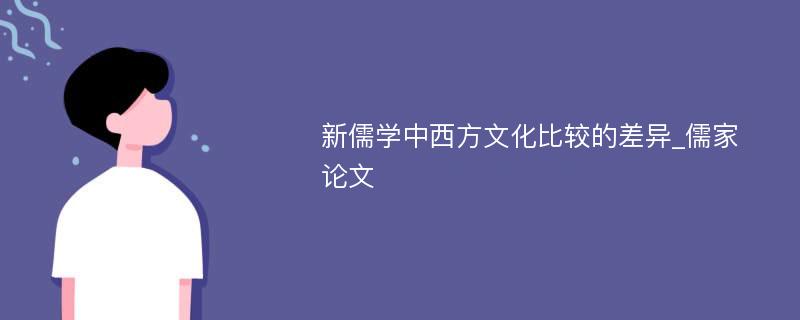
新儒家中西文化比较中的歧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中西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文化比较是现代新儒家的共同兴趣。新儒家对中国儒学传统的高扬,主要是通过将儒学传统与西方文化相比较而进行的。其对西方文化的看法,大致如下:(1)重科学,轻人生;重物质文明,轻精神文明; (2)心物对峙,天人为二;(3)西方文化如今已走到发展的尽头,且无法自救,只有靠中国的儒学思想去超拔。
不能不说,在对西方文化的批评方面,新儒家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是精彩的。面对欧风美雨对国人灵魂的涤荡,回首民族百年行迹的歪歪扭扭,比起一般的文化人来,新儒家似乎多一份广义上的宗教情怀,多一份悲天悯人的救世宏愿,富有极灿烂的伦理美,也是文化人所应有的品格。明乎此,我们才说新儒家诸贤都具有仰之弥高的文化品格。而牟钟鉴先生则从另一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新儒家是中国现代思潮中,最早起来纠正“五四”主流派反传统太过的偏失的。“五四”西化派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三点不足:其一,对儒学批判有太多的政治化情绪化成分,喜作漫画式的挖苦,其中不乏精彩动人之笔和震憾心灵的时候,但没有坚实的学术根基,不能算作系统科学的总结,其主要目标是揭露它、打倒它,而不是说明它、转化它。配合革命运动有余,推动文化更新不足;其二,忽视了儒学的复杂性,多重性,只看到它的时代性、贵族性、正统性,看不到它的普遍性、平民性、批判性,只看到它的糟粕和扭曲形态,看不到它的精华和内在生命,把传统文化都归结为“封建主义”,必欲铲除而后快,甚至要取消文字,有严重的文化虚无主义倾向;其三,长于破坏,短于建树。西化派的缺点被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正义、热情、民主、科学等美好事物所掩盖,继而被后继者所膨胀,挟其主流派思想而横行天下,很少有人能清醒认识并加以纠正。于是,反传统反儒学同反封建几乎同义,遂成为一面旗帜,进而青年以聚集其下为荣。文化上的“左”同政治上的“左”一样不容易纠正,在中国近代史上比较有市场,稳健的改良派不吃香,容易受到孤立,这大概与中国守旧势力太强大不愿妥协,新与旧的两军对垒不能不分明、战斗不得不激烈有密切关系。
二
新儒家诸贤无不以饱学深思称誉文化界。他们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对西学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但同时,他们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由于心的砝码全压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边,所以又不可避免地走向极端。他们眼里的西方文化,负面多于正面,消极意义多于积极意义,特别是对本世纪的西方文化,看法尤欠公允。
那么,作为一种自成体系的西方文化是否就象新儒家描述的那样呢?本文拟从两方面谈起:
(一)道德理性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
在新儒家看来,西方人重科学理性,中国人更重道德理性。这种看法并非全无根据。偏颇之处是,他们很少把握到科学理性与人生之关系,亦忽视了西方人的另一方面成就,即在强调科学理性的同时,不忘人生意义的提携。在这一方面,成中英先生的看法就公允得多。他认为:“任何一个物质文明的创造都有其精神力量作后盾,作为原动力。如果一个国家要维护其高度的物质文化,就不能不维持其对价值的意识,以及其统合过去和未来的一贯的思想能力。”(注:成中英:《世纪之交的抉择——论中西哲学的会通与融合》第84页,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在西方历史上,第一位注重人的地位与价值的思想家是普罗塔戈拉。他的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可以视为西方人的学问由自然知识转为人的知识与自然知识并重的宣言。普罗塔戈拉虽然标出有关人的学问的价值,但对其阐述却是零散的,无思想系统。真正完成由自然知识转为人的知识与自然知识并重的,是在希腊哲学史上圣贤般的哲人苏格拉底。在苏格拉底的哲学里,自然的“理念”,根源不在自然本身,而在于人的理性,或曰人的德性。因为他认为,这世界既不是物理世界,也不是数学世界,而是伦理世界即人的世界,善的世界。正是在这一基本的哲学立场上,苏格拉底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命题。其核心内容是知行合一。需要明了的是,苏格拉底所指的“知识”,不是自然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对人的理性自我认识的道德意识,是一个实践意义上的概念。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思想直接为柏拉图所继承。在柏拉图的哲学里,道德问题为主要内容。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后,道德哲学作为人们所关心的一门重要学问,在希腊罗马、仍作为哲学思想的主流为哲人们所注重,尤为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派所注重。虽然他们没有中国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但在追求心物平衡方面,却又与儒家那种“退则独善其身”的旨趣相合。
古希腊罗马的道德哲学是西方近代伦理学的理论来源。尽管文艺复兴时期以后,科学理性充分发展起来,但人的问题仍是西方哲学家所注重的。尤其是叔本华开其端绪的现代西方哲学,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反科学主义的思潮。像生命哲学、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都主张从生命的本源处提携人的生命价值。应当注意的是,新儒学的文化哲学,许多都是直接来源于西方人的思想,或者受西方人文主义的启发,或者直接用西方哲学来重新梳理中国儒学的义理,怎能说西方人缺乏道德理性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人文主义精神,需要新儒学的点拨呢?
关键问题是:一个民族能否仅仅以道德立国?“物质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美满,同精神生活的美满”应是同步的。时届21世纪,“如果其他民族已过上丰裕的物质生活,或走上政治民主化的道路,而自己这一民族却依然是落后的”,“没有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人格保障”(注:启良:《新儒学批判》第348页,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单凭善良的道德愿望,立国立世,难免显得空洞,苍白,无力。美国天普大学付伟勋教授更直接指出:“现代中国儒者如仍带有儒家道德的有色眼镜,去看世界其他学术思潮,恐怕有一天连自家门户都守不着。”(注:付伟勋:《现代儒学发展课题试论》,见《当代新儒家论文集总论篇》第52页。)
(二)本世纪西方文化的自救自新
除极个别人物以外,新儒家几乎都给传统儒学在当今及至未来加了一层世界意义。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今日的西方文化已经走到尽头,既不可能给人类带来福祉,也不能自救自新,唯有从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进口孔孟儒学,才有超越的希望。
诚然,19世纪后期以来,西方文化的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困局,经济危机,信仰饥荒,两次世界大战更是把西方人推到了苦难的深渊。但是,就近百年的世界历史看,这些现象不过是西方文化在前进的路途上所遭遇的挫折,而不能看作末日的征兆。
第一,资本主义作为近代世界一种新型的文化形态,肩负着领导世界精神的使命。不可免地要以血与火的面貌载入文明史。它是批判的,反传统的,无前例可循,且幼稚而不老成,免不了出现“偏差”。
第二,19世纪后期以来的西方文化界,各种新的文化思潮涌动起来。这些新兴思潮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从反理性主义走到非理性主义,从反科学主义走到人本主义。极端化总是欠妥,但彼时彼地又是必要的,因为对任何一种浓厚的传统,如果不用一种走极端的反传统的方式,就不足以构成反叛力量,亦不足以构成否定性的打击。
三
“文化比较之所以必要,究其实质,乃是人类自我完善的一种手段,或曰趋于真善美的一条途径。因为文化比较的大旨,就是去劣存优,去落后赶先进。”(注:启良:《新儒学批判》第345页, 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中国人所面临的不是单纯的对传统的态度问题,而是面临着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双重压迫下的痛苦选择。新儒家无疑是富有民族责任感的。传统的负荷之重,百年历史的路途坎坷,国际局势对民族文化转型的大不利,促使新儒家既关心人生问题,又关心中国问题,深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忧心。然而,这种忧心却流于一厢情愿,以“吾家旧物”之优秀而沾沾自喜,抱着救世主的愿望一心想着如何去超渡西方人,而无视这样一个事实:本世纪乃至未来世纪的最近年代,中国与西方世界处于两个文明时代,所面临的文化问题与社会问题迥异。我们的任务是如何博采众长,少走弯路,是如何尽快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西方人所努力的该是如何避免现代文明走上偏途,是如何应对“后现代”问题。如果把眼下的中国问题与西方问题扯到一起,作一锅糊涂的粥来煮,或是一味揭人之短,护己之短,都于事无补。这种“负责任”只能见其无能或极端不负责任,更有甚者,自戕自灭。像我辈浅薄后生,比起这些博学鸿儒来,只有惭愧的份儿,实在没有评头论足的资格。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尽一份绵薄之力,斗胆以为:当下新儒家中西文化比较中明智的做法应是对症下药,对己对人都得“科学分析,兴利除弊,互利互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