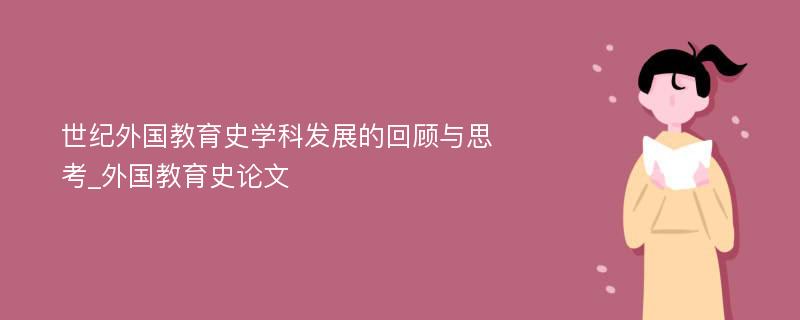
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世纪回顾与断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史论文,断想论文,学科论文,外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13X(2001)03-0023-05
一、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百年回眸
众所周知,我国的教育史学科分为中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学科领域。就中国教育史而言,研究者认为由黄绍箕提出设想,后由柳诒徵撰成的《中国教育史》是由我国学者编撰的第一本中国教育史著作,迄今已近百年,它标志着中国教育史学科的诞生。然而,外国教育史学科具体诞生于何年,其标志性著作是什么,尚无定论。一般认为,最早的外国教育史研究始于清末民初,创办于1901年5月的我国最早的教育杂志《教育世界》,曾刊载了许多有关外国教育史的研究成果。我国最早的有关外国教育史的著作均译自日本,如190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东西洋教育史》等。191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周焕文、韩定生合撰的《中外教育史》,虽体例较完备,但它不是专门的外国教育史著作。从现有资料看,中国学者最早编撰的外国教育史著作是商务印书馆1921年出版的由姜琦撰写的《西洋教育史大纲》,该书是根据作者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的教本修订而成的,全书约20余万字。自古希腊教育一直写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法英美等西洋各国的教育。据姜琦在书中称:在此之前,西洋教育史研究除了上文提到的《中外教育史》外,“绝无他著矣”。[1]据此我们可以认定姜著《西洋教育史大纲》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外国教育史著作。此后,多种外国教育史著作纷纷问世,由中国学者撰写的有刘炳黎编《教育史大纲》(北新书局1931年发行)、瞿世英编《西洋教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林汉达著《西洋教育史》(世界书局1933年印行)、蒋径三著《西洋教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雷通群著《西洋教育通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姜琦编著《现代西洋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庄泽宣著《西洋教育制度的演进及其背景》(中华书局1938年出版)、王克仁著《西洋教育史》(中华书局1939年出版)等等;翻译著作有格莱夫斯(F·Graves)著《中世教育史》(吴康译,商务印书馆1922年出版)、《近代教育史》(吴康译,商务印书馆1925年出版)、《近三世纪西洋大教育家》(庄泽宣译,商务印书馆1925年出版)、埃默森(M.I.Emerson)著《教育理想发达史》(郑梦驯译,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赖斯纳(E.H.Riesner)著《法德英美教育与建国》(崔载阳译,民智书局1930年出版)、《近代西洋教育发达史》(陈明志、唐瑴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库柏莱(E.P.Cubberly)著《世界教育史纲》(詹文浒译,世界书局1935年出版)、科尔(P.R.Cole)著《西洋教育思潮发达史》(于熙俭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迈耶(A.E.Meyer)著《近代欧洲教育家及其事业》(黄溥译,世界书局1939年出版);另有译自日文的著作多本。如《近代教育家及其理想》(中华书局1924年出版)、《欧美学校教育发达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日本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等等。
从上述外国教育史著述的出版情况可以推知,我国教育史学科形成于20世纪初,20年代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是外国教育史研究较活跃的时期,也可称之为第一个高峰期。先是受日本的影响,继而受美国的影响,虽然出版了一些由国人撰写的著作,但其内容和体系均来自欧美,还谈不上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教育史学科。从著作的类别看,既有通史类著作,也有断代史、专题史著作,研究对象限于德法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一个高峰随之消退。
新中国成立后,一切“以俄为师”,外国教育史学科更是全盘苏化。不仅从苏引进了教育史著作和教材,如米丁斯基的《世界教育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出版)和康斯坦丁诺夫的《世界教育史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4年出版),更从苏请来了教育史教师,培训高校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师资。这一时期外国教育史研究遵循唯物史观,强化了学科的党性原则和政治色彩,阶级分析方法被普遍采用。客观地说,唯物史观引入外国教育史研究并作为指导思想和方法,为学科发展指明了方向,注入了活力,但由于“左”的干扰,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况且“一边倒”的政策也是违反教育发展规律的,因此而造成的恶果是学科发展的迟缓,学科研究难以越雷池一步。惟一的一本由我国学者编写的《外国教育史》(曹孚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出版),仅是苏联教育史教材的复制品。尽管曹孚先生本人学识渊博,学贯中西,但临终也未能完成编撰我国自己的《外国教育史》教材的夙愿,只留下一份未来得及修订的编写提纲(初稿)。从解放初期到“文革”前,虽然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也取得过一些成绩,但总的研究水准和成果数量是不尽人意的,甚至不如二三十年代。“文革”十年,外国教育史学科更是备受摧残。
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复兴是在1978年以后。1979年11月,全国教育史研究会在杭州成立,外国教育史学科开始恢复和重建。这一时期的重要任务是拨乱反正,消除“左”的影响。研究者不再拘泥于苏联版的教育史课本,西方的教育史研究成果开始引入。在此基础上,学者开始探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批试图在内容和体例上有所突破的外国教育史教材纷纷问世,如王天一等人编写的《外国教育史》上下册,戴本博等主编的《外国教育史》上中下册,吴式颖主编的《外国教育史简编》等。这时期集大成之作是由滕大春主编的六卷本《外国教育通史》,它是由我国知名外国教育史专家学者集体编撰的一部学术巨著,在突破西方中心论、摆脱“左”的模式的影响、强调各国文化教育交流的意义、充分发挥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功能等方面,均产生了较大影响。
除了通史类著作,各种专题史、断代史、国别史著作以及资料汇编纷纷出版,较有影响的有《外国教育家评传》、《西方教育思想史》(共有三个版本)、《美国教育史》、《日本教育史》、《英国教育史》、《外国古代教育史》、《外国近代教育史》、《外国现代教育史》、《外国学前教育史》、《外国幼儿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世界教育名著通览》、《外国教育发展史料选粹》等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批外国教育史专业博士论文(专题史)的出版,代表了我国新一代青年学者的学术水平。如《近代欧洲对美国教育的影响》、《社会转型与教育变革——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研究》、《杜威教育思想引论》、《欧美国民教育理论探源》、《日本教育现代化的历史基础》、《日本近代职业教育发展研究》等等。据估计,1978~1996年的18年中,外国教育史书籍的出版和论文的发表,超过1949~1977年28年中的成果10倍以上,这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春风。我们可以将1978年以后十多年时间看作是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第二个高峰期。遗憾的是此次高峰期没有延续多久,90年代以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已陷入全面危机之中。
将前后两次高峰期进行比较,颇能说明一些问题。虽然从成果数量上看,八九十年代远远多于二三十年代,但大多数成果的水平并没有明显提高,标志性的成果不多。相反,重复劳动、急功近利的产品并非罕见。史料建设薄弱,翻译工作遭冷落,二三十年代尚翻译出版了一批国外教育史专著,而八九十年代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本。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内容和体系亦没有重大突破。以唯物史观指导教育史研究,这是二三十年代所没有的,但效果如何,实难评判,真正有创见的成果不多。相反,片面化、机械化、生搬硬套的现象时有所见。学科研究的方法几乎没有变化,仍是沿用几十年不变的传统方法。其他学科的最新研究进展和成果,国外教育史学科的新变化,似乎与我们关系不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八九十年代的第二次高峰期只是二三十年代第一次高峰期的复兴。由于学科本身没有多少变革和创新,经过短暂的繁荣,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机和困境。世纪之交的今天,正是此次危机的关口。如何摆脱危机,使外国教育史学科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教育史研究者的神圣使命。
二、新世纪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断想
我们要正视当前的危机,但更要对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前景充满信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新世纪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今后,我们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
(一)充分认识外国教育史学科的意义和功能
有一种观点,认为教育史是“向后看”,与“教育要面向未来”是背道而驰的。这种割断历史的错误观点是极为荒谬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鉴古知今”、“往事不忘,今日之师”、“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读史使人明智”,这些古今中外的格言和警句是对历史学科的肯定,也是对教育史学科的肯定。只要人类存在教育,只要教育科学具有存在的价值,那么教育史的存在绝不是多余的。
研究教育史已有很长的历史,一世纪古罗马教育家昆体良在《雄辩术原理》一书中就包括了教育史的内容。但作为一门学科,教育史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当时各国推行义务教育,“客观上需要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经验作为指导”,[2]这说明教育史与生俱来就是为现实服务的。在19世纪末的美国,教育史又获益于这种理论,即“教师应该至少知道其本国学校制度的发展,并以此作为他们专业素养的一部分”,[3]教育史因此被纳入师范院校的课程中。1905年,美国教育史奠基人孟禄(P.Monroe)撰成《教育史教科书》,力图通过教育史“破除教育工作者把兴奋点仅仅放在近前的教育实践的狭隘性,从而使他们能从历史长河中领略教育的意义、本质、目标和过程。”[4]美国教育家杜威更是将教育史看作是教育科学的实验室,予以高度重视。他强调教育科学中一些长期性和根本性的课题,实验室是无能为力的,若借助历史探索却能得出结论。巴茨(P.F.Butts)在《教育文化史》一书中说:“研究教育史,就其本身而言,是不能解决目前的实际问题的;但它使我们更为聪明地解决目前的实际问题。”“这是因为研究教育史可以帮助我们看出目前的重要问题是什么,这些重要问题是怎样出现的,过去曾怎样解决的,过去解决的办法能否用来解决目前的问题。”[5]
毫不夸张地说,今天我们面临的重大教育问题,几乎都无法与教育史截然分开。举例来说,我国当前提倡的素质教育理论决非空穴来风,它实际上与二千多年来人们所追求的和谐发展和全面发展教育是一脉相承的。翻开教育史著作,我们可以找出和谐发展和全面发展教育思想的线索。该理论最早由古希腊思想家提出,后由人文主义教育家继承和发扬,再由欧文奠定理论基础,最终由马克思发扬光大。再如,关于传授知识和发展能力的关系问题,几百年前就开始了形式教育和实质教育的争论,洛克、赫尔巴特、斯宾塞等大思想家、教育家都曾参与这场争论,争论双方各执一端,难有定论。其实,我们在当前的教育现实中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究竟两者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孰优孰劣,孰对孰错,完全可以从教育史中寻找答案。
我们的近邻日本对教育史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我国。日本学者认为,教育史能够直接为教育决策和教育改革服务。在他们看来,不重视历史研究,只着眼于现状,无异于本末倒置。因此日本许多研究教育的学者都通晓西洋教育史。日本教育史学会有2000多会员,遍及大中小学,其中近一半人专门从事教育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教育史学会的会员数大大多于比较教育学会。不少人专门致力于研究卢梭、裴斯泰洛齐、杜威,甚至陶行知也成为日本学者研究的热门人物。
教育史学科的意义是毋庸赘言的。
(二)继承已有成果,不断创新,不断完善外国教育史学科
老一辈学者在外国教育史领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为我们继续研究打下了基础。新一代的外国教育史学者应沿着他们的足迹,继续探索,不断创新。
创新,是新世纪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关键,惟有创新,外国教育史学科才能摆脱当前的危机,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创新绝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我们做大量扎实的工作。首先,我们要大力加强史料建设。研究历史,离不开史料;研究外国教育史,同样离不开史料。多年来,史料建设一直是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它也是制约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障碍之一。解决了史料问题,外国教育史研究才可能生存发展。其次,由于外国教育史学科的特殊性,需要直接引入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必要的拿来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战后欧美教育史研究异常活跃,除了传统教育史学,还有以克雷明(L.Cremin)为代表的“相互作用论”的教育史观,以卡次(M.Katz)为代表的激进派教育史思潮。可惜他们的代表作至今没有中译本,甚至一些优秀的传统教育史学著作,如巴茨的《教育文化史》、鲍文(J.Bowen)的《西洋教育史》也没有唤起我们翻译的兴趣。再次,我们要借鉴国外教育史研究的新方法,改变传统定性的描述方法。二战以来,教育史跨学科研究、比较研究、系统论与教育史的结合,对传统方法产生了根本变革,但我们过去在研究中很少吸收和借用。总之,尽管当代国外教育史研究异彩纷呈,方法更新,成果倍出,但我们仍固守传统的模式和方法,只有个别学者吸收了部分成果。没有新资料,没有新方法,固步自封,数十年甚至百年不变,外国教育史学科不陷入危机才怪呢?
(三)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实现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本土化
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国际交流。近年来我国教育史界很少举办国际性的研讨会,我们的学者也很少有机会赴国外参加国际性的教育史学术会议,我们几乎处在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我们不知道当前国外教育史学者的研究动向,不知道国际教育史研究的最新发展。1982年,滕大春先生在《华东师大学报》发表了《战后美国教育史上的流派和论战》一文,近20年后,我们对国外教育史发展的了解仍停留在原来的水平,我们几乎没有获取任何新的信息。美国教育史界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有什么新变化,我们茫然不知。其他国家的进展,我们所知更少。根本原因是我们太闭塞、交流太少。同样是研究外国教育,比较教育学在国际交流上做了更多的努力,几乎每次会议均邀请国际学者参加,赴国外研修的学者也大大多于教育史界。外国教育史学科要摆脱目前的困境,重振旗鼓,必须首先打开国际交流的大门。
当然,学习外国,要立足中国,学习外国的目的是为我所用,中国特色的外国教育史学科要以中国为中心,其研究的内容要根据中国的需要有所偏重、取舍,为中国当代教育发展和改革服务。“现实性”、“洋为中用”应是我们坚持不懈的追求。千万不可一味追求西方的学术标准和指标,盲目模仿,失去我们自己的特色。“先借鉴、继超越”,[6]是值得到充分肯定的策略。外国教育史虽然是研究外国的东西,但最终目标是既要国际化,又要本土化。
(四)建立重点研究基地,巩固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学术阵地
外国教育史学界以往已有很成功的合作经历,如《外国教育通史》、《外国教育家评传》以及即将出版的《外国教育思想通史》,均是全国教育史学者合作研究的成果。这种合作研究能够弥补外国教育史学科力量的不足,发挥学术带头人的优势,共同提高学术水平,但这种合作做得还远远不够。从历史上看,我们已形成了几个颇具特色的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学术阵地,如北师大、华东师大、河北大学、杭州大学、华中师大、东北师大,其中河北大学、北师大已先后独立培养出十余名外国教育史专业的博士,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今后仍需重点扶持和巩固这些已有阵地。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试图网罗更多的人加入外国教育史研究队伍是不易的。在人员较少的情况下,我们更应提倡合作研究、学术交流、资源共享,避免或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劳动,集中人力物力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以发挥最大效益。研究外国教育史光靠英语是不够的,我们要注意吸收通晓其他语种的学者加入我们的队伍。
由于种种原因,迄今我国教育史学科没有自己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这是教育史界的悲哀,泱泱大国,五千年的文明,儒家文化发源地,竟没有自己的教育史刊物。我们已经迈入新千年,教育史杂志的公开发行莫非还要等上一千年吗?
(五)加强外国教育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合作
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存在严重的自我封闭现象,今后应加大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和合作,借鉴其他学科的新方法。
过去中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虽属同一学会,但两门学科的交流极少,研究呈各自独立的局面,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如果我们能在中外教育史的结合上找出更多的研究课题,将会大大扩展外国教育史学科的研究范围,提高人们对外国教育史功能的认识。其实在欧美,教育史是不被分为本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两个学科的。教育史家既通外国,也通本国,两者结合,才能相得益彰。一方面我们要加强中外教育史学者的沟通合作,另一方面我们要培养既能研究外国教育史,又能研究中国教育史的通才。
外国教育史学科还应加强和比较教育学科的合作,这两门学科原就是姊妹学科,许多学者既是教育史家又是比较教育学家,中外都有这样的大家。美国有的高校将教育史、比较教育和教育哲学三门学科组成一个学域,是很值得我们参考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及学科建设成绩喜人,比较教育学者在国际交流、扩大学科领域、探索研究方法上,都取得了较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外国教育史研究还要注意与历史学科的合作。教育史既是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也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二战以来,西方史学发生了重大转折,如从传统的描述性历史转向分析性历史,从靠个人在文献故纸堆中爬梳资料的手工作业方式改为引用自然科学研究的计量分析方法;新的史学流派如分析史学、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年鉴学派纷纷登台。史学研究的内容大大扩充了,史学研究的方法呈多样化趋势,这些都值得教育史学科借鉴,实际上有的史学方法已经被国外教育史学者所借用,如历史比较研究法和历史系统研究方法等等,并出现了一批重要的成果。
作为历史学科的一部分,教育史相对来说还是一门新的学科,它“是一门正在发展而不是已经完成的研究领域。”[3]21世纪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振兴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我们中青年一代学者的肩上。
收稿日期:2001-0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