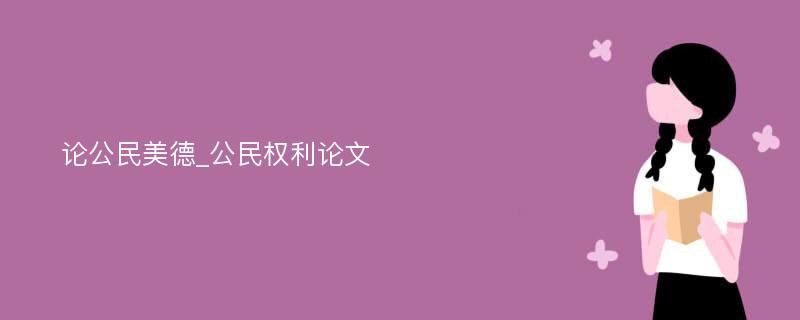
论公民美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德论文,公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公民美德:特征及其意义》一文中,笔者曾将政治性和公共性理解为公民美德的两大特征,并根据这一特征认为公民美德主要包涵爱国主义、公共参与、正义感、宽容和文明礼貌。(见吴俊)囿于篇幅,该文未对这些美德展开深入阐述。本文将围绕这些美德为什么是现代民主社会必备的公民美德,以及诸美德的内涵、美德实践面临的困境和实现的条件等问题,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一、正义感
正义既表现为制度,也表现为美德。从根本上说,制度的正义体现于对公民权利和公民义务的公正分配,美德的正义则是公民对这一公正分配的承诺和践行。在正义的制度和美德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和关联。这一方面表现为罗尔斯对个体正义感源自正义环境的论证,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如麦金太尔所说的:“只有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才可能了解如何运用法则”。(MacIntyre,p.158)其实,不仅正义法则的运用依赖于公民的正义美德,而且正义制度的设计、运行和维护也离不开设计者、操作者和维护者的正义感。因为只有心存正义之人才能设计出正义的制度,才能按照正义的原则来实施正义制度,才会遵守正义的制度。所以,正义制度只有对那些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来说才是充分有效的。
作为公民美德的正义,它表现为公民对权利和义务的均衡践履——得其应得,付其应付;既不能得其应得而不付其应付,也不能因为其所得而影响他人之所得。因为人们生活在一个互尽义务的社会中而实现互惠。如果人们放弃义务,利益便无从获取。在利益获取与义务承受之间保持基本的平衡,尽自己的本分而不伤害他人,乃是正义的最基本表现。所以,正义感是公民在正义原则的指引下所形成的对均衡的公民权利与义务的意识和情感。正义感“使公民能够理解、运用并在行动上遵循理性的正义原则”。(罗尔斯,2000年,第109页)当公民未能得其应得时,正义感会引发不满之情;得其应得时则会满意。当他人遭遇不公时,正义感会转化为对受害者的同情以及对伤害者的愤恨。当自己不幸成为不义之行的实施者时,正义感则表现为内疚和忏悔。正义感还表现为对正义行为的渴望,对不义之举的厌恶,以及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认同和期待。
之所以将正义(感)视为公民美德,因为它是一种具有普遍公共性的底线美德。正义的基础性表现为它是道德的基准,公民是按照正义与否来判断个人行为的道德与否的。斯密通过对正义与仁慈的比较,揭示了正义对社会存在的根本性。在斯密看来,“虽然没有仁慈之心,社会也可以存在于一种不很令人愉快的状态之中,但是不义行为的盛行却肯定会彻底毁掉它……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斯密,第109页)正义是社会存在的根基,因而它是公民必须遵守的强制性美德。正义感确乎是公民应该具备的一种最起码、最普遍的社会美德:没有起码的正义感,公民就失去了判断善恶的方向和标准,无法理解为什么只有在社会正义允许的范围内行使自由才是有意义的,从而也不可能在正义的范围内选择自己的价值理想和生活方式。正义还是公民与公民之间进行公共对话、裁辨并解决分歧的底线,公共舆论的合理边界由正义维系。同样,只有以正义为边界,公民对异己的言论和举止的宽容才不至于演化为对非正义的纵容。可见,作为道德的基础,正义感顺理成章地成为公民的其他美德诸如信任、仁爱、宽容等实现的前提。
罗尔斯将正义感实现的条件理解为正义的环境。环境之正义不仅包括正义的社会制度安排,还包括在正义制度中生存、因享有正义制度的好处而认同并遵守正义制度的社会成员。即是说,当且仅当人们生活于公正的制度之中,并且所有人都遵守正义的制度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时,人们才会普遍产生按照正义原则行动的欲望。(参见罗尔斯,1998年,第441、460、461页)罗尔斯确认了正义感形成的三个条件:第一,公正的制度得到认可。在公共生活日趋凸显、陌生人之间的交往日益普遍的当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将主要以制度为中介。只有当社会成员确认他们所依赖的社会制度是公正的时候,他们才愿意对制度所规定的内容作出承诺,才能意识并履行他们遵守制度的义务。第二,制度被正义地执行。只有制度被公正地实施,才能避免制度的虚假和失效。如果非正义行为得不到及时、公正的惩罚,正义之人得不到公正的对待,受害者和广大的社会旁观者势必产生“正义的愤怒和义愤”。这将严重打击人们按正义原则行事的愿望,产生社会正义危机。第三,受益于正义制度的人们普遍遵守正义的制度。如果说仁爱是一种高尚的美德,它的实施不以利益交换为动机,即使在预计对方不予回报的情况下仁爱者依然行善,因而是无条件的话,那么,人们产生正义的动机和行为则是有条件的,即以他人同样遵守正义制度为前提。那些在正义制度中生活并获益的“搭便车”者,由于违背了自己应履行的“抽象承诺”,他们对制度的不遵守让人们担心会损害自己的利益。所以,只有所有人都遵守正义的制度,才能让按正义规则行事的人们没有后顾之忧。因此,在正义形成的条件中,除了社会拥有公正的制度外,公民将他人视为平等如己的利益需求者、正视他人的利益和需要,也非常重要。此外,当正义愿望的实现存在风险、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时,正义行为的动机则会减弱。另一种情形是,当追求某种东西(比如财富、权势)的欲望过于强烈,压倒按照正义原则行事的愿望时,正义行为的出场也会变得较为艰难。
对于任何一个理性的人而言,个人利益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联是毋庸置疑的。任何不义之行必然有损于社会从而最终有损于个人。为此,正义之人不仅要确保自己不做不义之事,并且还要想方设法去阻止那些不义之举的发生。可见,尽管正义感是一种公民必须拥有的具有普遍公共性的基础美德,但当正义感的强化达到为了捍卫社会正义而不顾一切、甚至可以付出生命代价的程度时,正义则成为了一种极为高尚的公民美德。
二、文明礼貌
美德是内外之合,如郑玄所释,“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周礼·地官》)。当我们把公民美德理解为公民个体在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展现出的卓越言行时,那么,文明礼貌、得体、高贵、优雅、谦逊等公民风范均内蕴其中。作为一种公民美德,社会意义上的文明礼貌是指公民在公共生活中对他人的态度以及在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中体现出的行为适度和优雅得体。政治意义上的文明礼貌主要表现为公民在言论表达上的约束,以保证有争论的政治对话得以文明地进行。文明礼貌的最直接表现是公民对社会规范、法律规则的遵守①,其蕴含着公民的规则意识。毋庸讳言,一个社会的公民所表现出的礼貌程度体现了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社会公共化的发展趋势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越来越趋向于一个陌生人社会,因而如何与陌生人相处成为当代公民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面对没有亲密关系的陌生人或非亲近者,文明礼貌是基本的相与之道。尊敬陌生人,承认并尊重他人拥有和自己一样的平等地位和权利,对他人表示友好、善意,是文明礼貌之本。在面对因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等因素遭受歧视的人群时,公民尤其负有礼貌待之的责任。威尔·金里卡在阐述“自由主义的公民品质”的最基本要求时,特别将礼仪和非歧视性原则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商业机构雇佣黑人,为黑人顾客提供礼貌周到的服务,让黑人确确实实地感受到与白人一样的礼遇和欢迎,这就是礼貌。(参见金里卡,第329-331页)礼貌要求尊重他人隐私,“尤其不要侵犯性地刺探他人是如何生活的”;在不被恳请的情况下,“轻易表达对他人生活的评价或建议他们如何改进的意见”,不是文明礼貌的表现。(Calhoun,p.58)有些人可能具有一些不令人满意的特质,诸如呆板、反应慢、爱管闲事等,有礼貌的人出于对他人感受的考虑,往往不会主动表达对这些特征的评价。在某种意义上,礼貌、得体是对骄傲和自负或是过好的自我感觉的控制。当公民不太友好地对待陌生人时,表明他在言论和行动上过于随意,没有受到礼貌职责的限制。一个由众多没有自我约束的个人组成的社会是野蛮的。自我修养、自我约束是文明礼貌的基石。礼貌和得体常常在公民日常生活的细节处展现出来,诸如称呼、打电话、用餐、约会、乘车、馈赠,以及在剧院、图书馆、公园等公共场所应有的礼仪。文明礼貌还包括如何表示歉意、怎样保留对方的面子、避免让对方难堪、如何得体地化解尴尬,等等。总之,文明礼貌意在表示友好,营造融洽和谐的社会交往氛围。公民普遍的文明礼貌可以改善整个社会的人际状态,任何人都能从文明礼貌的交往中获得舒适、良好的生活感受。文明礼貌将公民与其可能遇到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友好地联系在一起,使社会共同生活趋向于更加和谐、美好。
在一个各种学说、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多元并存的民主社会中,文明礼貌与宽容、理性、平等、尊重等美德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公民适应于民主生活的基本态度和义务。按照罗尔斯的理解,当各种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无法调和与多元并存成为自由民主社会的恒久现象时,公民的理想强加给公民道德的“不是一种法律的义务”,而是文明礼貌的义务。这一义务要求公民相互间解释清楚他们所支持的政策“怎样才能获得公共理性之政治价值的支持”。(参见罗尔斯,2000年,第230页)在相互解释的过程中,当人们面对深刻的歧见时,必须通过理性对话寻求妥协和融合。文明礼貌是让有争论的理性对话能够以文明的方式持续下去的政治伦理条件。礼貌要求对话者在言论上有所节制,无论是在倾听、表达还是辩驳阶段,那些不利于理性对话之顺利进行的言辞均应当受到约束。对话者应通过礼貌来约束自己过于自负的表达,不是以尖酸、刻薄、具有讽刺性的语言和过激的方式,而是尽可能以大家更易接受的平和、优雅、得体的方式展示自己的观点。即便是不同意见之间的公共辩驳,文明礼貌也要求人们将侮辱、谩骂、攻击性语言拒之门外。“礼貌调控着争论,以至于对话能够在那些不同意见者之间继续而不是中断。”(Calhoun,p.269)文明礼貌的行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如果每个人都运用自己的个人标准去判断文明礼貌,那么,关于什么是文明礼貌的行为的理解则会歧义丛生。任何一个社会的规范,都是对该社会成员所共享的道德理解的抽象概括和反映。显然,社会共享的文明礼貌之观念也必然内蕴其中。如果说社会共享的规范规定了在特定场合下什么是文明礼貌、什么是野蛮粗鄙,那么文明礼貌则要求人们首先从遵守特定的社会规范开始。
文明礼貌作为一种公共美德的困境在于:一个彬彬有礼的纳粹分子让人们认为礼貌是一种具有伪善性的装饰。它是一种“纯形式的美德”,一种“美德的表象”。(孔特-斯蓬维尔,第1页)显然,在正义的不礼貌者和礼貌的不正义者之间,与其过于礼貌而不正义,不如过于正义而不礼貌。可见,与正义相比,文明礼貌是一种相对次要的美德。它的次要性和脆弱性表明,公民仅仅拥有行为外表上的文明礼貌是远远不够的!正义才是支撑文明礼貌大厦的根基。与其他美德相比,文明礼貌与礼节或得体的举止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文明礼貌的另一特殊性在于:它在不同的风俗文化中有不同的表达:在这种文化中视为文明礼貌的举止,移至另一种文化中则可能不再享有文明的称誉。实际上,真正的文明礼貌表现为得体的举止,但又不仅仅局限于得体的举止。可见,言谈举止的背后隐含的是不可见的道德因素,即对他人感受的考虑,对他人出自内心的尊重、宽容和体谅。
三、宽容
一个民主的社会是一个公共言论自由、因而歧义重生的社会。面对争论和冲突,宽容是和平解决的惟一方式。健康而成熟的公民社会必然以公民对政治权力的有效监督、对他人公共言论自由的理性尊重为前提。没有宽容,争论会升级为谩骂或人身攻击,从而导致暴力。没有宽容,公共讨论将失去确保畅所欲言的伦理资源,从而失去实际可行的空间,这样的社会不能被称为公民社会。因而,宽容成为社会公共领域中的一种必要美德。当代社会存在着文化多元主义的发展趋势,面对种族、性别、移民、宗教、弱势群体等群体权利的诉求,宽容乃是处于价值多元情境中的公民应采取的明智、通达的态度。没有了宽容,多元将难以维持。宽容是一种在多元差异中共存的基本方式和态度。
宽容为什么必要?人的多样性是宽容之所以必要的客观前提。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既不可复制也不可取代。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上的多样性,导致彼此间的差异是不可取消的。人的局限性则是宽容之所以必要的主观条件。人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去看待周边的人或事,而自我的无知以及认知理解能力的有限使得自我得出的判断可能为假。对他者的宽容则为承认人的认知和行为的可错性提供了空间。当然,宽容不是一种无原则的退让和放弃,它是有底线的。宽容以正义为边界,所以,对不当行为或过错行为的容忍和退让应以该行为不伤害社会和他人为前提。如果宽容超出正义原则而演变为对恶的纵容,那么这种宽容是变了质的,并将使宽容本身受到极大的威胁。
作为一种公民美德,宽容的主体是个人。积极意义上的宽容是对他人自主判断和选择的承认,消极意义上的宽容则是对异己言论、行为、生活方式的不干涉。“宽容是指一个人虽然具有必要的权力和知识,但是对自己不赞成的行为也不进行阻止、妨碍或干涉的审慎选择。”(米勒等主编,第820页)从这一定义中可以判断:第一,宽容的对象是他者。第二,宽容是强者(有力者)的美德,弱者的“宽容”是力所不及情形下无奈的选择。第三,宽容的前提是存在差异。如果被宽容者的言论、行为与自己无异,宽容者既不会产生道德意义上的不赞成,也不会产生情感上的不喜欢,那就无需宽容。由此可以认为,宽容是有条件的。反感和有能力去干涉却没有干涉,是宽容的要件。作为一种公民美德,“宽容要求我们接受人们,甚至当我们很不赞同他们的做法时也要允许他们实践。因而,宽容包含着一种中间态度,此种态度处于完全接受与坚决反对之间。”(斯坎伦,第210页)公民持守中道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公共空间的和谐与稳定,其前提是将他人视为与自己一样的自由和平等的人。
自由、多元和民主的社会需要宽容,但让宽容成为一种普遍的常态却十分困难。它对社会和个人提出了看似简单却并不容易达到的基本要求。对社会而言,社会制度环境必须民主、开放,具有高度的公共性。社会只有具备深厚的公共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基础,宽容才有可能成为公民的普遍美德。在一个由宽容的政府所创造的宽容的制度环境中,公民对政府决策的监督以及公民不服从行为才被鼓励。对公民个体而言,让宽容成为美德,公民首先要在认知上具备“人具有多样性而自我又具有局限性”的观念;其次,要具备“世界是我们的”共享意识,这样公民才有可能为他人存在、他人言说和行为留有空间;第三,要具有相互的善意,诸如同情、合作和友谊等。
作为公民美德的宽容常常面临各种困境。困境之一表现为宽容与平等之间的紧张。能力是宽容者的条件之一。厚德才能载物,宽容者必须是道德上的强者,才能克制自己,容忍他人。在宽容者与被宽容者两个权利主体之间,宽容意味着宽容者对特定权利的放弃。宽容原本产生于对不同主体之间平等地位的尊重。然而,“大人不计小人过”的宽容则预示着人格地位的不平等。被宽容者在获益的同时,感受到的是宽容者对自己的道德低估。宽容面临的困境之二表现为宽容与信仰唯一之间的冲突。现实生活中的宗教信仰冲突常常难以调和,宗教徒往往是在对异教的斗争中保持对宗教信仰的虔诚。在斯蒂芬·马西度(Stephen Macedo)看来,“对宗教多样性的强制学习是宽容的基本”;但在威廉·高尔斯通(William Galston)看来,这种强制学习对自尊是不必要的,“对来自于虔诚、保守家庭的孩子的自尊而言,宗教多样性的强制学习就是一个令人忧伤的威胁”。(Callan,p.213)然而,学习并熟悉世界的多样化宗教和其他文化、了解本国的宗教信仰系统及日常生活中的宗教表达是必需的,这有利于对多元文化形成正确的评价,为培育和谐的宽容氛围创造条件。困境之三表现为宽容对政治参与之激情的消解。麦克·沃尔泽(Michael Walzer)认为宽容与公民参与这“两类美德之间多少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江宜桦,第237页)宽容意味着某种妥协,对己见的不坚持往往让宽容者没有足够的政治激情。而对政府行为、决策的适当宽容则意味着公民批判性的弱化,它同样会影响公民的参与热情。尽管宽容之实现面临诸多困境,但在多元格局成为社会的长久之态的情景下,为了使公民既能保有各自不同的宗教观念、生活方式,又能稳定、和谐地共处于生活共同体中,宽容仍是一种必要的美德。
四、爱国主义
理性的爱国主义是以公民的政治认同为基本条件的。当国家合理的体制结构能够确保公民的权利和福利时,理性的公民必认可其国家尊严。这是公民对国家产生的根本政治认同。以国家的正当性为基础而形成的政治认同,使公民对国家持有基本的信任;只有通过公民自我理性认知的转化而非强制灌输,才有可能形成真实、健全的爱国主义。国家宪政制度的正当合法性以及公民对它的普遍认同,是爱国主义成为公民美德的基本条件。
作为一种公民美德,爱国主义对公民在认知和情感等方面提出了特定的要求。爱国主义要求公民必须具备这样的理解力:任何公民都是国家的组成部分并与国家具有政治同一性;离开了所属的国家,公民的身份便无从确认。个体的公民身份决定了他与同胞、国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政治伦理共同体。通过相互依赖及共享的文化和制度,公民与同胞对创造国家繁荣这一事业具有同等的、不可推卸的义务。爱国主义不仅是对生存空间的热爱,同样的国家历史和文化让同一疆域内的不同公民拥有了共同的语言、文化、心理、习俗和价值观念,共享的文明和文化让不同的公民对同一个国家有了共同的情感依恋和归属。这种依恋和归属滋生出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之情。
爱国意味着要承认民族历史中“至少有某种东西是宝贵的”。(贝尔,第131页)当然,这种“宝贵的东西”并不一定比其他民族中人们认为“宝贵的东西”更优秀。爱国主义不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它不是唯我独尊的自大和自负,也不是欲把优越强加给他者的霸权主义或者漠视他者的简单的排他主义。它只是共同体成员对自己所熟悉的生存空间、文化、生活方式的眷恋,以及为了维护和发展这一空间而奋斗的精神和实践。爱国主义要求一个人既要勇于承认他国的优点,也要敢于正视自己国家的不足。公民应当在正确认识国家的历史和政治的基础上,客观评价其合法性和正当性,正视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弱点。实际上,公民对政治不良决策的批判本身就表现出对政治共同体运行良好与否的关切;在这个意义上,反对恶法的公民不服从也应被视为爱国主义的表现。
有一种观念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将会日益模糊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世界将进入一个后民族国家的时代,公民资格不再为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成员所独享,世界公民将成为全球化时代人们的身份标志。然而,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人们的民族国家意识并不是越来越弱,而是越来越强。当民族国家遭遇险境时,公民维护民族国家的意识最为强烈,这在战时清晰可见。在和平时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日渐淡出,然而当人们可能在多民族国家的融合中日渐丧失本民族国家长期积淀的习俗时,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又被凸显出来。当一个国家置身于另一个规模更大的联盟之中时,消失的恐惧与自我保存的冲动混合在一起,它激发起公民的民族国家意识,使其充满对民族国家的深深眷恋及对其命运的深深关切。对大多数人而言,休戚与共、命运共通的范围“通常不超过国家”(同上,第139页),在国际范围内还很难形成命运共通感。欧洲联盟强调以欧洲为整体的爱国主义,然而,其公民的爱国主义却仍然局限于一国之内。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对人类所有的人都负有道德责任。在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看来,在规模上,民族(国家)是一个最合适的忠诚对象,它既可抵御超越民族国家的跨国联盟,又可与民族内更小规模的群体进行抗争。它面临的最大竞争对手是阶级;只有当公民无限忠诚于阶级时,才有可能改变公民对民族的忠诚度。(参见尼布尔,第73-76页)
五、公共参与
公共参与的意愿和行为不仅将臣民和公民区分开来,还将消极公民和积极公民区别开来。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公共参与就是界定实质性公民资格的标准。不仅如此,一些民主理论家们还将大多数公民是否充分参与到政治系统中去、进而影响社会改造进程,看作民主事业是否实现的标志。他们强调,任何一个政体若想实现并保持民主,就需要公民积极参与国家事务,需要他们具有公共参与所必需的知识、能力以及广泛的公民责任感。公民自治是政治民主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公民通过政治参与,表达自己的见解,倾听他人的意见,检审公共决策。公共参与既是实现公民自治的重要途径,又是其前提条件。
与权利相比,作为公民美德的公共参与更多地被理解为义务和责任。人们通常认为责任来源有二:一是与特殊身份有关,二是与所享受的权利相对。“我是公民”,因“生而入其中”,这种与生俱来的身份决定了公民所肩负的责任既不可剥夺也不可逃避。同时,在一个公正的社会中,一个人享受了多少权利就要承担多少责任;我们应以与关注权利相匹配的态度来承担责任,这是正义的基本内涵。因此,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既是公民理应承担的责任,也是公民的必要美德,更是公民取得实质性公民资格的前提条件。
公共参与的意义在于监督公共权力的使用,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它是一项需要参与者智勇双全的公共活动,因而必须辅之以勇气、商谈等美德才能实现。当阿伦特将公共参与公共事物所展现的卓越言行视为公民美德时,她也将公民跨越熟悉的私人领域、投入冒险的公共领域所需的勇气,认定为公民“政治之美德”的表现。(Arendt,p.36)从快乐、熟悉、可预见的私人领域到陌生的公共领域,从个人身份转化为公共身份,需要公民付出勇气、胆识。此外,公民以交谈、论辩的方式发表意见,投入公共领域,实现公共参与,因此,公共参与美德的展示必须以商谈为基础。商谈既作为一种技能又作为一种美德,包含于公共参与之中。如果我们把商谈、公共对话视为公共参与的一种必要手段,那么商谈作为一种衍生性美德,应该成为最受公民瞩目的美德。构成商谈、公共对话美德的三个基本要素是:以他人最易理解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回答他人的质疑;倾听并尽可能地理解他人最想表达的意思;让公共论辩以文明的方式进行并以相互妥协、达成基本共识而告终。
让公共参与成为全体公民普遍的美德追求,需要社会创造适当的条件。其一,对于为衣食住行奔波劳碌、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公民而言,把用于谋取生活资源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政治生活较为艰难,所以,社会经济发展应达到保障绝大多数公民拥有积极参与之时间和精力的程度。其二,社会教育为公民提供实行有效参与的必备能力,诸如适当的知识储备,特定的公共讨论技能,在思维上具备理性判断、批判的特质,合作的能力等。其三,成熟的参与制度是保障公共参与的重要因素。当公民发现自己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很有限时,参与的积极性就会下降。由于制度的原因所引发的公民在参与过程中的挫折感,将在最大程度上影响公民后续参与的积极性。其四,公民文化应有利于公民资格意识的开启和孕育。在公民文化的熏陶下,公民应获得这样的意识:公共参与是公民资格的实质性条件,它是防止强制和奴役的必要手段,也是确保公民权利的基本条件。我们应该用与维护权利同等的态度来履行这一义务。其五,社会允诺充分的政治传播自由。如果公民发表政论需要冒风险,他们就无法获得政治传播的安全感,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公民政治传播的愿望。所以,社会应该容许公民在人际间(不仅局限于家庭成员之间)轻松地发表政见。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和多大范围的人群中进行政治交流,显示了一个社会政治传播的自由度和政治信息的透明度。
注释:
①在《正义论》中,罗尔斯认为,公民应具有一种文明礼貌的政治义务,即不能以社会制度设计的缺陷为借口而不遵守制度;当然,前提是制度的不正义缺陷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即是说,公民应当认可并遵守有一定缺陷的制度,这是文明礼貌赋予公民的义务。(参见罗尔斯,1988年,第344页)在《文明礼貌的美德》("The virtue of civility")一文中,卡尔霍恩探讨了两种不同的礼貌:“政治的文明礼貌”(" political civility")和“优雅的文明礼貌”("polite civility")。(Calhoun,pp.255-259)其中对“政治的文明礼貌”的阐述,表达了与罗尔斯大致相近的看法——对法律、规范的遵守是文明礼貌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