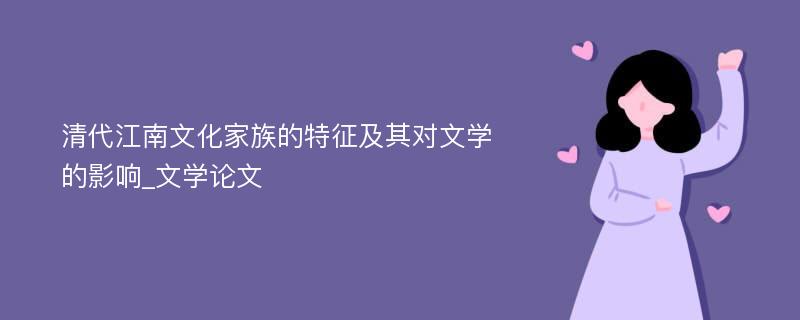
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特征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论文,清代论文,其对论文,特征论文,家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代江南文化家族是中国古代文化家族的典型。它集中了中古以来一般文化家族所具有的重视家学、以儒为业、科举兴盛、世代簪缨、一门风雅等特点,同时由于文化家族不仅重视联姻的门第层次,而且重视其文化层次,知识女性的角色意义非常明显,母系教育在家族中能够全面展开,发挥出培养学术和文学人才的重要作用。清代江南文化家族体现出的一系列特点,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在江南这个经济文化特别发达地区的影响力,也表现出江南士绅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支撑作用以及清代文化创造与文学创作民间化的趋势。以下对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特征及其与文学的关系从四个方面加以阐发。
一、重视家学,形成家族学术和文学艺术链
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家学传承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家学指家族传承的专门学术性的私学,广义的家学指诗书传家的文学艺术创造活动。
先论狭义的家学。学术文化发展到清代,呈现出蔚然大观之势,江南更是儒林茂峻、大师辈出,学术文化俨然有独步天下之势,尤其乾嘉考据学成就辉煌,形成了影响至巨的学术风格。为了实现思想文化方面的钳制,清王朝对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的风气遏止甚严,尤其在清初,大规模的群聚生徒、讲学议政的现象几乎荡然无存,因此书院聚徒宣讲的形式被私人闭门钻研所代替,博学之士往往于庭户之中沉潜经史,让思想腾跃于相对封闭的私人空间。这种政治文化生态,恰恰成为锻造“家族学术文化链”的特殊环境。有清一代江南家学兴盛,父子兄弟、亲戚族人、师生砚友往往形成学派、发源承流,究其缘由,除江南文化层垒的传统因素外,亦可以从这一客观环境中得到解释。
“家族学术文化链”是指家族学术传承生生不息的状态,是由不断出现的家族学术人才和学术成果中体现出的人文精神气度和持续影响构成。清代江南学术世家甚多,且各具一定的学术专业范围,如阳湖洪亮吉家族虽以诗学、经史、音韵、训诂、地理之学无书不窥,然于舆地、方志之学颇多研究,于疆域沿革最称专门,并以之传家。亮吉著有《西夏国志》十六卷、《补三国疆域志》十六卷、《东晋疆域志》四卷、《十六国疆域志》十六卷等,其长子洪饴孙著有《梁书州郡志》三卷及《汉书地理志考证》等,次子洪符孙著有《禹贡地名集说》二卷、《鄢陵县志》十八卷、《禹州志》二十六卷等,幼子洪璠孙著有《补梁疆域志》四卷及《战国地名备考》、《汉魏六朝隋唐地理书目考证》等,洪氏家族对舆地学的贡献在乾嘉之际可谓十分突出。另常州庄存与的祖父庄绛,“平生肆力于古,参订经史,凡天文、疆索、九流百家之书,靡勿穿贯”①,至庄存与复兴千年不传之学,成就为清代今文经学之大师。其学术思想在家族中深深驻根,从子庄述祖、孙庄绶甲、族孙庄有可,俱在经学研究上取得重要成果,而刘逢禄、宋翔凤治今文经学,发挥微言大义,学问皆出于舅氏庄述祖。二人作为常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又传学于魏源、龚自珍,使常州家法得以弘扬。苏州戈载继承家传音韵之学的事例也很典型。其云:“自揣音韵之学,幼承庭训,尝见家君与钱竹汀先生讲论,娓娓不倦。家君著有《韵表互考》、《并韵表》、《韵类表》、《字母汇考》、《字母会韵纪要》诸书,余皆谨谨校录,故于韵学之源流、升降、异同、得失,颇窥门径。”②后来戈载著《词林正韵》考韵审音甚精,被吟坛奉为正宗,当归其家学渊源。
当然,清代江南最典型的“家族学术文化链”当首推东吴惠氏。此点前人多有指出,如梁章钜《退庵随笔》称:“本朝经学世家,以元和惠氏为第一。”《清史稿》惠周惕传云:“清二百余年谈汉儒之学者,必以东吴惠氏为首。”叶恭绰说:“吴中惠氏仍世传经,至清初元龙、半农两先生,益显于时,卓然为一代大师。松崖先生继之,著述宏富,沾溉尤广,谈经门第,海内殆无伦比。至今言经学师承及吴中文献者,必首及,乌呼其盛矣!”③
再论广义的家学。如果说“家族学术文化链”是体现一个家族在专门学术研究、知识传承方面的连贯性的话,那么与此平行的还有一条“家族文学艺术链”,这是广义的“诗书传家”传统的深远、持久的表现。江南,既是一片学术文化的沃土,又有为数众多的家族长期参与了文学艺术的创造,这些家族胚育涵演至明清时代,往往便成为诗书笔翰流播海内累世不绝的艺文家族了。
这条“家族文学艺术链”在吴江沈、叶两大家族中显现的特别明显,薛凤昌(1876-1944)《邃汉斋文存》有《吴江叶氏诗录序》云:
沈氏自太常而下,桥梓棣萼,并辔连镳,绵延至于十数世,而风流照耀,先后相望。若夫叶氏,自明中叶迄于清季,数百年间,几至代各有人,人各有集。若天寥(绍袁)、若已畦(燮)、若学山(舒颖)、若分干(舒璐)、若文竹(昉升)、若改吟(树枚),尤皆主骚坛,负重望。风雅之传,今犹未沫,何其盛也!
吴江叶氏只是一个典型代表而已,其实,江南千百年人文气息浓郁,艺文环境优雅,诗书之泽渊广流长,因此这样的数代艺文流传形成“文学艺术链”的家族不胜枚举。这里不妨再看一看苏州府的情形。沈德潜曾说:“嘉靖以还,人文蔚兴,以三不朽传者,甲于吴郡。”④冯桂芬也说:“国朝右文稽古,鸿儒硕学辈出相望,遂驾宋元明而上。而有开必先,实惟吾郡人为多。”⑤如吴江袁氏,一家机杼,同织文章,八代风骚,酝酿出吴中非凡声华。昆山叶氏自文庄(叶盛)以来,世以风雅相传,群从昆弟,多工吟咏。长洲文氏更堪称典型,杨绳武撰《文氏族谱续集序》:“吴中旧族以科第簪冕世其家者多有,而诗文笔翰,流布海内,累世不绝,则莫如文氏。”康熙间文含纂《文氏族谱续集》,其中专门辑录《历世载籍志》一卷,文含自序云:“吾宗自涞水府君(文洪)以文学起家,风流奕叶,代有著述。”另有苏州韩菼家族、缪彤家族、潘奕隽家族,累世文华灿然;王芑孙家族、彭定求家族世为文学,前后多达十几代。近古苏州地区,操觚染翰,同样代不乏人。这些艺文之家在修撰族谱时皆以数百年诗礼相传不绝,文采风流而骄傲,实际上他们所自诩的正是家学渊源有自,诗书之泽不竭。
二、以儒为业,为世代簪缨而投入科场竞争
所谓“儒业”有两重意义:一为符合传统经世治国道德理想的事业,一为穷究经书典籍的读书活动。其实这两重意义是相互关联的,前者可以看作是一般士人的目的,是对获得体制内身份的追求,也是其生命的价值体现,而后者是实现其目的和价值的过程。从这一角度看,隋唐以后的中国古代士人,多为业儒者,而明清两代的江南,除部分以山人、处士、隐士的名目自居者外,大部分士人皆习“儒业”。因此,以儒为业也就成为江南文化家族的显著特征之一。
既以儒为业,则必须以学文读书为上。这种学文读书不是一般的基础性教育,而是终身以为职志的从学。虽然江南文人书生之学文读书往往表现为一种带有审美意义的习气,但对于大多数士子来说,仍然有着通过读书课业以完成举业,而成为统治阶级体制内官宦的现实要求。因为只有这样,对个人而言,才能真正成为衣冠之族;对家族而言,才能世代簪缨,门楣光宠。
科举的内容从明初以来便有了全新的制度设计,而考试科目和要求规定得越清楚,士子们的功利取向就越明确,所求之善巧捷径就越具体。在江南,士子们充分利用坊间大量印行的程墨、房稿、行卷、社稿等“新科利器”,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所拟数十题,参照成稿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记诵熟习,以备考场之用,这种做法几成风习了。
但是文学世界中的科举却充满了悲剧的气氛。打开一部部清代江南士人遗存的文集,人们到处可见关于科举的辛酸的记载,表明清代江南士人的科举史是一部充满悲愤、写尽血泪的历史。这里我们不妨试读常熟冯舒的一首科举纪实诗——《府试日赠同试老翁》:
提携笔砚入吴门,举足欲前心不奈。是时九月正初一,晓雾梦梦风若簸。府官朱衣呵殿来,诸生龌龊七百个。吾亦其中当一人,俯首羞颜岂堪涴。须臾垩板看试题,下笔无能但深坐。传餐最笑声喧豗,不觉日光已西矬。强将蜡烛续残篇,老眼昏花书字大。誓将今日了今生,糠粃从兹免扬播。踉跄交卷迫欲出,门钥不启愁无那。腰酸背楚立未能,长叹声高疾于呼。⑥
科举考试注定是一场将大部分参与者无情牺牲的残酷的竞争,冯舒最终是举业大战中的败北者,而有清一代踯躅名场数十年最终仍然一布衣者简直是一个庞大得难以统计的数字。可是“多少文人空皓首”的现实并没有使清代江南文人停止趋竞的步伐,在棘闱“三条烛”下,始终燃烧着江南士人的希望,而对于来自文献之邦的才子们,清帝也采取了措施让“英雄入吾彀中”,其中树立沈德潜名宿晚达的典型,应是朝廷鼓励江南士人竞奔仕途的高招。
沈德潜三十岁时,已名声播扬,康熙四十六年三十五岁时,与友人结“城南诗社”,在吴门诗坛声华籍甚。但成人后走上科举之途竟一路艰难,当他六十岁已是宏览博识的大雅之士、海内成就很高的诗人和诗论家时,仍蹭蹬科场。尽管如此,自到六十七岁他仍不甘放弃举业,恰恰造化弄人,这次竟然成就了一场“江南老名士”晚遇弘历帝的大喜剧!乾隆五年他荣登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很快名重中枢,弘历帝夔龙接席,与之建立起所谓“以诗始,以诗终”的关系,“我爱德潜德,淳风抱古初”⑦等众多赞语,更使沈德潜隆遇至极,令天下文人惊羡。
沈德潜是否果真“晚达缘诗遇”?乾隆在颁谕中曾特别强调“沈德潜诚实谨厚,且怜其晚遇,是以稠叠加恩,以励老成积学之士,初不因进诗而优擢也”。这种说法将“老成积学”置于“诗缘”之上,显然有统治者笼络文人,尤其鼓励江南文人长期积学以备仕进的深心在。乾隆帝深知三吴两浙,为人才渊薮,因此使江南文人专意科举,向附清廷,便是一种必须实施的文化策略和政治策略。无论如何,沈德潜这样的“江南老名士”式的标志性的人物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旦让他走过科举的独木桥,再迭施恩霈,将对江南士人,乃至天下士人是一个多么强烈的信号!乾隆帝在清代诸帝中可谓精于权谋并谙熟中国传统文化,其初登帝位不久就制造了一个江南士人年近古稀叩开帝阍、极享恩宠的事件,是其为强化文化控制做出的“以儒业延儒生”的极富智慧的选择和宣示。
事实上,乾隆帝的选择和宣示确实是奏效的。对于沈德潜鸿才晚达,主眷特隆,当时海内夸为盛事,吴中传作美谈,作为毕生以儒为业,追求科举功名而终获成功的示范,对江南士族终生业儒,精研八股,屡抑屡进地求取仕进无疑是一种激励。据明清进士题名录统计,清代江南共考取进士4013人,占全国近15%。也就是说,全国每7个进士,就有一个出自江南⑧。如此高的比例,显然既与以儒为业的地域文化风气有关,也与最高统治者的鼓励有关。
三、一门风雅,女性创作尤成蔚然大观
一门风雅,反映出清代江南文化家族内部文人化的聚合状态,诗性的生存方式。它是上层文化家族的一批文学天才或痴情于文学者的聚集,对家族之外,这种聚集通过比较优势显示出家族人文的优越;对内而言,它使家族本身就可能成为产生艺文和消费艺文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具有血缘关系、婚嫁关系的家人甚至嫡系兄妹自成社群,相互唱和,并留下家族性的艺文文献。
在讨论江南文化家族时,不能不提及吴江沈氏家族。沈氏家族从有诗歌作品流传的沈奎起,因愈益众多的族人参与文学活动,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学世家,清初至雍正间最为兴盛。沈奎五世孙中有文学家10人,六世孙中有文学家30人,七世孙中有文学家36人,八世孙中有文学家28人,九世孙中有文学家16人,十世孙中有文学家8人,十一世孙有文学家5人⑨。整个家族历时几百年持久地参与到文学创作中,延续着家族文学的荣耀,后人盛赞曰:“风雅之集,萃于一家,海内所希有也。”⑩与沈氏家族世代姻娅的吴江叶家,也是令晖道蕴,萃于一门的典型。这是一个充满文学气氛和民主精神的家庭,一家姊弟,相对几席,半世手足,朝夕吁吟。至今存留着丰富的家族文学文献,见证着叶氏家族文学创作的辉煌岁月。
另一个经典性的例证是松江宋(徵璧)氏家族。在宋氏兄弟叔侄唱和而结集的《倡和诗余》中,共收入宋存标、宋徵璧、宋徵舆三兄弟及宋存标次子宋思玉之作及其友人钱子璧、陈子龙的唱和之作共176阕,其中宋存标《秋士香词》29阕、宋徵璧《歇浦倡和香词》36阕、宋徵舆《海闾倡和香词》34阕、宋思玉《棣萼轩词》19阕,收入宋氏伯仲词118阕,同时收入与宋家唱和的钱子璧《倡和香词》29阕、陈子龙《湘真阁村稿》29阕。除宋思玉属晚辈外,其他诸子所收词不相上下,而且所用词调几乎全同,唱和数量几乎等同,体现出明显的文学家族性。一门之内,以散曲为体专门唱和,已足见风雅,而唱和之后,兄弟叔侄间又相互品评,往复商榷,展开家族内文学批评,并结集梓行,其热情参与且规模之大,在散曲史上叹为奇观。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门风雅”之“门”中,本来就包括了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关于女性作家的成长,冼玉清在《广东女子艺文考》自序中谈到三种因素:“其一,名父之女,少禀庭训,有父兄为之提倡,则成就自易;其二,才士之妻,闺房唱和,有夫婿为之点缀,则声气相通;其三,令子之母,侪辈所尊,有后世为之表扬,则流誉自广。”冼氏仅仅突出强调家庭环境中“名父”、“夫婿”、“令子”三个男性支点的作用,有相当大的局限。分析清代江南女性作家大量涌现、角色峥嵘的状况,不能不同时考虑到以下三个因素:一,晚明以来思想领域倡导人性解放,追求独立人格形成了新的社会思潮,女学得到尊重,女性走出家庭,拜师问学,以文会友,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许可;二,江南经济发达、文化积累深厚,整个社会知识水平较高,艺文气息浓郁,文学创作出现普及化倾向,精英活动逐渐转变为大众行为;三,地域文学和家族文学繁兴,使家族不仅是经济生产单位,也是艺术生产单位,因此文化家族女性的精神生活空间大为扩展,文学创作交流与批评的机会大为增加。概言之,清代江南女性创作骤增,乃时代固宜,风土固宜,文化演进固宜。如果缺少这样的视角观察,人们将很难理解清代江南频繁的女性创作活动和大众化的女性创作成果。
所谓“大众化的女性创作”是指清代江南女性有为数众多的女性参与了文学创作,长期存在的那种男性文人的专属性几乎完全消解,而在一种人文气息浓厚且比较自由、开放的环境中,大量的文学作品在江南女性笔下产生了。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载目凡21卷,清代占15卷,共收录历代有著作成集的妇女4200人,其中清代就有3800多人。而这些女性作家,有半数以上出自江南太湖流域。
检视清代江南骈萼连珠的女性创作,可以发现其鲜明的家族特征,许多文化家族往往集中了若干女性作家,并形成了某种关系,有母女诗人、姊妹诗人、夫妻诗人、妯娌诗人、姑嫂诗人等。读书论学,是她们生活的一个部分,而写作并以作品进行家族内外的交流,是她们的存在方式和精神寄托。徐珂在《近词丛话》中即言:“毗陵多闺秀,世家大族,彤管贻芬,若庄氏、若恽氏、若左氏、若张氏、若杨氏,固皆以工诗而著称”(11),费善庆等所编《松陵女子诗征》中亦云清代松陵地区“或娣姒竞爽,或妇姑济美,以暨母子兄弟,人人有集”(12)。
众所周知随园女弟子众多,其中不少都出于江南文学世家,镇江鲍之蕙是其中之一。之蕙父鲍皋,乾隆间著名诗人,同里颇有学其诗者,有“鲍派”之称,同时人将他与余江干、张石帆并称“京口三诗人”。其实最使鲍氏家族声名大噪的,是四位不同凡响的闺阁诗人。鲍之蘭有集,名《起云阁诗钞》;之蕙有集,名《清娱阁诗钞》;之芬有集,名《三秀斋诗钞》,三人俱以才名,为江南一时大观。在清代江南,文化家族之女性创作,不仅数量繁多,而且往往能够形成独自不同的风格,这是家族文学发展到自觉程度的标志。
四、重视母系教育,培育学术与文学人才
母仪与母教,是古代“齐家”的重要因素,历来受到重视。明清时代,母教的内容既包含了道德精神方面的指导和示范,即以良言嘉语教育子女,立身行事熏陶子女;也包含文化知识上的传授,即担当起家庭塾师的责任。江南文学家族林立,而母教颇有浇沃之功,常州词派开宗者张惠言家族几代人的成长史是一个绝好的典型。惠言先祖妣白太孺人二十二岁归张金第,十六年而孀,惠言之父蟾宾奉白孺人教,兄弟以儒学相励。惠言《先祖妣事略》有生动的记载:
孺人率二女纺织以为食,而课二子读书,口授《四子》、《毛诗》,为之讲解,有疑义,取笔记,俟伯叔父至就质焉。或谓孺人:“家至贫,令儿习他业,可以糊口。今使之读,读未成,饿死矣。”孺人曰:“自吾翁而上,五世为文儒,吾夫继之,至吾子而泽斩,吾不可以见吾翁。”卒命之学。文复府君有弟曰衍黄,老矣,教授于家,怜诸孙,恒诲之。尝语孺人曰:“而子可教,吾欲严督之,念其枵腹,不忍也。”孺人谢曰:“翁幸督之,枵腹何病焉?”及孺人所以教,言行出入罔间。三子皆以文行有声。(13)
及张惠言本人四岁时,又遭父亡之痛,母亲姜氏身兼严慈,承担起了鞫育训督之责,姜氏所经历的孤露窭贫与白氏相似,而抚子向学亦一如白氏,后来曾国藩作《茗柯文编》序曾极称“张氏之先,两世贤母,抚孤课读,一日不能再食,举家习为故常;孝友艰苦,远近叹慕”(14)。而作为一种家风,在张惠言妻吴氏身上同样得到承继发扬。张惠言四十二岁早逝,在家庭的悲惨的宿命面前,“孺人(按,即吴氏)自都下率子成孙扶柩南返,家贫如昔,而成孙年甫十四,或劝遣习贾以谋生。孺人曰:‘吾家十数世食贫矣,然皆业儒。隳祖业不可自吾子始。’不数年,成孙文学斐然,人皆谓编修宜有贤子,不知其实成于贤母也。”(15)张氏作为清代常州著名的文化家族,实赖几代母教而使文脉不衰、世业不替。白氏、姜氏、吴氏这样的“寡母教孤”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美德,也鲜明体现出江南普遍崇文的地域文化特点
这里我们需要将考察的视角移向与母教相关联的“外家”。在江南许多文化家族演进过程中,外家作为母系氏族的文化集成发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由于清代江南文化家族众多,风气相对开放,女性在这样的家族中从事文学阅读和文化研习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当她们及笄待字时,往往已经通经擅文。一般来说因为在婚嫁上讲究“德配”,即不仅重视联姻的门第层次,而且重视其文化和道德层次,因此所出嫁的大都是同样的文化家族。这样的家族需要她们在遇到丈夫长期游宦在外抑或不幸早逝时,亦严亦慈,教育和培养子女。而每当此际,为了使子女有一个更好的教育和成长环境,她们往往动员出外家的力量,让母系家族成为母教的延伸,使整个外家成为重要的支持力量;同时外家源于亲情,也源于文化传承的需要,有意识地培育、扶持外孙或外甥。这样在江南文化家族中,“母教”实际上扩大为“母系教育”,这对学术和文学人才的培养具有特殊意义。
在清代江南文坛影响最大的是阳湖洪亮吉之于外家蒋氏家族的关系。据吕培《洪北江先生年谱》及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三十《国子监生洪君家传》,知阳湖洪氏家族原自歙县迁来。亮吉父翘,字楚珩,无功名,而亮吉之母家蒋氏出自武进云溪蒋氏家族,这是一个著名的文化世族。亮吉六岁丧父,后即随母移居外家,至二十二岁其外祖母龚太孺人去世后离开,在外家共生活了十五年。可以说洪亮吉整个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外家度过的,外家给与他完整的文化养成。对外家教养之恩,亮吉须臾不能忘怀,自外祖母去世后,就尝欲仿东坡、晦庵作《外家纪闻》以志纪念。嘉庆二年,亮吉直上书房时曾作《元夕有怀四首》,开篇即云“半生思纪外家闻,清泪时时滴典坟”。
在清代常州文化家族中,不少著名文人都曾有过从学外家的经历,如陆继辂《先太孺人年谱》曾记述乾隆五十四年(1789)就读舅家的情况:“五十四年己酉,(太孺人)五十五岁。时生计日益困乏,不复能延师家塾。适从舅氏庄乐闲先生绳祖,延其族达甫先生宇逵课子荣诰及从孙轸,太孺人输钱四万,命不孝就读舅家。同学者为洪饴孙孟慈,董恒善贻令、敏善裕来,谢回庭兰。”康乾之际无锡顾栋高为著名文史家华学泉之甥,年轻时顾氏从华学泉习经,深有体悟,康熙六十年进士,授内阁中书,后归里专意究心经史,发明义理,著述甚富。刘逢禄是今文经学常州学派一代宗师庄存与的外孙,经学家庄述祖的堂甥,少时即从外祖和舅氏学,尽传庄氏之学,著有《公羊俞氏释例》、《公羊何氏解诂笺》、《左氏春秋考证》、《论语述何》、《尚书今古文集解》等,成为常州学派的奠基人之一。很有意味的是,刘逢禄在后辈中特喜外甥赵振祚(康熙名臣赵申乔的六世孙),因此振祚自幼能从刘逢禄读书,而通《春秋》、《易》、《礼》之学。
外家的文化扶持和教育,对清代江南文化家族文学力量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清初宜兴戏曲家万树,字红友,为当地著名戏曲家、词人吴炳外甥,能传其学。董士锡的舅氏为张惠言,士锡十六岁即从张惠言游。惠言为《易》学名家,士锡承其指授,治经学,对虞翻《易》义尤为精通。其词亦受惠言影响甚大,沈曾植称其为正嫡。杨芳灿舅氏为金匮顾斗光,顾氏乃著名文化家族,芳灿稍长,即从舅氏顾君游,为诗时得佳句。龚自珍在金坛段氏外家喜好其舅氏段右白诗,作诗云:“少年哀艳杂雄奇,暮气颓唐不自知。哭过支硎山下路,重抄《梅冶》一奁诗。”(16)诗下自注曰:“舅氏段右白,葬支硎山,平生诗,晚年自涂乙尽,予尚抱其《梅冶轩集》一卷。”可见,龚自珍之学诗颇受到其舅氏的影响。
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母系教育,从客观方面看,是江南人文繁兴、文化发达的环境影响所致,也是自明代以来江南文化家族之间为了家族利益盘根错节地通婚联姻的自然结果;从主观方面看,它反映出江南知识阶层传承和发展文化的使命感和自觉性。而无论如何,它使得江南“读书种子”的生根、发芽、成长有了良好条件和新的土壤,对家族人才培养有利,对于江南文化的整体提升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这种学人与外祖、舅氏的外家亲戚复加师生的关系,形成了独特的文学艺术和学术传承、影响的格局,对江南学术文化和文学创作形成不同流派,也有一定作用。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清代江南文化家族实际上也就是文学家族。这是江南历史文化与地域文化相互作用使然,由此也充分显示出江南文化家族在清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毫无疑问,在清代文学史发展中,江南文化家族的参与程度极高,从一定意义上说,江南文化家族的发展过程,也就是清代文学创作力生成的过程。因此,对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特征以及他们之间相互联系的认识,将有助于理解清代江南文学作者群的成长和创作环境,也有助于理解其创作的源泉和特质。
注释:
①汤志钧:《庄存与年谱》,引《武进县志·文学卷》,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版,第3页。
②戈载:《词林正韵·发凡》。
③《清惠松崖手札跋》,《矩园余墨》,[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页。
④沈德潜:《重修长元学记》,光绪《苏州府志·学校》。
⑤《冯桂芬集》卷二《思适斋文集序》。
⑥《默庵遗稿》卷一,清刊常熟二冯先生集本。
⑦《清史列传》卷十九《沈德潜传》。
⑧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⑨按照沈氏谱系,以沈文为始祖,沈奎为其五世孙。这里将沈氏作为文学世家考察,沈奎乃最早存有作品者,故以之为沈氏文学世代的起始。
⑩袁景辂:《国朝松陵诗征》卷一,清乾隆刊本。
(11)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12)费善庆等编:《松陵女子诗征》,柳弃疾序,锡成公司铅印本,1919年。
(13)张惠言:《先祖妣事略》,《茗柯文二编》卷下,四部丛刊本。
(14)张惠言:《茗柯文编》,四部丛刊本。
(15)包世臣:《皇敕封孺人故翰林院张君妻吴氏墓志铭》,《小倦游阁集》卷六,《包世臣全集》本。
(16)《己亥杂诗》其一四二,《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