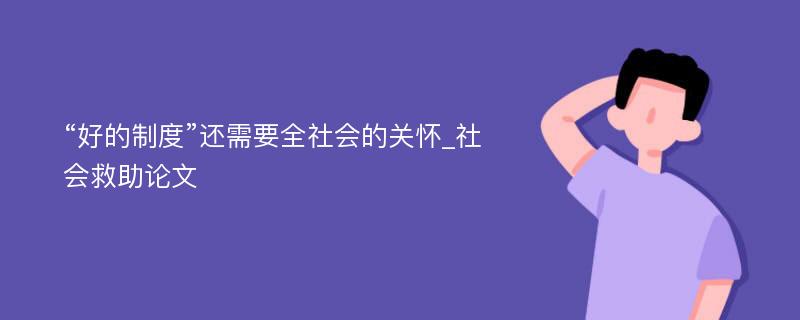
“好制度”还须全社会呵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社会论文,还须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低保制度是一项怎样的制度?
中国的低保制度,基本上与国际通行的社会救助制度别无二致。在拙作《中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报告》中,对社会救助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了如下的界定:“在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都实行以保障全体公民基本生存权利为目标的社会救助制度。其通常的作法是:根据维持最起码的生活需求的标准设立一条贫困线,每一个公民,当其收入水平低于贫困线而生活发生困难时,都有权利得到国家和社会按照明文公布的法定程序和标准提供的现金和实物救助。这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当前社会救济制度改革中试图创立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与社会保险制度不同,社会救助制度并不需要其对象预先进行投入(譬如社会保险制度的保险费缴纳),它只是根据公民是否因为收入骤减或中断而不能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来判断他(她)和他(她)的家庭能否得到国家(政府)的救助。具体而言,就是拿最低生活保障线来作为衡量的标准。所以,它被视为公民的一项最基本的人权——生存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社会中,权利和义务总是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的,并不存在没有义务的权利。说句大白话:“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是不存在的。公民在申领低保的同时,也必须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
首先的义务就是要向政府有关机构如实报告自己的收入及财产,同时,他(她)的生活方式或消费方式也应受到一定的限制。并不是中国政府(中央的、地方的)对中国公民特别苛刻,这是社会救助制度的国际通则。所以社会救助制度也被称为“须经家庭经济状况调查(Means Tested)”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发达国家,受助者除了要接受政府关于家庭经济状况的调查之外,还须定期(一周或两周)向政府有关机构报告自己在前一段时间寻找工作的经历。有的国家还规定,如果申请者有一定数额的可变现的财产,须折算为现金,按救助标准计算,待这笔钱用完后才能领取救助金。同时受助者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也受到限制,譬如不能外出旅游,也有规定不准养宠物的。国外的某些规定,可能比中国低保制度的规定更为严格。而且随着经济的不景气、失业的增多,社会救助申领者也增加,所以,这项制度在世界上总的发展趋势是偏向“紧”和“严”。
发达国家的教训与经验
全世界的社会救助制度都在向偏紧偏严的方向发展,是因为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是有教训的。二战后发达国家按照“福利国家”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社会救助方面总的政策取向是“慷慨”的。救助范围偏大、救助标准过高使这项制度得以“养懒汉”。市场化的劳动力配置无疑是允许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劳动力资源进行成本核算的(包括机会成本),如果社会救助制度的标准足以使一个家庭不劳而获而过上“体面”的生活,如果这项制度的标准明显高于一些“档次较低”的工作岗位的劳动报酬,那么,它就有可能“养懒汉”。事实上,发达国家如今已经普遍存在一个光想享受救助而不愿工作的社会群体,而且在这个群体中已经形成了—种贫困文化并世代相传。
在发达国家社会救助制度偏紧偏严的政策动向中,要求受助者在社区中做义工(志愿者)是一个很普遍的做法。或许在国人看来,做义工(志愿者)应该是一件“绝对自愿”的事,其实不然。在一些国家,譬如美国,一个年青人如果没有做志愿者的经历,在升学或求职时会被“另眼看待”,因为你连志愿者也不曾当过,你怎样证明你是一个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人呢?在另一些国家,譬如中欧的一些国家,当志愿者已经与服兵役一样成为制度,如果你因为身体的原因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去服兵役,那么就服“民役”吧,这也就意味着你将到一个社区中去做志愿者。这样的规定对一个社会来说,无疑是有好处的。所以,要求社会救助的受助者去社区中做志愿者实在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很普通的事,或者说是一件很光荣的事。
同时,国际上很多研究都表明,一个人如果半年以上不工作,他的工作积极性就会下降一半;如果一年以上不工作,他的工作积极性就微乎其微了。所以,长期失业对一个人来说,不仅是收人中断或减少的问题,它所引起的心理变化是更值得关注的。到社区做志愿者显然是使失业者参与社会并维持他的工作积极性的必要手段。
在社会保障的历史上,让社会救助制度的受助者参加公益性义务劳动的事例也很多,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让美国度过三十年代大萧条的“罗斯福新政”中的“劳动福利政策(Working Welfare Policies)”。当时,罗斯福总统组织了大批领取救助金的城市失业工人去修建铁路、高速公路等基础工程,这为以后美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借鉴这些国际经验,中国的《条例》中也加入了要求受助者参与公益性社区服务劳动的规定,这是受助者应尽的义务之一。当然,这要考虑受助者的身体条件。但是,我们绝对没有必要把它与“强迫劳动”一类的负面的认识挂起钩来。
慎待“好制度”
我们给“好制度”打上一个引号,是因为严格说来,一项制度或政策是无所谓“好”与“不好”的。因为时间、空间等环境条件的不同,行得通的就“好”,行不通的就“不好”。所以,可能用“有效”来表述这一层意思更为确切。而且,“好”与“不好”,是否有效,是动态的,与时俱进的。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目前对中国来说,是一项重要的制度,是因为中国的总量性、结构性的失业问题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同时,中国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的很多问题也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克服的。我们只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十年、二十年或者更长)寄希望于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覆盖全国所有城市人口并能以最少的成本(因为它的“须经家庭经济调查”的特点)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1993年在上海市首创至今已经十个年头了。但实际上,一直到2001年下半年,这项制度才突破资金的瓶颈走上正规,发挥出其应该发挥的作用。创建过程中的曲折和艰辛自不待说,其中遇到的最大的障碍就是社会上很多人,包括高层领导、政府官员、基层干部及其他相关或不相关的人,都担心这项制度会“养懒汉”。这是因为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有劳动能力而没有劳动机会的人也可能致贫这一客观事实,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同时,发达国家的教训也使怀疑这项制度的人有了口实。
要建立低保制度并使之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稳定真正起到作用,我们需要非常谨慎地掌握一个“度”。只要我们的制度的范围和标准是适度的,这项制度就可以发展起来并且在中国社会中起到其应有的作用。同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受助者也应该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自己不是“懒汉”,而是同样地在为我们这个社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在社区做义工,当然是低保对象证明自己的一个好机会。
毋庸置疑,低保制度的实施,对城市贫困人口是有利的。有社区干部评论说:“要是两口子都下岗,一时没有了收入,那真是比农民还作孽。农民还有土地,种点粮食多少可以填肚子,下岗的到哪里去找……低保制度真是发救命的钱。”一项有效制度是要靠全社会来呵护的。此前,据说重庆市在低保政策执行中出了点问题,有不符合标准的人领了低保金,于是,“养懒汉”的调子又唱起来了。接着,就是对这项制度的怀疑。如果这项制度被怀疑的浪潮冲垮,那么受害者就是那些占低保对象绝大多数的真正贫困的人和他们的家庭。
大连的经验
在执行有关公益性社区服务劳动的政策时,要关注低保对象的心理。也许“义务劳动”这样的词常常让人想起计划经济时期的政治压力,所以,在浙江省新出台的类似规定中,用做“义工”这样的词来取而代之,也许是一种比较聪明的做法。但是,从2000年开始,大连市组织低保对象建立公共服务社的经验可能更值得我们关注。
1999年,大连市根据《条例》的规定,在社区组织低保对象参加社区公益劳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00年,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与大连市民政局联合进行了一项行动研究和改革试点,将社区组织低保人员参加社区公益活动(注意,是“活动”,也就是不光是“劳动”)用一种组织方式固定下来,这个组织被命名为“社区公共服务社”。这样命名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给低保人员贴上带有消极意义的社会标签。
在研究和试点中,我们发现了社区公共服务社的很多优点。
1.通过参加社区公益劳动,譬如铲雪扫雪、保沽保绿、治安巡逻,等等,公共服务社的社员们感到自己也能为社区出力,以往那种觉得自己无用,觉得被社会遗弃的感觉消除了,社员们再次融合到社区之中;同时,社区居民则对这些低保对象改变了看法,不再认为他们是不愿劳动光沾国家便宜的“懒汉”,纷纷对公共服务社社员的劳动成果表示赞赏,使邻舍关系更加和睦、更加融洽;社区居民委员会则得到了一批可以专门从事社区公益活动的生力军,譬如,大连市的社会捐助活动开展得好,就是因为有这些社员能够随叫随到,上门收取捐赠物品,大大方便了居民。公共服务社在消除“社会排斥”、促进“社会融合”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获得了一个“三赢”的结果。
2.通过参加公共服务社组织的学习交流活动,使社员们摆脱了过去那种“见人矮三分”、“抬不起头来”的自我排斥、自我隔绝的心态。自从下岗、失业回到家里后,这些贫困人士大多感到很自卑,所以常常把自己封闭在家中,尽量避免与外界接触。现在有了公共服务社,社员们的背景都差不多,在一起活动也不再怕受到歧视。通过在一起学习,社员们对国内外的大事,尤其是与自己密切相关的政策法规,了解得更多了。通过在一起谈心交流,可以把心里的郁闷一吐为快,满足了下岗、失业人员在情绪宣泄和交流互动方面的精神需求。所以心情变好了,人心精神多了。
3.通过参加公共服务社的活动,社员们有了一条可靠的求职途径。社区和公共服务社也为社员的就业积极寻找出路,譬如为居民提供一些家政服务,为单位提供一些劳务服务。但这些工作常常是“零工”,时有时无,所以,有个社会组织对此进行工作调配和收入分配还是很有必要的。有工作时,就把社员们撒出去;没有工作时,又把社员们收回来。在分配上,将最低生活保障金和劳动报酬合并计算成“社会工资”,同时也考虑多劳多得,既有公平,又讲效率,这在一定意义上就将非正规就业正规化了。公共服务社成功地组织和帮助社员再次进入就业状态,即使这次的就业是临时的、非正规的。
4.通过参加公共服务社的活动,使社员们找回了“有组织”、“有单位”的感觉。沉淀在社区中的下岗、失业人员,大多属于“40-50部队”,这些人差不多一辈子都生活在计划经济时代,有组织、有单位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下岗、失业以后,最难受的就是什么依靠都没有了——有点事能找谁?一片茫然。社区公共服务社的成立使社员们重新有了“归宿感”,有一个专门的社会组织可以接纳和帮助他们,这对他们来说是极其重要的。通过公共服务社的活动,低保对象与低保制度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调适。公共服务社已经在维护社员的利益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譬如在与一些单位洽淡劳务服务时,公共服务社就作为集体谈判的代表出面。所以,社员们对参加公共服务社的活动也是很踊跃的。
5.通过公共服务社的活动,还可以对“隐性就业”进行“软性甄别”。因为公共服务社每星期要活动3-4天,实际上在外面有工作的人就很不方便了。社区对于经常不参加活动者就可以进行重点调查,如果确实有工作、有收入,就可以劝他(她)退出公共服务社,以及停止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在—般情况下,这些低保对象都会主动退出,所以起到了“软性甄别”的作用。这种甄别作用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目前在中国,由于没有必要的手段,要查清居民的收入是非常困难的,这也就给这项制度留下了一个明显的破绽或隐患。很多国际上的知名专家都对小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否可持续抱怀疑态度,因为这项制度时常被抨击为“养懒汉”,问题就在于没有一种令人信服的手段来证明这项制度确实救助的都是穷人。随着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可以预料,会有一天在中国也会有人提出类似的异议。所以,公共服务社的甄别作用对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意义,并不在于最后能够甄别出去多少不符合条件的人,更重要的是能够证明这项制度救助的都是穷人。这对城市贫困家庭的意义更大、更为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