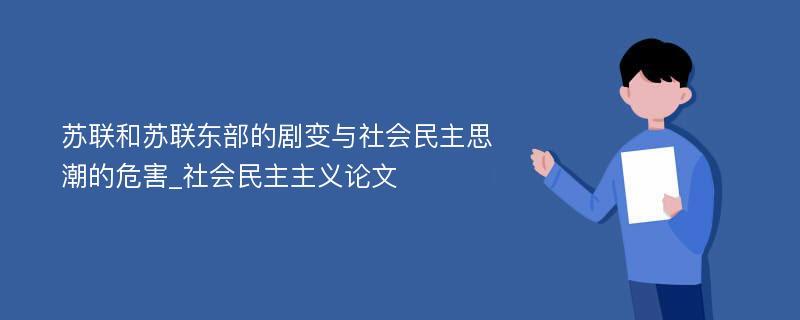
苏东剧变与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危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民主主义论文,剧变论文,思潮论文,苏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有人提出,在我国政治思想领域,尤其是在党内,必须警惕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泛滥。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我们党有一个优点,历史上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很小,这是同苏联东欧国家不一样的。但是,近一、二十年来,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各种思潮涌进国内,特别是苏东剧变以后,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我最近看到一篇谈论改革方向问题的文章,公然指责列宁、斯大林批判伯恩斯坦、考茨基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是错误的,说“欧洲社会党的社会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发展模式”,而且认为:“从大的趋势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斯大林模式是渐行渐远,与欧洲社会党的社会主义越走越近。”当然,这不是事实,而是他的愿望。他主张我国改革的方向应该是走欧洲社会党的道路。还有人提出要改造我们的思维方式,放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思维,转为“两者相互交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兼容状态”的思维;放弃“阶级定性的思维”,转为“淡化意识形态”,“阶级调和”的思维;放弃“淡化”不同阶级之间共性的“革命党”思维,转为顾及不同阶级利益的、从而“不同执政党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的“执政党”思维。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的指导思想,放弃马克思主义,转为社会民主主义。在我们党内,甚至在高级干部中,有人认为,世界上共产党衰落了,而社会党却日益兴旺,因而建议把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名字改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这些迹象表明,在我们党内,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已经有相当大的影响,不可低估。
应该看到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危险性,这股思潮如果不加注意,听任其蔓延和泛滥,就有可能重蹈苏联东欧国家的覆辙,葬送党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要知道,苏联东欧国家正是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即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指引下,把共产党改造为社会民主党,从而丢失政权、改变制度性质,甚至造成亡党亡国的悲惨局面的。我们党中央清醒地看到这种危险。早在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提出实行多党制后,我们党中央就明确指出,“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根本不是什么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向资本主义方向演变。”提出全党要“划清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苏联“8.19”事件发生后,我们党又重申这一点。戈尔巴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无需赘述。但从我国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仍在蔓延的情况看,中央的这一精神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戈尔巴乔夫是当代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的代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即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正如我们党中央的判断,“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因而在本质上同历史上的社会民主主义没有原则的区别。但是,这股思潮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由执政的共产党自己提出来的,因而也具有一些特点。我认为,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从意识形态来说,它是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从社会制度来说,它主张实行做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从历史作用来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它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桥梁。社会民主主义(包括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而是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推行社会民主主义路线,正如中央指出的,不是完善社会主义,而是向资本主义方向演变。苏东剧变这一历史事实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戈尔巴乔夫是主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趋同的。他在1990年(即东欧国家已经发生剧变、而苏联行将解体的时候)所写的《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一文中写道:“资本主义现在远不是从前的资本主义了。”“社会主义是一种世界进程,它不仅限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范围,我们从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看出了它的许多表现。社会主义的一些特征,诸如公有制、计划化、社会保障,在某种程度范围内已经成了先进的西方社会生活习以为常的部分。现代的民主和法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主义思想和行动的成果。”[1](p21) 顺便说一下,这篇收入由勃兰特和戈尔巴乔夫共同主编的《未来社会主义:政治论坛》一书的文章,与他写的《改革与新思维》相比较,更能反映戈尔巴乔夫的真实思想。
应该说,戈尔巴乔夫这段话是十分混乱的。第一,他把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存在的东西,硬说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例如公有制。他把资本主义股份公司当作公有制了,这遭到了西方政治家的嘲笑,因为股份制只是资本的组织形式,它本身并不能说明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第二,他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特有的东西了,例如,计划经济、社会保障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可以用的发展生产、保证社会稳定的方法,民主和法制的具体设施(不是指民主和法制的阶级本质)作为社会行为的规范,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有的东西。这一类共性的东西并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本质特征。这些东西是可以相互借鉴和学习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实行这类做法并不等于出现了社会主义因素。
社会主义因素,作为社会主义特有的本质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不可能产生的,更不可能越来越多。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说过,由于俄国“国内没有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2](P542,543) 毛泽东在读这本书时表示赞同这一意见,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已经产生了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但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建立起来的。”[3](P30) 在另一处,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都根本不能产生,当然也就说不上成长。这是我们同修正主义者的重要分歧。修正主义者说,城市中的公用事业是社会主义因素,说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歪曲。”“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3](P76,298)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可以在封建社会中产生并初步成长起来,因为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它们是私有制的两种形式;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和成长的,因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而公有制与私有制是根本对立的,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才能建立公有制经济关系。至于说到政治上的社会主义因素,那更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自发地产生和成长了。美国标榜最自由、最民主的了,但美国决不允许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决不允许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美国法典第18篇第2385条规定:“任何蓄意鼓吹、煽动、劝说或讲授推翻或摧毁美国政府的行为,包括因此而印刷、出版、发表、传递、出售、分发或公开展出任何书写品或印刷品,都要处20年徒刑或2万美元罚款,或者两者并罚。”美国共产党党纲上出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字样,其领导人就因此而身陷囹圄。把持政权的垄断资产阶级是不会允许政治领域的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的,更不用说成长与发展了。在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政党可以容忍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只要不危及资产阶级统治),但决不会同意马克思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恰恰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本质特征。戈尔巴乔夫鼓吹西方国家里社会主义因素越来越多了,正好表明他与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伯恩斯坦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叛徒,而他在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恰恰是他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从社会基本制度的角度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种替代关系:或者按照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或者在特殊条件下,由于阶级力量对比发生逆转,社会主义演变成为资本主义,像苏联东欧国家发生的剧变那样。在现实生活中,垄断资产阶级也不允许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趋同”成为一种新的制度,即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的所谓“第三条道路”。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竭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妄图重新恢复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苏东剧变正是和平演变战略的得手。“趋同”,只是某些人的幻想,而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事实。
“趋同”论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上也是不存在的。然而在我们国内,有一些人却在积极渲染这一理论。例如,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充满活力,是不会灭亡的。社会主义正在吸收资本主义的优点,而资本主义也吸收了社会主义的某些优点,“两种不同的主义和不同的制度的国家,有由过去的完全的对抗逐步转向互相兼容、互相合作的趋势。“估计将来会在全世界范围内无声地逐步扩大为兼容并包各种制度长处的大混合经济。”因此,有的学者提出,我们应该改造思维方式,不要再讲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了,应该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正在相互交汇,否则就会“在社会进程中被淘汰。”这种观点值得我们关注和分析。
二
戈尔巴乔夫主张放弃阶级立场,主张阶级调和。国内也有人提出,共产党讲阶级斗争,阵地越来越缩小,社会党讲阶级调和,阵地越来越扩大。“阶级定性”和“阶级调和”两种思维方式一直处在此消彼长的状态,但“以阶级定性来思考问题的方法并没有战胜用阶级调和来思考问题的方法”。“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情况进一步逆转:用前一种思维方式来处理问题的共产党,阵地不断收缩,而后者的阵地不断扩大,出现了‘资进社退’、‘资攻社守’的格局。”这就是阶级定性的思维方式之过。他们公开主张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要求采用社会民主主义的阶级调和的思维方式。
社会民主主义是反对阶级斗争、主张阶级调和的。但是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决不能放弃。列宁曾经说过,社会的发展呈现出复杂纷繁而又不断更换的现象,似乎混沌一片,无法把握。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他指出,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彻底贯彻了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和伟大动力,因而阶级斗争理论是了解和把握阶级社会发展的钥匙。所以,“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4](P30)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者在谈到社会问题时始终不能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只要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列宁的这一论断就不会过时。抛弃了阶级斗争理论,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
这一点,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看得很清楚。美国最后一任驻苏大使马特洛克就说过:“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阶级斗争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5](P169) 这个连美国都可以认可的“别样的社会”,无疑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连美国都可以容忍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无疑就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显然,对于阶级斗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的认识,他要比某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高明得多。
应该看到,在当前,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还十分激烈。观察意识形态的斗争,不能不分清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这是判断一种思想、观点正确与否的基本标准。这种区分是客观的现实,不是“改造思维方式”就能否定得了的。正如列宁指出的:“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他还说:“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6](P38) 在思想政治领域淡化“姓社姓资”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也不符合客观实际。
在存在阶级的社会里,必须坚持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江泽民总结了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国内改革开放出现的新情况,在2000年6月28日召开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纠正过去一度发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不等于阶级斗争已不存在了,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这种观点与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与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7](P34) 这一论断对分析当前国际国内一系列重大问题具有指导意义。
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大规模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已经过去,阶级矛盾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就是一个例证。就拿最近发生的事来说吧。有一位“著名教授”在去年3月的一个会议上,公开叫嚷共产党执政不具备合法性,要求实行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主张军队国家化,要求学习“台湾模式”等等。他认为这套主张不应该掩掩盖盖,而要“图穷匕首见”,抛去包裹匕首的地图,公开说出来。这样赤裸裸地要求共产党下台,要求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主张实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难道还不能说明阶级斗争就在眼前!怎么能闭着眼睛反对“阶级定性”的思维方式呢?
从国际上看,这种阶级斗争更为明显,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我国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正在进行着激烈地斗争。正如列宁指出的:“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相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不是为苏维埃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4](P330) 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就是这种激烈斗争的很好证明。苏东剧变这场激烈阶级斗争的尘埃刚刚落定,难道我们转眼就忘怀了,就要否定“阶级定性”的思维方式吗?
另一个问题是苏东剧变的原因。有的学者认为,苏联东欧国家之所以发生剧变,是因为坚持阶级定性的分析方法,思维僵化,仿佛运用阶级调和的思维方式就可以保住政权。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亲手葬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戈尔巴乔夫是竭力反对阶级观点,淡化意识形态、主张阶级调和的。他认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坚决抛弃同全人类共同价值相对立的”“阶级立场”,主张超阶级的“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正是在这种淡化“阶级定性”的阶级调和的思想指导下,在阶级敌人以夺取政权为目的咄咄逼人的进攻面前,使得苏联共产党看不清楚斗争的实质,不能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而采取调和、妥协的办法,结果步步退让,最终拱手让出政权,导致亡党亡国的悲惨局面。而苏东剧变使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了低潮,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事实表明,正是放弃“阶级定性”的思维,在“阶级调和”思维的指导下葬送了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使得社会主义的“阵地不断缩小”。
三
有人认为,整个国际形势是共产党衰落,而社会党兴旺。我认为这种判断是错误的。贬损共产党的历史、吹捧社会党的“成绩”的论断,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苏东剧变的时候,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纷纷宣布改变党的性质,把党的名称改为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戈尔巴乔夫也主张把苏联共产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只是因为局势变化太快,没等改名,苏共就被解散了),一时间社会党国际欢欣鼓舞,认为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不行了,社会党、阶级调和的理论可以大行其道了。然而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新保守主义占了上风,作为资本主义左翼的社会党并不吃香,不要说苏联东欧国家的由共产党改名而来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纷纷被逐出政坛,即使欧洲已经执政的社会党也大多数丢失了政权,沦为在野党。很明显,对资本主义做点改良的理论和实践是经不起历史的检验的。改良主义只能充当资本主义的伙计,资产阶级需要时拉来帮帮忙,不需要了就一脚踢开。与此同时,中国等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共产党的领导,通过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威力。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8](P382,383)
在苏东剧变、社会主义跌入低潮的形势面前,有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发生了动摇,以至提出要“改造思维方式”,要转变立场,从马克思主义转为改良主义,从共产党转到社会党一边。在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主张放弃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就具有泛滥的条件。这叫做“革命低潮综合症”。
既然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怎样处理同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呢?我认为,在处理同各国社会党、社会民党的关系时,应该把不同性质的问题区分开来。应该把意识形态问题与党际关系区分开来。在意识形态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切复辟资本主义的行为,都必须批判。理论原则问题,必须分清是非,因为理论是非直接关系到我国国内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直接关系到我们走什么道路,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理论上差之毫厘,实际工作会失之千里。对于错误观点和主张,必须旗帜鲜明地进行斗争,决不能含糊其事、模棱两可,更不能听之任之,任其自由泛滥。吸取苏东剧变的教训,我们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必须坚决批判,防止这股思潮在我们党内和社会上蔓延。尤其是在党的干部队伍内部,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更应该如此。要知道,让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泛滥,最终是会导致亡党亡国的悲剧的。
在外交上我们应该广交朋友,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了形成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我们必须在国际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凡是愿意同我们交往的政党和国家,我们都应该建立联系。外交上我们决不能以意识形态划线,意识形态不一样,也可以发展友好关系。我们规定了国与国之间的五项基本原则,党与党之间的四项基本原则,只要符合这些原则,都应该开展交往。所以,尽管我们批判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但并不影响我们同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建立友好的党际关系。
在我们内部、尤其是在党内,应该对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性质有清醒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发展同它们的关系。从根本性质来说,它们是资产阶级政党,因为它们不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只是要求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作一点改良。这是与我们根本不同的。我们在同他们打交道时,一定要看到,共产党与社会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政党,不要抹煞两者的原则区别,更不能借口相互学习,否定自己的基本理论和实践,吹捧社会党的改良主义理论和政策,主张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曾经出现过。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干的。他说:“我国对外部世界是开放的,为的是研究和利用他人经验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在社会民主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中,我们看到了许多有意义的、富有启发的内容。我确信,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中深刻的变化以及社会民主党内的进程,我们正变得彼此接近起来。”“今天,在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已不再存在从前是他们分裂的鸿沟。”共产党正在批判自己的错误,对十月革命、共产主义运动进行重新思考和改造,因而共产党与社会党之间“不仅在政治立场上而且在世界观立场上都接近了。”[1](P20) 戈尔巴乔夫通过向社会党学习,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迈过了“思维鸿沟”,提出了“新思维”,也就是社会党的思维。正是在“新思维”的指导下,苏联发生了从共产党到社会党、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急剧变化。这一教训,难道不应该让热衷于向社会党学习的某些人引以为戒吗!
但是,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终究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左翼。在不触动雇用劳动制度这一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这是它们同保守党等右翼政党不同的地方。它们在执政期间为加强执政地位而采取的某些具体做法,也值得我们借鉴。此外,在外交政策上,它们一般讲主张维护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因而与我们有许多相同之处,可以进行合作。所以,我们主张同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建立广泛的联系和多方面的合作关系。
总起来说,我们在思想上必须同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划清界限,在外交上则同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建立必要的关系。这两者应该统一起来。
四
胡锦涛同志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后,有人认为,实现和谐,必须放弃矛盾和斗争的理论,应该把社会党的阶级调和论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这是极大的误解。在讨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时,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决不能撇开辩证唯物主义,用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
应该承认,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尤其是他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哲学基础。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9](P213) 这一段话,是对宇宙发展规律的最一般的概括,适用于一切事物,当然也完全适用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在矛盾的对立统一这种哲学思想指导下,来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
首先,能不能构建和谐社会,取决于矛盾的性质。并不是任何社会都可以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要看在这个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矛盾的性质。
在古今中外都有过不少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然而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这只是一种愿望、一种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在存在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社会制度下,社会矛盾主要是阶级矛盾,这种矛盾是具有对抗性的,它只能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冲突来解决。在被统治阶级斗争的压力下,统治阶级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这也就产生了所谓的“太平盛世”),但根本利益对立的阶级之间是不可能形成和谐关系的。因而应该明确指出,在对抗性矛盾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是谈不上构建和谐社会的。希冀在存在压迫和剥削的阶级社会里实现和谐,那必然是缘木求鱼。
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当然,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存在矛盾的,但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使得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面前形成一种平等的关系,任何人都不可能凭借所掌握的生产资料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这就为消灭剥削和压迫奠定了基础。在这种条件下,人们之间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此基础上出现的矛盾不再具有对抗性,它完全可以通过民主协商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非对抗性,决定了人与人之间有可能形成和谐关系,有可能构建和谐社会。
在我国,全国解放以后,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阶级矛盾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对抗性矛盾已经不占主导地位。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矛盾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因而从性质上说,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范围内,通过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式,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予以解决。在非对抗性矛盾占主导地位、基本上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有可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目前,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抗性的阶级矛盾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是这种矛盾在社会中已退居次要地位,占主导地位的已是非对抗性矛盾,而且具有对抗性质的阶级矛盾,除了少数反社会主义势力同人民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敌我矛盾外,大多数已经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用非对抗性的方法来处理。这就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了前提条件。
其次,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这是客观事实。构建和谐社会,不能建立在否认矛盾的基础上,相反,应该正视矛盾,不断解决矛盾,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
按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都是矛盾的运动。毛泽东指出:“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9](P213,216) 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曾经有人认为,只有存在阶级对抗的社会才有矛盾,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就没有了。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命题,创造性地发展了唯物辩证法,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之间的和谐关系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和谐社会需要党和人民通过艰苦的工作去构建。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同一切事物一样,矛盾着的对立面的统一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社会主义的和谐,作为矛盾着双方统一的一种状态,是相对的,而矛盾双方的斗争则是绝对的。只有公开承认矛盾,并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才能保持矛盾双方的统一,实现社会的和谐。而且和谐即统一状态是动态的、变化的,而不是静止的、不变的。一个矛盾解决了,实现了和谐,新的矛盾又出现了,又需要去解决。正是在不断出现矛盾、而又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与和谐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和谐,决不是意味着维持现状,更不是否认矛盾、掩盖矛盾;恰恰相反,只有承认矛盾,并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才能实现和谐。不敢正视矛盾,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掩盖矛盾,让社会矛盾积累下来,就有可能导致矛盾尖锐化,甚至使本来是非对抗性质的矛盾向对抗性矛盾转化,这样就不可能建设和谐社会。可以说,承认矛盾并正确加以处理,则和谐关系存;否认矛盾、回避斗争,则和谐关系亡。用社会民主主义的阶级调和理论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不仅在理论上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而且按照这种理论,在实践上就不可能下大力气去揭露和解决社会生活中客观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而是千方百计地加以掩盖和粉饰,这种想法和做法,最终是会葬送和谐社会的建设的。
标签:社会民主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政治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阶级斗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