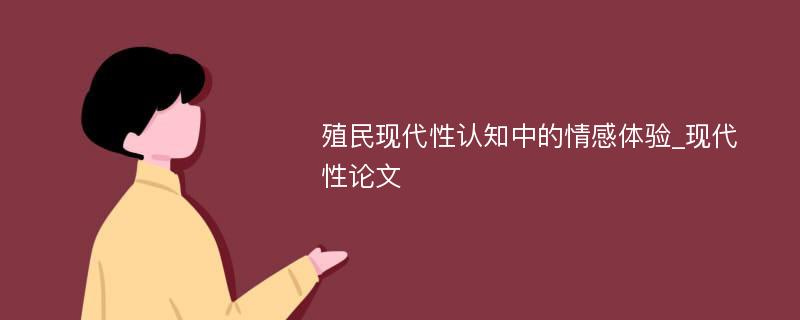
殖民现代性认知中的情感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认知论文,经验论文,情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0)5-0085-07
殖民现代性是现代性进入殖民社会引发的多重变貌和矛盾纠葛的总和,它既不同于自然萌生发展的原发现代性,也不同于被主动引入的继发现代性,后者虽然经历了从“他者现代性”到“自我现代性”的转移,但其主体相对独立统一;而殖民现代性存在不同的现代性主体,即给予方和接受方,其相互关系并不对等,所谓“依赖他者式的近代化”①正道出了殖民现代性的重要特征。②由此形成的殖民现代性因而有了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殖民者自认的现代性;二是被殖民者眼中的现代性。
由于殖民现代性包含被殖民者的认知层面,两者间形成了所谓“看”与“被看”,即观察与被观察的关系,前述被殖民者的相关文学表述可视作观察的不同形态;不过这种观察与被观察者作为纯粹对象的情形不同,如果将殖民社会当作一个巨大的容器,其中包含着殖民现代性内容的话,那么被殖民者也同时被放置于这个容器中,与身边密集散布的殖民现代性因素共存,经过长期浸淫,这些因素逐渐大量地附着在他们身上而难以剥离,因此这种从殖民社会内部由原本具有文化异质性的被殖民者所作的观察,既与殖民者不同,也与一般意义上的“他者”相异,换句话说,如果把殖民现代性看作一个社会文本,身处产生这一文本的环境之中或之外的阅读者,其认知并不一样。不仅如此,由于被殖民者原有文化抗体③强弱和形式的差异,当他们置身于殖民社会容器中的时候,各自的现代性认知就不同;当容器被打破后,对殖民主义的清理也存在程度和侧重点的差异。
造成原有文化抗体强弱和形式差异的原因十分复杂,个人和群体的经验和想象、殖民社会演进的不同阶段,乃至个体性格心理因素等等,都可能发生作用。除了诸如民族、阶级、文化身份、个体经历等比较确定性的因素外,情感也是值得关注的部分,只是对它的分析可能会涉及社会学、心理学等多重学科,难以获得相对清晰的认识,特别是这些情感表达相对零散而随意,很可能使分析落不到实处。但情感影响确实存在,殖民时期的各类文学文本,包括传记、杂感等无不是情感记忆的写照,这些记忆很可能决定了被殖民者的思考面向和选择。问题的出现源于研究者的困惑,即当人们从各个角度探讨殖民社会发展脉络及殖民地文学特质之后,仍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在同一时期被殖民者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现代性认知;文化抗体强弱和形式差异的原因仍然不能充分说明。例如,在殖民统治末期,既有坚定的抵抗殖民主义者,④也有充分皇民化的民众,他们可能有共同的教育背景,相似的社会经验,却有不同的殖民社会文本的解读,这些解读可能又反过来影响到他们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又导致解读差异的扩大。以左翼思潮来说,其影响有目共睹,而单个文化人对它的接受却迥然相异。从情感经验入手可能有助于思考这些选择和差异的不确定的一面。如果说前述对殖民现代性表征和左翼书写的分析仍然是从一些确定性因素入手的话,情感经验的分析就是对相对不确定的认知因素的考察。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威廉斯的说法,“认识人类文化活动的最大障碍在于,把握从经验到完成了的产物这一直接的、经常性的转化过程相当困难。”“在一般承认的解释与实际经验之间总是存在着经常性的张力关系。在可以直接地明显地形成这种张力关系的地方,或者在可以使用某些取代性解释的地方,我们总还是处在那些相对而言还是凝固不变的形式的维度内。”他认为,经验、感觉等个人形式不能被化约为凝固不变的形式和范畴,“实际上存在着许多那些凝固的形式完全不讲的事物的经验,存在着许多它们的确不予承认的事物的经验。”因此他提出了“感觉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又译“情感结构”)概念,来确定“社会经验和社会关系的某种独特性质,正是这种独特性质历史性地区别于其他独特性质,它赋予了某一代人或某一时期以意义。”⑤这一概念“被用来描述某一特定时代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普遍感受。这种感受饱含着人们共享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并能明显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它具有潜意识的特征,因为“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不是有意识进行的,而往往是通过经验来感知的。”⑥“它在我们的活动最微妙和最不明确的部分中运作”,“突出了个人的情感和经验对思想意识的塑造作用,以及体现在社会形式之中的文本与实践的特殊形式。”它同时具有动态性,会随着社会变动“始终处于塑造和再塑造的复杂过程之中。”⑦当然,所谓感觉结构原本试图解释的是某一时代在“凝固的形式”⑧之外人们的感受与经验,并未强调同一时代不同人群的不同感受及其由来,但对情感经验与思想意识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视仍然提供了文本解读的新着力点,并可能凸显文学特有的情感记忆。尽管我们尚未做到运用此概念寻找殖民地台湾文学的感觉结构,像它的提出者在《文化与社会》⑨中对英国文学家和思想家所做的分析那样,但至少能够从中获得启发,尝试正视文学文本中情感经验的流露,并由此解释殖民现代性的认知差异;虽然可能仍然不能确切说明这些情感经验的成因,但毕竟可以换一个角度,从“凝固的形式”或明确的范畴之外寻求别一种说法。
回到文学文本。如果以过去常见的阶级、民族,或已经从热点转为寻常的身份、认同等“凝固的形式”出发,文学文本中的情感经验就可能不会受到特别关注,因为情感经验的变异性和模糊性或者使精确冷静、前因后果式的辨析失效,或者使自身在辨析中缺失。以情感经验为对象虽然可能流失某些确定性,但也可能创造新的论述空间。仍以前述中文写作为例,从文化想象层面看,中文写作的某些模式化表述不完全是由于写作者艺术表现力的不足,更可能是想象的结果;从情感角度看,它也可能是作者情感经验的表达,那种悲愤、无奈、绝望的心态无疑是当时普遍社会心理的写照。同样,日文写作的多重想象也是情感经验随殖民社会演进从相对单一过渡到复杂的产物,随着殖民同化的深入和殖民暴力形式的改变,被殖民者对殖民统治的情感经验也发生了改变。
分析可以从殖民统治引发的情感反应开始。殖民初期遭遇的抵抗,可谓台湾面对殖民统治的最初反应,表现在写作中,就是在以中文写作为主的时期,形成了相对一致的情感表达,即殖民压迫导致的痛感体验,并延续到部分日文写作中,所谓痛感体验就是由痛苦经历引发的情绪。⑩很明显,那些带有鲜明反抗殖民倾向的文本大都书写了被殖民者的惨痛经历和愤怒、屈辱的情感,形成了情感和思想意识之间的有机脉络。杨逵《公学校》中台湾少年遭受日本教师的毒打非常典型地代表着由痛感经验引发的仇恨和愤怒。相似情节的文本比比皆是,更不用说大量警察形象传达的恐怖经验。由于痛感的强烈程度,写作者几乎完全专注于此而无法顾及其它,或者说,痛感体验影响着文学想象的形成,进而左右着文本的思想意识。张深切《里程碑》中,打在身上的日本剑甚至直接唤醒了主人公的民族意识,这部传记虽然写于战后,但殖民时期的情感记忆如此深刻甚至略显突兀,它直接关联到人物的身份认定、道路选择和命运走向。这也是一个情感经验决定思想意识的突出例子,它说明痛感体验一旦与给予者的身份和被给予者的心理、情感相关联,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挣脱一般意义的束缚,实现从情感到观念的过渡。当相似的经验逐渐汇聚起来之后,一个时期的基本情感结构就会慢慢浮现出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确定意识的形成完全取决于情感,其它因素的综合也会产生影响,再以杨逵的写作为例,具有强烈情感倾向的《送报夫》、《自由劳动者生活的一个侧面》、《公学校》等文本直接控诉殖民主义的方式就带有左翼文学的理念色彩。但是,如果没有最初的、直接的,甚至带有冲动性的情感经验,文学文本就失去了描绘和记录生动复杂的精神状态和社会心理,并从中曲折地透露思想意识的特质,这也是威廉斯认为情感结构的设置特别适用于文学艺术的原因吧。(11)
不过由痛感体验直接激发思想意识并不能代表本时期台湾文学的全部情感样态,特别在殖民中后期,尖锐的痛感体验呈现逐渐减退消隐的过程,文本中的情感经验逐渐多样化,殖民主义或殖民现代性认知不但通过直接的痛感体验书写来进行,也出现了不同体验相混杂和单纯的快感体验的情感书写。相对于杨逵,殖民中后期多数作家的痛感书写并不直接来自明确的敌对力量,龙瑛宗笔下陈有三的痛苦更多出自殖民社会的精神折磨,它和主人公的个性气质一起共同构成了混杂纠结的情感,殖民社会结构对人物的压抑、下层社会的丑陋和民众性格的扭曲从不同角度激发人物的痛感体验,使之成为被殖民者绝望精神状态的写照。陈有三感受的台湾的落后愚昧流露出现代性对他的教化,但殖民社会却没有提供他享有现代性的可能。陈火泉《道》的人物陈青楠纠缠在痛感和快感的双重体验中,因总督府专卖局的肯定而获得的愉悦与因不是日本人而不得升迁产生的愤懑交织在一起,不过这种对立情感均由同一个对象激发,而且愉悦最终战胜了愤懑,他仍然从这个带给他对立情感的对象那里看到了希望,自认为找到了成为日本人的路径,这使他的情感没有演化成真正的社会批判意识,毕竟在某种境遇中形成的愉悦体验很难转化为对这种境遇的彻底否定。反过来,《植有木瓜树的小镇》的社会批判几乎全部来自绝望的痛感体验,与结合痛感体验和左翼观念的杨逵式批判有所不同。殖民现代性带给周金波写作的基本情感则是快感体验,毫无疑问,睡在榻榻米上的《水癌》主人公先是沉浸于日式生活方式带来的愉悦感受,再从这种感受过渡到对皇民化政策的赞美,由情感到思想意识的过渡平顺自然,没有阻碍。与专注于从痛感体验延伸到对殖民社会罪恶的控诉相反,周金波专注于快感体验而赞美一切日本事物,榻榻米本是日本的传统事物,原无现代性可言,但因为源于文明的日本,它就能够带来现代性的愉悦。(12)这种爱屋及乌式的快感体验与殖民现代性认知似乎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因为殖民现代性的认同感太强烈,才会情绪化地认同现代性给予者的一切;因为在日本生活方式中感受到愉悦——“在塌塌米上开始过像日本人的生活!”——才会进一步理解和赞美殖民政策。《“尺”的诞生》中少年吴文雄将自己想象为日本士官的弟弟或亲戚,“他那快乐的幻想”确实带来了转瞬即逝的愉悦;尽管他在小学校外感受到深深的失落,但却与痛感体验相差甚远。
比较这些文本中快感/痛感的来源是颇有意味的。杨逵所传达的痛感体验来源于殖民者和压迫阶级,其批判指向单纯而明确;陈有三的痛感体验既来源于殖民现代性,也来源于非现代性因素,它们从两个方向压迫着他的灵魂,人物在双重痛感体验中走向毁灭,又通过毁灭实现了殖民社会批判,陈有三的命运埋葬的不仅是传统的丑陋,还有被殖民者的现代性幻想。两位作家上述文本的共同情感特征是痛感体验控制了文本的基本情感走向且缺乏快感体验,尽管痛感内涵不尽相同:来自殖民者的是压迫性的、引发屈辱和愤怒的痛感;来自传统落后面的是接受现代文明的知识分子感知包括自身在内的民族性格负面因素带来的切肤之痛。在陈青楠那里,情感经验增加了快感成分,而且两种对立的感受来自同一个对象,即殖民者既带来痛感,也带来快感,后者使人物看到了希望,实现了皈依和认同。到了周金波,情感经验再度出现两个来源,但与杨逵写作的痛感来源相反,他的痛感完全不来自殖民者,而来自被殖民者的愚昧落后,也就是非现代性因素;同时他将快感来源指向殖民现代性,这一点又与龙瑛宗截然不同。同一个对象,在杨逵和周金波的文本中激发的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情感,如果说上述文本对殖民现代性的态度呈现从批判到肯定的过渡的话,杨逵和周金波恰好处于这一过程的两级。
在两极之间还存在一些较为含混的情感经验,或者说其痛感或快感不那么直接和明确,吕赫若和张文环的写作就是如此。如果比较两种情感经验的话,痛感体验的来源相对明确一些,无论是吕赫若的《月夜》、《庙庭》、《财子寿》,还是张文环的《阉鸡》、《论语与鸡》等,均指向传统的落后性,情感表达倾向于沉郁苍茫或略带讥讽,但与殖民语境没有直接关联;在快感体验方面,张文环对《重荷》少年从公学校获得的愉悦的处理如前所述,以儿童视野回避了殖民性;无独有偶,吕赫若《木兰花》中铃木善兵卫的照相机带来的惊奇也是从儿童的眼光中流露的,加之《邻居》中善良的日本夫妇,他们共同改变了以往的殖民者想象,隔离了体制化的殖民现代性,使快感来源落实到了个体的人与人性上面,从而同样回避了对殖民现代性的直接的价值判断。
如果将文本内涵扩大到殖民社会容器之外,我们会发现另一些从现代性视野展开的观察,而且依然是从情感经验开始的,那就是吴浊流、钟理和书写大陆经验的文本,如《南京杂感》、《夹竹桃》、《泰东旅馆》等,大陆中国在这些文本中展现了社会贫困落后和人性丑陋堕落的一面,作者由此生发的痛感体验常常被当今的本土论述当作接受殖民现代性的台湾人不认同落后的、缺少现代性的大陆中国的证明。这样的结论忽略或刻意简化了这些痛感体验产生的复杂性,吴浊流、钟理和来到大陆,首先是因为他们把这里当作摆脱原有痛感体验的理想之地;其次,除了原乡的想象和古老文化的骄傲,他们对大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和现实处境知之甚少;再有,经历了殖民现代性的洗礼,他们虽然暂时离开了殖民社会,却仍然带着在这个容器中浸染的痕迹,因而无法回避以现代性的眼光巡视曾经寄托着理想的土地。由于共同经验的缺乏,他们的痛感和批判也与大陆知识分子存在差异,最为明显的是从“他者”位置,从大陆外部,或所谓“文明高地”的被殖民者立场看待祖国的,因而这种情感带有多面性。大陆中国引发的情感既不同于杨逵式的、由殖民压迫产生的痛感,也不同于周金波式的、完全处于殖民者位置对原有“自我”的否定,而是由于陌生感和理想幻灭导致的失望所生发的痛心疾首,况且他们的“他者”位置并不出于自我选择。此外,最初的痛感体验随着观察的逐渐深入而发生了变化,《南京杂感》的这段话代表着吴浊流的理解:
中国俨然像海,不论什么样的,全抱拥在怀中。……中国是海。是想填也无法填的海。是世界上不能没有的海。不知海的性质,而以为海是危险的地方,无可如何的地方,而顺其自然则不可;而想要清净这海的企图,也是不可能的。不如把海当海看待,才有办法解开我们的迷。(13)
文本最后,还有这样的表述:
忘了中国与日本有此不同的一面,徒然拿日本的尺度,拿“白发三千丈”做为夸言的标本,或责难其夸张过度,是非常不当的。忘了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离愁似个长”的下一句,断章取义,甚至因而以为对中国的某一方面洞见其非,不能不说是大大的谬说。(14)
这表明吴浊流没有从殖民者立场,以现代性作为绝对尺度看待和理解大陆中国,也说明他开始从最初的痛感体验中沉静下来,意识到对象的复杂性。
由于情感经验具有不确定性,与思想意识之间的关系也并非一一对应,即不能简单地将情感和意识完全等同,因此将情感当作意识形成的证据需要格外谨慎和耐心。在一些作家和文本那里,两者的关系较为直接,情感表述相对明确和一贯;而在另一些作家同一时期的不同文本或不同时期的文本中会出现彼此矛盾的情感表达。《南京杂感》存在从以现代性眼光审视大陆到现代性尺度逐渐淡化的脉络;20多年后的《无花果》中祖国军队的落后装备和精神状态引发的失望又重新浮现出现代性尺度。《夹竹桃》对民族弱点的近乎诅咒式的评价在作者“看到缅甸战线祖国勇士们活跃在硝烟弹雨下的英姿”(15)后也发生了改变。这一方面显示作家情感本身的复杂性,一方面说明情感面临新的刺激会发生变异,《无花果》现代性尺度的重现显然与光复后的政治生态密切相关。情感经验的背后存在着种种复杂多变的因素,其走向也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这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战后台湾的殖民现代性认知状况。
战后,殖民社会的诸多问题并未在台湾得到充分清理,其基本表现是,对殖民统治的复杂情感始终或隐或显地影响着台湾社会思潮和民众心理,“二二八”事件使本就对台湾社会缺乏深入理解的外省政治势力抓紧了意识形态控制和对异己力量的镇压,使反共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大批殖民后期坚持反思殖民主义的台湾知识分子战后大多左倾,成为国民党政权的清算对象,殖民主义倒成了避而不谈的潜在问题。殖民体制和独裁体制被有意无意间加以比较,曾经的殖民现代性痛感体验被专制的压迫感所置换,而现代性快感却被保留,因为后者似乎成为对抗独裁体制的精神力量或在专制面前保持心理优势的情感因素。(16)这样的结果是,当台湾社会民主化开始后,出于对威权时代的逆反和长期以来自身利益被忽视产生的不满,殖民现代性成为可借用的资源,用来抵御威权统治,进而转化为所谓本土特质的重要部分,并成为区隔台湾和所谓“外来者”,以及大陆中国的有效标记。在激进的本土论述中,殖民现代性快感被夸大,几乎成为全部快感体验的源头;外来者,更确切地说是来自大陆中国者,就成了全部痛感体验的渊薮。当快感/痛感来源被如此设定后,分散的经验逐渐凝固为总体的结构,殖民地“肯定”论述于焉浮现,原有的“抵抗”论述却日渐边缘化。(17)有趣的是这些体验的表述很多时候仍然是情感式或情绪化的,人们通过快感/痛感的描述,形成某种思想倾向和评判标准,这在“肯定”论述中更加明显,除少数明确肯定殖民主义的表述外,大多数的“肯定”论述诉诸情感,以含混、温情、浪漫化的方式赞美殖民现代性的舒适、现代、文明,以“中国人”和日本人对台湾的“好坏”和现代性程度的高低作尺度,唤起了一些曾经体验到和期待享有殖民现代性快感的人们的怀想和倾慕,使对殖民主义的批判和反思在温情脉脉中消弭于无形,逐渐形成了亲近前殖民者、远离大陆中国的文化心理取向。相比周金波式的快感表述,当今的“肯定”论述委婉曲折,渐进式地从情感上压缩“抵抗”论述的空间。
由于“肯定”论述与本土意识互为表里、彼此促进,且与现实政治斗争结合紧密,这种从快感/痛感体验出发的感觉结构已经演变为权力话语,使寻求多元化的台湾社会在地理、文化、历史、血缘诸中心相继被瓦解之际(18)形成了新的话语中心,当这些论述运用这一话语以回避对殖民主义的清理时,已经在瓦解原有论述中心的理念下重新建构了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并使自身陷入自我解构的处境。在“肯定”式情感结构向权力话语过渡的过程中,也存在这样的理论建构,其特点是以理论回避价值判断,把相对明确的意义含混化,筛选符合理论建构的材料来印证现代性对台湾的正面意义。例如,有研究者以双重边缘(19)的说法将殖民地台湾知识分子对殖民主义的抵抗解说为追求纯正现代性的行为,在突出了东方式殖民主义及其与被殖民者同文同种的特质后,试图说明殖民地台湾在寻求一种超越殖民主义的现代性并由此建构自身的民族主体意识。这种论述以现代性既覆盖了殖民性,又遮蔽了民族性,似乎可以实现既超越日本殖民主义,又超越原有中华民族主义的目标,十分符合当下瓦解既往话语中心的潮流,但却并不符合当时台湾民众反抗殖民统治、寻求民族解放的实际状态。事实上,民族传统一直是台湾抵抗殖民主义的重要思想和精神力量,这在与大陆五四运动对传统的清算相对比时更加明显。(20)知识分子通过日本接受西方现代性,却无法从殖民现代性中提炼“正宗”的现代性来抵抗东方的殖民主义,(21)即便东方殖民主义包含的现代性具有“二手性”,它仍然是台湾现代性的根本来源,且与殖民性原本就是一体两面,赖和这样的思想启蒙者也难以将二者截然分离,他们(包括吕赫若、张文环等)能做的是在表现对文明和进步的向往时尽量回避其殖民印记。
对殖民主义“肯定”或“否定”论述的“超越”表面上似乎能够摆脱对立论述的纠缠,但在对殖民主义,包括其精神和情感遗存未经辨析清理的情况下真正的超越是否可能?或者这种“超越”只是主体性建构中的策略?无论如何,“超越”论述建构在某种情感经验的基础之上,可以说是那些含混模糊的情感经验的明确和“中性”的说明。
以上对殖民地台湾新文学情感经验的粗略分析其实仅仅是问题的提出,还有许多复杂现象有待说明,比如,不同的情感经验怎样统合为一个时期的基本情感结构;殖民主义引发的痛感/快感及其遗存的产生机制究竟如何;情感经验与文学文本显现的思想倾向是否是直接对应的关系;当以“对接受殖民现代性是否存在内心的犹疑与挣扎”来区分皇民作家和同时代其他写作者的时候,这种“内心的犹疑与挣扎”究竟是如何产生的等等。在同一个殖民和后殖民语境中,毕竟存在着相似境遇和经验的人群中文化抗体的强弱之别,需要进一步探索的就是这些差异背后的东西。
注释:
①《“同化”の同床异梦》,陈培丰著,台湾麦田出版公司2006年,第210页。
②例如,台湾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诉求是设置台湾议会,并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其实质是争取权力;但未能实现最终目标,只有到殖民晚期才出现有限度的地方议会自治。这说明被殖民者对现代性的追寻要依赖殖民者有选择的“给予”。
③这里借用生物学概念,所谓文化抗体指生存于某一文化环境中的人群对异质文化的免疫力,在殖民社会特指为保存民族文化或维护民族主体性而对殖民同化的抵抗。
④相关论述见“蓝博洲文集”《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台湾作家》,台海出版社2005年版。
⑤〔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6、139、140页。威廉斯还指出:“我们谈及的正是关于冲动、抑制以及精神状态等个性气质因素,正是关于意识和关系的特定的有影响力的因素——不是与思想观念相对立的感受,而是作为感受的思想观念和作为思想观念的感受。”“从方法论意义上讲,‘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是一种文化假设,这种假设出自那种想要对上述这些因素以及它们在一代人或一个时期中的关联作出理解的意图,而且这种假设又总是要通过交互作用回到那些实际例证上去。……它并不比那些早已更为正规地形成了结构的关于社会事物的假设简单多少,但它却更适合于文化例证的实际系列范围。历史上如此,在我们现时的文化过程(它在这里有着更重要的关系)中更是如此。这种假设对于艺术和文学尤为切题。”见《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第141、142页。
⑥赵国新:《情感结构》,《外国文学》2002年第5期。
⑦阎嘉:《情感结构》,《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3期。
⑧威廉斯所说的“凝固的形式”指各种明确的范畴、意识形态,不变的社会普遍性等,是与变化的、生动的、能动的因素相对应的事物。那些变化的、生动的、能动的因素,如感觉经验等,可能会被习惯性地转化为凝固的形式。
⑨〔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⑩与痛感体验相反的则是快感体验,这一概念的使用受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司晨的学位论文《早期革命文艺的快感形态研究》(2009年)的启发。
(11)文学研究越来越偏重理论对文本的直接切割使研究者逐渐远离了对情感表达的关注,或者简单地将其放入艺术表现范畴。本文尝试的就是寻找情感与思想意识之间可能存在的并不具有确定性的联系。
(12)吕正惠《抉择:接受同化,或追寻历史的动力?——战争末期台湾知识分子的道路》已注意到“‘塌塌米’本身则是纯日本事物,跟‘现代化’的‘文明进步’毫无关系。”并提出了“二手现代化”的说法。见“亚洲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经验——地区冲突与文化认同”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文化论坛2007年10月,第150页。
(13)(14)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4·南京杂感》,台湾远行出版社1977年版,第89页。
(15)张良泽编:《钟理和全集6·钟理和日记》,台湾远行出版公司1976年版,第13页。
(16)许多回忆文章、杂感或访谈录都记载了人们回忆当时外省人来台对现代文明的陌生,以及回忆者由此产生的诸多笑谈和鄙夷,流露出“文明人”的优越感。
(17)对殖民主义的“肯定”和“反抗”是一种概括性的说法,散见于一些研究者的论述中,如《同化の同床异梦》第八章“结论”就分析了这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并以“肯定论”和“反抗论”概括之。但文化思想界并没有两种倾向的大规模直接交锋。“肯定”式思维通常以情感和心理方式渗透于民间,以直接或委婉地肯定殖民现代性作为重要表现形式。
(18)全球化时代的思想理论界普遍存在消解既往话语中心的冲动,似乎历史、民族等传统话语论述早已过时、落伍,在具体社会活动中也是如此,台湾原住民工作者张俊杰指出,为了争取权益,讨回公道和正义,他们在寻找新的言说方式,因为历史、民族、血缘论述在台湾已经没有说服力。源自张俊杰《从台湾原住民角度看两岸关系》的演讲,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文化论坛”第38讲,2008年12月12日。不过冷战后诸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911”的发生显示的民族、宗教、文化冲突表明这些传统话语远未失去其作用。
(19)即日本处于西方殖民主义的边缘,台湾处于日本殖民主义的边缘,由此推导出这样一种结论:“日本殖民主义的东方性导致边陲精英们选择一种现代的和支持西方的策略来建构他们的反话语。”“他们不仅批判日本人不彻底现代的统治,而且也建构了他们自己作为现代或向往现代的民族主体。”见吴叡人《东方式殖民主义下的民族主义:日本治下的台湾、朝鲜和冲绳之初步比较》,“亚洲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经验——地区冲突与文化认同”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文化论坛2007年10月,第164页。
(20)战后来台的大陆作家陈大禹曾谈到“台湾的反侵略斗争,有点矫枉过实的现象,就是保留前清所遗留的法制与生活习惯,作为反抗侵略的表现……但在事实上,这些封建残遗的思想习惯,无论如何是不适于二十世纪的今天的。”《1947-1949台湾文学问题论议集》,台湾人间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这是当时两岸知识分子对传统持不同态度的又一说明。
(21)蔡培火、李春生等是台湾少数的具有基督教背景的知识分子,蔡氏提倡的罗马字或许可谓以西方现代性对抗东方殖民主义的实际行为,但它不仅没有得到殖民者的认可,也没有被民众所接受,因为后者认为这是放弃汉字,背离了文化传统。
标签:现代性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文学论文; 大陆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后殖民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