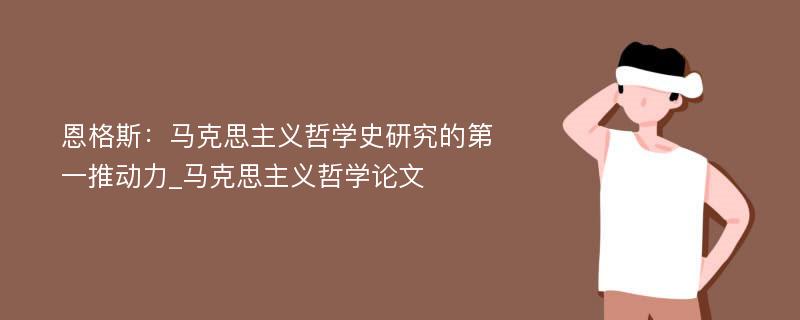
恩格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第一推动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推动力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马恩对立论”这个当代神话的形成与演化过程中,法国著名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吕贝尔发挥了一种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因为正是他改变了对立论的传统论证思路,以思想史研究的形式论证了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对立,从而使对立论在莱文手中被升级为一种基于主观故意的“欺骗”论。那么,历史的真相是否真的像吕贝尔猜测的那样呢?回答不仅是否定的,而且正相反:恩格斯晚年不仅非常重视马克思早期手稿和书信的出版工作,而且还有意识地通过为马克思撰写传记、为马克思的著作撰写新版序言等方式引导同时代的读者将注意力集中到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去,以此来历史地、准确地理解其基本理论本身,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形成提供了最初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第一推动力。
作为革命导师,恩格斯在宣传马克思和他本人这个问题上始终非常谨慎,一向反对为马克思和他本人举行任何公开的庆祝活动,特别是在生前举行这样的活动,“除非这样做能够达到某种重大的目的”[1](P.309)。在马克思生前,他只是应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请求为党的出版物《人民历书画刊》写过一篇《卡尔·马克思》,以简明扼要的方式向党的基层群众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思想发展过程及其理论贡献,并将马克思低调地定位为“第一个给社会主义、因而也给现代整个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基础的人”[2](P.328)。在同时期创作的《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还在驳斥一些错误思潮的同时对马克思的思想来源及其革命性的贡献进行过一些零星的说明。恩格斯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和马克思清楚地看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一时期的巨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降低党的理论水平为代价的,马克思的学说因此出现了被庸俗化的可能性,只有用正确的学说去引导工人群众,“有非常健康的本性”的工人群众才能克服思想上的“幼稚病”。[2](P.345)综观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前所做的这些宣传工作,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此时最关注的是对马克思的两个伟大理论贡献及其意义的阐发,同时,他也对马克思开始理论活动的社会环境以及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时间进行了简要但却重要的描述。[2](P.328)
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更加不遗余力地宣传马克思的理论。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恩格斯最初将《资本论》遗稿的整理出版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来做。但在这项伟大工作的艰难进行中,我们看到,恩格斯越来越重视对唯物史观形成过程的描述:在从1886年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哲学的贫困》与《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各个新版序言,到1892年的《马克思,亨利希·卡尔》等一系列著述中,恩格斯不断地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强调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是由马克思独立发展出来的,马克思在1845年春就把这一思想“考虑成熟”了[3](P.252)。与这种关切相一致,恩格斯还越来越关注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1892年,恩格斯为马克思整理了一张详细的“已经发表的著作”目录[4](PP.400-404),这使得人们第一次比较完整地了解到马克思在1848年以前的著述情况;1895年初,当恩格斯得知能够找到完整的《莱茵报》时,他立刻准备出版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论文,进而形成了一个出版马克思全集的计划。[5](PP.445-447)吕贝尔攻击恩格斯有意识地忽略马克思柏林笔记、克罗茨纳赫手稿、巴黎手稿、布鲁塞尔笔记等早期手稿的出版是非常不公正的。事实上,恩格斯肯定马克思的早期手稿“的确有巨大价值……我的夙愿是一有可能即出版这些作品”,[5](P.341)他之所以没有能够完成这一夙愿,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时间问题:“一个人绝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内,既要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安排其他遗著的出版,又要同各个社会主义政党保持多方面的联系。”[6](P.511)要知道,当恩格斯于1884年3月花了一年时间方才简单整理好马克思装满了“六个大箱子”的全部遗稿时已经是64岁的老人了。
正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一个人继续担任欧洲社会党人的顾问和领导者……(各国社会党人——引者注)都同样向恩格斯征求意见,请求指示。他们都从年老恩格斯的知识和经验的丰富宝库中得到教益。”[7](P.96)既然指导实践的工作如此繁重,那么,恩格斯为什么还会这样关注追溯唯物史观的形成这种似乎非常学究的理论工作呢?
第一,它关系到如何保卫马克思、反击同时代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的中伤与诽谤这一原则问题。马克思学说的广泛传播彻底打破了同时代资产阶级学者的沉默阴谋,因此,一再有资产阶级学者跳将出来对马克思进行恶意中伤与诽谤。这一切在马克思去世后开始进入高潮。在哲学上,同时代资产阶级学者曲解马克思哲学的实质,不是把它同黑格尔哲学混同起来,就是将它和费尔巴哈哲学等同起来。在经济学上,他们要么攻击马克思剽窃了一个他根本就不知道姓名的洛贝尔图斯的学说,要么干脆宣称唯物史观是自己发现的。在与这些资产阶级学者就具体问题进行逐一斗争的同时,恩格斯感到越来越有必要澄清唯物史观的由来与发展,因为一旦史实得到澄清,中伤与诽谤就会不攻自破。
第二,它是教导青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需要。凡是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书信卷的人可能都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印象:恩格斯在教导伯恩斯坦和考茨基这两位学生方面投入了极大精力,他往往要用很大的篇幅就一些具体问题给后者以详细的指示。其所以如此,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后者对作为马克思学说基础的唯物史观缺乏真实的理解。让恩格斯感到忧心的不仅是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两人的哲学水平,事实上,他还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青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水平始终感到忧虑:“二十年来唯物史观在年轻党员的作品中通常只不过是响亮的词藻。”[8](P.310)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当19世纪80年代前后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完成了理论的创立,这使得他们是按照一条截然相反的顺序(即主要是从《资本论》出发)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加之他们是在一种敌视德国古典哲学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因此,他们对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基础的唯物史观的真实内涵和革命意义缺乏深刻的理解,非常容易成为一些流行哲学思潮的思想俘虏,从而危险地滑向唯物史观的对立面(他们后来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旦我们明白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恩格斯创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真实意图了:他不过是在号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多学习一点哲学和哲学史,因为马克思和他本人创立的唯物史观是黑格尔学派解体过程中“唯一的真正结出果实的派别”[9](P.242),而“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人”。[9](P.258)
如果仅仅从数量上看,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形成与发展的相关论述并不多,而且也不集中,但对于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形成而言,它们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这绝非仅仅因为恩格斯是历史上第一个自觉从事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与发展史研究的人,而更重要的在于:
第一,他预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必要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学科地位奠定了基础。普列汉诺夫、梅林和列宁是最先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之必要性的三位马克思主义者,也正是他们的工作勾勒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大致轮廓。在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依然健在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会想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呢?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现实的政治与理论斗争使他们充分意识到了恩格斯的开拓性工作的重要性:要想战胜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和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修正主义者的攻击与歪曲,就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特别是它的形成史。半个多世纪后,当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在苏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时候,其依据事实上也正来自恩格斯的指示精神。
第二,他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方法论基础。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哲学史研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正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确立了一个典范——让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明白如何研究社会历史、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条件,进而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哲学观点。”[9](P.692)同样还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示范着将上述方法落实到对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的研究中去,让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掌握了研究的基本要领进而有所发展:作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俄文版译者,普列汉诺夫遵照恩格斯的精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前的哲学思想的关系做了一般分析;梅林不仅完成了恩格斯的嘱托,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遗著,而且详细分析了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发展与德国当时社会政治发展进程之间的内在互动关系;列宁则综合了前两者的合理成果,系统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方法体系。
第三,他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简要而宝贵的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路线图。关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恩格斯从历史见证人的角度为后人提供了两点极其重要的信息:马克思是在《德法年鉴》时期转向社会主义的[1](P.393),其标志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2](P.329);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大致出现在1845年春天[3](P.252),并在《哲学的贫困》中走向成熟[4](P.205)。列宁正是依照这一简要的路线图大致探察出我们今天广泛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分期模式。
最后,我愿意用列宁《卡尔·马克思》中的一句话来结束我们今天关于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讨论。这句话是列宁针对第二国际内部当时业已出现的将恩格斯与马克思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而说的:“要正确评价马克思的观点,无疑必须熟悉他最亲密的同志和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著作。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10](P.94)我以为这句话在当代中国尤其具有现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