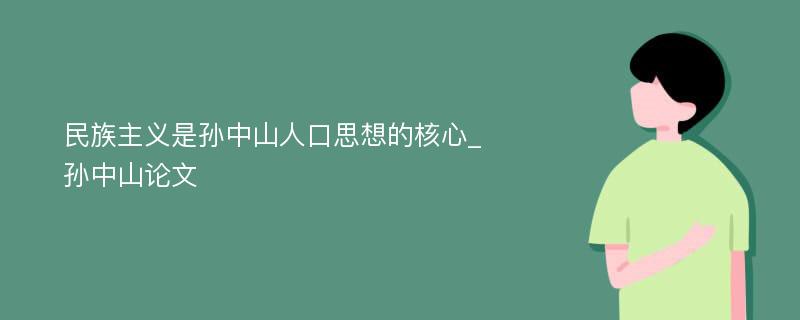
民族主义是孙中山人口思想的核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人口论文,核心论文,思想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以来,伴随着人口学的勃然复兴和史学研究的纵深发展,孙中山的人口思想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涉及此专题的中国人口思想史和人口史著书,以及专题的学术论文已有十种以上。我在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中,(注:参见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230—237页。 )也曾对此进行了概略的评说。无庸讳言的是,孙中山毕竟不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人口思想家,他的人口思想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涯中逐步形成的,且有一些前后矛盾之处,这就对研究孙中山的人口思想带来一定的难度。我以为,正确理解孙中山的人口思想,必须将此纳入孙中山的革命实践和三民主义思想体系中综合考察,方可避免就人口论人口的弊端,而把握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则是理解其人口思想的钥匙。
一
先秦以来,“众民说”与“寡民说”就成为中国人口思想中争议的焦点。时至近代,是主张增加人口还是减少人口,仍是思想家们无可回避的问题。对此,孙中山的看法是前后矛盾的。
1894年6月,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详尽论述其“富强之大径,治国之大本”四事: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接着,以“时势之危急恐不能少须”的忧虑之情发其议论:
“盖今日之中国已大有人满之患矣,其势已岌岌不可终日。上则仕途壅塞,不则游手而嬉,嗷嗷之众,何以安此?明之闯贼,近之发匪,皆乘饥馑之余,因人满之势,遂至溃裂四出,为毒天下。方今伏莽时闻,灾荒频见,完善之地已形觅食之艰,凶祲之区难免流离之祸,是丰年不免于冻馁,而荒岁必至于死亡。由斯而往,其势必至日甚一日,不急挽救,岂能无忧?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胡以养民?不养民胡以立国?”(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页。)
1924年1月27日至3月2日, 在孙中山所作的关于民族主义的六次演说词中,他不仅不同意当时中国人口已经太多的观点,而且为乾隆以来“中国人口总是不加多,外国人口日日加多”的状况感到极大忧虑,“觉得毛骨耸然”。孙中山讲道:
“一百年之后,全世界人口一定要增加好几倍。……中国是全世界气候最温和的地方,物产顶丰富的地方,各国人所以一时不能来吞并中国的原因,是由他们的人口和中国的人口比较还是太少。到一百年以后,如果我们的人口不增加,他们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们便用多数来征服少数,一定要吞并中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不但是失去主权,要亡国,中国人并且要被他们民族所消化,还要灭种。”(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96页。)
孙中山是一位真正忧国忧民的爱国之士。他对“人满之患”的忧虑跃然纸上,又对“人不加多”的忧虑溢于言表。两种忧虑的截然不同,正反映了孙中山政治思想的转变轨迹。
1894年中日甲午战前,孙中山的主要经历是习医悬壶及“求知当道”,而其思想主流仍属改良主义范畴。《上李鸿章书》正是孙中山改良思想的代表文献,他开宗明义讲道:“当今光(风)气日开,四方毕集,正值国家励精图治之时,朝廷勤求政理之日,每欲以管见所知,指陈时事,上诸当道,以备刍荛之采。嗣以人微言轻,未敢遽达。”他推崇李鸿章有“育才爱士之心”,报陈富强治国之四事,希望李鸿章“有以玉成其志。”(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16、18页。)《上李鸿章书》是由孙中山1894年1月拟就,后经陈少白、 王韬及郑观应润色修改而成的,其“四大之纲”与郑观应《盛世危言》有明显的师承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改良主义思想家们如薛福成、梁启超、严复等人,在论及当时中国人口问题时,都不同程度地承认或强调“人满之患”。孙中山以人满之患,危机四伏立论,希望当道者采纳其改革意见,这是符合其当时思想轨迹的。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失败之际,甲午炮火已弥漫于黄海和朝鲜半岛,而清朝统治者仍歌舞升平,准备庆祝西太后六十万寿大典。孙中山的改革理想完全被严酷的社会现实破灭,他继而认识到,清政府已不可救药,“和平方法,无可复施”,余下来的只有革命一途。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在入会会员的誓词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成为同盟会的宗旨,接着,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正式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注:《孙中山全集》第六卷, 第237页。)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作为民族主义的反满和反帝始终是三民主义的首要组成部分,但辛亥革命前后反满和反帝又是有所侧重的。大体而言,辛亥以前现实斗争的需要把民族主义集中到反满上,从《兴中会章程》到《同盟会宣言》,反满都是一以贯之的革命口号。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甚至这样讲道:“维我中国开国以来,以中国人治中国,虽间有异族篡据,我祖我宗常能驱除光复,以贻后人。今汉人倡率义师,殄除胡虏,此为上继先人遗烈,太义所在,凡我汉人当无不晓然。”(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6页。)
辛亥革命,“只提出反满的口号,未曾提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以致革命党人一经推翻满清政府,便多数认为民族主义革命已告成功。”(注:《胡汉民先生在俄讲演录》第1集,第2页。)甚至孙中山也一度将民族主义置之一旁,中华革命党党章和宣言就没有再提民族主义的任务。然而,民国后的现实教育了他,他很快纠正了这一错误,认识到,清朝虽已被推翻,但独立的中国并未出现,中国仍在帝国主义的宰割和支配之下,他告诫同志,“而谓满清已倒,种族革命已告成功,民族主义即可束诸高阁矣”。由是,孙中山再次强调民族主义的革命纲领,并且愈来愈朝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方向前进。孙中山忧虑中国人口增加缓慢,而列强人口增加迅速,以至百年后,中国有亡国灭种之危险的思想,正是在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主义旗帜下展开的。
二
在《民族主义》第一讲中,孙中山首先强调,“要救中国,想中国民族永远存在,必要提倡民族主义。”他以世界近代历史发展的事实,介绍了欧美各国和日本以民族立国而独立强盛的情况,认为:“用世界上各民族的人数比较起来,我们人数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也应该和欧美各国并驾齐驱。但是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8—189页。 )同中国“没有民族精神”一样,列强人口日益增多,而中国人口则不见增多,在孙中山看来,这同样是一种亡国灭种之忧。他以百年来列强人口和中国人口的增长作比较,认为,美国增加十倍,英国增加三倍,日本也是三倍,俄国是四倍,德国是两倍半,法国是四分之一,而中国自乾隆以来,近二百年时间仍是四万万。这样,“到一百年以后,如果我们的人口不增加,他们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们便用多数来征服少数,一定要并吞中国”。到那个时候,中国仍有亡国灭种的危险!
在2月3日的《民族主义》第二讲中,孙中山开篇即讲道,“自古以来,民族之所以兴亡,是由于人口增减的原因很多,此为天然淘汰。”(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97页。)他认为,中国此时同时受到天然力、政治力、经济力三种压迫,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没有过的。在天然力方面,孙中山仍然强调了中国在人口方面受到西方人口迅速增加的压迫,认为“天然力虽然很慢,也可以消灭很大的民族。”并举例指出:“美洲在二三百年前完全为红番之地,他们的人数很多,到处皆有;但从白人搬到美洲之后,红番人口就逐渐减少,传到现在,几乎尽被消灭。由此便可见天然淘汰力,也可以消灭很大的民族。”(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98页。)在政治力方面,孙中山历数边疆地区大片领土丧失,内地许多地方也被列强瓜分霸占的事实,认为,“中国人从前只知道是半殖民地,便以为很耻辱,殊不知实在的地位还要低过高丽、安南。故我们不能说是半殖民地,应该叫做次殖民地。”(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02页。)在经济力方面,孙中山又历数了中国海关、银行、交通运输为列强所控制,租界与割地的赋税、地租、地价、列强特权经营,投机事业、战争赔款等,总损失不下十二万万元,他认为,“专就这一种压迫讲,比用几百万兵来杀我们还要厉害。”(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09页。)
应当指出的是,孙中山虽然将人口问题提高到关乎民族存亡的程度去认识,把人口问题同政治、经济相提并论,作为民族主义的三大问题来看待,但他绝不是人口决定论者。在孙中山看来,人口的消长是一种天然力,而政治力和经济力则是“人为的力量”,“这两种力关系于民族兴亡,比较天然力还要大”,(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97页。)“还要快而且烈。”(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98页。)在《民族主义》第五讲中,孙中山甚至从时序的角度对三种力的压迫作了概括:“中国现在受列强的政治压迫,是朝不保夕的;受经济的压迫,刚才算出十年之后便要亡国;讲到人口增加的问题,中国将来也是很危险的。”(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7页。)
同同时期的人口思想家相比,对马尔萨斯人口论和盛极一时的“黄祸论”的批判,是孙中山人口思想的异彩之处,而这种批判同样是以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富强的国家立论的。早在1912年,孙中山应中国社会党之邀所作的演讲中,他就树起了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旗帜。孙中山讲道:“是时英格物家马耳国(今译马尔萨斯)者,著有《人类物产统计表》一书,其主脑谓物产之产额,有一定之限制,而人类之蕃息,为级数之增加,据二十五年一倍之说,推之将来,必有人多地少之患。生众食寡,天降疫疠,国际战争,皆所以减少人口之众,防止孳生之害,而合于世界演进之原理。于是乎国家殖民政策缘此发生,弱肉强食,劣败优胜,死于刀兵者,固属甚多,其受强族之蹂躏,沦落而至于种族灭绝者,又比比皆是也。”(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 第513页。)这里, 孙中山虽然是以社会主义学说的对立物介绍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但他用“种族灭绝”的概括之语倒是值得重视的。后来,在《民族主义》的演讲中,孙中山更以法国人口减少为例,告诫中国青年不要中了马尔萨斯学说的毒。在扼要介绍马尔萨斯人口论原理后,孙中山讲道:“法国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国都要多,因为马尔萨斯的学说宣传到法国之后很被人欢迎,人民都实行减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为中了马尔萨斯学说的毒。中国现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马尔萨斯学说所染,主张减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国已经知道了减少人口的痛苦,现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国的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并存。”(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95页。)
1904年8月31日, 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中,对当时盛行的“黄祸论”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批驳:
“有人时常提出这样一种在表面上似乎有道理的论调,他们说:中国拥有众多的人口和丰厚的资源,如果它觉醒起来并采用西方方式与思想,就会是对全世界的一个威胁;如果外国帮助中国人民提高和开明起来,则这些国家将由此而自食恶果;对其他各国来说,他们所应遵循的最明智的政策,就是尽其可能地压抑阻碍中国人。一言以蔽之,这种论调的实质就是所谓“黄祸”论。这种论调似乎很动听,然而一加考察就会发现,不论从任何观点去衡量,它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个问题除了道德的一面,即一国是否应该希望另一国衰亡之外,还有其政治的一面。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只有当中国人被某一外国加以适当训练并被利用来作为满足该国本身野心的工具时,中国人才会成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如果中国人能够自主,他们即会证明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再就经济的观点来看,中国的觉醒以及开明的政府之建立,不但对中国人,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全国即可开放对外贸易,铁路即可修建,天然资源即可开发,人民即可日渐富裕,他们的生活水准即可逐步提高,对外国货物的需求即可增多,而国际商务即可较现在增加百倍。能说这是灾祸吗?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正像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从经济上看,一个人有一个穷苦愚昧的邻居还能比他有一个富裕聪明的邻居合算吗?由此看来,上述的论调立即破产,我们可以确有把握地说:黄祸毕竟还可以变成黄福。”(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3—254页。)
孙中山从道德、政治、经济三方面批驳“黄祸”论,驳斥了帝国主义者的谬说,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他满怀信心地讲道:“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物换星移,今天,孙中山这一思想仍然闪耀着绚丽的光辉。
概而言之,孙中山的人口思想是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即为一种民族主义人口论。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孙中山并没有确切地了解世界人口变动的真实情况(如他对美国等国的人口估计失实),因而将人口因素夸大到关乎民族存亡的程度。但是,他将人口压迫,同政治压迫、经济压迫一起看作为民族主义的三大问题,他对马尔萨斯人口论和“黄祸”论的无情批驳,都是从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振兴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立场出发的,而这恰是同时代的其它人口思想家难以企及的。
三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人口论,还有其深刻的思想来源,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在我看来,除了中国传统的“民众论”思想影响外,孙中山更多地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和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人口经济思想,则是孙中山民族主义人口论的直接来源。
进化论是孙中山民族主义人口思想的理论基础。“动物之强弱,植物之荣衰,皆归之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进化学者遂举此例,以例人类国家,凡国家强弱之战争,人民贫富之悬殊,皆视为天演淘汰之公例。”(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07页。)孙中山不仅熟悉这种风靡一时的进化论,而且把人口演变看作为进化原则支配的社会生物现象。在《民族主义》第二讲中,孙中山把人口增减径直称为“天然淘汰力”,认为,“人类因为遇到了天然淘汰力,不能抵抗,所以古时有很多的民族和很有名的民族,在现在人类中都已经绝迹了”。依孙中山看来,中国民族在四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虽然也曾经受了许多次天然力的影响,但经过“天时人事种种变更”,中国仍有四万万人口,这是因为“我们民族所受的天惠,比较别的民族独厚”,(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97页。)“此后中国的民族,同时受天然力、 政治力和经济力的三种压迫,便见得中国民族生存的地位非常危险。”(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98页。)在第三讲中,孙中山更以进化论为基础,再次谈到列强对中国的三种压迫:“照进化论中的天然公例说: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优者胜,劣者败。我们的民族到底是优者呢,或是劣者呢;是适者呢,或是不适者呢?如果说到我们的民族要灭亡要失败,大家自然不愿意,要本族能够生存能够胜利,那才愿意。这是人类的天然思想。现在我们民族处于很为难的地位,将来一定要灭亡。所以灭亡的缘故,就是由于外国人口增加和政治、经济三个力量一起来压迫。”(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17—218页。)
亨利·乔治的人口经济思想也是孙中山人口思想的重要来源。早在1912年《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孙中山对亨利·乔治的学说就有概括介绍,他讲道:“美国有卓尔基亨利(按:即亨利·乔治)者,一商轮水手也,赴旧金山淘金而致富,创一日报,吹鼓其生平所抱之主义,曾著一书,名为《进步与贫困》。其意以为,世界愈文明,人类愈贫困。盖于经济学均分之不当,主张土地公有。其说风行一时,为各国学者所赞同。其发阐地税法之理由,尤为精确,遂发生单税社会主义之一说。”(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13—514页。 )孙中山非常推崇亨利·乔治的学说,他曾在不同场合把自己的主张同亨利·乔治的单税论联系在一起,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体系中的民生主义就是以亨利·乔治学说为蓝本的。(注:参见夏良才:《论孙中山与亨利·乔治》,《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 为了阐述“单一土地税”理论,亨利·乔治在《进步与贫困》中用很大的篇幅对马尔萨斯人口论进行了猛烈批判,他指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把贫乏和穷困的原因归之于人口过剩,我认为它不是由于自然界的吝啬,而是由于社会的不公正。我认为,因人口增加而新添的嘴,并不比原有的嘴吃得更多,而他们所带来的双手自然会生产更多的东西。我认为,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人口越是增加,在财富的平等分配下,每个人所获得的享受也就更多。”(注:参见陶大镛:《亨利·乔治经济思想述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显然,孙中山的人口思想同样受到亨利·乔治的影响。所不同的是,孙中山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简单批判上,他将人口问题同政治、经济结合起来,作为民族主义的主要问题之一,具有鲜明的抵制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色彩。
这里还需指出的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人口思想对当时和随后的中国人口思想界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同孙中山一样,他的追随者廖仲恺也深受亨利·乔治学说的影响,并且翻译过《进步与贫困》的部分章节,发表于《民报》第一号上。廖仲恺曾严厉地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他认为,在文明进步的国家,人口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的比例关系正和马尔萨斯的论断相反,因为人口的增加有“自然的限度”,而发展生产的潜力则是很大的,“人口增加,断不会到可怕的程度,用不着那些灾害、罪恶、战争种种为人道之敌的东西来限制他。也不怕国家发达,文明进步之后,人口会弄到领土装不下的。所以‘人满之患’终归是一句傻话罢了”。他着重指出,中国的人口密度比西欧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低得多,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决不是什么“人满之患”,成问题的倒是“民穷财尽”。(注:廖仲恺:《中国人民和领土在新国家建设上的关系》,《廖仲恺集》(修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页。)而造成“民穷”的主要原因是地主对土地的垄断和对农民的剥削,所以他坚决拥护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另外,民国以来人口学界的“乐观派”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孙中山民族主义人口论的影响,他们或从国际战争的角度考虑,主张奖励人口生殖;或从增加劳动力资源、促进农业开发、发展工业化立论,反对盲目节制人口;也有人以为中国的贫困不是由于人口太多,而是由于经济制度的不合理。如蔡步青在其长文《马尔萨斯人口论与民生主义》中,就坚持“人口增加未发现若何过庶的状态,可以不必忧虑”,“许多人误会贫困就是人口过庶所产生的现象。如果放下冷静的头脑来考虑一番,却其中大大的有一个致贫困的总因。这个总因就是经济制度不好”。他认为,“中国现在民生问题的发生,不在人口问题,而在数千年相沿下来的经济制度之改良。”(注:见《指导》第23—25期。)应当说,尽管孙中山的人口思想中也存在一些不科学,甚至在今天看来是错误的东西,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
最后还需指出的是,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人口思想中,他不仅就中国当时人口问题的现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且就如何解决人口问题,提出了发展农业,移民垦荒,提高人口素质等重要主张,这些都是孙中山民族主义人口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有关论述颇多,兹不赘述。
标签:孙中山论文; 进步与贫困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民族主义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孙中山全集论文; 上李鸿章书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中国人口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