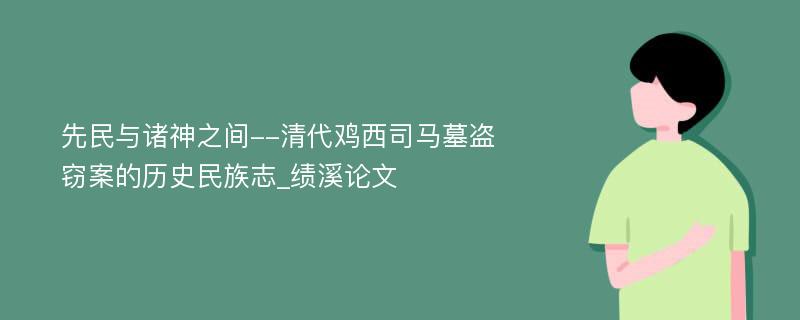
祖先与神明之间——清代绩溪司马墓“盗砍案”的历史民族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绩溪论文,司马论文,神明论文,清代论文,祖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资料与路径
在“十姓九汪”的徽州,汪公是汪姓的祖先,又是徽州的地方“土神”,是地域之神。在清代道光年间,围绕着徽州绩溪县登源汪公庙庙产和司马墓坟业的讼争,呈现了地域崇拜、宗族认同、绅权治理、祭祀礼仪、司法实践、风水观念、地权纠纷等要素的整体性历史实践。
以往的宗族制度和民间信仰研究均涉及祖先崇拜,而地域崇拜尽管牵涉到宗族的活动,但基本是在民间信仰研究的学术领域里得到解释的。在“民间信仰论模式”的解释体系中,祖先崇拜的观念和仪式被当作文化象征符号,以此探讨“中华帝国”的政治意识形态。武雅士(Arthur P.Wolf)在那篇影响深广的论文《神·鬼·祖先》中,根据在台北市郊三峡乡的田野调查,将民间观念中的神鬼观作了类型学的划分,即神象征帝国科层制中的官员,鬼象征危险的陌生人,祖先象征亲属关系。①而如此之分类,是基于中国人在地观念的“原始分类”,还是人类学家的象征论类型解释?武雅士在台湾做田野调查的亲密合作者庄英章通过细致的田野工作,对神、鬼、祖先的关系进行了再思考,他是在象征实践论的框架内进行解释的,只是更关注当地人在神、鬼、祖先观念方面“应用解决思维上的矛盾之处,从而促成其行为的合理性”,②并发现房头神崇拜这一“祖先和地方神明之间的一个中介象征,其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继嗣原则和居处原则之间的转换机制”。③
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则以台湾“山街”的田野经验,解释“地方性的仪式和崇拜与政府及其正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而不在于撰写这一制度的历史”。④在王斯福的研究中,地域性崇拜对于帝国科层制的象征意义,并不是简单的模仿和复制,而是有着地方社会历史实践逻辑的。然而,祖先崇拜作为地域信仰的一种,在王斯福的解释体系中,并没有涉及宗族组织的实践意义。
华琛(James L.Watson)在关于天后信仰的标准化问题上,探讨了“在文化标准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传统的一个方面——即由国家当局鼓励对被‘允准’(approved)神灵的信仰。”⑤虽然华琛也关注到地方士绅、宗族和民众在“神明标准化”过程中的实践角色,但主要关注王朝国家正统性的表述和治理,并且是在民间信仰的知识脉络里推进其问题意识的,对于宗族制度关注不多。
在宗族制度研究中,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的宗族模式论至今仍是不可越过的。弗里德曼虽也关注到祭祀、丧礼、风水、生死观等祖先崇拜的诸种仪式和观念表现,但他更关注宗族内部结构、宗族间的关系及宗族与国家的关系,特别是注意到基于地产分配而产生的不平等和宗族平均主义观念之间的纠结。⑥华如璧(Rubie S.Watson)沿着弗里德曼祭祀群理论的思路,研究了香港新界的宗族组织,呈现了宗族组织内部因地产支配的不平等而形成的社会分化,但丧仪、祭仪过程和墓地风水观念,则在一定程度上凸现了族人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世系群经济和政治的完整性有赖于超越财富和阶层差异的所有成员经常是物质层面的支持。因此,世系群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无疑在跨越富人与穷人之间鸿沟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⑦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宗族意识形态可以说是宗族制度的基本内涵,但在“制度论模式”的宗族民族志文本中,观念和仪式的意义是在宗族结构的框架内得到解释的。⑧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学者试图整合这两个看似相对独立的“知识领域”,或者从经验层面,将祖先崇拜和地域信仰融合在所研究的经验事象中。以研究道教史起家的法国汉学家、民俗学家劳格文(John Lagerwey)在与中国学者合作的华南客家研究中就发现祖先和神明是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他就此解释道:“乡村生活为两种相互渗透的社会秩序与民俗所支配:其一与宗族社会结构有关;其二则与神明崇拜有关……如果神明与祖先是传统社会宗教崇拜的核心,那么举行崇拜的地方则取决于一个象征系统——风水原则。”⑨劳格文及其民俗学合作者的这一研究可以被概括为“历史民俗志”,对祖先与神明通过风水原则结合起来由民俗事象形成的地域历史过程描述有余,而对地域社会秩序再生产的人的历史主体性则呈现不足。
科大卫(David Faure)也认为神明祭祀和宗族制度不可分割:“虽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把祭祀神灵与祭祀祖先区分开来,但是,中国的广义‘宗教’,必须把祖先信仰与祖先祭祀包括在内。”与此相应,其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在于:“我们亟须做大量的开拓研究,研究人类的活动如何影响区域社会的形成……其中一个共同问题是:地方神灵与祖先何时被整合到王朝国家的意识形态之中?”⑩此前他与合作者刘志伟已将宗族看作一套与王朝典章制度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11)从而显示了试图整合政治经济分析和文化解释二元困境的努力。科大卫的学术团队在“神明与祖先结合的区域类型”及“正统化”历史实践的问题意识指导下,“走进历史田野”,试图通过呈现长时段历史时期在王朝典章制度和正统化意识形态支配下,祖先和神明的结合方式如何反映了地域社会秩序的形成过程。(12)
以往的研究使笔者认识到,汪公信仰不仅是象征论意义上的仪式,也是家族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呈现了社区的社会再生产机制,映射了地方民众的人格建构和宇宙观想象,更是王朝典章制度的治理手段,是对中国文化历史实践的整体论呈现。本文正是围绕清代绩溪司马墓讼争,在地域社会的历史脉络中解释汪公信仰如何将地域崇拜和祖先崇拜结合起来,更深层的问题意识则是揭示地域社会秩序场境中的整体动员机制。
这里有必要对“地域社会秩序场境”和“整体动员机制”两个关键词做进一步的阐释。“地域社会秩序场境”绕不开日本著名史学家森正夫的“地域社会论”。1981年,森正夫在一次地域社会史的研讨会上提出对此后日本史学界明清史研究卓有影响的“地域社会论”观点,指出,所谓秩序或秩序原理,与进行生命的生产或再生产的场所,即人们生存的基本场所紧密关联着,它对于整合那些构成这个场所的人们的意识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换言之,虽然孕育着阶级矛盾和差异,但面对着共同的再生产的现实问题时,每个人都处于共同的社会秩序下。这样由共同领导者统治下的被整合的地域场所叫做地域社会。这是和行政区划、市场圈等实体概念不同的方法概念。(13)虽然也不断有学者批评,但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这一概念,的确对后来的社会史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此后,日本明清史研究更关注地域社会形成的过程和内在秩序,而很少不加讨论地在行政区或市场圈的地域范围内研究区域社会史了。(14)岸本美绪由此提出“秩序场境”概念,某种程度上,森正夫的地域社会论所提出的,“正是一种不一定与明确的实体性团体范围相重合的‘场境’,或者说是一个人们在意识中共有的认识的、观念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内部,人们确认相互对立竞合的各种势力、承认自己的领导者、与他人形成结合关系、构成团体以及选择方针政策。这类似一种竞技比赛场境的形象,而所谓‘秩序’则可以比喻为参加比赛的人们所共有的关于竞技规则的认识以及对彼此行动所包含意味的理解。”(15)
本文提出“地域社会秩序场境”概念,不仅注重地域社会的观念史意义,更要将行政区划、市场网络(16)对于地域观念形成的意义纳入分析视野。比如行政区划对于研究者来说,不仅仅构成诸如“华南”、“江南”、“华北”、“西南”、“徽州”或某个省、府、县的地域及行政研究单位,还有其人文空间意义。施添福通过对岸里社地理区域的形成过程的研究,阐明了“地理区不是学者为了研究上的方便而切割出来的便利空间,而是需要经过阐释始能界定的未知领域”;(17)在关于清代土牛沟“番界”对竹堑地区地域空间的分隔的研究中,揭示出土牛沟行政区划造成了一个区域内部地域社会空间的分化,并孕育了不同的社会特质和社会经济特色。(18)在徽州地域社会史的脉络里发掘地方文献的历史民族志意义,不应将徽州不加讨论和反思地作为一个研究单位,而应在问题意识和方法论上揭示历史当事人的地域观念,注意特定历史事件所映射的徽州地方社会秩序运作的基本原则。
地域社会秩序场境不是在历史地理学背景下提出的,其题中内在地蕴含了一个地域社会秩序得以成立的运作原则,所谓的运作原则不是僵硬的理论法则,而是地域社会如何被组织起来的“整体动员机制”,它是流动的、鲜活的人的历史实践。董晓萍和法国学者蓝克利在山西洪洞、赵县和霍县交界的四社五村做水权的田野调查时,将该地的水利概括为“不灌溉水利”,称之为“不灌而治”,揭示了四社五村共享水利的级差秩序与整体社会动员。(19)他们提出了“整体社会动员”概念,比较确切地反映了当地水利的特点,也从整体上呈现了当地人的生存伦理;但语焉不详,未能就此展开充分讨论,其毕竟局限在狭小的村际地域范围内,无法理解一个特定地域社会秩序的历史实践逻辑。本文将“整体社会动员”发展为“整体动员机制”概念,突出地域社会秩序的结构和过程的融合。
当然,问题意识不是预设的,而是在对经验资料的深度解读中逐渐形成的。本文的基本资料是汪氏宗族于清代光绪年间编纂的《汪氏登原藏稿》,该资料又名《汪司马墓案稿》,是道光七年(1827)“司马墓盗砍案”和光绪十八年(1892)“司马墓盗葬案”讼争案卷的汇编。绩溪县有“横打官司,直耕田”的民谚,(20)即耕田要“老实”,否则就“人哄地皮,地哄肚皮”,而打官司,则不免要“横着点”,为打赢官司甚至不惜动用欺骗手段。清代名吏汪辉祖对于诉讼中当事人表述的“陷阱”深有体察,将其概括为“无谎不成状”。(21)对于法律诉讼案卷的解读方法,笔者曾从社会记忆的角度做过探讨,认为不应纠缠于“两造”的表达是否“属实”,应看到其表述背后的诉讼策略。(22)
此外,本文还使用了《越国公祠墓志》、《重建吴清山墓祠征信录》、《新安汪氏宗祠通谱》等族谱类资料。对于族谱资料的利用,史学界已有很成功的研究。族谱资料关于族源的记载,往往较多附会,刘志伟认为,不能以其所记述事实本身是否可信来评价,而应考虑到有关历代祖先故事的形成和流变过程所包含的历史背景,应该从分析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入手,把宗族历史的文本放在当地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去解释。(23)本文的定位不是关于汪氏宗族史的研究,也不是以司马墓讼争为个案的法律社会史研究,而是透视与宗族相关的地域信仰及地域社会的形成,故对族谱资料,更可结合宗族支派分布和族源传说,解释地域空间秩序的结构。
研究路径服从问题意识和基本资料。汪司马墓讼争案不是发生在两个“村族”之间,而是涉及徽州府甚至宁国府、严州府、池州府等州府的汪氏宗支,甚或关系到在京为官的汪姓族裔;讼案且与国家祀典、黄册、鱼鳞图册、里社等王朝典章制度密切相关。西佛曼(Marilyn Silverman)和格里福(P.H.Gulliver)提倡一种“历史民族志”(Ethnography of History),即“使用档案资料以及相关的当地口述历史资料,描写和分析某个特定且可识别地点的民族一段过往的岁月。民族志可以是一般性的、涵盖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或者,它也可以集中注意力于特定的题目,如社会生态、政治活动或宗教。这种民族志学最后带领人类学家远离民族志的现在、自给自足的‘群落’和稳定的‘传统’这类根基久固但粗糙的设计和假设。”(24)历史民族志(25)方法蕴含了对“民族志现在时”无历史感的批评,试图将共时性和历时性有机结合起来,并试图将“小地方”与“大社会”融合在网络状的空间结构中。本文循着这一路径,将地方文化放在王朝典章制度和政治经济体系的历史脉络中进行解释,也将事件史和长时段的结构史结合起来,(26)惟其如此,才能理解王朝典章制度、正统化意识形态、政治经济体系等对于地域社会秩序形成的历史实践意义。
二、汪公墓、祠、庙的空间秩序
宋代罗愿在《新安志》中说:“汪氏……唐歙州刺史汪华居新安,故望出新安。今黟、歙之人,十姓九汪,皆华后也。”(27)“十姓九汪”之说概源于此。然考诸汪氏族源,则传说不一。如汪氏江南始祖,就有不同说法。罗愿以为,汪氏族源即使在宋代已不可考:“(胡伸)《行状》称,汉建安二年,龙骧将军文和为会稽令,因世乱避地,家于新安。文和之名,他书无所见……按纲之由新安徙既在陈时,则汪氏之居此旧矣,岂得言自王始乎?太平兴国中,有为王庙记者,言王乃隋将宝欢之族子,或谓陈、隋以上始处此邪。本之龙骧则荒远,就王为说则简陋,俱未适中,故内翰至此略而不言,若以新安之族,由王而望始著则可尔。”(28)明代汪道昆在《始祖龙骧将军墓域碑阴》中则载:“吾宗得姓,自鲁颖川侯汪始。汉建安二年,龙骧将军讳文和为会稽令,始渡江南。于时郡新都而治始新。公迁始新,因而占籍。其后始新入歙州,公卒,与夫人孙合葬邵石山。胄子弭寇将军讳轸卒,与夫人李合葬都督山。后世附葬邵石山者墓二十五,附都督山者六,而公实江南汪氏始祖也。后复割歙东略隶淳安,世远支分。”(29)如果汪姓江南始祖为龙骧将军文和,那么其始居地始新和葬地邵石山,在宋代应该隶属新安,故罗愿有龙骧将军“家于新安”之说;在明代,则已属严州府淳安县。
明代《新安名族志》也将文和视为汪氏新安始祖:“汪始于颍川侯,鲁成公黑肱次子夫人姒氏,生侯有文在手曰‘汪’,遂以名之,后有功于鲁,食采颍川,号汪侯,子孙因以为氏,望鲁之平阳。汉灵帝中平间曰文和,以破黄巾功,为龙骧将军;建安二年,因中原大乱,南渡江,孙策表授会稽令,遂家于歙,是为新安汪氏始迁之祖。”(30)
对于族源传说,不必做历史考据以辨其真伪,而在于发现其中所映射的宗族认同。(31)章毅通过对《新安名族志》及若干家谱资料的解读,比较了《新安名族志》中提到的休宁县汪氏26个族支和程氏32个族支在族谱中的族源表述,发现他们的祖先都存在着“渡江祖先——本地始祖——分派祖先”这样三个层次。对于汪氏来说,是“汪文和——汪华——汪华诸子及兄弟”,而在这些人物当中,除了本地始祖汪华外,其他的“祖先”真实性并不高。“始祖和渡江祖的结合,使明代的汪、程二氏能够充分地表达出自身与文化正统的关系。”(32)族谱中关于族源的表述,当然有正统化的逻辑存在,但分派始祖的可信度反不如新安始祖汪华的可信度高,这样的解释恐怕还需要再做推敲。汪华同时代的汪姓族裔的族支难道都绝后失传了吗?明代族谱攀附汪华作为显祖,这恰是正统化表述的逻辑,无法在历史考据的意义上认为,汪华作为新安始祖之说的可信度更高。
徽州汪氏因“显祖”汪华而成望族,故汪华在汪氏族谱的叙事结构中占据着最为权威的地位,祖先祠、墓的修建及祭祀成为宗族强化凝聚力的主要手段。而汪华得到历代朝廷的敕封成为地方神,则使汪氏宗族的祖先崇拜具有了正统性,其表现在,歙县云岚山汪公墓、乌聊山忠烈庙、吴清山汪公庙、灵山院汪祠、崇福寺汪祠等五处,明清时代载诸礼部祀典,并经户部批准,“税亩免征”。(33)而葬浙江严州府淳安县邵石山(即小金山)的汪氏江南始祖龙骧将军文和公,汪华高祖军司马叔举公和汪华的儿子所葬墓地,均未能享受历朝免征的“待遇”。可知,在汪氏祖墓的空间秩序结构中,歙县云岚山汪华墓始终是最重要的标志性“地景”。
清道光年间,汪氏宗族的吴清山祠管理机构(祠首)对于该处三十三世祖澈公墓的祭奠,也要邀集云岚山汪公墓祠祠首先至云岚山汪公墓,然后才至吴清山澈公墓。虽然《新安汪氏宗祠通谱》的编纂者将新都侯澈公作为新安始祖,但祭祀的先后顺序显示了云岚山汪王墓和吴清山澈公墓的等级隶属关系:“吾宗以新都侯为新安始祖,越开两国公皆本所自出,祠墓距云岚山不远,爰集同人之经理云岚山者,亲而上之,并及吴山焉。”(34)在族源的表述上,清代吴清山宗祠通谱的编撰者和明代汪道昆的叙事逻辑仍然保持一致,但在祭祀实践上,则发生了很大变化,即清代将云岚山汪王墓看作汪氏祖墓地景的中心。
绩溪县登源军司马叔举公墓,在清代汪氏族裔的族源表述中,则从显祖汪华那里获得“正统性”的支持。嘉庆十五年(1810)三月,绩溪县令在汪氏族裔礼部侍郎汪滋畹等官绅的呈请下,发布保护登源司马墓的禁示碑文,(35)禁碑特别强调,叔举公在宋代“以子越国忠烈王功,追封世惠垂祝善应灵明侯”。汪氏宗族在道光七年的司马墓“盗砍案”讼争中,曾到云岚山谒汪王墓,在云岚山附近汪王墓祠首处开会议事。基于正统性的道德化叙述,祠墓志和族谱尤其注重阐明坟业的宗族公产性质,《越国公祠墓志》在《税业》卷云:“志郡邑者,首详疆域,次及形势,正疆界也。志墓,何独不然?山川有形,税亩有额,弓步有界,按册备登,广隘短修,瞭然于目,则承先业,护陇邱,供数典,杜豪侵,均于是乎在。”(36)
常建华在对徽州府汪氏祠庙祭祖的研究中,就专门述及墓祠,“所谓墓祠,就是建于墓旁的祠堂,以此岁时节日上冢祭祀先人及合族。”(37)云岚山墓祠当然是祭祀汪华,而吴清山墓祠,则祭祀澈公、道献公和汪公。绩溪登源军司马叔举公墓近也有忠烈庙,祭祀汪华。由是观之,汪氏祖先祭祀的正统性,即使是对于汪华的先祖,也要从汪华那里得到正统性的支持。
作为神明的汪公,则在忠烈庙内得到祭祀。忠烈庙,除吴清山、乌聊山、灵山院、崇福寺、唐金山之外,徽州府六邑均有多处“行祠”。程敏政对于行祠之制有过很好的解释:“古忠臣烈士有俊功大惠于世,有国者必崇祀之,著于令,有家者常祀之外,亦别有先祖一祀。著于礼,礼法并行不可偏废,而况有俊功大惠于世者,置弗祀者可乎?专祠矣而复祀于家则亵,置弗祀则简。于是中古以来,有行祠之设,卜地为之,其制视公祠则杀,视家礼则隆,亦犹民间不敢僭称社稷而曰义社也。”(38)常建华认为:“忠烈祠属于名人特庙,而且带有地域神的性质,但是对于汪氏来说,它无疑是一所祖庙。”此说显示了忠烈庙作为祖祠和神庙的双重性质,但他接着又说:“国家建庙纪念有功于国家的‘忠臣烈士’是一种‘专祠’,也是‘公祠’。对于被纪念者的家族来说,这种专祠则是一种先祖的祭祀,因此又卜地设置‘行祠’,介乎公祠与家庙之间。从形式上看,行祠是作为‘公祠’之‘专祠’的分祠存在的,实际上行祠除了具有地域性外,主要是作为子孙立祠祭祀始祖或先祖存在的,是一种宗祠。”(39)仅从程敏政的论述延伸出“行祠实为宗祠”的解释,似乎还缺乏历史实践层面的佐证。
行祠之设,最初可能是某一村落宗族(可看作弗里德曼所说的localized lineage)所设的宗祠。但对于成为地域神的“忠臣烈士”来说,他姓家族也要祭祀,甚或有他姓绅衿捐资助修,遂使“行祠”呈现了复杂的面相。擅长“长时段”分析的历史学家,会注意到宗祠和神庙在不同时代的转化逻辑。林济考察了明中叶徽州宗族“专祠”的复兴和发展,显示了“从‘专祠’的神祖及名贤功德祖特祭配享中发展出反映宗族结构的祖先象征体系”,从而形成了后来宗祠祀礼的基本格局,甚至认为这一过程从宋元时期就开始了。(40)章毅更认为,元明之际,随着理学的社会化,徽州宗族观念兴起,地方神庙也开始了宗族化转向。(41)历史学家对于长时段的把握,提醒笔者更谨慎地看待明代中后期至清代徽州神庙和祠堂间的复杂关系。忠烈庙(汪王庙)建筑的维护及祭祀礼仪的变化,恰恰说明,宗族的力量(特别是汪氏宗族)在汪王庙的维护和祭祀过程中,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但直至清代中后期,并未排除汪王庙的神庙性质。当然,歙县云岚山的汪王墓祠除外,它始终是汪姓宗族祭祀祖先的大宗祠,徽州汪姓宗族将其作为联宗活动的“标志性地景”,盖源于汪氏宗族对于汪王墓的族产性质的认定。
郑力民通过对徽州汪王庙的社庙结构的研究,发现在歙县南乡的孝女会所属诸村落,“每一寺庙为相关村族共有,这在传统徽州乡村社会是一通则。所以每逢迎神赛会,这才会具体表现为,一寺庙之神只能被这一些村族所接送……一庙诸社的现象就自然立体地呈现出‘众社拱庙’的样式”,这也就是社庙结构。并将这一“众社拱庙”的社庙结构看作徽州一体化进程的最核心要义。(42)在汪公祠墓庙的空间秩序中,固然六处“标志性地景”占有不容忽视的核心地位,但六邑的忠烈行祠,也在汪公信仰的空间结构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如果没有这些行祠,那么歙县乌聊山、吴清山、崇福寺、灵山院及绩溪登源五处忠烈庙的祭祀则只能是来自六邑城乡汪氏宗支的祭祖活动,而不可能演变为地方神明祭祀。
三、祭祀、坟业与庙产:道光七年司马墓“盗砍案”
道光七年农历五月的一天,经过了一场风雨,绩溪登源司马墓护荫的松树被风吹倒了两株。忠烈庙的看庙人广度和尚及徒僧赫即报告附近仁里等八社的管庙首事,众人一同将“风折”松木并枯树11株抬至忠烈庙内。此时正值八社重修忠烈庙之际,以程姓为主的众首事以为这11株松木正好派作修庙之用。此事被八社之内梧村的汪连喜知道了,汪连喜迅即往县城报告给东作门宗支的汪南纪,二人遂至庙阻止。包括梧村、汪村等汪姓聚居村落,组成祭祀汪公的八社,首事们当然以为用唐金山司马墓附近的树木做修建忠烈庙之用,是很自然的事情。而汪南纪等则认为,汪公可以为众社所祭,而司马墓荫木,甚至忠烈庙产都属汪姓“世业”。双方互不相让,最后汪南纪先行禀告县衙,并通知徽州六邑诸汪姓宗支陆续分别控案到县。这就是汪姓族人所谓的“司马墓盗砍案”。“盗砍”是六邑汪姓族人的表达,源于汪姓宗族对于坟山和庙产的主张;对于八社,修庙的正当性来源于八社对忠烈庙的祭祀和对庙产的捐助。
道光七年七月初八日,汪南纪代表县城的东作门汪姓宗支先行控告至县,其禀状(43)云:
禀为看管盗荫,先行呈明,叩拘究追事,缘身始祖叔举公安葬十一都土名白杨坑坟山一业,本月初六日,身在该山经过,骇见登源庙主持僧广度、徒弟僧赫带领僧俗数十人在该山盗砍。身即往阻,已被砍倒三五尺圆围不等松树十一株。迫冺地保往验。奈保不家,只得奔告本族宗长,修书通知各县各族公同叩案。即时难以齐集,身合抄呈前县主碑文告示,先行匍叩,宪大老爷恩赏拘案讯究盗荫,各族感戴,上禀。
据此,汪姓族人主张对司马墓坟业占有,而对于忠烈庙产,并未有明确的表达。
七月十三日,东作门汪姓宗支又联合绩溪县的雄路、孔灵、辇显、古塘、夹川、高桥、黄荆塝、梧村和歙县靠近绩溪的坦头等九族,共十族向县衙递呈禀状。这次动员了十个宗支中的官绅具名禀状。禀状内容与东作门族禀状大同小异,不赘述。倒是这十个汪姓宗支向六邑及外府汪姓支裔的“传启”,除叙述司马墓的坟业归汪姓所有外,对于忠烈庙八社祭祀的正当性倒也持肯定态度:
敬启者,我汪氏四十世祖刘宋军司马叔举公墓地在绩溪东七里登源唐金山(鳞册称“白杨坑”,今依徽州府志及绩溪县志称“唐金山”),山势壁立,前滨大溪,一冈横亘,状若眠弩,形家呼为将军踏弩,实越国、开国两公高祖也。地额三百一步,树墓槚数十株,墓前里许,公之遗宅在焉。越国公保障六州,殁而为神,土人即是宅奉烝尝,榜曰忠显,公之故宅,世谓之登源庙(宋政和中赐庙额曰忠显,厥后累封至八字王,改赐庙额曰忠烈,详载府县诸志中)。初住羽流,今住释子,守庙兼守墓也。庙与墓之前后左右通计田地山三十四亩有奇,悉付住庙人收执,其税在十一都二图六甲登源庙户解纳,梧村族人之都图也(越国公九子,第九讳献,早死无后,仍八子,其七子散居四方,惟第八子讳俊留居梧村,世守祠墓。前明副使公溥,侍御公滢,其后也,详见二公墓志铭)。该处邻村每岁花朝日迎庙神祭赛祈福,号曰八社赛花朝,梧村族人亦与焉。夫今日之神庙,固曩日之故宅,而汪氏之墓地,实神明所发祥,越国公遗爱在六州,六州之民不能忘越国公者,亦安能忘公之高祖耶?矧八社尚司马公桑梓之区,其感戴宜复何如也?嘉庆七年淮安支裔廷珍以翰林学士奉命督学皖江按试徽郡道,出绩溪,曾檄守令出示封植祖陇。十五年休邑支裔礼部侍郎滋畹予告归里,复鸠各宗绅士呈请绩溪令清公勒碑严禁樵苏。迩来人心不古,妄生觊觎,墓上荫木,被僧俗盗伐,不胜纷扰,附近诸族屡经呈究。盖事在得已,故勉力支持,未尝申告远方诸大族也。
八月初一日,以歙县诸汪姓宗支为主,又有祁门县、黟县、绩溪县的少数汪姓族裔,在乌聊山忠烈庙召开会议,商讨诉讼对策,进而壮大汪姓的声势。
八月初三日,以程姓为主,包括梧村、汪村汪姓在内的八社也呈递诉状,对于庙产与汪姓坟业做出界分:
具禀状程修五、程敬敷、程羽丰、程雨顺、汪永贵、汪聘三、汪社璨、汪灶有,王观宝、王灶永、王德进、王邦本、方启宝、方光庆、胡有松、洪士有、张永妹、周灶来、戴光祥、汪赏桂等,禀为奸唆妄控泄忿败公叩吊察核事切,越国汪王福国庇民,众姓建庙供奉神像,并制各产,以为香灯修理之需。嗣至雍正年间,众姓立议,将土名白杨坑声字一百六十三、四、七等号山地栽养木植,挨班封守,并请示禁,以备修庙取用,历来无异。甫有汪姓出请示禁,八社众村以其即神后裔,未妨奸埋,任请不较。今庙颓塌,身等现修十只有三,竟在缺料,本欲抽砍。该树本年五月适被风雨,损倒松木二株。遂有贪利不仁之汪连喜勾同虎嵎在城之汪南纪,藉禁有根,公然将倒松木披杈锯不(疑为木),并将枯木锯倒三株,欲运肥己。身等闻觉,斥阻,议将仍有枯木四株亦锯,同运庙内作用。讵喜与纪怀恨,旋唆伊姓衿士妄控庙僧,希欲败公报睚,不思该处之业,汪姓仅有六十四号墓地二十步,仍尽庙众之产,鳞册注明,分庄确凭。鳞册存户房,叩吊可阅。至树,八社供养,示议凿凿不磨,如谓树系伊家,势必有业,墨据岂容奸唆,空口妄控,败公坑庙,为此……
八社将汪姓宗族的“妄控”表述为“败公坑庙”,显然是将忠烈庙的祭祀与庙产看做是“公”。其表述细节中,甚至将汪南纪和汪连喜锯倒松木看做是“肥己”,于忠烈庙祭祀与庙产则属“私”。这与汪姓的“盗砍”表述在“事实”的陈述上有出入,在道德表述的层面是针锋相对的。王姓县令针对“两造”的表述,批曰:“该山树株若果众姓栽植,以为修理汪姓祖庙之用,固属义举,但汪姓祖坟久葬于此,坟荫示禁盗砍,由来已久,僧人广度砍伐之树,是否在于汪姓坟界?抑在众姓公地,候饬吊契据质讯察究。”此时,县令还是显示了“实事求是”的公正态度,对于所谓“盗砍”树木究竟属于汪姓坟界还是众姓公地,须结合契据等证据方能判明。在王姓县令看来,庙产属于“众姓公地”。
六邑的汪氏宗族将雍正年间八社合议粘呈县衙,称之为“八社私立合议”,在六邑的汪氏宗族看来,八社对庙产的主张相对于汪氏坟业,是“私”,在权利和道德上都不具有正当性。禀状的作者并就此评述道:“先是雍正初年,主持庙僧懒惰不能侍奉祖庙灯香,经管祖墓荫树,八社于庙祀奉王祖。欺僧弱门,并恃社内有梧村、汪村等处我姓支裔在内,将僧逐去。我姓登源庙户税簿强占经管,潜萌异志,吞据税业。于雍正三年私立合议十五纸,越请前县宪范给示,续于五年,复逐去主持僧人,再请前县宪王给示。梧村、汪村等处暗懦支裔,私利众产为己有,遂扶同立议请禁,不通报各族。此众族支裔之所以不知八社之恃为朋据税业也。八社之中,程姓富强,程姓遂为能干之总,因循渐积,墓庙税业尽由其掌管矣。”
此处所说“八社”,从实际参与的村落看,是十三个村落。他处记载,为登源十二社。二月“十二日为花朝日,粘红纸于花果树,祝其繁茂,谓之挂红。”“十五日,登源十二社挨年轮祀越国公,张灯演剧,陈设毕备,罗四方珍馐,聚集祭筵,谓之赛花朝。其素封之家,宾朋满座,有主人素未谋面者。”(44)
清代乾隆五十三年(1788),沈复至绩溪县衙为幕僚,记述了他和同僚游仁里所见“花果会”祭汪王的盛况。“绩溪城处于万山之中,弹丸小邑,民情淳朴……又去城三十里,名曰‘仁里’,有花果会,十二年一举,每举各出盆花为赛。余在绩溪适逢其会,欣然欲往,苦无轿马,乃教以断竹为杠,缚椅为轿,雇人肩之而去。同游者惟同事许策廷,见者无不讶笑。至其地,有庙,不知供何神。庙前旷处高搭戏台,画梁方柱极其巍焕,近视则纸扎彩画,抹以油漆者。锣声忽至,四人抬对烛,大如断柱,八人抬一猪,大若牯牛,盖公养十二年始宰以献神。策廷笑曰:‘猪固寿长,神亦齿利。我若为神,乌能享此。’余曰:‘亦足见其愚诚也。’入庙,殿廊轩院所设花果盆玩,并不剪枝拗节,尽以苍老古怪为佳,大半皆黄山松。既而开场演剧,人如潮涌而至,余与策廷遂避去。”(45)沈复在庙会现场甚至不知道所祭何神,并误以为花果会(当是“花朝会”之误)“十二年一举”,实际是十二社轮值,每年二月十五日举行。(46)对于某一社来说,十二年方才轮值一次,故所养之猪“大若牯牛,盖公养十二年始宰以献神”。
“八社”和“十二社”的不同表述,也是可以理解的,社的数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变化。(47)社的设立,并不以村落大小为标准,而与村中首领的财富和威望及宗族势力有很大关系。(48)据现绩溪县汪村(行政村)南观村人、退休干部汪福琪先生2005年撰文,并引用其九十高龄老母亲的回忆,“民国15年(1926)南观村举办花朝会。南观一个仅百十余人口的小村,但在祭祀汪华举办花朝会时却单列一社,因村中富户居多,故有经济实力举办盛会。这期花朝会由村中首富汪老永(名顺成,号老永)当‘斋官’。汪老永经商江苏,富甲登源,时又兼任十三都都董,在民间有一定威信。汪老永家房屋有数十间,在村中心地带,自东向西,连成一片,占全村的四分之一。”(49)亦可推测,社的单位在不同的年代会有变化,雍正三年(1725)八社合议中,南观和庙头为一社,应为史实;民国年间,南观村汪老永“富甲登源”,又任“都董”,南观村单独为社,也是可信的。而在雍正初年,“八社之中,程姓富强,程姓遂为能干之总”,仁里程姓在花朝会中的势力显然是最大的,故“因循渐积,墓庙税业尽由其掌管矣”。六邑汪姓认为雍正初年,“梧村、汪村等处暗懦支裔,私利众产为己有,遂扶同立议请禁,不通报各族,”相对于六邑汪姓的“大公”,梧村、汪村的汪姓支裔的行为即是“私利众产为已有”。
而对于徽州六邑汪姓的联宗(50)活动,梧村、汪村的汪氏族人则有着另一番表述。清代乾隆三十七年,汪村、梧村汪氏宗支修谱,族裔汪谨撰《谱成告庙文》(51)曰:
大清乾隆三十七年岁次壬辰孟冬月宜祭日支下裔孙谨告,维我登源司马开基,肇衍新安万派。越国诞降,爰开令绪千秋四方,自昔播迁,一支由来居守敝庐,愿处敢忘桑梓,敬忝省墓宜殷。爰近云岚卜筑,同深世守之思,其笃宗盟之好,历阅六朝,年周八伯,衣冠相望于前人,诗礼敬承于后代,巍然右族赫矣……小子欲取旧文重加考订,但念末俗滋偷,人心不古,籍统宗而射利,罔顾攻令森严,假征会以为名,不惜多方强附天亲也。而以人合之名场也,适为利薮矣。某等恪遵定例,痛鉴前车,第详本支不侈,合族跋涉长途,甘膺况瘁薪水,自任勇往驰驱,将各族之人丁尽皆收续,数百年之阙略,备悉载登,支匕祖妣,恍若列眉,派派子孙,郎如执掌。告之先祖,编颁族人,呜呼!笔则笔,削则削,深维往迹之难;贤其贤,亲其亲,敢倚世德之厚,更祈阴佑益牖……
汪谨对于“籍统宗而射利,罔顾攻令森严,假征会以为名,不惜多方强附天亲”的联宗行为,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咸丰二年(1852)刊刻的《越国公祠墓志》载:“道光二十七年奉府宪同饬各县出示严禁假冒告示……兹因墓祠殿宇倾颓,业经公议各支派批捐兴修。本年五月二十七日,曾沐县主给示,悬祠晓谕杜害。第职祖椒蕃瓜衍,子姓偏延郡邑,讵料有不法匪徒,伪刊墓祠图章,在外撞骗银钱,以致离祠路远支派难辨真假,乐输不前。”(52)这也从另一侧面印证了汪氏村级宗族和联宗组织之间的矛盾。
民国年间,梧村汪姓族谱的编者又将明代“癸巳司马道昆传帖”收录谱中,其中关于登源司马墓祭田的记载,特别提到梧村、汪村的捐助:“兹届祭期,余小子力疾而申前议,请十族各一人,行者各携四缗,兼之近墓梧村、汪村亦各出四缗,共四十八缗,付彼买田若干亩,以供祭事,岁以为常。”(53)道光七年“盗砍案”中,除梧村汪连喜参与六邑汪姓的呈控外,梧村、汪村的汪姓族人均未在六邑汪姓禀状上具名。六邑汪姓族裔谓汪村、梧村族裔“暗懦”、“私利”,而仁里村监生程修五领衔的八社诉状则称:
禀为尊神敬祖由来已久叩鉴情由事,越国汪公生捍大患,殁为神灵,登源八社建庙崇祀,每岁花朝迎请祈福,号为八社花朝。公裔梧村、周村、汪村、门岱、闾坑、辛田、宗洲各派皆与焉……今八社捐输办理,数百年来,立议请示,众姓节次修理,供奉香火。在八社为尊神,在社内公裔为敬祖……
诉状表述了八社汪公神明崇拜和汪姓祖先崇拜的道德正当性,也在忠烈庙祭祀的“考古”基础上表达了对庙产的“主张”。
八月初八、九两日,歙县、休宁县、绩溪县、宁国府旌德县等地的汪姓族裔在绩溪雄路村集合,前往登源会宗省墓,并形成“决议”,决定在歙县乌聊山忠烈庙设立公所,通知六县外省外府族裔,呈讼府县,进一步动员汪姓族裔中的官绅势力参与其中。八月十三日,汪姓族裔再递禀状,这次动用的汪姓族裔中的官绅地位较前显赫,地域范围也扩及到徽州府之外,领衔禀状的有歙县原任池州府教授卓异候补知县汪熙、休宁县原任卢州府教授汪忠均、婺源县举人汪松泰、祁门县举人汪豫、黟县翰林院检讨汪淦、绩溪县廪生汪泽、太平府繁昌县生员汪杰、浙江杭州府昌化县廪生汪为俨等。此次禀状,并呈登源税册作为证据:
旧籍成化八年一户登源庙十一都二图墓神庙,承管道人王伯寿,民实在田地山三十四亩五分七厘二毫,内田五亩九分四厘九毫,地十亩八分二厘三毫,山十七亩七厘九毫。
对于登源税册,汪熙等又写了如下“帖说”加以解释:“成化八年,汪姓已有税籍,田地山业何待八社捐输,分明是雍正年间逐我庙僧,盗我税籍,私立议据,以窃食我租利,难逃犀照。”又引“前明支裔司马道昆万历辛丑年,重议登源标祭事宜”:
登岭山墓地祠地树木俱召与守祠墓道人长养,荫庇祠墓,不许外人侵盗,亦不许看守自盗,并私刁树枒,如违,罚出本年各项租利,再犯,另召他人看守。其柴草给与道人冬月砍烧,其墓前地亦给与自种自食,以作看守勤劳之资,永为定例。
并撰“帖说”:“前明万历年间已有树木,何待八社兴养?且坟荫祠荫,汪姓素皆茂植,宗谱与前明支裔司马道昆议合。今来龙坟祠木荫已无一存,侵食至坟之前后左右。痛及剥胄,支裔万难隐忍。即是修庙,亦无斩伐高祖坟荫为曾孙茸庙宇之理,况盗砍本是肥私,不按律究办程有妹、邵邰等之罪,职族何能甘心?”“帖说”可以理解成是“他者”的历史解释,其对坟业、树木、庙产的主张建立在对宗族历史的“考古”基础上,并带有浓烈的道德表述取向。所谓“斩伐高祖坟荫为曾孙茸庙宇”,说的是“盗砍”军司马叔举公墓地荫木,为其曾孙汪王修庙,似乎不合礼制。如此之表述,和前述“司马叔举公因汪越国显”的表述,又有抵牾之处。绩溪县有民谣云“横打官司、直耕田”,诉状中对于“理”的表述,蕴含了追求功利的机会主义倾向。
在汪姓呈送的一份乾隆四十年徽州府的告示中,有如此之表述:
生族迁新安始祖叔举仕齐,代官军司马墓……至宋邑令赵公、李公两奉敕修,后又造基德、绿照两亭于左右。前明郡守董公为立丰碑。裔孙左司马道昆率各族重整。其墓旁所附葬者,即始祖之孙名僧莹,仕隋为海阳令,袭封戴国公,至宋朝,以子越国忠烈王功,追封世惠垂祝善应灵明侯。郡守袁公为书神道碑,详载绩志,墓祠之前建有忠烈王庙。嘉靖年间,尚书胡公宗宪倡修其庙,裔孙御史溥副使滢又建劝忠楼,此皆请于朝者。前朝既荷,敕恩皇朝,尤沐祀典,庙貌久为众姓群瞻,墓祠则属我汪姓世守,岁历千有百年,代传五十余世,松楸并茂,柏槚成行,第子姓殷蕃其鹿,不億为商、为宦,分寓四方,世远年湮,或被侵于樵牧,或受害于豪强,是均未可逆料。与其匡救于已灾,不若绸缪于未雨。
这份“证据”,着重强调的是对于司马墓和戴国公僧莹墓“坟荫”的保护,主张“墓祠则属我汪姓世守”,而对于忠烈庙,仍承认“庙貌为众姓群瞻”。由于梧村、汪村、南观等村落的汪姓也参与了八社祭祀汪王的庙会活动,在他们看来,墓与庙是一个整体“地景”,不可分割。明代天顺年间梧村族裔苏州知府汪祐清在“登源八景并序”中将司马墓和忠烈庙融合在登源的总体地景之中,序曰:“吾梧村去县治东南十里,前有溪,右有登岭,岭丽有川而流,与溪水相合,因名曰登源。源之南北,峰峦环列,岩洞虚豁。始祖司马公墓、忠烈公庙咸在焉。居之四围,有龙鬃高峰,石泉飞漳……”(54)八景为龙峰晴云、金山晓雾、岛崖春雨、绿照秋波、隐张层崖、富陵叠嶂、清溪沙鸟、野坞松风。八景之说,存在于很多徽州古村落中,是村落家族文人的地景想象,由此呈现出“入住权”意义上的村落边界意识。
在县衙的堂讯中,“两造”还各据理力争,互不相让。但是后来,徽州府宪马和安徽提督学院汪的批文,使讼案发生了根本转向。府宪批曰:“候饬县加差干役勒限严拿究办。”提督学院汪批曰:“仰县官吏,文到,立即加差干役,勒限严拿程有妹、程邵邰、程东煌、程东台等及管庙僧人到案严讯,按律究办,毋再纵延,大干未便,火速火速,须牌。”八社屈服于官府的强大压力,经过邑绅调解,“两造”和息。
递呈“和息状”的邑绅猜测可能是县衙指定的,而非八社和六邑汪姓出面邀请,因为这样的调解,而不是民间调解,而实际上仍是官府审判的一部分。(55)最后,八社退还税簿,偿还树价,安奠醮坟。
这起讼案,最后以汪姓联宗组织的胜利而告终,官绅的力量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八社的官司虽然输了,但忠烈庙的祭祀权并未被剥夺,花朝会还要按年轮值,年复一年地办下去,这也意味着,庙会的“文化领导权”仍在仁里程姓。六邑汪姓对于“盗砍案”的善后工作,一是禀呈“县主”勒碑示禁,再次借助官府的权威,强化对忠烈庙产和司马墓坟荫的占有;同时在绩溪县城东作门宗祠成立由六邑族裔代表参加的公所,清理司马墓税业。而忠烈庙庙产和司马墓坟业的界限能够就此得以厘清吗?(56)
四、讨论
回到本文主题,道光七年的“盗砍案”不是一般的家族坟山之争,这一讼案将徽州祖先崇拜和地域崇拜的逻辑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呈现了徽州地域社会秩序场境中的整体动员机制。该案所反映的汪公信仰的祭祀圈和信仰圈的结合,显示出汪公信仰成为徽州地域社会的“标志性民俗”,换言之,汪公信仰成为徽州一体化的象征。民俗学家刘铁梁在民俗志书写的意义上提出“标志性文化”概念:“所谓标志性文化,是对于一个地方或群体文化的具象概括,一般是从民众生活层面筛选出一个实际存在的体现这个地方文化特征或者反映文化中诸多关系的事象。”(57)汪公信仰作为明清直至民国时期徽州的标志性民俗,在地域上覆盖了作为一个文化区的“一府六邑”,在规模上囊括了徽州的所有村社和普通大众,在社会事象上涵盖了地域崇拜、宗族认同、绅权治理、祭祀礼仪、司法实践、风水观念、地权纠纷等政治、经济、宗教诸多要素,映射了徽州地域社会秩序运作的基本原则,呈现了该地域社会的整体动员机制。
“盗砍案”中,祭祀和庙产是两个“关键词”。此处的祭祀主要是指八社忠烈庙祭祀汪公,当然,“在八社为尊神,在社内公裔为敬祖”,其表达的是将地域崇拜和祖先崇拜结合起来,实际上梧村、汪村、南观等汪姓聚居村落,在忠烈庙没有单独的祭祖活动,八社的花朝会是祭祀汪王的庙会。(58)因此,祖先崇拜服从地域崇拜逻辑。汪公在徽州成为“土神”、“新安之神”,但祭祀是在村际的地域空间内展开的,可以用台湾学者的祭祀圈概念来解释。林美容将祭祀圈定义为“一个以主祭神为中心”、所属居民共同举行祭祀的地域单位。(59)林美容在对草屯镇祭祀圈的研究中,看到祭祀圈中“同姓结合”的一面,但更注重的是以庙宇为中心的地方祭祀组织。花朝会是一个以共同祭祀汪王为中心的村落联合地域单位,是一个祭祀圈。但是,由于村落均是家族聚居型的,如仁里是程姓,梧村、汪村、南观是汪姓,八社轮值,实际是以村落家族为单位的。
相对于“祭祀圈”的民间信仰解释,科大卫所说的入住权对此也有一定的解释力,所谓入住权是指在一指定疆域内享用公共资源的权利,包括开发尚未属于任何人的土地的权利、在荒地上建屋的权利、在山脚拾柴火的权利、从河流或海边捕捞少量鱼类和软体动物以改善伙食的权利、进入市集的权利、死后埋葬在村落附近土地的权利,等等。拥有入住权的依据是,权利是祖先传下来的。这些关于历史的观念,对于村落组织极为重要,村民们正是通过追溯祖先的历史来决定谁有入住权、谁是村落成员。(60)其要义在于村落宗族通过追溯共同祖先完成对入住权的确定。官府在对绩溪登源司马墓、歙县云岚山汪王墓、乌聊山忠烈庙、吴清山忠烈庙的示禁碑文中,屡次提到禁止当地民众“盗荫损害、纵畜践踏”的行为,实际上,屡禁不止的原因在于,附近拥有“入住权”的农民,以为他们可以享有放牛、砍柴等“共有的权利”。(61)
“盗砍案”的关键在于庙产之争,对于忠烈庙庙产的使用,“两造”均有“公私相对化”的表述。八社将汪姓联宗的“妄控”斥为“败公坑庙”,将忠烈庙的祭祀和庙产均当作八社之“公”;汪姓联宗将梧村、汪村在乾隆年间与仁里等八社共立忠烈庙会合议行为,视为“私立合议”,梧村、汪村“暗懦支裔”行为是将“私利众产”据为己有,这无疑将忠烈庙产视为汪姓联宗组织的公产。从忠烈庙产的形成看,既有八社中他姓捐输,也有汪姓“割田入庙”。在八社中的程姓等他姓看来,忠烈庙产和司马墓“坟业”虽在地理空间上有边界,但以坟山“荫木”修缮忠烈庙,在法与理上都是具有正当性的,都是为了祭祀汪王之“公”。而在汪姓联宗组织看来,忠烈庙和司马墓坟业,均属汪姓“世业”,双方在这次讼案中立场不一,对“世业”的解释有着不同的意义。
从形式上看,“盗砍案”将祖先崇拜和地域崇拜要素融为一体,如果仍局限在“祭祀圈”概念所指向的村际地域,或者入住权所指向的地域化宗族空间范围内,则只能解释村际的祭祀活动和庙产、坟业之争,无法解释在徽州一府六县范围内的汪公信仰何以成为标志性民俗,即汪公为何能成为徽州“土神”、“新安之神”。郑力民通过对汪公信仰的“众社拱庙”的社庙结构的解释,推演出“徽州一体化”概念,即试图回答“汪公信仰何以成为徽州一体化的象征”(62)这一问题。“众社拱庙”的解释,和林美容的“祭祀圈”概念颇为接近,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力,但在徽州一体化的解释中,却是在“不完全统计”的想象中推测的:由于徽州“十姓九汪”,故歙南孝女会所属村落之外的六邑各处,也基本是这一“众社拱庙”的格局,故汪公信仰能成为徽州一体化的象征。这个解释尚待商榷。
笔者认为,如果仅局限在村际层级,很难令人满意地回答这一问题。林美容继祭祀圈研究,又提出信仰圈概念,所谓信仰圈,以一神及其分身之信仰为中心,是区域性的信徒所形成的志愿性的宗教组织。祭祀圈局限于村际范围,信仰圈则是跨乡镇的。祭祀圈和信仰圈并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仪式空间,而是呈现了由祭祀圈到信仰圈的转化趋向,“以村庄为最小的地域单位,逐步扩大,”波及地方性或区域性的人群。(63)林美容所说的信仰圈是局限于地域崇拜的自愿性信仰组织,比如妈祖进香活动的组织体系及其仪式空间。信仰圈概念使笔者认识到汪公之所以成为“徽州土神”、“新安之神”,和徽州汪氏宗族的联宗组织活动密不可分,不妨将此看作基于祖先崇拜的信仰圈。
“盗砍案”中,汪氏联宗组织的宗族网路,显示了比《新安名族志》中更具说服力的徽州汪氏宗族的空间分布,当然,汪姓世系分布还可以通过《汪氏统宗谱》、《汪氏统宗正脉》等族谱类资料得到证实。但仍能看出,“盗砍案”讼争过程中,汪氏联宗组织的权威结构,呈现了与徽州汪公祠、墓、庙空间秩序结构相一致的逻辑,即以云岚山汪王墓祠首为核心的等级隶属关系。同时,汪氏宗族等级结构的城乡差异,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对于司马墓的“标祀”(即清明祭祀),由近墓族裔“每岁清明祭扫,仅办香循行故事”,绩溪县城东作门族裔居督察地位。梧村的汪连喜许是和八社中的梧村、汪村汪姓族裔有矛盾,发现“盗砍”后,往县城汇报给东作门宗支的汪南纪,此即说明同姓结合的城乡等级关系。汪姓以此为契机,讼争过程中多次展墓会盟,动员了所能动员的族内官绅参与诉讼,事后呈请官府示禁,对始祖坟山加以保护;重修祖墓、重整庙宇、清理“坟业”,坟山讼争本身就是一次绝好的会盟联宗的机会。
日本学者上田信将由宗族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分为三个层次,即居住在同一村落中的同族集团,因分支和迁移而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同族集团的同族联合,由于分支、迁移一度中断到一定时期再度接续上的同族合并。上田信重点研究了浙东的同族合并现象,并认为在明代,县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单位,在此基础上,清末(19世纪)以后同族合并的范围有超越县的重要倾向。(64)上田信所界定的宗族的三个层次,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预先的分类,而实际上在联宗活动中,并没有表现出如此的层次,也许同族联合和同族合并的分类在实践上反倒不如同族集团和同族联合的意义更为重要。他关于“清末同族合并的范围有超越县的重大倾向”的观点,倒是和本文所揭示的汪姓联宗相符。上田信所说的同族集团,即是弗里德曼定义的地域化宗族(localized lineage),同族联合和同族合并即是联宗组织(higher-order lineage),(65)钱杭在关于联宗和联宗组织的研究中,认为,无论是在一县或数县范围内,还是在一乡或数乡范围内,联宗的结果都形成了一个地域性的同姓网络。(66)
司马墓坟山讼争伴随的汪姓联宗,形成了一个甚至跨越徽州府地域的同姓网络。动员徽州府外的汪姓族裔,只是为了扩大声势;而徽州汪公墓、祠、庙的空间分布,又决定了汪氏联宗活动基本还是以徽州六邑为主。联宗组织的活动,必须建立在共同祖先的认同之下,对于祖墓风水的建构也成为宗族认同意识的有机组成部分。日本学者濑川昌久对香港新界联宗组织的风水与移居的研究认为:“在所谓‘上位世系群’规模的联合组织中,成为其构成单位的,全是个体性的村级宗族;汇集于联合组织宗祠祭坛上的祖先牌位,以及每个参加宗祠建设和祭祀等活动的现存成员”,从根本上说,也都认同他们各自出身的村落。(67)同样,研究过香港新界厦村邓氏的美国人类学家华如璧认为,厦村邓氏地方继嗣群是通过合并先前分散的单位而形成的。(68)这些分散的单位即是村级宗族。可见,联宗组织的基本单位仍然是村级宗族,也就是弗里德曼所说的地域化宗族。关于徽州宗族的研究,已有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如韩国学者朴元镐的徽州方氏研究,(69)荷兰学者宋汉理的休宁范氏宗族研究,(70)美国学者贺杰根据《新安名族志》所做的“宗族与社会流动性”的研究,(71)日本学者中岛乐章对宗族山林纷争的研究,(72)等等,他们均是在宗族制度史的研究框架内和弗里德曼对话,是就宗族论宗族,而未顾及民间信仰,尚未形成区域社会秩序层面的问题意识。
林美容将祭祀圈和信仰圈看做是民间社会的自发性组织,认为其“与官方的行政官僚体制无关,封建帝国时期,政府最低的行政单位只到县,县以下无行政官,较不受官僚体制的控制,也是民间得以自由发挥其组织力的空间。”(73)本文讨论的很多研究所提供的田野经验和讨论都对林美容的“民间自发论”提出否定性的论证。在司马墓“盗砍案”中,朝廷和官府始终没有将作为地域神明的汪公和作为祖先的汪公完全分开表述。在对待宗族的态度上,儒家正统意识形态所采取的态度,在表达和实践上均是家族伦理本位,但在对待联宗的态度上却是充满矛盾的。日本史学家井上徹认为:“宋儒主张通过复兴周代的宗法原理,形成由宗子统合的宗族集团,以此为单位,世世代代为政界输送人才,实现世袭的官僚家系。这一宗法主义理念与科举官僚制度理念的抵触是不言而喻的。最早面临这个问题的是明朝。明朝在官方礼制(家庙制度)中明确表示要摒弃宗法主义……乾隆年间制订的家庙制度沿袭了明朝摒弃宗法主义的方针,没有把宗祠纳入家庙制度中。清朝的官方态度无疑是否定宗法主义的,并将象征宗法实现的宗祠排斥在正式的礼制之外。换句话说,清朝把宗子在宗祠中以祭祀为媒介统合族人,或者把义田、族谱、家塾等作为统合的物质基础排斥在礼制框架之外,实际上就是采取了容忍的面对现实的政策。”(74)朝廷和地方官对于纳入礼部祀典的神明祭祀,是持积极支持态度的,而对保护家族墓地则持谨慎态度。在汪公坟山示禁和保护过程中,地方官始终将汪氏坟山的保护纳入汪公信仰的正统化话语体系中,这使汪姓宗族也认识到,对于汪氏坟山的保护“事业”来说,作为神明的汪公,其意义大于作为祖先的汪华。否则,就无法解释,徽州汪氏对共同祖先的追溯为何以汪华为核心。
在民间信仰的“标准化”和“正统化”的讨论(75)中,科大卫、刘志伟认为:“要对正统性问题做出社会史的解释,需要辨认某类行为到底跟哪一个知识谱系和师承传统相联系;在该师承传统的谱系内,哪些人掌控着判定何谓正统的权力。”(76)判定何为正统化的权力,无疑是掌握在拥有书写权的官绅阶层手里。如上文所示,族谱和地方志对于汪公墓、祠、庙空间秩序的表述,有不一致之处,但在清代,徽州汪氏族源的叙述,仍服从于汪公地方神明信仰的正统化表述,以至于云岚山墓祠志的编纂者也将郡县志的编史学作为典范加以效仿。
汪公在徽州既能成为地域之神,在“祭祀圈”的地域范围内为里社所祭祀;又因徽州“十姓九汪”,形成一个个地域化村族,在此基础上的联宗活动,祭祀祖先汪华,因此形成汪氏祖先崇拜的“信仰圈”。徽州理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所培养的官绅集团,也为儒学正统化在徽州民间的渗透提供了权力保障。(77)汪华在历朝不断得到敕封,其墓、祠、庙由历代官府主持重修,汪氏宗族官绅的呈请是最重要因素之一,而不断出现的墓、祠、庙讼争,也为此提供了契机。与其说汪华集神明与祖先于一身,不如说,神明崇拜和祖先崇拜的有机结合,显示了徽州汪公信仰的地域社会标志性文化的整体化特征。这是历代皇帝、知府、县令、乡绅、族老、徽商、胥吏、村民、和尚、道士各色人等多元互动的历史实践结果。该讼争呈现了地域崇拜、宗族认同、绅权治理、祭祀礼仪、司法实践、地权纠纷等要素的整体性历史实践。当然不能说,这一“事件”成为整体性的历史实践范畴,而是其所映射的汪公信仰的地域社会秩序场境,构成一个整体动员机制。莫斯借用其他人类学家的民族志材料,研究了原始社会的礼物交换,他将礼物交换看做是“总体的社会事实”,(78)莫斯认为礼物交换,如毛利人的“hau”的观念与制度,就是一种“总体呈献体系”,不能将其肢解分别进行法理学、神话学和经济学的分析。如莫斯的学生迪蒙所言,在“复杂性稍小而协调性易见”的原始文化中,“整体”可以一目了然,“礼物”就属于这种情况。(79)汪公信仰作为标志性民俗,呈现了徽州地域社会秩序场境中的整体动员机制,其也构成莫斯所说的“整体社会事实”。传统农业社会,颇类似于“复杂性稍小而协调性易见”的原始文化,比较容易找到如此带有整体动员机制的“标志性民俗”。
注释:
①Arthur P.Wolf,ed.,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
②庄英章、许书怡:《神、鬼与祖先的再思考——以新竹六家朱罗伯公的崇拜为例》,庄英章、潘英海编:《台湾与福建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5年。
③庄英章、李翘宏:《房头神与宗族分支:以惠东与鹿港为例》,《“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99年第88期。
④王斯福:《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赵旭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中文版序”。
⑤詹姆斯·沃森(即华琛):《神的标准化: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对崇拜天后的鼓励(960-1960)》,韦思谛编:《中国大众宗教》,陈仲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8页。
⑥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4页。
⑦华如璧:《兄弟并不平等:华南的阶级和亲族关系》,时丽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74页。
⑧关于祖先崇拜的研究,不能不提及许烺光、渡边欣雄和马丁的研究,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讨论。参见许烺光:《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和社会流动》,台北:南天书局,2001年;渡边欣雄:《祖先再考——祖先崇拜之社会研究的批评》,《汉族的民俗宗教——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Emily M.Ahern,The Cult of the Dead in a Chinese Village,Stand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⑨劳格文主编:《客家传统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75页。
⑩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卜永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6、431页。
(11)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2)贺喜:《土酋归附的传说与华南宗族社会的创造》;唐晓涛:《三界神形象的演变与明清西江中游地域社会的转型》;谢晓辉:《苗疆的开发与地方神祇的重塑——兼与苏堂栋讨论白帝天王传说变迁的历史情境》;陈丽华:《从忠义亭到忠义祠——台湾六堆客家地域社会的演变》;以上均来自《历史人类学学刊》2008年第6卷第1—2期合刊。贺喜:《亦祖亦神——广东雷州所见正统化下的礼仪重叠》,《新史学》2009年第4期。
(13)转引自常建华:《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森正夫近年回顾了这一概念提出的学术史背景,并寻求“地域社会场境的秩序论”的自我超越路径,森正夫:《民众叛乱、社会秩序与地域社会观点——兼论日本近四十年来的明清史研究》,于志嘉译,《历史人类学学刊》2007年第5卷第2期。
(14)参见常建华:《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5)岸本美绪:《伦理经济论与中国社会研究》,王亚新译,滋贺秀三等著,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344页。
(16)由于篇幅所限,对于市场体系在地域空间形成中的意义,不再展开讨论,可参见王铭铭对施坚雅的市场层级理论的讨论和批评,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146—147页。
(17)施添福:《区域地理的历史研究途径:以清代岸里社地域为例》,黄应贵主编:《空间、力与社会》,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5年,第68页。
(18)施添福:《清代竹堑地区的土牛沟和区域发展——一个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清代台湾的地域社会:竹堑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黄卓权主编:《研究丛书》(8)综论篇(1),新竹:新竹县文化局,2001年,第110页。
(19)董晓萍、蓝克利:《导言:不灌溉水利传统与村社组织》、《不灌而治——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献与民俗》,《陕山地区水资源与民间社会调查资料集》(第4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3—27页。
(20)刘汝骥:《陶甓公牍》,“绩溪县民情之习惯”,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第10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影印本,第611页。
(21)汪辉祖:《续佐治药言》,张廷骧编:《入幕须知五种》,光绪十年刻本。
(22)张佩国:《口述史、社会记忆与乡村社会研究——浅谈民事诉讼档案的解读》,《史学月刊》2004年第10期。
(23)刘志伟:《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谱牒研究——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9页。
(24)西佛曼、格里福编:《走进历史田野——历史人类学的爱尔兰史个案研究》,贾士衡译,台北:麦田出版社,1999年,第25页。
(25)“历史民族志”实践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结为“在档案馆里做田野工作”。与“历史民族志”相近的另一种民族志实践是“历史的民族志”(Historical Ethnography)。“历史的民族志”虽也要运用地方历史文献和口述历史资料,但所面对的时间是“当下”,而不是“过往的一段岁月”,因为历史活在当下,所以,当下也富有历史的厚重感,其基本特征可以归结为“在田野工作中做历史研究”。可参阅John and Jean Comaroff,Ethnography and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Boulder:Westview Press,1992.
(26)法国历史学年鉴学派第二代领袖布罗代尔提倡一种“长时段”结构分析的总体历史社会科学研究,将对应的“短时段”事件看作“转瞬即逝的尘埃”(参见费尔南·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1页)。整体史书写对本文的意义在于,将事件史纳入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中进行理解,正像保罗·利科批评布罗代尔对事件史的偏见时所说的,“事件虽被赶出了大门,却又飞进了窗户。”(参见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王建华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42页)
(27)罗愿:《新安志》卷1《州郡·姓氏》,萧建新、杨国宜校著:《〈新安志〉整理与研究》,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26页。
(28)罗愿:《新安志》卷1《州郡·姓氏·汪王庙考实》,萧建新、杨国宜校著:《〈新安志〉整理与研究》,第38—39页。
(29)汪道昆:《太函集》,胡益民、余国庆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1451页。
(30)戴廷明、程尚宽:《新安名族志》,朱万曙等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第183页。
(31)参阅臼井佐知子:《徽州汪氏家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江淮论坛》1995年第1、2期。
(32)章毅:《迁徙与归化——〈新安名族志〉与明代家谱文献的解读》,田澍等主编:《第十一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30页。
(33)《汪氏登原藏稿》第2册,同治八年九月初七日,“户部请禁呈词”,光绪二十二年(绩邑)东作门敦叙祠仿聚珍板(版)。
(34)汪云:《新安汪氏宗祠通谱》,“序”,道光二十年吴清山祠藏板(版)。
(35)《汪氏登原藏稿》第1册,“嘉庆十五年县主告示碑文”。
(36)《越国公祠墓志》卷2《税业》,咸丰二年越国公祠藏板(版)。
(37)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8页。
(38)程敏政:《篁墩文集》卷14《休宁汊口世忠行祠记》,《四库全书》第1252册,第245页。
(39)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第37页。
(40)林济:《“专祠”与宗祠——明中期前后徽州宗祠的发展》,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0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5页。
(41)章毅:《理学社会化与元代徽州宗族观念的兴起》,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9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20页。章毅:《元明之际徽州地方信仰的宗族转向:以婺源大畈知本堂为例》,《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7年第47期。
(42)郑力民:《徽州社屋的诸侧面——以歙南孝女会田野个案为例》,《江淮论坛》1995年第4、5期。
(43)《汪氏登原藏稿》,(绩邑)东作门敦叙祠仿聚珍板(版),印于光绪丙申秋月。下引“盗砍案”内容恕不一一注明出处。《汪氏登原藏稿》封面写作“登原”,而文中则写作“登源”。汪公大庙遗址即在今登源河畔。
(44)清恺修,席存泰纂:《绩溪县志》卷1《风俗》,嘉庆十五年刻本。
(45)沈复:《浮生六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第122—123页。
(46)新编《绩溪县志》谓花朝会有大、小花朝之分,大花朝十二年举行一次,小花朝逢闰年举行。(绩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绩溪县志》,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第1054页)新编县志未注明资料来源,笔者猜测,所谓大花朝十二年举行一次,概来自沈复的记载。2010年8月初,笔者到徽州做田野调查,实地考察了歙县云岚山汪王墓、绩溪县唐金岩(即唐金山)汪司马墓、汪公大庙遗址,并访问了附近南观村、仁里村等村落的汪福淳、汪俊庚、程加明等先生,他们的记忆和解释均“验证”了上述推测。
(47)笔者在绩溪县城拜访了绩溪县当地的徽学专家方静先生,他也同意这一解释。
(48)参见赵世瑜:《明清时期江南庙会与华北庙会之比较》,《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224页。
(49)汪福琪:《汪村南观花朝会》,《绩溪徽学通讯》2005年第2期。
(50)钱杭认为:“同姓宗族间的联宗多以实际存在的经济区域和生活区域为范围,如乡、县或相邻地区……在大多数情况下,联宗的直接成果,一是可以极大地唤醒各同姓宗族之间的历史认同感,二是能够成为一座桥梁,将各村落范围的宗族,整合成一个具有某种实际功能的地域社会。”钱杭:《血缘与地缘之间——中国历史上的联宗与联宗组织》,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24—25页。
(51)汪行广等主修:(绩溪)《汪氏世守谱》,“谱成告庙文”,民国4年木活字本。
(52)《越国公祠墓志》卷4,“道光二十七年奉府宪同饬各县出示严禁假冒告示”,咸丰二年越国公祠藏板(版)。
(53)汪行广等主修:(绩溪)《汪氏世守谱》,“癸巳司马道昆传帖”,民国4年木活字本。
(54)汪行广等主修:(绩溪)《汪氏世守谱》,“登源八景并序”,民国4年木活字本。
(55)这或许就是黄宗智所说的介于官方审判和民间调解之间的第三领域,参见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08页。
(56)据《越国公祠墓志》、《重修吴清山祠征信录》、《新安汪氏宗祠通谱》等汪氏族谱资料记载,自明至清后期,围绕歙县五处祠、墓、庙和绩溪县司马墓的讼争,大约每隔三十年就有一次(郑小春对明清徽州汪氏祠墓纠纷的研究,较全面地整理了汪氏祠墓纠纷的时空分布,参见郑小春:《明清徽州汪氏祠墓纠纷初探》,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编:《徽学》第4卷,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当然,族谱的记述体现了宗族集体记忆中的选择性“失忆”,即打赢的官司载入墓志和宗谱,而输了官司,则可能羞于记载了。在祖墓纠纷中,官司的输赢对于“两造”固然重要,但无论输赢,借机“会宗展墓”、重修墓祠、“呈官示禁”,无疑使联宗组织将官府的正统性和村落宗族的认同有机结合起来,联宗组织过程中城乡权威秩序也得以强化。
(57)刘铁梁:《“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58)2010年8月初,笔者去南观村、仁里村,访问了退休教师汪俊庚、汪福淳先生。他们说,南观、汪村、梧村等汪姓村落在花朝会轮值时,先将汪王神像抬到祠堂;仁里以程姓为主,在抬汪公时,也在祠堂祭祀显祖程忠壮公。笔者又访问了仁里村的村干部程加明先生,四十多岁的程先生回忆,他小时候还记得离村数里的忠壮庙,但程忠壮公在附近村落没有成为众姓供奉的神明。
(59)林美容:《由祭祀圈来看草屯镇的地方组织》,《乡土史与村庄史——人类学者看地方》,台北:台原出版社,2000年,第121页。最早提出祭祀圈概念的是日本学者岗田谦,台湾人类学者施振民、许嘉明关于祭祀圈的田野工作,也较为知名,施振民:《祭祀圈与社会组织——彰化平原聚落发展模式的探讨》,《“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75年第36期;许嘉明:《彰化平原福佬客的地域组织》,《“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75年第36期。
(60)科大卫:《皇帝和祖宗》,第5页。
(61)汤普森对“共有的权利”有如此之解释:“共有的权利是一个精巧的并且有时是复杂的关于财产要求、关于等级制度,以及关于优先接近资源、关于调整需求的惯用语,它作为一种地方法,必须在每个地区实行,并且绝不能当作‘典型的东西’。”爱德华·汤普森:《共有的习惯》,沈汉、王加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3页。
(62)王振忠认为,六朝以后,随着隋唐时期全国的统一,汪华信仰成了徽州一体化进程的象征。(王振忠:《新安江》,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33页)是否在隋唐时期,汪华信仰就已经成为徽州一体化的象征,尚待进一步的历史田野工作。
(63)林美容:《由祭祀圈到信仰圈——台湾民间社会的地域构成与发展》,张炎宪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88年,第101、120页。关于祭祀圈与信仰圈的关系,林美容另一篇文章有系统的阐述,林美容:《台湾区域性祭典组织的社会空间与文化意涵》,徐正光、林美容主编:《人类学在台湾的发展——经验研究篇》,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9年。
(64)上田信:《地域与宗族》,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宋元明清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89页。
(65)Maurice Freedman,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Fukien and Kuangtung,New York:Humanities Press,1966,p.21.
(66)钱杭:《血缘与地缘之间——中国历史上的联宗与联宗组织》,第344页。
(67)濑川昌久:《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钱杭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93—94页。
(68)华如璧:《兄弟并不平等:华南的阶级和亲族关系》,第46页。
(69)朴元镐:《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70)宋汉理:《徽州地区的发展与当地的宗族——徽州休宁范氏宗族的个案研究》,刘淼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88年。
(71)贺杰:《明清徽州的宗族与社会流动性》,刘淼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
(72)中岛乐章:《清代徽州的山林经营、纷争及宗族形成——祁门三四都凌氏文书研究》,《江海学刊》2003年第5期;中岛乐章:《围绕明代徽州一宗族的纠纷与同族统合》,《江淮论坛》2000年第2、3期。
(73)林美容:《由祭祀圈到信仰圈——台湾民间社会的地域构成与发展》,张炎宪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120页。
(74)井上徹:《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礼制》,钱杭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201、202页。
(75)这一讨论肇始于华琛关于香港新界天后信仰中对“神的标准化”的解释,以及1988年华琛和罗友枝主编的关于中华帝国晚期丧葬仪式的论文集(James L.Watson,Evelyn S.Rawski,eds.,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2007年又有苏堂栋(Donald S.Sutton)在Modern China(vol.33,n o.1)上主持的一组针对华琛“标准化和正统化”理论的批评文章。
(76)科大卫、刘志伟:《“标准化”还是“正统化”——从民间信仰与礼仪看中国文化的大一统》,《历史人类学学刊》2008年第6卷第1—2期合刊。
(77)唐力行将徽州的地域文化特点归结为:“徽州社会以其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造成了一个特有的区域社会生活体系:徽商、徽州宗族与新安理学始终处于互动互补的状态中。宗族文化是新安理学的核心。宗族为了在山地有限的生存空间争得生存发展的权利,必得依靠科举张大门第。徽商为宗族聚居、为文教科举提供物质条件。宗族组织、宗族文化强大的内聚力又是徽州商帮特别强固、富于竞争力的内在机制。”唐力行:《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页。
(78)马塞尔·莫斯:《礼物》,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4页。
(79)路易·迪蒙:《论个体主义:对现代意识形态的人类学观点》,谷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