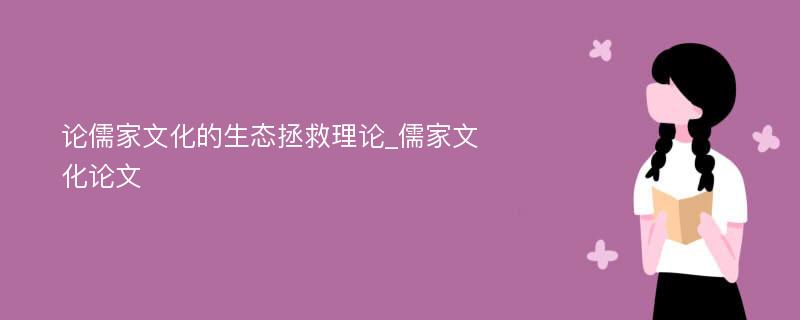
评儒家文化拯救生态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儒家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1)03-0137-04
面对全球性的能源、生态和环境危机,相当数量的中国学者提出了一种颇具“国粹”意识的见解或“拯救”方案,其典型者宣称:当前问题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比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更重要;而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应该从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中去寻找灵感;东方道德的基本原则是“和”,这个伦理原则的哲学基础就是人与大自然相和谐的“天人合一”思想;西方有些人现在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而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很多东方人反而没有认识到;因此要大声疾呼“只有东方的伦理道德思想,只有东方的哲学思想能够拯救人类”。儒家思想堪称“东方思想”的典型,所以为评说的集中和方便,上述见解和主张便不妨被视为“儒家文化拯救生态论”。
对于这种见解和相似的思想倾向,我们感到有必要冷静地思考和分析这样一组问题:究竟该怎样看待现代一些西方学者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寻求”?该如何看待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和实质才算确当?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实质、其生态保护意识在整个儒学中的地位又是怎样的?进而,生态的拯救和保护是否非得启动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可?
关于现当代西方学者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寻求”
现当代积极向中国传统文化寻求的著名西方学者,似可举英国哲学家B·罗素、历史学家A·J·汤因比和科技史学家J·尼达姆(汉名李约瑟)为代表。
二战前,罗素在《中国问题》(1922年)一书中就作过这样的中西文化比较:西方人喜欢用权力统治人类、征服自然,其生活方式以“效率主义”(竞争、冒险、不知足)为特点,西方文化最显著的长处是科学技术和方法,但西方的“效率主义”会导致破坏,最终只能使人类灭亡;中国人对生活所抱的态度是消闲娱乐、温厚典雅、知足常乐,中国文化最显著的长处是对人生目标的看法,“中国人发现了如能被全世界人采用就会使整个世界幸福的人类生活方式”;中西文化的前景应该是相互交流、取长补短,但中国人成功的希望很大,西文人成功的可能性却小得多,因为西方文化在近现代的优势地位会使西方人总是把中国人当做他们的学生,而不肯向中国人学习。(注:转见许苏民《比较文化研究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0页~第339页。)
二战后,面对一方面是科技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是能源、生态和环境全面危机及核威胁之间的尖锐矛盾,汤因比更明确断言:“西欧的活力会导致分裂,而不能促成稳定和统一”,要把西欧的力动性缓和到既对人类没有破坏性又可以提供活力的源泉的程度,就只能到西欧以外去寻找这种动力的创造者;中国有儒教的人道主义、合理主义以及大统一的政治经验等许多历史遗产,“这些都可以使其成为全世界统一的思想上和文化上的主轴”;所以,“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国家,而是中国。……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是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注:转见许苏民《比较文化研究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56页~第358页。)李约瑟在认真比较中国和西方科技思想史的基础上也指出:有机的自然主义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它表现在人际关系上便是一种和谐的“合作精神”和“团结气氛”,而西方占统治地位的则是机械的自然观、个人主义和“竞争、贪得无厌”;所以,在“人类将如何对付科学与技术的潘多拉魔盒”的问题上,谁要想“寻找一种牢固地建立在人性上的伦理学,一种能证明抵制各种控制社会的使人类丧失人性的发明都是正当的人道主义的伦理学,一种根据人类面临着由自然科学带来的不断增长的力量所提出的大量而惊人的选择前,可心平气和地判断将来采取什么最好方针的伦理学,那就让他们听一听儒家和墨家的圣人、道家和法家的哲学家是怎样说的吧”;总之,要对科技发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伦理的和政治的控制,那就要“按照东方的见解行事”。(注:转见许苏民《比较文化研究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0页~第383页。)
这些西方学者溢美中国传统文化的诚意或可不疑,中国的儒家文化拯救生态论似乎也跟他们的看法无异,但细加审辨,我们还是能够发现其间的差异和共同存在的不足。
首先,从根据上看,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好是工具式的,即它不过是西方人出于西方文化危机意识对本文化作自我反省的“附产品”,因而他们眼中的中国文化就难免是变了形的、理想化的,但他们能在西方文化客观上处于优势或强势的背景下做这样的反省则是理性的。而中国学者宣扬自己传统文化的世界意义和现代价值,则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自近代迄今一直整体处于劣势或弱势的背景下做出的,因而或多或少都出于民族传统文化的自恋心态和自保意识,带有情绪性、盲目性。
其次,在中西方文化发展的前景问题上,罗素、汤因比、李约瑟三位学者所持的都是互补论或融合论,明显地表现出文化开放的宽广心胸和气量,因而有利于各国、各地区和各民族心平气和地联手对付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问题;而儒家文化拯救生态论的典型者则同O·W·斯宾格勒和S·P·亨廷顿一样,持的是中西文化冲突论的立场,(注:季羡林先生的“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就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之论即是明证。——《二十一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载1992年3月10日《文汇报》。)其心胸、气量、效果可想而知。
再次,儒家文化拯救生态论者和上述西方学者似乎都忽视了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和哲学思想赖以存在的基础,(注:即,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J·S·穆勒、R·琼斯和J·S·密尔集中研究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作过深入分析的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稳固的社会基层组织,以农业和手工业密切结合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为经济基础,以及以“东方专制主义”为上层建筑的“封闭”、“停滞”的社会。)以及各国、各地区和各民族普遍认可的处理当代国际政治、文化(生活方式)关系的基本准则,(注:就我们的论题而言,这样的准则应该就是政治独立、文化(或生活方式)多元并存,即相互尊重的对方的政治、文化(或生活方式)选择。)而这就意味着:1.传统儒家文化本身也存在一个必须“转型”的问题,因而在具体给出将它应用于当代社会的操作办法并证明其可行性之前,对它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意义”作任何溢美,都不免有主观主义之嫌;2.将中国人的传统政治模式、伦理生活方式向世界推广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是危险的。
最后,儒家文化拯救生态论者既没有对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实质作出客观、全面的理解,也没有能够恰如其分地看待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实质和生态保护意识在整个儒学中的地位。
关于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和实质
当儒家文化拯救生态者宣称“只有东方(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能够拯救人类”的时候,实际上就暗含了在当前国内学术界颇为流行的这样一种见解: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西方近代科技理性”(即,以人与自然二分对立的认识论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论为基础,强调人类运用科技发明征服自然的思想观念);生态危机的实质是“西方近代科技理性的危机”。
近代科技理性作为直接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工业文明(或近代科技文明)的主导观念,自然“罪不可免”,但认识仅止于此就很难解释这样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1.为何在以“天人合一”思想著称的中国古代农业文明中也照样存在诸如西北地区、黄土高原地区这样的大规模生态破坏?2.据恩格斯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至迟到19世纪中叶,人们事实上已经认识到了人类生产行为对“自然界惯常行程”的干扰,即意识到了生态平衡和生态保护的重要性,(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8页。)然而,生态破坏为什么就没有随科学理性的进步而得到相应的遏制,反而愈演愈烈、直到爆发当代能源、生态和环境的全面危机呢?3.就当前来看,在西方国家的生态环境、西方人的生态保护意识普遍改善和提高的同时,为何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最为严重的又恰恰是有着“天人合一”思想传统的中国这样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分析可以知道,西北地区大沙漠的形成和黄土高原的大规模水土流失,都主要是由于历代中原王朝在与西北和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中为了加强和巩固边防,在这两地加紧农田开垦而造成植被破坏的结果;(注:西北地区的情形,参考陈业新的《秦汉时期西北开发的历史教训》一文,见2000年12月8日《光明日报》。)近现代生态破坏的势头之所以难以遏制,主要是在近代科技水平、市场竞争的背景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追求高额利润而不断扩大再生产和进行世界性经济扩张的结果;而当代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问题之所以在发展中国家最为突出,也主要是在生产、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先进的西方国家步入高科技(或环保型科技)的后工业社会,使工业化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发展中国家则由于国际经济和政治利益冲突、国内市场竞争和高人口出生率带来的巨大压力,由于本身科技发展水平整体滞后的极大限制,难免就会出现以能源、生态和环境破坏这种“杀鸡取卵”的方式来求得物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这就足以表明,全球性能源、生态和环境危机的根源和实质,并不仅仅在于思想观念上的偏差,更主要的是在于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群与群)之间的利益竞争和冲突。(注:“大跃进”时期,我国在“超英赶美”思想的主导下造成大规模和大范围的生态破坏,也是这方面的铁证。)进而,当代方兴未艾的生态伦理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在表面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根本上则是以生态问题为中介、以利益问题为核心的人与人(“群”与“类”、今人与后人)的关系问题。所以,把生态危机问题仅仅或主要当作观念问题来看待是远远不够的,从生态危机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重威胁这一现象出发,判定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当前比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更重要”,也显然过于简单和直观。
关于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和生态保护意识
传统儒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内涵,因对“天”的解释不同而差别很大。如,有以神意(“意志之天”)释“天”而主张人的行事、社会的治理应服从神意的,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在殷商之际发端,大成于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也有以德性(“道德之天”或“义理之天”)释“天”而主张人的道德本性源于“天”、人际伦理关系应遵循“天道”或“天理”的,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发端于孟子,中经《中庸》而大成于宋明理学;还有以“自然之天”释“天”而主张人事应随顺自然界的本性、因循自然界的法则的,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在先秦时的原始儒学直至宋明理学中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
当然,从上述三种“天人合一”的观念出发都是可以引出生态伦理的主张和生态保护的要求的,如,《礼记·祭义》所谓“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教也”;《孟子》所谓“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仁义法》所谓“质于爱民,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谓仁?”等等。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在传统儒学的演进中“意志之天”意义上的天人合一观念至唐代以后就逐渐式微,“自然之天”意义上的天人合一观则始终显得模糊、暖昧,惟有“道德之天”意义上的天人合一观念成为正统和主流。自《孟子》所谓“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以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的“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模式始,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就逐渐倾注于伦理道德领域。宋明时期,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思想,程颢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点,朱熹的“与理为一”的理想,以及王阳明的“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等说法,都不过是对孟子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思想模式的进一步解释和发挥。正因为如此,传统儒家文化中才会出现这样一种有趣而难堪的情形,即生态保护意识最浓,其思想与当代认识论意义上的生态伦理最为接近的,是荀子这位儒、道、法、墨诸家思想杂糅,并极力主张“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杂儒”。(注:荀子关于生态保护的集中论述,见于《荀子·王制》。)
简言之,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在总体上或主导方面是为其“内圣外王”的基本价值取向服务的,它在本质上主要是一种以个体对宏观宇宙生命的感悟和体验为基础的诗化或审美化了的人生道德修养境界,它与建立在科学和认识论基础上的当代生态伦理思想相去甚远,因此无论儒家文化拯救生态论者怎么超拔其当代意义都是没有多少根据的。
关于启动儒家思想文化拯救生态的方案
抽象地说,对于人类共同面临的生态拯救这一急务和重任,各国、各地区和各民族都有责任积极发掘各自文化传统中的有用资源,并应当相互交流和借鉴,而儒家文化拯救生态论者想给科技的发展建构一种人文前提或人道主义的观念制导系统,想让发展中国家尽快跻身后工业文明或“生态文明”的行列,最大限度地消除工业化带来的种种生态负效应,这种心情和初衷也可以理解。不过,拯救和保护生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来自实践的应用性课题,因此传统儒家文化是否真有拯救生态的效用和能耐,启动传统儒家文化来拯救生态的设想和努力是否真有价值和意义,都要取决于是否能成功地将传统儒家文化与当代生态保护的实践“对接”,即取决于它们是否具有应用、操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般而言,对于批评性的意见,我们不必强求它具备应用性或可操作性,因为“批评”本身的性质决定着它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对社会现实和既有观念的“解构”,在于思想的“启蒙”;而建设性的意见则应当具有可供应用和操作的层面,否则理论本身就只会是无果之花,甚至会成为永无休止的笔墨官司、纸上游戏。以此衡量,作为一种建设性意见和主张的儒家文化拯救生态论,其可悲之处就在于至今在口号、宣传的层次上裹足不前。
可以说儒家文化拯救生态论之所以陷入这种窘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传统儒家文化本身的特点和局限决定的。兹举数端如下:
其一,我们已经讨论过,传统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在主导倾向上并不是一个科学理性或认识论的命题,而乃是一个道德理性或审美体验论、人生修养论的命题,因此尽管它也有利于生态保护的一面,并可以作为一种供个体选择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但在现实生活中却难以保证它被所有人甚或多数人接纳和奉持,也就是说它并不具有必然性和普适性的意义。
其二,就生态环境的拯救和保护而言,克服传统科技理性步入的误区、更新观念是非常必要的,但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还是开发生态型的科学技术,而传统儒学因价值取向上的偏差是很难成为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的。(注:冯友兰先生在谈到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技的时候就曾指出过:“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照他自己的价值标准,她毫不需要。”参看《中国哲学的精神:冯友兰文选》,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76页。)
其三,生态危机的深刻根源和实质在于人际利益冲突,而追求利益又始终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有力杠杆,这种严酷的事实注定采取儒家那套在道义上呼吁“和为贵”和“节欲”的办法还过于迂缓。换言之,在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的过程中,对人际利益进行协调,对急功近利的生产行为和不利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进行禁制,最现实的途径和最有力的措施恐怕还是健全法制,而儒家思想明显属于“人治”的范畴,因而在这方面也是提供不了多少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和有用思想资源的。
总之,传统儒家文化并不能直接为当代生态环境的保护所用。那么能否用“对它做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解释和发挥”(注:汤一介:《儒学的现代意义》,载《百科知识》1994年第3期。)的办法来使它在这方面产生积极作用呢?对此,我们的看法是:不能说绝对不可以,但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是否非得如此,有没有其他更直接、更有效的途径?儒家文化拯救生态论者之所以要大声疾呼重视和启动传统儒家文化,正说明传统儒家文化是现代人所陌生的,也即是“断代”的,这样,复兴和创造性地拓展儒家文化的努力就只有在当代文化背景中的确缺乏生态保护的思想资源的情况下才确有必要。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当今世界并不缺乏这样的理论资源,相反,这样的理论资源无论在中国和国外都可谓汗牛充栋,而且都已经成了学术讨论、社会教育和舆论宣传中的主导意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得不认真地去思考,启动、修补乃致根本性地改造本身就“先天不足”的传统儒家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面对人类所共同面临的生态、能源和环境的全面危机,我们主张与其简单地重复或苦心修补甚至根本改造儒家传统文化,倒不如面对现实,敞开胸怀,放眼世界,直接利用富有当代时代特征和适应当代社会发展要求的思想资源,建构起人与自然环境之间互补和谐、协同进化的当代生态伦理和生态哲学,并加强理论的应用性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