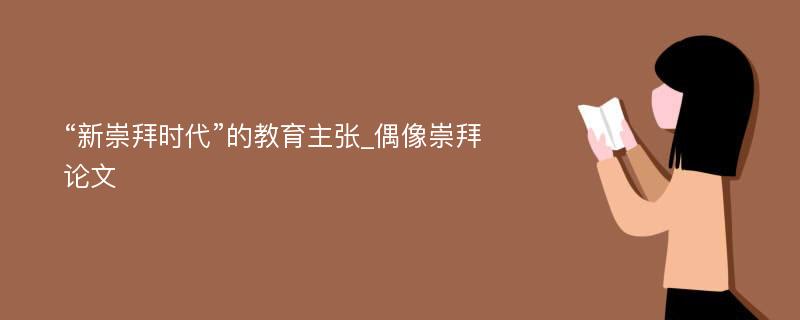
“新崇拜时代”的教育命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命题论文,崇拜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心有星星结 青少年“粉丝”群体的迅速崛起
在价值多元的文化冲击下、在注意力经济的引领下粉丝们组成了规模空前的团体,创造出了一整套严密的“游戏规则”,俨然形成了自己的“江湖”。他们冲击着时代,也改变着自己。
在QQ聊天工具的那头,一个网名叫李月月的大一学生,飞速地打着字,向记者讲述了她成为“玉米”(某选秀节目冠军李宇春的粉丝们对自己的称呼)之后的生活:“从在电视上看到她第一眼之后、我的生活被完全改变了。在她参加选秀比赛期间,我每天都说服我认识的人为她投票,因为一个人投票的数目是有限的,后来我又开始到街上向陌生人拉票。比赛结束后,我买她的专辑,说服学校超市放她的歌,买票看她的演唱会。因为‘玉米’的代表色是黄色,我的耳环、项链都买黄色的,手机和牙膏都用她代言的牌子。”月月还告诉记者,她每天晚上都会在宿舍花上四五个小时的时间上网,到“百度春吧”、“玉米基地”等“玉米”们聚集的网络平台发帖子表达对李宇春的支持,在各网站关于李宇春的人气调查网页上投票。现在,月月是“全国玉米圈QQ群”的管理员,每天带动群内全国各地的“玉米”讨论有关李宇春的话题。在采访中,她一再强调:“比起一些‘玉米’,其实我做得挺少的。”据她介绍,“全国玉米圈”仅仅是区别于其他“玉米”群落的一个名字,并不代表规模很大,她所管理的只是一个很小的网络群落,她也只是众多“玉米”中的“一粟”。
除了“玉米”群落,在选秀中崭露头角的选手们,也都有着各自的拥趸者。“凉粉”、“盒饭”、“花生”、“醒目”、“乐橙”等,就是一些选秀明星的粉丝们为自己的群体起的名字。除此之外,像姚明、刘翔这样的体育明星,于丹、易中天这样的文化明星,刘德华、周杰伦这样的港台娱乐明星,都拥有着庞大的粉丝团。虽然,众多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对象呈多元化,比如,也有一些青少年追崇比尔·盖茨等财富和智慧的拥有者,但是青少年群体迷恋或崇拜的对象,主要集中于影、视、歌、体明星。
在此之前,人们对偶像崇拜一词并不感到陌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邓丽君、三毛、琼瑶就分别成为不同时代青少年的崇拜对象,这种不同的偶像选择散发着浓浓的时代味道。如今的青少年偶像崇拜也不例外,不仅显示了当代青少年压力巨大、价值观逐渐多元、个性空前张扬的时代特点,更从过去的个体行动骤然变身为一种群体行为。同时,这一群体伴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也被打上了“迅速”、“虚拟”、“海量”、“主动”的新媒体烙印。越来越多欣赏或痴迷于某一偶像的青少年,通过网络组成各种各样的粉丝群体,出入于各个演出场所,现身于与偶像相关的专业网络基地。
据一项调查显示,国内各种成规模的粉丝团已经有2000个以上,比较活跃的有300个以上。其主体是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出生的人,年龄在15岁至30岁之间。较小的团体成员有数百人,较大的则在数万人甚至10万人以上。例如,一个专门的粉丝网站“粉丝网”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吸引了850万用户,其中周杰伦的粉丝就有70多万。此外,网络上还有各种其他形式的歌迷组织,以2007年某选秀节目冠军陈楚生的全球歌迷会为例,这个歌迷组织下设地方分会,每个分会都有负责人。同时,陈楚生在网络上还有官方论坛和百度贴吧,其中的百度贴吧在陈楚生出道至今半年时间里,已有1244万篇帖子,并以每天约5万篇的速度增长。在贴吧中,除了吧主等管理层,下面的粉丝被细化成投票组、宣传组、美工组、视频组等,分工明确地为陈楚生集纳人气。不仅如此,没有参加固定组织而散布于全国各地的“散粉”们,也会以偶像的各种活动为“号令”,短时间内迅速聚集。粉丝群体的这种种表象,开始引起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等各领域学者的注意,并由于此种现象对青少年的成长带来巨大影响,引起了教育者的警觉。粉丝群体,已然在21世纪粉墨登场,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壮大。
我迷故我在
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心理机制
对粉丝群体的出现,一些人不解,一些人不屑,甚至还有一些人鄙弃。然而,青少年粉丝现象并非偶然,其背后是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娱乐文化空前繁荣、身心压力日趋沉重所带来的时代冲击,并被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发展规律所左右。
“我想,没有人会像我一样,为了一个从不认识的人做同一个梦,反反复复。这些话你也许永远看不到,这些付出你也许永远体会不到,这些爱你永远想象不到,可是不论你与我擦肩而过或是消失在霓虹的尽头,亲爱的,我都会念着你的名字,一直一直……”
这是“百度春吧”上,一名“玉米”留下的深情寄语,更多的青少年粉丝把这种对偶像的喜爱和思念化为种种被旁观者视作疯狂的行为:买机票飞往遥远的城市只为看一场偶像的演唱会;省下吃饭的钱,奔赴不同的音像店买多张偶像的CD,以此改变唱片销量的统计数字;花大把的时间,与偶像所在的经纪公司谈判,为偶像争取利益。粉丝群体,以前所未有的行动力,引来了无数的关注目光,同样,也引来了旁观群体的集体不解甚至蔑视。
“我觉得他们追星就是因为生活太好了,被家长惯的。”“让他们了解了解那些吃不上饭、上不起学的农村孩子,看他们还追不追星?”“有这样的时间做点什么不好,国家算白培养他们了。”“如果我的孩子也这样,我就打死他!”这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的上一代人对青少年追星行为的主流看法。“疯狂”、“扭曲”、“败类”等词汇也不断出现在一些受访者略带情绪的观点陈述中。然而当下看似让人无法理解的青少年偶像崇拜,是否真的如一些人认为的那么无知与盲目?
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学系副教授岳晓东,对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研究了十年之久。在他看来,青少年偶像崇拜问题不应只从道德角度进行分析,更应探寻这一群体偶像崇拜的心理动机。他说:“青少年通过对不同偶像的认同和依恋,来确定自我价值,寻求自我发展,从这层意义上讲,偶像崇拜作为一种特殊的心理行为,是青少年时期心理矛盾运动的产物,有非理性和盲目性的一面,也有必然性和过渡性的一面。”
“什么是偶像?偶像就是自己站在哈哈镜前照出的那个影像。青少年偶像崇拜投射出的是崇拜者心中的某种潜在欲望。”岳晓东认为,青少年的偶像崇拜首先源于心理上的“自我映射”需求。每一个人都有璀璨的梦想,青少年更是对梦想有着无限的追求,但是当他们发现理想和梦幻难以实现时,往往会痴迷于某一偶像,将自己的梦想交由偶像代替完成。正如记者采访的一位“玉米”所言,“我把我的梦想交给她,让她带着我的梦想飞翔”。
青少年的偶像崇拜起到了心理补偿作用的观点也被一些专家提出。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其心理会经历由极度依赖父母到个性逐渐独立的变化过程,在心理学上,此种现象被称为由“即亲感”向“遥亲感”过渡。在这个过程中,父母的影响力逐渐下降,青少年开始寻找假想性和虚幻性的精神支撑,因而会出现对某一偶像的极度崇拜,作为成长过程中父母对其安慰作用降低的心理补偿。同时,反叛的心理让他们希望由别人代替父母对其进行引导。一个中学生给赵薇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也想成为一名演员,可我的父母认为那是不务正业,您说我应该怎么办?”
在“全国玉米圈QQ群”的管理员月月看来,成为一名“玉米”让她找到了强烈的归属感,她说:“打理这样的一个QQ群,与伙伴们讨论和支持同一个人,很幸福。”更多“玉米”也纷纷在网络上表达:“‘玉米’群体更像一个兴趣小组,可以在一起探讨各种事情。”“在枯燥乏味的现实生活中,能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是件很棒的事。”中国文化管理学会国际学术交流总监、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张嫱认为,偶像崇拜是对青少年孤独心灵的安慰,给他们带来了群体的温暖。她说:“事实上,很多粉丝平常在现实世界很可能是被压抑的,因为普遍的观念认为迷恋偶像是肤浅、幼稚的事。因此在网络上的粉丝可以轻易地找到同好,而且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或对他们的行为加以价值判断。”
此外,青少年偶像崇拜,也可以让青少年得到有益的发泄和释放。学者何小忠分析说,在偶像崇拜的队伍中,那些处于青春期的学生们,性心理迅速发展、膨胀,急于寻找一个目标来附着和释放,当他们把这种情感投射到异性明星身上时,他们可以为“星”动情、为“星”如痴如醉、神魂颠倒。对他们来说,偶像就像“天上的星”,只能盼和看却永远摘不到,使这种感情被宣泄得既彻底,又安全。最后,由于追星梦不可能实现,他们会自动放弃,并带着追星过程中获得的满足,回到现实的生活中去。
因此,岳晓东指出,偶像崇拜表达的是青少年对梦想和生活的美好追求,是其发泄不满和倦怠情绪的大胆呐喊,也是对传统价值体系与教化内容的叛逆表达。其终极目标是在寻找自我,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正常心理现象。对青少年偶像崇拜行为,我们既不应采取淡化态度或者不干预态度,也不应该把偶像崇拜定义为一种纯品德行为,简单粗暴地加以排斥和否定。
一半清醒一半醉 不同粉丝间的个体差异
当下的青少年粉丝群体,一些人从偶像崇拜的过程中获取自身发展的养分,一些人被偶像的光辉照耀得失去本真颜色。正是这种差异,使加强对这一群体进行引导显得极为迫切。
新时代的粉丝群体,区别于过去跟风式的被动崇拜,越来越以一种主动而独立的方式,为自己吸取养分、为社会增添活力。在这个变革的年代,青少年粉丝群体的种种行为,散发出颠覆的味道。
在苏醒“EP发布会”上,北京市崇文区某学校一个网名叫樱桃的中学生,格外引人注意。她手里捧着一大束粉色的玫瑰花,在等待的过程中显得紧张又幸福。身边的人都亲切地称呼她为铁杆小“醒目”(苏醒歌迷对自己的称呼),因为在苏醒出道的半年时间里,她上街拉过票,参与过有关苏醒的大大小小十次活动,也去苏醒拍摄新歌MV的现场探过班。但她告诉记者,这些不是最令她骄傲的事情,她不断提高的英语成绩才让她觉得最高兴。“他是我学习的动力,我不仅喜欢他漂亮的转音,更喜欢他在比赛中的拼搏精神。他的英语特别好,喜欢上他后,我也疯狂地学习英语,这使我每次英语考试成绩都有提高。”因此,她自认为是一名优质粉丝。
何洁的粉丝小奇,她的追星经历甚至让她获得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在大学期间,出于对何洁的喜爱,小奇组织了很多的“盒饭”(何洁歌迷的自称)支持何洁进行比赛,通过组织各种各样的歌迷活动,小奇的组织能力得到了表现和锻炼。这让她毕业找工作时,在一家广告公司的面试中脱颖而出。她说:“我企盼何洁实现梦想,同时我自己也没有松懈。”
李宇春的歌迷们更是发起成立了“15元基金”,加盟的歌迷每月定期向一所孤儿学校捐款15元。“玉米”们还为中国红十字会下辖的“玉米爱心基金”捐款,目前已募集了将近200万元。F4成员言承旭的歌迷为他成立了言承旭春蕾班、捐助台湾展望会、捐助奥比斯流动眼球医院……从2003年至今,“旭迷”们参与的大大小小的慈善活动,总共募集到款项100万元人民币左右,而这些钱,均出自粉丝们的自发捐款,所有的资金明细均会在网站中被详细列出。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张嫱说:“当代粉丝的主体是主动的、积极的,网络的连接使得粉丝如虎添翼,展现了庞大的力量。那种粉丝都是无知与被动的评价,是因为对粉丝没有正确的理解,可以说是典型的偏见。”
但是,偶像崇拜者中也有一部分青少年迷失了方向。香港城市大学的岳晓东指出,在粉丝群体向人们证明他们积极、健康的同时,也无法掩盖一部分青少年粉丝让偶像成为了梦想的“独裁者”。他们在迷失自我的过程中,演出了一幕幕悲剧。
2003年,大连一位16岁少女在家中自杀,起因只是母亲没有给她买偶像张国荣的唱片;2004年,武汉女歌迷为思念谢霆锋而跳河寻死;2005年,选秀节目“超级女声”的粉丝们因为听闻节目有“黑幕”而扬言要集体自杀;2007年,众多媒体又集中报道了由于偏执追星而家破人亡的杨丽娟。
有专家指出,虽然青少年的偶像崇拜会对崇拜者自身和社会产生一定积极影响,但其消极作用也是明显的:一是由于过度崇拜明星而疯狂参加偶像的活动、购买明星物品,使青少年的消费大大增加。二是由于过高评估偶像价值,使青少年的自我意识和信心降低,缺乏清醒的自我认识。三是由于过分认同和依赖,导致青少年对其崇拜的偶像想入非非,做出不切实际的危险行为。
对于粉丝群体中存在的个体差异,粉丝们自己也并不否认。在他们看来,粉丝的“江湖”中,有“高手”,也有“小兵”,有“正义的代表者”,也有“邪门歪道的拥护者”。“在粉丝里,什么样的人都有。”某歌手北京歌迷会会长晓岚说。
粉丝显现出的巨大力量既可以对个人成长和社会进步积极推动,也可能留下一幕幕人间悲剧,这种不同粉丝间的巨大差异,表明偶像崇拜本身并无对错,重要的是崇拜者自身如何把握尺度。因此,专家指出,教育者对青少年的偶像崇拜不应嗤之以鼻,而应正确引导,对其作用于青少年的巨大影响,不应不闻不问而应因势利导,最终将偶像崇拜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挑战化为促进其健康发展的机遇。
给我一双慧眼 对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教育引导
教育工作者应该一边摘掉自己的“有色眼镜”,走到粉丝群体中,帮助粉丝们形成批判性思维;一边擦亮青少年的“慧眼”,帮助他们寻找偶像的精神内核,以助推青少年个人的健康成长。
“青少年粉丝群体像一艘没有舵的船,需要有人在成长的航行中为其把握方向。”中国传媒大学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室的张洁认为,无论是郭敬明的作品《梦里花落知多少》被法院判定抄袭之后,其粉丝对郭敬明拒不道歉的支持、对法律的无理谩骂,还是一些选秀明星的追崇者们对其他偶像进行攻击,那是缺乏批判性思维,无法认清偶像,也无法认清自己的盲目行为。不仅如此,一些青少年学生在追崇偶像的过程中,荒废了自己的学业,甚至把学习和做人的理性态度都抛弃了。例如,在选秀节目“超级女声”的比赛过程中,一些中学生逃课奔赴各赛区的比赛彩排现场,为偶像呐喊助威。一位平时成绩很好的上海学生,因为听说自己的偶像张国立导演和“超女”周笔畅共同合作的电影到上海选秀,而不顾高考在即,跑去报名参加比赛。这样的“执著”所带来的不仅是遗憾,更会给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之路种上苦果、铺上荆棘。
张洁说:“青少年偶像崇拜虽然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并受到青少年心理发展规律的影响,但并不等于他们的行为不需要教育的引导。其实,这些青少年粉丝的疯狂行为,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并不知道是谁在享受着他们的付出。”浙江省一次关于青少年偶像崇拜的调查显示:青少年把零花钱的60%都花在了偶像崇拜上,他们许多关于偶像商品的消费行为,明显体现了炫耀性消费的特点。一些专家指出,即使当代粉丝群体具有了较强的主动性,但粉丝们始终还是站在娱乐产业链条的消费终端。他们越疯狂,这条产业链便越稳固,经济公司的利益就越会得到满足。
针对粉丝们的热情越来越被利用为商品化、市场化的筹码,而多数粉丝却并不了解媒体运作规律的现实,张洁提出,引导青少年群体冷静、理智地支持偶像,需要对青少年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对青少年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就是要破除媒介的神秘感,让他们了解娱乐产业的内部规则。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才能更好地发挥创造性,以积极健康的态度支持自己的偶像,而不是沦为流行文化的被动接受者与消费者。”张洁说,“应该让那些看着荧屏痴情呐喊的崇拜者们了解,他们在电视中看到的热泪盈眶的粉丝们,很有可能会在节目结束后,直奔经纪公司要钱!通过这样的媒介素养教育,不仅会减少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极端、扭曲行为,也会锻炼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最终作用于学生学习与生活的一点一滴。”
在岳晓东看来,对青少年的偶像崇拜行为进行教育引导,不但必要并且紧迫。首先,应引导青少年多元选择偶像。教育工作者应引导青少年选择更多的影视和体育领域之外的杰出人物,这种崇拜将会是一种较为理性的、有条件的、相对性的心理认同。其次,要引导青少年多元认同偶像。如果青少年过多重视偶像明星青春貌美、多才多艺及性格反叛等特点,而缺乏对其成功原因的探寻和认同,青少年偶像崇拜则容易走入歧途。因此,教育工作者应该引导青少年从不同层面来认同偶像,以此避免青少年过分神化偶像而引发极端行为。
同时,目前的家长和学校重视通过榜样教育对青少年进行思想品德和意志品质的引导。但是为青少年树立“官方”榜样和学生自己选择偶像一直存在着某种对立:一方面学生不断更换自己崇拜的偶像,无视教育榜样的存在;另一方面学校忙于加强榜样教育的力度,希望驱走青少年心中的偶像。
针对学生态度与学校愿望之间的巨大反差,岳晓东提出了“偶像一榜样”教育。一方面,要将“偶像榜样化”,引导青少年把偶像当作平常人来看待,淡化青少年对偶像的顶礼膜拜,强化对偶像的榜样学习,学会从不同层面接受同一位偶像,再从不同偶像身上吸取同一养分。另一方面,要将“榜样偶像化”。要引导青少年从亲朋好友身上汲取成功的元素,将他们视为自我成长的偶像。因为,这些榜样虽然不具有名人的感召力,却贴近青少年,可随时给他们帮助和指导。正如岳晓东所说:“对青少年进行‘偶像—榜样’教育,能协调偶像崇拜与榜样教育的矛盾冲突,调动学生参与榜样学习的积极性,使青少年对偶像批判性接受,多元化认同,最终开拓榜样教育的新方向、新资源与新模式。”。
然而,这一切之于青少年偶像教育的探索,还仅仅停留于愿望之上。“春春,只要你一回头,永远是一片黄澄澄的玉米地!”“苏醒,你的成功承载了我们共同的梦想。”“楚生,告诉我们你希望到达的地方,我们会助你越飞越高!”越来越多的青少年粉丝正心甘情愿地沉醉付出,这提醒着我们,使他们的热情与冲动积淀成青少年自身的五颜六色,将是这个变化莫测的“新崇拜时代”中,全社会共同的教育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