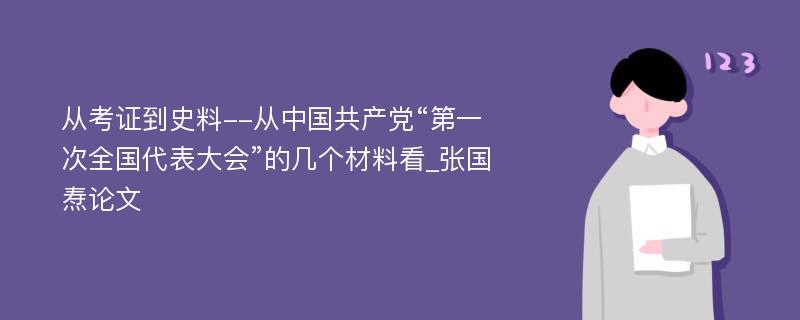
由考证学走向史料学——从中共“一大”几份资料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大论文,史料论文,中共论文,走向论文,资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1)05-0093-08
中共“一大”因在秘密状态下召开,除后来发表的回忆录外,保存下来的历史资料极少。故此,要弄清“一大”的历史事实,必须对这些历史资料作严谨的分析。众所周知,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有关“一大”的考证研究,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笔者曾就此评论说,“如果以研究工作的劳动效率观之,对中共成立史这一历史长河中短暂的一幕所投入的研究量之大,是不同寻常的”。[1](P4-5)笔者也曾对各种回忆录的真实性作过谨慎分析,并依据原始资料对其作了比对、订补;这项工作反映在拙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
还在撰述《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时,笔者即已感到,更需要作谨慎分析的是通行见解的形成过程,以及这些见解引以为据的史料的形成过程,而不仅是回忆录。关于“一大”通行见解的形成过程,拙著也曾对董必武回忆录的前后变化作过探讨,并提请注意共和国时期意识形态对回忆录的限制。[1](P255-264)但是,实际上,此类意识形态限制不仅影响有关个人回忆历史,还影响了早期党史重要史料的翻译和编纂。本文将对中共“一大”研究中现今仍被视作重要史料的几份资料进行探讨,并试图表明这样一种看法,即今后中共“一大”研究所需要的,不是对现有各种资料进行比对的“考证学”,而是充分斟酌、分析资料内容的“史料学”。数十年的成果和积累,要求中共“一大”研究必须从“考证学”进一步走向“史料学”。
本文将要展开论述的是研究“一大”的学者都非常熟悉的几份资料,即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葛萨廖夫《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和《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1929年12月31日)》。通过探讨,我们将看到,在共和国时期党史研究中,史料的翻译、整理、编纂等无一不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笔者坚信,通过了解这一事实,以资料为前提的“一大”研究将进一步深化。
一、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的几个版本
陈潭秋发表于1936年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作为“一大”代表本人执笔的早期回忆录,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该回忆录由于谈到了“一大”的召开时间(1921年7月底)、代表人数(13人)和大会讨论情形,学者将其作为一级资料而经常引用。但奇怪的是,这部回忆录的原文到底如何,中国国内却从未发表。也就是说,大多研究“一大”的学者对此背景毫不知情,因而对该资料的利用只能是不完整的。
陈潭秋的回忆录,是为纪念中共建党15周年而撰写,最初发表在莫斯科发行的共产国际机关杂志《共产国际》(中文版)1936年第4/5期合刊上。《共产国际》除中文版外,还有俄文版、德文版、英文版等,也都刊载了陈潭秋此文①。不过,考虑到陈潭秋的外语能力,他不可能直接用外语撰写回忆录;就常识而言,中文版所载回忆录应是原文,而其他语种版本应是由中文翻译的。
《共产国际》是共产国际的代表性机关杂志,但该杂志刊载的陈潭秋回忆录,在其后相当长时期内未得重印,也没有人标明出处加以引用②。中国国内重新发表该回忆录,是在共和国成立后的1950年代初。刊载该文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依据《中央关于收集党史资料的通知(1951年7月)》,为收集和研究中共党史资料而刊行的内部刊物《党史资料》第1辑③。《党史资料》在刊登该文时加了如下《编后记》:
陈潭秋同志的《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于1936年,曾在1936年7月出版的《共产国际》上发表,这次在本刊刊载时略去了末尾论述当时政治形势的一段。
从《编后记》看,《党史资料》在转载《共产国际》版回忆录时,仅省略了部分原文。但事实并非如此。经比对可知,两个版本不仅文体迥异,大会会期、代表人数等部分内容也有经过改动的痕迹。具体而言,在《共产国际》中文版中,“一大”代表从各地来到上海的时间作“7月下半月”,大会于“7月底”召开;但在《党史资料》版中,“7月下半月”被改为“6月的下半月”,大会召开日期则被改作“7月初”。由于被改动的是两处而非一处,且其内容互为关联,故决非排版失误等非主观原因所造成,而是为了把原本明确为“7月底”召开会议的资料,用于证明会议于“7月初”——即当时的通行见解——召开而做的改变。而且,关于“一大”代表的人数,《共产国际》中文版称“这次到会的一共有十三个人”,而《党史资料》版竟将此句删除。
此外,明显不同的文体则表明,《党史资料》版不是从《共产国际》中文版转载而来,可能是利用其他语言版本重译的。何以如此?去年,中国青年作家丁晓平发表《陈潭秋与其珍贵的〈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以下简称“丁文”),[2]其中照录了该回忆录的翻译手稿(原始文本及编辑删节文本),为我们破解谜底提供了重要线索。
值得关注的是,丁文照录之翻译手稿(16开,共计7页,钢笔手写,译者和编辑修改者不详,时间亦未注明)④,尤其是编辑删节文本与《党史资料》版完全一致,据此可以断定,上述有关“一大”会期及代表人数的改动、删除发生在编辑阶段。丁氏推测,该翻译手稿成于1970年代后半期,曾刊于《百科知识》1979年第2期;[3]这是因为丁氏不知道曾有过《党史资料》版。笔者认为,该手稿无疑是1950年代初为《党史资料》翻译的。不过,丁氏的重要贡献在于,除翻译手稿外,他还为我们介绍了编辑删节文本,如下事实也才浮出了水面,即《党史资料》版并非录自《共产国际》中文版的汉语原文,而是将译成外语、刊载于其他外语版《共产国际》的回忆录重新译回汉语而成。1950年代初,《党史资料》编辑部很可能未能找到中文版《共产国际》,因而不得不利用俄文版或英文版译回汉语⑤。
《党史资料》的编辑改动译文中“一大”会期和代表人数,应是意识到译文中这些方面与当时的通行见解(7月1日开幕、12名代表)⑥有抵触,从而出于政治考虑作了处理,以使其符合通行见解。为不违背通行见解而改动资料这种缘木求鱼的做法,放在现在,无疑属于“篡改”行为;但在当时,党史研究界的原则是学术和研究为政治服务,因而这种行为不过是忠实于原则而已。毋庸讳言,“一大”在当时不是历史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但是,《党史资料》决非一般刊物,而是为“便于党内高级干部研究党史的参考”[4]而仅面向极少数高级干部和专家发行的内部图书。而读不到《共产国际》版的众多学者无疑会认为,该回忆录既然刊载于如此刊物上,必是“第一次大会于7月1日召开”的铁证,甚至连始终坚持“7月1日开幕说”的李达等“一大”直接相关者,其回忆录也难免受到影响⑦。
《党史资料》刊载的经过改动的陈潭秋回忆录(重译本),在党史研究借助改革开放政策而重新起步时,经若干修改后被转录于《百科知识》(1979年第2期)、《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刊,1979年)、《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0年)等书,从而广为人知⑧。只不过,尽管《党史资料》版擅自改动过的日期、人数等在转载过程中得到了恢复和订正,但资料并非陈潭秋原文这一《党史资料》版的最初错误不仅未得到纠正,反被进一步掩盖。例如,《百科知识》在刊载陈潭秋回忆录时,明知是重译自外语版,却加了这样一个编者按:“陈潭秋同志的遗作《回忆党的“一大”》是他在1936年6月7日为纪念党诞生十五周年而写的,曾发表在当时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上”。“6月7日”之说,恐怕不会有任何根据。而“曾发表在当时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上”的解释,本身虽然不错,但《百科知识》转载的是从《共产国际》外文版重译而成;按语等于要读者相信这篇译文就是《共产国际》中文版刊载的汉语原文。
重译的问题并未止于《百科知识》。中共“一大”权威性资料集、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馆资料》(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收录的陈潭秋回忆录,注明“按中央档案刊印”,但其文本与丁文所介绍的翻译手稿(原始文本),即本来为《党史资料》重译的那篇文章完全相同。中央档案馆竟然采用《党史资料》译者重译的译稿,而且还特意注明“按中央档案刊印”,这可能吗?最近,中央档案馆藏陈潭秋回忆录的文本形式被公之于众,也为我们提供了答案。所谓中央档案馆藏陈潭秋回忆录,实际上并非陈潭秋手书汉语文稿,而是俄文打字件,共10页。[5]从陈潭秋运用俄语的能力考虑,该打字件应非出自陈本人之手,而很可能是为了在《共产国际》俄文版刊登而由汉语译成俄文时的译稿。然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却对原件实为俄文只字未提,将其汉语译稿——而且是30年前《党史资料》的译者重译的译稿——原样采用、发表,并堂而皇之地称其为“中央档案”。作为资料集编纂者,这种做法和态度实在缺乏严谨。另外,该资料集编辑经考订称,陈潭秋该文执笔时期应为“1936年6、7月间”,但该书所收李玲论文又作“1936年6月7日为纪念党诞生十五周年写”⑨。“6月7日”之说,恐怕不是依据某件档案资料,而仅是沿袭了上述《百科知识》按语而已。也就是说,这部“中央档案馆编”的资料集,从内容到解说都未做充分的资料调查。⑩
据笔者所知,首次根据《共产国际》中文版重录陈潭秋回忆录的,是1980年刊行的《“一大”前后》(二),距回忆录发表已过去45年之久(11)。但是,严格地说,该书所录也不完整。比如,原文“何叔恒”、“张国涛”分别被订正为“何叔衡”、“张国焘”。此类处理也许出自善意,但论述刘仁静现状部分之“现在在国民党警察所特务机关卖力气”被改为“现在国民党警察所特殊机关卖力气”等,则显然失当。也许这些都是大意而造成的误写、误印,但考虑到陈潭秋回忆录的重要性,总期尽量保持原貌为好。
总之,由于《“一大”前后》大体照录了陈潭秋回忆录的汉语原文,多年来的混乱状态本应就此了结,但实际上各种版本林立、学者引用混乱的状态仍在继续。例如,十年前为纪念中共建党80周年而编的回忆录集《亲历者忆——建党风云》,[6](P21-26)与《“一大”前后》一样采用了《共产国际》中文版;但三年前刊行的有关党的历次大会的大型回忆录集《从一大到十七大》,[7](P35-39)不知何故却采用了重译本(即上述丁文所说翻译手稿原始文本)(12)。更加奇怪的是,去年刊行的《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1921-1949)》(13)竟将问题最多的《党史资料》版原样录入。也就是说,曾将“一大”会期改作“7月初”的那个版本,在未经任何说明的情况下被重新刊印、发行。该资料集编者称,从《党史资料》转载陈潭秋回忆录等9篇文章,也是为了重温前辈编纂《党史资料》等的贡献。[8](P412)然而,如果《党史资料》刊文经得起推敲,此说当然有其道理;但将问题多多的版本再次刊行,却让人难以理解。在这里,我们只有期待建国初期“一大”研究因资料编纂缺陷而陷入长期混乱的状况,不要因为该资料集而重演。
二、葛萨廖夫《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的几个版本
1950年代初刊载于《党史资料》、使“一大”研究陷入混乱的资料,除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外,还有葛萨廖夫著(张诚译,徐永瑛、赵一鹤校)《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1953年第7期)。关于该资料,《党史资料》的编者按如下:
本文原名《中国共产党简史》,写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作者是当时参加中国革命活动的一个外国人。……本文过去有过一种中译本,编在北洋军阀张作霖于1928年出版的所谓《苏联阴谋文证汇编》里,译文非常拙劣,且有歪曲原意处。这次翻译是根据英文本,一些显然误记的事件、年月已经订正,没有史料价值的地方均经删略。
众所周知,1927年4月,张作霖强行搜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没收了大量俄文档案,其主要部分被译为汉语,翌年由京师警察厅出版,此即所谓《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其中一篇就是被归入“中国共产党类”的《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所收文件中,有些确属张作霖政权为反共而捏造,如《致驻华武官训令》等,故利用时须十分谨慎(14);但并非所有文件皆属捏造,其中几件,已在莫斯科的档案馆发现了类似原件。[9]至于《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从内容上基本可以断定并非捏造,而是1920年中期在中共有关人士帮助下撰写的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宝贵资料。按《党史资料》编者按所说,由于《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所收《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在人名推定和译文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于是从英文版另行翻译,此即《党史资料》版。
《党史资料》并未就英文版底本进行说明,但据认为应是1928年初Peking & Tientsin Times(京津泰晤士报)或China Illustrated Review(中华星期画报)所刊载的文章(15)。实际上,还在《党史资料》收入该文之前的1951年,著名史料学家金毓黻就已经在《进步日报》(天津)上发表文章,介绍了他所发现的《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版)(16)。所以,《党史资料》也许是通过金氏获得其英文版,而后将其译为汉语的。只不过,《党史资料》刊载的《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其问题比《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版还要多。
首先是有关原作者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以“葛萨廖夫”为原作者。“葛萨廖夫”极可能是China Illustrated Review以“A Brief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为题刊载时所标注的作者“Kisseleff”的音译;[10]但是,“Kisseleff”却并非原作者,而仅仅是校订者(17)。《党史资料》没有标注“葛萨廖夫”的罗马字音,就断定“作者是当时参加中国革命活动的一个外国人”,从而使所谓“葛萨廖夫”这个外国人所写的资料,带上了某种神秘色彩。
不过,《党史资料》版更大的问题在于内容被随意改动。就上述分析陈潭秋回忆录时已经探讨的“一大”会期、代表人数而言,英文版分别作“1921年5月”、“11人”(《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版分别作“1921年约在5月”、“出席代表计11人”);但《党史资料》版却分别改作“1921年7月”、“参加大会的代表有12个”。这些改动,就是编者按“一些显然误记的事件、年月已经订正”的意思。篡改和随意改动尚不止于此。关于结党时期的活动,原文中1920年初参与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7人的名字、北京小组成员中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和广州小组的陈公博、谭植棠等皆被删除,叙述陈独秀在建党方面作用的部分也被删除。
也就是说,在《党史资料》版《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中,凡是不符合当时中共党史定论的部分,都被改为符合定论;凡是与围绕毛泽东叙述历史这一党史基本框架有所冲突的人物的活动和功绩全部被删除。这份资料,由于至今未发现上述陈潭秋回忆录那样的翻译手稿或编辑删节文本,其编辑过程尚难以了解,但其遭遇恐怕与陈潭秋回忆录类似。
载有《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的《党史资料》的发行范围有多大,不得而知;但是,党史专家因确信其为真实史料而陷入混乱,是不难想象的。而且,由于1979年以后的主要资料集都收入了该文,混乱随之进一步扩大。仅就笔者所知,上述《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册,1979年)、《历史资料选编中国共产党“一大”史料专辑》(1979年)、《共产主义小组和党的“一大”资料汇编》(1979年)、《中共“一大”资料汇编》(1979年)、《“一大”前后(一)》(1980年)等,都根据《党史资料》版收录或节录了“葛萨廖夫”的文章。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中共“一大”资料汇编》对《党史资料》版作了进一步改动,将“一大”开幕日期径直改成了“1921年7月1日”。改动史料使其符合定论这一建国初期以来党史界的作风,在党史研究重新起步的时期仍未消减,近年的《从一大到十七大》(2008年)仍节录了“葛萨廖夫”的文章(略去了有关“一大”的部分)。这期间,有几篇探讨早期中共党史的论文曾引用“葛萨廖夫”文对某些具体史实作了“考证”;但是,如果不能自觉认识到“葛萨廖夫”文曾被整理、编辑,所谓“考证”亦不过沙上楼阁而已。另外,由于“葛萨廖夫”文叙述的时期下限是国民革命(北伐),因此,“一大”以外其他以该文为根据的党史研究,无疑也都值得怀疑。
如此说来,我们从事“一大”研究的学者所能利用的,难道只有稍好于《党史资料》版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版吗?或者只有韦慕庭(Martin Wilbur)费尽周折整理出来的英文版吗?可喜的是,近年有比这份资料更准确的汉语版本可资利用。那就是一直致力于中共党史俄文资料的收集、翻译的马贵凡氏所翻译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述》(18)。
实际上,原苏联学者很早以前就在利用一份与《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十分相近的资料,即加鲁尚茨、科瓦廖夫、卡尔图诺娃等学者引用过的俄语资料《中国共产党小史》(Крaткий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лaртии)。据加鲁尚茨介绍,该文发表在俄语杂志《Кaнтон(广东)》1927年第1期(总第10期)上,原作者为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顾问纳乌莫夫(C.Н.Наумов),笔名使用“卡拉乔夫”(Калачев)(19)。早有学者推断,俄文版《中国共产党小史》很可能就是《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版、《党史资料》版的底本;而马贵凡氏将卡拉乔夫《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述》全文译出,则证实了这种推断是正确的。据马贵凡氏转述加鲁尚茨的介绍说,纳乌莫夫(1899-1966)曾这样谈到该文的执笔过程:
当年苏联驻北京全权代表Л.C.加拉罕曾请求在广州的鲍罗廷为他起草一篇介绍中共历史的简要概述。鲍罗廷遂委托纳乌莫夫来完成这项任务,同时请张太雷给以协助,为他提供材料和建议。纳乌莫夫是在1926年秋同张太雷一起乘火车由广州去北京的途中写完这篇概述的。
如果该说明无误,那么,为纳乌莫夫执笔提供帮助的就是张太雷;换言之,文章利用了张太雷提供的资料,反映了张太雷的认识和见解。到底是否如此,当然还需进一步探究(21);但毫无疑问的是,马贵凡译《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述》必将取代此前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版和《党史资料》版(当然应与韦慕庭整理的英文版相互比对)。而葛萨廖夫著、张诚译文本,尽管对于探讨共和国时期党史研究的不正常状态仍然有其价值,但研究早期党史,则不宜继续使用。
顺言之,属于纳乌莫夫执笔文本系统的资料还有一件,即《上海革命史资料研究》(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编,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出版)所收录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策略(讨论大纲)》。该文著者不详,系“1927年1月4日社会科学研究会编印的供党员内部学习的一份读物。原件系手刻蜡纸油印,现藏中国革命博物馆”(同书第312页)。该资料叙述的是早期中共的活动,较之纳乌莫夫执笔文本,尽管细节不同,但“一大”代表数也作11人,而且成立时期十分接近,故二者之间应存在某种关联。
与中共有关的内外人士撰述的早期党史,对后来1920年代至1930年代形成的党史以及有关人的回忆、信息积累等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22)。正因如此,在利用1927年以后产生的有关早期党史的回忆录、记录时,不应将其作为原始材料,而应与上述早期党史著作相互比对,并慎重考虑其产生过程。在下一节里,我们将从史料学角度,对形成于1929年底的另一份资料进行探讨。
三、《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与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
《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1929年12月31日)》,是何叔衡就中共“一大”某些细节询问董必武而得到的回信(23)。该信因产生于同为“一大”代表的董、何二人之间,于是作为“一大”的早期记录(回忆)而成为“一大”研究经常利用的资料。不过,该信尽管日期已经判明,但写于何地、经过如何却并不明确;而且何叔衡致董必武信至今未能发现,因而利用起来困难较大。回信中有关信件往来的部分如下:
叔衡同志:
二十六日的信,今日午后接到一张欠资的通知后,才往邮局去取来,照你所约“五日”之期已赶不及了,幸而有张同志之便,免得又经邮局周转,耽搁时日。不过关于第一次中共代表大会,我已记不甚清,只尽可能的写出来,供你们的参考。……以上是我所能记着的。国焘同志还能记得许多,请问问他,当更知道详细点。……弟 必武 十二月卅一日
关于这封回信,冯铁金氏在2006年发表了值得关注的见解。[11]冯氏把这件资料与近年发现的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24)(时间不早于1929年,以下简称《讲稿》)联起来考虑,并对回信背景——何叔衡为何向董必武询问“一大”情形——作了如下解读:
何叔衡1929年12月26日给董必武写信,是缘于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两次听了张国焘关于建党初期情况的讲课后而写的。……听完第二次讲课后,或许是为了解一大的更多情况,他便在1929年12月26日给董必武写了一信,询问一大的有关情况。
冯氏的可贵之处在于重视史料的形成过程;而就整体框架而言,其考证也颇具说服力——交换信件的何与董当时都在莫斯科、董委托代转回信的“张同志”即张国焘、信件往来与《讲稿》有关等。但可惜的是,“听了张国焘关于建党初期情况的讲课后而写”这一部分还有再作商榷的余地。也就是说,如果何向董询问“一大”情况是在张国焘讲课之后,董回信中“照你所约‘五日’之期已赶不及了”一句所表露出的急迫感就难以理解。何叔衡为何要求董从速回信呢?最自然的解释应是:为赶在张国焘讲课开始前得到答复。董回信中称“幸而有张同志之便”,由此可知回信是让张国焘捎给何叔衡的。个中情由可能是这样的,即张国焘因迟迟不见何叔衡带来答复而直接去找了董必武——如此则一切都可得到解释(25)。也就是说,必须讲中共党史课的张国焘向何叔衡询问,或者要求何叔衡向董必武询问“一大”有关情形,于是才有了何、董之间的信件往来。由此亦可推断,张国焘《讲稿》的产生、尤其是论述中共“一大”的第二次讲课,应在《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之后,亦即从董、何等“一大”参与者处确认了相关情况之后。具体而言,应在1930年初。
张国焘《讲稿》,除董、何提供的信息外,很可能还参考了上述纳乌莫夫的文章。因为,《讲稿》有关“一大”前北京小组的部分记述——“一共有八人”,其中有六名无政府主义者——与纳乌莫夫文一致。当然,张国焘也是北京小组成员之一,即使不借助纳乌莫夫文,也能忆得起这些情况(26)。另外,《讲稿》以“一大”时党员数为57人,显系承袭了中共六大(1928年)时编订的《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份比例表》[12]的数字。据认为,该统计表应是为参加六大而集合到莫斯科的党员们,就自己出席过的历次大会共同汇总情况而成。而既参加过“一大”、也出席了“六大”的,只有张国焘和何叔衡二人,因此,“57人”这一数字有可能原本就是该二人提出的。
在把握以上背景的基础上,再次面对张国焘《讲稿》时,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讲稿》所列“一大”代表名单中为何没有何叔衡的名字。《讲稿》说,“当时到上海开会的有11名代表。上海是李汉俊、李达,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武汉是董必武、陈潭秋,湖南是毛泽东,广东是陈公博、包惠僧,山东是王尽美、邓恩铭,日本是周佛海(似乎止11个表决权)”,没有提到何叔衡。而如下两个事实表明,这并非记述错误。一、《讲稿》手稿相关部分作“湖南是毛泽东□□,广东是……”即“毛泽东”后留有约两字空白,透露出张对是否应在“毛泽东”后加上“何叔衡”,直至最后犹豫未决;二、张国焘与何叔衡都可能参与汇总的上述六大统计表,也以“一大”代表为11人,其中并没有何叔衡的名字(27)。
自张国焘在1970年代出版其回忆录《我的回忆》之后,人们对其“何叔衡未出席一大说”作过各种探讨。此前的主流见解认为这是“大叛徒”张国焘的又一个谎言。但是,如果张国焘在还是中共领导人时就持同样看法,则将其一概斥为反共人士的诽谤就十分勉强。事实上,上述冯铁金氏后来就引用《讲稿》等大量有关资料,主张《我的回忆》的说法并非凭空捏造(28)。冯氏对所引有关资料的解释不无问题,但如下两点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一、何叔衡不待“一大”结束就回了湖南(29);二、至少在张国焘看来,从他还是中共党员直至脱党之后,何叔衡从来就不是“一大”代表。更何况,张在知道了董、何间信件往来及其内容(董必武在回信中称何为代表之一)之后,仍在《讲稿》中去掉了何叔衡的名字,表明张国焘对这一点是坚信不疑的。
关于“一大”代表,人数暂当别论,至于到底哪些人出席了会议,现状是仍只有依靠回忆录来决定(30)。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张国焘履历有何污点,他一贯不承认何叔衡为“一大”代表的立场,是应该得到尊重的。
众所周知,顾颉刚先生曾指出,中国古代传说带有层积性——即资料越新,后世附加上去的东西越多——从而为中国古代史研究开辟了新天地(所谓“层累造成说”)。这种史料的层累现象,决非只限于古代史,现代史领域也同样存在。“一大”代表的回忆录,包括张国焘的有关撰述,无一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参考了已有资料而成,我们对此似乎过于漫不经心(31)。而对史料层累性因主观性资料改动而愈加错综复杂,我们又关注过多少?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此前被视作原始史料或早期回忆录的资料,实际上只是各种信息的复合体、堆积物;正因如此,“一大”研究不应回避脚踏实地的努力,以细致梳理错综复杂的史料生成过程。这应是以重返史料生成现场为前提的历史学、史料学的基本立场。中共党史要摆脱特殊学术领域、跨入真正历史学领域,则中共的出发点“一大”的研究应该迈出第一步。而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共和国时期包括“一大”研究在内的党史研究、党史资料编纂的进程作全面探讨。
注释:
①俄文版为Чен Пан-цю[Чень Тань-цю],Boспоминания о I съеэде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Коммyнистичеc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1936,№14,cтр.96-99.德文版为Тschеn Pan-tsiu[Chen Тanqiu],Erinnerungen an den I.Parteitag der KP Chinas,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1936,Heft 9.S.900-904.英文版为Chen Pan-tsu[Chen Tanqiu],Reminiscences of the First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1936,no.14,pp.1363-1366.另,据说巴黎出版的《全民月刊》(第1卷7/8期合刊,1936年)也曾转载陈潭秋回忆录,笔者未见(参见陈乃宣《陈潭秋》,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2-203页)。
②受陈潭秋回忆录影响而写出的第一篇有关中共“一大”的文章,很可能是萧三《对〈毛泽东故事选〉的几点重要更正》(《北方文化》,第1卷第6期,1946年5月)。该文对两年前发表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解放日报》,1944年7月1-2日)一文作了订正,就“一大”代表宿舍(上海法租界蒲柏路一个女子学校)、租界警察搜查会场(第四天晚上)作了补充;而这些也都是陈潭秋回忆录中的内容。就此推断,萧三很可能在1946年初读到了陈潭秋回忆录,并且很可能是《共产国际》俄文版。只不过,萧三的这篇订正文对陈潭秋回忆录只字未提。
③至1955年,《党史资料》共刊行24辑。第1辑未注明发行日期(编后记日期为1951年10月30日),但合订本第1辑作“1952年第1辑”,即作1952年创刊。另,该杂志编辑据说是缪楚黄(参见李海文主编《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第2编,四川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12页)。
④丁氏据该翻译手稿收藏者介绍说,翻译手稿已于2009年北京某收藏拍卖会上被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以2万多元购得。
⑤据邵维正氏的记忆,陈潭秋的文献是“由几个懂俄语的青年人从俄文翻译过来的”。参见:丁晓平《陈潭秋与其珍贵的〈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党史博览》2010年第7期。
⑥当时最具权威的党史著作即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1951年)有关“一大”这样记述说:“1921年7月1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举了十二个代表,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有关“一大”的通行见解的变化,请参阅前引拙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255-264页。
⑦直到逝世前,李达一直坚称大会是7月1日开幕。1959年中央档案馆向他求证时,他也回答:“一大开会的具体时间,是七月一日”(《给中央档案馆的一封信(1959年9月)》,《李达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21页)。另,《党史资料》第1辑载有李达《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回忆》,他读过《党史资料》是没有疑问的。
⑧在笔者手头的资料集中,《历史资料选编中国共产党“一大”史料专辑》(重庆市历史学会编刊,1979年)、《共产主义小组和党的“一大”资料汇编》(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资料室编刊,1979年)、《中共“一大”资料汇编》(西安师专马列主义教研室党史组、西北大学政治理论系党史教研室编刊,1979年)等都收录了基于《党史资料》版的重译本。
⑨李玲《〈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本的来源和初步考证》,《党史研究》,1980年第3期;后收于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决定在各语种《共产国际》上发表三、四篇文章,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是在6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的决定(1936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370号文件);陈潭秋回忆录应作于该决定之后。而陈曾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上作过演讲(《陈潭秋在庆祝党的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提纲)[原文没有时间]》,《中共党史资料》第3期,1982年),回忆录很可能写于此次演讲前后。那么,那次纪念活动(第一次建党纪念活动)是何时举行的?《中共党史资料》编者称,“纪念会的时间,据判断,当在7月31日或8月7日前后”,而对《提纲》标注了1936年7月的日期。但6月23日的书记处决定纪念活动在8月7日举行,因此,陈潭秋回忆录应写于6月底至8月上旬之间。关于发表时间,《共产国际》中文版1936年第4/5期合刊没有标注出版日期,转载回忆录的俄文版则注明1936年8月发行。但实际上,二者似乎都发行于9月以后。因为,该期《共产国际》刊载的季米特洛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写于同年8月31日(《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5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该书第二版也从《共产国际》中文版1936年第4/5期合刊转录了陈潭秋回忆录。另,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部会编《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第1卷(东京:劲草书房,1970年)收录了依据《共产国际》中文版翻译的陈潭秋回忆录。
(12)对照已刊行各版本可知,其所转载的应是前引《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册)载重译版。但对原文“广东代表鲍怀琛”一句却加上了“(此处应为陈公博——编者注)”的错误注释(第35页,应为包惠僧),从而使读者陷入更大混乱。
(13)李海文主编《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1921-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0年。该书原为2005年刊行的同名书,2010年作为“人民·联盟文库”之一再次发行。
(14)参见习五一《苏联“阴谋”文证〈致驻华武官训令〉辨伪》,《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习五一《查抄苏联大使馆内幕》,《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2期。
(15)这些英文版,C.Martin Wilbur(韦慕庭)曾以A Brief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为题作过介绍(Wilbur and How,Documents on Communism,Nationalism,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1918-1927:Papers Seized in the 1927 Peking Raid,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6,pp.41-78),而关于1927-1928年前后所没收档案的各种英文版本,该书pp.566-567解说述之颇详。A Brief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一文后被收入Wilbur and How,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1920-1927,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本文所参照英文版即为此文。另,陈公博在《苦笑录》中曾说:“恰好那时在上海的英国别发书庄出版了一本英文书,那是张作霖在北京围抄俄国大使馆,没收许多共产党的秘密文件,翻译成英文发刊,作为反对国民革命军的一种宣传”,认为“别发书庄”即上海的英文出版社Kelly & Walsh 出版过没收档案的英文版。实际上,别发书庄在1927-1928年前后出版的是张作霖的传记Putnam Weal[本名Bertram Lenox Simpson],Chang Tso-Lin's Struggle Against the Communist Menace(张作霖反对共产主义威胁的斗争),Shang hai:Kelly & Walsh,Ltd.1927,并无任何证据显示该社出版过没收档案;陈公博之说应为记忆错误。
(16)金毓黻《二十四年前的一篇中国共产党简史》,《进步日报》,1951年8月10日。金毓黻早在《关于整理近代史料的几个问题》(《新建设》第3卷第2期,1950年11月)一文中表示将编纂近现代史(革命史)史料:“一谈到革命史料就与反革命史料有了关联,二者是密结在一起,而无法分开的,我们就依据这样的原则来整理这几段的史料”。另,叶永烈《红色的起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称:“1950年,中国的中共党史专家发现了一篇苏联人葛萨廖夫写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么一篇历史文献,竟是从一部蓝色封皮、线装的书中发现的。那部书的书名颇为惊人:《苏联阴谋文证集汇编》!”(第25页),明确了重新发现汉语版的时期;但没有提及英文版是如何被重新发现的。
(17)前引Wilbur and How,Documents on Communism,Nationalism,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1918-1927,p.490.《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版《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未标注作者。另,战前日本的中共党史学者大塚令三《中国共产党年志稿》(《满铁支那月志》第12卷第12期,1932年)亦称“原文为キセルエフ[Kisseleff]以俄文写就”。可见,只要利用英文版,误认Kisseleff为原著者是难以避免的。
(18)马贵凡译《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述(卡拉乔夫同志在中国研究组会议上作的报告)》,《中共党史资料》第81辑,2002年。译自原苏联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1968年出版的《信息通报与学术报告[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е сообщения и нaучные доклaды]》第6期。
(19)参见:Гарушянц,Ьорьба Китайскиx Марксистов за создани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Народы Аэии и Африки",1961,№3(加鲁尚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亚非人民》);Ковалев и Картунова,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о первом сьезд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Aфрики",1972,№6.(科瓦廖夫、卡尔图诺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新资料》,《亚非人民》)。
(20)参见:蜂屋亮子《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の重译と、大会会期和代表についての论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的重译与对大会会期和代表的考证]》,《お茶の水史学[御茶之水史学]》第31号,1988年;前引Wilbur and How,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pp.442-444;李丹阳、刘建一《“革命局”辨析》,《史学集刊》,2004年第3期;石川祯浩《中共“二大”与中共党史研究史》,《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5辑,2005年(原载[日]《东洋史研究》第63卷第1期,2004年)。
(21)李丹阳氏指出,《中国共产党简史》与张太雷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1年)对“一大”前地方组织的介绍并不一致,认为“张可能不是《中共简史》资料的主要提供者”。这个观点不可忽视。李丹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起源》,《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22)如Ju An-li,Die Кommunistisсhe Internationale und die Entstehung der kommunistisсhen Partei Chinas,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1929,No.9-11,S.656-664(俞安礼[音译]《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共产国际》德文版)、瞿秋白《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1929年底或1930年初,《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都参照了某种早期党史著作。
(23)最早提到该信的应是前引李玲《〈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本的来源和初步考证》。后来,《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3期刊载了该信全文,随后,《中共党史资料》第3辑(1982年)、前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1982年)、《“一大”前后(三)》(1984年)等相继予以全文收录。另,《中共“一大”南湖会议》(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年)附有该信照片。
(24)[俄]舍维廖夫(К.B.Шевелев)提供《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百年潮》,2002年第2期。《讲稿》的具体写作时间不详,据舍维廖夫称:“讲稿写在1929年印制的笔记本上”。据此推断,《讲稿》的执笔时间不早于1929年。
(25)董必武回信称“供你们的参考”,所谓“你们”应指何、张二人。
(26)或许,为纳乌莫夫提供相关资料的不是张太雷(参照第9页的注释),而是张国焘。
(27)前引赵朴《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一)》称,代表作11人,但名单仅载10人姓名(张国焘、刘仁镜[静]、董必武、包惠僧、李达、李汉俊、毛泽东、周佛海、王烬美、陈公博),即没有何叔衡、陈潭秋、邓恩铭的名字。后来的《讲稿》补上了陈潭秋、邓恩铭,唯独何叔衡未得补入。可见,张国焘是坚信何叔衡不是“一大”代表的。
(28)冯铁金《何叔衡是“一大”代表,但未出席“一大”——兼论出席“一大”的代表是12人,不是13人》,《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7辑,2007年;冯铁金《关于何叔衡未出席“一大”考证续补》,《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8辑,2008年。也有人不同意冯氏见解,如唐振南《何叔衡出席了中共“一大”——答冯先生的来信》,《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9辑,2009年。
(29)冯氏的根据是,《谢觉哉日记》1921年6月30日条(记述8月12、15、18日事)记载“而叔衡又迭缄相促,乃于阴历七月十五[阳历8月17日]往省”(《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0页)。另,前引唐振南《何叔衡出席了中共“一大”——答冯先生的来信》就冯氏对资料的解读及其观点提出异议,但对何叔衡在“一大”结束前就离开了上海的看法表示同意。
(30)到底哪些人是中共“一大”正式代表之所以不易确定,其主要原因在于,尽管各种回忆录出现了13人的名字,但当时记述大会概要的俄文资料(《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556-559页)却称“参加大会的有12名代表”。
(31)顺言之,写于1936年的陈潭秋回忆录,似乎也在几个方面参考了《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