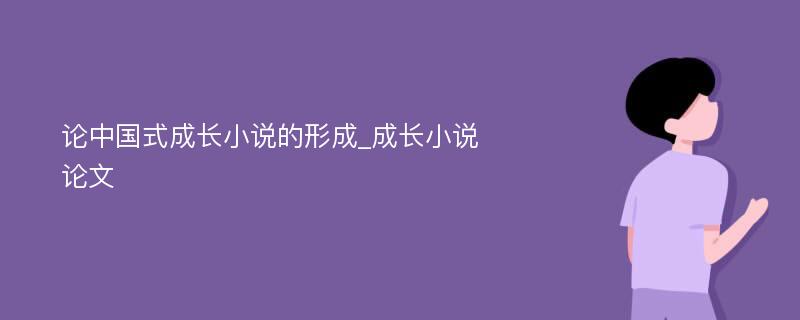
论中国式的成长小说的生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0257-5876(2006)11-0004-08
成长小说,虽然曾经得到过巴赫金等人的已成经典的解说,但从字面上看,似乎无须过度诠释,顾名思义,它就是叙写成长的小说,即记述人物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身心所经历和遭遇的小说。把成长小说理论进行固化的原教旨式的理解,反而容易导致更为严重的格式化和俗套化,从而影响我们对这一类小说的多种可能性的衡估和开掘。如果按照西方评论家所给定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巨人传》、《痴儿历险记》甚至《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等标本来衡估这一类创作的话,成长的完整性和“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亦即“不得不成长为”“新人”① 的概念就很容易束缚成长小说新的文学视界的拓展。即便遵照巴赫金所归纳的五类成长小说——纯粹的循环型成长小说、与年龄保持着联系的循环型成长小说、传记型小说、训谕教育小说、现实主义的成长小说——也很难在中国语境中找到完美贴合的例子,如果非要死抱着权威观点不放,我们的研究与评论就有可能丧失对于文学现场的有机的鲜活的创造性参与功能。
因此,在参照国外理论的同时,对于中国式的关于“成长”的文学反应,对于中国式的成长小说的源流与现状,我们理应有自己的探析和评说。
在生活中人们习惯性的理解里,“成长”一词,伴随着从童真到青春的“常态”,往往意味着“天天向上”并“欣欣向荣”的过程,是人从小开始,身体和心智的慢慢健全,直至长大成人,显然这里不仅是生活伦理的积习成德,还含有习以为常的“正确理解”。但是,在这常态背后,一般都隐藏着过来人观察、欣赏和审视下一代的眼睛,蕴含着溺爱、嗔怪、期盼和自得的情感因素,终究是一种成人对未成年人的照耀。这犹如身高所带来的视角的高低,客观上造成的效果是:对成长主体来说,成长,更多的是被看管的价值外在的体验,没有多少“主语感觉”,是为满足社会的普遍要求或者家长的规约,最符合日常生活伦理意愿的尺度就是“我成长,但是长成你们希望的样子”,向着给定的榜样仰视着成长,于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跟巴赫金所说的“不得不成长为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相比,这就不仅仅具备了被动性的前提,更显现出了只要成长就必须要遭受公共模塑的境遇。
而文学,在观照这一现象的时候,却总是从变量甚至是从非常态的背景和经历切入成长,首先就要试图找回个性,执拗于“我成长”。在我们所能想起的成长小说中,那些被给定的价值,几乎成为成长叙事中或者被尽量掩饰和羞于表达的东西,或者被作为对立面而尽力要抛却的负担,甚至构成成长主体逆反式自我塑造的动力。那些形象总是从反叛开始,动作性很强,再经历挫折和痛定思痛,由精神的不羁到沧桑历尽而正视生活的教训,无论后来走向精神的强大自足还是归于妥协,小说的基本架构总是成长主体与外在影响相互较量的挣扎史,往往落归于某种群体信念或者集群生计,最终仍是回到被感召、被照耀的轨道。
中国式的成长小说,它所涵盖的成长过程具有特殊性。有两种现象值得我们玩味也堪可思量:一是,在生命起点上与西方没有太大差别,而在终点上则极其模糊,有着明显的“成长期延长”的特色,西方在年龄上传统的“成人”仪式完成之际,我们的个性成长可能刚刚开始,我们拥有相对晚熟的成长,似乎青春期没完没了,这一点,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已有一些带有“晚熟的成长”性质的经典性作品;二是,无数的作品可以作证,在20世纪的前八十余年漫长的小说史中,中国式的成长故事、记忆和想象呈现出驼峰状,在童年和少年之间曾有一个丰饶地带,青年时期则又是一个高耸的山陵,少年至青年的成长形象虽然大量充斥,但概念化、平面化作品居多,到了近二十年,我们的成长小说则在这一薄弱区域出现了疯长、隆起、文学品质远远高过两头的势态,盛大狂欢之景至今不见消遁迹象,成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佳作最集中的领域,甚至可以看作近二十年来中国小说最为壮观的制高点之一。
在笔者看来,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在80年代中期之前的成长小说,基本上是从非常态的历史思潮背景中汲取个性成长的力量,“幻灭”——“动摇”——“追求”的历程清晰可辨,并逐渐显现新的人生观、世界观,从热情过剩的忧郁、彷徨到热烈有余的抉择、歌唱,充盈了成长的“现代性”。正是这种成长小说,一方面使得“个人性”与“历史”通过主人公的成长达成了既对抗又共生的结构关系,另一方面更让“成长史”成为社会变革史或者说“历史大事年表”的文学注解。但是,其细微之处仍然布满了成长的纹路。
事实上欧美的成长小说,也经历了从“完型”的成长小说到“在路上”(“成长中”和“成长状态”)的转型过程。在中文版西方理论家的著述里,我们可以找到弗朗西斯·约斯特、艾布拉姆斯、巴赫金等人关于“成长小说”的诠释,以及国内对此素有研究的专家的界定②,无论表述上叫它“教育小说”、“修养小说”还是“发展小说”、“塑造小说”等等,其理论上有较为系统化的趋向。其过程则已经绵延了三个多世纪。
中国的成长小说其实也经历了并不短的创作历史,如果从《西游记》算起,则比西方还早两个世纪。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把《西游记》读作成长小说。更有许多令人佩服的聪敏读者已经感觉到了其中的成长况味。笔者见过一篇趣文,作者把《西游记》完全读成了“青春成长”作品,头头是道地从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的成长中分别读出了前青春期的英雄主义、青春期的个人享乐主义、后青春期的自我修炼③;甚至有一篇颇有影响的网络文章认为:“孙悟空,显然是一个民间精英成长的典型版本。”④ 这显然是从“教育小说”的维度所进行的理解。但是,《西游记》的成长小说价值应在它的背面:从美猴王到齐天大圣再到孙行者直至斗战胜佛,他的精英之路是逐渐消匿天真快乐的猴性(童真)的过程,取经之路上数度被肉眼凡胎的唐僧驱逐,其内心的煎熬、瞬间的迷乱便是成长小说的最为动人之处,每当孙悟空变成了一个爱哭的孩子,都是在向成长的原发地进行渐行渐远的苦涩的诀别。自由纯真,这个至美的性情,因为可爱的虚荣好胜心的引诱而落入劫数,最终被当作了妖怪,被天神排压、被佛界和师傅的咒语惩罚直至根除,七十二变的自由完全成了抗过八十一难的工具。他被管束着的成人仪式终止于“成佛”。终成正果的故事是完全可以反过来读的,是内在个性的被迫妥协史加上天性之火的自我扑灭史。正如笔者所看到的关于《西游记》一篇短文所透视的——“有一种成长叫‘悟空’”⑤。孙悟空的成长之路和成长代价亦完全可以作为一代代青少年成长的隐喻。如果说我们非要找到一部中国成长小说完成版杰作的话,那么,《西游记》是再合适不过了。哪怕是按照西方成长小说的套式,无须管它是中国还是外国,无论是从成书年代看还是从成长的复杂性、深刻性以及内容与形式的整体统一来说,《西游记》都应该是此项的首选。
《西游记》式的上天入地的宏大成长小说独一无二,到了现代,中国成长小说已经完全着陆行走。现代白话文起步阶段的以女性作家为主体的“问题小说”和以渴望自由尊严为名以宣泄本能为实展现青春困境的“零余者”小说,都有成长小说的质素(两者合一,再加上30年代的“海派”风情,不禁令人联想到90年代中后期“70后”作者的部分作品,比如卫慧的《蝴蝶的尖叫》、《像卫慧那样疯狂》、《黑夜温柔》)。那时候除却先入为主的观念过强的《少年漂泊者》等“革命文学”,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应该是茅盾的早期作品《蚀》三部曲。
在动荡的历史变革中,青年难以自持的身心成长的反应被作家机敏而理性地把捉到作品之中,一代青年知识者的悲哀成长被活化在被给定的成长历程里。“(1)革命前夕的亢昂兴奋和革命既到面前时的幻灭;(2)革命斗争剧烈时的动摇;(3)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⑥ 茅盾用三部中篇连缀起来的这部长篇作品,分别指向浪漫理想的碰壁与破碎、意志的薄弱与情欲的诱惑、幻灭真正到来的精神的空虚绝望甚至堕落,追求的警醒其实已经被悲观的情绪埋葬。它所涵盖的现代青年三个时期的内心与行动世界,不是简单的单元故事,而是成长的旅程。在人物和架构上对现代成长小说的艺术摸索,给后人提供了许多新的经验。第一部《幻灭》和第二部《动摇》,主人公分别只有一两个,而第三部《追求》则以四个青年知识者的成长作为观照对象,突出了成长群体的软弱特质。对这一群体的带有些许自然主义倾向的理解、对女性心理和欲望的出色把握,还有对成长矛盾性的难得的感性体悟,与其后期作品相比,作者对“小资情调”的痛挽之心相当真切,具有珍贵的感同身受的成长抒情气息。章静、方罗兰与孙舞阳以及章秋柳、王仲昭、史循、张曼青,就是现当代中国成长小说中常见的因冲动和情欲而事业与理想落空、因敏感而憔悴的“无力青年”形象的鼻祖。这些人物的“怀疑主义”精神气质,几乎可以视做梦魇一样的“时代病”,用史循的话说,就是“在怀疑者看来,都不过是怀疑罢了”。
像茅盾这样,对巨型历史阶段或事件的依凭,导致了成长小说主人公的大龄化,同时“小资情调”与革命的既矛盾又共谋也成了成长小说的母题。一直到《青春之歌》,这种倾向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前者依凭“大革命”,后者依凭“九·一八”和“一二·九”。如果把《蚀》和《青春之歌》连起来阅读,我们会发现“成长”和“革命进步”关系得到“修正”的痕迹。1958年初版的《青春之歌》在整体上祛除了《蚀》那种极度压抑和悲观的情绪,但是伴随革命道路的找寻,其积极、执著、坚定的革命情绪内里其实仍是浪漫天真的情调,只不过前者是面对黑暗和失败的挽歌,而后者是走向光明和胜利的颂歌。一个是下落式的飞蛾扑火的毁灭式成长,一个是上升式的追赶太阳的新生式的成长。而《青春之歌》这一“符合历史逻辑”的成长是以对小说的不断的修改来完成青年的“正确”成长道路的⑦。同是“晚熟成长”的革命成长小说,在意识形态有所调整后的80年代,韦君宜的《露莎的路》主人公的个性反思则可以与《青春之歌》主人公的自得欢欣形成了十足的对照。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时期,另一部著名的成长小说是王蒙的《青春万岁》,那时候,对王蒙这样的年轻人来说,似乎“祛小资化”已经不成为问题,但是,这部小说里面雪藏了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没落小资男人,是主人公杨蔷云的女同学苏宁的哥哥苏君,一个在类似于同期的俄罗斯文学作品里时而闪现但挥之不去的病态男人形象,正是他的存在,使得这部看似透明的高歌新社会新生活的成长小说残留着耐人寻味的时光与历史的复杂影像,并使作品不能轻易被文学史所淘汰。
当代文学中这些以“青春”命名的小说中的“青春”含义,仔细品来,并不简单,因为它不仅是飞跑和溜冰,更是有所停顿有所回溯的左顾右盼的“成长”,“所有的日子”里必要包含健康少女的欢乐也要悄悄收藏病态青年的伤怀。
如上所述,成长的抒情曾经走了由阴云遮月到阳光流淌的两极,在这中间地带,恰是被成长小说长期忽略的视域。90年代,曹文轩以《草房子》为代表的多部成长小说可谓填补了这中间温凉可感明暗可鉴的空白。甜蜜的回忆意味着忆者的感伤,它使文本充盈着美感、谐趣,其实更体现出了成年作者的现实态度。美与深刻的伴生,导致感人肺腑的成长小说的出现。“少年之美”与“落日故人情”的结合,适当的安慰、适量的暴力在苏北乡村背景下为少年成长提供了田野撒欢和草垛迷藏,重拾童真与童真中的恶作剧并行不悖,成长小说中的稀缺的“诗性”已经确凿地嵌入了文学的体内。
这一时期的成长小说可谓繁花错彩,对成长的不同的个性体验和想象,丰富了中国式的成长小说的内蕴,呈现出对成长本身的情味的各种表现取向。70年代的生活带来的成长记忆形成了创作的富矿。
同是在苏北地域的成长形象,程青的长篇小说《十周岁》里的唐冬青和《草房子》里的桑桑的成长有着质的差别。桑桑的成长给人体温一样的“暖”,唐冬青的成长则是湿冷冬夜般的“寒”。孤独、无助,小小年纪的天真纯然的女孩子,过早在家庭的裂痕、人群的异样中冒着寒气,生活给成长设置了苍凉的暗角,她本能地寻找“暖”之所在,在变态的情境中,她找到了变态的取暖方式,成了最动情地表演“诉苦”的主角,成了受人关注但根本谈不上关照的明星。她似乎找到了乐,但那却是更深的苦,她所诉的苦不是她自己的,她把别人的和自己幼小的心志能够想象的苦都收拢在自己那里,痛快淋漓的释放同时也就是不断累加的储存。这一切是她所经受的身心蹂躏的逆反式的强烈反应,却丝毫不能解决或者减轻她的苦痛与所受到的伤害。一个不可能单一呈现的成长小说时代,人生、命运的多层面展开,是文学繁富之景的征象。
这一时期的成长小说佳作如王朔的《动物凶猛》、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苏童的“少年血”系列小说已被一些专门研究者作了细致的评析⑧,除了以上作品而外,笔者认为,能够体现近二十年成长小说成就的作品至少还有:迟子建早期的“北极村”系列作品,洪峰的《离乡》,述平的《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摄于一九七六》,左建明的《欢乐时光》,叶弥的《成长如蜕》与《美哉少年》,王彪的《成长仪式》,潘向黎的《十年杯》,李洱的《遗忘》,金仁顺的《五月六日》和《恰同学少年》,卫慧的《艾夏》、《神采飞扬》,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和《玻璃虫》,东西的《耳光响亮》,李冯的《碎爸爸》,魏微的《流年》、《化妆》和《异乡》,叶兆言的《没有玻璃的花房》,裘山山的《少女七一在1973》、《你坐渡船去干什么》,荆歌的《鸟巢》,毕飞宇的《枸杞子》、《雨天的棉花糖》、《怀念妹妹小青》、《玉米》、《玉秀》、《玉秧》,艾伟的《少年杨淇佩着刀》、《乡村电影》、《穿过长长的走廊》、《去上海》,黄蓓佳的《没有名字的身体》,王刚的《英格力士》,李傻傻的《红X》,何大草的《刀子和刀子》,杨怡芬的《含糊道》,巴桥的《姐姐》、《阿瑶》,盛可以的《北妹》,黄咏梅的《骑楼》、《一本正经》,刘玉栋的《我们分到了土地》、《八九点钟的太阳》,蒋韵的《隐秘盛开》,瓦当的《漫漫无声》,徐则臣的《啊,北京》,李铁的《冰雪荔枝》,朱辉的《牛角梳》,老了的《动物学》等等。
跟以往依傍重大历史事件和流程的成长小说不同,80年代中期之后的成长小说,则更愿意将历史和现实还原为日常生活流程。成长过程较为完整的作品,趋向于一个自足自认的世界,童年少年时期,有着较为充分的自我游戏、记忆和见识,到了青年时期,便从认死理钻牛角尖的倔强、用力挣脱的焦虑归为不甘的无奈、言和。
成长的来路,一条指向70年代,一条指向现实。更具体的背景还是日常生活。
70年代是近些年来成长小说一个典型的历史背景,但作家们并没有将这样的年代“事件化”,这一段在动乱时期相对平稳无序的时间,几乎使青少年们找到了自由冲动的借口。
《美哉少年》、《流年》、《没有名字的身体》主要并不展现冲突,而是呈现“出走”、“观感”、“寻觅”等意绪。《美哉少年》的小小的男主人公有个耐人寻味的名字——李不安,他不满足于静态的生活,在外面做了流浪儿,收获了奇遇、伤感和空虚并终归回家;《流年》在左邻右舍和静物面前永远都是充满善解,对流逝的时间出奇敏感,爱着更痛惜着时光所带走和催生的一切;《没有名字的身体》明显具有相对完整的“成长史”的形态,可是,爱情所连带的残缺与焦渴令主人公内心伤痛累累,即便身体已经成人,但身体无以名状,成长仍未完成。
如果说这些女作家的作品主要是写童真的可爱、温情的心思和对所爱的谅解,多数男作家的成长小说动作性要明显增强。动心思与动手动脚,也给成长小说写作带上了某种性别差异。前者往往对生活和情感是一种和解的态度和怀念的亲切,后者则是在回望中多多少少怀有惊悚和后怕。
苏童的《刺青时代》,成长中的孩子的以占山为王的兴奋贯通全篇,他们的行为是对大人和古人的戏仿,但是饱含着游戏天性,他们有自己的酷烈世界。王彪的《成长仪式》是通过青春期本能的宣泄和对成人生活的偷窥来印证成长的,三个伙伴之间诡异的较量使这篇小说布满了对成长友情的怀疑。叶兆言的《没有玻璃的花房》是继《动物凶猛》后,更为成熟地描摹“文革”后期少年浪荡生活的成长小说。“老气横秋”,这个成语多次出现在对这群“坏孩子”的神情和心理的状态描写中,童真被成熟的伪装所遮蔽,他们自觉地加入成人道貌岸然的斗争游戏,过早地品尝成人不可告人的性爱禁果,欢天喜地地放逐于成人自顾不暇的境地,“坏孩子”的“成长”被时代催生加速,节节胜利,屡屡得逞,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战无不胜。一旦这些已经成为自我的经历和成人世界的重复,他们就无比快捷地老练沉着起来,百无聊赖的小无赖们既被成人利用,也顺便找到了窥探隐秘并刺激自己“活力”的理由。壮观而混乱的红卫兵武斗,触目惊心的邻里打骂,各色人等的欲望追逐,穷富尊卑的瞬间变换,见多了,除了“老气横秋”还会怎样呢?在这样的少年人群之中,“我”多于他人的记忆是身边“反革命分子”的被处决、父子二人共与一个女人的非正当关系以及“唯一的好孩子”无辜的替罪惨死,所以,他是这部成长小说里真正在成长的主人公,他老气横秋,他更敏感,他知道后怕。
以70年代为背景的成长小说,值得重视的佳作还有《英格力士》,它是近年出现的最有阐释价值和才情的成长小说,它用貌似玩世不恭的叙事腔调其实极为严肃地对成长中的内心尊严感进行了认真的深度剖视,展现出关于成长的、前所未有的多面性。英语老师高雅气质吸引着少年的追望,随着世道人心的变异,家长和老师都出了问题,于是,在布满阴影的时代,昔日的尊严持之无据。无论是在成长中的青少年的情境还是成人的世界,情欲的考验、生活的磨损、社会阶层的挤压、价值实现的机遇等等都对生命尊严构成威胁和不怀好意的诱惑,尊严感在内心最温软的地方沉没死亡,整个世界只在地下保留着可怜的爱意,阳光之下,没有什么可以自己把持。
在现实生活的层面,成长的代价便是成长之梦的破碎。单纯地活着和轻松地过日子的不可能,美好愿望的受阻,是这一时期大部分叙写日常生活的成长小说的基本主题。
述平的《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所叙写的成长深具形式意味,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初到工作岗位,总是被告知以同样的准则,他的生活正如成长的原初面貌,是一张白纸,别人总是打算涂涂抹抹又被橡皮擦来蹭去,似乎直到主人公歇斯底里崩溃为止。结束学生时代便意味着进入了生活并开始新的成长。接下来,被改写的命运,便是主人公要具备足够韧性、必须去面对的事情。作品带着先锋小说的余绪,内容稍显简化,形式、观念的意义大于内容。
叶弥的《成长如蜕》是重构成长小说的名作,由于主人公是弟弟,因此它的指向是现实生存中的“他者”的成长,丰实的生活,尖锐的问题,对理想化的成长憧憬的否弃,遥接鲁迅的《伤逝》中对实在生活本身的严峻性的考量。看来是一种旁观者的叙事,冷静的“他者”目光里面,其实还是一种创作主体对于成长主体的深情凝视。在魏微的现实题材成长小说《异乡》里,从城市回到家乡的成长者的身份遭受了亲人的质疑,自我解释的不被相信的尴尬使得自己陷入了无乡的凄凉境地,相对于她以往的《乡村、穷亲戚和爱情》等回忆性作品,这篇小说依然语调温柔,给我们耳目一新感觉的是内里那一股钝痛的穿透力;她的另一部近作《化妆》也有一种成长痛感,嘉丽在身份转换中试探和找补旧爱,被庸俗的对方彻底瓦解,她的成长仪式悲剧性地得到了完成。正如爱默生所说:“一个心灵也许沉思了若干年,可是所得到的自我了解还不如恋人的爱情在一天中所教给的多。”⑨ 只是,我们的成长小说中的爱情所教给主人公的,大都是梦的破损和“长成”后的心碎。
李铁的中篇小说近作《冰雪荔枝》显示了一种艺术的结实,以结结实实的艺术功力写出了荔枝成长的破碎历程,在近年的中篇小说中,无疑属于难得一见的佳作。叙事的环扣设置和节奏的控制都把捉得恰到好处。学校生活的微妙的爱意萌动是那么真纯,洗澡时的心机如此幼稚可爱,木房子里的激情之爱如伊甸园偷食禁果一样的欢娱,季节、民俗、风物的描写也是细微鲜活质感十足。这篇小说不仅仅是为重负和悲哀而写的,荔枝在投入父母的成人较量之前与之初,有着属于她自己的成长经历和美梦,那是寒风冰雪般的情境里小小村姑春心萌发的嫩芽,它招展着纯洁朴素的芽尖,散发着清新美妙的香味,没有防范和猜忌,只有向往和争取。渐渐地,它长出了藤蔓,被牵绊在了由父亲编织的孽缘上头,从此再也难以挣脱。成长之美易碎,毕竟也是曾经经由了美的,而这并不作为小说的重心的部分,作者对温情所下的气力决不弱于那些篇幅更长的残酷过程。父亲的所作所为是所有孽缘的源头。母亲通过荔枝去盯梢报复花心的他,而她自己则逐渐形成以捉奸为乐的病态;安子通过和荔枝恋爱报复他,安子却逐渐真地爱上了荔枝,这时候荔枝已经对真爱失望至极——这孽缘的绳结都系在荔枝一个人身上,荔枝的成长就成了被孽缘所捆绑扭曲的人生过程。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年的创作中,相对不甚完整的“成长断片”和“成长中”小说,数量空前地涌现出来,如此大量的作品本身也构成了今日成长小说的一个新的母题样式,即“成长的破碎”。这又与美国50年代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的超常生活状态的成长有所对应。但是这二十年来的中国成长小说,无论你怎样说其凸显了足够多的反叛和暴力因素,也无论它如何叙写受挫的成长或者成长的被改写之痛,社会性的历史性的“大事”在小说中都只是“生活”,它在成长主角的眼中,而不是在父兄、老师和集体意志的掌控下。
随着80年代中期先锋文学的异军突起,中国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也将国外文学参照系移向西欧、拉美和北美,对中国现代以来特别是早期当代文学影响最深的俄罗斯文学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冷遇。但是,实际存在的参照物让我们无法回避。我们越来越分明地感觉到,19世纪上半期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一类的形象,在我们当前的文学写作中是一种积压般的存在。那种对现状不满意自身又不作为、敏感多思又孱弱无能的青年性格,正迅猛地增加着中国成长小说形象的人口数量。同时,我们如果稍加认真一点去参照俄罗斯文学产生“多余人”的时代,就会发现,我们缺少了俄罗斯当年与“多余人”共存互映的“新人”形象系列——中国式的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别里托夫、拉夫列茨基、奥勃洛摩夫比比皆是,而中国式的英沙罗夫、叶琳娜、巴扎洛夫、薇拉、吉尔沙诺夫、罗普霍夫、拉赫美托夫他们在哪里呢?在那个灿如星汉的俄罗斯文学辉耀世界之此前此后,仅在法国,也分别有的“世纪儿”、“局外人”令全球瞩目。多年以后,当我们的阅读遇到自己似已泛滥的“成长”书写,我们就不能不逼问:重新建构中国式的“成长小说”,是否要尽快决然地走出“多余人”和“世纪病”的宿命?
目前,我们的成长小说,最明显的问题,是主体精神虚弱和叙述软化的倾向。这种状况,甚至会让我们无限缅怀曾有《少男少女,一共七个》(陈村)、《你不可改变我》(刘西鸿)等成长小说杰作的80年代中期。新一代作家很少珍视前人已有的创作基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这两个互为因果的创造的基本条件上面,我们对前一点的储备相当匮乏,不仅对悠远的传统吸收不够,甚至对“前一代”已经登越的平台也常常是无知无觉。尽管他们具备了与已积累的文学传统的现时区别性,但显然在对人间和生命的体察方面,缺少陈村、刘西鸿、王朔他们那种景深感和自如而强劲的叙述能力。
个人的成长史总归要表达个人精神的存留和赓续,而我们现在更大量地看到的是互文式的“群似”:身体的留念、情殇、在痛彻的自我审视中放弃自我精神的追寻和建构,心神的失措和行动的试错不断得到表现却显然缺少灵魂的冒险和强有力的自我成长精神。成长的主角主要是一个个观察者、忆念者和妥协者,最终几乎都通向“无力青年”的形象塑造,这也许就是中国式的人生情境所必然规约出的中国式的成长模式。集中阅读的时候,就会留下令人不安甚至失望的印象:文本表层感性发达,文本的深层理性脆弱。而中国式的成长小说,无论它的叙事指向还是它的精神力量,都不应该到此为止。
注释:
①《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页。
②可参见如下著作中的有关论述:弗朗西斯·约斯特《比较文学导论》(廖鸿钧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朱金鹏、朱荔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巴赫金《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晓河译,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等。另参见冯至、杨武能分别为歌德的《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或译为《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译本所写的序言。
③雁沉寒水:《〈西游记〉里的青春成长》,载《青年文摘》2003年第9期。
④十年砍柴个人文集,见http://www.bookzx.net/htm/q9122/208341.php。
⑤黄妍:《有一种成长叫“悟空”》,载《青岛日报》2006年9月1日。
⑥茅盾:《从牯岭到东京》,《茅盾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30页。
⑦笔者最早读到的涉及《青春之歌》与成长小说的关联的论述,是李杨《抗争宿命之路》(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的第三章,这是一部关于1942—1976年中国文学的极富学术启示价值的专著。
⑧参见李学武《蝶与蛹——中国当代小说成长主题的文化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樊国宾《主体的生成——50年成长小说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许美霞《论中国当代成长小说的内涵与个案》(见http://210.34.4.13:8080/lunwen/default.asp)。
⑨爱默生:《美的透视》,佟孝功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