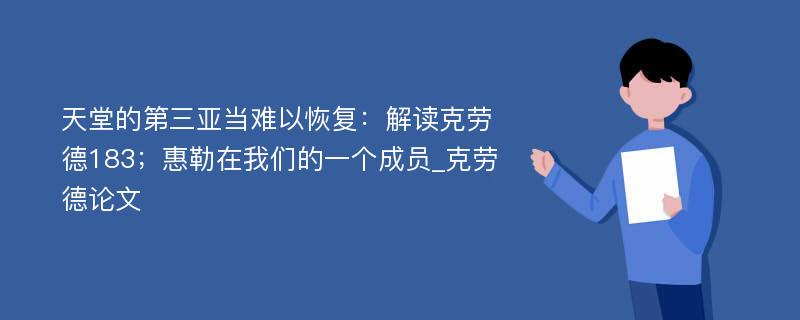
“乐园难复”的第三亚当——解读《我们的一员》中的克劳德#183;维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当论文,克劳德论文,乐园论文,维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22X(2009)05-0086-04
0.引言
美国著名女作家维拉·凯瑟(Willa Cather,1873-1947)为了纪念自己在一战中牺牲的表弟,创作了小说《我们的一员》,该作品获得了1923年的普利策小说奖。主人公克劳德·维勒是个天真浪漫、有理想的农村青年,力图创建自己的乐园。他厌弃唯利是图的重商主义,抵制机器对自然的破坏和对人性的摧残,因而与自己的父兄等人难以相容;他希望通过上大学过上有意义的生活,但因父亲的功利心而中途辍学;他与妻子艾内德的婚姻被证明是场灾难。在乐园梦破灭后,他参加了一战,最终带着虚幻的满足感牺牲在战场上。
在小说的第一章第十五节中,作者通过克劳德与母亲维勒夫人共读弥尔顿的《失乐园》这一情节,已经暗示了克劳德“失乐园”的命运。在《失乐园》中,魔鬼撒旦因蔑视上帝的权威,对抗天庭,被打入地狱,忍受烟熏火燎。撒旦虽被击败,却并不气馁。他自知打不过上帝,就把目标转向了上帝创造的人类。伊甸园里的阴谋使得人类从此丧失乐园,心向往之却不能复归。撒旦通过使人类的堕落来报复上帝,然而他的复仇没有休止。他又瞄向了第二亚当耶稣,诱之以名利权势,但却被识破,人类因此保留了“复乐园”的希望。像耶稣一样具有博爱之心的克劳德想成为重归乐园的第三亚当。然而,工业社会的魔鬼在先进机器的武装下,神通更为广大,手段更为隐蔽,单纯的克劳德防不胜防,多次被愚弄,最终踏上一条不归路。弥尔顿在《失乐园》中为迷途的愚人安置了一个所在——“愚人乐园”。克劳德怀有赤子之心,品德高尚,希望像耶稣一样为人类献身,但他缺少耶稣的慧眼和警觉,因而落入撒旦的陷阱。他未能成为耶稣那样的圣人,反而成了“愚人乐园”里的“神圣愚人”。
有论者认为:“自然激发了凯瑟的反讽,以及她对悲剧的洞察。自然向她表明:世界可能是美丽的,充满生命的喧嚷,但却对它的生灵的安乐完全无动于衷。”(Acocella,2000:89)凯瑟笔下的农场有着伊甸园般的美丽,克劳德起初也像堕落前的第一亚当一样,过着无忧无虑的农耕生活,然而工业社会里的撒旦岂能容忍人间乐土的存在——这位地之子仍然笼罩在“失乐园”的阴影中。第三亚当克劳德作为有浪漫理想的农民之子,万难逃脱工业化魔鬼的折磨和诱惑。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阐述。
1.不合时宜的浪漫自然观
浪漫主义者对大自然顶礼膜拜,把其中的生灵视作同类——鸟儿饿死笼中是一种残忍行为,而一棵砍倒的树会引发生命脆弱之感。(桑德斯,2000:514)像伊甸园里的亚当一样,克劳德同样怀有对土地和大自然的亲近感,对牲畜、草木颇为关切,然而在利益竞争愈加疯狂的工业社会里,人们对土地和自然物的感情已经逐渐物化和淡漠。雇工杰里看到老马莫莉被钉子扎入马蹄,却不予治疗,致使马腿肿得像大象的腿一样。克劳德认为他父亲雇用的是乡里最粗野和最龌龊的人,“所有的马都恨杰里”。①(Cather,1991:41)被逐出乐园的人类生出的邪恶之心在杰里身上可见一斑。克劳德5岁时,由于母亲抱怨一棵樱桃树太高不易采摘,父亲便锯倒了那棵树,因为买镇上的成品水果,花费远远低于自己种植的,克劳德心疼至极,当着母亲的面骂父亲是“该死的傻瓜”,认为上帝必定会惩罚做这种事的人。掌握了机器的农民心思只用于扩大再生产,对利益的角逐压倒了对生态的温情。
克劳德的浪漫主义有时也显得过于天真。比如在暴雪压塌了猪圈把猪压死了十几头后,克劳德痛悔不已。但他痛苦的并不是经济上的损失,而是对猪的怜悯。即便是死猪他也舍不得剥了卖肉:“我要是屠宰了它们,就永远不见猪肉。”(83)克劳德仿佛成了一位不杀生的佛教徒。但这种悲天悯物在现实中显得幼稚甚至可笑。在工业文明浸染的乡村,一切都用重商主义的价值观去衡量,克劳德自然免不了与之发生抵触。
2.物质乡村与精神城市的对立
在机器的诱惑下,人们对利益的竞争日趋激烈,引发了各种罪恶,使人类变得更加堕落,人性进一步远离神性。乡村也难逃机器之祸,人们不再珍视过去曾引以为豪的东西。浪漫主义者曾认为,城乡是对立的两极:城市是邪恶的所在,而乡村则是未受污染的地方。但工业社会的扩张,使他们看到了“工业主义在一向优美的地方正产生的丑恶,注意到了那些在‘生意’里发了财的人的庸俗,憎恨这种丑恶和庸俗”。(罗素,1976:273)在克劳德看来,乡下已变得难以忍受——他父兄就是被机器扭曲了心灵的典型。批评家盖斯马尔称维拉·凯瑟是“愈来愈重物质的文明中一个精神美的捍卫者”。(凯瑟,1983:7)克劳德正是凯瑟树立的捍卫者之一。
为了以城市来对比乡村,凯瑟故意忽略了城市的阴暗面,而把它作为克劳德的精神寄托地。在她的笔下,城市形象发生了改变:它代表着互相理解和精神抚慰。克劳德到城里上大学时,结识了同学俄立奇的家人。这个家庭和谐融洽、平等自由的交流让他羡慕,而自己的家人相聚时,却气氛沉闷,寡言少语,说话小心翼翼,唯恐触及敏感话题。这家人也不像他父兄那样动辄购买机器,而机器在他看来就像金钱一样,不能带来快乐。机器像撒旦一样邪恶,起着离间人们的作用,是剥夺人们幸福感的异己之物。机器和金钱使人们离伊甸园更远。
他在州立大学选修了“欧洲历史”课,教授指定他的期末论文题目为研究圣女贞德,一位基督教圣徒。克劳德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去写这篇论文,似乎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克劳德没有强烈的宗教信念,但对殉教者却顶礼膜拜。殉教者在与魔鬼的斗争中超越了自身,获得了生命的意义。然而他却忽略了:贞德是葬送在自己人的手里,那些法国贵族把她出卖给了英国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贞德被愚弄了,是一位“神圣愚人”。但浑然不觉的克劳德却似乎通过贞德,看到了创建精神乐园的希望。他满心希望通过教育,跳出农门,寻求更充实的生活。
然而,就在克劳德踌躇满志,准备继续在大学攻读并研究贞德时,依靠机器扩张农场的父亲给了他当头一棒:回家经营农场。克劳德感到“似乎一个圈套突然落到身上”。(57)他被父亲剥夺了继续受教育的机会,已没有能力跻身于那些他所仰慕的名人之列。他是一个农民之子,甚至连善解人意的俄立奇夫人似乎也认为农场是最适合他的地方。但克劳德并不认为这种生活值得付出。机器和钱能带来安全感,但这种安全感泯灭了人身上所有最好的品质,却培养了卑劣的品性。他就像吃了智慧果的亚当一样,不满足于无智无虑、没有冻馁之忧的生活,渴求更高层次的存在。《失乐园》中的大天使米迦勒对被逐出伊甸园的亚当说:“在你的内心/另有一个远为快乐的乐园。”(弥尔顿,1984:477)第三亚当克劳德坚信,品行高洁者在尘世终将觅得乐园。他要继续求索,加入“针对无聊人生的圣战”。(Van Doren,1921:92-93)
3.宗教与“理想女人”共设的迷局
浪漫主义者坚持精神的独立性,相信“自律的心灵摆脱和越过仁慈的僧侣集团,寻求他自己的救赎方式”。(布鲁姆,2000:162)在现代工业社会,宗教已不再主导意识形态,但却依然能够左右个人的命运。机器引发的对利益的竞争使得社会变得冷酷,这似乎也波及到宗教——在机器时代,宗教对芸芸众生的苦难也带着机器的冷冰冰。克劳德瞧不起牧师维尔登,但后者却施加影响,使得克劳德被家人送入圣堂学院——一所教会学校——上学。这与他的心愿相悖。“正是那些他最不喜欢的人和事塑造他的命运。”(27)4年下来,他几乎没有学到什么——要是不借助字典和语法书,他还是不能阅读希腊文的《新约》。牧师总是把克劳德的名字读成“土块”(Claude与clod发音相近),这使他恼火。天主教徒艾内德也同样有这个口误。小说的最后,佣人马海莉在克劳德死后,因为想念他,有时把维勒“夫人”错叫成“土人”,这都暗示着他悲剧性的命运。克劳德逃不过上帝对亚当和土地的诅咒,而撒旦始终对他虎视眈眈。
克劳德虽然对宗教有看法,却认为有信仰的女人心灵会发出芳香,就像他母亲和女友艾内德一样。她们相信天堂有乐园在等着她们,而他也会有自己的乐园——他幻想着婚姻会造就人间乐园,艾内德将是琴瑟和谐的第三夏娃。他对婚姻寄托了极大的希望,但准岳父罗伊斯先生在犹豫半天后,忍不住警告他:“你会明白,关于生活,几乎任何你所相信的玩意——尤其婚姻——都是谎言。我搞不懂人们为啥偏偏想过那种生活。但他们就要过”。(125)一语成谶,克劳德的婚姻没有给他带来幸福,反而造成了他人生的另一重大打击。进行蜜月旅行的第一夜,新娘艾内德独自睡在列车包厢,把他赶到了污秽不堪的吸烟车厢。这位虔信天主教、表面上一本正经的艾内德竟然像她母亲罗伊斯夫人一样,也是性冷淡。正像最理解他的格蕾德斯所认为的那样,使世界变得美好的东西——爱和善良,闲适和艺术——已被锁入牢狱,像他哥哥贝里斯那样的成功人士掌握着钥匙,而克劳德会变成“一台巨大的机器,里边的弹簧是破碎的”。(129)
艾内德说克劳德就像《圣经》中的约拿一样。无辜的约拿为了救船上的人,被上帝抛入鱼腹,熬了三天三夜,出来后,因为上帝言不由衷,屡次捉弄他,约拿禁不住向上帝发怒。克劳德就像约拿一样,被命运捉弄,屡次受挫。约拿敢于向上帝叫板,软弱的克劳德却逆来顺受,默默吞咽着苦果。宗教和婚姻——两者都披着神秘的面纱,并结合于艾内德一身——合力把他推向深渊。在冷酷的工业社会里,宗教和婚姻没有给他带来安慰和温情,却反而成了撒旦的助手。
4.战争——机器对“机器”的毁灭
在多重打击之下,克劳德陷入了极度苦闷。“欧战的爆发是个缓解——在精神上的确必要。”(Cooperman,1970:133)克劳德似乎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他本来就有深厚的“法国情结”——他要像圣女贞德一样,筑起血肉之墙,去捍卫有着抽象意义的纯洁的巴黎。在农场,人生的梦想已经破灭,他只不过苟且偷生;也许,在法国能找到寻觅已久的乐园?
入伍后的克劳德对战争持理想化、浪漫化的看法,以为自己会像冷兵器时代的骑士一样作战。训练营的士兵大都持这种堂吉诃德式的想法。这些年轻人极其单纯,对战争没有任何直观的经验。布洛克认为:
当时几乎没有人(军人也不例外)知道现代技术战争对个人、对整个社会意味着什么。几乎没有人相信这场战争会持续到圣诞节以后;更没有人会料到,大战最终结束之后,1914年的欧洲将一去不复返了。欧洲各国首都的群众之所以为宣战而欢呼,那只是出于无知,而不是出于某种集体死亡的冲动。(1992:43)
撒旦操纵的机器不但在肉体上摧毁人类,还要在精神上予以麻痹愚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让士兵还未来得及展示任何骑士风度时就把他撕成碎片,现代机器装备的宣传机构则使人心甘情愿地变成了炮灰。克劳德虽是一介农夫,但并非文盲,曾受过高等教育,他之所以轻易地被卷入战争。附属于文化意识形态的媒体的宣传起着相当大的作用。电话、打字机、电报等技术发明使信息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媒体借此对民众进行快捷的、狂轰滥炸式的战争宣传。通过媒体,克劳德和母亲密切关注着法国失陷的一城一地。作为官方的传声筒,媒体的战争报道是有倾向性的:对同盟国进行妖魔化,把协约国描绘成无辜的受害一方。同盟国进攻法国所运用的武力被描述为具有不可预测效应的自然灾难,就像海啸、地震或火山爆发一样——一种史无前例的毁灭力量挣脱束缚,降临世上。这种邪恶势力比起曾入侵罗马帝国的野蛮入侵者“匈奴王”还要更残酷、野蛮。(137-138)克劳德母子完全陷入了国家宣传机器所编织的罗网中,而未能察觉这一切都是利益集团的精心谋划。
克劳德乘坐的运兵船因疫病而死亡无数。他和幸存的战友们终于到达法国。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他的手下被屠杀,他却赞美“这美丽的土地,这美丽的人民”(326),因为“他的幸福是完整的;克劳德没有因机器的死亡效应而痛苦,反而愉悦在几乎像性高潮过后的放松中”。(Cooperman,1970:136)他完全陶醉在对战争的巨大幻觉中,以为自己是在为某种目标和理想而战。克劳德战死沙场,正应验了格蕾德斯的话——克劳德变成了“一台巨大的、破碎的机器”,而捣碎这台机器的是“‘理想女人’‘家庭’‘社会’和生活自身”。(Cooperman, 1970:136)克劳德痛恨机器对人性的摧残,但想不到自身已变成了被洗脑的机器,因为他已经把“政府的战争宣传内化为自己的话语、理想与抱负”(李公昭,2007:62)。撒旦化身的机器魔兽已经成为统治者争夺利益的强大工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信教的克劳德却比大多数信徒更遵守戒律,正像华兹华斯诗中称颂的:“他们是能听人讲十诫而感到/无需自责的人”(1986:17)。克劳德是一个道德上没有瑕疵的人,和海明威笔下的战争人物相比,农民之子克劳德就显得太完美了,太“温良谦恭”了。别的士兵寻欢作乐,与驻地村子的女人谈情说爱,而克劳德却无动于衷。联想到克劳德在猪死后都舍不得剥了卖钱,可以说,他似乎树立了一个圣人的形象——跟耶稣一样,具有博爱精神,不惧磨难,甘于为世人献身。但第二亚当耶稣没有被撒旦所蒙蔽,第三亚当克劳德却没有意识到工业社会里的撒旦手段之阴险狡诈,从而误入彀中,变成一个道德上完美、行动上受蒙蔽的“神圣愚人”。一个“义人”,却被稀里糊涂地钉上了战争的十字架,这是对战争和社会现实最大的反讽。在工业化社会里,克劳德的浪漫主义观念已变得苍白无力,正如希克斯对凯瑟做出的评价:她不能面对人世的残酷,相反却退隐到一种倦怠的浪漫主义中。(Acocella,2000:25)
查内认为,克劳德像仪式小丑——神圣愚人的一个版本——那样行动。仪式小丑为了社群的总体利益而扮演一个被禁止的社会角色,单纯幼稚、浑然不觉。(Charney,1978:172)这种行为使他们成为说实话者,而说实话是神圣愚人的核心概念。(Rosowski,2005:126)克劳德的浪漫话语表现出其直接、天真、不加调和的特点,在功利而虚伪的现代社会自然寸步难行。罗苏斯基认为,当暴政统治时,每个人都是愚人;而《我们的一员》可以加个副标题“愚人历程”:它以主人公的扮演愚人开始,追踪他因惧怕被嘲笑而做的逃离,并颂扬他把自己释放到追求光辉业绩的愚行中。(Rosowski,2005:123)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小说不是悲剧,反而是喜剧,因为“在悲剧中我们忍受痛苦;在喜剧中痛苦是个愚人,痛并快乐着”。(Fry,1965:17)当战友因瘟疫或战斗而大批死亡时,克劳德竟感到欣慰,可见他多么强烈地表现出“神圣愚人”的特点。
5.结语
弥尔顿在地狱边缘为那些迷狂的愚人安置了一个所在——“愚人乐园”。第三亚当克劳德希望重归伊甸园,却懵懵懂懂地落入“愚人乐园”。这不能全然怪他,他面临的境地远比第一亚当险恶。在工业社会,撒旦以机器为辅助,设下重重陷阱,既从精神上也从肉体上对人类进行愚弄和摧残。未能参破迷局,从而被愚弄的“神圣愚人”又何止克劳德一个!
注释:
①Willa Cather,One of Ours(New York:Vintage Classics,1922),文中的引文均出自该书,以下只标页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