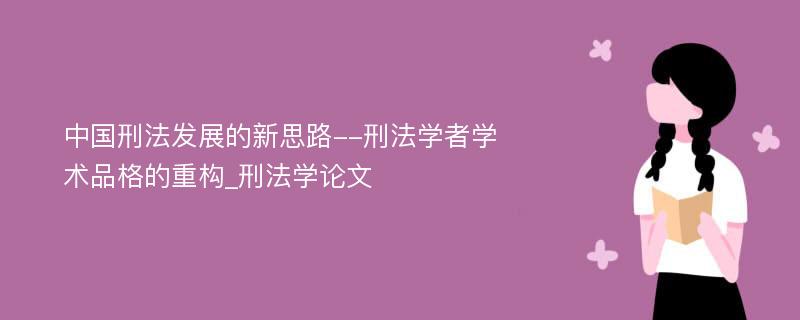
中国刑法学发展的新思路——刑法学人学术品格的重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人论文,刑法论文,品格论文,中国论文,新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福科认为由学科、知识、权力组成的学科规训制度是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一种生产论述的操控体系,是主宰现代生活的种种操控策略与技术的更大组合。没有任何一个孤立的个人可以完全摆脱这一体系。这种客观事实似乎将我们导向“刑法学术研究必然衰落”的宿命论,仿佛我们大家都只能被动地随波逐流而不能有所作为。所以刑法学界的同仁们在议论当前的学术研究状况时都多有不满意之感,可行动起来却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这一体系的牵制。但是前景并非黯然无光,因为人是具有相对意志自由的,我们这一代刑法学人完全可以通过重塑自身的品质来复兴学术,尽管这需要艰辛的劳作,可能要付出痛苦的乃至自我否定的代价。下面结合刑法学研究中的问题,从个人的角度对“刑法学向何处去”谈几点浅见。
1.刑法学术之“根”。“根”即刑法学研究的落脚点。我国刑法理论是从苏联进口的,经过老一辈刑法学家的改造,已经基本成形,形成学术传统,在我国理论界、司法界扎根。近年来,留欧、留日的大批中青年学者对社会危害性、犯罪构成、犯罪概念等我国的基本刑法理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形成以批判为“时髦”的潮流,大有刨“根”的颠覆意味,欲以欧陆、日本刑法理论取而代之。笔者认为,传统刑法理论固然有不少问题,批判者指出的问题也并非空穴来风,但是就因此而颠覆“旧”基础,将欧陆、日本刑法理论照搬过来以消除问题恐怕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历史不容阉割,历史的铁律在于“不存在将过去推倒重来”。理论一旦建立并生根,它就具有一种自我复制、繁衍的能力,这反过来又是产生特定问题的源泉之一。尽管我们好像可以自由地走任何一条路,比如无视问题的存在而继续原地踏步,或者抛弃原有的基本理论,全盘移植大陆法系刑法理论的符号体系,但这只是逻辑上的可能。事实上,只要我们开始选择了某条路,比如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社会危害性理论,那么将不得不去解决属于这条路中的特定问题,而不是将历史的选择推倒重来,当然我们仍然拥有自由和创造性的空间,但已经被特定化了。这也许带有强烈的“本土化”色彩,但从理性上思考,“本土化”并不是“固步自封”的代名词。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有的刑法理论和实践问题。理论框架、概念、范 畴、命题组成的是一种理论模式,但“学术不只有一种模式、一种构架”,(注: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8页。)也不能抽象地说这种模式好,那种模式坏。况且深究的话,大陆法系各国的刑法理论模式也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大一统”。不管是大的理论构造、刑法思想、刑事制度,还是具体的个罪问题,都因民族思维方式(民族精神)的差异以及文化、政治、经济背景的差异而呈现出多样性。作为实践理性的刑法学研究,不能像哲学家行走在路上而眼观遥远的星空,一心想着“生活在别处”,(注:昆德拉讲了一个故事:有个人申请移民签证,官员问他:“你打算到哪里去?”他说“哪儿都行”。官员给他一个地球仪说:“你自己挑吧!”。他看了看,慢慢转了转,对官员道:“还有没有别的地球仪?”参见[捷]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程一荣译,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39页。)否则就会摔掉大牙乃至跌入深渊。笔者以为,这里的“根”就是苏力教授所说的“本土化”问题。除了宏观理论模式的本土化,刑法的许多具体问题也与本土化相关,诸如对犯罪概念的理解、“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提法问题、亲告罪问题、我国邪教犯罪问题、“东突”恐怖犯罪问题、婚内性暴力问题、死刑问题,等等。对这些问题如果不搞实证研究,不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特性出发,仅凭概念的逻辑推演,其结论是值得怀疑的。所谓实证研究薄弱,乏定量分析其实也是一个是否“扎根于本土”的问题。
当然“扎根于本土”的命题,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西方刑法理论的成果和发展趋势,“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然而首先这人要沉着,勇敢,有辨别,不自私”。(注:鲁迅:《鲁迅论文·杂文集》,同心出版社2000年版,第476页。)我们必须分析研究西方刑法理论背后的哲学基础、民族精神、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背景。我们要借鉴的是他们用以解决刑法特有问题的那种睿智,而不是表层的永远在流变的具体的概念、术语。只有这样,才可能避免拿来的刑法概念、理论、观念、原理,对他们而言是如此的理所当然,输入到我国就可能有一种血型不对应的异质感,而且还有一种永远也跟不上他们的脚步的挫折感。
2.刑法学术之“视”。有了落脚点,扎稳了脚跟,还得睁开眼。当前我国刑法学研究视野狭窄,刑法学研究多是对刑法条文进行以概念为中介的形式逻辑推理,好像刑法是一个不关社会现实的逻辑自足的天国。如果说在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相对简单而稳定的古代农业社会,尚可“不出户,知天下”,“不行而知,不见而明”,(注:《道德经·四十七章》)那么在现代社会就不适宜沉浸在概念的天国中冥思苦想,而必须睁眼看世界。不仅要看,而且还得多视角地看。法学从很大意义上讲从来就不是一个自治自主的学科,它涉及社会的所有方面。法学有自治与开放两个纬度,开放意味着“法学不能满足于自给自足,而需要从其他的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中汲取营养”。(注:贺卫方:《法学:自治与开放》,《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法律、法学发展的动力很少来自于法律概念自身的推衍,而更多来自法律之外的社会现实的促动或其他学科的渗透。从根的角度看,“扎根于本土”要求以问题为中心,也必须多视角、多学科整合研究。“法律的生命始终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注:[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页。)所以刑法学研究也必须“超越法律”。(注:[美]理查德·A·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目前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等视角研究刑法问题的论著实在是凤毛麟角,我国刑法学要有所突破,应当从这些方面着手开拓。但是多视角多学科研究也有一个驾驭问题,不是随意塞进几个其他学科的时髦术语就称得上多视角多学科研究的,因为多视角多学科研究在本质上讲是一个思维内化的过程。
3.刑法学术之“思”。当我们扎“根”于本土进行交叉、全方位的“视”,所得到的东西仍然是混杂的,因此还必须有一个“思”的操作问题。具体到刑法学,我们不得不先讨论“片面的深刻”和“刑法学流派之提倡”的观点。提出上述观点的学者其实是以独到的眼光从不同侧面触及到刑法学研究之“思”的问题。毋庸讳言,长期以来,我国刑法学研究缺乏一种思想的棱角,对许多问题采用的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种貌似全面而辩证的公式化论述,似乎什么都说到了,但又什么也没说具体,也说不下去。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式既是结论也是理由,仅此而已。正是因为对这种状况的不满,所以才出现甘冒“违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或“走片面极端”之名的“片面的深刻”和“客观主义(刑法学流派之一)之提倡”的主张。对此,笔者是持欣赏态度的。这种研究思路有其针对性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不片面无以深刻”的命题是成立的。打一个比方,“疱丁解牛”要做到游刃有余,其工具必须是一种“刀”,刀的构造必是“片面”的,而不能是“方圆”的。给疱丁一把圆木状的“刀”,恐怕他也只能将对象打死、砸成肉浆,而不可能在解剖时做到游刃有余、筋骨分明。只有使用片面之刀的疱丁才会深刻地研究自己所面对的不断变化的活生生的解剖客体的体形、体质、结构,才会思考怎样更好地使用刀,从哪里入手,什么地方难行或不可行,不断地从解剖实践中总结经验,才可能形成解剖之道。“学派意识”就是刑法学研究者手中之刀。它使每个研究者意识到自己的理论核心,不轻易动摇基本立场,批判时认清他人背后的根基,证明时尽量保持具体观点与基本立场的一致性,否则就只能是使用大棒的疱丁,反正最后都是一堆模糊的肉浆,也就无所谓什么解剖之道,左右逢源,此亦可,彼亦可,怎么砸都行。
从某种意义上讲,思想都是片面极端的或者说都要通过片面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不片面、不尖刻就无以一针见血,无以刻骨铭心,无以产生强烈的刺激和反应。正如龙勃罗梭与“天生犯罪人”、弗洛伊德与“性欲”、尼采与“强权”、苏力与“本土”等常被人进行符号互换。但是正常社会的本性要求其发展的常轨应当是平和中庸的,如果社会生活也像思想一样走极端,其危害无穷。刑法学的发展有时候需要“片面极端”的思想激励,但作为一门以实践理性为核心的刑法学,仅仅停留在或满足于“片面的深刻”或永远执守在“客观主义”的一端,恐怕是将手段混同于目的了。所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刑法学研究中不可抛弃。当然真正的辩证法是一种以“对立”、“片面”、“分割”为中介、为前提的“对立统一”。也许国人把孔子单纯地理解为“中庸论”者是一种误解。在笔者看来,孔子也是一个辩证法论者。孔子主张“吾叩其两端而竭焉”,(注:《论语·子罕》)叩即追问,端即极端,竭即尽力。可见孔子在认识论上也竭力追求“片面的深刻”和“两端的分离”,在此基础上才有“中庸”的实践主张。如果我们将二者合起来,其辩证法思想可表述为“叩其两端用其中”的对立统一。
4.学术之“色”。学术之“根”、“视”、“思”最后可归之一个“色”字。“根”是我国刑法学术总体之色,是刑法学人共同构造出的“大色”。“视”与“思”是刑法学人因其知识结构、研究方法、生活经验以及思维方式的差异所决定的个人学术研究之“特色”。从思维与视角上看,有人善于哲理思考,有人善于逻辑推理、语言分析,有人善于社会学思考,有人善于心理分析,有人善于实证研究,有人善于经济分析,不一而足。孔子提倡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思想中,“不同”大概也含有个性特色的意思。惟此,才可能真正产生学术的交锋和争鸣,不断完善批判双方理论上的缺陷并推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合理化。
当然“知易行难”,我国刑法学研究的革命首先要从刑法学人做起。刑法学人要有革自己的命的牺牲精神:首先要耐得住寂寞地去学,“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其次要受得起学术之苦,“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最后才可能厚积薄发,“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注:况周颐、王国维:《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年版,第202-203页。王国维先生曾引用古代三位大词人的这几句词,来比喻学术、事业、人生必经的三种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