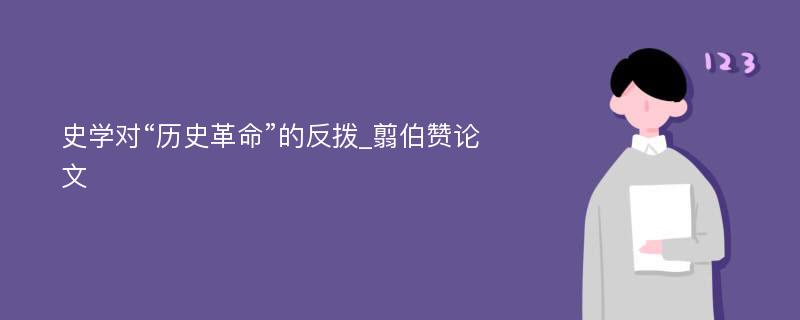
历史主义对“史学革命”的一次反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主义论文,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34(2003)01-0012-08
1950年到1976年“文革”结束的二十七年间,中国史学界似乎从来就没有平静过,总 是处在惊涛骇浪之中,随着全国政治运动的反反复复,史学界中的运动也此起彼伏。( 注:对于史学界相关的状况,参见周朝民等编著《中国史学四十年,1949-1989》(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1949-1989》(北京:书目 文献出版社,1989),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6)。)1958年经济上“大跃进”的狂热也波及了史学界,因而掀起了“拔白旗,插 红旗”和集体搞科研的运动,在陈伯达、戚本禹等人的倡导与号召下,一场所谓的“史 学革命”迅速展开。“厚今薄古”、“打破王朝体系”、“打倒帝王将相”、“以论带 史”等口号,在史学界沸沸扬扬。当时作为北京大学历史系系主任的翦伯赞,“对此十 分忧虑”,(邓广铭《值得我们学习的几件事》)[1](19-20)而他又是全国史学界的领导 人物,“想把全国史学界的方向道路问题、学风问题把握好”,(张芝联《我认识的翦 老》)[1](73)因而他针砭时弊,奋笔直书,分别写出了《历史科学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 争》、《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目前史学研究 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等一系列文章,(注:分别刊于1958年7月15日《人民日报》、19 59年3月《新建设》(后又刊于1959年3月28日《光明日报》)、1959年《红旗》第十期、 1962年5月《江海学刊》)。试图对当时史学界的狂热加以净化,极力宣扬历史主义的观 点与方法。1961年3月以后,在编写历史教材的时候,他以历史教科书编选组组长的身 份,又写出《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等文章,作为编选教科书的纲领性文件 ,很好地贯彻他历史主义的思想。他本人主编《中国史纲要》,而他与郑天挺先生主编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郑老自己又主编《中国史学名著选》以及其他的历史教科书, 都可以说很好地体现了历史主义的观点,这样使他和其他史家宣扬的历史主义思想不致 流于空泛,同时也是对“史学革命”一次很好的回击。因为本人掌握资料的关系,故本 文以《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和《中国史学名著选》为中心,对这次教材编选的背景、特 点以及相关的内容加以阐述,进而试图把握六十年代初中国史学界的状况及相关史家的 心态。
一、背景与原则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以后,翦伯赞先生就任北京大学历史系系主任,而原来的系 主任郑天挺先生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系主任。郑老和翦老解放前并不认识,解放后由相 识、相知到互相合作,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傅同钦、克晟《记1961年文科教材会议 一兼忆翦老与郑老》,第100-103页)[1]郑老在北大执教多年,又有十八年北大秘书长 的经历,弟子门生遍天下,在北京以至全国史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翦老作为马 克思主义新史学的代表,代表新中国史学研究的新方向,所以在建国初期的史学运动中 ,翦老总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以领袖的身份号召群伦。六十年代初历史教材的编撰 ,使二老交往渐多,终成朋友。
关于历史教材以及其他文科教材的问题,建国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为政界和学界所 关注,“一九五三年九月的综合大学会议、一九五四年七月的文科教学研究座谈会、一 九五六年六月的教材会议,都有过不少讨论。”(郑天挺《自传》,第709页)[2]翦老和 郑老作为历史学界的重要人物,都参加甚至主持了有关的讨论,所以如何解决教材问题 成为当时学界的一大任务。1958年前大多照搬苏联的,而在1958年的“史学革命”的狂 潮中,大学里不断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搞教材,甚至让没有学过那门课的学生来编写教材 ,“一门课的教材许多学校在编写,反复在编写。”(周一良《纪念翦伯赞同志》,第1 2页)[1]课程内容则经常变动,教材修改频繁,年年改,时时改,少则一年改一次,多 则一年改数次,让大学师生无所适从。大学里的混乱不止于此,学生还用机械的、标签 式的“阶级观点”教育他们的老师,在“厚今薄古”的口号下,主张历史学要为现实政 治服务,同时轻视历史学的基本训练。面对这种情况,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吴晗 等等纷纷撰文,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地对“史学革命”进行了批评。郭沫若指出打破 王朝体系,简单地把王朝抹掉是反对历史主义,“显然是不对的。”[3]吴晗连续发表 了《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厚今薄古和古为今用》、《论历史知识的普 及》和《如何学习历史》等文章,对此进行批评。翦伯赞这一时期在史学理论界则最为 活跃,连续发表七八篇论文,探讨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而对于大学编写教材的问题 ,翦老也相当有意见,“他主张教材编好以后,应当实践使用,稳定几年,在这期间抓 紧重要问题的研究,取得研究成果以后,回过头来在修改教材。”(周一良《纪念翦伯 赞同志》,第12页)[1]北大历史系师生结合,1960年以后,也打算编写一部中国通史, “可是师生之间关于社会分期问题争论很大,闹得不可开交,以至无法进行下去。”( 邓广铭《值得我们学习的几件事》,第16页)[1]北大如此,全国的情况就更糟,这样教 材作为高校一个大问题亟待解决。
1958年的“大跃进”,给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都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接下 来的经济大萧条,使得中央不得不调整政策。1961年初,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对整 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工 作,也深感高等学校教学秩序混乱,教学质量严重滑坡,提出要解决高等学校的教材问 题,文科、理科都要解决,这样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具体 主持,开始了文科教材的编撰工作。1961年3月,文科教材编写组的预备会议在北京召 开。4月,正式召开文科教材会议,周扬在报告中对1958年以来的教育界存在的问题一 一进行了分析,如“红与专、政治与业务、书本知识与活知识、论与史、古与今、中与 外、文与道的关系”都加以剖析,(田珏《翦老活在我心中》,第119页)[1]提出“不抓 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做到“党与非党合作”,为学术界开创一中良好的风好 ,(第335页)[4]清除1958年以来的混乱思想的影响。
参加历史组会议的有翦伯赞、郑天挺、周一良、齐思和、邓广铭、杨向奎、黎澍、陈 翰笙、白寿彝、杨生茂等,历史组除以上学者外,尚有唐长儒、方国瑜、蒙思明、金应 熙、何兹全、傅衣凌、黄云眉、韩儒林、尹达、马长寿、冉昭德等等参加。会议以翦伯 赞为历史组组长,郑天挺、周一良为副组长,田珏为秘书。会议拟定了历史系大学生的 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读书目录,印发全国高校。并决定了一系列历史教材的编写计划。具 体项目有:黎澍主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史学概论》,郭沫若主编 《中国史稿》、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周一良、 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周予同主编《中国历史文选》、郑天挺主编《中国史学名著 选》、吴于廑主编《外国史学名著选》、白寿彝、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翦伯赞、 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参考资料》和《外 国史学史》等等。(田珏《翦老活在我心中》,第120页)[1]会议以后,各项工作就相继 启动,一直到“文革”开始前的五年时间里,编选出来许多教材,对于中国高校教学与 学术研究,都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使得建国以后关于教材的编写终于得到部分落实 ,而且历史学的教材比较好的贯彻了翦伯赞等宣扬的历史主义思想,因而可以说是历史 主义对“史学革命”一次成功的否定,尽管“文革”开始以后,历史主义又再次被打倒 ,但通过教材的编写,在中国史学界已经生根。而这次教材的编写,是“文革”前中国 史学界少有的几次建设性的合作,因为建国以后,中国的学术界一直倡导“破旧立新” ,但更多地在“破旧”,大批判性的学术活动席卷全国,“批胡适”、“批胡风”、“ 反右”、“大跃进”,都重在推倒学术界既有的一些传统与思想,而真正“立”的东西 很少,尽管当时也出版过一些史料,(注:如1952年到1961年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 刊》,1956年由吴晗组织标点中华书局出版了《资治通鉴》等等。)但这些东西都淹没 在学术界一浪接一浪的大批判之中,六十年代初教材的编写,则是“立新”的一次很好 的尝试。
翦老在这次教科书编写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组织上都功不可没。计划制定不久, 翦老就写了《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从理论上清除1958年以来“史学革命 ”在思想上造成的混乱。文章分八个部分,分别探讨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民族关系、 国际关系的原理,主张历史研究要用发展的观点、全面的观点,同时对如何处理人民群 众与个别历史人物的关系、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史与论的关系等一直困扰史学界的 问题进行了梳理。1961年7月最初发表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内部刊物)上,11 月《文科教材编选工作通讯》(内部刊物)刊出,12月22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23日 ,在吴晗主持下,北京历史学会对此文进行了大讨论。(张传玺《一代史学家与出版家 的革命情谊——记翦伯赞与金灿然的交往》)[1](208)这篇文章刊出以后,立即在史学 界引起极大反响,被称为“史学界的‘高校六十条’”。(田珏《翦老活在我心中》, 第121页)[1]这自然是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的纲领性文件,当然也是其他历史教 材编选指导性的文件。文章中,翦老对1958年以来的“史学革命”一些混乱的说法,一 一清理,很好地阐述了他的历史主义的思想。当然也是《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和《中国 史学名著选》编选的原则。郑老学风一向以务实求真著称,对于翦老的观点,郑老自然 是心有所肯的。下面就以《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和《中国史学名著选》为中心,具体探 讨相关的问题。
二、组织结构:翦老总其责,郑老专其事
六十年代初,历史教材的编撰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翦老除主编《中国史纲要》 外,还统筹其他的计划。郑老则具体负责《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与《中国史学名著选》 的编选工作。郑老在教材会议后,为了工作方便,就一直住在北京,直到1963年夏,工 作基本结束,才返回天津。1961年4月教材会议指示和分配任务后,各段负责人于七月 六日和七月十九日开了两次小组会议,彼此交换意见。8月,郑老草拟了《关于编辑<中 国通史参考资料>之意见》,对于《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编选之对象、原则、目的作了 说明与规定。指出此套书主要是给历史系本科生作参考教学用的。内容选择上有四条要 求:
1,系统地选择比较完整(具有首尾)的原始资料,(不选论文,可以加考古报告、调查 报告);2,只有在缺乏完整资料时,如古代的、隋以前的、经济的,才纠集零散片断的 资料;3,尽量多选时代较早的文献,不用转手资料;4,资料只许删节,不许改动(除 了某些少数族名称如獠、猡、猺)(《关于编辑<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之意见》,1961年8 月14日)[1](505)
可见,核心原则是尽量用原始材料,而且要保持原样,不作人为删节,而选择的原则 是“注意资料的阶级性、真实性和典型性”,这个原则并非一定得执行,所以又特别加 了一句“只是提注意,而不是贯彻,不是统治阶级的资料不收”。而目的是两个:“一 ,充实历史知识,接触更多的文献;二,训练阅读能力,不断地阅读文言文。”(《关 于编辑<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之意见》,1961年8月14日)[5](505)
郑老起草这个《意见》以后,与翦老商量,翦老1962年3月,在苏州编写《中国史纲要 》时,写信给郑老,其中有言: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是为讲授和学习中国通史教科书作参考用的。要针对教科书中 提出的历史事件、人物和典章制度选录资料;但不要受教科书的限制。可以超越教科书 的范围,选录一些足以说明重大历史问题的资料。这些重大历史问题是应该写进教科书 而没有写进教科书的。通史资料不只是消极地注释通史,最好能发挥积极的启发作用, 帮助学生从具体史实去认识规律和特点,让他们不仅知道得出结论,并且知道如何得出 结论。[4](337)
翦老提出这个编选原则以外,也列出了16条意见,供郑老参考。郑老结合翦老的意见 ,最后写成《关于编辑<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的初步意见》,刊登在《文科教材编选工作 通讯》十一期上。这就作为编选《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的原则,同时也适用于《中国史 学名著选》的编辑。
这两套书采取的是丛书主编统筹规则,制定原则,最后审定稿件。各分册主编负责每 册书的《编选说明》,具体的编选、注释工作。翦老主要负责《中国史纲要》的主编工 作和整个历史教科书原则问题的把握,对于这两套书主要由郑老负责,不过,在大的原 则问题上,郑老总会与翦老商量,告知翦老,或征询翦老意见。
尽管是全国教科书的编选计划,而且是在中宣部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项目,但是当时 参加者还是颇有顾虑,在编选资料的过程中,郑老将这种顾虑归结为“四怕”:
(一),怕选帝王:《史记》、《汉书》都不选汉高祖,《三国志》只选曹操,不选刘 备、孙权;(二),怕选贵族将相:《后汉书》不选窦融、马援(怕有功的外戚),外戚选 了梁冀;《史》、《汉》不选萧何、韩信,其他书也都不选名将名相;(三),怕诬蔑少 数民族;《后汉书》选例,在标准的第一条就是“少数族历史另有专辑,不录”,实则 并无此专辑;(四),怕犯错误:《史记》不选《伯夷叔齐列传》,实则经过批判的人更 应该知道他们的历史。(郑天挺《关于编选<中国史学名著选>之意见》1961年8月15日)[ 5](509-510)
经过了“反右”和“史学革命”的冲击,编选者心有余悸,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尽 管郑老也经受了冲击,但是他还是秉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负责的精神,通过信函努 力消除编选者的顾虑。
作为主编的郑天挺先生,相当认真负责。因为两套书都是为大学教科书性质,所以在 编选过程中,主编要考虑所编出的书,是否利于教学,同时还考虑到学生的购买能力。 而且因为当时教材匮乏,各校要求迫切,所以又要求进度较快。如郑老1962年7月27日 致函中山大学董家遵先生:“《隋唐五代史参考资料》闻尊处甄选已毕,略加简注即可 完成,至深钦慰。现各校需用孔殷,催促颇亟,尚请于八月底以前交下,以便可以克期 出版。”(《函董家遵1962年7月27日》)[9](519)从1961年4月开始,各校就开始两种资 料的编选工作,最快者六、七月间就已经完稿,在1966年“文革”前,《中国通史参考 资料》已完成古代部分第一、二、三、四、八册,近代部分亦由龚书铎先生编完上、下 二册,并且得以出版。《中国史学名著选》则出版《左传选》、《汉书选》、《三国志 选》、《资治通鉴选》四册。其他未出版的书,也大多完成了。
当时编选资料固然是为了大学教学的需要,但参加编写的史学家并非止于此。1962年4 月,郑老与翦老商量后,历史组决定编写中国断代史九种。为此郑老特别准备信函如下 :
此间近有编辑中国断代史计划,分九册,每册三十至三十五万字,定名为××史纲要 。内容、论点及编排,全由主编者自定。九册只求衔接,不求论点一致。合之可以成为 一套断代史,分之亦可以独立各成一书。期以两年半完成,一九六四年出齐。其中((史 一册,咸推吾兄主编。九册分期如:……如有不妥,尤盼教正。(《致中国断代史诸主 编》,第516页)[5]
遂决定各册主编如下:徐中舒《先秦史纲要》、翦伯赞《秦汉史纲要》、唐长孺《魏 晋南北朝史纲要》、汪《隋唐五代史纲要》、邓广铭《宋辽金史纲要》、韩儒林《元史 纲要》、傅衣凌《明史纲要》、郑天挺《清史纲要》、昭循正《民国史纲要》。九部断 代史的主编,皆参与了当时的历史教科书的编撰,汪篯与邵循正先生参与了翦老主编 的《中国史纲要》,所以九种断代史的编选计划,可以说是教材编写的继续。可惜因为 不久政治气候的变化及随之而来的“文革”,使得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变成现实。
作为历史组副组长的郑天挺先生,当时除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和《中国史学名 著选》外,亦过问其他的编撰事宜。如《中国历史文选》由周予同先生主编,其间周先 生与郑老往为书函数度,征询意见,商榷相关的编选事宜。若1961年8月25日,郑老致 函周先生:
顷上海寄来尊选《历史文选》清样,注释精确扼要,而解题尤见概括之审,非淹贯大 师不能办此。拜服拜服。《史通》校注之想,弟怀之四十年,性既疏惰,旧时又奔走衣 食,不能得善本,蹉跎无成;近已嘱杨翼骧为之。浦二田于刘书诵习尚熟,但识见太陋 ,且有妄改处,诚如尊论,实不足观。刘子玄书有创有因,有批判,有继承,学者多赏 其创而忽其所因,遂疑刘氏之前无史学,非笃论也。然刘氏于因袭前贤处,既未一一说 明,非饱学如兄莫能抉示,此则尤盼随时见教者也。(《函周予同1961年8月15日》)[5] (511)
在现存保存郑老的信函中,有周予同先生于1961年9月11日、11月27日和1962年1月8日 致郑老的信。如1961年9月11日的函中周先生言:
接八月四日手教,深感老友关怀之深,敬先致谢意!《中国历史文选》上册已交中华书 局付排,如按口头约定,九月开课当可有书。下册因保证教师休息,只有初稿,尚须大 力修改。其中选目,尊见甚是。现已与同志们协商,将谭嗣同、严复二文抽出,改选顾 炎武、钱大昕、赵翼三家,惟选何篇,意见尚未一致。兄有高见,肯即示知。(《周予 同1961年9月25日》)[5](532)
可见,郑老对《中国历史文选》的选目内容亦提供意见,并且担当审稿任务。而当时 与负责《世界通史参考资料》编选的武汉大学吴于廑教授亦有书函往来,了解相关进度 及内容。
由上可知,作为丛书主编,具体负责以下几方面的事情:制定编选原则,明确编选方 针与目的;统筹全书规划,协调各书内容;审查各册内容,使之做到既符合历史事实, 又适用于当时学生的需要。而当时由资料开始,到编选断代史纲要,实际上有一揽子计 划。从组织形式来讲,这是建国以后,全国史学界大规模的一次合作,是一次由上而下 的由中央统一安排,统一调配,用行政命令式的,完成国家的计划,这是计划体制下所 进行的科研活动,其计划性、政治性、紧迫性是其明显的特点。在当时的时代下,教科 书的编撰,政治的需要是第一位的。与当今个体申报项目,国家拨给经费,定期完成任 务的模式是完全不同的。
三、从教材内容上看历史主义的影响
正如前面提及,六十年代初,历史教材的编撰是对1958年“史学革命”的一次否定。 而1958年的“史学革命”具体而言有三大问题:打破中国通史中的“王朝体系”,要写 劳动人民的历史;“厚今薄古”;政治挂帅。(第327页)[4]而王学典先生归结为:“就 是打破王朝体系,打倒一切帝王将相,打倒所有历史上的剥削阶级的‘革命’,是‘见 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的革命。”(第95页)[6]对于“史学革命”的否定,除翦老一 系列论文中进行批驳外,在教材编选内容上亦有相当具体的体现。而就《中国通史参考 资料》和《中国史学名著选》而言,则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以唯物史观对“王朝史体系”的重新塑造。
“打破王朝体系”是“史学革命”的一个根本的观点。他们提出,“在教材中把帝王 将相的活动,统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斗争,以及传统视为十分重要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沿 革都予以删减。”甚至连王朝的称号和王朝本身的历史也要从中国通史中削减或删去, 以“体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突出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7]翦老在 《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的文章中,对这种极左的历史虚无主义进行了批判,他提出 所谓“打破王朝体系”,“要打破的是以王朝为体系的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点,不是 王朝的称号。”因为王朝的称号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是时代的符号。而且“王朝的 称号和公元与世纪一样,并不妨碍我们去发现历史规律性”,而对于要将帝王将相的活 动及传统中十分重要的政治制度沿革都予以删减的说法也进行了批驳,指出所谓打破王 朝体系,“不是用一种简单的方法,如去掉王朝称号和它的始末等等所能解决的,而是 要求史学家对中国历史上的某些带有关键性的问题进行细致的、深入的研究,并且在这 种基础上再对中国历史进行全面的、综合的研究。”这样“才能写出一部不是按照王朝 断代而是按照社会性质分期的中国通史”。(翦伯赞《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8](24 )可见,对于“史学革命”所提出的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
在翦老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和郑老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中,就很好地贯彻 了翦老的思想。作为编选的主导思想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 ,但有很好地契合中国历史。前面五册是以一个时代的历史为单位,将相关的史料编排 一起,后面三册元、明、清则是一个朝代一册。从每册的目录看,可以说是每个断代史 的提纲,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多方面的内容,在翦老看来“经济是历史的骨 骼,政治是历史的血肉,文化艺术是历史的灵魂”,故而书中将方方面面的资料都搜罗 进去,以给学生提供全方位的知识。所以从形式到内容上都是对“打破王朝体系”的一 种否定。
其二,对“以论带史”的否定:将经典著作的内容蕴涵在史实的陈述中。
1958年的“史学革命”中,“以论带史”是其中叫得最响的口号之一。在所谓的“拔 白旗、插红旗”的运动中,史料被看成是无足轻重的东西,甚至等同于资产阶级的史学 ,史料与“白旗”几乎成了代名词,后来干脆宣称“以论代史”。
翦老虽然也反对“唯史料论”、“史料即史学”的观点,但对于“以论带史”的提法 ,翦老“非常厌恶,他到处讲话,作报告”[1](18),反对这个口号。他认为“‘以论 带史’这个口号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因为‘以论带史’的提 法,意味着研究历史要从理论或概念出发,不从具体史实出发。这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 作上的提法是不符合的。”同时批驳了把史料与资产阶级史学等同起来的观点,认为“ 史料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他认为“材料是知识的源泉,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不 应该拒绝历史资料,拒绝历史资料就是拒绝历史知识”。(翦伯赞《目前史学研究中存 在的几个问题》)[8](84-85)
郑老在编选教材的过程中,也发表了《历史科学是从争鸣发展起来的》,指出“理论 和史料必须都要第一手的,不能辗转抄录”[9](306),并且借在北京高校历史系讲课和 做报告的机会,大讲史料的重要性,读书的重要性。而郑老对史料的重视与精通,在史 学界则是有口皆碑的。白寿彝先生评价郑老对史料的重视如是说:
他对于历史资料,提供广泛阅读,力求全面。他提出研究历史,要做到“深、广、新 、严、通”五个字。所谓“广”,就是要求详细地占有材料,以尽可能多的资料为前提 ,提出对历史的看法。要掌握资料就必须大量读书。他在读书时力求把握书中的精华, 反对“浅尝辄止”,或者华而不实的读书态度。(白寿彝《爱国、进步、谨严、笃实》) [10][3]
郑老主张读书要精读,在《自传》中对于如何精读、如何读史料,有详细的论述:
精读要一字不遗,即一个字,一个名词,一个人名、地名,一件事的原委都清楚;精 读是细读,反复地读,要详细作札记;精读一书不是只读一书,是同一时间只精读一本 ,精了一书再精一书。[2](709)
如何读书,如何读史料,是对史料高度重视的一种体现。历史教材以郑老作为《中国 通史参考资料》和《中国史学名著选》的主编,是对郑老熟知中国史籍的一种肯定。而 这两套书正是给学生提供史籍的阅读材料,以加强他们的基本功。《中国通史参考资料 》前言曰: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是全国高等学校分工编选的,主要的目的是围绕中国通史教学 中提出的问题,系统地选择比较完整的原始资料,供高等学校历史系学生阅读,以充实 历史知识,训练阅读能力。(《前言》)[11]
而《中国史学名著选》则是:
为高等学校历史专业课程史学名著选读编写的,目的是在通过选本训练学生阅读古典 历史文献的能力,并略知我国古代著名历史著作的各种体裁和基本内容。(郑天挺《<中 国史学名著选>前言》。)[12]
两套书上都是为大学生有关课程提供教材,最终目的是让学生们学习史料、了解相关 基本史料。在《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中,尽可能全面系统地收集、排比相关史料。每册 书皆收录数十种史料。以每册书末所附录参考书目看,古代史第一册收录75种史料,第 二册收录64种史料,第三册《魏晋南北朝》收录38种史料、第四册74种,第五册125种 ,第六册125种,第七册136种,第八册111种。近代史上册116种,下册89种。凡正史、 实录、编年史、史料笔记、政书、文集、方志、类书、碑刻等等相关史料皆是搜罗范围 ,这样学生可以尽可能地接触相关史料,通过对史籍与史料的学习,从而掌握相关的技 能与历史知识。
《中国史学名著选》选录六种著作,《左传选》、《史记选》、《汉书选》、《后汉 书选》、《三国志选》与《资治通鉴选》,是我国传统史学中几种最基本而最具代表意 义的史书。在编选过程中,每册前面皆附录《说明》,“简单介绍它的内容、体例、写 作经过和通行版本,以及著者的生平、重要著述和学术影响,并说明选本的选录原则。 ”[12]如缪钺1961年7月22日致郑老函中谈及《三国志选》说明言:“《三国志选》前 言初稿已大致草毕,其中分四部分:一,《三国志》作者陈寿之生平;二,《三国志》 撰著情况,书中观点方法之说明与评价;三,裴注之评介;四,本书选录标准、所据版 本及编选体例。”而注释亦有原则。来新夏对《史记选》的选录注释原则解释说:“重 点放在对人名、地名和典章制度等的注释上。注释多据旧注和前人成果,力求简而不繁 ;间存异说,但不广征博引。一般不作语句通释,留待教师在课堂上讲解。”(郑天挺
《<中国史学名著选>前言》[12]可见,对于史书与相关史料进行尽可能的说明与解释, 以利于学生学习。
“史学革命”轻视和反对史料,而历史教科书中却大谈每朝每代的重要史料,作为大 学教学之用,自然是对轻视史料的否定。除此之外,周一良和吴于廑主编了《世界通史 参考资料》和《世界史学名著选读》,充分显示对史料的重视。是对“史学革命”的又 一方面的否定。
其三,对“打倒帝王将相论”的否定:给帝王将相应有的历史地位。
1958年“史学革命”时期,在教学中避免提到历史人物,“有些教师把商鞅变法改为 秦国变法。凡是讲到汉高祖的地方,都用‘汉初’二字代替他的名字。讲林则徐焚毁鸦 片,也认为可以不提林则徐的名字。甚至讲儒家学说,有人不提孔子。”而前面提到在 编选《中国史学名著选》时候,史家有“四怕”,其中心内容就是怕选帝王将相,因而 担心犯错误。翦伯赞公开主张,“全面地讲述历史,应该是在肯定历史必然性和人民群 众是历史的主人的原则下,承认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因此在讲述历史时,就不必 避免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的名字,包括帝王将相在内。”[8](37-38)
六十年代初,历史教材编纂时,尽量避免“史学革命”的错误。对帝王将相给与应有 的地位,即以《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和《中国史学名著选》为例,既不回避帝王将相, 也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叙述政治史时,帝王将相的传记资料多有摘录。在当时 不太注重知识分子的时代,却特别注意收录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的相关传记材料, 这相当难得。例如《魏晋南北朝》册,收录了数学家刘徽、祖冲之,历算家何承天、张 子信的史料。《隋唐五代》册,对韩愈、刘禹锡、柳宗元、刘知几、李白、孙思邈等有 关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的传记资料皆录入。《宋辽金》册,则收当前了朱熹、陆九 渊、陈亮、欧阳修、苏轼、辛弃疾、司马光、郑樵、李心传等文、史、哲大家的传记资 料。这难能可贵,自然也是对“史学革命”的一次否定。
而《中国史学名著选》中,从上面所引的郑老与诸史家的信函中看出,郑老特别指出 应当收录一些重大人物的传记。在郑老所作的《关于编选<中国史学名著选>之意见》中 特别提出八项内容:
1,特定内容:如春秋时代的列国争霸;2,主要制度:如叙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的《 食货志》;3,重大事件:如商鞅变法选《史记·商君列传》,赤壁之战选《三国志· 周瑜传》,农民起义选《史记·陈涉世家》;4,突出的生产技术和科技贡献:如《三 国志·华佗传》;5,哲学文学的成就:如《汉书》选《董仲舒传》,《后汉书》选《 王充传》;6,少数民族事迹:《史记》选《匈奴列传》、《三国志》选《诸葛恪传》 ;7,历史任务:如代表一个时期的,如项羽、汉武帝;8,特有体裁:如《史记》《世 家》、《十二诸侯表》,等。[5](507-508)
最终具体落实到《中国史学名著选》的内容则是:“选本重点选录名著的代表作品, 包括它所反映的这一特定时期的主要典章制度、重大历史事件、杰出人物的活动、科学 技术的发明与发现、文化思想流派和民族关系等内容以及著者的历史观点。”[12]一共 七个方面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杰出人物的活动、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发现、文化思想流 派和著者的历史观点四项内容都涉及具体的历史人物。
综上所述,六十年代的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以具体的行动对1958年的“史学革命”进行 了有力的回击,对于“史学革命”所提出的口号——进行反击,最终取得了应有的成绩 。而在人员的使用上,实际上也是对“史学革命”的否定。“史学革命”中,提出不要 先生,不要专家,而1961年的文科教材编纂,组织的都是全国第一流的专家,编选者皆 是某方面或某断代的最为权威的学者,实际上是专家著述,与1958年学生教育老师,群 众领导专家的做法自然是一种否定。
四、余论
1961年4月开始的文科教材编纂,到1966年“文革”前,共编出大学文科教材五百余本 ,而历史类教材也有五十余本。事实上,1965年底,编撰者就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 当时戚本禹在《红旗》13期上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不点名地批评翦伯赞、吴晗 的历史观,主张历史研究危险是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1966年3月24日,戚本禹 在《红旗》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把翦伯赞的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说成是“两 篇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文革”一开始,文科教材办公室就被撤销,自然教材 的编撰计划就全部停顿。翦伯赞及其历史主义又成为被攻击的靶子,思想被批判,人身 亦受到攻击,最终翦老于1968年12月,以死抗争,表现了一代史家不屈的风范。“文革 ”以后,《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和《中国史学名著选》等文科教材相继得以完善和出版 ,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大学生学习的主要教材,使其价值得以体现,至今依 然值得学术界重视。
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这次历史教材编纂的前后时代时,我们不能不慨叹老一辈史学 家的艰难与不易,在政治与学术混为一谈的时代里,政治挂帅、统治一切的时代里,学 术也只能庸俗化,只能依傍在政治的臂膀里,苟延残喘。学术失去了空间,失去了应有 的自由,苍茫大地上只有一片萧条,何来万紫千红的学术春天?好在这样的时代已经过 去,改革开放以来,真正迎来了学术的春天,当今中国的学术正沿着应有的规律,向前 迈进,在世界学坛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收稿日期:2002-1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