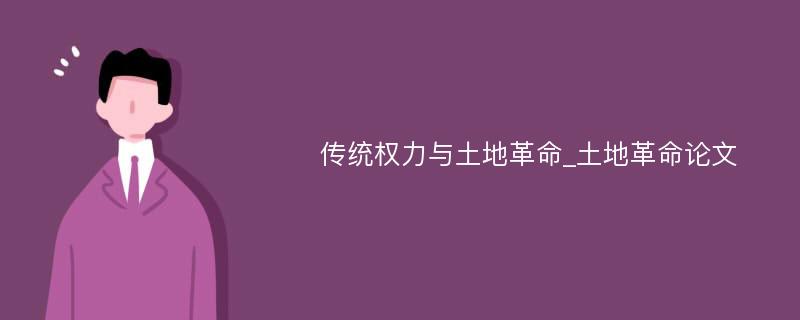
传统势力与土地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土地革命论文,势力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5.03.007 本文所指的传统势力主要是指宗族势力、地方势力(地主豪绅)和地方主义、传统思想等。这些传统势力在中共的纲领或决议中,是明确宣布必须废除的,且在革命斗争之下必然会彻底消除。然而革命实践与革命政策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距离,即这些传统势力以顽强的姿态阻碍土地革命,其消极性远远超过中共的理想预期。这种政策与现实的较大偏差迫使中共中央不得不调整策略。在中共积极的革命应对情况下,中共才逐步开始掌握土地革命的方法和策略,在此基础上推动革命的展开,继而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目前学界而言,黄琨、王奇生、陈德军、何友良等学者对宗族势力、地方主义等与中共革命的关系有比较深入的分析,①但尚缺乏对传统势力与土地革命的关系的全面论述。本文试图通过论述传统势力在土地革命中的多层次阻碍作用,来客观反映革命斗争的复杂性以及革命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重要性,并且通过考察中共对传统势力的利用等方面,以折射中共革命应对的灵活性,从而在更为客观的层面来展示土地革命的艰难,以及中共的革命智慧。 一、中共革命思想与农村社会的传统观念不相容,导致它的社会渗透难以深入 (一)中共中央的革命预期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确立了苏维埃革命(土地革命)的道路。苏维埃革命要求废除传统势力和落后思想,建立工农民主专政。这一革命理论在土地革命初期予以明确。苏维埃革命方针确立之后,中共中央就要求在传统势力强大的农村,中共领导的农民斗争应该坚持“不交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的方法,立刻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迅速歼灭豪绅,分配土地。②对农民迫切的土地要求,中共中央认为农民与地主势不两立,必须毫不客气地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旧时田契佃约一概宣布废除。③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乐观估计,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可以使地主阶级的经济政治地位发生根本动摇。④随后不久,中共中央在关于湖南全省暴动的决议案中,更是激动地表示在一些暴动地区“豪绅在乡村政权已完全被农暴打溃”。⑤换言之,通过农民暴动,地主豪绅等传统势力毫无疑问会被消除。1928年6月,中共“六大”决议案对革命形势的分析更为客观,但对消灭传统势力的彻底性仍然持肯定态度。它认为,“为了要完全消灭中国农村中所有的封建遗迹,为了要让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尽量发展”,中共必须推翻豪绅地主官僚的政权,解除反革命势力的武装去武装农民,建立农村苏维埃政权。⑥要言之,土地革命之初,中共中央依据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借鉴苏联革命模式而确立的革命设想,对农民暴动充满了激情和乐观,对传统势力的强大和顽固性估计不足。 实际上,传统势力在多层面阻碍了中共土地革命的推行。从浅层次地来说,它使中共革命思想的传播陷入困境;从内部而言,又消极影响了党政军建设;从动员和军事斗争上看,又阻碍了土地分配和革命战争的顺利推行。 (二)革命思想渗透的困难 要开展土地革命,必须使农民认识中共的革命思想。在宣传中,中共在暴动早期过分强调了农民生活的艰难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强烈革命性,即似乎只要中共到农村一呼应一发动,农民就会跟着起来闹革命。但事实却是很多农民要么毫无反应,要么革命受挫后又缩回以前的状态,要么左右摇摆,敢于彻底干革命的农民并不多。革命思想渗透不深的原因之一,就是传统理念与中共的革命理论具有不相容性或抵触性,以及传统思想具有历史持久性。 传统理念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宗族思想。宗族的存在形式已经成为民间习惯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族思想几乎深入农民的精神灵魂,宗族势力在社会中起着很大的作用。⑦正因为宗族的存在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所以导致阶级斗争主张在农村的传播遭到很大的抵制。关于农村宗族势力和思想的普遍性,在中共的报告中屡见不鲜。江西省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典型区域,其宗族势力的影响力尤其大、宗族观念深入人心。⑧福建作为沿海省份,这一现象同样普遍。根据福建情况的报告,甚至在土匪和工人中都存在家族式或宗族式的组织方式。⑨宗族思想在客观上与阶级斗争主张不相容,因为阶级斗争要求农民必须彻底废除宗族势力、思想,以无产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其传播的艰难性不言而喻。1929年2月25日,杨克敏在其《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对中共宣传工作的困难进行了精到的阐述。他说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一切落后,封建宗法思想充满乡村,农民做梦也想不到机器工业是一个什么样儿,是一回什么事,帝国主义到底是一回什么事,因此,实在很难使农民有进步的思想发生。”⑩可见,宗族思想不仅成为农民文化的一部分,而且也成为中共推广阶级斗争理论的障碍物。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不得不感慨“非有—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11) 与宗族势力相联系的是地方主义。这一传统势力在农村中具有很大的影响。毛泽东担忧地指出,由于受地方主义影响,一般群众和党员很难接受共产党的主张,“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指农民)也是不大懂得的”。(12)尤其在江西省、湖南省等地,不仅有一般的地方界限,土客籍斗争和观念也很严重。1929年4月4日,彭德怀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地域界限意识在群众甚至在一般党员的脑海中根深蒂固,虽然经过革命宣传和洗礼,但这一现象并没有得到消除。(13) 农民不仅阶级观念非常淡薄,而且对地方势力即中共所要革命的对象——地主、豪绅还有很高的信仰。这一思想不仅存在于革命之前的社会,还存在于中共宣传和开展革命的过程中。无疑,它造成中共的困扰,也使革命思想渗透难以深入。关于农民信仰地主豪绅的情况,各省都有。1929年,江西省委指出,有许多地方的农民竟然一举一动不能不自觉地得到统治当地的豪绅的允许,为此,它无奈地承认“这些都是农民运动的很大的障碍”。(14)实际上,江西各地都有农民崇拜地主豪绅的现象。泰和农民“崇拜老土劣”(15),而南广县的地主富农“在乡村中的威权依然存在”(16)。即使在赣北的苏区,根据一般群众心理仍然可以看出“实在一般豪绅地主的势力还蕴藏在群众中间的,并没有彻底肃清,并且时时有死灰复燃的可能”(17),农民不愿意与地主豪绅为敌。在这一情况下,中共要宣传阶级斗争,号召农民起来杀豪绅地主,必然要遭到农民的冷眼。 农民的保守思想和封建习俗的约束同样严重。主要表现为对革命的动摇、犹疑、观望、害怕,希望尽早结束战争过和平生活。这种思想在革命看不到很大希望时尤其突出。1928年初,福建平和县在暴动后遭到敌人猛烈反击,农民抵挡不住压力,很多人纷纷出逃,“虽用极好宣传,亦无法一时安定人心”(18)。1928年初,桂系军阀打入陆丰县,农民受到极大的伤害。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领导农民向敌人斗争的努力仍然成效不大。很多农民“发出幻想妥协,以祈不罹白色恐怖之祸”、“表示得过且过,红旗、白旗均可以”(19)。可见,农民对革命思想的接受有一个艰难的过程,其思想中固有的保守观念阻碍了革命思想的接受。封建习俗对妇女的约束最为明显。很多妇女不仅社会地位低,而且对其参加革命运动,社会上抱有偏见,认为其发挥不了多大作用。(20)很多亲历妇女工作一线的中共干部对此也深有体会,说到:“我们教育妇女时,发现妇女工作很不好做。我们的爱好习惯、文化水平与这些农村妇女相去甚远,以至于很难找到与他们相互沟通的渠道”(21)。可见,妇女在封建习俗约束下对革命思想很难接受。 二、传统势力的强大和顽固性,使得中共的党政军建设难以顺利进行和迅速取得成效 传统势力不仅浅层面地阻碍了中共革命思想的传播,更深层次地滞碍了中共内部的建设,导致党政军建设难以按照预期的速度和深度开展。这一现象在土地革命初期尤其明显。地方报告时常谈及这一问题,中共充满了忧虑。 (一)党建的封建性残余 传统势力对党的建设产生消极影响,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各地党的文件都有所反映。其主要表现为: 其一,党的组织建设具有强烈的封建色彩 1929年2月,杨克敏在关于湘赣边苏区的报告中详细阐明了党的缺点,指出“农民党的色彩特别浓厚”,其“地方观念、保守思想、自由散漫的劣根性”非常多;此外,延续封建社会征兵时的做法,竟然“公开的用拉夫式的‘上册子’办法征收党员”;由于受封建专政思想的影响,在党内也遗留了“个人专政,书记独裁”和“崇拜个人、英雄”的恶习。(22)这一情况导致党的组织不牢固,成分混杂,民主集中制也无法真正实施。 由于根据地在农村,中共党员也基本以农民为主,而这些农民党员的思想意识往往是家族式的、地方主义的。毛泽东对此有着精辟的阐述,他指出: 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23) 可见,党的组织由于受制于家族式的社会构成,俨然也变成了家族式的党组织。在这种情况下,要打造“布尔什维克”的党自然困难。 由于党在征收党员时用“拉夫式”的方法以及家族式的党组织构成,这就给土豪劣绅、地主等传统势力制造了可反击的机会。1928年7月1日,中共海丰县的报告就指出了这一问题,认为由于入党条件放得太低,导致党员“只有数量增加,质量并没增加”,不得不进行整党,淘汰地主豪绅等投机革命的人。(24)1930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在其决议中也指出,地方党部“充满了豪绅地主分子”,要求“对豪绅地主富农分子应在工作过程中坚决的毫不迟疑的肃清”。(25)即使在开展革命比较顺利的赣东北根据地,这一情况到1931年也时常发生。一部分地主富农甚至“站在党的领导地位”(26),因此,改造党成为必然之举。 其二,封建思想意识渗透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 由于根地处在农村环境,农民的各种封建思想也带进了党内,影响了党的思想建设。各地的报告相继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说明。1931年4月,闽北分区委检阅过去工作的观点,指出:“同志及群众的农民意识还依然很浓厚。整个的党与群众,依然在家族主义地方观念的封建领域中讨生活。”(27)赣西南根据地同样如此。党内农民意识“笼罩一切”,地方界限尤其突出,吉安西区等地出现了排外风潮(28),安福的同志反对永新在安福工作的同志,固江的土客籍界限闹得利害(29)。赣东北根据地的情形类似。由于党员成分中农民占多数,所以“党内充满着农民意识”,在工作中“具有浓厚的地方保守观念”(30)。简言之,党内的农民意识已经严重影响了党的思想建设,造成了党内思想的混乱,不能从根本上确立马列主义思想的绝对领导地位,影响党的工作能力和队伍素质的提高。 封建思想同样影响了党的作风建设。1929年,闽西特委在其政治决议案中认为地方主义等观念影响了党的作风,指出“一些同志对整个部队或某个同志不满意,不运用组织的方式去解决,很随便的在群众中公开宣布,引起群众对整个部队的不满意”。(31)可见,党的作风受到了封建意识的严重影响,造成了工作作风上的落后。 其三,党在群众中的信仰削弱 党建的薄弱不仅影响了党本身的巩固,也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此外,由于封建传统势力的阻碍,革命思想无法在农民中得到认同。这两方面的作用都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削弱。1929年9月6日,刘作抚在其关于赣西情形的报告中,阐述了党在农民中威信很低的现实。报告说到:“在吉水曾发现少数农民,因为他们有国民党的‘从前国民党宣传何等漂亮,而今国民党得到政权我们的利益又在何处?不理我们,压迫我们!’共产党也还是一样的宣传,将来得到政权还是与国民党一样的。”(32)可见,由于党本身工作的问题无法使农民信服,造成了他们把中共等同于国民党的误解。这很不利于革命的开展和党的威信的树立。 (二)传统势力对中共政权建设的反渗透 传统势力不仅对中共领导的苏维埃政权进行阻扰甚至破坏,封建思想也影响了政权内部的建设。 很多地方都有地主豪绅混进苏维埃政府的报告。这一情况严重地影响了中共政权的威信,不利于政府职能的实施。造成这种现状的大部分原因就是地主富农在农村的势力还很大,农民对他们还有一定的信仰或者说敬畏。1928年,毛泽东对此有生动的描述。他说:“初期的政府委员会中,特别是乡政府一级,小地主富农争着要干。他们挂起红带子,装得很热心,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使贫农委员只作配角。……这种现象虽不普遍,但在很多地方都发现了。”(33)杨克敏关于湘赣边情形的报告印证了毛泽东的话。他指出,由群众选举产生的苏维埃政府,“有许多投机分子、小地主混进里边来”,所以,“要求真正的贫农为基础的薄弱苏维埃,是不可能的”(34)。显然,地主豪绅富农受各种原因驱使,尤其是权力观念的驱使,试图抢占政府的领导权。这无疑对中共的政权造成极大的冲击,削弱了政权的工农性。 关于地主豪绅等地方势力的权力欲望、抢占中共政权的行为,共产国际进行了论述。它认为: 开始时苏维埃政权使人害怕,现在对于富农和豪绅来说并不太可怕了,因为富农和豪绅利用我们斗争和建设中的许多缺点,往往热情地欢迎苏维埃政权,欢迎红军,建设苏维埃,当然从中获取好处。富农们常常掌握主动,控制苏维埃机构甚至控制党。……他们学会了利用苏维埃政权,利用在规模如此宏大的运动中自然会出现缺点和不足。(35) 可见,地主豪绅等传统地方势力在中共的革命斗争下,并不是坐以待毙。他们利用了苏维埃政权出现的弱点,去掌控政权,以保持原有地位。 地方主义、宗族等观念也影响了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和稳定。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苏维埃政权一旦得到外来居民的支持,那么外来居民就对本地人进行报复、杀害;而苏维埃政权一旦得到本地居民的支持,那么他们就杀害外来人。(36)这种现象毫无疑问对政权稳定不利。有些人基于传统认识,认为苏维埃政府与以前的政府一样,都是与老百姓隔离的,甚至认为“苏政府杀人非常厉害”,导致“有话不敢说,有事不敢做”。(37)对政府认识的模糊甚至误解必然造成政权建设和工作开展的困难。即使是政府委员也是封建思想遗留严重,阻碍了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建设。 (三)军队建设的传统观念 “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阻挡了中共扩军的步伐。各根据地都有类似的报告。1930年6月8日,信江特委在其报告中,担忧地指出“正在扩大红军的组织当中,士兵要求请假归田的很多,同时民众都有不愿为士兵的倾向”(38)。福建省等地出现了农民“鄙视士兵”甚至“仇视士兵”的心理(39),群众“怕当红军的情绪非常浓厚”,很多人为了不当红军甚至逃到外地做工,远渡南洋,或者假装生病(40)。农民的这种传统观念对中共的扩红工作必然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此,很多根据地都出现了旧社会“拉夫式”的扩红现象。赣东北等根据地由于用“拉夫招兵”的方式进行扩军,结果“在群众中竟发生‘逃兵’不愿当红军的现象”。(41)闽西等地为了完成指标,甚至用旧社会常采取的“强迫、指派、抽签、轮流、雇佣、欺骗”等方法进行扩红,从而导致“豪绅、地主、富农分子也来当红军,流氓、罪人、动摇分子送到红军”的现象。(42)换言之,传统观念仍然阻碍了中共军队的发展和内部稳定。 在红军内部,也出现了各种不利于军队建设的封建传统思想。很多士兵有很严重的雇佣思想,他们基于传统思想,认为当兵是赚钱,是混饭吃,“仅仅对长官个人负责任,不是对革命负责任”(43)。赣东北等地的红军内部甚至出现了“分等级的制度”(44)。红军内部也存在地方观念,不愿意跨区域作战,不愿意离开家乡。这些思想对军队的影响无疑是消极的,削弱了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三、中共的革命斗争遭遇传统势力的阻击和反抗,时常陷入困境 中共要在农村发动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彻底消除传统势力,传统势力也不可能善罢甘休,而且农民也没有立即投身革命的热隋和勇气。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斗争必然陷入各种危机。中共代表杨克敏的话很具说服力,他认为革命的原素在乡村要弱于封建势力,“封建宗法的势力要较革命势力雄厚”,即使在革命已经开展不错的地方,也是“一个封建势力与革命势力对峙的局面——一方面是苏维埃的政权,一方面是潜伏的豪绅地方的势力与公开的白色势力”(45)。可见,处于斗争中的中共党员已经开始认识到,在农村始终存在革命势力与封建势力的斗争,而封建势力还往往具有—定的优势。正因为如此,中共在农村的革命总会遭遇各种困难。 其一,地主豪绅势力对革命进行抵制 地主豪绅势力并不甘心中共来革自己的命,必然要用各种方法和手段来进行阻止,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准农民参与革命,试图维持自己的威权和势力。 在根据地建立之初,革命遭遇到地主豪绅的顽强抵抗。弋阳、横峰等地的豪绅针对中共的革命宣传,进行了反革命宣传,使农民对中共革命产生了怀疑,不愿意卷入中共的武装斗争,从而导致革命势力陷入孤单的境地,工作不易扩大。(46)在东江,情况也一样。地主豪绅对中共革命进行特意歪曲,“大造谣言谓本党要杀老人小孩及一般妇女,作浪兴风”,使农民不愿意接受革命理论。他们的这一宣传也有一定的效果,很多农民“受反动派之欺骗而反对本党(即共产党)”(47)。当然,其行为背后的原因是“地主豪绅见着革命民众觉悟起来于己不利”。反革命宣传是地主豪绅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手段,用来抵御中共的革命宣传,保持自己的话语权。 农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了对地主豪绅的某种信仰,而地主豪绅利用这种威力反击中共的革命。广东紫金县在革命暴动之初,农会几乎都被“一班聪明小地主豪绅所把持”,这些人除了夺取群众,还对革命势力进行内部消灭,杀害部分革命群众。(48)即使在赤色县——海丰,地主豪绅也想方设法进行革命破坏,常常利用“农民传统之观念在农民背后之唆弄”,使农民之间起纠纷,互相打斗。(49) 地主豪绅即使到了革命队伍,也不能排除他们会因为利益的丧失等问题而退出革命队伍或武装叛变。闽北地区崇安县革命领导人左诗瓒的叛变就是一个例子。他起初参加革命,并不能说完全是投机,但“革命的发展与党的工作的转变已经和他个人的地位和利益发生了冲突”,再加上父亲、兄长的强烈反对,以及身边地主富农出身的人鼓动,他毅然叛变了革命。(50)他们的叛变对革命的损失是很大的。 其二,农民内在的封建思想顽强抗拒中共的武装革命 实际上,除了地主豪绅的鼓动,农民自己也有自己的顾虑,内在的封建意识已经长久主宰了他们的思想,想要一时根除绝非易事。农民的这些封建意识顽强抗拒中共的武装革命。他们想过着无动乱的日子,不想生活发生变化。 武装暴动之初,中共在陕西的活动因为群众的不支持,陷入孤立的境地。中共不仅不能得到群众的响应,而且“群众反有反对我们的危险,至少亦不喜悦我们与他接洽”(51)。中共在当时是“造反”派的代表,群众基于长久以来明哲保身的思想,不愿意与中共为伍。即使在革命暴动发展迅速的江西省,很多农民仍然不想“跨雷池一步”。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感到必须要斗争,但总是害怕政府的镇压、革命失败后的迫害,此外,也不愿意放弃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农耕生活方式。有些地方的农民甚至向中共“请求停止斗争”。(52)福建的永定县是闽北地区发动武装暴动较早的县,中共在其武装斗争过程中,也强烈感到群众不仅对中共“毫无认识”,而且“苟安的心理”很普遍,甚至“与反动民团妥协”。(53)农民对革命的淡漠有其思想基础,诚如学者王奇生所指出的一样,“对当时大多数农民而言,拥护阶级斗争或革命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54) 其三,宗族、地方矛盾与阶级矛盾相混淆,阻碍了阶级斗争的发动 因为宗族和地方势力的普遍,在农村比较表象的矛盾就是宗族矛盾和地方矛盾,这两个矛盾还时常交叉在—起。这两个矛盾是农民能亲身感受到的,而中共所要揭示的阶级矛盾对农民而言,则往往过于抽象或难懂。在农村开展革命经常遇到的情形是宗族矛盾、地方矛盾与阶级矛盾混为一谈,把阶级斗争演化为宗族、地方之间的械斗。 宗族势力过大,使阶级斗争的发动极为艰难。赣东北的乐平,因“封建势力过于利(厉)害”,导致“均在宗族关系之下去作斗争,很少普发乡村的阶级斗争”。各村都被地主豪绅把持,农民遇到什么问题他们都要过问。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自然比较难于发动”(55)。井冈山等地区土客籍矛盾突出,地方主义根深蒂固。土籍和客籍学生不能进一个学校念书,土籍人把客籍人看作是外来户,低人一等。土客籍矛盾的突出性,“把阶级矛盾掩盖着”。而且豪绅地主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常常利用“这个矛盾挑起械斗”,以“破坏革命势力”(56)。毛泽东也痛心地指出,土客籍之间时常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而敌人善于利用这一矛盾来挑拨群众关系和党群关系。(57)这当然不利于开展革命的阶级斗争。 其四,封建武装组织与中共争夺势力范围和群众 由于农民长期以来受封建神明思想的影响,他们建立的武装很多都带有神秘色彩。这些武装在农村具有较大的势力,在农民心目中也有较高的地位。农民对红枪会、大刀会、三点会、盖天党之类的封建武装组织并不排斥,甚至还有很高的信仰。江西的吉水县民众“信仰红枪会”(58),泰和县民众则“很迷信神道”(59)。安徽徽州普遍存在三江、义会的流氓组织,这种组织不参加生产劳动,专门“以赌博吃饭”,而且“差不多劳苦工农及保卫团的士兵,不在此组织的很少”(60)。即使到了1934年,这一情况也没有大的改变。在川陕苏区,敌刘湘竟然还能利用“红灯教、神团、盖天党、孝义会、扇子会等反革命团体欺骗穷人”(61)。也就是说,这些武装具有较大的封建性,与中共的革命武装具有较大的区别。 由于许多群众对中共的认识不清,加上这些组织的特意拉拢或强迫入会,很多人都加入了这些组织。大刀会、三点会等基于自身的利益,认为中共搞革命,是与其争夺地盘、群众和资源,为此,对中共产生了敌视心理,他们与中共展开了争夺势力范围和群众的斗争。在川陕,盖天党对中共的诸多政策都不认同。他们对群众宣传“红军不红,红军是混闹,只有盖天党才是真正的救大家”,“土地改革不合理,哪能轻易把土地分给别人”。在强势的宣传下,他们又强迫群众参加盖天党,实行“一人不参加杀全家,一家不参加杀全族”的政策,同时,又用“神水咒符”对农民进行迷惑。(62)在宣传和武力的双重作用下,很多农民都被迫加入了盖天党。此外,很多农民由于没有革命思想的指导,为了反抗反动政府,习惯性地组织封建武装。例如,陕北清涧、横山、安定县农民在发动抗粮斗争后,因没有找到红二十六军和共产党,竟然在横山县成立红枪会。(63)要言之,中共的革命斗争阻力一部分来自传统武装的争夺。 四、艰难处境下的革命政策调整:中共的革命应对 土地革命初期,传统势力展现出来的强大、顽固性以及破坏性,迫使中共不得不立足于客观现实,适时调整策略。尤为重要的是,中共在革命实践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传统势力的消极性远超预期,但并非不可利用。简言之,传统势力在特定的情况下也能发挥特定的功效,使中共的革命以一般民众能接受的方式进行,取得意想不到的成效。鉴于此,中共中央不再囿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阐释,而站在了更为客观、实际的角度来思考土地革命展开的问题。对传统势力,中共虽然在理论上持反对态度,认为传统势力必须废除,但在具体实施上,又不得不做出调整,提出可以适当地利用这些关系,以使革命顺利进行。正是这种积极灵活的革命应对,中共的土地革命才得以逐步展开,并在各地建立农村根据地。 (一)处于传统网络中的地方革命领导者利用其势力地位,树立革命威信,动员农民参与革命 中共要在陌生的农村开展革命并不容易,尤其在土地革命初期,其一,语言不通;其二,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一个陌生人闯进来,十分显眼,容易受到排挤,要隐蔽开展斗争几乎不可能;其三,外地人不了解当地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很难开展工作。即使在革命开展相对好的时期,外地干部也很难在当地立足。陕北地区十分缺乏革命干部,陕西省委就派遣了一部分干部帮助其开展工作。但是,事实却很无奈。由于省委派去的一部分人都是外地人,“到处没办法站足,农村中语言上的困难”(64)。其他的中共党员也反应了这一问题。1930年5月12日,金贯真在报告中要求中央派干部,一定要派本地人,指出“普通的还是不派好,因语言关系恐在工作上反有阻碍”(65)。看来,外地人无法在当地开展革命工作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鉴于这一因素,中共在土地革命初期主要是派遣党员回原籍开展工作。尤为重要的是,在当地有名望或有地位的革命领导者还可以利用传统社会资源进行革命斗争。因为他们在农村具有势力地位,其投身革命的行为对农民而言具有很大的激励作用,在农民中间树立了一定的权威,从而拉近他们与农民之间的关系。 方志敏是回到原籍开展革命取得成功的实例。方志敏所在的方氏家族是大族,在弋阳很有势力,与县政府的多个部门有关系。方志敏充分利用了这些传统社会资源,其革命行动减少了诸多阻力。他可以相对公开地进行革命,把自己的亲戚朋友、关系较好的村民拉进自己的队伍。之所以能迅速号召不少村民参加革命,与方志敏所在的家族势力大密不可分,因为农民更愿意跟着有势力的人干事,觉得成功机会要大得多。革命亲历者阎红彦也指出,晋西游击队之所以早期能在陕甘高原开展斗争,重要原因就是“晋西游击队中的干部大部分是陕北人,也是一个有利条件”(66)。贺龙在湘西的暴动同样发挥了自己的社会资源优势,号召的很大一部分人都是他的绿林弟兄。革命中的诸多例子表明,要在农村开展革命,拥有本地的社会资源是一个优势。 在革命实践中,富有家庭出身或有家族势力的革命领导人更容易取得农民的信任(67),更易开展斗争。在兴国,民众的姓氏观念极为浓厚,而肖姓在本县是大姓,极有势力。兴国革命领导人肖华承认这种姓氏关系有效地帮助了革命势力的生长和发展,认为这是兴国革命运动顺利发展的原因。赣西南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曾山也说,其所属延福地区在革命初期阶段,参加革命的多是青年学生,有不少的青年知识分子党员家里有钱、有很多土地。(68)受家族主义等思想影响,很多地方全族或全村参与革命。在赣北等地的村庄,就出现过“全族加入农协”的情况(69)。广东等地也出现了“革命乡村”(亦称“共产村”、“赤色乡村”)(70)。 要言之,传统势力对中共土地革命的开展主要起了阻碍作用,但是它也有可以利用的价值。从各地开展土地革命的情况看,处于传统网络的地方革命领导者凭借其本身的势力地位,减少了不少革命阻力,更为有效地动员农民起来革命,并较快树立自己的革命威信。 (二)传统组织方式为中共提供革命动员的一种渠道 对农民进行革命动员是在农村开展革命极为重要的—环。革命动员的重要性也已经在中共的各项决策中有比较清楚的论述。要进行革命动员,对农民进行革命思想的洗礼,并不是那么容易。农民是一个受传统思想影响较深的社会群体,要他们接受中共的革命思想,进行暴力革命,必然要采取农民所愿意接受的方式。传统组织方式有较强的封建性,但又有较大的群众性,因此,对其进行合理利用也成为中共的权宜之举。 中共的革命指导者——共产国际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也逐步趋于理性。1928年2月25日,共产国际就提醒中共应注意群众的说服工作和教育工作。它指出“只有说服群众,使他们相信党所提议的方法之正确,只有取得群众中之绝对的赞助和完全的信仰,才能指导运动”,并“有系统的日常不断的执行提高群众阶级意识的工作,指导他们的日常斗争,组织他们”。(71)至于动员群众的方法,共产国际在中共“六大”上提出必须利用工人中的兄弟会及其他半封建式的组织,认为“真正革命者乃是能在任何困难条件之下,仍能钻到各个地方去”。(72)共产国际的指示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即必须对农民进行阶级思想教育,并可利用封建式组织传播中共革命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革命理念才能被广泛接受,并把广大的工农动员起来。 与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相一致,中共也一直在探索革命动员的途径和方法,试图利用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封建组织,把工农大众团结起来。1929年初,中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其决议案明确提出,“至于豪绅利用封建关系的农民组织,亦必须打入进去,发动斗争夺取其群众,消灭反动领袖,改变封建团体为阶级组织。”(73)也就是说,基于现实的考虑,对封建性质的组织进行利用,在中共方面,有了一定的认可。 在革命暴动之初,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利用农协的名义进行革命动员,但由于农协的革命色彩浓厚,很多农民不愿意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党组织灵活采用了农民的传统组织方式,如农民兄弟会、互助会、拳术馆、铁血团等(74),以代替农协来开展革命工作。在赣东北,方志敏采用了农民革命团的组织方式。农民革命团作为群众武装组织,充分利用了农民的一些传统心理,含有一定的封建性。在成立仪式上,成员必须在红纸名单上画押,喝鸡血酒。(75)每个团员都要宣誓,要忠诚于革命事业要遵守如下公约: 1.绝对保守秘密,不得走漏消息; 2.利用亲邻关系,秘密发展新团; 3.利用打猎名义,各人准备武装; 4.大家齐心协力,听从上级指挥。(76) 从其公约内容看,“利用亲邻关系,秘密发展新团”,实际上就是利用农村的传统社会关系,以亲帮带的作用,来发展革命力量。“以打猎名义”无疑也是传统社会生活的写照。应该说,这种带有一定封建性的武装组织极大地迎合了群众的心理,拉近了革命者与农民的距离,有利于发动农民起来革命。这是赣东北革命斗争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 与此类似,江西省寻乌县党员利用太平天国时期“三点会”组织发动群众。(77)在湘鄂赣,鉴于农民害怕入农协将遭到迫害的心理,中共利用“很灰色的团体名义,如禁赌拒毒,以及什么菩萨会的名义”(78),对农民进行组织动员。在安徽的徽州,中共利用兄弟团的名义,去夺取三江、义会组织的群众,以对他们进行革命思想的改造,“必使他们认清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土豪劣绅、大地主、资本家”(79)。在陕甘边,中共同样对哥老会、红枪会、软扇会等封建组织进行了利用和改造,争取它们的群众。(80)在福建的永定县,甚至用铁血团的名义对农民进行革命组织。(81)这些组织都是当地农民所熟悉的,长久以来为农民起义所经常采用的。中共利用了它们的形式,并对它们的内容进行彻底改造。 这些带有封建性的组织在农民中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农民更加乐意通过加入这种组织来进行革命工作。其原由一方面是长久以来的传统思想,另一方面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贵溪的周坊起义对此进行了有力的说明。1928年初,中共派邵忠、邵棠到贵溪周坊做起义工作。在他们的鼓动下,不少人有闹革命打土豪的决心。但是,通过何种方式来组织农民,让他们犯难了。在与穷苦农民商议之下,邵棠提出,发动农民组织“十三太保”、“二十四大王”,还有“九友结义”和“一百单八将”。这些组织,虽然其内核是革命性的,但从外表看来是单个的封建小团体。这些组织很受欢迎,符合了农民即想革命又不愿意过于冒险的心理,也与农民的传统文化保持了一致,因此加入的人像潮水一样,一个周坊村,只三四天的功夫,就有五分之四的贫苦农民参加了“十三太保”“一百单八将”或“九友结义”等组织。(82)中共通过建立兄弟会、猎户团、反日会等组织,宣传党的政治主张,目的是“将广大劳苦工农群众完全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83)这些组织在中共的领导下,逐步加以改造,成为革命性组织。农民在其过程中也不断地接受革命思想的教育,成长为革命者,响应中共革命。 即使在革命宣传方面,同样不能脱离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中共经常都要利用农民的传统聚集方式进行宣传工作。1929年8月16日,中共漳州县委报告指出,“乡村亦须尽可能的利用‘墟日’及‘神日’等机会公开宣传,鼓动斗争”(84)。在南方,庙会是农民最喜欢的娱乐节日,中共也利用这个机会开展演讲,扩大其思想影响。 (三)传统武装组织为中共的革命斗争准备一定的条件 虽然传统的群众武装组织带有浓厚的封建性特征,但也呈现了一定的革命性,在有些地方甚至成为了农民反抗强权社会的主要形式。对农村社会的这些武装,是彻底消灭或置之不理,还是对其利用,成为了中共不得不认真思考的现实问题。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总体战略上并不看好这些武装,认为其反动性占主导,必须予以消灭,但鉴于革命开展的困难,又认为要理性利用它们,即一方面夺取它们的群众,另一方面把它们改造成为中共掌握的革命性武装组织。(85)在其思想的指导下,各地的共产党基本上对传统的武装进行了拉拢与改造,使其为中共的革命服务。基于上述策略,这些传统武装组织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共的武装革命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各地的执行情况基本没有违背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的策略。江西、福建、陕西、湖南等地都有哥老会、三点会、大刀会、红枪会等这类武装组织,中共地方组织对它们进行利用改造,也是适应革命实际的必然举措。 1928年7月19日,福建省永定县制定太平里秋收暴动计划,要求把部分小刀会等他们认为的“土匪”武装实行改编,以“作为暴动的一种付(辅)力”。(86)莆田县部分农民在中共的大力宣传下,利用自己的传统武装,进行了反捐税斗争。在此斗争中,中共试图引导农民走向武装暴动,但由于各种因素未能成功。(87)这也表明中共想把农民传统武装的斗争变成革命暴动的努力。中共漳州县委在其革命暴动中,充分利用了“三点会分子骚乱统治阶级”(88),达到煽动革命火焰的效果。福建各县在武装暴动中利用三点会、大刀会等武装的策略,与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相一致。由于福建各地普遍存在大刀会、三点会等武装组织,福建省委在中央精神的指导下,于1929年7月做出决议,要求必须孤立其领袖,并“可派同志参加进去活动,向其下层群众宣传,使其群众逐渐分化到革命方面来”(89)。此后,福建各地基本按照这一策略开展工作,尽力改编大刀会、三点会等,只对顽抗者予以武装消灭。 江西情况也差不多。中共在组织于都暴动中,合理地发挥了“三点会”的作用。鉴于西乡地区步前、罗坳、三门滩一带“三点会”很有势力,中共与三点会进行谈判磋商。双方达成协议,即在保证他们绝对服从中共领导的前提下,李英、刘为美、李骏、张文焕、尹绍伦和丘偶等六人同意参加“三点会”,“三点会”进行暴动的准备工作。(90)东固根据地的主力红军更是直接改编自段起凤、段起龙两兄弟领导的绿林武装,此外,还收编了另一孙氏绿林武装。没有这些绿林武装,东固根据地的革命力量将很难发展如此迅速。 从各地的执行情况来看,中共在发动革命的过程中确实利用了这些传统武装,而且也收到了—定的成效。虽然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中共中央对这些传统武装并不看好,不断强调它们的反动性,认为它们将影响党的队伍,随时会倒戈,但是客观现实又使得它不得不对其进行利用,否则革命武装很难迅速壮大、革命暴动也很难扩大范围。中共中央利用传统武装的策略,客观上为地方上的革命工作提供了更多的方法和途径。这也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能很快在各地开展暴动工作的—个重要因素。 五、结语 传统势力在土地革命中的消极作用之大,超过中共的革命预期。对中共而言,其主张是彻底消灭一切封建残余势力和落后思想。革命理论的解释话语是:传统势力是不容存在的反革命势力。然而,传统势力并不会那么容易、彻底地被消灭,它从各个层面消极影响了中共的土地革命。从各地推行革命的实践来看,传统势力极大地阻碍了中共革命思想的传播、党政军建设和革命斗争的进行,妨碍了这些革命工作的实施,必然对中共的革命进展十分不利。农民根深蒂固的宗族思想、地方主义和传统观念世俗的束缚对中共的土地革命理论产生了抵抗作用。这些思想从本质上来说与中共的革命理念是不相容的,因为农民认同的是亲情社会,而不是等级分明的阶级社会,中共的阶级斗争往往被他们演化为宗族斗争和地方斗争。而以地主豪绅为代表的传统势力在中共革命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坐以待毙,等着被打倒。他们有着丰富的社会资源,在社会中具有难以撼动的威信,这些都是他们与中共对抗的有利条件。在一定条件下他们往往能占据优势局面,使中共在农村中的革命尤其是早期革命时常陷入困境。中共要在农村站稳脚跟,必然要融入农村社会,大量吸收农民入党、参军、参与政权建设。随着农民尤其是地主豪绅富农进入中共的党政军体系,问题也随之而来。他们在方方面面影响着中共的党政军建设,其封建思想如影随形。这也是毛泽东等人要整党、加强党的政治教育的重要原因。应该说,传统势力对中共革命的消极作用不仅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强大和顽固的,斗争远比中共预期的要艰难得多。 现实的残酷迫使中共作出革命策略的调整,灵活应对传统势力。立于革命实践,中共认识到传统势力也有两面性,即传统势力在土地革命中的作用是双重的,它对中共革命的消极作用是主体,这是不容否认的。与此同时,否定传统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共革命的利用价值,也是不客观的。乡村社会固然有根深蒂固的社会网络组织和文化情感,但一旦中共掌握这些资源,便可以打开缺口,迅速发展自己的革命关系网络。方志敏、贺龙、刘志丹等人利用自己的势力地位成功开展革命便是例证。兄弟会、农民团等虽是封建式组织,但其形式却能吸引农民。中共利用这种组织形式便可以更为迅速地把农民聚拢到革命队伍中。换言之,中共合理地借鉴了这些组织的外壳,而其组织内容有了质的不同,加入了革命的要素,即“旧瓶装新酒”。这种变装了的组织方式既能保护农民的人身安全,符合农民的心理,又能团结更多的群众到中共的周围,何乐而不为?即使如大刀会、哥老会等传统武装也不是铁板一块,它们中的大部分都有反抗强权社会的朴素目标,与中共的革命目标有了某种的重合。正是因为两者斗争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有一致性,中共才能对大刀会、哥老会等武装进行利用与改造,从而壮大了自己的革命力量。从中共对传统势力的策略调整可以反映出中共的革命智慧,即它在面对传统势力的强大破坏力之时,能够及时调整思路,灵活应对这一阻力,从而得以在传统势力顽固的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并在短短几年内建立多块稳固的革命根据地。 注释: ①黄琨的《中共暴动中的宗族组织(1927-1929)》(《史学月刊》2005年第8期)、王奇生的《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1927-1932)》(《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陈德军的《乡村社会中的革命——以赣东北根据地为研究中心(1924-1934)》(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论著对宗族等反革命势力阻碍土地革命的开展有过不同层面地论述。 ②《中央复陈独秀函——关于革命形势的估计和暴动问题》(1927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52页。 ③《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1928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页。 ④《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222页。 ⑤《中央对湖南全省暴动和对平江工作的决议》(1928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285页。 ⑥《土地问题议决案》(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52页。 ⑦朱汉国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3页。 ⑧《湖南省委给湘鄂赣边特委的信》(1929年12月30日),《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1页。 ⑨《赵亦松关于福建工作情况的综合报告》(1928年7月29日),中央档案馆、福建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8年下册),1984年内部出版,第90页。 ⑩《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6页。 (11)《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页。 (12)《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4页。 (13)《彭德怀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4月4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164页。 (14)《中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1929年),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二)),1988年内部出版,第316页。 (15)《中共江西省委转录赣西各县及二团给赣西特委的报告》(1929年6月2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一)),1987年内部出版,第214页。 (16)《中共南广县委给苏区中央局的综合报告》(1932年10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二)),1992年内部出版,第95页。 (17)《子修:赣北工作综合报告(三月至七月初)》(1930年7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一)),第265页。 (18)《中共平和县临委给省委的报告》(1928年3月加日),中央档案馆、福建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各县委文件)》(1928-1931),1985年内部出版,第17-18页。 (19)《中共陆丰县委关于二月至六月的斗争情况给省委报告》(1928年),中共海陆丰县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43页。 (20)《中共海丰县委关于敌人状况和党各时期策略等给省委报告》(1928年7月1日),《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第329页。 (21)史沫特莱:《革命时期的中国人》,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页。 (22)《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137页。 (23)《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4页。 (24)《中共海丰县委关于敌人状况和党各时期策略等给省委报告》(1928年7月1日),《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第321-322页。 (25)《中共陕西省委全体会议关于陕北党组织目前几个中心斗争与策略路线的决议》(1930年7月9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26)《中共赣东北特委第三次执委会决议案》(1931年3月28日),《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5-266页。 (27)《中共闽北分区委第一次扩大会政治决议案》(1931年4月),《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册,第281页。 (28)《中共赣西南特委工作报告》(1930年9月28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二)),第38页。 (29)《张启龙关于赣西工作情给中央局的报告》(1930年7月12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年),第105页。 (30)《中共赣东北特委第三次执委会决议案》(1931年3月28日),《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册,第265-266页。 (31)《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警卫大队工作报告》(1932年3月22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 (32)《刘作抚关于赣西情形的综合报告》(1929年9月6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138页。 (33)《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3页。 (34)《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139-140页。 (35)《马马耶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30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9卷,第118页。 (36)《马马耶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30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9卷,第117-118页。 (37)《崇安徐淮报告》(1930年11月),《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册,第235页。 (38)《中共信江特委关于党和红军情况的报告》(1930年6月8日),《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册,第142页。 (39)《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紧急代表会议文件》(1928年10月),《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8年下册),第245页。 (40)《中共闽西特委报告第一号》(1930年11月29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闽西特委文件)》(1928-1936),1984年内部出版,第206页。 (41)《中共中央给赣东北特委的信》(1931年2月19日),《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册,第248页。 (42)《中共闽西特委扩大会议决议案》(1930年10月22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闽西特委文件)》(1928-1936),第174页。 (43)《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2-93页。 (44)《中共中央关于信江特委与赣东北特委合并及工作问题的指示》(1930年6月25日),《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册,第163页。 (45)《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109页。 (46)《弋阳、横峰工作报告》(1928年10月),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册,第79-80页。 (47)《中国共产党东江特别委员会布告》(1928年1月),《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第223页。 (48)《中共紫金县委的报告》(1928年1月22日),《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第188页。 (49)《海丰农民暴动与地主政府高压的概况》(1928年),《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第373页。 (50)《丘泮林闽北巡视报告》(1930年10月),《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册,第210-213页。 (51)《陕西代表团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5月4日),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9),1992年内部出版,第389页。 (52)《江西工作近况》(1928年7月8日),江西省档案馆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4页。 (53)《中共永定县委报告——斗争形势及县委扩大会决议案》(1929年7月6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各县委文件)》(1928-1931),第108-109页。 (54)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88-189页。 (55)《中共江西省委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28年4月15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年),第213页。 (56)陈正人:《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罗荣桓、谭震林等著:《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56页。 (57)《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4-75页。 (58)《刘作抚关于赣西情形的综合报告》(1929年9月6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137-138页。 (59)《中共江西省委转录赣西各县及二团给赣西特委的报告》(1929年6月2日),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一)),第214页。 (60)《刘震给中共中央报告——关于徽州社会状况及组织情形》(1931年7月29日),《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册,第337页。 (61)《省委通知第十号——为粉碎红灯教、神团、盖天党等反动组织事》(1934年4月3日),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资料选编》,1978年内部出版,第111-112页。 (62)《关于反动组织“盖天党”的调查资料》,《川陕革命根据地资料选编》,第126-127页。 (63)《共青团陕北工委关于陕北工作情况给团中央的报告》(1934年7月15日),《陕北革命根据地》,第189页。 (64)《黄子文关于陕北党组织状况的报告》(1932年2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陕北革命根据地》,第90-91页。 (65)《金贯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9D年5月12日),《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册,第125页。 (66)阎红彦:《陕甘高原早期的革命活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65页。 (67)黄琨:《革命与乡村——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46-47页。 (68)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页。 (69)《子修:赣北工作综合报告(三月至七月初)》(1930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江西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505页。 (70)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191-192页。 (71)《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1928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1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109页。 (72)《国际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1928年),《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1卷,第173-174页。 (73)《中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1929年),《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二)),第304页。 (74)《龙岩县委扩大会议的决议案》(1928年10月15日),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各县委文件1928-1931年),第63页。 (75)《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1935年3月),《方志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页。 (76)邵式平:《弋横农民武装起义》,《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下册,第59页。 (77)黄琨:《革命与乡村——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第34页。 (78)《鄂东巡视员曹大俊的报告》(1929年8月31日),《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辑,第134页。 (79)《刘震给中共中央报告》(1931年7月29日),《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册,第340页。 (80)习仲勋:《陕甘高原革命征程——回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259页。 (81)《中共闽西特委关于各县情况给省委的报告》(1928年11月21日),中央档案馆、福建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闽西特委文件)》(1928-1936),第31页。 (82)邵柴生:《回忆周坊起义》,方志敏、邵式平等著:《回忆闽浙皖赣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8-309页。 (83)《中共赣东北省委给徽州工作委员会的信》(1932年7月8日),《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册,第444-445页。 (84)《中共漳州县委报告——县党代表会议的情况及决议》(1929年8月16日),中央档案馆、福建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各县委文件)》(1928-1931),第137页。 (85)《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共军事工作的训令》(不晚于1928年5月4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7卷,第439页。《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农民问题决议案》(1930年8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2卷,第236页;《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1928年7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400页。 (86)《永定太平里秋收暴动计划》(1928年7月19日),中央档案馆、福建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闽西特委文件)》(1928-1936),第4页。 (87)《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练文澜巡视莆田工作报告》(1929年4月26日),中央档案馆、福建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年上册),第187页。 (88)《中共漳州县委致省委信》(1929年3月30日),中央档案馆、福建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各县委文件)》(1928-1931),第101页。 (89)《目前党的主要策略与今后工作总方针》(1929年7月2日),中央档案馆、福建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年下册),第24页。 (90)丘偶:《关于于都暴动的情况》,《回忆中央苏区》,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