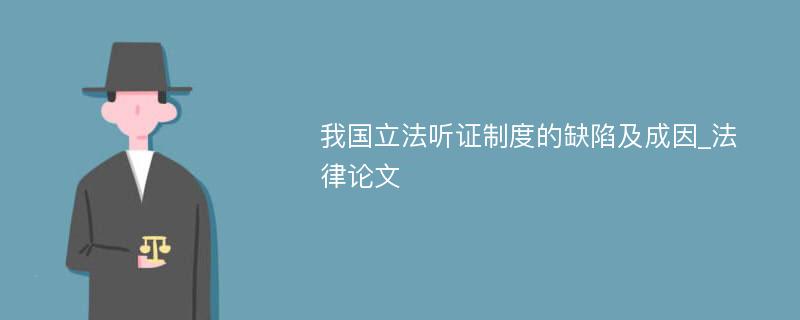
我国立法听证制度的瑕疵及其缘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缘由论文,瑕疵论文,制度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意义上的立法与民主理念及制度是息息相关的,所以特别重视立法程序的设计和运用,在许多法治国家都确立了“无程序即无立法”的原则。各国的立法实践证明,立法的民意代表性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民主立法程序彰显和体现的。
现代立法程序是一种通过多数表决作出民主决策而使一切法律具有可变性的制度设置,是经过冲突、对抗和妥协而形成的、在尊重少数基础上的多数决议。同时,为了限制恣意、保证人们作出富有理性的公正选择,民主的立法程序对多数意见的形成设置了多重“否决门”的程序制度,立法听证就是其中的一项程序制度。它在承认并尊重利益的千差万别、保证各种利益平等表达且充分博弈中,为少数挑战、质疑和否定多数意见提供制度保障,是通常意义上的立法程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正当法律程序的一部分,听证制度最初在英国只适用于司法审判领域,体现为公平和救济原则。后来,这一制度从英国传到美国,美国又把它移植到立法和行政中,作为增加立法和行政民主化以及有关当局广泛获取信息的主要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听证制度又传到日本和拉丁美洲一些受美国影响较大的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行政权力的不断膨胀,西方社会加强公众参与立法和行政事务的呼声越来越高,听证制度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成为司法、立法和行政领域中一项行之有效的民主程序。
作为一种程序的民主,立法听证是指立法机关在制定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益的法律时,赋予利益相关人表达自身利益的权利和机会,并将这种利益表达作为立法依据或参考的制度形式和实践。这是因为,立法是一种涉及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不同利益群体间利益的平衡与倾斜的公共决策问题,立法决策的结果往往是一个各方利益平衡和妥协的方案,所以,其决策过程必然是一个各方利益协商与协调的过程,而立法听证程序则在制度上为各种利益群体提供了一个表达群体利益的场所和机会。在听证会上,听证参加人可以基于其代表的利益群体之利益,通过阐述自己的观点、反驳他人的主张,使决策者充分了解各种利益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立法者的最终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在当代法治国家,听证制度已经成为公民参与立法的一种“日常化”的渠道,它不仅能促使当权者关心人民的切身利益,而且能给予每个人参与立法的可能,从而使人们都有同样的途径进入到宪法所建立的政治秩序中。在立法实践中,议会立法必须由议会下辖的不同事务委员会或法案委员会举行听证会,通过立法听证会广开言路、集思广益,立法机构在听证意见的基础上对法案作出取舍。比如,加拿大的立法程序规定听证是必经程序,法案在经过议会全会二读后必须由各专业委员会举行听证,不经过听证的法案不能成为法律;在美国,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要求所有的法案都必须经过听证程序,但是,联邦议会不经过听证的立法实际上只是例外,这种例外一般是由国会换届期间或休会期间或其他特殊原因造成的。
在我国,听证制度是个舶来品,是西方民主政治和宪政文化在异域的衍生。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被确立为改革的目标取向,立法听证制度才被我国法学界所接受并在实践中广泛运用。
立法听证制度在我国的引进,最初是从地方立法开始的。一般认为,1993年的深圳价格审查是我国听证制度发育的雏形;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过,标志着听证制度在我国的基本确立。199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把听证程序引入行政决策领域,该法明确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1999年9月9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举行《广东省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条例(草案)》的听证会,开创了全国立法听证之先河。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正式把听证制度纳入立法领域,成为立法机关在立法活动中听取民意、民主立法的制度保障。
从此,我国法学界和立法机关也越来越强调立法听证程序的重要性。据统计,从1999年至2004年,省级人大常委会一共为39件地方法规的草案举行了38次立法听证会。从地域分布来看,除台湾以外的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有24个地方举行了立法听证会;从时间分布来看,1999年举行了1次听证会,2000年举行了5次听证会,2001年为7次,2002年是6次,2003年7次,2004年12次;① 从听证会的内容来看,涉及的社会关系十分广泛,有关经济管理与规范市场秩序的、有关城市建设与管理方面的、有关社会保障的、有关教科文卫和交通安全等社会管理的、有关环境和资源保护方面的、有关行政监督方面的,等等。从此,立法听证开始逐渐成为我国民主政治生活尤其是公共决策民主化进程中的普遍事件。以后,广州、上海等地又相继以条例、办法、规定等形式制定了本地区的立法听证规则,到2002年7月,全国已有17个省市的人大常委会制定了立法听证规则。②
在我国法治建设过程中,立法听证在很大程度上逐渐成为一项实现人民主权原则、维护公民政治参与权利的重要制度,这是我们的基本判断。但是,听证制度在我国还远远未达到现代法治和民主政治的要求,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公民参与的角度来看,我国现有的听证会存在问题的关键,不仅是它还没有成为公民参与立法过程的一种正常的渠道,而且在于听证制度中存在公民参与的严重不足。综观各地举行的立法听证,几乎所有的听证会都是强势利益集团把握着听证会的话语权、压制异己的观点,或者是某些利益声音的缺失,其结果,立法听证会必然就变成了“盛装表演”、流于形式。
与法治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民参与立法严重不足,这里既有听证会设计技术缺乏的问题,又有一种观念和制度的缺陷。
一、在立法听证会的制度建设方面
在西方国家,人们普遍认为:立法听证制度是为公众和利益集团提供了一个进入政治程序的机会,所以听证会必须程式化,只有明确规定听证参加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公开听证的过程和结果,才能保证听证会的公开、透明和公正,避免个别利益集团垄断或操纵听证会。为了保证公民参与立法、促使当权者关心人民的切身利益、提高立法质量,各国对听证会的一般流程,乃至于听证准备和进行阶段中的具体细则,都作了程式化的规定。听证会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程式化的司法程序,即在立法机关主持下,由相关利益方进行控、辩,让公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识别问题、权衡各种论点和论据,以表明自己的信念并阐明立场,听证委员会居中裁判、作出初步决定。比如:韩国《国会法》规定,在全体委员的1/3人要求或决议下便可召开听证;德国《基本法》则规定,最低法定决议人数为1/4人;日本《国会法》规定,对税务问题或财政预算“必须”召开听证;美国《众议院议事规则》规定,任何听证至少要有两名委员参加,为了使所有的合理观点都得到表达,议会委员会邀请证人的范围很宽,如果大多数少数党委员于听证结束前向委员会主任申请,应当允许委员会的少数党委员邀请自己提出的证人。
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听证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在于尽量提高立法公开的程度、限制立法机关秘密活动的范围。根据各国法律的规定,立法听证公开、透明的制度性要求之内容,包括:听证会采用预先公布原则,以保证公民对听证会的知情权;一般事项举行公开听证,准许公民旁听会议过程;在听证过程中,委员可以对证人直接质询,以增加外界对委员个人意见的透明度;听证资料公开,包括有关提案人对法案所作的说明、会议记录、委员会的审查结果的报告书以及其他与法案有关的文件,以便让公众了解立法的理由、背景、法的精神和原则。立法听证公正的制度性要求之内容,包括:听证会采用证人正、反比例制,从而给各利益方以平等表达的机会;以正、反对等的模式进行辩论,通过不同意见的对抗展现各种观点的利弊;对证人在听证会上的发言以特别的保护,保证不同意见的充分表达、言者无罪。事实证明,只有按照规范举行听证,才能收到客观与公正的效果。
为了达到听证会的预期目标,各国基本上都建立了听证结果处理公开化、制度化的回应机制,即有关听证会的完整报告交由国会的会议记录员整理,不同意见者可自备一份意见报告书作为附件,一并送往国会及负责的调查委员会,听证会报告必须向社会公布;举行听证的委员会将就听证报告重新举行内部会议,参照听证会各方意见,进行议案之审查;立法决策机构对委员会会议的报告应作出回应,并公布于众。立法听证陈述人也应继续关注听证会的善后工作动向。
立法肯定利益,但却不能允许利益集团的恣意妄为。立法听证会的公开、透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利益集团的恣意妄为。因此,听证会的公开和公正,不仅是立法听证会本身所具有的特征,也是立法听证会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所要达到的共同目标。
相比之下,我国目前的立法听证会基本上是立法机构主导的选择过程,听证程序规则的简陋、粗疏无疑是一个基本缺陷。在制度建设方面,我国听证程序的瑕疵及其缘由主要在于以下三方面。
(一)立法听证的法律依据存在较大的模糊性
我国在《立法法》制定之前,立法听证完全是地方人大的探索和尝试;《立法法》颁布实施之后,听证活动才有了全国性的法律依据。但是,《立法法》只有第34条涉及到了立法听证的问题,而且根据《立法法》的规定,立法听证在我国只是立法机关听取各方面意见的一种形式而已,法律并没有对立法听证会的一般流程及听证准备和进行阶段中的具体细则作出程式化的规定。在实践中,对这种公民参与立法的形式中的诸如立法听证的动议、诉求的表达、利益的交涉等众多环节,各地方的具体做法不尽相同,官方也含糊其辞。可见,我国立法听证的法律依据是非常模糊而且不充分的。我国立法听证的法律依据的模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立法法》中有关立法听证问题的规定非常简单,弹性也较大,不像价格法那样对于价格听证有刚性的规定;二是很多地方,包括已有早期实践的一些地方人大也还没有为听证会制定专门的听证制度规范;三是立法听证实际进行的次数很少,进行与否随常委会领导人的注意力的转移而转移,有的成为立法公开性的点缀品。”③ 据统计,“在已经举行的27次立法听证会中,有5次没有制定听证规则,9次从掌握的资料还无法判断是否制定了听证规则。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制定听证规则的省、市,有的是由人大常委会制定地方法规,有的是由主任会议或者委员会制定长期适用的听证规则,有的则是制定只适用于当次听证会的、临时性的听证规则。当次适用的听证规则,大多是在听证会工作方案中加以规定”。④ 总之,由于法律依据的不足,立法听证会不得不游离于正式规则,使强势利益集团的恣意妄为成为可能。
(二)听证会的公开性、透明度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这是因为,一方面,现有的法律规定太原则、难以操作。比如,《立法法》虽然提出听证会是立法过程中听取意见的一种形式,但是,并没有明确它是立法程序中必需的环节,既没有突出它的地位,也没有明确规定到底哪些法律或法规的制定和修改必须进行听证、哪些机构有权决定举行听证会、听证的主体和内容如何确定等,法律对听证会规定得如此含糊,必然会在实际操作中产生许多麻烦。在听证会的举行过程中,组织者可以左右会议的进程,从而使听证会有些环节的操作总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另一方面,有的地方根本没有制定听证规则,听证会带有明显的临时性和随意性,甚至类似于某种政治活动,其组织工作的投入极其重视程度完全由当地领导人决定的。再一方面,有的地方即使有了听证规则,这些规则在实践中往往也会被束之高阁。比如,在关于确定听证参加人的问题上,武汉市人大常委会曾经决定采用“证人正反比例制”审核参加人,但“考虑到参加人的意见不会太广泛,为了避免讨论得零碎”,最终没有规范参加人的意见比率和总体人数。总之,立法听证的公开、透明和公正,需要规则和制度的保证,如果没有规则和制度,那么,个别利益集团就可能控制或操纵听证会、压制其他利益方的声音,听证会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三)听证结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立法听证会在各国都只是个咨询性机制,召开听证会只是公众参与立法的一个渠道或过程,如何采纳听证意见才是关键。但是,我国对听证会的结果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无论是《立法法》还是各地的立法听证规则,对立法听证结果的后续处理或听证陈述人意见的处理方式和程序都没有予以规定。在现实操作中,听证会的主持人往往按照个人的偏好或者本部门的利益对听证会的结果进行任意取舍或变动。由于我们过去的立法是部门起草,许多地方性法案都是政府以议案的形式提出的,立法中追求部门利益的现象比较严重,再加上行政主导的体制,导致很多立法听证过程被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把持话语权,成为他们维护甚至扩大自身权力和利益的途径,这样,听证的结果不了了之,听证的效能也难以保证。
二、在立法听证会的法律观念方面
在观念层面上,主要是立法听证的定位问题。立法听证的定位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事实上,对立法听证会的定位取决于立法机关对立法听证的认识。西方人创设听证制度着重于其民主性或执行性的功能目标,而我国引进立法听证的初衷,则在于它的形式性、工具性的功能目标。
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众多利益集团的并存是人类个性和主体性的直接体现,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的实质是对各种利益关系的界定、分配和协调,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民主政治就是程序政治。甚至有人认为立法机关是各种利益的天然聚集场所,“立法者的选举程序创造了一个立法市场,在其中,立法者向那些在金钱和投票上有利于他们获胜的人们‘出售’立法保护”。“立法程序是有特殊利益间的交易所决定的。……法律的制定和颁布是以总成交的买卖”。⑤ 因此,如何把立法活动控制在人们所能容忍和接受的限度之内,便成为法治国家所共同关注的问题。也就是说,现代民主国家均规定立法听证制度,是因为它更符合民主政治的本性。
在当代法治国家的议会立法中,立法听证虽然不是一个必经的程序,但也是一个基本的程序,以公共和理性的沟通来化解利益冲突,尤其赋予利害关系人参与表示意见的机会,未经听证就制定法案的情况是例外。这是因为人们深知,如果让人类社会完全听凭利益对法律的支配、利益的优势者成为立法的主宰,那么,人类社会就无异于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虽然立法肯定利益,但却不能允许利益集团的恣意妄为;虽然利益影响立法,但不应该让立法成为利益的奴仆。由此可见,西方人创立的听证制度是一项渗透着“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立法程序,这一程序可以使多数意见经过公开听证的过滤后成为合法的公意,同时为少数挑战、质疑和否定多数意见提供制度保障。
与西方的法律观念不同,我们借鉴和接受国外的听证制度,是在于它的程序性民主形式——一种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形式而已,而不是因为它更符合民主政治的本性。
我国《立法法》第34条明确规定:列入议程的法律案,立法机关“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这就意味着,立法听证会和立法座谈会、立法论证会等其他听取意见的形式是一样的,都是有关机关在立法活动中听取群众意见的一种方式或渠道,至于是否采取听证会形式,完全取决于法案的起草机构和立法机构。正因为如此,《立法法》对立法听证范围、听证主体、听证公告、听证主持人、举行听证过程等内容,都没有作出具体规定。
笔者以为,尽管在获取立法信息的手段、组织的程序方法等方面,立法听证会和传统的座谈会、论证会形式有着许多相同之处,但是,作为一种正式的立法参与形式的听证会,应该与座谈会、论证会有所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在重要性方面
听证会比座谈会、论证会重要得多,它是一种更加公开的立法程序。在我国,座谈会和论证会是一种传统的听取公民或专家意见、倾听社会呼声的方式,也是我国民众所广泛熟悉、认知的一种政府与公民交流的形式。但是,这些形式多为非制度化的,更重要的是,它完全由立法者意志所掌握,法案的起草机关或审议机关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取舍,从代表的邀请到召开会议以及会议结果,都是不公开的,也不受公众监督。相比之下,立法听证会是一种为公众提供主动、自愿参与的制度渠道,除非有必须秘密举行的理由,立法听证会从确定会议代表到会议举行及听证的结果,每个阶段和步骤都必须公开,而且,公民或组织是否参与听证会、对法案是支持还是反对,这完全取决于本人而不是会议的组织者。在西方国家“公民在立法方面的听证权利正在日益成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并逐渐同司法反面的听证权利一样,将会被视为一项基本人权。在民主化法治化程度高的国家,在一些重大法律问题上,公开听证制度正在与公民投票制度相结合,成为直接民主制的一种重要形式”。⑥ 如果有关利益团体或公民因没有被邀请参加听证而使自己的意见没有得到表达,他们甚至有权诉诸于媒体。
(二)在程序性方面
听证会比座谈会、论证会严格得多,它是一种在场式的、带有对抗性的征求民意的程序。由于座谈会或论证会的对象是内定的,组织者往往会根据自己的意愿或偏好在比较熟悉的人员中选择与会代表,一般不可能邀请支持和反对法案观点的人同时参加。邀请者和被邀请者是熟人关系,彼此之间能较快地达成默契,即使持有不同意见的专家也只能代表某些专业人士的意见,而难以广泛代表民众或利益集团的意见。况且,座谈会和论证会的召开会议都是不公开的,不存在程序上的要求。相反,听证会的实质是对法案进行充分论证的过程,即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言人在同一场所进行面对面的讨论与交流,各方面的意见通过辩论、质证得以充分展示,这样法案中的一些矛盾也会暴露得更加充分,意见也会更全面。由于听证会是自愿选择参加的,那些支持和反对某议案的人都会积极参加,所以,辩论是听证会的灵魂。它在程序上往往采取支持者和反对者交替提问或陈述,从而使听证会具有某种对抗的性质。
(三)在结果性方面
听证会比座谈会、论证会有效得多,它是一种提供了交流空间的正式制度。与座谈会或论证会不同,立法听证获取的民意会成为立法的依据,而座谈会或论证会的意见只是作为立法的参考。通常,座谈会或论证会是由法案的起草机关或审议机关自己召开,由委员会或者有关工作机构主持,请谁或不请谁出席座谈会是会议的组织者说了算的,这就难免带有邀请者的偏好或随意。因此,以这种方式征求的意见可能存在着倾向性、片面性和不真实的问题,工作人员只是在座谈会后对其内容整理出一份综述简报,作为有关委员会或常委会会议审议法案时的参考。也就是说,如何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其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会议的组织者手中;征求来的意见是否采纳或采纳哪种意见,往往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但是,立法听证会比座谈会、论证会重要得多,它在法治国家是立法的必经程序,不经过听证的法案是不能成为法律的。“程序始终与恣意相对峙,是作为限制人类恣意的制度化产物而存在的。倘若没有程序制度的笔,或许正义、民主、权利、平等、自由等美好的文明理念都可能泯灭于人性的阴霾之中”。⑦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立法法》将听证会与座谈会等形式等量齐观是不适宜的,这种观念如果长此以往不仅会挫伤公民参与立法的热情、损坏立法的质量和权威,而且也影响听证制度在立法中的地位。同时,《立法法》对听证会的这一定位,表达了立法机关对立法听证程序的一种认识和理念。在法的理念上,当形式主义和法律工具论成为一种思维定势,程序一直是作为实体目标的伴随物而被诉求——重实体而轻程序,立法听证被视为等同于立法座谈会或论证会等其他听取意见的形式,也是很自然的了。
为了让公众亲眼见到体现自己意志的法律形成过程、民意的形成过程,应该逐步转向立法听证会之民主性或执行性功能的定位,因为民主政治就是程序政治,民主立法离不开程序的保证,立法听证作为立法活动中的一项程序制度,既需要相关的制度规范来体现,还需要相关的观念来支持。应当指出,民主的发展进程和程序的制度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国立法听证的发展应在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实现其民主性功能定位,听证规则的制定、实践和完善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注释:
①武增:《地方人大立法听证的情况、经验和问题》,资料来源:http://www.yihuiyanjiu.org/yhyj_readnews.aspx? cols=171211&id=2177,访问日期为2007年6月1日。
②谢章泸等:《对地方立法听证运作的思考》,资料来源:http://www.law-lib.com/lw/lw_view.asp? no=5900,访问日期为2007年6月1日。
③陈斯喜、蔡定剑等:《地方立法听证调查报告》,资料来源:http://www.chinaelections.org/xjzl/readnews.asp? newsid=%7BDCF3E312-CD28-44D9-BEA0-3F776AE21F3C%7D,访问日期为2007年6月8日。
④陈斯喜、蔡定剑等:《地方立法听证调查报告》,资料来源:http://www.chinaelections.org/xjzl/readnews.asp? newsid=%7BDCF3E312-CD28-44D9-BEA0-3F776AE21F3C%7D,访问日期为2007年6月8日。
⑤苗连营、宋雅芳:《对立法程序的哲学审视》,载《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⑥杜钢建:《议会立法听证程序比较》,资料来源:http://www.yihuiyanjiu.org/yhyj_readnews.aspx? id=2040&cols=171216,访问日期为2007年6月8日。
⑦刘武俊:《立法程序的法理分析》,载《中外法学》2000年第5期。
标签:法律论文; 听证会论文; 立法机关论文; 立法法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法律制定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