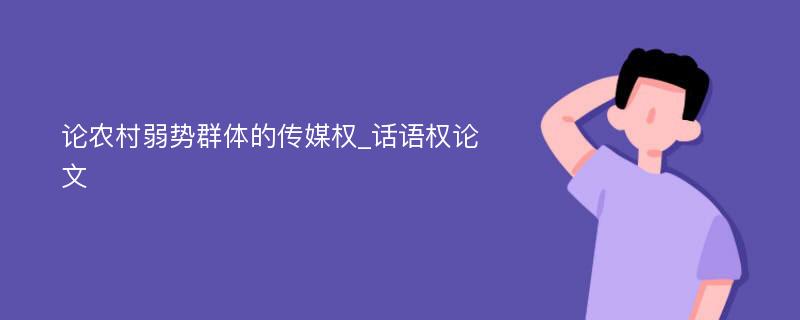
论农村弱势群体的媒介话语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弱势群体论文,媒介论文,话语权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农村弱势群体的受众调查
农村弱势群体不仅在经济生活和社会地位上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在媒介资源的享受和利用方面同样处于弱势,这一点从我们所做的农村弱势群体受众地位调查以及各类媒介和机构的农村受众调查中都得到证明。根据调查显示,农村弱势群体作为大众媒介受众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1.在大众传播工具的拥有量方面不及城市受众 农村弱势群体经济实力匮乏,限制了他们购置大众传播接收工具。在我们调查的近百户农村弱势群体中,拥有彩色电视机56台、黑白电视机42台,还有8户没有电视机。而在城市, 2001年每百户城市受众拥有彩色电视机为120.52台。
2.媒介消费的时间相对较少,选择媒介的自由度低 据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对12个省的调查,2001年农村受众平均每天收看电视的时间为153分钟,城市受众则是192分钟。而我们的调查显示农村弱势群体平均每天收看电视的时间为136分钟。2003年城市化程度高的上海市受众拥有37套免费节目和31个付费电视频道,而安徽太湖县平均每户能接收到的电视频道只有6个。
3.对信息的极度渴望与信息资源获得的有限在我们针对农村弱势群体的电视受众调查中显示:收视频度排名在前10位的节目中,信息类占7个,有71%和58%的电视观众将国内新闻、国际新闻选为最喜欢的节目类型。例如收看中央台的《新闻联播》节目的受众占总数的87%,安徽太湖县电视台引进的《星火科技30分》节目的受众占总数的 62%。可见,农村弱势群体受众也拥有想了解外界情况变动的欲望,尤其是对致富信息的渴求。但是,至今全国为农民开通的专业频率和频道极少,央视七套农业节目在许多农村地区收不到。大多数农村弱势群体受众表示从电视中获取有关农业政策信息、新技术、农产品市场等方面节目的信息非常稀少。而关于报纸,当都市报层出不穷时,以农民为受众定位的报纸寥寥可数,报纸在农村市场很难发行,农民几乎接触不到报纸。
4.农村媒介资源网络建设基础差,受众选择媒介的自由度低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一系列城市优先发展政策使得农村在媒介公共资源投入方面与城市的差距十分显著。在大众媒介普及化的今天,城市里的广播电视网络仍由政府投资建设,而农村中的有线广播网却要农民自己出资铺设,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更没钱投入,这导致农村受众中至今仍有45.2%的人无法享用省级有线公共网接收卫星电视节目,只能靠自备的普通室内(外)天线收看有限的几个台,清晰度和稳定性都不理想,接收的质量和效果都受影响。
这些既缺乏接近媒介的条件和能力,又缺乏参与传播活动机会和手段的农村弱势群体,最终只能被动地、无条件地接受来自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而几乎无法得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各种信息,也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基本上失去了媒介话语权,成为信息弱势群体。
二、处于“失语”边缘的农村弱势群体
应当说,大众媒介作为社会公共资源是归全民所有,人人都应该拥有媒介话语权,但事实并非如此。农村弱势群体基本上处于失语的状态,他们在媒介话语权的争夺中被边缘化。为什么农村弱势群体的媒介话语权被忽略?
1.我国社会的阶层分化以及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使得媒介话语权的分配模式产生了显著变化中国社会阶层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推进下的分化,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断裂”,这使得农村弱势群体在经济、社会地位和媒介资源的占有使用上都就处于弱势地位。“传播媒体所隐含的意义与语言的功能亦有相近之处,它不但是一种情感与思想的传达工具,同时亦是一种自我存在的依据,特别在此信息泛滥的世代,失去了传播能力与传播工具,就等于失去说话与表达的能力,甚至导致自我本质的丧失,并且将自我形象的诠释权,拱手交于媒介掌控者的手中,而这样的权力关系,亦会落入弱肉强食的恶性循环中。”
2.大众传播事业的产业化、商业化趋势导致农村弱势群体的话语权被边缘化 随着舆论宣传体制改革的推进,大量媒体被推向市场,实行市场化运作,在近乎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为了生存,大众媒体受经济利益驱动,把注意力转向“强势人群”,对受众中的“弱势群体”却越来越缺乏关注和热情。社会强势群体拥有媒介的控制权,拥有主要的话语权,引领媒介发展潮流,决定社会舆论导向。
产业化与商业化还导致大众媒介城市中心主义倾向,农村弱势群体成为媒体关注的盲点。我国各级电视台的节目普遍带有浓厚的都市化倾向,并有不断加剧的趋势,即使有些农村报道,也主要是从城市化的视角来观照,与农民远远不能的需求错位。
3.吸收和运用媒介信息能力的低下导致农村弱势群体没有主动争取话语权的观念和积极性美国传播学者蒂奇纳通过实证研究指出信息“知识沟”的现象:当一个社会体系中的信息流增长时,那些受过较高教育、具有较强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们比受教育较少、地位较低的人们更好地吸引信息,这样,信息增长导致了知识沟的扩大而不是缩小。文化知识的匮乏,经济的落后限制了农村弱势群体接受现代新知识、新观念,与社会强势群体的知识沟越来越大,导致经济发展滞后。其结果是政府和媒体往往成了他们的代言人,而他们普遍缺乏与媒体打交道的经验,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不知道如何寻找解决问题的机构,他们自感“人微言轻”,不知道如何有效表达他们的不满和困惑,他们在大众媒介中没有声音,他们选择了沉默。
于是,在大众媒介中,在人们的认知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表现出双重刻板印象的农村弱势群体。在新闻报道、影视剧、广告中,农民以忠厚、老实的形象出现,但更多的是把他们描写成穿着上的土气、言语的粗俗、行为的不合时宜、思想上保守的“乡下人”。尤其是那些在城市中的农民工,我们在大众媒介中总是看到他们在春节挤满了火车站和汽车站,总是成群结队在城市街边的地下劳动力市场等候雇用,总是城市中各类犯罪事件中成为主角,总是抢占了国有下岗工人本能获得的就业岗位。城市的居民歧视又害怕这些涌入城市中的陌生人,总怀疑他们有犯罪的倾向。对于弱势群体,尤其是生活贫困的群体和残疾人群体往往被描写为社会发展的牺牲品、旁人的负担、无赖或者是改变生活的超级英雄等。展现在大众媒介中的农村弱势群体集中体现了这两类刻板印象,他们的利益表达更加受到限制。
三、重返话语阵地与媒介责任
若把媒介视为一种社会资源,这种资源的配置显然不应仅以集团利益为原则。无论是市场条件下还是计划条件下,对社会资源的配置都必须以公众利益为基础,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促进下,中国的新闻媒体有了许多根本性的转变,传播方式上从“以传播者为中心”到“以受众为中心”的转变使得媒体开始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努力满足多层次弱势群体的多种利益表达需求。
所以,在对农村弱势群体经济上扶贫的同时,应当政府和媒体应当积极实施受众教育,培养他们的争取和运用媒介话语权的主动意识。今天的受众教育与培养至少应包括两方面:
(1)提高农村弱势群体整体文化素质,促进他们现代意识形成。面对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农村弱势群体在科技使用能力与生活方式、观念上大多迟滞与落后。因此,改革传播教育体制,丰富教育内容,提高受众现代文化素质是首要。
(2)实行媒介传播教育,帮助农村弱势群体了解各种媒介特点,学会正确接触媒介,同时使他们具备基本传播能力,转变传播观念,掌握媒介话语权。事实证明,受众素质提高就能以主动态度参与传播活动,行使话语权维护自身权利。
从大众传媒的受众地位来说,农村弱势群体是有特色和个性需求的受众群体,大众传媒应该深入了解他们的需求特色和信息的解读能力,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改革节目设置、提高节目质量,增强传播效果。在涉及农村弱势群体的报道上,要尽量注意克服刻板印象带来的负面效应,“给农民以国民待遇”,为弱势群体提供利益表达的渠道,营造农村弱势群体的话语中心。
摘自《安徽大学学报》:社科版(合肥),2005.3.150~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