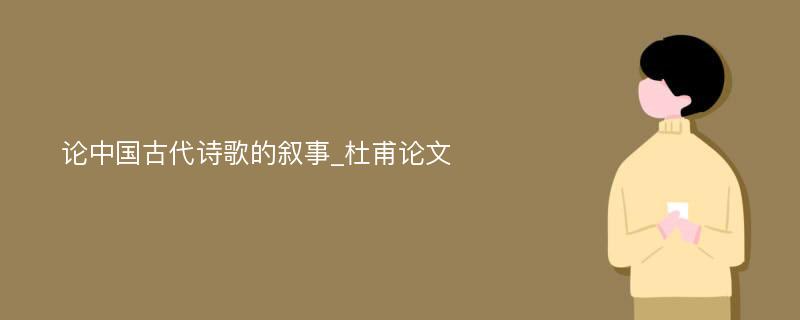
中国古代诗法叙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诗法叙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试就中国古代的诗法问题进行简要的回顾,并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意在引起诗学界的兴趣,对中国古代诗法进行较深入的探讨,以便推动我国诗歌创作的发展。
[关键词] 中国 古代诗法 叙论
诗法的探讨,滥觞于唐,兴于宋,盛于元明清。讨论的焦点,是“死法”与“活法”。
有没有诗法?回答是肯定的。但是诗法是个很难用三言两语就能讲清的问题,所以大作家往往避而不谈,陶渊明、谢灵运、李白都没有谈怎样做诗,杜甫偶有提及,也没有展开去谈。宋代黄庭坚对诗法兴趣大,但也没有就此作长篇大论,苏轼、陆游也往往有意避开。宋人周紫芝《竹坡诗法》有一则记载,颇能反映苏轼对诗法的态度:有明上人者,作诗甚艰,求捷法于东坡,作两颂以与之。其一云:“字字觅奇险,节节累枝叶。咬嚼三十年,转更无交涉。”其一云:“冲口出常言,法度去前轨。人言非妙处,妙处在于是。”
观东坡两颂,其一是不客气地批评了明上人沿孟郊、贾岛余习,爱“觅奇(句)险(句)”,喜欢咬文嚼字的做法,这种做法违反了诗歌创作的美学原理。诗歌之美不在奇险,而在自然有味,用汤惠休的话,就是“芙蓉出水”,用李白的话,就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用皎然的话,就是“至丽而自然”,故苏轼在第二首中提出了纠正的办法:不要效法前轨,而以常言作诗,好诗通常是冲口而出的“常言”,要脱去别人已用过的陈言,用自己的语言作诗。苏轼巧妙地回避了所谓的“捷法”,用自身的创作经验解答了明上人的问题。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说,诗、赋、杂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即孔子所强调的“辞达”,而不必受什么诗法文法的束缚,文由己出,文随己意。他在《文说》中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智者,常行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己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观苏轼诗,大都是随物赋形而物态毕肖,冲口而出而自然有味,如《赠刘景文》诗云:“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桔绿时。”《中秋月》云:“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大都是寻常用语,一经道出,则味之无极。苏轼大才,作诗如同游戏,不言法而自有法度在,但其法为自我之法,不必效仿前人,所以他不屑于言诗法。陆游也不喜欢谈语法,儿子问作诗,他赠诗云:“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无诗法可教,这也是他的经验之谈。
但是诗法毕竟是客观存在的,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不掌握诗的内在规律,无以为诗。例如壮家对山歌,其章法,句法,声调是基本固定的,而内容则根据需要,层变迭出,就是唱上几天几夜也唱不完。这里边就有法度在。壮人能作山歌,也不是天生的,而是有人教的,先教上一阵,入门了,再多作多唱多听,自然熟能生巧,而亲自对歌,是长进的最有效的途径。诗人虽有天生的素质,但绝非不学而能,只是明学暗学而已,明学是拜能者为师,求其指点,暗学是诵读现成诗章,自己揣摩。人人都可以学会做诗,但没有诗人的素质,不能成为出色的诗人。所谓诗人素质,是天生的极强的感受力、捕捉意象力、语言表达力和强烈的表现欲,再就是善于摹仿前人又能超出前人。大诗人可以谈他对诗的体验,而很少谈诗法,原因在于其形象思维能力强而抽象思维能力弱,诗法需要的是抽象思维能力。诗人能感受法度的存在并自觉地应用它甚至发展它,但要他明白地说出何为诗法,是比较困难的。
诗法自古存在并自觉地被应用于创作 最明显的例子,是《诗经》中比兴手法和重章叠句的大量使用,这是诗法在表现手法和结构形式上的具体反映。屈赋中有“兮”字法,或在句中,或在句尾,起调整节律的作用。“古诗十九首”,看起来天然浑成,无法可言,但绝非无法可依,细绎“行行重行行”,“庭中有奇树”等诗,便可看出意脉运行其间,因而首尾一贯,这就是结构法。齐梁时期,由声律论而产生的永明新诗体,使诗歌节律更合谐,音调更响亮,这里边就有律法——声律。谢眺诗不仅工于发端,起承转合亦已基本具备,观其《赠西府同僚》、《入朝曲》等,都有法度在。钟嵘评谢眺诗,尝云:“眺极与余论诗,感激顿挫过其文。”可知谢眺曾就有关诗歌问题与朋友进行过争论,他的诗启发了有唐一代,不外乎声律、色彩、结构三个方面,要皆不离乎法。
唐诗极盛,却似乎极少言法,但并不等于说唐诗人不讨论、不探讨诗法问题。特别是像李杜这类大诗人,虽然很少有诗法论述形诸文字,但并不等于他们不谈诗法,更不能说其创作全都自出机抒,不遵法度。李白不言诗法,但其诗法得于曹植、谢眺诸人,因其极谙熟于诗,故不言法而法自在其中,此所谓“大匠运斤成风”者。杜甫作计,人多称其有家学渊源,杜甫亦自云熟“精《文选》理”,“理”即为文之道,法在其中,又云“读书破万卷”,“破”者,得其匠心独运之处,杜甫诗,极尽变化之能事,皆从“理”、“破”中来,正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在杜甫诗论中,有两句涉及到具体的诗法问题,一句是“佳句法如何”,他只提出问题,没有回答,宋以后对此展开过许多论述,可见影响极大。一句是“晚年渐于诗律细”,这是他的自我总结,后人对此讨论不多。杜甫诗是一个诗法武库,后人研究,各有所得,但有待发掘的还很多,即使不研究,多读杜诗,亦可悟其诗法之精妙。就句法论,就有层递,对照、倒装、叠用,有拙句,有巧句,有实句,有虚句,难以尽述。杜甫自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诗之精微,难以言传,叶燮曾指出“月傍九霄多”,“钟声云外湿”等,以证诗理,是识其精微处,可谓杜甫知音者。天宝年间,杜甫与李白交往时,曾就诗歌问题进行过讨论,分手之后,杜甫意犹未已,在给李白的诗中,还说:“何时一壶酒,重与细论文。”这是耐人寻味的。他与李白之间,在诗歌创作问题可能有许多共同体验,但两人诗风不同,看法上可能有许多分歧,据传李白有“饭颗山前嘲杜甫”的话题,不能说没有根据。按当时的情况,李白名气很大,比杜甫大一个年龄段,杜甫虽做得一手好诗,但年轻,在诗星灿烂的开元天宝初尚未放出异彩,杜与李论诗,按杜甫的性格,亦颇自负,而人长得瘦,李白嘲之,是自然之事。但也并非恶意,无非是开些玩笑,平息争论。但杜甫是极认真的人,他很想能找个机会,两人对坐,在酒酣耳热之际,重开话题,再细细地讨论诗歌问题,但他始终再也没能找到这样一个机会,这对杜甫来说,是终身憾事。两位伟大诗人论诗,想必是很精彩的,然而我们既没有看到李杜先前论诗的记录,更无缘目睹两人的热烈争论。我们只能从两人的创作实践中,从其作品中,凭我们各人的悟性,去领略其天工人力之一二。李杜论诗的事实告诉我们,伟大诗人不仅重视创作实践,也是重视理论研讨的。并不像后人所说的唐人不言诗法而诗自精。没有诗法的引导,是很难进入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的。
李杜之后,谢灵运十世孙皎然作《诗式》,对诗歌创作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和总结。《诗式》中“明势”、“明作用”、“明四声”、“四不”、“四深”、“二要”、“二废”、“四离”、“六迷”、“六至”、“七德(得)”、“五格”、“文章宗旨”、“用事”、“取境”、“重意”、“辨体”、“复变”等一系列问题,都与诗歌创作有关。其中也包括了诗法方面的一些问题。例如“用事”中之论比,兴;“取境”中驳“不要苦思,苦思则丧自然之质”之说,认为“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辨体”中说“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更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更逸”;“复变”中认为复古与变通是诗歌的发展规律,变通是主要的,复忌太过,变则造微,不忌太过,要在不失于正,等等,这是唐人诗论中涉及到诗法问题的有创见的一些论述。对后人有较大的启发,严羽的诗论,就是在《诗式》和司空图的诗论的启示下发展起来的。
由于唐人已将诗歌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诸法完备,艺术技巧臻于完善,宋人要在这块土壤上继续耕耘,并获得好的收成,就得认真研究唐人如何写诗,因而出现了诗法的研究 这方面宗杜的黄庭坚首先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工作,随后,其宗派弟子就此继续研究,提出“学诗当识活法”的口号。黄庭坚的研究从杜诗入手。他的结论是:“杜之诗法出审言,句法出庚信,但过之耳。杜之诗法,韩之文法也。”(见《后山诗话》)黄氏的结论是有根据的,杜审言是杜甫的祖父,高宗咸享年间进士,为修文馆直学士,与李峤、崔融,苏味道被称为“文章四友”,其五言律格律谨严,颇多佳制,为唐五言律的奠基人。杜甫律诗,法度森严,人称诗中孙吴,自有其家学渊源。杜甫对于庚信,也格外推崇,可知对庚信诗文深有研究。但杜诗是所谓集大成者,杜审言,庚信只是对杜甫影响较大的两位前辈。黄庭坚虽然主张学杜甫,但也主张学其“句法简易”处。但在当时,江西诗派诸人多以杜甫诗法为法,不知变通,故该宗派中的吕本中提出“活法”之说,他说:“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话法矣。谢元晖有言,‘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见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活法说”对明清诗评家,有不小的影响,他们一谈及诗法,大都不敢说得过于具体。但宋元论诗者似乎不在此限之内,姜夔云:“不知诗病,何由能诗?不观诗法,何由知病?”只强调诗法,不论死法,活法。严羽则将诗法一分为五:“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包罗相当广泛。元人揭傒斯从自身经验出发,强调了诗法的作用,也说:“学问有渊源,文章有法度。文有文法,诗有诗法,字有字法。凡世间一能一艺无不有法。得之则成,失之则否。信手拈来,出意妄作,本无根源,未经师匠,名曰杜撰。”(《诗法正宗》)认为法是成功的前提。元代另一著名诗人杨载撰《诗法家数》,指出:“大抵诗之作法有八:曰起句要高远;曰结句要不著迹;曰承句要稳健;曰下字要有金石声;曰上下相生;曰首尾相应;曰转折要不著力,曰占地步,盖首两句先须阔占地步,然后六句若有本之泉,源源而来矣。地步一狭,譬犹无根之潦,可立而竭也。”接着又就如何学习前人问题谈了自己的体验,并指出了掌握法则的途径,即学习前人,日积月累,认真揣摩,融贯诸法,然后有得。杨载在书中对各种体裁诗歌的作法都有阐释,如论绝句之法,说:“绝句之法,要婉转回环,删芜就简,句绝而意不绝,多以第三句为主,而第四句发之。有实接,有虚接,承接之间,开与合相关,反与正相依,顺与逆相应,一呼一吸,宫商自谐。大抵起二句固难,然不过平直叙起为佳,从容承之为是。至如宛转变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若于此转变得好,则第四句如顺流之舟矣。”言简意赅,确为经验之谈。元人范德机则作《木天禁语》,对诗法有较详尽的分析,如其绎唐人李淑《诗苑》一书之篇法为“一字血脉”、“二字贯穿”、“三字栋梁”、“数字连序”、“中断”、“钩锁连环”、“顺流直下”、“双抛”、“单抛”、“内剥”、“外剥”、“前散”、“后散”等一十三法,并目之为“屠龙绝艺”,以为“此法一泄,大道显然”,可知他对诗法有较深入的研究。然而遭到了后人的非议,明人杨慎指责说:“作者泥此,何以成一代诗豪耶?”由于学者忌于舆论的压力,故从明代起再也没有产生象《诗法家数》、《木天禁语》这类较系统地研究诗法的著作。
在明代,对诗法的争论相当热烈。明初,由于受科举影响,士子们大都沉湎于八股文,只知《四书》、《五经》、时文范本,偶有诗作,也多是“台阁体”、“理气诗”。面对这萎靡的文坛,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慨然倡导复古,以振文坛风气。他们主张古诗学魏晋,近体学盛唐,当时“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可见影响极大。但李梦阳过于强调格调、法式,只知泥古,不求创新,故李、何之间产生了分歧,进行过激烈的辩论。李梦阳说:“李某岂善文者,但能守古而尺尺寸寸之耳。”又说:“右之工,如倕,如班,堂非不殊,户非同也,至其为方也,圆也,弗能舍规矩。何也?规矩者,法也。”(《驳何氏书》)这种尺寸古人的观点,自然招来批评,何景明说:“追昔为诗,空同子刻意古范,铸形宿镆,而独守尺寸。仆则欲富于材积,领会神情,临景构结,不仿形迹。”何氏对摹拟之说不肯苟同,主张拟而能变,他说:“曹刘阮陆,下及李杜,异曲同工,各擅其时,并称能言。何也?皆能拟议以成变化也。若必例其同曲,夫然后取,则既主曹刘阮陆矣,李杜即不得更登诗坛,何以谓千载独步也?”何氏的反驳,确实打击了李梦阳泥古的要害。但何景明并不主张废诗法,他自有其诗法观,他以“辞断意属”,“联类比物”为“不可易之法”,主张为诗当“推类极变,开其未发,泯其拟议之迹,以成神圣之功”既总结了诗文发展的规律,也指明了诗歌创作应当努力的方向。他在这篇有名的《与李空同论诗书》中还运用了一个著名的比喻,说明诗法与创作,前人与后来者的关系,他说:“佛有筏喻,言舍筏则达岸矣,达岸则舍筏矣。”意思是,前人之诗及诗法,好比送我到达彼岸的木筏,未达彼岸之前,则使用它,到达之后,则把它放弃,以免成为累赘。既已学会做诗,则应匠心独运,力求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为什么还要拘泥成法,不敢越出雷池一步呢?筏喻之说是很有启发性的。
清人对诗法的意见,以清初的王夫之,清中叶的叶燮两人比较具有代表性。王夫之着力于破“死法”,叶燮则主要在阐明“活法”及比“活法”更为深广的问题。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说:“‘海暗三山雨’接‘此乡多宝玉’不得,迤逦说到‘花明五岭春’,然后彼句可来,又岂尝无法哉?非皎然,高棅之法耳。若果足为法,乌容破之?非法之法,则破之不尽,终不得法。诗之有皎然,虞伯生,经义之有茅鹿门,汤宾尹,袁了凡,皆画地成牢以陷人者:有死法也。死法之立,总缘识量狭小。如演杂剧,在方丈台上,故有花样步位,稍移一步则错乱。若驰骋康庄,取涂千里,而用此步法,虽至愚者不为也。”王夫之反对死法,认为死法起于识量狭小,他把起承转收看作是死法之一,认为不足于展骐骥之足。但观唐之名家,如王、孟、刘长卿,刘禹锡,乃至李、杜,其律诗多用此法,只是不露形迹,岂能概之为“死法”?明清人多好为大言,喜欢标新立异却易偏离事实,杨慎、王夫之概莫能外。叶燮论死法与活法,也极力反对泥于起承接合之类,他说:“死法则执涂之人能言之,若曰活法,法既活而不执矣,又焉得泥于法?而所谓诗之法,得毋平平仄仄之拈乎?村塾曾读《千家诗》者,亦不屑言之。若更有进,必将曰:律诗首句如何起,三四如何承,五六如何接,末句如何结,古诗要照应,要超伏,析之为句法,总之为章法。此三家村词伯相传久矣,不可谓称诗者独之秘也。”(《原诗·内篇上》)叶燮认为客观事物的“理”、“事”、“情”是诗歌反映的对象,诗人“先撰乎其理,揆之于理而不谬,则理得;次征诸事,征之于事而不悖,则事得;终絜诸情,絜之于情而可通,则情得。三者得而不可易,则自然之法立”。但是,客观事物的“理”、“事”、“情”既千姿百态又变化多端,所以,这“自然之法”又有“死法”与“活法”的区别。“死法”只能反映或描绘出事物的常态,如“眉在眼上,鼻口居中”,叫“定位”;“活法”则能反映或描绘出事物的发展变化与“妍媸万态”,是“神明之中,巧力之外”的“变化生心之法”,叫做“虚名”。因客观事物变化无穷,故诗歌的表现手法也应随之变化,即所谓“作者之匠心变化”。叶燮论诗法,充满着对立辩证的关系,带有总结性质。其后,沈德潜又折中论之,说:“诗贵性情,亦须论法。杂乱而无章,非诗也。然所谓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应,承接转换,自行神明变化于其中;若泥定此处应如何,彼处应如何,如碛沙僧解《三体唐诗》之类,不以意运法,转以意从法,则死法矣。试看天地间水流云在,月到风来,何处著得死法?”(《说诗晬语》)翁方纲《诗法论》则申之以“肌理”之说,主张“诗中有我在”,“法中有我以运也”,意谓以我运法而不为法所役。
通过上述回顾,我们了解到,诗人和诗评家们一般都承认诗法的存在。自南宋以来,在诗法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所谓“死法”与“活法”之争,多数诗评家都倾向于“活法”。但是,应当引起注意的是,大胆肯定诗法作用的人,如杜甫、黄庭坚,揭傒斯、杨载、李梦阳、李攀龙、王世贞等人,大都旗帜鲜明地提出向前人学习,并不将前人的诗法视为“死法”,他们大都大胆学习,努力实践,在诗歌创作中取得很高的成就或有相当的成就,一般都在当时诗坛上占有一席之地,甚或成为诗坛领袖,而反对“死法”,倡导“活法”者,在创作实践中一般都没有突出的建树。这种现象是否给予我们这样的启发:即只有深入创作实践,才有可能切实了解前人成法(或经验)的宝贵,才敢于大胆言诗法,并结合自身实践,将其具体化?从先秦至唐宋,中国古典诗歌一直在发展着,它凝聚着一代又一代诗人的智慧,是否应当概之以“死法”或“成法”而不加以深入研究,而简单地以所谓“活法”代之?活法是需要的,但具有高度艺术技巧的成法(不应视为“死法”)首先是要认真总结和借鉴的。从艺术发展的规律来看,首先是要了解前人已达到的高度,加以继承,或加以利用和改造,推陈出新,方能谈得上发展。在这一点上,杜甫是学习、继承、改造和发展的典范。后人动辄目前人之成法为“死法”而不肯下功夫去学习和借鉴,这也许就是中国古典诗歌至李杜为止而长期不能再向前跨越的悲剧根源。
Comments on Ancient Chinese Writing-Forms of Poetry
Lu Lingxiao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The writing-ways of poetry had been the subject of much controversyfrom the Song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This article tries to reviewsome of the writing-ways of poetry and expounds my own views on thesubject with a view to being able to arouse attention of the friendsin poetry field.so as to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of poetry creationin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