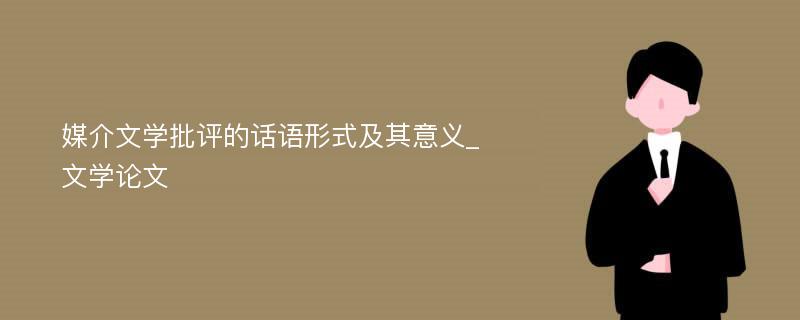
传媒文学批评的话语形态及话语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文学批评论文,形态论文,意义论文,传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9)09-0171-03
早在20世纪20年代,法国著名学者阿尔贝·蒂博代从批评主体的角度,将文学批评概括为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三种形态。
按照蒂博代的说法,传媒的批评,属于自发的批评,也被称为“口头批评”、“交谈式批评”或“新闻记者的批评”。“自发的批评是由公众来实施的,或者更正确地说,是由公众中那一部分有修养的人和公众的直接代言人来实施的。”① 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由于交流渠道、传播手段的相对简陋,公众的意见大多在俱乐部、沙龙、咖啡馆或街头巷尾等场所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来表达,那么今日的情形则发生了巨大变化。20世纪90年代后,不仅传统意义上的报刊杂志不断进行扩版增容外,作为当代传媒主力军的电子传媒,如电视、广播以及计算机互联网等,正在以日趋权力化的“媒体符号”改造着社会生活的文化结构与公共空间。正式凭借传播载体多样、灵活、便捷等优势,传媒批评迅速扩张着话语空间。创作新潮的命名,文坛事件的制造、文学奖项的评选,文学新人的推出等等,媒体积极参与其中,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引领大众文学感受与文学消费的主导力量。传媒批评使文坛的批评生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原有的批评秩序、规范、权威、理念渐趋消解,对此,学界从2000年始便不断有人著文对传媒批评提出质疑与批评,一些文艺单位还召开了专题研讨会。
其实,给“传媒批评”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很难。“媒体”,也常被称为“媒介”,原是指一种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中介物。根据美国传播学家施拉姆的见解,“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②。“媒体”概念的外延较“媒介”稍狭窄一些,通常用以指称大众传播媒介。③ 在当下,“媒体”这一概念主要用以指称以普通大众为传播对象的印刷文字读物,如报纸、各种时尚流行杂志以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等。而所谓“传媒批评”,主要是指上述大众传媒机构开展的批评活动,除了指媒体工作人员,如新闻记者、编辑、专栏制作人以及普通大众所发表的批评文字外,还包括由大众传媒组织策划的或是推波助澜的文学批评。大众传媒也很注重吸收学院批评资源,亦即蒂博代所说的职业批评和大师批评加入其中,培养出了诸多所谓的媒体知识分子。较之传统的文学批评,传媒批评的兴盛使人类自由表达的空间得以有效拓展,积极推进着文化的民主化进程,在引导普通大众的审美文化活动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媒体文化的发达改写了“大一统”状态下政治资本独享解释权、经济资本单一性交换的利益分配格局,使传统的文化等级界线渐趋模糊,使个人的话语空间得到无限的扩展。这也正如杰姆逊所描述的,“成千上万个主体突然都说起话来了”,文学成为众人参与的过程。媒体批评话题的多样化、批评文体的宽泛性以及批评文风的平民化等等,丰富着我们这个时代文学批评的立体图景。它与主流批评、学院批评共同营构了互补、争鸣、共生的批评格局。现代批评之父圣伯夫曾满怀激情地如此形容:“它更为警觉,更为关心现时的声音和生动活泼的问题,就某种程度来说,它装备更为轻便,它向同时代的人发出信号……它应该指定它的英雄,它的诗人,它应该依附于它喜爱的人,用它的爱关心他们,给他们劝告,勇敢地向他们呼喊光荣和天才的字眼(这使见证人大为愤慨),羞辱他们身边的平庸之辈,像军队的传令官一样高声为他们开路,像侍卫一样走在他们战车的前方……”④
认识一种话语形态,首先需要了解它的产生和存在。每一种话语背后,都有着自身的文化环境和价值体系,都存在着相应的运作逻辑。传媒批评也不例外。尽管传媒批评兼具媒体属性和文学批评属性,但由于作为其身份成规的媒体始终是其赖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所以其运作逻辑暗含着“媒体优先原则”。
毋需赘言,生存于一定社会环境中的大众媒体的主要功能是新闻传播,在中国,这一领域也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但19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大众传媒的产业化进程,一个突出的趋势是生产经营活动在媒体生存和发展中的地位渐趋凸显,媒体越来越多地以“企业行为”介入市场,以往存在于传媒主体间平和、稳定的关系逐渐为一种利益攸关的竞争关系所取代。由此,竞争机制、赢利最大化原则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渗透到媒体机构的生产过程中,并直接影响到生产者的行为选择。在这种机制下,是否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通常成为衡量一个媒体机构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受产业逻辑和利润动机的支配,媒体机构的守门人会严密监视市场的可售性以及发行量、阅听率、收视率等统计数字,以期在竞争中稳操胜券、赢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当大众传媒不再仅仅是一种传播工具,而是以超乎想象的力量作为独立的经营实体介入到社会生产的诸多领域时,它也把以市场为驱动力的上述运作机制挟入人类精神文化领域,而且嵌入到了其结构组织的认同性内部。媒体批评表现出的诸多特性及其价值诉求,其实都受制于媒体自身的运作逻辑。尽管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现象的文学批评从本源上来说与“市场”、“效益”等范畴并无天然的联系,但依旧难逃媒体机制这只“无形之手”的左右。这种无形的力量可以对文学批评生成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进行调控,对各种要素进行有机组合和支配,随时随地对批评场域施加强大的影响。
在传媒批评的话语建构中,文学批评这一人类具有神圣性和权威性的精神生产活动已不再是单纯的学理性研究,取而代之的是新闻性或游戏味。现象学美学家杜夫海纳曾指出,批评家的使命可以有三种:说明、解释、判断。尽管传媒批评也在实践着文学批评说明、描述、评价、阐释的功能,但由于其与生俱来的“文学之外”的运作逻辑,使其陷入一种难解的悖论。传媒并不只是简单地将信息由传者转达给受众,在商业价值和娱乐原则的驱动下,媒体工作者强调自身机构在规模巨大的传播场域中的阅听率、收视率,媒体批评也同样必须将满足这一统计数字,作为实现自己“意义呈现”的首要立场。为最大限度地获得当下展示效果,传媒批评并不是逢事必议、有评就发。媒体通常会遵照策划者的意图对文学事件进行非自然的叙述,将具有个体性和独创性的文学批评活动转换成一种公众性的集体事件表演,当然也会根据读者的意向随时调整其叙述方式以及话语内容。而所论事件的发生、发展与结束通常具有非常规性,不是由事件主角的作者或批评活动的主体来决定,而是通过媒体和媒体的精心运作来加以操纵。一如《三秦都市报》在2000年度对“青年文学博士李建军直谏陕西文坛”这一事件的报道及系列策划。主持这一系列报道的记者杜晓英谈道:“首篇刊发出来,我预料到文学界将发生一场地震我知道这个领域向来只有一种声音,是态度真诚但本质虚假的声音。我们太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了。而这声音宛若天际一声炸雷。《三秦都市报》这样的报道,形成的冲击力、深刻性和影响范围在陕西历史上堪称前所未有。在西安这个传统的城市里,敢于打破文学批评界死寂格局,不顾忌名作家面子,将少勇的批判言论作为争鸣的引子,当时,也只有《三秦都市报》有这个格调、眼光和胆略。”⑤。而《三秦都市报》理性而激情的新闻行进,在自觉地发现、创构、诱导受众接触、思考这一批评事件的过程中,尤其是通过“意见环境”的制造,引领社会上大量“孤立分散”的个人参与其中,使这个新闻形成一个强大事件。几个月持续不断的深度掘进,无疑使其报纸的阅读率和发行量有了迅速飙升。其实,这也是大众传媒与生俱来的“设置议事日程”能力的一种体现。其产生的客观效果,在于以形成“新闻热点”的方式扩容某种现象、某类话题的“在场”频率,反复吸引受众的注意力。
大众传媒介入文学批评的姿态是热忱的,也是富有策略性的。如前所述,传媒批评的兴趣指向并不在于对具体文学现象的内在分析和深入诠释。麦克卢汉曾指出,传媒产品的传播价值在于传媒所凝聚的受众的注意力资源。由此传媒批评在其运作过程中表现出很强的策划意识与策划行径,这种策划性广泛地表现在批评话题、批评栏目、播发形式以及议程的设置等方面。当下层出不穷的以媒体策划为中枢、以学术为表征、为获得市场准入证而在不同时机组织播发的书评、新书发布会以及作家研讨会、对话录等,均是媒体策划意识的鲜明体现。其策划的核心,在于整合行为主体的各类显性资源和隐性资源以期达到和益最大化。为争取信息接收终端的受众量,遵循市场逻辑的媒体批评尤其热衷于“文化抢位式”的追捧和炒作。这种炒作正在使文学批评活动自身所涵载的“超越性”、“可能性”的精神性思考沦为“消费性”和“现世性”。
“只争朝夕”的传媒批评在当下已成为广大受众日常文学的“收视指南”和“阅读向导”。这也使批评本身直接进入日常文化消费场域,批评成为一种消费。一般而言,文学批评是围绕着文学作品及其相关现象而进行的一种审美对话,一种文学思想生产。它是“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和缺点的科学。它是以充分理解艺术家或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所遵循的规则、深刻研究典范的作品和积极观察当代突出的现象为基础的”⑥。但一些媒体批评者对作品内容和审美价值缺少细密的解读,话题是否新鲜热闹,是否别致、有争议,是否能引起受众的广泛关注和兴趣是其选择、过滤和呈递的标准与出发点。其解析和推介的潜台词多是情、色、欲等等。尽管观点偏颇,或者未读原著任意作解,但经媒体一再强化报道,极易左右舆论的方向。蒂博代对此的说法较为尖刻:媒体批评“不读书”,“至于这些人的所谓幽默感,欣赏趣味和爱好文学等等,他们有一个非常简便的来源:他们装出他们读过的样子……他们进行猜测,听别人议论,做出选择,然后通过从他人交谈中听来的意见确定自己的看法。他们于是提出自己的看法。”造成这个原因是他们大多数人“忙于社交和经商”⑦。甘森和莫迪格利亚尼则认为媒体批评有其自身的“阐释包”,媒体对不同的事件有不同的阐释技巧。按照媒体的逻辑而非文学批评的逻辑,媒体常常把作家作品中具有新闻价值的质素从一个完整的生命中肢解出来,经过整合、强化或者极端化加以传播。在消费语境中,媒体批评时常“比其他批评更难以避免后人难以容忍的判断错误。它表达的是时髦的趣味,而时髦的趣味不仅有它难以预料的变化和荒唐,它并且顽固地顺着某些危险的斜坡而下,使这些倾向成为一种牢固的传统”⑧。我们看到,为了迎合受众的时尚潮流和接受水平,一些编辑、记者的话语实践通俗、“抢眼”,价值陈述滑落,批评伦理缺失。审美、经典、启蒙等等话语被不断解构或“恶搞”。在“讨论公共话题的时候,他们所遵循的,不是自己所理解的公共立场,而是隐蔽的市场逻辑,即使在诉诸批判的时候,也带有暧昧的商业动机,以迎合市场追求刺激的激烈偏好”⑨。传媒批评这个话语群落的存在,传媒批评在价值层面上的虚无色彩,其价值立场的混乱杂糅等已带给批评界无尽的隐忧。
综而观之,当下对传媒批评可谓毁誉参半。批评主体的不同,导致了批评的不同话语现象。批评主体的文化身份所引起的批评立场与方法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无论何种批评话语,向读者说话是其重要功能之一,是用火把来引导游人,使人们在黑暗不明的矿坑里看得出地下的财宝。现代社会可以说是“他人引导”的社会,而“他人引导的人却不再知道到底什么是正确的”。转型期的困惑与茫然,种种社会现实与压力带来的焦虑与恐惧,使得公众形成一种对于审美形象和精神引领的强烈依赖。但对于普通公众而言,他们可能并不具备独立的判断基础,这就尤为需要构筑文学批评的良好秩序并发挥文学批评的神圣职责。作为当代媒体文化衍生与绵延的必然结果,传媒批评“是庞杂的现实,它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是一种文学判断,也是一种经济功能;是言说,更是行动。它所牵连的人群和利益远比传统的‘学院派批评’更繁多、更复杂”⑩。作为新兴的批评力量和一种活力澎湃的批评形态,传媒批评具有合理、合法、合情的在场性,对其采取简单的抵制立场是不现实的。但传媒批评在主体精神的构建方面一如俞吾金所指出的,应确立法律意识、责任意识和平等对话意识。(11) 的确,当代文坛良好批评氛围的构建,首先有赖于传媒批评组织者、参与者、传播者的主体精神、文学素养的提升,以及符合中国国情的批评制度、批评文化的健全。
注释:
① 阿尔贝·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赵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46页。
② 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44页。
③ “媒介”的泛指意味浓厚一些,在宽泛意义上还有可能包括亲身传播媒介甚至物理传播、生物传播的介质。如果细致辨析,由于“媒体”的“体”字有“机体”、“个体”之意,所以更多的是指大众传播媒介的组织结构层面,即特定的一个个媒介机构,又可笼统地涵盖其组织结构和传播的渠道设施两大部分。参见杨鹏《厘清“媒介”概念规范学术用语》,《当代传播》2001年第2期。
④ 转引自阿尔贝·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赵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53页。
⑤ 参见《青年文学博士直谏陕西作家》http://www.sanqindaily.com/News/20081228/50753.html.
⑥ 普希金:《论批评》,载《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下,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1245页。
⑦ 阿尔贝·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赵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2-13页。
⑧ 阿尔贝·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赵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57页。
⑨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8页。
⑩ 李敬泽:《今日热读·主持人语》,《南方文坛》2001年第3期。
(11) 俞吾金:《媒体批评如何走出自己的怪圈》,《文汇报》2003年3月23日,第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