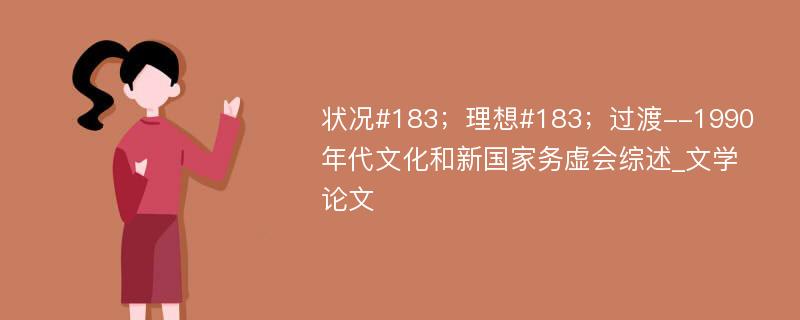
状态#183;理想#183;过渡——九十年代文化与新状态退谈会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状态论文,纪要论文,文化与论文,理想论文,退谈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12月3日,《钟山》编辑部、 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和江苏省物产文化传播中心联合在北京举办“九十年代文化与新状态”恳谈会,谢冕、刘心武、洪子诚、雷达、张韧、白烨、王干、陈晓明、张颐武、朱晕、应红、邵明波等十多位评论家、作家出席,对九十年代文化的各种现象进行梳理、回顾、反思,对新状态等问题作了深入,详尽的描述和富有启发意义的探讨。现将这次研讨会的发言提要刊登如下,以飨读者。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状况是比较好的。作家和批评家拥有一定的创作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度,来自非文学方面的干扰少得多了。大家以比较自由的心态,“各说各的话”。文学走向多元格局,大家都有自己的观点,各自不同的表述。虽然有很多的不同意见,但比较正常。文学和艺术按照自己的轨道运行,这是多年来我们希望看到的局面。不再是用一种声音来统一、代替大家的各种各样的声音,而是各人按照自己的思考、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文化背景来谈问题。大家在这样的氛围里,充分地交换意见,表述自己的见解,各种各样的意见冲撞、交流,最后达成融汇、共存,这是比较正常的,是一种常态。
九十年代大家关注的命题很多,如人文精神、文学的理想、文学热与弘扬民族文化、国学重建、重写文学史、“后现代”、“后新时期”、新写实、新状态等。文学界流传一句话:“新南京、后北京、重上海”,表明每个地域里,大家关心的问题是很不一样的。另外随着“世妇会”在北京召开,女性文学的书出了很多,如“红罂粟”、“红辣椒”、“紫丁香”、“她们”等丛书,女性主义批评也在兴起,也很引人注目。这些问题都需要反思、回顾、梳理。九十年代已经过去了六年,时间过半了,需要梳理、检讨我们所做的工作。今天把各位请来。就是想就以上问题展开讨论。
王干(《钟山》编辑部):
《钟山》1996年新设《思潮反思录》栏目,意在对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出现的一系列文化问题、文学问题、理论问题进行梳理,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现在需要用平静的、客观的研究态度面对九十年代文学,不能简单地用一种声音、一种标准、一种方式去解决丰富多彩的问题。今天,请各位畅所欲言,对《钟山》提出建设性的建议、批评,对新状态小说进行清晰的分析。
一、新状态不仅是个小说的问题
谢冕:今天到会的各位都各有各的观点,大家坐到一起,比较冷静地,而不是情感式的交流意见,还是“各说各的”,不一定强求统一。希望多交流,有交锋也没关系,尽量求得学理上的探讨。
张韧(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九十年代出现了许多带“新”字的小说: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新思维、新乡土、新都市等等。有人认为这些小说已经烟消云散,是过去时了。我觉得九十年代出现“新状态”等“新”字号的小说,这是一种历史现象,五年、十年以后回顾这段文学史,可能不会忘记它们。因为它们的出现不仅仅是商业包装,而是文学处在一种低状态下的一种“突围”,想冲出来。虽然存在误区,但应当肯定这种“突围”。南京《钟山》倡导的新状态小说,出现了一些不错的作品,如韩东的《大学三篇》、刁斗的《罪》、艾华的《启蒙》等。北京的新体验小说、吉林的新新闻小说,也有新作品出现。有的平淡一些,有的还在苦苦挣扎,还有新作家、新作品出现。新状态等小说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培养了一批六十年代出生的、三十多岁的作家,让他们一展才华,形成了新文学近期的“坡度”,这是非常重要的。再次,九十年代小说出现了个人性、个性化的特征。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样子”。但这些小说缺乏时代性、历史感。当然也不能用后者否定前者,只有个性化,才有可能出现时代性、历史性的作品。还有一个现象,许多小说有好情节、好故事,但缺乏深刻的思想容量,宽度,人们只是戴着新面具出现。应该说,九十年代文学还是大有希望的。
洪子诚(北京大学中文系):进入九十年代,个人化的写作倾向比较明显,作家也越来越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声音。这是值得肯定的,是文学进步的标志。但文学的个人性程度还不是作家创作的主动要求的结果,而是有很多的其他条件在内。文学潮流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包括新状态等小说的出现。在文学运动中,为某种目的性而设定目标,目前还存在。对文学预设目标,进行探讨、指导,有合理性。但很多名目是商业性的东西,为达到某种标志而推出一批作家,并受到关注,可能不能把个性完全发挥出来。文学评论从潮流的角度衡定作品,而不是从作家本身的创作来衡量,可能障碍个人性的形成。
谢冕:新状态不一定限定在小说方面,而可以有更多的涵盖。文学的诸现象、诸品种,甚至艺术方面的一些东西,都可以涵盖进来。如诗歌,八十年代现代诗的思潮很多,现在沉淀下来的,好像只有“状态诗歌”,还有些后现代倾向的作品。如王小龙、梁晓明、韩东、于坚等人的创作。“各人喝各人的茶,各人讲各人的话”。还有以伊沙为代表的,具有消解意义的那一部分。后新时期以来,诗歌也并不落后,只是理论上给予的支持,关心不够。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的“大转型”,在文学艺术方的表现,可能也还是有的。
二、制造思潮与适应多元
陈晓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今天,我想说一说文学的命运和我们的抉择。现在有些讨论出现“错位”,对文学本身的命运没有给予充分的理解。我们处在一种怎样的历史情境之中,这是无法回避的。如果不是历史地对待这些文化现象,不是历史地对待文学由来已久的一种历史进程,很多讨论可能出现错误。
在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社会出现两极发展趋势。一个是多元化状况,另一个就是对多元化不能承受的状况。历史的实际是多元化,然后是相当一部分人对这种多元化不能承受。因此存在着多元化与反多元化的一种对抗,或者说是一种反本质主义与本质主义的一种对抗。这种对抗,不能像过去那样上升到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模式之中,恰恰相反,这种状况本身就是社会多元化的表现。八十年代后期,文学在“制造”潮流,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文学自身产生潮流。过去的文学是和意识形态推论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推论实践就能推动潮流,像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都是历史本身提供的。现在我们发现文学潮流是被“制造”出来的,包括新写实、新状态、后现代主义、重写文学史等。我对“制造”文学潮流这种现象表示足够的历史尊重。在这个时代,文学恰恰是在“制造”潮流之中,才保持了它最低限度的历史敏感性。如果文学连“制造”潮流的想象力都没有,那它反抗“后工业化社会”,真的黔驴技穷了。后工业化社会的思潮是被制造出来的,人们必须制造思潮,这就是人对“命名”的一种重新定位。过去我们认为是由上帝“命名”的,是从《圣经》或某一部经典著作中拿到的,人只有通过“倾听神的声音”,才能对世界“命名”。现在不需要“神”,也不需要绝对的权威、绝对的经典,小人物通过他的想象力,他就可以“命名”。
到了九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个特定的状况,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被“消解”了,经济实力主义势头强劲。社会一旦把实用理性作为它的意识形态的话,那么肯定要消解“精神”。1992年第二轮经济大潮后,社会考虑的是如何通过行动来达到理想,而不是通过想象来达到理想。这是社会非常大的变化。人们长期以来是通过想象、通过“话语”来达到理想的,九十年代人们不得不通过行动来达到理想。这是一个用行动代替思想的时代。这使文学面临困难。但文学依然用自己的方式反抗这种东西,包括人们“制造”的一些文学潮流,是对人们行动的一种转变,希望在这个时代依然提供一种想象的东西,通过“话语”复制,达到仅有的一种理想状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必须制造潮流,不断复制。这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这恰恰表明人类处在一种比较平和的状况之中,比较实际,能够反省文学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文学在这种历史处境中所能做的事情。
为什么相当多的人对多元化不能承受呢?这是对“本质”、“神本”的一种迷恋,认为社会还需要中心化的东西来统摄社会的想象关系,蔑视对普通群众生活方式的批判,不能理解在这个时代行动的重要性。我们应当尊重这个社会通过行动去达到具体的生活目标,在基本尊重的前提下进行批判,这才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姿态。还想在这个时代取消所有行动,去通过想象,通过和“神”的对话来建构一个本体论的神学模式的话,这是非常困难的。这个时代不是不要理想,而是我们可能有什么样的理想,怎样保留理想。比如说不断“制造”文学潮流,这就是一种理想的冲动。所有的理想必须是对历史情境、文学命运和我们自己命运的一种认识,这样的理想主义,可能才是切合实际的。把过去传统工业社会、启蒙主义设定的理想移植到今天这个社会,可能是比较困难的。
新状态是一个内含很丰富的概念。为什么王干、张颐武和《钟山》提出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本身是一个象征,是一种“文本”。“状态”是很难定义的,“状态”是对象很难把握时使用的概念。为什么用“状态”来描述中国文学的现状,描述在后工业化社会转型时期的这样一种文学情境呢?新状态的特点是非常鲜明的。第一,不再能明确找到文学的方向感,只能表述个人的记忆,个人的经验。文学在整体上失去了方向感。失去方向感并没有什么不好,不要一听到失去方向感就觉得完了。因为我们不必再奔赴一个终极的目的,不再需要进行“精神迁徙”,现在人类现实就可以生存下去了。就整个社会、历史来说,最高理想无非就是和平、理性、发展,这些东西是非常实在的,具体的,可以通过人类的具体作为、理性化的交往就可以达到。文学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中,这是一种非常有象征意义的一种把握。第二,从表述方式上看,主体的意识也失落了,个人不再充当历史的主体,觉得自己就是一种个体,个体处在一种游走的状态。因为价值多元化了,人的交往多元化了,接受的信息非常广泛,交往立体化、交叉化了,个人就不能一直处在主体的位置上。同时,个人的存在权力受到尊重,每一个人的存在,每个人的价值选择,都有他的合理性,主体处在一种漂移的、流动的状态。所以新状态是有相当的合理性和涵盖面的。第三,在叙事方面、语言方面,都与个人的记忆有关,与个人的随意创造有关,更多的打上了个人化的印痕。总之,新状态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是在这个时代反省个体在文化存在中的命运及存在的一种方式。
谢冕:我们需要交流。晓明的描述很好,是这种状况。需要探讨的是:文学在这样的状况下,究竟还能保留什么样的价值呢?文学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陈晓明:当然有。人类在“后工业化社会”中,是处在“交往理性”上来理解差异的。过去文学是号召大家奔向一个共同目标,现在文学是寻找差异性,个人以他个人的记忆,对待生活的方式,进行交往。现在人们在同一个平面上进行交往,文学的本质不再是关怀“终极价值”,而是关注“交往理性”。
谢冕:陈晓明今天讲的,比较偏重理性,重视行动。现在文学的确展现出多元化的前景,这个前提我们是共同的。你认为当前出现了多元化与对多元化不能适应这样一种现象,认为文学失去了方向感、目的性,强调理性,强调行动。我有一个疑问:在现代社会中,或者说是“后工业化社会”中,人的灵魂需要寄托、安慰,物质社会更需要人际之间的交往,精神与情感变得非常重要。不然的话,我们不能理解在西方后工业化的社会他们还需要宗教。理性、情感之外,在社会机制上需要文学通过情感对人润滑?
陈晓明:这不矛盾。这里牵扯到对“交往理性”内涵的理解。“交往理性”定位在平面差异性上的交往,承认差异性,不再是像过去那样是对“神”的诉说。文学在很大意义上可以这样认为,某一个叙事者讲了一个故事,你可以把它看成纯粹是一种个人的经历,是个人讲述的神话,仅此而已。通过他的讲述,你可以获得一种想象的、情感上的满足,而不是你们共建了一个想象关系。
谢冕:有时候我不知道这种期待是否合理。比如,我读了何顿的小说,觉得很有趣味,很爱读,平常人,以平常心读,觉得很爱读。但读过之后,觉得有点欠缺。当然,消费的过程是很愉快的,故事很丰富,很迷人。完了之后我期待:他讲这些干什么?
陈晓明:在这种差异性的个人化的小说中,如何找到一种有力度的现实和历史的穿透?看他们的小说,会有一种不满足感。我觉得朱文的状态相当不错。他有一个非常奇妙的特点,就是把这个时代无聊、乏味、平庸的东西拎出来,进行敲打、发问,如《傍晚光线下的一百二十个人》、《食指》等。朱文可能是九十年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属于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作家。在后工业化社会,在文化走向日常化的时候,作家如何运用技巧把琐碎的东西拎出来进行刻画,这是值得研究的。
三、新状态作为一种孔道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九十年代文学形式变化特别大。先不能着急,先了解情况,然后进行不同的描述,不同的分析,这一点非常重要。现在看来,文学、文化方面新的东西非常多。六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如新状态阵营中的何顿、韩东、朱文、徐坤、陈染、林白、述平、刁斗、邱华栋等一大批作家,创作力非常旺盛在对当下的描述、表现的力量也是非常强的。这个现象必须研究。
王干:以前,老是要求作家写当代生活。九十年代,新状态作家都是写当下的生活的。哪怕是一个游走者,一个局外人,与当下的社会生活、文化状态也是密不可分的,正如通常所说的“滴水见太阳”。以前要求写“正剧”,我们现在没有写“正剧”,没有把它“正剧化”而已。
张颐武:这些作家的创作力非常旺盛,创作数量非常大,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从传统现实主义的标准看,也有相当的质量。他们一出手起点就较高。这些现象怎么解释?最早商量新状态问题的时候,就感觉到对这些作家没有一个合适的解释。新理论、新框架的提出,首先是因为理论在重大的文学变化面前感到非常无力,描述与解释,难度非常大。新状态以及其他一些“新”概念的提出,都是基于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解释的困境”。新状态这些概念的提出,是对这种状况的一种挑战。另一方面,也有刊物包装方面的因素。不断处理这些变化的情况,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主体变成非主体的个体,寓言式的文化目标的消解,大众文化的崛起,大众文化中很多复杂、暖昧、含混的东西对文学的干扰、进入,雅俗文化的合流,雅文化流通方式的通俗化等,解释比较难。没有解释就进行批判,可能过于仓促,过于着急,缺乏理论的深度。
九十年代发展到今天这种状况,有一个过程。在知识分子内部出现了许多分歧、争议,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这些分歧、争议也很正常,这是新时期以来首次出现这种状况。知识分子集体参与社会进程,曾经是非常投入的。各种分歧、争议的出现,标志知识分子原有的共识,有了一定的破裂的迹象。这种分裂,不是有没有理想的分歧,而是要有什么样的理想。这种理想是沟通的、对话的理想,容忍社群内部的差异性,容忍社群内部不同的声音,然后寻找基本共识,也是可能的。把差异作为中心,然后尝试在沟通中建立共识,这样就可以找到一些共有的冲动和问题。目前社会中社群内部的矛盾是非常大的。北京周围出现了“河南村”、“新疆村”、“浙江村”等,而且在以几何级数增长,这种混杂性在急剧扩张。北京越来越像“国家村”。社会的矛盾,社群内部的冲突,在急剧变化的社会中已经成为一种隐含的因素。这种状况下,不能用对抗性的办法解决问题。新状态“新”在哪里?一个是全球化,一个是市场化,造成全新的状态。如移民,过去是一大批移出去,现在有一批外国人移进来,内、外移民都有。社会的混杂、掺杂,已经到了没法控制的局面。如何顿的小说,不是没有理想,力度不够,但确实非常真挚,表现的是民间的世俗情感,在世俗关怀中生长,不同社群,不同理想之间,寻找一种对话关系。多种理想之间,不能互相替代,但是可以沟通,形成有差异的、比较和谐的社群关系,尤其是找到一种沟通的“孔道”,这对于目前中国的“后现代”、“后殖民”的社群来说,各种文化之间需要沟通的途径。知识分子内部有很多误解,说一部分人没有理想了,这可能是一种想象的认知。现在是要在不同的理想之间寻找到一种沟通的“孔道”,这是当务之急。新状态就是切入今天的“孔道”的尝试。
洪子诚: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社会之间贫富差异比较大。中国社会的分层化是一个长期的现象,过去是意识形态分层,现在转移到财富拥有多少的分层。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现在除了沟通之外,还需要分流,文学也需要分流。理想也有各种需要,也应该满足各个阶层的追求、需要。
刘心武(中国作家协会):我想问谢老师一个问题,你觉得小说中缺一种东西,缺的是什么?你能描述一下吗?
谢冕:这个问题说起来话长了。我觉得中国的文学和批评,缺乏“自律”,这是我个人观点。我有一种焦虑,可能是很虚妄的。中国的文学家,需要保持一种清醒。当前商潮滚滚,人欲横流的情况下,中国应该有一部分人,总得思考一些问题。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悠久的一个民族,应该有一批作家,立志于创造出人类最好的东西来。我为什么批评一些现象呢?比如对贾平凹的批评,他很聪明,很有才华,但在《废都》中有些不重视自己的才华,让人惋惜。完全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来,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可能有人认为问鼎诺贝尔文学奖是很没有意思的事情,可我不这样看。我认为诺贝尔文学奖还是一个标志。一个社会,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价值观,但一个民族,需要有些人做这样的事情,像普希金、海明威、梵高、大江健三郎那样,取得令人瞩目的、不会过时的成就。我觉得朱文、刁斗、述平这些这么有才华的作家,要是写人生正常的状态,从中提炼出一些东西来,会增加一些份量。
陈晓明:对于新状态的一些年轻作家来说,他们的作品可能还缺乏一种力度、穿透力。可能他们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但对生活日常性的一种表述中,力度是直觉、内在的。
刘心武:我谈些思维的断片。谢老师的这种焦虑我特别能理解。我们共同经历了一些重大的社会变化,有比较接近的生命体验。对九十年代文学有些焦虑,觉得有些欠缺,也是爱护的态度。当前文学确实出现了无力想象的困境。坦率地说,整个人类目前处于困境之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理想的破灭。人类历史上一度开放的硕大花朵凋谢了,当年我们是多么兴奋啊!现在硕大的花朵被非常具体的世俗欲望击碎了,只剩下一副“怪相”,让我们这些戴红领巾长大的人,有一种破灭感。我承认这是一个理想破灭的时代,但我不焦虑。
政治社会理想不能要求文学家来提供。文学家虽然不去表现社会政治理想,但他的理想肯定包含社会政治理想的取向。但当社会上实用理性弥漫的时候,文学家没有社会政治理性可以依托,你不允许他惶惑,这是不现实的。九十年代只能出现这种文学,也只能是这种状态,也就是新状态。但这种新状态不宜评价很高。为什么是新状态呢?因为它不得不告别一些东西,这是告别可能是被动的。将来回顾这段文学史,可能是被忽略不计的。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你没有办法。一部精略的中国文学史,干脆就没有你这一章。中国历史上有过很多这样的时期。
我将自己定位在民间空间上祈求理想,也就是诉祈求生理想。坦率地说,现在有些作家发表的作品没有人生理想。比如王朔的作品,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其描绘的生活场景:此时此地,此生此意。不追求不朽,也不追求永恒。贾平凹的《废都》也没有理想,诗酒消磨。在性和梦中消耗残生。新状态的一些作品主观上也不想提供任何人生理想,但有认知价值。如《废都》提供了非常真实的理想破灭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多年后可能有史料价值。
四、90年代文化的过渡性
雷达(中国作家协会):今天中国社会是多元并存的社会,文化是多元并存的文化,文学自然也是多元的文学。九十年代文学发生了许多事件。一是文学的商品属性明朗化。原来潜隐,现在明朗了。这对文学的功能、地位,都有影响。市场经济,后冷战时代,物化浪潮的兴起,使得物质和精神的冲突,金钱和良知的冲突剧裂化了。今天的作家做的工作是不够的,但是是可以理解的。其次,关于理想,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话题。在今天的作品中灌注鲜明的文化理想是很困难的。新状态强调块和面,而不是线性思维,因为前面终极的东西看不到了。今天的价值体系是多元的,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理想、崇高。建立切实的价值、理想观,难度是很大的。如在《废都》中,作者与主人公拉不开距离,不能站得更高。小说表明,一旦失去理想,会变得多么可怜。知识分子所处的生存与精神困境,这是有世界性的。性只是一个通道,表现的是自我丧失的一种状况。今天的知识分子是否都落得庄之蝶一样的下场,但困境恐怕是一样的。这也是九十年代的一种现象。再次,很多作品采用文化视角,文化眼光,写历史,写本能,写性,意识形态的因素很少,写家族史的小说也是文化视角下的产物。
白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时期文学马上就二十年了,这是五分之一个世纪,总结反思是非常有必要的。文学与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过渡性。二十年有两次重大的过渡,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是第一次过渡,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期是第二次过渡。第二次过渡规模和程度都大得多。从文化角度看,主要是角度的过渡,过去我们不从属于自己,代表官方、政治、中心、主流,现在才出现了角色的转换,走向边缘化、民间化、职业化,过去是“我们”,现在变成了“我”。重新寻找精神依托,锻造自己的生存能力,成为文化人不得不考虑、不得不解决的问题。从文学上看,是方式的过渡。运作方式不一样,商业手段介入了文学。其次是文体上的过渡。传统的东西没有了,家族史、自传化长篇小说出现了,出现了散文化、杂文化的倾向,长篇小说成了文坛的自由市场,很繁荣,但也混乱,精品不多。新状态是文学方式变化的一个概括。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成了主流,文化素质较高,艺术上出手不凡。但作品尚缺乏力度、厚度,带有太多的随心所欲。
朱晖(《光明日报》社):当代文学的起点是六十年代的文学,现在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一批作家成了文学的主流。这是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前者是作为漫画化的、作为抨击性的东西出现的,那时的理想主义是带有很多现实意义的,要表现新生活的新气象,新主人的新面貌。但后来进入末流,第三次创业没有完成,成了喜剧。今天的主人,应该是珠江三角洲那些“创业”的人。他们指责文学,说你们写的是“亡国之音”,寻找当代“创业”的代言人。我们在承认文人被推向边缘的同时,也得承认文学还是圈子内的话语。他们是经济时代的主角,我们只不过是配角。大体可以说,长江以南,要求表现史诗式的创业精神,长江以北,还是后工业化的灵与肉的冲突,主要感觉到的是经济、商潮的负面效应,更多苦闷、愤怒、宿命的东西。
新状态小说的出现,是非常值得考察的现象。我比较赞同九十年代文学的提法。1989年是很有意思的起点,此前文学的困惑和文学的支撑点都是政治,一种代表是尽量把政策用好用活,另一种代表则要剥夺政治的权力,拼命扩大文学的势力,现在两种代表都走到了尽头,离开了领袖、文学史核心的位置,新时期就结束。后新时期,或者说九十年代的文学,出现了国际化的色彩,泛人类的话题,但新状态不是最大的筐,什么都可以装进去。这个概念与后新时期有点重合。六十年代作家群是新状态的主力,他们的作品让人感觉缺了点什么,描述缺乏理想,并不等于要求表现理想。目前还缺乏力度、厚度。相反,有些作家有能力承担时代的任务,但是他不去承担,让人失望。有理由相信,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一作家群,可以在原来废墟生出的小草中间长出参天的大树来。
(邵明波 整理)
标签: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九十年代论文; 艺术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废都论文; 陈晓明论文; 作家论文; 谢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