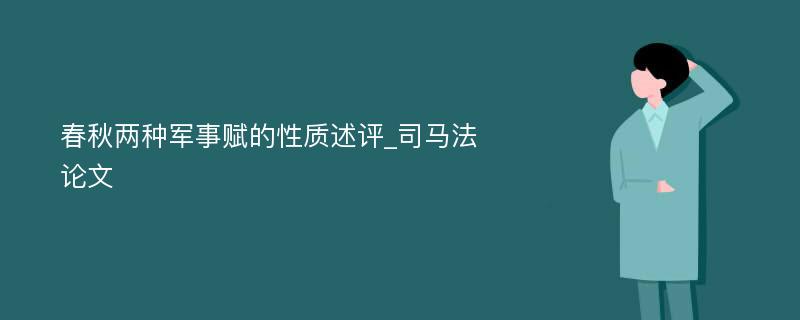
春秋时期两种军赋性质的检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性质论文,春秋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春秋时代,不论在政治或战争上均出现了莫大的变化,而记载当时局势变动的可靠史料,则当推《左传》、《国语》等被汉人奉为经书的几部史籍。可是各书记载春秋时代的制度和史事,却时有分歧以至于矛盾,然则面对此等紊乱的材料,加上后世如汉儒之释经、六朝以至唐《疏》、清人的考证、近代以来中外学界对这时期史料的探究和诠释,史料似乎更加分歧,结果仍然很难还原出一套清晰而较合乎事实的历史画面。尤其春秋时之史料多载于经籍之中,成了历代以来学者研治的主要对象,造成这段原已纷乱的史事更加复杂,人言人殊,原来已是一套套列国互有不同的异制,载于出自不同地域、撰者、时代的典籍,再经分属今古文派经师的诠解、清代学者的攻驳辩难、近人从疑古与辨伪学、文献学上的讨论,交织出一幅极其混乱的画面。以下试由春秋时代同载于古本《司马法》中的两种军赋制度探究二者之间的性质。
《春秋经·成公元年》记载鲁国实行了一种新的赋制:“三月,作丘甲。”《左氏传》对此解释道:“为齐难故,作丘甲。”[①]《诗·小雅·信南山疏》及《礼记·坊记疏》云:“《成公元年·左传》服注引《司马法》云:‘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有戎马一匹,牛一头,是曰匹马丘牛。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生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谓之乘马。’”[②]是传的本事,乃鲁成公元年(公元前590年),鲁国为防备齐国进攻,于是设立了丘甲制度。《诗疏》和《礼记疏》则记载了汉代经学家服虔引用《司马法》作为解释。
有关丘甲制度的内容,服虔引用《司马法》所载的有关条文以为解释;从字面上说,丘是指地方的单位,甲则为地方所要抽出人手以当“甲士”之役。由于这是一种向平民征抽兵员的制度,因而亦可视为一种军赋系统,而本段《司马法》之文,《汉书·刑法志》、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皆有引用。然而郑康成注解《周礼·地官·小司徒》“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时,却引用了《司马法》中另一条不同的军赋制度,其文曰:
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为终,终千井,三千家,革车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终为同,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礼记·坊记疏》引马融说亦节用本条《司马法》之文。两条军赋制度的分歧,主要在于地方单位的划分及“乘”这一单位的供员人数。服氏所引者,地方单位为邑、丘、甸,所出战车为长毂,兵员合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共七十五人。而郑氏所援引者,地方单位曰通、成、终、同,所出战车属革车,兵员合士十人,徒二十人而为三十人,二者相去甚远(并见《昭公元年》服注引《司马法》条),而历来亦为此而争论不休。
两条不同的军赋,清人以来颇多推测,归纳起来,说法约有五种:
一以两项军赋,分属不同性质:即一为“畿外邦国之法”、一则“公邑乡遂之制”,此乃同时间所行不同地方单位的两种赋制。主张其说的包括《周礼·地官·小司徒》、贾公彦《周礼注疏》、孔颖达《礼记·坊记疏》、梁玉绳校《逸周书》、王鸣盛《蛾术编》卷六五及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等。如刘氏之说便谓:“不同者,《小司徒》辨畿内都鄙之地域,谓公卿大夫畿内采地之制,此之所谓诸侯邦国出军之法,故不同也。”[④]则两种军赋,为采地与邦国的不同。故《司马法》得并载二制。而服子慎所引本条,实属于乡遂及诸侯国推行的一种,名曰“畿外邦国法”。
第二种看法,则以为两个赋制,并没有地域上的差别,其不同只在于制度的执行方式上。主张其说者有:江永《周礼疑义举要》卷三、金榜《礼笺》、刘宝楠《论语正义》卷一、黄以周《礼书通故》及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二○等。
若江慎修《周礼疑义举要》卷三言:“七十五人者,丘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调发之通制。《鲁颂》‘公车千乘’、‘公徒三万’,正与《司马法》合。”[⑤]孙仲容《周礼正义》卷二○则谓:“七十五人者,任民之法,非即兵车一乘之数;三十人者,出军之法,兵车一乘,二十五人,余五人将重车也。”[⑥]即本派意见,以为其一之制度乃征兵的常制,一则为加调兵员时所引的临时方式,服注所引之制,即江氏所谓“丘乘之本法”。
以上两派之外,又有从《司马法》一书本身的性质着眼者,于是产生了第三、四种说法。
第三种以为两种军赋的差别,本乃为古今文制度的不同,故实难以强行疏通。主其说者乃今人金德建。金氏在所著《司马迁所见书考》第五十八章《司马法的流传和作者的推测》[⑦]及《司马兵法兵车出师之今古二说及来源之解释》一文[⑧]即主上说。金氏谓:“……《司马法》的每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即应是《周礼》的每乘所有的人数,这一说的《司马法》亦即是古文说。后说‘七十人,徒二十人’与前说不同,应属于今文说。”[⑨]金氏从军赋制度的不同来说,认为乃今古文经的分野。观其想法,颇具新意,即避免了清人为了调和及妥善安排二说而作的繁琐论证、制度纠缠以至牵合附会,且从经学角度而言,由礼制入手以判别今古文经学的异同,正为清末廖平以来所提出的一条理清二派胶结的“特效药方”;观乎金氏举列二说之与文献互合处,用判二法今古文所属之余,再进一步追溯今古文的来源,从典籍所载的史例以求出二说产生的时代背景,窃以为其法极为可取。且施之于治经,正能扫清藩篱,以见本源,对判明经说来源及今古所属,极有帮助。然施之于本条,尚有其不足者。
所以说金氏有不足之处,实因本条的军法,既可取征于史,而非空谈礼制;加上金氏在考证时,受到所用资料不全的影响,逆推出自相抵牾以至不大合理的结论。勿论其忽略了先秦经子诸书所载有关一乘三十人的记载,而反以《吕览》及《淮南鸿烈》作为史证根据(因据二书,仍可得出每乘三十人之法“系古时确有”这种制度的结论)。其最不可通者,乃在于用《后汉书·匈奴传》并《孙子》张预注引曹操《新书》以证《司马法》“七十五人一乘”的说法,引证之余,竟又“得出”以下的结论:“这又可见古文经说的产生于其时的物质环境上,不免受到其时实际制度的影响而立说的。”[⑩]其理论本身固无大误,然以《司马法》古文说只能合于东汉以至曹魏时之史事,无形将《司马法》古文说为古制的记录完全否定;且金氏在文中明言:“《司马法》的前说(七十五人制)可谓与《周礼》的六军三军是相通的。”[(11)]金氏既以“七十五人制”属古文说亦根据其有合于《周礼》而推论出来,今又以其说产生于东汉、曹魏,难道即以为《周礼》成书于东汉之后吗?如此说来,则其主张又比康南海《新学伪经考》之说更要“骇人”矣!且金氏在其《司马兵法的流传和作者的推测》一文之中,本曾明言《司马法》一书“最初是出于齐威王时候的大夫们所述作,而后来流传到西汉初年的时候,经师们又曾经把部分的材料增加进去。”[(12)]依金氏言,就算至迟加入《司马法》的材料,下限亦不过西汉,现在金氏又以东汉以后的例子来证明,并以此说的产生乃受实际制度的影响,无疑跟其说互不相符;且将其下限硬推至东汉以后,甚或以《司马法》中的古文说材料为东汉人所羼入,意下即以服虔所引《司马法》的材料乃服氏根据东汉兵制而伪造,附入其书,成为与“三十人制”今文说不同的所谓“古文说”;是其说法与刘申受、康南海的刘歆伪造古经说没有大异。实际上金德建之说,也间接贬低了今文经的价值,把一些对春秋时军制的实际记录也看成东汉人的增益,其说并无实证,因而自然难为学界接受。且又有自相矛盾之嫌。
金氏辨别今古,从经学角度来说,固多可取;然而本条所载军赋,如加深入考释,证以历史事例,则又不宜简单地划分为今古二项。由于今、古文的制度并不相同,“赋殊”(赋制不一样)的问题仍然未获解决。本条《经》文的来源,实根据史事而来,则由史事上去探究这条不太关涉《经》义的条文,又当比较辨析《经》文的今古学为清晰。且先秦典籍中所记载的制度,实难以简单地区分出其究属于今文还是古文;如金德建氏视为今文说的“三十人制”,根据金榜、孙诒让等人的详细考证,这项制度实多本于《周礼》,且于《左传》、《管子》皆可得到验证,则本条又当有古文说的成分,可见金氏所言,或未尽当。如此分别,实难将军赋之制理清。因而欲要解决此题,未若归于征实,取诸书战争例子及记载而加以归并检验,以求出二赋的曾否实施,还有时代与地域的先后,用以复原它的原来面目。金氏用今、古文作为区分,仅能解决二者表面的矛盾,而未能对于二者的实施及取以证明《左传》的问题作出彻底的分析。
可见金氏探讨这问题的本意虽然比较其他清代学者为新颖,可是他硬将材料看成属于东汉古文家所制造而补入其书中,实在难以取信于人。
第四种看法,乃面对两种不同的军赋制度,二者又似乎各有佐证,可是经过仔细的检核后又有部分未能找出实例作为支持,于是乃有学者转而怀疑《司马法》一书的可靠性。若清人惠士奇《春秋说》卷一二云:“《司马法》以田赋出兵,其法本于春秋,行于战国,非周礼也。……杜预以《司马法》注《春秋》,往往不合,多类此。”[(13)]查杜注所引用的《司马法》条文同于服虔的引用,因而其注解实袭自子慎而稍改其意。(也就是刘文淇所说的“服杜虽同据《司马法》,意各不同也。”[(14)])惠氏于此,所以批评杜注引用《司马法》时不称其书,而以为其军赋出于“周礼”,与军赋内容并不相同,杜注用《司马法》注《左氏》多不合,这是由于他把春秋时的制度误看成周制的缘故。
此外,对《司马法》一书,最不信任者,当推日人竹添光鸿为代表。其《左氏会笺》之中,便花了大量篇幅以举证《司马法》的不可据信。其中一个理由,即为这两种军赋制度的不同。其文曰:“据《周礼》‘九夫为井,四井为邑,……谓之乘马之法。’而《周礼·小司徒注》所引又与此不同。”[(15)]由这个不同,继而举出证据而说:“盖计地出车,《周官》本无此法,《司马法》不但不合于《周官》,与诸经均不能合。”[(16)]竹添氏的怀疑,可谓最激烈者。而另一外国学者瑞典人高本汉亦以《司马法》不可信,其云:“服虔称他的注解是引用了《司马法》的说法;而郑玄所引的《司马法》则又与服氏的不同,可见,《司马法》的材料是靠不住的。”[(17)]夷考以上三说,惠定字所言实际上并没有否定《司马法》一书,只是以其制度行于春秋,而杜氏的著书,却为《周礼》之用,实在有诬于《司马法》。因而惠氏实际上是针对杜氏的淆乱书名。
至于竹添光鸿举列大量《传》文的史例、制度来证明《司马法》之与《左氏》不合,固有可取,也可见《司马法》所定立的军赋规定,确实有不符于《左传》、《周礼》者;然而竹添氏不知“三十人一乘”及“七十五人一乘”之制,本为一项条文的规范,对于实际出战征调军队时,又不必一一符合于条文。尤其成公元年“作丘甲”以后,郑国子产亦于昭公四年(公元前538年)“作丘赋”,《孙子兵法·作战篇》亦载孙子行“丘役”的事,这也是改变成法、扩大征兵数量的条文,其所实行的制度已与《周礼》不同,又怎可以斤斤的求为互证呢?且《左氏》所记载,也是实行出来的实例,尤其在春秋中叶以后,形势渐改,成规日坏,各国也自行他们的“权宜之制”,在取用《周礼》、《司马法》的条文以求准绳于《左氏》,又怎能一一尽合?竹添氏也许昧于文献所载不合,而指斥《司马法》与《左氏》不符,从而否定其书的价值,不免与人有鲁莽灭裂之感。且竹添氏从据《左氏》条文,而得出“车之多寡,固不必尽准乎其徒之数,亦不必尽准乎其民之数矣”;此等说法,固然足以纠正杜元凯引用《司马法》说《周礼》的错误,且又用史事来否定“诸经”所载的制度,因《周礼》、《司马法》以外,准民出车、随徒合乘之法,来明载于《孟子》、《管子》,用实例以勘条文,这只能说是各国渐变成规之势日成而似不可据以否定条文之所载。因典籍所载,本来就记录了由井田制破坏后的史事转而否定《司马法》记载的条文,且斥其与“与诸经均不能合”,不免有颠倒本末之嫌矣。
就是《司马法》所载制度有与《周礼》条文不合的地方,这也是微细之处的不同及性质各别,实未可如竹添氏般一下子否定其书。诚如对此等问题了解最深刻的孙诒让有言:
作《司马法》者,未尝不知井与不井,形体不一,但分地校量,则纷互杂糅,不便计算,故设此计里令赋大略之疏率,无论井与不井,一以此通之;不过谓地方百里可出车百乘,地方三百十六里有奇可出车千乘,地方千里可出车万乘耳。彼本不谓尽天下皆为井田,而说者必欲牵就井数夫数,一一校核,求其密合,其有当乎?[(18)]孙氏所言,深明礼制同异的缘由,指出了治礼时牵求诸制切合无间这种做法的不妥,亦足以回答竹添井井因数未不同而所提出的质疑。至于高本汉只因为看到郑、服二家引用条文的不同,即遽而否定其书的可信,那就更不足论了。
第五种理解,则多从春秋时期各国局势的改变着眼,尤其因要争夺渐趋剧烈而日有变化的战争模式。在春秋中、后期始,战争形式渐次为车战变为步兵战争,徒卒地位亦大为提高,由于战争频仍,兵员及物质数目的需求亦大增,间接促成了田制和军赋的转变。而《司马法》中记载郑玄注所引用的“三十人一乘制”正为周代以来比较通行的军赋成法,而服所引“七十五人一乘制”则当为战争形式改变,对步兵需求大增的形势之下而改变的新赋制,而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晋人“作爰田”、“作州兵”,正是改行新制出车之法的明确记录。其后成公元年(公元前590年),鲁国为防备齐人而推行的“作丘甲”、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楚人“量入收赋”及昭公四年(公元前538年),郑之执政大夫子产“作丘赋”等记载,皆为对战争需求的扩大而变易井田及军赋旧法的措施,此为春秋形势发展的必然,这也是导致了《司马法》中载有两种不同军赋制度的主因。
近年学术界对于军事制度颇有研究之风,如今人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19)]、韩连琪《周代军赋及其演变》[(20)]、陈恩林《先秦军事制度研究》[(21)]及田旭东《司马法浅说》[(22)],皆主张以春秋形势作为判别两种军赋的标准,他们所持的原因,应当亦同为根本于春秋中后期军事大势的变化而提出的。
此派的特点,重在战争模式的转变以探求此用赋不同的现象,其观点由以往清人纠缠于诸经异同以至否定两种军赋的做法更加宏大:彼等乃从整个时代的转变及军事上的需求来说明。此派大致把“三十人制”看成西周至春秋中叶的旧制,由成公元年“作丘甲”始,乃有七十二人制的出现,如《昭公十年》、《昭公十一年》、《二十一年》所载的“徒七十人”一词,正为“七十二人制”实施的反映,这种说法及证据,也足以消除金德建以“古文说”七十二人制出于东汉以后的误解。
综观上述五派,第一、二派属于传统学者在释经上的争论,不免陷入了“经文各殊,设法疏通”的迷雾里,近人在前人纠缠不清的基础上,又提出今古文的分歧一说,以图解决两种法制载记的不同。这个方式虽然因此而避开了二法之间的纠缠,可是仍没有理清两种军法的本质,且更使用了今文派所谓“古文经学家伪造资料”的臆测来说明问题,实在有欠客观。另一些外国学者,则只看到了文献所反映出来的表象并不一致、制度上所开列的数据也不相同,于是轻率地否定了《司马法》的记载,完全无视于清人的考订成果,亦不足取。近今学界在对这个问题作出探讨时,虽未有专门就经学方面出发,然而却能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再从宏观的历史眼光分析不同的军赋制度如何在这个“剧变”的时代中此起彼落——随着战争形式的转变而产生改革,以应付时势的所需;其中所关涉的问题也大。当时的情势,也正是由对别国的侵吞,促成了战争频仍,在战争形式的改变上,由使用起来比较灵活和快捷的“步兵”取代了以往只适合于平地使用的战车;加上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在大国威胁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各国对兵员及物质的需求亦大增,于是以往的军赋制度也开始改变,各国纷纷把以往丘甸所出由周制的三十人,改变为《国语·齐语》所载的“齐式”五十人,继而至鲁所实行的“丘甲之制”的七十五人,如此,以往只有公族才可以担任的“甲士”(即“革车”的旧制),现在变成了丘夫亦得参与其中,进一步促成了井田制度的崩溃,继而亦由“税亩”及“丘赋”来作替代。因此,第五种的看法实际上取能兼顾春秋时局的发展,不论在制度、史事、经义方面,均能较合理地弄清两种不同军赋制度之间的性质和关系。
站在理解服子慎注解之事上来说,也只有第五种说法最能体现服说的真义。如依第一种说法,即本于《周礼》贾公彦《疏》以下,视服注为“畿外邦国之法”,即只施行于乡遂、邦国,其说法则只是纯粹为了区别郑注所引用的“三十人制”,不免有强加区别之嫌。此说孙仲容已有驳斥。第二种说法则把服注所引用的军赋的条文看成“丘乘之本法”或“在国制军之定法”(语见黄以周《礼书通故》卷四○[(23)])。此说法既能区别郑注所引的条文,且又能配合《成公元年》“为齐难故”的前因,更避免了“七十五人制”无法在《左传·成公元年》以前找到记录的客观证据,是其说法本亦可取,然而为了要说明二法得同时期推行,于是便须疏通“邑”、“丘”、“甸”与“通”、“成”、“修”、“同”的关系,其中所涉颇为广泛;且二者条文,也未必可以一一互通,这是本派的一大缺点。第三种说法把服注所引的军赋制视为“古文说”,理据则在于其说可与《周礼》互通。其说本亦无妨,惜金氏又以为其法只能取证于东汉以至曹魏,把此法的产生途径归于东汉古文家的“制造”,换言之等如以服虔伪造《司马法》的材料!幸而取“七十五人制”来证明《左氏》等先秦古籍,即可知金氏的推论殊不可据。亦可见其说的方法上虽有足取之处,然而于解决两种军赋性质与关系的问题上,也没有大的助益。
第四说则只看到了两种军赋的区别及所列出的数字不能凡完全符合于《周礼》及《汉书·刑法志》等籍,即行否定了《司马法》一书的价值,如竹添氏虽以杜元凯为指斥对象,但实行上服、杜皆引用了《司马法》,则此派亦同样以服氏引据不可靠的材料以注释《左传》,对服氏之义亦无甚发明。今人童书业《春秋左传考证》亦赞同竹添氏的否定杜说,且谓:“后儒多举战国以后之书以解释古文古文献,故多不可信。”[(24)]童氏又以“丘”当作“兵”。童氏这样的看法可谓人云亦云,完全无视于清人的考证成果,大大违背了事实,亦不足论。
第五说从战争模式改变之上着眼,在清人考据的基础上肯定了郑注所引“三十人革车说”本为周代成法,而及后所以改成了五十人以至七十五人的“长毂丘乘法”者,正处于步卒渐成为战争的主角,需求大增,开征兵员之法正是始于成公元年鲁国所行的“作丘甲”。换言之,由于“作丘甲”,才产生了服注所引《司马法》所载的“七十五人”定制,亦即今人陈恩林在“先秦军事制度研究》中所说:“……‘七十五人制’是在实行‘丘甲’、‘丘赋’制度以后产生的,所以它和‘丘’字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丘甲制以前,它并不存在。”[(25)]由此反映了服氏用《司马法》本条“七十五人制”的记载来注解“作丘甲”,正能恰切指出了军制变革后的制度内容。杜氏虽然同样引用本法,然其竟首冠以“周礼”,大大违背了郑注“三十人制”本为周法说的事实,亦宜乎其受惠士奇之抨击。本派之说,颇能彰显服注的深意,亦合乎春秋的大势及事实发展。
服氏所引《司马法》的“七十五人制”,班孟坚修《汉书·刑法志》时,即取以作为殷周制度的内容。班氏有云:“二伯之后,寝以陵夷,至鲁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赋,搜狩治兵大阅之事皆失其正。《春秋》书而讥之,以存王道。”[(26)]刘孟胆谓“此是古《左氏》谊。”[(27)]由于班氏以为成公元年“作丘甲”,《春秋》所以书之,实有“讥鲁失其正”的大义,于是近人叶德辉乃据此以申明服氏之意。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二三引叶氏说云:“服引《司马法》丘甸之制,以明古者丘无甲,甸始有甲,今丘而作甲,虽所出之数不尽如甸赋,而要为扰民之事。”[(28)]叶氏又批评杜预和颜师古云:“杜注云:此甸所赋,使丘出之,则一丘而其一甸之赋,是四倍其赋也。颜注袭杜,失经义矣。”叶氏所言,似乎有理,然而实可商榷。抑有甚者,其说实在暗窃自清人李贻德。查《春秋左传贾服注辑述》卷一○有云:“案:服备引《司马法》丘甸之制,以明古者丘无甲,甸始有甲,今丘而作甲,虽所出之赋不尽如甸赋,而要为厉民之事也。”[(29)]取李次白之说与叶氏互相比勘,则叶氏袭用李氏的痕迹,昭然可揭矣。而李氏、叶氏所引申的服说,其前提根本于班书所说的“讥鲁古义”,服注虽未申明,但此义仍然可取。至于杜氏、颜氏之说,叶氏评之为失经之义。而李次白则同意杜说,并发挥杜意云:“杜氏直云:‘此甸所赋,使丘出之,讥重敛。’噫!叔孙豹之罚御叔也,不过倍其赋而已。今一丘之中,而使具一甸之赋,是四倍其赋也。虽后世暴君汗吏,犹将贻而不敢信,而谓‘秉礼’之鲁,竟肆然以是令其民乎?”[(29)]比合于二者之说,“作丘甲”既具班氏所谓“讥鲁”之义,服注之意在于表明鲁国的扰民、厉民,则杜氏提出“讥重敛”之义,原则上与班孟坚、服子慎之说一致。而叶德辉既承认服氏有“讥鲁”之义,却又言杜元凯“失《经》意”,互相矛盾,殊不可通。探讨郋园之意,或以为杜氏在理解“丘”的负担比较以前增加四倍,在数字上并不正确,(事实上,确有学者以为“丘”的负担只增加了三分之一,而非杜元凯所说的四倍,明人胡宁《春秋通旨》、清人沈彤《春秋左传小疏》卷一、近人黄云眉《读左氏传札记》[(30)]、今人傅隶仆《春秋三传比义》[(31)]皆主其说)是以叶氏乃有此言。然而似又不必斥责杜氏为“失《经》意”!郋园在申明服注之意时既于暗袭李氏,说杜、颜之注则又有厚诬二家之嫌,葵园《补注》引解《志》,似乎也不能不算是失误了。
对于杜元凯以《传》有“讥重敛”之义,刘孟胆只援引顾亭林、沈小宛、朱允倩之说来纠正杜氏言“出赋”之误,对于《经》旨则只云服、杜引《司马法》意各不同,而未加评论。大抵依班氏之义则服、杜可以同有“讥鲁”之旨;然而依照今人解释“作丘甲”之法为“七十二人军制”所以产生的开始,则服虔引用《司马法》又实在远比杜氏改易书名作《周礼》以说经的做法为优胜。
至若《经》文“作丘甲”是否确有讥意?只从三字以言,今已无从睹见,据孔子之政治观点,对国家加赋,大抵亦不会表示赞同;况且此“作丘甲”之制为变易周时旧法者,而《左氏·哀公十一年》载有孔子言于弟子冉有以评论季孙氏“欲以田赋”时有云:“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32)]则取田赋之法与“丘甲”(或丘赋)相较,孔子又以“丘”甲为足。此“丘亦足”之“丘”,当即《成公元年》之“作丘甲”。可见班氏之“古义”虽或合乎孔子的政治观点,但在明文之上则未必有直接的根据。再看《传》文于“作丘甲”前,明言“为齐难故”,则上述第五种主张谓“丘甲”乃一扩大征供之制,亦未尝不合于《传》意。且比班义有更加“直接”的依据,这也可算是“古谊”和“本义”的分别。若然,则服氏《解谊》所“解”之义,于此实又为“本谊”矣。其引用了材料极为可靠的古兵书《司马法》来解释鲁国推行“丘甲”制的重大意义,虽然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误解,然而在近年军事史研究之上,却能证明他的解释能符合鲁作丘赋一事所反映出来的时代意义。
注释:
① [唐]孔颖达等:《左传正义》卷二五,《十三经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一版。
② [唐]孔颖达等:《毛诗正义》卷一三,《十三经注疏》。又:[唐]孔颖达等:《礼记正义》卷五一,《十三经注疏》。
③ [唐]贾公彦等:《周礼注疏》卷一一,《十三经注疏》。
④ [清]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香港,太平书局,一九八六年十月。
⑤ [清]江永:《周礼疑义举例》卷三,[清]阮元主编:《皇清经解》卷二四五,上海书店,一九八八年十月。
⑥ [清]孙诒让撰、王锦文等点校:《周礼正义》卷二○,北京,中华书局,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版。
⑦ (12) 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第五十八章,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二月版。
⑧ ⑨ ⑩ (11) 金德建:《司马兵法兵车出师之今古二说及其来源之解释》,《古籍丛考》,上海书店暨中华联合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13) [清]惠士奇:《春秋说》卷一二,《皇清经解》卷二四○。
(14) 《春秋左氏伟旧注疏证》。
(15) (16) [日]竹添光鸿:《左氏会笺》卷一二,台北,新文丰,一九八七年一月二版。
(17) [瑞典]高本汉撰、陈舜政译:《高本汉左传注释》,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一九七九年六月二版。
(18) 《周礼正义》卷二○。
(19) 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十月版。
(20) 韩连琪:《周代军赋及其演变》,《文史哲》一九八○年第三期。
(21) (25) 陈恩林:《先秦军事制度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月版。
(22) 田旭东:《司马法浅说》,北京,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五月版。
(23) [清]黄以周:《礼书通考》卷四○,台北,华世,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版。
(24) 童书业:《春秋左传考证》卷一《赋制及其改革》,《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六月第二版。
(26) (28) 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二三,北京,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九月版。
(27) 《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
(29) [清]李贻德:《左传贾服注辑述》卷一○,[清]王先谦编:《皇清经解续编》卷七六六。
(30) 黄云眉:《读左氏传札记》,《史学杂稿续存》,济南,齐鲁书社,一九八二年五月第二版。
(31) 傅隶朴:《春秋三传比义》(下),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版。
(32) 《左传正义》卷五八。按:本文之“丘”,钱宾四先生以为指孔子,说颇奇特,似有可商榷处。今仍依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卷一、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及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以“丘”为“丘赋”(说本杜注),诸说皆较钱氏更合乎《传》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