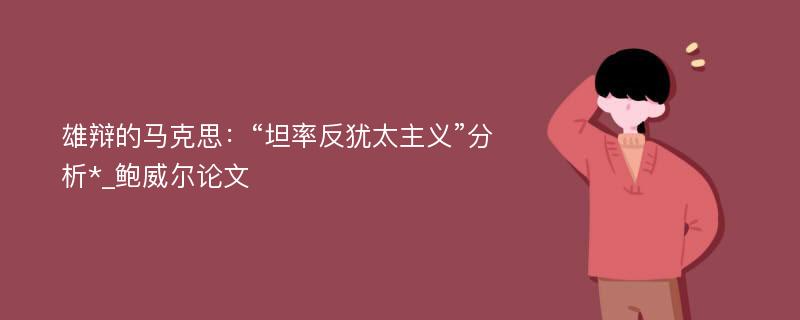
能言善辩的马克思:析“率直的反犹太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能言善辩论文,率直论文,主义论文,反犹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建/朱伟 译
25年前,埃德蒙·西尔伯尼在涉及“社会主义者与犹太人问题”这一敏感课题时,指出:“我们不必从马克思对犹太人的论述中摘章寻句,就不仅能而且必须把他归类为直言不讳的反犹太主义者”。这一论断遭到了芒特·斯科普斯的理论抗争。斯科普斯在其论犹太人问题文章的第六部分“无例外则无规律:论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中,标举了与前者相反的例证。1977年,后者又在论述马克思女儿爱琳娜的专著中,披露了鲜为人知的例证(此例同样属于未明的编年史范围):马克思曾斥责维也纳反犹太人团体残虐犹太人的行径。据此,斯科普斯指出:我们可以从中透过马克思“率直的反犹太主义”外观而窥见其关怀犹太人的内在心声。西尔伯尼对斯科普斯的例证不以为然,他驳解道:作为人类学家的马克思,在上述情况下,他暂时压下对犹太人的恶感,是势所必然的。但除此之外,这两个例证没有更深刻的意义,“因为马克思后来又强调了自己对以色列儿童的观点依旧故我。”
年青的英国学者罗伯特·S·威斯特里切, 从另一个方面用他的最新剖析杰作《革命的犹太人:从马克思到特罗特斯凯》,横决了理论界对马克思的凝滞视界。可是,在本原性对比研究的基础上,他却要我们确信:把马克思关于耶路撒冷的报告“引述为他同情当地穷苦犹太人的宣言是一个错误”。因为马克思“对犹太人的私人反感”是“不能用他对犹太人受虐惨景的一次表白来抵消的,无论这类惨景发生在俄国、波兰、奥地利——匈牙利,或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地方。”鉴于这类否定过度的观点在其他宏文杰作中也盘根错结,我们不得不沿循蜿蜒曲折的路途去探源《论犹太人问题》,以考求问题的真谛。
事实上,在青年黑格尔分子布鲁诺·鲍威尔首次发表论犹太人问题文章的前四个月,身为科伦《莱茵报》主编的马克思正热衷于报界的笔战,他的对手是记者卡尔·海因里希·海尔梅斯,后者作为《科伦日报》资深的撰稿人,负有控制报界对自由读者影响的责任——遏抑新发行的《莱茵报》在科伦以及其他地方的影响。为此,海尔梅斯与《莱茵报》的精神领袖马克思之间展开了激烈逐鹿。马克思在1842年7月9日于故乡特里尔寄给阿诺德·卢格(当时的密友)的信中写道:“我大概还得同科伦的海尔梅斯继续论战一个长时期;尽管这个家伙十分愚昧、庸俗和迂腐,正因为有这样的品性,他才成为庸人们的代言人——我还是打算不让他再继续饶舌下去。”〔1 〕此信除了表达自己对论敌的嗤之以鼻之外,也涵括了他对其精神产儿(历史唯物主义——译者引)的慈父情怀(这也是标帜马克思到达历史唯物主义之途的一块里程碑,遗憾的是,这个背景至今尚未引起理论界的充分注意)。
马克思反击海尔梅斯的计划需要六个星期才能准备就绪,而其中举步维艰的原因也可以从7月9日的信中略见一斑。马克思在信中哀叹道:“从4月以来直至今天,我总计起来大约只工作了四个星期, 而且还是断断续续的。由于最近的丧事,我不得不在特里尔呆了六个星期,而余下的时间都被不愉快的家庭纠纷分散和浪费了。我的家庭给我设下了重重障碍,使我目前陷入极为窘迫的境地,尽管我的家庭经济情况并不坏。”〔2〕此外, 马克思虽然忧虑“书报检查制度”将带来局势的逆转,他还是要求他的犹太朋友——前科伦地方法院的法官哥贝尔特·奥本海姆负起对《莱茵报》的法律责任;并要求他“如有可能,把海尔梅斯所有反对犹太人的文章都寄来。”〔3〕引人注目的是, 信中对“反对犹太人”这个词组是用粗体字强调的。他认为:海尔梅斯对犹太人的态度——或更精确地说,反犹太人的丑行——将成为自己的绞刑架。因为,“然后我(马克思——译者引)将尽可能快地给您(奥本海姆——译者引)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即使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也要把它纳入另一条轨道。”〔4〕由此可见, 马克思在尚未获得海尔梅斯反犹太人的文章之前,就已下决心反对他了。
如果我们审查海尔梅斯论述犹太人公民的所有文章,就会瞠目结舌:他对普鲁士西部省份发展的评论与马克思厌恶犹太人商业庸性(更不必说莫泽斯·赫斯后来倡导的犹太复国主义精神——潜在于犹太主义中的兽性争利精神)的思想不谋而合。然而,海尔梅斯考虑到《科伦日报》的前景(特别是它与《莱茵报》的关系而引发的前景),他采用了小心翼翼的对比态度:这位来自普鲁士奥斯特马尔肯地方的海尔梅斯,由于不赞同犹太人在基督教统治下的自治,因此,他可以被归宗为“吉姆·克罗”分离主义(泛指反少数民族主义——译者引)、种族隔离主义和“非雅利安人”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海尔梅斯的理性起点后来也就是鲍威尔的思维出发点。然而双方在走向上大相径庭:鲍威尔在理论触及现实时嘎然止步;而海尔梅斯却向“执意把任何事物都纳入不同轨道”的革命者提出了种族主义的目标。由此,我们可以肯定,这位《科伦日报》的代言人事实上必然被《莱茵报》击败;而且只要马克思继续采用正确的战略战术,新的胜利就会接踵而至。
然而不幸的是,马克思不仅没有乘热打铁,而且还因过于瞻前顾后,而“把报纸完全搞糟了”(根据众所周知的卢格于1844年5 月给哲学家费尔巴哈的信)。这其中的原因是:一方面,马克思作为主编,必须相机处理新闻观点以应付“书报检查制度”;另一方面,他作为后起的学者与政论家,当时不仅没有著作,甚至未能创著导向性的论文。因此,他需要更多的理论准备时间。而在此同时,那些进展较快的作者们超越了他:1842年5月份, 与马克思结盟的报纸同事发表了《普鲁士国家中与犹太人有关的立法问题》的回忆文章;6月份, 《莱茵报》主张“犹太人的市民平等权”;8月份, 报纸发表犹太人的立法要求再次撞击“持最不知羞耻的异议的《科伦日报》”;9月份, 该报又眷注于“普鲁士犹太人的法律的宗教状况”。一个半月后,布鲁诺·鲍威尔论犹太人问题的主要文章就在卢格的《德意志年鉴》上因势问世了,该文大量使用了马克思的理论用语。此后,马克思一直深陷于与书报检查人员的智斗,而且这个斗争伴随着《莱茵报》的完全被封而达到了顶点。
幸运的是,卢格向马克思提供了另一个发表严肃作品的机会。他在8月初向马克思建议:“你喜欢评论书籍出版物吗? 我指的是在年鉴上。”卢格这里指的是《德意志年鉴》。但是到1843年,该杂志的命运与《莱茵报》殊途同归,也终于难逃被禁的厄运。随后,卢格倡导在巴黎出版定期刊物《德法年鉴》以取代《德意志年鉴》的地位。马克思欣然接受这一建议。因为对于马克思(以前仅作为时事评论员)来说,能在连续出版的定期刊物中充分地表述炉火纯青的思维成果,其滋味之甘美,远胜过撰写日常社论。此外,他还拥有了比在普鲁士莱茵地区更广阔的自由论坛。因此,巴黎的环境使马克思如鱼得水,尽管卢格认为“此地没有超尘拔俗的理性”——仿佛“辩证法退化到傲慢无礼”。最终,马克思(与他的《论犹太人问题》的读者一起)在巴黎的革命风尚中透彻地领略了革命的动力学。例如,他品味出我们今天尚在讨论的“永恒的革命现象”。
在《德法年鉴》终于于18个月后应运而生时,代替马克思反海尔梅斯目标的,是与布鲁诺在“犹太人问题观”上的分庭抗礼。在这个“率直的反犹太人组织”(西尔伯尼和威斯特里切指称《德法年鉴》的专用名词)中,是三个非犹太人的撰稿者(迈克尔·巴枯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阿尔诺德·卢格)对五个犹太人(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特、享利希·海涅、莫泽斯·赫斯、约翰·雅各比、卡尔·马克思)。该刊所发12篇稿件中的3 篇(包括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犹太人问题的论争。
对马克思这一时期活动的研考,是至关重要的,缺了这个环节,就无法公正地察验马克思“犹太人观”的立场。众所周知,作为撰写《论犹太人问题》的社会学家,马克思始终如一地把犹太商人们描绘为“斤斤计较的庸人”,无论他们是富甲天下的罗斯柴尔德五兄弟(犹太巨商,他们在1820-1830年间,几乎提供了欧洲国家所需的全部贷款)之一,还是散见于莱茵地区的974名小贩(19世纪40年代, 该地区的犹太小贩数)概莫能外。这个命题是在“傲慢的辩证法突变”的羽翼下诞生的,其反题与合题都源于对罗斯柴尔德“笑话”的模拟:罗斯柴尔德曾以向一名社会主义者讲话之机驳难社会主义:“你要瓜分财富,说在我拥有的几百万这样或那样的财富中,有你根据总人口平均的那一份;拿去吧,这是属你的一角银币。”马克思引用海涅“巴黎报告”中的语言对此反唇相讥:“对法国的犹太人来说,与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一样,金子是时代的上帝,而工业是至高无上的宗教。”马克思还把论点进一步引申为:“犹太人就是商业庸人。犹太人都是如此吗?同样也看一下基督徒吧。”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真实意蕴是:只要是资本家,无论他是资本主义的、犹太人的,抑或是基督教的,都只是处于“不同跑道”的同类人;另一方面,身为政治家的马克思,在对待有所作为的犹太政治力量方面,其态度与此有天壤之别。
马克思于1843年3月13 日写信给卢格说:“本地犹太教公会会长刚才到我这里来,请我替犹太人写一份给议会的请愿书,我答应给写。”〔5〕这是昭示马克思关怀犹太人的历史决定性文献。当然, 马克思对犹太人正义要求的认同(可能是赫斯的父亲向犹太教公会会长建议:向马克思提出以上要求的)是不能与赫斯晚辈(莫泽斯·赫斯——译者引)的富有侵略性的犹太复国主义同日而语的。另外,马克思作为无神论者与犹太教信仰者之间也阻隔着理性鸿沟,双方在指向上的互斥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与此同时,马克思却与布鲁诺的反犹太教思想拉开了足够距离,他在同一封信中写道:“不管我多么讨厌犹太人的信仰,但鲍威尔的观点在我看来还是太抽象。”〔6〕最终, 马克思的思路落在了政治动机:“应当在基督教国家上面打开尽可能多的缺口,并且尽我们所能把最大量的合理东西偷运进去。至少,应当试着去做,——而激烈性将随着请愿被一次一次地拒绝而增长起来。”〔7〕由此可见, 虽然马克思与鲍威尔同为“率直的反犹太人主义”理论家,但后者的策略水平只能望前者项背:鲍威尔根据否定资本主义的思想,提出了“犹太人非犹太教化”、“基督徒非基督教化”的根本要求——这在政治实践中只能一事无成。而马克思却宣布:自己准备支持由46个犹太教派首领以宗教团体名义发起的有限改革尝试。
我们姑且不论马克思执笔的请愿书的命运,这里颇堪玩味的是,在请愿书上鉴名的不仅有《莱茵报》的创办人,也包括《科伦日报》的所有者。请愿书中提出:偏僻省份议会的首要改革就是“赋予犹太人在民事和政治事务中的完全平等权”。可见,该文件代表了莱茵自由人士在革命前夕的共同希冀,而其中各种观点的融合,反映了各派对整体利益的集中思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解决了该问题的抽象部分。一年之后,他又强化和对象化了他的革命计划。
另外,我们还要特别提及《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此书对马克思1843年至1844年间创立唯物主义的影响非同小可。该书的旨趣在于批判鲍威尔及其同伙。这表明马克思要与自己曾尊敬过、保护过的思想家“作最终的清算”。同时,鲍威尔曾据有过的挚友位置也将由恩格斯取而代之——在卢格也从马克思波动的朋友圈中退逸而去后。虽然恩格斯留在《神圣家族》中的笔触微不足道,但他却扮演了合著者之一的角色。事实上,他甚至名列主要作者之前。马、恩组成了迷人的小队。或许由于马克思在感情上、知识上和物质上得益于后者甚多,这使得他的风格也向后者倾斜——变得更结构化、定型化、客观化:马克思现在用论述“商业和工业的组织”来取代“贪得无厌的、寸利必争的犹太人商业庸性”,用戏谑“辩证扭曲与曲解”来笑谈“投机商人的笑语”,——然而千真万确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向读者提及他自己的缺失(其中包括他曾用“最终的人类解放”来涵盖“政治解放”,由此造成二者的缠绕不清)。马克思在此书中只用了两页纸来阐述莱茵省议会关于“解放”的争论;而对犹太人问题,他却通过三个犹太人的交流圈来再三补充说明。
在第一个圈中,马克思(西尔伯尼声称:“除了布鲁诺的著作外,他是否读过别的论犹太人的文章,都不能确定。”)站在与鲍威尔一伙批判家大相径庭的犹太代言人一边。代言人之一是神学家古斯塔夫·菲力浦逊,他在《鲍威尔论犹太人问题的思想应受到进一步审验》一书中诘难了鲍威尔,由此自身也陷入被攻击之中。马克思支持菲力浦逊说:“不管绝对的批判怎么说,菲力浦逊先生用以下的话来责备它时,决没有说出什么不尽情理的话:‘鲍威尔在思索的是一个特殊类型的国家……国家的哲学理想’。布鲁诺先生把国家和人类、人权和人本身、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混为一谈,就必然会思索或者至少是想象一个特殊类型的国家即国家的哲学理想。”〔8〕
在第二个犹太人圈中,首席教师塞谬尔·希尔施博士出生于特里尔附近,并受过黑格尔思想的培训。他在外观上比菲力浦逊更为敏锐。就在菲力浦逊论著出版的同一年,一位莱比锡的出版家以《犹太主义、基督教国家和现代批判》为名,发表了希尔施“诠解鲍威尔犹太问题观的信”。如果我们能体悟到希尔施著作在犹太教育学方面的权威性,那么我们也就能通过马克思对此的得体答复,透视到青年马克思身上炽燃着何等热烈的犹太民族精神,这甚至影响了他对自身观点的表达。事实上,我们只要回眸“马克思祖先身上勃发着的犹太法学激情的往事”,就可以领略到:马克思作为耶路撒冷(犹太族——译者引)的学者与作为政治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马克思用以下的语句臂助希尔施,他的结论性观点显然不是来自鲍威尔的著作。
“布鲁诺先生说:‘犹太人对历史弹簧的压力,引起了反压力。’和他这一论断相反,希尔施先生完全正确地指出:‘所以说,犹太人对于历史的形成必然起了某种作用。而如果鲍威尔自己也肯定了这一点的话,那末,另一方面,他就没有权利断言犹太人对于现代的形成是毫无贡献的。’布鲁诺先生回答道:‘眼中的刺也起了某种作用,是否可以说它对我的视觉发展作了什么贡献呢?’刺,就象犹太精神在基督教世界中一样,从我生下来那天起就在我的眼中,现在仍然在我的眼中,并且跟眼睛一同成长和发展。这样的刺并不是普普通通的刺,而是和我的眼睛分不开的一根罕有的刺,它必然会对我的视觉的高度非凡地发展有所贡献。所以,批判的‘刺’并没有刺痛正在朗育的希尔施。此外,上面提到的那篇批判文章已经向布鲁诺先生表明犹太精神对‘现代的形成’的意义了。”〔9〕这里, “率直的反犹太主义”对具有自身历史及影响历史力量的犹太主义退避三舍了(马克思以前曾直接了当地遣责犹太主义,并且没有因为辩证法的缘故而放过它)。这是继马克思以前援助犹太人请愿活动之后的第二个积极事实。但其后,马克思又在《神圣家族》中责难“那些软弱的反对派”中的两位牧师,并在神学家面前重申反对犹太主义,同时双倍地羞辱“超神学家”——布鲁诺。
马克思甚至还臂助当时饮誉遐迩的犹太解放斗士里谢尔,这从另一个视角看,是不可思议的。加布里埃尔·里谢尔是第三个犹太人圈中的核心人物。他曾因其犹太血统而被禁止在海德尔伯格大学任教,又被剥夺了汉堡律师和黑森地区市民的资格,最终不得不于1840年屈就汉堡公证人之职。里谢尔以前曾通过自己的出版物,欢迎“有口皆碑的杂志文章——《莱茵报》的出类拔萃佳作”。现在,《莱茵报》从前的鼓舞者和指导者又反过来赞许里谢尔对鲍威尔国家概念的批判。马克思论道:“里谢尔先生和布·鲍威尔相反,他(鲍威尔——译者引)指出他的国家(即批判的国家)必顺驱逐‘犹太人’和‘基督徒’。里谢尔先生说得完全正确。既然鲍威尔先生把政治解放同人类解放混淆起来,……所以鲍威尔先生在他的‘批判的国家’中也就必然把犹太人和基督徒送上绞刑架了。”〔10〕马克思还进一步赞誉“里谢尔对反犹太人的不平等的经济措施的抗争”,指出:“犹太人的政治解放以及赋予犹太人以‘人权’,这是一种双方面相互制约的行为。当里谢尔先生顺便谈到行动自由、居住自由、迁徒自由、经营自由等等时,就正确地阐明了犹太人力图使自由的人性获得承认的意义。‘自由的人性’的所有这些表现在法国人权宣言中得到了极其肯定的承认。”〔11〕从中可见,在马克思赞赏犹太伙伴(里谢尔——译者引)并立足于法国革命宪法而追求犹太人解放的行为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因素。
然而,马克思在为犹太人要求人权的文章中,并没有放弃反对“犹太精神”的斗争。典型的事例就是,文章中一再引述海涅精心制作的“辩证法的跳跃”。我们在前面已提过这方面的第一个例证。在此,我们再次枚举马克思在这方面的第二个例证:“金钱是我们时代的上帝,而罗斯柴尔德是它的提倡者。”“汉堡的人口从古代时起就由犹太人和基督徒组成,而前者没有付出巨大的牺牲。”此外,在1844年6月, 当海涅正沉浸于将迸射出眩目异彩的诗意朦胧之中时,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挚友——贝尔奈斯借助于巴黎的《前进报》,讥笑“来自莱茵河西岸每一寸土地上”的犹太人的商业精神(见贝尔奈斯的专题文章《来自马克思故乡特里尔的文件》)这一次,马克思以他惯有的辛辣呼应道:“犹太人就更有权利要求承认自己的‘自由的人性’,因为‘自由的市民社会’具有纯粹商业的犹太人的性质,而犹太人老早就已经是他的必然成员了”〔12〕。总之,马克思对犹太人的态度颇具两面性: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号召通过毫不掩饰的革命战争以实现长远的前景目标:“你们犹太人,以及基督徒,都是利己主义者,将来你们会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而在《神圣家族》中,他却提倡可操作的短期目标:“既然你们全都是具有商业精神的人,你们就必须相互容忍。”由此可见,所谓的马克思“率直的反犹太主义”的公开教义仅此而已。
另外,西尔伯尼和威斯特里切认定,马克思个人对犹太人的评论,无可置疑是否定的。我们却认为,马克思评论中所展示的矛盾情结,洞若观火地证明了托马斯·迈耶尔(在另外领域中)研考马克思和伯恩斯坦时得出的结论:在马克思的信与著作中,幽默与意识、改革愿望与激进热情、深邃论文与简化小册子、反犹太人的旧辙与反资本主义的新意融汇合一。在这方面,马克思对待费迪南德·拉萨尔的态度就是典型例子。
多年来,马克思在与其终生不渝的战友恩格斯通信时,总是戏谑地蔑称拉萨尔为“易济施”——这一绰号发轫于弗雷德里克大帝时的犹太法庭。海涅曾多次重复这一谑语来嘲讽易济施派的作者。在有一封信中,马克思使用这一专用词,竟不下9 次〔13〕。然而,当拉萨尔因决斗而弃世时,马克思并没有认为这是一次“率直的反犹太主义”的胜利。相反,他领悟到自己与死者(马克思也曾溢美他是“阿喀琉斯”)之间的唇齿关系。他指出:拉萨尔是“老近卫军”成员,是共同敌人的敌人。他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这几天来,拉萨尔的不幸盘旋在我的脑际,达到可诅咒的程度。他毕竟是老卫士之一,并且是我们的仇敌们的仇敌。”〔14〕
根据以上的例子,我们就能排除威斯特里切的错误而自信:问题的结论已在马克思信里的叙述中不证自明了。此外,我们还必须涉猎与马克思生活直接有关的亲戚们,通过他们与马克思的交往来发现:造成后者“反犹太主义”的“客观刺激”。历史的记载是:当马克思的生活一贫如洗时,他却不能从亲戚那儿觅得任何帮助。他曾两次写信给腰缠万贯的嫡亲;指望出于共同的犹太背景能使对方接济自己,但每一次除了辛辣的嘲笑外一无所获。在这种境遇下,他迁怒于一般的犹太人(认钱不认人的犹太人)就顺理成章了。这个难以断定的理由比任何东西更能说明:马克思与那种盲目狂热、极端好战的“犹太族的天敌”,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此,如果用语言学的术语“反犹太主义者”来比附马克思,未免有失于张冠李戴。
事实上,马克思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或更精确地说,直到他最后一次执笔论及犹太人时,他仍然展现着两张面孔:一张冷若冰霜,另一张体贴入微,有时两张面孔似乎同时闪现。例如,1883年,一位出尔反尔的社会民主党人阿道夫·赫普涅,急不可耐地争着出版作者(马克思—译者注)在美国所写的新序言的《共产党宣言》时,恩格斯对此啧有烦言,他于11月9日写信问马克思:“赫普涅, 这个小小的犹太人为着‘宣言’的一篇序言,竟要把手枪对准我们的胸膛,你以为怎样?”〔15〕马克思在第二天的回信中,不仅没有丝毫的反犹太情绪,还设身处地地为犹太伙伴作了解释。他指出:“他(赫普涅——译者引)可自由刊印我们的莱比锡版的序文,俄罗斯人于去年刊印一种新的译文,这也可提及。他如认为没有我们方面特殊的新序文,即值不得再印‘宣言’,那他可以依照情形,干或不干。‘把手枪对准胸膛’是‘我们的人’的性质和方法,所以小赫普涅忍受干或不干这一着,正是自然的事情”〔16〕。事实上,犹太精神所陶治出的更多人不是“小赫普涅”这类人,马克思也未遗漏这一点(例如,他称誉老约翰·雅科比的战斗精神不亚于年青人)。爱琳娜·马克思(不幸的是,西尔伯尼在其文章中对她只字未提)讲述了她父亲对于世界历史中最著名的犹太人——拿撒勒的耶稣的观点。
“在这方面,他告诉我被有钱人杀害的木匠的儿子的故事,”爱琳娜回忆说,“他怆怀着尊严与直率!多次对我说:‘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应该仇视基督教,因为它也教导我们:应当爱护孩子。’”另外,我们也必须注意到马克思对最伟大的犹太哲学家巴鲁赫·德·斯宾诺莎的看重:马克思曾专心致志地摘录后者的《神学政治论》。正是斯宾诺莎的学说,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占据在中心位置。以上两个事实,已经由法国的马克思学家——马克西米利恩·鲁贝尔拿出了真凭实据。
总之,我们在研究马克思“率直的反犹太主义”时,是不能对以上两个事实熟视无睹的。因为根据犹太人的标准,耶稣和斯宾诺莎是更有权威的代表人物。而且马克思自己也曾模仿斯宾诺莎的思理写道:“对神的存在的证明不外是对人的本质的自我意识存在的证明。”〔17〕根据马克思的行径,一位巴伐利亚的犹太官员汉斯·拉姆还令人深省地指出过:“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中可以得到证明,马克思从未受到宗教割礼。”这看来是言之成理的。而正因为马克思是通过青年黑格尔派式的理性思索才确定信仰的,因此他自然希望犹太同胞们能被更合理性地对待。也就是说,与马克思同时代的普鲁士人,虽然自矜为彻底的平等主义者,但他们直至1847年后期仍然否定犹太人的平等地位。直至25年后的“第二帝国立法”,才赋予了犹太人以平等身份。最后,总结全文,我们开诚布公地希望,未来的哲学文库不会把《论犹太人问题》一文描绘成:“马克思的残忍梦想——一个非犹太人的世界。”
*本文译自 The Philosophical Forum, 美国波士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注释:
〔1〕〔2〕〔3〕〔4〕〔5〕〔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7卷,第430页;第428页;第433页;第433页;第443页;第443页;第443页。
〔8〕〔9〕〔10〕〔11〕〔12〕同〔1〕,第2卷,第111页; 第112页;第121页;第145页;第145页。
〔13〕〔14〕《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第199-200页; 第217页。
〔15〕〔16〕同〔13〕,第4卷,第673页;第674页。
〔17〕同〔13〕,第40卷,第2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