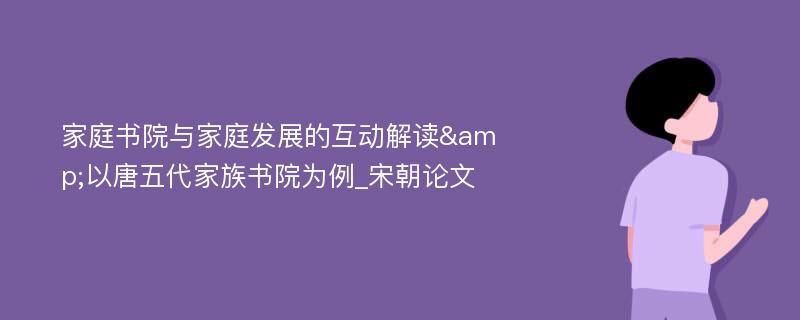
家族书院与家族发展的互动解读——以唐至五代时期的家族书院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族论文,书院论文,互动论文,为例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我国古代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起源来看,家族力量是书院教育兴起的重要促进因素。中唐以来,许多家族举全族之力兴办书院,家族书院以“期取青紫”和“家传孝友”为宗旨,通过培养有孝悌之德的族人和参加科举的生徒,形成家族聚居的伦理环境,从而维护家族稳定,促进家族发展。家族书院与家族发展的紧密结合和互动,成为我国古代教育史、文化史上独特的景观。
一、期取青紫与家传孝友:家族书院的双重目标
家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共同体,受小农自然经济的局限和宗法伦理的影响,家族成员往往聚族而居,其中更有累世同居,义不析产,人口几百数千的大家庭。隋大业元年(605)进士科的创立标志着科举取士制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科举的初衷虽只为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但一经出现即对社会文化诸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对一个家族而言,“是否兴旺的标志首先是经济实力,其次是有没有宗族子弟出入官场文坛,获取社会声望。而宗族子弟获得社会声望与地位的可靠途径,从唐代开始,是走科举入仕的道路。”① 家族通过举办书院培养科举人才,保家护族,促进家族发展。
始建于唐大顺年间(890—892)的江州(今江西九江)陈氏家族书院——东佳书堂是我国古代早期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代表。大顺元年(890),陈氏家族第七代主持陈崇制定《江州陈氏家法三十三条》,其中规定“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弟侄子姓有赋性聪敏者,令修学。稍有学成应举者。”② 稍后制定的《陈氏推广家法十五条》规定:“如有资性刚敏人物清醇者,严教举业,期达道以取青紫。”③ 东佳书堂培养本族子弟应科举的办学宗旨十分明确。据其第八、九、十世登科名录载,自陈诰始有20余人举进士,他们或官至某某大夫,或为某县令、某州参军等。家族子弟中举步入仕宦之途,以自身荣贵形成对本族的保护,其影响不限于聚居之地。唐宋时期,先后有唐僖宗、南唐烈祖、宋太祖、太宗、仁宗等褒旌陈氏为“义门”,宋太宗、仁宗亲为赐额、赐诗,南唐中书舍人徐锴、北宋初权臣文士如杨亿、钱若水、宋琪、张齐贤、晏殊、王禹偁等也都为陈氏撰记、题诗④。陈氏把这些敕赐、题赠之作悬于楼楣,记于家谱,自然为家族涂上了一层最好的保护色。
家族子弟中举及第后,有的直接用自己的俸禄来反哺家族,减轻家族的经济和供养压力。有的还利用自身的影响,惩戒不法之人,保护家族财产不受侵占。如前文所提到的江州陈氏,“真宗景德二年,侄(陈)延尝受殿中丞知南容州,赴任便路经过本家,见诸庄子侄勾当不告家长,擅自典卖田产。(陈延)到任后奏:‘乞就差官,深虑不省,卑幼递相仿效,坏祖先之义范、辜负圣朝奖励鸿恩。追邻臣家卑幼子侄与承典豪民一处提戡,将庄田所典得钱谷着敕降断还’。”⑤ 通过努力,陈氏族产陆续被追回,后来“虽至困穷不敢私卖田产上负圣恩。”⑥
“群贤肄业文方盛,孝友传家族更豪。”⑦ 家族书院除培养科举人才外,亦十分重视人伦教化,通过对家族子弟宗法伦理意识的培养,以维护家族基本生活规范和秩序。
江州陈氏自唐开元间陈旺“因官置产占籍于江州德安县永清村”后,至陈衮一辈共八世,“合族同处,迨今千人。”⑧ 人口增多,给家族管理带来许多的问题,如公共事务的安排、公共财产的分配等。维护家族聚居而不至于分崩离析既需要家族主持秉公无私和“夙兴夜寐不惮勤劳”,也离不开族众的支持和配合。“(陈)衮以为族既庶矣,居既睦矣,当礼乐以固之,诗书以文之,遂于居之左二十里曰‘东佳’,因胜据奇,是卜是筑,为书楼、堂庑数十间,……,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学焉,”⑨ 陈衮虽不是东佳书堂的创建者,但其主家时看到家族人口的不断增多,“当礼乐以固之”,从而增广书院,使之规模扩大以至于“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学”⑩,其中以教育配合宗法制度建设的良苦用心不难理解。没有家族成员敬祖认宗、谨守家法的纲常意识,没有维系家族血缘与群体感情的孝悌观念,家族聚居必然无法持续下去,在这里家族书院对“家传孝友”的追求甚或高于对科举的要求。《江州陈氏家法三十三条》中有诸多如“弟侄除命出执作外,凡晨昏定省事,须具巾带衫裳,稍有乖仪当行科断”等严格规定,但制度的实施既靠外在的奖惩强化,更重要的是实施者将制度内化为自我意识,只有这样方能使之“化有形为无形”,自觉遵守。家族子弟在书院接受教育,读圣贤之书,学伦理纲常、礼义廉耻,在严厉的宗法制度大背景下,耳濡目染,自觉践履家规家法要求,“由学而礼让著,由让而孝义敦,”(11) 从而达至“言斯出矣身则践之,揖让周旋之仪,孝友姻亲之行,修乎闺门之内,形于群从之间,少长有礼,丝麻同爨,乡党率义,人无间然”的结果。(12) 通过人伦教化,书院教育成为培养家族合格成员,维护家族稳定的生活秩序,促进家族发展的重要手段。
二、经费保证与开放办学:家族的主动选择
“与私学不同的是,书院有产业,譬如宋朝的书院大都置有院田,用来进行生产活动,保证书院的基本物质和生活需求。”(13) 没有持续的、稳定的经费来源,师资的延聘、书籍的购买、生徒的膏火费等无从着落,书院教育自然也无法维持下去。家族书院的经费则主要来自家族供应,江西古代最早的书院——桂岩书院为唐宪宗时国子祭酒幸南容创办的一所家族书院。幸氏家族雄厚的经济实力为桂岩书院提供了有力的经费保证。书院创办者幸南容为“南昌郡丞茂宏公曾孙,江南一时阀阅称显者以公家为最。”(14) 幸氏所居的洪城俨然就是一个大庄园,其间有祠宇、古刹、瀑布、泉流,落涧穿谷,“凝眸四顾,山居错杂,鸡犬相闻,俨若图画。”(15) 幸氏生活优越,经费宽裕,有财力创办书院,构学舍、聘名师、藏群书,聚族众以教育之。在家族书院的经费来源中又以家族给予的学田拨付为主。如陈氏东佳书堂在有“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的同时还有学田二十顷,以为游学之资。陈氏割良田二十顷作为书院办学基金,通过学田的固定收入保证了书院聚徒、教学、购书、藏书等各项事业的稳定发展。据文德翼《求是堂集》载,至宋初,陈氏“所藏贴与书,号天下第一,”(16) 东佳书堂发展为鼎峙江东的三书院之一,(17) 如果没有家族的经济资助是很难做到的。
家族对书院发展的支持不仅仅表现在经费上,更多的家族在举办的书院中突破了一般家塾较为封闭的性质,招收外姓子弟,实行开放办学。《江州陈氏家法三十三》的制定者陈崇在创建东佳书堂之初即把家族书院的开放性作为书院办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他要求对来东佳书堂求学的“宾客”实行开放政策,“应宾客寄止修业者并延待于彼,一一出东佳庄供应周旋。”(18) 至南唐时,四方游学于东佳书堂者,“自是宦成名立者盖有之。”(19) 和东佳书堂齐名,鼎峙江东三书院之一的奉新(今江西奉新)华林书院建于五代时期,胡氏本南昌大族,“一门守义,四世不析。”(20) 北宋初期胡仲尧对书院加以增扩,“筑室百区,聚书千卷,子弟及远方之士从学者数千人,岁时讨论,讲习无绝。”(21) 据范仲淹《赠大理寺丞蔡君墓表》记载,蔡元卿青年时曾不远千里从山东莱阳赴华林书院求学,“至江西之胡氏义学,与群士居,非礼不由,非道不谈,君子愿交焉。”(22) 由此可见华林书院的学生来源很广。胡氏本族子弟和其他求学之士共处一室,相与研磨,共同促进和提高,使胡氏子弟时有登科第而名于世者。建于五代时期的窦氏书院也是一所家族书院,书院创办者窦禹钧致仕后,“于宅南构一书院,四十间,聚书数千卷。礼文行之儒,置之师席。凡四方孤寒之士无供需者,公咸为出之。无问识与不识,有志于学者,听其自至。故其子见闻益博。凡四方之士由公门登贵显者,前后接踵。”(23) 族外生徒入读书院可增长本族子弟的见识,而在诗赋作为科举考试主要内容的唐、五代时期,家族子弟与外姓生徒相与唱和,切磋诗艺,使本族子弟的诗赋水平和科考的命中率都得到提高,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难理解家族为何要“设驿马于四郊,来远客于千里”(24),家族书院以“同时侪流登是选者以十数,初覆一篑,盖由椎轮,后来之人贯鱼而进”(25) 而自高。在科举的指向下,开放办学成为家族的主动选择,在扩大书院生源对象的同时,更提升了家族书院的影响,促进了书院的发展。
三、科举:家族书院发展的动力与桎梏
书院与家族发展的互动,丰富了书院教育的内涵,使早期以民间力量为主的书院教育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家族书院唤来了唐宋书院千姿百态的春天,”(26) 而在书院教育与家族发展的互动中,科举是其中重要的促进因素。
(一)科举是书院发展的重要促进力量,书院教育和科举制度有着密切关系。我们曾经认为书院和科举“势不两立”,以书院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和积淀下来的诸如学术自由、民主办学、独立研究、大师治教等宝贵的古代大学精神来表征整个的古代书院发展史,导致与历史事实的背离。仅以唐至五代时期的家族书院观照,科举制度是古代书院起源和发展的重要促进力量。通过对书院发展史的历史考察,有学者提出“科举制度是书院发展的基础和动力”(27),从家族书院和家族发展的互动关系来看,这个命题含有内在的逻辑必然。如江州陈氏要求“吾族之内有隽秀子弟专心向学者,无论富足之家,勿吝束修,延师课读;即贫乏之家,必当竭力培植,毋令可造者无成。”(28) 开科取士背景下的“可造者”即为中举之士,从这个角度而言,科举考试这种政治选拔制度促进了书院教育的发展,这是因为自唐以来“科举制度的重要性又在社会风气中得到反映。一个读书人不入仕途,则极少有机会表现他的特长,发挥他的创造能力,也极少有机会带给一家、一族以荣誉。所以一个人的进学中举,表面上似乎只是一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的结果,实则是父祖的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贤妻的茹苦含辛,经常是这些成功的背景。”(29)
(二)科举是家族书院发展的动力,同时也成为书院精神形成的桎梏。书院精神是我国古代大学精神的代表,家族书院对家族的依赖导致书院中大学精神的缺失。如前文所述,维护家族稳定,培养家族科第人才,提升家族声望是家族书院的办学目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家族书院缺少办学的自主性、教学过程的民主、怀疑和批判精神,绝大多数只能停留在科举考试预备机构的层次上,难以成为学术研究、自由讲学的阵地。如东佳书堂虽创办于唐,时间不可谓不早,五代时期即“鼎峙江东”。但因局限于家族办学宗旨,为科第而不为学问,其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影响很难与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媲美。家族书院虽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开放办学,但只限于对求学对象的开放,书院的管理权等仍然把握在宗族手里,离真正意义的社会化的开放办学尚有距离。故此,绝大多数的家族书院无法摆脱因族盛而兴、族散而荒芜的命运。幸氏的桂岩书院自幸南容创办至其孙幸轼于唐中和二年(882)举家徙于郡后,“书院自是芜矣”。北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江州陈氏奉旨分析,共分为大小二百九十一庄,遍布江南、两直、川浙、闽、广等地,东佳书堂无人经理,遂迁建于德安县城,后或为书院、或为县学、或为民居而至无闻。就这一点而言,具有私学性质的古代家族书院的兴衰对今天民办高校的发展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26)胡青:《书院的社会功能及其文化特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9页。
②(18)(28)陈增荣:《义门陈氏宗谱》(民国25年宜春德星堂刊本),江西省图书馆。
③④⑤⑥(13)(17)阮志高等:《江州陈氏东佳书堂研究》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专刊,第8、18~24、13、13、25页。
(22)(23)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四库全书本,卷十四、卷三。
⑦宋琪:《寄题东佳书院》,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⑧⑨⑩(19)徐锴:《陈氏书堂记》,同治《德安县志》(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卷三。
(11)(24)(25)杨亿:《南康建昌县义居洪氏雷塘书院记》,《武夷新集》四库全书本,卷六。
(12)(21)徐铉:《洪州华山胡氏书堂记》,《骑省集》四库全书本,卷二十八。
(14)邱泽奇:《社会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
(15)(16)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6页。
(20)王禹偁:《诸朝贤寄题洪州义门胡氏华林书斋序》,《小畜集》四库全书本,卷十九。
(27)胡青:《科举制是书院发展的基础与动力》,《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29)(美国)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