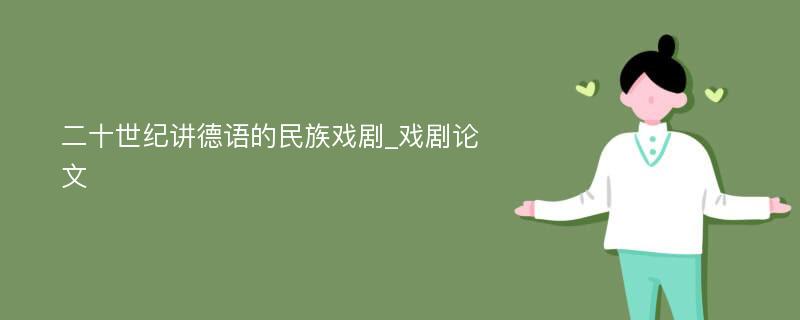
二十世纪德语国家戏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语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戏剧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在欧洲相继出现了自然主义和表现主义文艺运动,前者主要发生在法国,后者主要发生在德国,但它们又都是带有国际性的文艺现象。
在这个时期,德国戏剧演出活动出现了一派生机,剧院数目不断增加,一些剧院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如梅宁根剧院打破了一般宫廷剧院的传统,不以盈利为主,而是面向大众,专心上演话剧,甚至去别国进行巡回演出,扩大它的影响。1889年成立的柏林自由舞台,在著名导演奥托·布拉姆(1858~1912年)领导下,专门上演当代戏剧作品,首先是易卜生、比昂松、托尔斯泰、豪普特曼等人的剧作,为推动法国戏剧艺术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布拉姆关注现实题材的演剧倾向,在欧洲产生了广泛影响。马克斯·莱因哈德(1873~1943年)是布拉姆之后的另一位才华出众的德国导演,他具有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倾向,刻意追求绚丽多彩、宏伟壮观的舞台效果,但往往显得华而不实。德国戏剧界在他的领导和影响下,涌现了一大批出色的演员,其中名声最响的是巴塞尔曼(1867~1952年),他曾经积极参与自然主义戏剧运动,被认为是易卜生作品的最佳解释者。
本世纪20年代,是德国戏剧发展的“黄金时期”。这就是“魏玛共和国”时期,后来布莱希特称这个时期“不论它有多少弱点,却有一句实实在在的格言:艺术属于人民”。就在这个“言论和艺术表现自由”的氛围里,德国戏剧活动呈现出一派人才济济、丰富多彩的局面。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既有军国主义传统,又有工人运动传统的德国,成了欧洲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战争与和平进行全面较量的场所。这种较量在戏剧活动中的突出表现是,剧院成了讨论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论坛。当时流行的所谓“时代戏剧”,即描写现实题材的戏剧,以其反映现实生活中引人注目的政治、社会、道德问题,最能引起观众兴趣,常常引发广泛的社会讨论。其代表性作品有费迪南·布鲁克纳(1981~1958年)表现社会道德问题的《青春病》(1924年)、抨击魏玛共和国司法机构的《罪犯》(1928年);有弗里德里希·沃尔夫(1888~1853年)表现反堕胎法的《氰化钾》(1929年)、表现无产阶级革命起义的《卡塔罗水兵》(1929)和表现中国革命的《戴阳的觉醒》(1930);卡尔·楚克迈耶(1896~1977年)的时代批判剧《奎本尼克上尉》(1931年);彼得·马丁·兰佩尔(1894~?)的《教养院的骚乱》(1929年)等。即使以历史为题材的剧作,也都是讨论现实问题,因此也具有“时代戏剧”的性质,如汉斯·约塞·雷菲什与威廉·赫尔左格合作的《德莱弗斯案件》,就是以法国历史上德莱弗斯审判案为题材,揭露和批判了魏玛共和国司法的虚伪性和社会上泛滥着的排犹思潮。
一度陷于衰落的奥地利大众戏剧,在20年代又有了新的发展,厄顿·封·霍尔瓦特(1901~1938年)遵循当时流行的“时代戏剧”倾向所创作的剧本,把大众戏剧推到了一个新的、现实主义的高峰。他的《斯拉德克,黑暗帝国的士兵》(1929年)描写了当时国防军和司法机构中的反动发展倾向和征兆,表现了小市民的极端放纵和残忍的社会根源及其危险性,预示了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苗头。《意大利之夜》(1930年)则描写了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批判了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姑息养奸错误。这出戏标志着霍尔瓦特大众戏剧创作的重大进步。《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卡西米尔与卡洛琳娜》、《信念、爱情、希望》等都是他的大众戏剧中的精品,它们不再追求旧大众戏剧中的廉价笑料和“大团圆”结局,而是更注重揭示个人与社会的对抗这一主题。20年代德语国家戏剧界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许多奥地利戏剧家纷纷来德国谋求发展,如霍尔瓦特在德国开始戏剧创作,布鲁克纳到柏林创立“文艺复兴剧院”,倡导“时代戏剧”的创作与演出。原因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奥匈帝国的解体,奥地利在文化上陷入了保守主义,而德国文化界的自由氛围却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施展才能的天地。不仅许多奥地利艺术家来德国谋求发展、匈牙利1918年革命失败后,那里的许多知识分子也纷纷来德国谋求发展,如尤利乌斯·哈依的某些剧本,一度成了德国舞台上的当红剧目。
20世纪德国戏剧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现象是,1928年成立的“德国戏剧联盟”,它团结了许多先进的剧作家、导演、演员为德国进步戏剧事业的发展,戏剧创作与演出活动的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活动成为德国革命工人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著名导演埃尔文·皮斯卡托(1893~1966年)曾经创建“皮斯卡托舞台”,进行政治文献戏剧实验。他的演出活动强调技巧性,在话剧里加入歌舞成分。他对舞台进行改革,运用平台、圆形舞台和转动带增加舞台的动感和变化,并运用文献资料、电影、幻灯、机械装置等扩大舞台上的表现手段。他曾经导演过托勒的《当心,我们活着》、沃尔夫的《戴阳的觉醒》、布莱希特专门为他改编的《好兵帅克》和阿尔丰斯·巴克的《旗帜》等。他的实验演出带有早期“史诗剧”性质。皮斯卡托致力于消除舞台与观众之间的界限,把剧院办成讨论社会问题的议会,观众既是参议员,又是立法群体。皮斯卡托的实验,启发了布莱希特,他于1927年在歌剧《马哈哥尼城的兴衰》后记中首次提出关于史诗剧的设想,而后他又进行了关于“教育剧”的创作实验,试图用表演者与观赏者统一起来的方式,解决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相脱离的问题,引导观众变传统被动的艺术享受为积极主动的艺术欣赏。皮斯卡托和布莱希特的这些探索,是与20年代中期,在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高潮中,艺术家们曾经设法突破欧洲传统美学藩篱,建立适应新的革命形势需要的美学规范的努力分不开的。当时艺术家当中有一个流行口号:“艺术功能的转变”。他们的探索便是这种追求“功能转变”的一部分。他们的舞台实践和美学思考,大大推动了德国戏剧的发展,颇带有“美学解放”的性质。此外,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围绕德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形成了上百个业余的“宣传鼓动剧团”,类似我国抗日战争时期演出活报剧的宣传队,它们那灵活机动的演出活动,也为德国戏剧的发展与普及从艺术角度注入了活力。
1933年,希特勒法西斯势力篡夺政权以后,德国戏剧发展形势急转直下,“黑暗的30年代”,取代了20年代的“黄金时期”。几乎所有德国戏剧家,由于政治、种族、宗教等原因,纷纷逃亡国外,他们失掉了剧院和观众,在异国他乡其艺术活动天地和可能性,受到极大限制。令人惊讶的是,从1933~1946年,德国戏剧,当然是指流亡在外的反法西斯剧作家的创作,却取得了空前的大丰收。据统计,在这段时间内约有420位剧作家,创作了724部剧本,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广播剧、电影脚本和活报剧。在流亡的条件下,这样多剧本只有极少数能同观众见面,绝大部分都是剧作家们有意识地作为德意志民族的良智和德国文艺的代言人而创作的“抽屉作品”,且大部分表现的是反法西斯内容,他们期望有朝一日,德国观众把它们作为反省民族灾难和耻辱的文献来观看。由于脱离舞台实践,绝大部分剧作家在剧本创作中放弃了20年代所从事的艺术实验,出现了向传统戏剧表现形式回归的倾向,只有布莱希特(1898~1956年)始终坚持了他那很有艺术个性的探索,完善了他的艺术表达方式,创作了一系列成熟的史诗剧剧本,如《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西蒙娜·马卡尔的梦》、《四川好人》、《高加索灰阑记》、《伽利略传》等。一向对布莱希特的艺术探索抱有成见的匈牙利学者卢卡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看到这些史诗剧作品时,不得不对布莱希特的天才创造性表示肃然起敬,他后悔自己对布莱希特的成就认识得太晚了。史诗剧这一新戏剧体裁的出现,丰富了世界舞台的面貌,给后人的戏剧创作与演出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启示。在以反法西斯主义为题材的剧作中,还有沃尔夫的《马姆洛克教授》、《弗洛利茨多夫》,布鲁克纳的《神族》,托勒的《哈勒神父》,兰佩尔的《纳粹的黄昏》等。汪恩海姆继轰动一时的《捕鼠器》之后,又创作了《肇事者》。此外,还有许多借历史题材,影射批判法西斯主义的所谓“历史剧”。
希特勒法西斯攫取德国政权并吞并奥地利以后,中立国瑞士的苏黎世剧院成了德语国家戏剧界的一叶方舟,它虽然无法容纳众多的德奥戏剧界流亡人士,却也尽可能地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提供了继续从事戏剧活动的可能性,如朗霍夫、林德伯格、霍尔维茨、希尔施费尔德、金斯贝格、吉瑟等都在这里度过了艰难的流亡岁月;布莱希特的一些剧作,如《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伽利略传》等,最初都是在这里上演的。这些不仅繁荣了当地戏剧生活,推动了戏剧艺术的革新和发展,而且大大提高了苏黎世剧院在戏剧发展史上的声望和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瑞士戏剧不但在这个基础上得到空前的繁荣,而且不产生了两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剧作家:马克斯·弗里施(1911~1991年)和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1921~199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奥地利,没有出现有世界影响的剧作家。从60年代开始,奥地利出现一股致力于“反戏剧”的创作潮流,作家们在维特根斯坦和毛特纳语言哲学影响下,主张从对现有语言的批判性反思入手,达到批判现实的目的。奥地利著名的“格拉茨公园论坛”派的创作实验,一方面表现了晚期资产阶级社会里人们的自我人格失落感,另一方面也表现了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和意识形态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一分为二,戏剧发展也走了各不相同的道路。开始时,东部以演出古典剧目为主,如莱辛的《智者纳旦》,歌德的《伊菲革尼在陶里斯》、《埃格蒙特》,席勒的《强盗》、《阴谋与爱情》等。倍受重视的是流亡作家反法西斯内容的剧目,如沃尔夫的《马姆洛克教授》、《博马舍》,魏森博恩的《地下工作者》,盖奥尔格·凯泽的《八音盒》和《士兵田中》等。前苏联作家的剧目被奉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榜样,如《乐观的悲剧》、《克里姆林宫钟声》、《莫斯科性格》等。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东部以倡导现实主义的戏剧道路为主。朗霍夫领导的柏林“德意志剧院”、马克斯·瓦伦亭领导的“高尔基剧院”等,都为这条道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布莱希特和他的夫人海伦·魏格尔在皮克总统支接下于1949年创立了柏林剧团,进行了一系列史诗剧演剧方法的实验,演出了他在流亡期间创作的主要剧目,如《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伽利略传》、《高加索灰阑记》等。布莱希特还亲自率团到法国巴黎、英国伦敦进行访问演出。这个剧团形式独特、手法新颖的演出,大开了观众的眼界,为丰富和发展现实主义演剧方法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引起戏剧界人士的广泛兴趣和深入思考。在布莱希特史诗剧理论影响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剧作家,创作了一些无论内容或形式都表现了突出个性的剧本,如埃尔文·施特里马特的《猫儿沟》、《荷兰人的未婚妻》,赫尔姆特·巴耶尔的《弗林茨大娘》,彼得·哈克斯的《忧虑与政权》、《莫里茨·塔索》,福尔克·布劳恩的《翻斗车》,海纳·米勒的《克扣工资的人》、《女迁居者》等。它们的作者以辩证唯物主义态度,既歌颂英雄人物及其业绩,又注意描写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困难,敢于触及东德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曾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有时遭到来自国家领导层的干预和不公正的对待。哈克斯和米勒都有过多次类似经历。
六七十年代,东德戏剧出现一股所谓“新古典主义”潮流,作家们利用神话传说、圣经故事和古典戏剧的题材,以陌生化和寓意方法,表现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和认识。代表作有哈克斯的《和平》、《安菲特里翁》、《亚当与夏娃》,米勒的《俄狄浦斯王》、《菲罗克泰特》、《普罗米修斯》和布劳恩根据中国刘邦起义的故事创作的《大同世界》等。这些作品大都具有多层次结构,比喻、象征、哲理性强等特点。由于它们多有喻意现实的效果,常常被同行戏称为用“奴隶的语言”写成的作品。
海纳·米勒(1929~1996)是布莱希特以后表现了突出艺术个性和艺术创新能力的德国剧作家。他从一开始就以其敏锐的眼光、犀利的文笔描写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从50年代末期以来便成为东德颇有争议的剧作家。他那些新古典主义剧本,以其精炼的语言、优美的韵文,表现了作者高度的艺术才华,在评论界引起强烈反响。70年代以来,他创作了一批被称为“结构式戏剧”的作品,如《战斗》、《巩德林的生平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莱辛的睡眠梦幻呐喊》、《德国女神在柏林之死》、《任务》等。这些作品以其艺术上的创新性和内容的哲理深度,引起许多国家戏剧界同行的关注。由于他的剧本在结构上具有片断性特点,又常常被视为西方后现代主义戏剧的代表人物。
德国西部戏剧则经历了另外一条发展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德具有社会批判倾向的现实主义戏剧成就不大,代表性作品只有魏森博恩的《地下工作者》、楚克迈耶的《魔鬼的将军》和沃尔夫冈·博歇尔特的《在大门外》等。流亡作家如布莱希特、沃尔夫、凯泽、托勒等人的剧目,并未受到剧院重视。舞台上演出的是大量从西方,特别是从英国和法国来的剧目。萨特的剧作及其存在主义哲学,贝克特、阿达莫夫、尤涅斯库等人的荒诞剧,对西德50年代戏剧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西德也产生了一系列英法荒诞派戏剧的模仿之作,如希尔德斯海默的《钟》、《误点》,格拉斯的《洪水》、《恶厨师》、《还有十分钟到达布法罗》,米歇尔森的《赫尔姆》等。50年代后半期,瑞士剧作家弗季和迪伦马特那些社会批判性作品被搬上西德舞台,在西德才出现了试图描写社会问题的剧作,如马丁·瓦尔泽的《橡树与安哥拉兔》、《黑天鹅》等。直到60年代初期,德国“纪实戏剧”的出现,才使西德戏剧摆脱了模仿英法戏剧的处境,表现了独立的品格。著名导演皮斯卡托的提倡和扶植,对这类戏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是他第一个发现了罗尔夫·霍赫胡特那部在当时的出版界遭到冷遇的剧本《上帝代理人》,并把它搬上西柏林人民舞台。它的演出揭开了西德纪实戏剧的序幕,同时也以其批判教会纵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罪行,而震惊西方政界、宗教界和文化界。这一流派的代表作有海纳·吉普哈特的《奥本海默案件》、瑞典德语作家彼得·《法庭调查》、魏斯的《马拉/萨德》等。“纪实戏剧”以其题材的现实性、主题的尖锐性,常常引起社会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皮斯卡托青年时代把剧院办成讨论社会问题的议会的理想。
60年代后半期以来,原流行于奥地利和德国南部的“大众戏剧”,重又出现了复兴的局面,代表作有马丁·施佩尔的《巴伐利亚三部曲》,菲利克斯·克萨沃·克罗茨的《痼疾》、《家务事》,法斯宾德的《莱因的自由》。70年代以后,西德戏剧从公开的社会批判倾向转向自省倾向,剧作家波多·施特劳斯的《熟悉的面孔,复杂的感情》、《重逢三部曲》和《伟大与渺小》等,以对现代社会能为个人提供什么样的条件的探讨,引起戏剧界的关注。
戏剧事业发达与否的标志,关键还是看剧本创作成就。德语国家现代类型的戏剧始于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而就剧本创作成就来说,德国的莱辛、席勒、歌德代表了18世纪德语国家戏剧创作的鼎盛时期,那时无论是奥地利还是瑞士,都无人能与他们比肩而立。19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奥地利剧作家如格里尔帕策、莱蒙德、内斯特罗伊、安岑格鲁贝等人的剧本创作,在德语国家占了领先地位。也就是这时开始,维也纳取得了欧洲“戏剧之城”的雅号。这些剧作家共同创造了奥地利戏剧事业的辉煌。格里尔帕策被文学史家称为“奥地利的歌德”,自他以来,奥地利戏剧文学界人才辈出,精品迭现,尤其是在“大众戏剧”方面,为世界戏剧舞台增添了新的色彩。遗憾的是,我国德语文学界历来忽视奥地利戏剧的翻译和研究,时至今日,对奥地利戏剧文学的介绍几乎仍是空白。但愿这个缺憾能引起德语文学界同行的关注,在戏剧界和出版界协助下,迅速改变这个局面。
到了20世纪上半叶,德国戏剧创作又取代奥地利的地位,获得了辉煌成就,尤其是布莱希特树起了史诗剧大旗,大大推动了世界各国戏剧界艺术观的变革,影响了20世纪后半叶的剧本创作和演出活动。自70年代初期以来,布莱希特剧目在德国的上演频率,曾长期居高不下。80年代末期以来,也仅次于莎士比亚剧目上演频率,屈居第二位。布莱希特剧作在德国观众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20世纪下半叶,瑞士出现了弗里施和迪伦马特这样两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剧作家,使瑞士戏剧第一次在德语国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地位。如果说在此之前瑞士戏剧受惠于德奥戏剧创作成就的话,那么现在瑞士戏剧创作成就,反倒成了德国和奥地利戏剧发展的重要动力。本世纪最后一位卓越的德国剧作家海纳·米勒,像布莱希特、迪伦马特一样,再一次成为世界各国戏剧界瞩目的对象,他于1995年底去世,很可能为本世纪德语国家戏剧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奥地利戏剧由于过分耽于语言哲学的阐释,始终未能取得观众的普遍理解,至今仍在实验的荒辟小径上艰难地跋涉着。戏剧若是缺乏哲理性,可能令人感到不耐看;戏剧若是成了某种哲学观点的婢女,可能会令人感到无法看。天才的剧作家,总是在这二者之间艰难地选择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