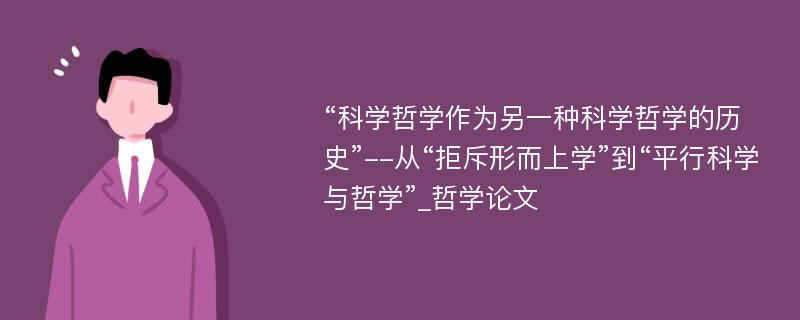
“科学哲学史作为另一种科学哲学”——从“拒斥形而上学”到“科学-哲学并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哲学论文,哲学史论文,形而上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种哲学的兴亡存废,折射着时代精神的高下分合,关系到家国天下的何去何从,不得不察! 科学哲学曾经对人类理性做出了重大贡献,其所倡导的分析方法等已经成为哲学从业者的基本能力,并影响到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诸多学科。但目前这门学科本身已经成为濒危学科,或许只有“往日的辉煌”(费耶阿本德)。 科学哲学的“病症”及其诊治由来已久。O.纽拉特和K.波普尔早在维也纳学派鼎盛时期就对观察命题作为“基本命题”(protocol sentence)的合法地位提出质疑,W.V.蒯因指出了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之间的划界存在诸多问题,T.库恩用“范式”的不可比性命题粉碎了马赫开创的“统一科学”的纲领,“索卡尔事件”暴露了所谓“后现代”科学哲学家已经失去了对科学的起码尊重,在“学术左派”和自然科学家之间的“科学大战”毁掉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就作为科学哲学根基的科学(physics)与形而上学(metaphysics)之间的天然同盟关系。①正如哈德卡斯尔(Gary L.Hardcastle)等在《逻辑经验主义在北美》(明尼苏达科学哲学研究丛书第18卷)所言,“综观当今学术文化,当代科学哲学甚至不是最宽广地反思科学的令人尊敬的领域。科学社会学、科学社会史及科学文化的研究等具体学科,成了作为人类实践的科学研究中更为有意义的问题、更为广泛地被人们阅读和论争的对象”②。 如果从1996年第一届国际科学哲学史大会所成立的“国际科学哲学史研究会”(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简称HOPOS)算起,科学哲学史研究在近20年的时间里着力于寻找科学哲学陷入思想困境的理论根源并探索重建的可能性,认为分析传统所倡导的“拒斥形而上学”导致了相对主义(在本质上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泛滥,危及了科学哲学本身的合法性,同时也动摇了哲学本身的存在价值,并波及全球性社会生活的离乱。 回归经典是救治哲学观念误区(misconception)乃至时代精神离乱(The spiritual anachronisms)的不二法门,F.弗里德曼等科学哲学(史)家指出,或许只有“回到康德”才能救治哲学观念的迷茫和时代精神的错乱。 康德哲学或许是我们思考哲学问题的可行范式,按照先天综合判断的进路,我们判断或预设学术史与学术的统一,(某种)哲学与哲学本身的统一,哲学本身与世界图景(或时代精神)的统一,是为准则如下。判断一:学说史或思想史本身可能就是一种做学问的方式,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都倡此说。科学哲学史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科学哲学的合法性得到了思想史的肯定,而是意味着科学哲学面临着“革命”或“重建”。思想史考察不仅仅是建设性的,而且更是批判性的,甚至是“治疗性的”。判断二:(某种)哲学与哲学本身可能是统一的甚或是同一的,不论是法哲学还是科学哲学,都必须认同何谓哲学的前提性问题,否则便立即失去其作为哲学探索的合法性。当科学哲学受到思想史质疑的时候,同样受到质疑的还有哲学本身:对科学哲学的思想史考察其实就是从科学史与哲学史的双重视野来拷问哲学何以可能及如何可能。判断三:不同的哲学体系正是用抽象的哲学语言来诉说人世间的是非冷暖,而且很可能是一种最切近于世态炎凉的真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总是某种“时代精神的精华”(黑格尔/马克思)或“世界图景”(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这意味着学术问题和社会思潮问题是相通的,当年维也纳学派的“拒斥形而上学”论断可能不曾料到它将带来当今相对主义盛行或民族主义大行其道。因而,对哲学的拷问并不仅仅是学术精英在象牙塔内坐而论道,而是以思想的方式对时事的评说。 面对普遍观念受到嘲讽的时代,通过对哲学某个学科的思想史考察来反思哲学本身,并通过思想史考察来评说当代的思想问题,或许是思者不可推卸的思想责任和社会责任,也是可以操作的或可行的学术策略:从熟知的学科进展到哲学本身,再到时事问题的解答。这也是F.培根、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维特根斯坦等思想巨匠在探索学术与社会问题的关系时留下的宝贵的思想遗产。 为了学术规范起见,本文采取命题化的论证方式,从乌贝尔(Thomas Uebel)和毛曼(Thoms Mormann)的“科学哲学史作为另一种科学哲学”(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 Philosophy of Science by Other Means)命题为线索,梳理科学哲学史从“拒斥形而上学”转向“科学-哲学平行”的思想历程。我们认同科学哲学史研究认为传统科学哲学的病根在于用科学来取代或“消解”哲学,因而拯救科学哲学的根本性思想举措乃在于正确处理科学与哲学之间的思想关联,特别是恢复或重建哲学在理解科学上的话语权。当然,本文并不是一味译介科学哲学史研究的牙慧,而是进一步挖掘其在科学与哲学之间的思想关联特别是在何谓科学(史观)、何谓哲学以及如何做哲学等重大学术问题上的思想价值。 按照这一理路,我们依次讨论三个在逻辑上密切相关的命题:“科学哲学史”能否成为“另一种科学哲学”?“另一种科学哲学”能否担保“科学-哲学并行”?“科学-哲学并行”能否推进对哲学本身的反思? 1.“科学哲学史”何以能作为“另一种科学哲学” 科学哲学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有诸多定义或理解③,其中T.乌贝尔和托马斯·毛曼所提出的“科学哲学史就是另一种科学哲学”(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 Philosophy of Science by Other Means或者Conceiving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 one of the ways of doing philosophy of science)颇具代表性。为了论证这个命题,我们将就“科学哲学史作为另一种科学哲学”分解成两个议题来讨论。 1.1 科学哲学史研究能否洞悉科学哲学分析传统的深层矛盾? 自1996年“国际科学哲学史大会”宣布成立“国际科学哲学史研究会”(HOPOS)以来,学界就何谓科学哲学史问题展开了热烈的甚至是激烈的讨论。在诸多看法中,主流性的观点往往把科学哲学史理解为分析传统的思想演进,也就是维也纳学派从奥地利的“科学的逻辑”转向美国的“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以分析传统观之,科学哲学史就是分析哲学史,这种观点的实质就是用分析传统作为编史学来查验科学哲学的历史,因而分析的科学哲学史不可能洞察科学哲学的深层矛盾。 T.乌贝尔在《当代分析科学哲学史的某些评价》一文中对这种主流看法提出了不同意见,概述如下:第一,科学哲学的分析传统因其“拒斥形而上学”而不可能认真地对待思想史,“分析的科学哲学在学术起源上缺乏历史意识”④,因此,分析的科学哲学不可能有其自己的思想史,也不能期待科学哲学的分析传统会成为编撰科学哲学史的编史学纲领。第二,分析传统的科学哲学“缺乏历史意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分析的科学哲学就是没有思想史源流的“无源之水”,而是植根于欧洲当时的学术文化:其一,马赫作为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科学哲学家,其与迪昂等人的法国约定主义学派之间富有成果的交流对逻辑经验主义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其二,新康德主义的科学哲学(Neo-Kantian philosophy of science)特别是马普学派(Marburg wing)的继承人卡西尔(Cassirer)的有关研究为早期逻辑经验主义提供了时空哲学。但就总体而论,科学哲学的分析传统源自康德的哲学传统,维也纳学派所谓的“拒斥形而上学”在思想上并不真诚。第三,更进一步地,科学哲学的分析传统并不是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是一种“统一科学”的世界观,而是诸多思想元素的折中,如奥地利-德国实证主义(Austro-German positivism),法国的约定主义(French conventionalism),英国的经验主义(British empiricism)特别是罗素的逻辑主义(logicism),希尔伯特及其追随者的形式主义(formalism),等等。 基于上述考量,科学哲学史研究发现,科学哲学的分析传统及其现存科学哲学诸派的最大问题,也许并不在于观察命题与理论命题的划界以及“范式”是否可比等具体问题上的疏漏,而在于处理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出现了原则错误。由于“拒斥形而上学”的思想目标而导致了对自身哲学信念的严重失察,如此造成了还原论(罗素)、独断论(维特根斯坦)、形式主义(卡尔纳普)、相对主义(库恩)以及各种“经验论纲领”(爱丁堡学派)的泛滥。 科学哲学史研究认为,现存科学哲学的致命伤在于科学与哲学关系问题上的失衡,特别是试图用科学方法取代哲学观念的原罪。“在我们看来,企图将哲学变成知识的一个分支(如心理学或数理逻辑)是愚蠢的,因为这些职能是在元科学的层次上致力于促进知识的新的可能性。同样,把哲学变成科学本身也是愚蠢的,这种努力将不利于哲学为达到对新范式的共识而相互冲突;我们无法预知某种新范式或哲学的元范式可能满足下一场科学革命的需要。最后,为哲学因缺乏科学水准而遗憾也是愚蠢的,因为科学与哲学是互补的,这才符合人类知识的辩证法。”⑤ 1.2 科学哲学史研究能否倡导一种有别于分析传统的科学哲学? 与黑格尔的哲学史就是哲学相匹配,乌贝尔的思想可以概括为“科学哲学史就是科学哲学”,但问题是,科学哲学史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科学哲学?它是一种与现存科学哲学保持基本共识的新流派还是一种在原则上不同于分析传统的科学哲学?为了延续并发挥乌贝尔的看法,T.毛曼正式提出了“科学哲学史就是另一种科学哲学”(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 Philosophy of Science by Other Means)的哲学命题。 第一,既然作为命题而存在,那必然存在于某种分类体系的逻辑结构中,毛曼首先区分了“分析的科学哲学史”(History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和“非分析的科学哲学史”(history of non-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在“非分析的科学哲学史”中又区分出“19世纪的科学哲学史”(History of the 19th Century Philosophy of Science)和“欧洲科学哲学史”(history of continental philosophy of science);在“欧洲科学哲学史”中又区分出“法国传统的科学哲学史”(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the French Tradition)等。这就意味着,科学哲学史不是唯一的,就逻辑结构而言,分析的科学哲学史和非分析的科学哲学史是等价的。 第二,在这种分类的基础上,毛曼认为,分析的科学哲学及其编史纲领过分迷恋科学哲学的分析传统,进而把其他有价值的思想排除在外。“某些深陷分析传统的哲学家认为,分析的科学哲学是唯一值得认真对待的科学哲学,在历史进程中那些与科学相关的所有其他探索简直就是形而上学垃圾。”⑥这就是说,分析的科学哲学史并没有公正地对待与之相竞争的其他纲领。 第三,基于这种考虑,“做科学哲学史研究意味着以某种方式进行科学哲学研究”命题至少蕴含着如下含义:科学哲学究竟有无历史(抑或逻辑经验主义真的“拒斥形而上学”)?我们是坚持还是质疑分析传统的思想路线? 第四,对科学哲学进行思想史考察,绝不意味着对这门学科的辩护,而往往预示着对它的怀疑和反思。“科学哲学史研究有助于用思想史的资源克服当代科学哲学的理论危机。……科学哲学史作为研究科学哲学的方式有助于克服在许多哲学阵营中广为流行的历史健忘症。”⑦ 上述四点,其实就是毛曼对“科学哲学史就是另一种科学哲学”这一命题进行的四个界定:科学哲学史具有编史学的多样性;力戒分析的科学哲学史的独断地位;科学哲学史研究也就是科学哲学研究;思想史研究方式有助于破解当代科学哲学的诸多理论难题。“科学哲学史的基本属性依然是科学哲学(still predominantly philosophy of science)。科学哲学史的研究规程是历史学的(Its modus operandis is historical),它的研究目的绝不意味着仅仅(尽管非常有必要)确立有关历史事件的性质、时间和人物。”⑧ 2.“另一种科学哲学”能否担保科学-哲学并行 上述分析表明,“科学哲学史作为另一种科学哲学”对分析传统的批判是恰当的,但它能否建构一种与现存科学哲学相匹配的思想体系,或者说它是否能够为科学哲学这门濒危学科提供新的思想契机,则是值得关注的。 2.1 “另一种科学哲学”能否开出科学哲学的新思路? 现存科学哲学基本上把科学哲学等同于英美的分析传统。“科学哲学史作为另一种科学哲学”认为,在英美的分析传统之外也存在科学哲学。 古廷(Gary Gutting)在《欧陆的科学哲学》一书中提出了一种与英美分析传统不同的科学哲学,认为“科学哲学这一哲学的分支学科源自19世纪康德的批判哲学,也源自现代科学对哲学事业观念的挑战”⑨。2008年12月18日—20日,维也纳学派国际学会召开了以“欧陆视野的科学哲学”(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a European perspective)为题的会议,其目的是通过全欧洲的共同努力推进对欧洲科学哲学(European philosophy of science)的共识,认为欧陆科学哲学具有深广的历史维度,历史维度不仅存在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之中,也就是科学哲学史之中,而且也存在于将文化和社会科学作为其学科组成部分的哲学之中。⑩例如,齐米苏(Cristina Chimisso)在《当代科学哲学史的法国传统面面观》中进一步论证了法国传统的科学哲学,认为法国科学哲学传统的奠基人物有笛卡尔、启蒙运动者(the Enlightenment)和孔德(Auguste Comte)等人,值得关注的人物有迪昂和彭加莱等。在当代,巴什拉和康居汉姆的“历史认识论”(historical epistemology)已经成为法国科学哲学的代名词。(11) 我们以为,或许科学哲学的欧洲传统(包括法国传统)是存在的,但能否超越现存科学哲学则需要论证。如果欧洲传统的科学哲学仅仅按照欧洲的科学思想逻辑自行演化,那只能证明欧洲传统的科学哲学是与分析传统并行不悖的;如果欧洲传统的科学哲学不仅有其自己的科学思想逻辑,而且还能够包容并超越英美传统的科学哲学,那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另一种科学哲学”。但就目前来看,所谓科学哲学的欧洲传统仅仅在强调认识论的历史维度(巴什拉)、认识与旨趣的关联(哈贝马斯)等方面有所作为,而尚未形成统一的研究纲领或理论体系,因而很难包容或超越科学哲学的分析传统。 综而观之,欧洲传统的科学哲学或许可以归并为非分析的科学哲学,但绝不可能是有别于现存科学哲学诸派的“另一种科学哲学”。 2.2 “另一种科学哲学”能否理解为非分析的科学哲学? 分析传统往往把科学哲学及其历史界定于从维也纳学派的“科学的逻辑”到美国的“科学哲学”之间,有人以库恩思想为界,有人放宽到“后现代”,但以逻辑经验主义为起点则是不可置疑的。 从科学哲学史的视角来看,即使将科学哲学理解为对科学进行哲学研究这种最为广泛的定义,也无法将分析传统的一己之见当成科学哲学的不二法门。正如“科学哲学史就是另一种科学哲学”这一命题的倡导者乌贝尔所说:“科学哲学史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打破了分析的科学哲学的某些实践者执迷于分析传统的褊狭。这种历史态度并不意味着‘分析传统’这个称谓没有任何意义,而是强烈地建议对于哲学信众而言把分析传统绝对化是错误的,这种历史态度提醒我们,分析传统仅仅是思想史诸多环节中的一环,它与其他相关环节之间的链接、影响和重合都是可能的。”(12)基于这种理解,科学哲学史研究的主题就是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 这就意味着,“科学哲学史作为另一种科学哲学”主要针对现存科学哲学在科学与哲学关系问题上的失衡特别是用科学取代或消解哲学的“原罪”,转而倡导科学与哲学之间的思想平衡特别是重建哲学在科学反思中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视域和方法的不同,学者们的方案并不一致,大致有如下几种观点: 平行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现存科学哲学用科学语言分析的方法“拒斥形而上学”破坏了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并存共生关系,但科学哲学史研究则特别关注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平行发展关系。正如弗里德曼所说:“我的主题就是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漫长的思想史中一直是相互关联的。科学与哲学共同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到前3世纪的古希腊,在晚期中世纪、文艺复兴和13世纪—17世纪的早期近代得以繁荣,推动了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的诞生直到今天。”(13) 连续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在科学命题(知识)和哲学命题(知识)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正如蒯因所说的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二分法并不存在一样,科学知识与哲学知识也是连续的。在《科学哲学史》这部代表性著述中,D.斯丹普(David J.Stump)将科学哲学史定义为“科学的哲学”(scientific philosophy),以区别于分析传统的“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而“科学的哲学可以指示许多不同的哲学家,但总是以如下思想相关:第一,认为哲学是一种客观的、真正的知识;第二,认为知识是统一的,因而哲学和科学是连续的;第三,哲学的变革起因于科学的新近进步;第四,倡导哲学及其知识的普遍性;第五,提倡科学的世界观”(14)。 互补的观点:在这种观点看来,科学与哲学不仅是平行发展且连续不断的知识谱系,而且是在结构上互补但在功能上各异的思想整体,弗里德曼就设计了一个科学与哲学作为统一整体的理性结构,“我的想法是,用一个平行的、相关的科学哲学的同时发展的历史来补充库恩的科学编史学。为了充分地理解科学知识的辩证法,我认为,我们需要用常规科学、科学革命和哲学构建三重结构来取代库恩的常规科学革命的二重结构,这里的哲学构建就是所谓的元范式或元框架,它能够导致或维系某个新科学范式的科学革命”(15)。 我们可以把科学与哲学的“平行的观点”“连续的观点”和“互补的观点”概括为或表述为“科学-哲学并行”。其实,这些表述无非是强调科学与哲学的统一,知识与观念的统一,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但是,“科学-哲学并行”有两个问题需要深入探索:其一,这一范畴类似于T.库恩所说的“范式”(Paradigm),但库恩的“范式”本身就备受诟病;其二,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思想史(包括科学史和哲学史)中找到这一范畴的本真表述,它是否就是柏拉图的“范型”,笛卡尔和洛克的“观念”,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维特根斯坦的或卡尔纳普的“逻辑句法”,福柯的“知识谱系”?这有待学术史的艰深考察。创造一个有价值的观念来表达时代精神是哲学最有意义、也是学人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3.“科学-哲学并行”能否推进对哲学的反思 传统观念往往把哲学区分为不同二级哲学学科的集合,如国外有认知哲学、科学哲学、政治哲学、生命哲学等,国内则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国哲学、中国哲学等;似乎每个哲学的二级学科都是一个自足的世界。本文以为,或许哲学确实存在二级学科,但这些二级学科并不是像库恩所说的那样是“不可通约”的“两个世界”,而是且只能是探索普遍观念的不同路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所谓的哲学二级学科都必须以自己的方式或路径回答何谓哲学、如何选择“世界图景”以及人类向何处去等共同关心的普遍理性问题。否则,就没有资格称之为哲学!哲学分支或世界图景可能有多种,但哲学只有一个! 一门哲学学科的合法性不仅仅在于它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还在于它能否对本学科的重大问题提出新的思考。笔者认为,科学哲学史研究所倡导的“科学-哲学平行”可能蕴含着重要的学术旨趣。 3.1 “科学-哲学并行”如何回答何谓哲学问题? 何谓哲学是任何一种哲学探索都必须直面的根本问题,回避或淡化何谓哲学的问题都难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哲学劳作。同时,对何谓哲学的不同回答也是检验某种哲学探索的学术旨趣和思想力度的重要标度。 在思想史特别是哲学史上,几乎所有重量级的哲学家或重大的哲学体系都十分重视回答何谓哲学的问题,并以重新回答何谓哲学问题来展开自己的探索。换言之,如果在思想史上出现了某种对哲学的重新定义或不同理解,这也恰恰是哲学取得重大进展或思想革命的理论征兆。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维特根斯坦等都是在思想史上重新定义哲学而开启哲学变革的旗手。例如,马克思将哲学理解为“改造世界”就开启了“实践哲学”的进路,而维特根斯坦将哲学定义为“语言批判”就标识着分析运动的肇始。 “科学哲学史作为另一种用科学哲学”不满于传统分析主义试图通过用数理科学取代哲学来“拒斥形而上学”,而是主张从科学知识的维度来理解哲学,D.斯丹普就曾经从五个方面概述了哲学的科学本性或知识本性。“科学的哲学可以指示许多不同的哲学家,但总是与如下思想相关:第一,认为哲学是一种客观的、真正的知识;第二,认为知识是统一的,因而哲学和科学是连续的;第三,哲学的变革起因于科学的新近进步;第四,倡导哲学及其知识的普遍性;第五,提倡科学的世界观。”(16)这就意味着,哲学就是(科学)知识的观念化,从事哲学劳作就是将实证知识提升为普遍观念的思想过程。亚里士多德、笛卡尔、洛克、莱布尼兹、康德、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维也纳学派等就是将某种知识变成哲学观念的典范。 这种哲学观,至少有助于重新审视三个问题: 第一,重新恢复西方自然哲学的优良思想传统。相较于其他文化传统包括中国哲学传统,西方哲学最鲜明的特色之一就是漫长的自然哲学传统,这种传统从古希腊一直延续到“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一传统的实质就是科学与哲学融为一体,互相补益。这一传统不仅创造了蕴含“形而上学蓝图”的近代科学体系,而且也创造了各种依照“科学准则”建立起来的哲学体系,如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斯宾诺莎的“伦理学”、黑格尔的“逻辑学”、马克思的“资本论”、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等。 第二,破解“拒斥形而上学”给哲学带来的思想难题。我们知道,传统科学哲学特别是逻辑经验主义所提出的“拒斥形而上学”,其矛头不仅仅指向海德格尔等现代思想家在“存在”问题上故弄哲学玄虚,也不仅仅指向所有传统哲学中的本体论体察,而且在于质疑哲学本身的合法性。“科学哲学史作为另一种科学哲学”就在于倡导科学与哲学之间的血肉关联,并从这种血肉关联中把握哲学的科学属性,认为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不必也不该“拒斥形而上学”,特别是不必也不该怀疑哲学。 第三,试图弥合“两种文化”的分野。哲学作为一种思考文化根基的基础性学科或科学,有责任对重要文化的走势作出判断或评估。C.P.斯诺在20世纪50年代准确地发现了一种思想危机即“两种文化”,新康德主义者M.弗里德曼在《分道而行》一书中曾经分析了科学主义与存在主义背离康德的思想过程,这种分离对当代学术文化产生了深远的思想影响。科学哲学史从“科学-哲学的平行”出发,“认为科学与哲学是互补的,这才符合人类知识的辩证法”(17)。不论是用科学取代或消解哲学的分析传统,还是用哲学超越科学的人文传统,都是错误的,至少是有偏差的。 因此,科学哲学史研究特别是“科学-哲学并行”的观念,不仅打破了科学哲学的分析传统,而且也对近现代以来的“两种文化”的“分道而行”提出质疑和挑战。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科学哲学史研究已经解决这个跨世纪的学术难题,而是说这种研究提供了超越“两种文化”对峙的思想目标,因而是值得追求的。 对于中国学界而言,探索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并从“科学-哲学并行”(也就是实学与玄学的互证)的视角反思并重建我们的学术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也许,西方哲学形态的现代性就在于西方科学与哲学的并行发展,而中国哲学的被动局面可能根植于科学的不发达以及科学与哲学的背离。 3.2 “科学-哲学并行”能否改进哲学的学术方法? 学术进展比知识增进更有意义。如上所述,重新定义哲学本身对哲学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比定义哲学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改进哲学家进行哲学劳作的思维方式,或者说,哲学的进步不仅仅表现为提出新的哲学观念或“世界图景”,还在于哲学家们提出哲学观念或“世界图景”的思维方式。按照我们的思路,一种有创意的哲学观念或“世界图景”的提出并不是哲学家的灵光一现,而是思想方式的重大革命。在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能够超越前苏格拉底派哲学,就在于他开创了用“三段论”(syllogism)和“四因说”的说理方式;笛卡尔之所以开创了近代哲学,乃在于他将数学分析的方法推进到哲学思考之中;康德哲学的伟大意义恐怕也不在于整合了经验论和理性主义的二元进路,而在于开创了“分析-综合判断”的先验分析方法。 “科学哲学史作为另一种科学哲学”反对离开科学来研究哲学的思想套路,坚持用科学的方法或“拟科学”的方法来思考或探索哲学问题。这种哲学思维方式就是坚持科学与哲学的相互关联,并在这种关联中把握哲学的思维方式,因而这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实质就是回到康德探索哲学的思想路线,“对于弗里德曼而言,康德就是一个典范,因为他提出形而上学应该关注经验可能性的先验条件。……对于弗里德曼而言,康德对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通过把纯数学和自然科学作为形而上学考察的起点,从而把形而上学从神坛上拉回到人类知识本身”(18)。 这种思维方式至少具有如下几个思想要点: 第一,坚持科学与哲学的统一的哲学认识论路线有助于克服哲学本身所固有的超验冲动,淡化哲学的“玄学”或“形上学”弊端,注重在科学知识的思想关联中维系哲学的科学属性,从而担保哲学的科学性与思辨性的统一,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 第二,坚持科学与哲学的统一的哲学认识论路线有助于提升哲学的认识论水平和方法论层次,克服哲学研究中的思辨陋习。哲学思考源自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传统,具有知识性与智慧性统一的特征,但自文艺复兴的科学革命以后,科学和哲学开始分离,哲学渐渐沾染藐视科学知识的哲学中心主义,尤以黑格尔哲学为著。而传统的科学哲学又走向了“拒斥形而上学”的误区,造成经验主义的泛滥,导致相对主义猖獗。科学哲学史研究主张科学与哲学统一的研究路线,力避藐视科学的哲学中心主义以及同样藐视哲学的唯科学主义。 第三,坚持科学与哲学统一的哲学认识论路线有助于从科学知识及其活动中挖掘哲学的思想资源,将科学知识提升为普遍的哲学观念。我们知道,在人类的诸多文化资源中,科学知识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它可能是唯一的关注真理的文化职能部门,为我们提供有关世界的真理性判断。哲学作为真善美的统一,作为人类的观念性建构,有必要从科学知识中汲取观念的要素,用以作为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思想资源。其实,在哲学史上,有相当一批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哲学体系就是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如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与他的“四因说”,笛卡尔的数学与他的“哲学方法”,牛顿力学与康德的“批判哲学”,罗素的数理逻辑与分析哲学等。 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改进科学哲学“拒斥形而上学”或轻慢哲学的研究套路,坚持用“科学-哲学平行”的纲领来建构科学哲学的理论体系和思想规范。 3.3 “科学-哲学并行”能否增进人们对哲学(史)或思想进步的重新理解? 不论何种哲学,是科学哲学还是伦理哲学,都不能回避对何谓哲学(史)以及如何做哲学(史)的问题。反之,对哲学及其历史的理解也会影响到具体哲学学科的探索。 黑格尔对哲学及其历史的看法对哲学研究及其反思具有持久的影响。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就是哲学史,这种哲学(史)观对于寻求理性之间的思想链接或许是有意义的,但它的最大问题是将哲学研究局限在历代专业哲学家的思想轨迹之内,似乎哲学与其所在的文化环境没有任何瓜葛。但这并不妨碍黑格尔在具体的哲学理论与哲学思想史之间进行了一次最富成效的建构,对此,当代学者的诠释是,“哲学研究具有历史性”(Doing philosophy historically)与“哲学史研究具有哲学性”(Do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philosophically)这两个命题是等价的。(19) 针对传统哲学的这种“思辨”属性,现代科学哲学特别是它的分析传统倒是十分重视哲学与其相关领域的关联特别是与科学的密切关联,认为必须对哲学进行科学改造,使其科学化。但是由于分析传统的局限性,哲学往往被理解为“科学命题系统”的“语言批判”(维特根斯坦)或“逻辑句法”(卡尔纳普)。这就意味着,科学哲学将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提高到哲学研究的议程,但却陷入了分析主义的一孔之见。 从科学哲学史研究的视角看,维也纳学派以及库恩等人的问题并不在于他的相对主义,而是“哲学并没有得到历史的审视”。因此,科学哲学史研究特别重视哲学在科学的思想体系及其变革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一,科学史研究应特别关注哲学史,其二,哲学史研究应特别关注与之相关的科学史的重要性。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这种考量的动机在于,如果不认真考虑科学和哲学在思想史中的相互作用,就不可能有正当的哲学理解,也不可能有正当的科学史理解。……没有科学史的哲学史,或既没有科学史也没有哲学史的科学哲学,都是不可能的”(20)。 从逻辑的角度看,“科学哲学史作为另一种科学哲学”无疑是黑格尔“哲学就是哲学史”的合理推演,只要科学哲学还属于哲学,它就逃不出这个逻辑。同时,这个命题也必然地要求科学哲学史对现存科学哲学各派观点的包容与超越,也包括对以往哲学思想的包容与超越。“科学哲学史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打破分析的科学哲学的某些实践者执迷于分析传统的褊狭。这种历史态度并不意味着‘分析传统’这个称谓没有任何意义,而是强烈地建议对于哲学信众而言把分析传统绝对化是错误的,这种历史态度提醒我们,分析传统仅仅是思想史诸多环节中的一环,它与其他相关环节之间的链接、影响和重合都是可能的。”(21) 按照这种理解,我们必须从科学与哲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考察哲学及其历史。正如麦克米林(Ernan McMullin)所说,“知识是统一的,因而哲学和科学是连续的”,“哲学的变革起因于科学的新近进步”等。这就是说,我们不应在哲学思想自身的逻辑中来理解哲学及其历史,而应该在科学与哲学之间的思想互动关系中来把握哲学的起源、发展及其多样化:哲学源自科学的探索,哲学的发展取决于科学革命,哲学的多样化受制于思想家对科学及其发展的不同理解。 一部哲学史,其实质是科学改变哲学的历史。这意味着,当哲学工作者面对哲学的停滞无所适从的时候,到实证知识中汲取思想可能是哲学最靠谱的选择。知识既是我们炸毁旧哲学的重磅炮弹,也是重建新哲学的可靠柱石。 当时代精神错乱了,可以听听哲学家的意见;当哲学家的意见错乱了,可以听听科学家的意见。只要科学还在,哲学就有希望;只要哲学有希望,时代精神就不会死!(22) ①Steve Fuller,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its Discontents,New York:The Guilford press,1993,introduction x. ②Gay L.Hardcastle and Alan W.Richardson,Logical Empiricism in North America,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3,introduction,viii. ③国际科学哲学史研究会(HOPOS)给出了一个官方界定,科学哲学史“在于对科学给予哲学的理解,这种理解有助于诠释哲学、科学和数学在社会、经济和政治语境中的思想关联”(HOPOS Journal Online)。这种理解看似寻常,但却至少透露了科学哲学史研究的基本要义,强调对科学进行哲学理解的基础地位,这与分析传统“拒斥形而上学”有原则上的不同。 ④Thomas Uebel,Some Remarks on Current History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in Stadler(ed),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a European Perspective,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B.V.2010,p.9. ⑤Michael Friedman,Dynamics of Reason,U.S,Stanford:CSLI Publications 2001,p.24. ⑥⑦⑧Thomas Uebel.Some Remarks on Current History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in Stadler(ed.),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a European Perspective,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B.V.2010,p.31,p.31,p.19. ⑨Gary Gutting,Contiontal Philosophy of Science,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5,introduction. ⑩F.Stadler(ed.),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Springer,2010,pp.7-8. (11)Cristina Chimisso,Aspects of Current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in French tradition,In Stadler(ed.),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a European Perspective,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B.V,2010,pp.42-43. (12)Thomas Uebel,Some Remarks on Current History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in Stadler(ed.),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a European Perspective,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B.V,2010,p.17. (13)(14)Michael Friedman,Dynamics of Reason,U.S,Stanford.CSLI Publications,2001,Preface,p.44. (15)(16)David J.Stump,From the Values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 to the Value Neutrality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s,in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edited by Michael Heidelberger,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002,pp.147-148. (17)Michael Friedman,Dynamics of Reason,U.S,p.24. (18)Marry Domski and Michael Dickson,edited,Discourse on a New Method:Reinvigorationg the Marriage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Carus Publishing Company,2010,p.5. (19)Jorge J.E.Gracia,Philosophy and its Histor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p.44. (20)Michael Friedman,Synthetic History Considered,in Marry Domski and Michael Dickson,Discourse on a New Method:Reinvigorating the Marriage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Carus Publishing Company,2010,p.573. (21)Thomas Uebel,Some Remarks on Current History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in Stadler(ed),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a European Perspective,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B.V,2010,p.17. (22)本文虽然结束,必留有诸多疏漏。本文开头时曾承诺命题化论证,但囿于诸因,这一承诺并未兑现:思想的一致性或许不成问题,但如何将思想变成命题,并在命题间推演,疏漏甚多,或仅仅是一种学术期望而已。标签:哲学论文; 科学哲学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科学论文; 思想史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哲学史论文; 逻辑分析法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哲学家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范式论文; 康德哲学论文; 历史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