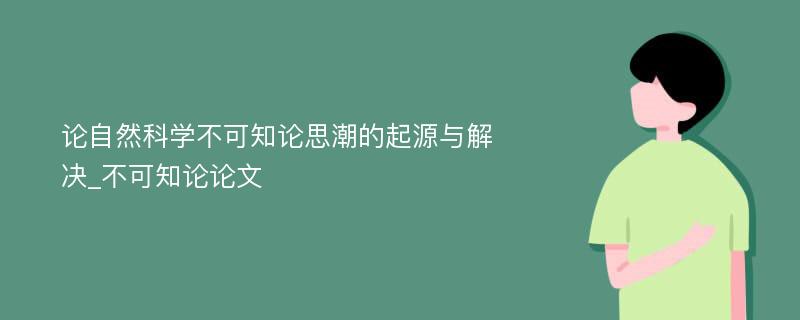
论自然科学不可知论思潮的根源与化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可知论论文,思潮论文,自然科学论文,根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80(2005)02-0008-05
人类史是一部不断追求客观真理的历史。黑格尔说:真理诚然是一个崇高的字眼,然 而更是一桩崇高的业绩,如果人的心灵与情感依然健康,则其心潮必将为之激荡不已。 但事实上,人们的自负和自卑,都会封闭探索真理的道路。
在近现代认识史上,不可知论哲学继承和发展了古代怀疑论传统,对自然科学和科学 哲学有着经久不衰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辩证思维而误读了自然科学的内在本质 、实证基础、表述形式和发展特点,也会使自然科学同不可知论发生扭曲的联系。其结 果,便是自然科学和科学哲学中不可知论思潮的不时泛起。显然,对不可知论的自然科 学表现进行历史审视和根源剖析,对哲学和自然科学各自健康发展与相互沟通都有重要 意义。
一 自然科学开辟道路与怀疑论哲学传统
“不可知论”(agnosticism)是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T.H.Huxley,1825~1895)于1869 年最先使用的哲学术语。他提出“不可知论”一词的原意,是指既对信仰上帝的苏格兰 国教纲领表示怀疑,同时又拒绝无神论,对关于存在无限的客观世界及其可知性的唯物 主义论断表示怀疑,从而把“上帝是否存在”这一类问题搁置起来。恩格斯称这些信奉 不可知论的自然科学家为“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者”。
不可知论思潮的哲学渊源,可追溯至古希腊罗马以皮浪(Pyrrhon,约公元前365~前27 5)为代表的怀疑论(scepticism)哲学,并在历史进程中谱写了怀疑理性、怀疑信仰、怀 疑经验科学的蜕变三部曲。皮浪学派认为:既然人们对每一事物可以有两种相互排斥的 看法,因而由感觉和理性得来的知识都不可靠;既然人们什么也不能确定,就应放弃判 断;即使人们真的认识了某一事物,也无法确切地说出来,因此最好是三缄其口。在欧 洲文艺复兴时期,伴随科学春天到来的是皮浪怀疑论哲学的复活。法国的蒙台涅(M.E.
de Montaigne,1533~1592)等人极力宣扬皮浪哲学,视之为消解教会文化专制主义的良 药、批判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利器,从怀疑理性走向怀疑信仰,为新科学的产生扫清道路 。
近代以来,为冲破独断论哲学的束缚,自然科学往往借重怀疑论哲学传统。近代欧洲 把怀疑论发展到极致的是休谟(D.Hume,1711~1776),他认为要回答在感觉之外是否有 物质实体或精神实体(包括上帝)都是超越人的认识能力的。康德(I.Kant,1724~1804) 是科学极限论的始作俑者。他说是休谟把他从莱布尼茨的“独断论迷梦”中唤醒了。他 在《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一书中写道:真理王国“是由自然界本身禁锢于不变限界 之内的岛屿”,“是一个被广阔的、汹涌澎湃的大洋”环绕着的王国。在那里,眼看就 要消融的云和冰好像是一些新的岛屿,“经常用虚无缥缈的希望欺骗渴望有所发现的航 海者”,诱使他们进行冒险,可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冒险进行到底”。[1]康德 毕竟出身于自然科学家,承认“物自体”的存在,把上帝放逐到认识无法超越的“彼岸 ”荒岛上让信仰去膜拜,同时确立了科学理性在“此岸”经验世界的最高权威。
19世纪上半叶,随着自然科学成为一种社会建制,对传统科学的怀疑和反思也加强了 。正如约翰·巴斯摩尔(J.Passmore)指出:当时的自然科学“决心在与思辨形而上学的 鲜明对比中展示它自身,自然而然地从新康德主义的武库中拾取武器”。[2]其中影响 最大的是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1838~1916)。从本质上说,罗素(B.Russell)和维 特根斯坦(J.Wittgenstein)等人的逻辑实证主义只是逻辑化的马赫主义。马赫在力学、 声学和光学等领域都有重要建树,又是世界上第一位科学哲学教授,对经典物理学的机 械论思想作过深刻批判,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创立有过重大启示。马赫自己说,他的哲 学是以康德的“批判唯心论”和不可知论作为全部批判思维的出发点。但实际上他没有 跟到底,很快又回到巴克莱(G.Berkeley,1685~1753)主观经验论的怀抱。
量子论创立者普朗克(M.Planck)和著名物理学家A.索末菲(A.Sommerfeld)等人,都严 厉抨击过自然科学中的唯心论和不可知论思潮。1908年,普朗克公开发表了与马赫主义 决裂的讲演,震动了当时的科学界和哲学界。
在20世纪后半叶,逻辑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结合产生了操作主义,以主观经验论和 不可知论为特征,对自然科学界影响甚大。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物理学家布里奇曼(W.
Bridgman,194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1905年爱因斯坦在建立相对论有关同时性概 念时,也受到过逻辑实证主义影响。对此,布里奇曼认为这是实证主义获得成功的“最 好例证”。但爱因斯坦最终选择了斯宾诺莎(B.Spinoza)实在论作为自己的“宇宙宗教 ”。他一再声称:“我不是一个实证主义者。我相信外部实在世界构成了一个我们不可 放弃的基础。实证主义者主张:凡是不能观察到的,都是不存在的。但是这种观点在科 学上是站不住脚的。”[3]
二 自然科学偶像崇拜与极限论的罪过惩罚
在人类思想史上,独断论和怀疑论始终处于两极振荡之中。20世纪以来,科学的空前 进步竟产生了一个悖论:科学至上观和科学极限观同步增长。
20世纪一开始,牛顿原理的至高无上性便被相对论和量子论推翻了。在这种摧毁性的 历史事件压力下,部分哲学舆论摆向另一极端,对科学偶像崇拜进行罪过的惩罚。由于 现代科学及其思维方法的发展,严格决定论、机械因果观受到了严厉批判,主体性、或 然性等概念逐步被科学界所接受。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否定一般决定论和因果律对客观 实在发生怀疑的强劲思潮。例如英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金斯(J.H.Jeans)作 为剑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从现代物理学革命中得到6个重要结论,其中有一半是不可 知论性质的:“我们不可能得到外界精确的知识”;“自然的过程不可能适当地表示于 空间和时间的构架内”;“就我们的知识所涉及者来说,因果性是没有意义的”等等。 [4]
另一方面,科学界一些人仍在追寻最小的“宇宙之砖”和最后的“宇宙谜底”,他们 相信物理学能找到“万物至理”(Theory of Everything)。1992年,美国著名物理学家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温伯格(S.Weinberg)在《终极理论之梦》一书中认为,众多的解 释最后收敛于越来越简单的原理,以终极理论告终。他推测,初露头角的超弦理论可能 会导致对宇宙的“终极解释”。[5]著名的数学家柯特·哥德尔(K.Godel)则相信打开“ 终极之谜”的钥匙早有了,它就隐藏在莱布尼茨(G.W.Leibniz)关于单子论的论文中。 凡此种种,不禁使人想起古希腊先哲们的信念:只要智慧女神雅典娜手中的猫头鹰在黄 昏起飞,就能觅到打开宇宙圣殿的金钥匙。
对“宇宙终极解”的追求,受到了有辩证思维素养的科学家的抨击。物理学家戴维· 玻姆(D.Bohm)指出:终极理论有如插入鱼缸中吓唬鱼儿的一道玻璃屏障,其结果是“终止对真实世界的进一步探索”。[6]科学史家萨顿(A.Sarton)则认为,把科学对世界的认识作用推向极致,就必然导致科学蜕变为某种偏见的体系,其基本原理将变为形而上学公理、教条,变为“新的圣经”,从而陷入科学偶像崇拜;同时他主张“有条理的怀疑精神”。2004年春夏,被誉为“活着的爱因斯坦”的霍金(S.W.Hawking),也终于正式声明放弃对“万物至理”终极定律的不懈追求,这一事件具有重要意义。
在历史钟摆的另一极端,20世纪以来的西方学术界时不时掀起“科学终结论”思潮。 早在60年代,法国著名物理学家皮埃尔·俄歇(Pierre Auger)发表“科学的极限”一文 ,对人类科学前途深感悲观,引发热烈争议。1989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古斯塔夫· 阿多夫大学召开过题为“科学的终结”研讨会。会议组织者最后忧心忡忡地宣布:科学 作为一种统一、普遍而又客观的追求,已经结束了。1997年,《科学美国人》杂志资深 撰稿人约翰·霍根(J.Horgan)出版了一本颇有争议的论著《科学的终结》,副标题是“ 在科学时代的暮色中审视知识的限度”。他也宣布:伟大而又激动人心的科学发现时代 已一去不复返了!值得注意的是,霍根的“科学终结论”特色,在于它是由独断论和怀 疑论混成的一杯奇特的“鸡尾酒”。他坚持认为现代科学已有的理论是极其成功的,其 正统性永远也不可能被超越;同时他又悲观地认为,对于那些真正基础性的科学问题, 科学本身是永远解答不了其谜底的。沃伦吉亚(J.B.Verrengia)在《洛基山新闻报》(19 96.7.28)上批评说,约翰·霍根对科学后备军的“忠告”是:“五彩的灯光已经熄去, 晚会已曲终人散,回家去吧!”但正如《纽约时报书评》(1996.6.30)所说:“对于科学 已行将就木这一论点,不论你持赞成还是反对态度,世界毕竟都不会因此而‘终结’。 ”
三 自然科学经验基础与现象论的感觉陷阱
通过观测和实验所获得的经验事实是自然科学的坚实基础。但是,如果离开了理论思 维的思考,不仅无法将两个最简单的事实或数据联系起来,而且存在不知不觉中滑向不 可知论和神秘主义泥潭的危险。在近现代西方哲学许多流派中,如新康德主义、马赫主 义、实用主义、新实证主义、存在主义等等,都因袭了实证主义以感觉论否定科学真理 客观意义、崇尚怀疑论的传统。
19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力图摆脱旧自然哲学“科学之科学”的君临地位,强调自身 的经验基础和实证特征。旧自然哲学走向解体的同时,也使一些自然科学家产生蔑视一 切理论思维的倾向。最肤浅的经验论成了经由不可知论走向神秘主义的坦途。英国博物 学家华莱士(A.R.Wallace)与达尔文同时独立提出“自然选择”生物进化思想,但他囿 于“眼见为实”,在1844年听了江湖术士关于麦斯默尔催眠术的讲演后,竟然相信伪科 学的“催眠颅相学”,从此热衷搞“心灵现象”实验,还加入各种“神媒”团体。英国 物理化学家克鲁克斯(W.Crookes)创制了克鲁克斯管,发现阴极射线和铊等化学元素, 也由经验论深深地陷入了唯灵论泥潭。他从1871年起为研究降神术而设计了种种物理仪 器,却忘了使用一件最重要的“仪器”——怀疑批判的头脑。T.H.赫胥黎凛然宣称自己 是“达尔文的斗犬”,但他作为一个崇尚经验论的自然科学家,首创“不可知论”这一 术语是意味深长的。
实证主义哲学首先提出“反形而上学”口号,力图把认识根源问题从科学中排除出去 。其创始人孔德(A.Comte,1798~1857)把人类知识发展分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 和实证阶段,认为一切知识都以实证事实为基础。这是思想史的一大进步。但他进而认 为,科学对象只能限于经验现象,科学功能只能叙述事实而不能说明事实,否则就是追 求“形而上学”即超验的本质或原因。孔德举例说,对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只能问“怎么 样”,而不能问“是什么”和“为什么”。“至于确定这种引力或这种重力本身是什么 ,它们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我们一律认为无法解决,是不再属于实证哲学范围的, 我们很有理由地把它们让渡给神学家们去想象,或者交付给形而上学家们去作烦琐的论 证。”[7]
马赫认为,物理要素复合体即“感觉的复合体”,科学方法即“感觉的分析”,“感 觉要素”是统一科学的基础,也是世界统一的基础。有些学者认为,在微观领域,时间 、空间和客体的实在性由于主体与客体关系不可分而不可知。按照物理学中的操作主义 观点,物理概念的内容不是取决于物体属性,而是取决于我们实现该概念的操作,物体 的属性“应在操作中去寻求自己的意义”。爬行的经验论者认为只有直接可感知的东西 才是真实的,概念既然不可感知就是虚假,他们希望“看”到时间,“嗅”到空间。早 期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在物理学中,凡是不能或者还没有为仪器所直接探测到的物理事 件都是主观虚构。后来,卡尔纳普(R.Carnap)等人进而认为连间接的经验证实都不可能 了,他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中叹息说,我们在清醒中还是在梦中是无法判定的。
在感觉问题上,一些主张唯物论的不可知论者也承认感觉是高度组织起来的物质的特 性,是外部物质作用于感官的结果,但又不承认“感觉中的物”与“现实中的物”有类 似、相似之处。例如,俄国哲学家普列汉诺夫(Г.В.Плеханов,1856~1918)的“象形文字论”,德国著名生理学家、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H.L.von Helmholtz,1821~1894)的“符号论”。后者还以人的眼球结构的局限来论证人的认识的绝对极限。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诚然蚂蚁能看见人所不能看见的紫外光线,但是人能知道这个事实本身足以说明,人的感觉器官的局限并不是人的认识极限的证明。因为人除了眼睛,还有其他感觉器官;还可以制造出种种延伸感觉器官功能的工具;而更主要的,人有大脑及其思维活动。
四 自然科学数学化与约定论的幻觉屏障
科学思想史表明,如果说狭隘经验论是通向不可知论泥沼的古道,则数学化进程在极 大推动科学进步的同时,约定论又成了滑向不可知论深渊的幽径。
数学研究现实世界和可能世界的数量关系与空间形式,具有抽象性、集约性、精确性 和普适性的特征,为科学研究提供一种简明精确的形式化语言、辩证思维的表达方式、 定量分析和理论计算的方法,以及逻辑推理和科学抽象的有效工具。科学数学化的程度 是科学进步的重要标志。马克思说过,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 正完善的地步。数学化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之一。
但是,随着自然科学理论日趋形式化、符号化和高度抽象化,以及创造性的想象力、 类比、直觉、科学美学等方法的运用,对自然科学数学模型本质的争议,又不时旧话重 提:它们是自然客体的拟真反映还是“纯粹思维的创造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关 于物理学数学模型的本质问题有过一场激烈论战。马赫和德国物理学家奥斯特瓦尔德(C .W.W.Ostwald)等人主张以“函数关系”取代因果性、规律和物的客观实在性。马赫在 《功的守恒定律的历史和根源》(1872年)中提到:“我很久以前就企图用数学函数概念 代替原因概念,即用现象的相互依存关系,严格地说,用现象特征的相互依存关系来代 替原因的概念。”[8]马赫认为,科学理论和数学模型只是描述经验的“方便的作业假 说”,是“补充经验的简便的经济的手段”,而这些手段与现象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如 果科学家因其成功就假定原子论数学模型的实在性,那么他就混淆了把科学的丰饶领地 与形而上学思辨的烂泥坑区别开来的界限。
法国数学物理学家亨利·彭加莱(H.Poincare)正是从数学的符号化、形式化和约定化 特征出发构建约定主义,最终否定了科学概念和理论的客观性。皮埃尔·杜恒(P.Duhem )也说,一个理论就是由试图尽可能简单、完全、精确地描述一整套实验规律的数学命 题所构成的系统;一个物理理论并不是“解释”,解释应该留给形而上学家。
一些科学家严厉驳斥了约定主义。奥地利物理学家玻尔茨曼(L.Boltzman)认为,不能 用数学模型的主观形式来反对其反映的物理原型的客观内容。他指出,自然界的统一性 显示在关于各种现象领域的微分方程式“惊人的类似”中,“用同一方程式可以解决流 体动力学的问题,也可以表达势论。流体的漩涡理论和气体的摩擦理论显出同电磁理论 有惊人的类似”;[9]而用微分方程式表明的世界图景,只是“排列在三维空间中的巨 大数量的物依照一定规律在时间上变化的图景。”[10]普朗克也坚决反对物理学数学模 型约定论。他说,原子是实在的,这不折不扣和天体是实在的一样,当人们说氢原子重 1.16×10[-24]克时,其真实性好比月亮重7×10[25]克一样。诚然,月亮是看得见的, 然而海王星的质量在天文学家用望远镜看到它之前就已经测定出来了。爱因斯坦更指出 ,马赫“认为科学所处理的是直接材料,这种科学观使他不承认原子的存在。”[11]“ 马赫多少有点忽视了这样的事实: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存在的,我们的感觉印象是以客观 事实为基础的。”[12]但是,当晚年的马赫和奥斯特瓦尔德从荧光屏上看到由α粒子轰 击发出的点点闪光时,最终还是勇敢地承认了原子的存在。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物理学家约翰·惠勒(J.A.Wheeler)等人竭力宣称“现实世界 并非完全是物质的世界”。他从数学的约定性出发,认为“世界只是想象中臆造的东西 ”。为此,他在“信息论、物理学和量子论:寻求其间的纽带”一文中,提出一个近乎 禅宗偈语的命题:“万有源于比特”(the it from bit)。他说:“每一个有,……每 个粒子,每个力场,甚至时空连续统本身……其功能、含义及其绝对存在,都来自于设 备对‘是或不是’问题所给出的答案,都来自二进制选择,都来自比特”。[13]以至80 年代初期,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年会的组织者们在分组讨论时竟把惠勒与三位灵学家 置于同一议题之下。可见,由于数学化进程的加强,数学精神浸入物理学的判断方法和 对物理学的理解中去,使一些人产生了对物理学客观性的怀疑和思想动摇,似乎数学的 抽象虚构,在物理实在和科学家用以理解这个实在的科学方法之间放置了一重不可逾越 的屏障。
五 自然科学探索精神和虚无论的绝望解读
什么是科学精神?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徽的背后,镌刻着一行意味深长的箴言,言简意赅 地对此作了回答:“不崇拜权威,不人云亦云。”从本质上说,科学精神就是不断探索 、创新和求实的精神;就是反对愚昧和迷信,不盲目崇拜任何偶像;就是对客观真理的 无止境的追求。科学精神对包罗万象、无所不知的传统自然哲学体系的破坏,是历史的 巨大进步。但是,科学精神的批判特征和科学真理的相对意义,也很容易使缺乏或鄙视 辩证思维的人们产生虚无主义倾向。
科学假说是科学探索精神的集中体现,它以科学性与猜测性统一为特征,本质上有别 于常识经验、哲学思辨和宗教神话。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 科学假说以业已检验的科学原理和不完备的经验事实为基础构建新的理论陈述,对已知 现象进行新的因果诠释和对未知现象进行超前预测。
科学进程越是快速发展时期,不可知论思潮越是容易泛滥。人们常常会听到来自科学 界一些诸如此类的告诫:永远不要费心追赶一辆公共汽车或一种科学新理论,因为你总 会很快等到下一个。“对缺乏逻辑和辩证法修养的自然科学家来说,互相排挤的假说的 数目之多和替换之快,很容易引起这样一种观念:我们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质。”[14]
例子比比皆是。例如J.H.金斯说,原子模型有卢瑟福行星系模型、波尔兹曼模型和量 子力学模型等等,“因此,我们永远不能够肯定哪一个模型是对应于实在。简言之,我 们永远不能够具有某种有关实在性质的知识。”[15]费耶阿本德(P.Feyerabed)从批判 “科学至上论”和“终极答案论”出发,更是把一切“追逐客观真理的热情”都斥之为 “疯狂的举动”,并于1987年出版了《告别理性》一书。在美国拉特格斯大学任教的英 国哲学家科林·麦金(C.McGinn)甚至认为,人类面对一些重大科学问题,就像一只耗子 永远不可能求解一道微分方程一样。
人的认识是一个“永远的、没有止境的”运动过程。由此,决定了一切科学真理都具 有辩证否定的因素(作为联系和发展的环节),决定了科学史实际上是不断以比较不荒诞 的谬误替代较为荒诞谬误的历史。但是,如果对自然科学发展形式作虚无论的相对主义 解释,看不到科学真理是相对性、可变性与客观性、守恒性的矛盾,看不到人的认识存 在非至上性与至上性的矛盾,看不到科学实践的本质力量,就很容易不知不觉滑向不可 知论泥潭。不可知论同科学探索精神的扭曲联系,源于“它片面地歪曲地接受了辩证法 的若干组成部分(例如,相对主义)”。[16]而科学态度要求我们,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 的意义上,而是科学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 切知识的相对性质。事实上,“人不能完全把握 = 反映 = 描绘全部自然界、它的‘直 接的整体’,人在创立抽象、概念、规律、科学的世界图画等等时,只能永远地接近这 一点。”[17]总之,“无限地接近”既不等于“穷尽”,也不等于“不可知”。
六 科学实践:对不可知论最强力的天然解毒剂
单靠逻辑论证无法从根本上驳倒不可知论,所幸的是人们在论证之前已经有了行动。 恩格斯说,把不可知论以及其他一些哲学怪论驳斥得最彻底的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 诚然,任何时代的科学实践都不可能完全证实或驳倒一切理论,但任何理论最终要由科 学实践结果来评判,却是毫无疑义的。科学实践是对不可知论最强力的天然解毒剂。
以天文学史为鉴。美国天文学家哈勃(E.P.Hubble)在《星云的世界》一书中指出:天 文学的历史就是不断开拓视界的历史,知识有如波涛起伏那样向前发展,每个波都代表 我们又找到了解释观测资料的某些新线索。也就是说,科学的一次次进步都是对不可知 论和独断论的一次次否定与超越。
孔德在1856年作过两个天文学预言:(1)人类永远无法知道其他星球的化学成分;(2) 人类永远无法看到月球背面情况。但是历史很快就嘲弄了他。只过3年,德国的基尔霍 夫(G.R.Kirchhoff)和本生(R.W.Bunsen)通过分析比较太阳光谱认证了太阳大气的元素 构成。孔德预言113年后,人类登上了月球。
20世纪50年代末,法国物理学家布里渊(M.L.Brillouin)等人讥笑现代宇宙学只是一曲 “纯粹的幻想”,是“痴人做梦”。1964年美国射电天文学家彭齐亚斯(A.Penzias)和 威尔逊(R.W.Wilson)共同发现3K微波背景辐射,强有力地支持了“我们的宇宙”具有统 一起源的看法。
20世纪60年代,法国物理学家皮埃尔·俄歇在“科学的极限”[18]一文中提出著名的 “四大极限”,怀疑人类的能力。我们可以看看40余年来科学实践是如何反驳俄歇的。
第一,俄歇提出“观测极限”:不管人类能制造多么灵敏的望远镜,也无法观测到100 ~150亿光年距离之外的河外星系。他说:“这里有一种绝对的分界线,它构成了关于 我们知识的确定的壁障。”事实是:时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天文学家已观测到距地球 120亿光年以外的类星体,并正在制造观测能力更强大的下一代望远镜。第二,俄歇提 出“旅行极限”:不可能访问太阳系以外的行星,“甚至是否可以到太阳系中较远部分 去旅行,也使人有所怀疑。”他的话音犹存,1969年7月16日美国“阿波罗11号”登上 月球;7年后,“海盗1号”、“海盗2号”相继在火星着陆,并进行了生命考察实验; 随着90年代末美国“探路者”号等探测器的火星实地考察,人类登上火星也排上了议事 日程,估计在2015年左右会梦想成真。第三,俄歇提出“能量极限”:人类用加速器获 得的能量,“永远不能达到极强宇宙线的天然能量10[18]电子伏或更高。”从本质上说 ,俄歇的“能量极限”是人类今天的历史极限,而不是永恒极限。虽然目前尚无法对此 作出确切预测,但是模拟宇宙天体极端条件的仿星学及其实验技术的出现,正是尝试打 破这种极限的开始。诚然,人类永远无法人为制造宇宙中的许多演变过程,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人有可能认识其机理和规律,从而趋利避害,造福人类。
最后,俄歇提出“思维极限”:人类大脑的思维能力迟早有一天也会“发现它的边界 ”。“人类思维能力的增进类似于马戏团中的动物在训练过程中所获得的长进”,而最 终一切努力“也只能迟缓我们心灵最终的‘饱和’”。现代脑科学研究指出,人脑神经 细胞的个数约为1000亿,达到银河系恒星总数量级;一般人的记忆能保持70~80年以上 ;人脑未加开发使用的潜力超过90%;有的学者甚至说,如果人们终生好学不倦,则人 脑中储藏的各种信息量,相当于5亿本书籍的知识总量,即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书的50 倍。这里还仅仅提及个体人脑储存信息的潜在能力,尚未考虑到其他方面更为重要的能 力,以及人类作为认识和实践主体的整体效应,尤其是人—机互补系统建立所产生的不 可估量影响。可见,俄歇的极限思维只是俄歇本人的思维极限。
综上所述,要求对人类万能论与人类无能论进行两难选择,相应地对科学万能论与科 学无能论进行两难选择,必然使思维走入绝境。只有彻底搞清相对主义和辩证法的关系 问题,才能同时与独断论和怀疑论划清界限。审视自然科学不可知论思潮的根源及其解 药,使我们想起了康德同乡、大数学家希尔伯特(D.Hilbert)在哥尼斯堡的一次演讲。 他在提到孔德不可知论幻灭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结束语:“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必 将知道。”[19]
收稿日期:2004-09-08
标签:不可知论论文; 科学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数学素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物理学家论文; 数学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马赫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