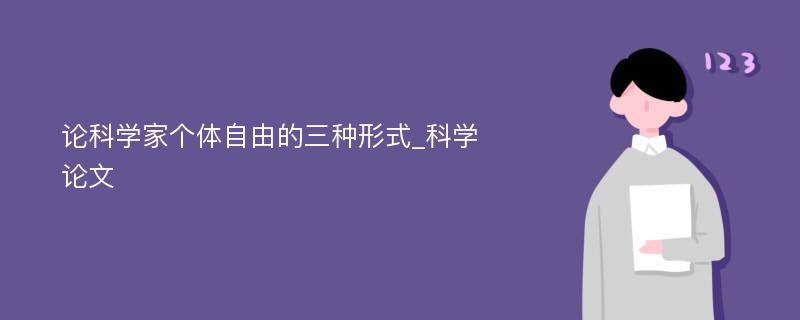
论科学家个人自由的三种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种论文,科学家论文,形态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由是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实现科学创新的基本条件。追求自由是科学家的重要品质,也是科学的基本精神。科学活动的自由应当是内在自由和外在自由的统一。其中,内在自由是科学创造活动不可缺少的精神品质,是科学创造的源泉,也是科学家的独立意识和人格的彰显;外在自由是科学家所享有的能够自由地探索真理、传播科学思想的经济和政治权利,是科学活动的社会环境。正确协调和处理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的关系,是保证科学正常、健康和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为此,我们以科学的历史发展为视角,尝试性地提出科学家个人自由的三种基本形态:无待自由、职任自由和责任自由,并认为责任自由是现阶段科学家个人自由的最高形式,实现和保证科学家的责任自由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使命。
一、业余科学活动与无待自由
古希腊学者所从事的科学和哲学探索活动对近世科学的最大贡献,就是确立了以探索和传播真理的自由为主要内容的理性主义原则。古希腊城邦民主制度为这种理性自由主义原则提供了社会保障。但是,古希腊不存在科学家的职业角色,从事自然知识的探索只是某些哲学家或占星家的业余爱好,他们的活动受好奇心驱动,没有任何功利目的。(本-戴维,第89页)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因为人们最初是被好奇心引向研究(自然)哲学的——今天仍是如此……所以,如果他们钻研哲学可以避免无知的话,那么,他们为求得知识本身,不考虑功利应用而从事科学活动,就是一种个人权利。”(麦克莱伦第三和多恩,第82页)这一时期科学家虽然享有绝对的思想自由,但由于科学活动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还不具有举足轻重的决定性作用,科学活动几乎得不到社会的支持,由此便决定了其衰落的命运。
与古希腊相比,近代科学活动的最突出特征就是科学的价值得到了官方的承认,一些得到官方认可的科学组织开始建立。科学组织的建立导致社会上产生了相当数量的科学家,像牛顿、波义耳、拉瓦锡等,但这一时期科学研究仍然没有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参见赵佳苓),社会上也没有出现一种由国家支持、专为科学提供经费的机构,科学研究仍然只是一种业余活动,科学家是一些业余的科学爱好者,他们必须用从事其他职业的收益来维持个人生活以及支持科学活动。即使像法兰西科学院这种专职的研究机构,科学院的院士设置也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精英职位:“这些职位不允许尝试把科学工作变成一种固定的职业”。(本-戴维,第161页)事实上,直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科学家中的大多数还是来自上层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的业余科学爱好者。直到19世纪初,科学研究从根本上说是科学家个人的事业,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是业余爱好者,“甚至那些有大学职位的人,也不被期望从事做独创性研究。科学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有其他生活来源的人作为次要职业的业余爱好”(齐曼,第61页)。在这一时期,科学没有发展成为一种职业。科学家依然保持了古希腊学者研究的风格,保持着个体独立的自由探索、自由发表研究成果的特点。普赖斯把这种高度自由的科学称为“小科学”。个体研究、自由选题、“只求知识,不问应用”,是业余小科学的典型特征。
我们把业余科学时代科学家所享有的这种自由,称作“无待自由”。所谓无待自由,是指不受任何外在事物和外部条件控制、只凭内心意向去求索的自由。与“无待”对应的是“有待”,它是指事物的运行或人的某种愿望和要求的实现要受到一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因而不能不有所凭借、有所依赖。“有待”和“无待”的说法源自《庄子·逍遥游》中的“犹有所待”和“恶乎待哉”这两句话。在庄子那里,“有待”和“无待”意味着人生的两个层面。“有待”意味着活动会受其所依赖的外在事物的限制,意味着要承担某种义务,在手段方面是不自由的;反之,“无待”意味着活动本身就是目的,在手段方面是自由的和自主的。在庄子看来,只要“心无所待”,就能悠然自得,不受世俗欲望的支配,就能“物我为一”,从而达到一种真正自由的境界。
业余科学家的价值取向与庄子的这种“无待而逍遥”的人生追求一样,都保持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和独立人格。在很大程度上,业余科学家探索自然奥秘出自一种内在的生命冲动,而不是出自任何世俗的功利性,因而,他们的探索仅仅是为了追求真理本身,无须借助外界力量,也不被要求为现实社会承担任何责任。亚里士多德指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是为了消除愚昧和无知,也可以说是为了自由。为求知而从事学术,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寻求智慧,这是“无待”的境界,也是求知的最高境界。近代天文学家第谷说:“当政治家或其他人使他不胜烦恼的时候,他就应该坚决地带着他的财产离去。人在各种条件下都应该昂然挺立,无论至何处都是上有青天,下有大地,对一个具有活力的人来说,每一个地方都是他的祖国。”(转引自戈兰,第14页)这就是业余科学家的科学追求和人生理想。余英时认为,西方所谓的“知识分子”即源于这种近代型的科学家知识分子形象。(余英时,自序,第3页)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拥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始终保持一种独立的人格。
总之,处在无待自由状态下,业余科学家以追求真理为唯一目的,没有掺入任何功利的和非自然的个人情感的因素,因而无待自由本质上是一种主要体现为内在自由的自由形态。这是科学创造的前提,也是维持人类生存和社会进步的基础。但是,由于无待自由本质上是一种脱离世俗基础的自由,缺乏社会支持的思想和物质基础,因而其研究活动常常会在此双重挤压下被迫中断。
二、科学研究的职业化与职任自由
从19世纪中叶开始,科学研究逐渐成为一项专门的职业,科学家实现了职业化。科学研究的职业化可以保证科学家有稳定的生活来源,使他们不再为生计而奔波,可以有充足的经费和时间从事研究。然而,任何一项依靠外来资助所维持的活动,无疑都会受到相应的外来条件的限制。正如贝尔纳所说,职业科学家“在经济上受到双重挟制,不但他个人的生计,取决于他是否能讨好他的雇主,而且作为科学家,他必须有一个往往成为他自己主要生活动力的工作领域。为了取得(在)这个工作领域从事科研的机会,购置设备和雇佣助手的经费,必须讨好施舍金钱的当局。”(贝尔纳,第451页)因此,科学研究的职业化使得科学家和政府之间建立了一种社会契约,契约双方作出了各自的承诺:一方面政府负责对科学活动提供经济和政治条件的支持,科学家的外在自由得到了合法保护;另一方面,科学家从事研究的好奇心必须服从政府的需要和制度安排,从而科学研究在运作方式上发生了变革,科学家的内在自由受到了约束和限制。
科学研究一旦作为一种职业在社会生活中建立起来后,就具有了一种谋生的性质,原来完全受个人兴趣驱动的个体自由研究,开始被定向的集团协作劳动所取代。科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存在,既要最大限度地争取得到社会支持,又要尽可能地保持科学系统自身的自主性,这时科学家的活动同时受到了组织和社会的双重控制。我们将这种态势下职业科学家所享有的自由,称作“职任自由”。
“职任”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有两种含义:一指官员的任职和职责,二指某项具体的任务派遣。也就是说,职任是指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行为主体应该承担的责任、任务,是指“食他人之俸禄”不得不去承担的任务,它强调的是必须和命令,因而具有强迫或被动的意义。所谓职任自由,则是指科学家为完成外界赋予的定向任务而享受到的权利。职任自由与无待自由是对立的两极,它是一种“有待”自由。由于职任自由是科学家用自己的某项专业技能作为工具换取来的自由,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屈从于某些实际利益而失去捍卫真理的尊严,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个人的空间,因而职任自由是一种主要体现为行动层面的外在自由。从科学的历史发展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把职任自由划分为弱职任自由和强职任自由两个阶段。
从19世纪中叶到二战结束,科学研究主要在军事科研和工业研究领域实现了建制化发展。为了获得从事研究的权利,科学家必须迎合政府或企业的功利性需要,从而成为政府或企业研发组织的雇员,被研发机构雇去做全时的研究工作,从事着任务定向研究。与此相应,研究过程以及研究成果也被置于雇佣机构的控制之下。于是,科学中的个人主义和自由研究被集体主义、任务定向和实用主义所取代,科学研究成为向社会提供物质支持的功利性手段,而科学本身的目的意义及其固有的精神价值式微,基础研究被严重忽视。但是,这一时期存在于大学中的基础小科学仍然主要依靠私人基金会和社会慈善机构的少量资金来维持,少数学者仍然可以凭个人兴趣从事自由探索研究。我们把这一时期科学家的个人自由称作“弱职任自由”。
二战结束后,基础科学研究进入了规划科学的时代。在由政府统一资源配置的规划科学背景下,科学家的选择只有纳入国家规划和计划,才能获得实现的机会。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基础研究进一步引入国家目标。在基础研究中引入国家目标意味着基础研究的方向选择必须首先考虑国家的利益,为国家目标服务。政府通过科学规划和各类计划进一步控制着基础研究的方向、方式和应用,科学家被政府的“效用规范”驱动着,失去了对真理的狂热追求和献身精神。与二战前的阶段相比,他们拥有较少的自主性和较多的政治约束,这时科学家所享有的自由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科学家个人自由的“强职任自由”阶段,其特点集中表现为科学研究的国家主义、产业化,研究成果的局域化,以及科学奖励的政治化与知识生产者角色之间的冲突。在这一阶段,科学研究的自主性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科学家自由探索的空间严重缺失,科学家探索和思考世界奥妙的好奇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扼杀。
与此相联系,职任自由不可避免地具有如下两个缺陷:第一,由于科学仅仅被看作是政府或企业产生效益的工具,是国家创造财富的动力,这就使得社会对科学的支持极易因为受到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影响而中断,最终导致科学持续发展的动力枯竭;第二,科学家受雇于政府机构或企业从事特定指向的研究工作,致使其选题的自由和发表自己思想的自由的权利被剥夺,提供资助的当局一般也不允许他们承担专业以外的其他职责。如此一来,科学家的自觉能动性受压抑,不能自主地担负应有的社会责任。例如曼哈顿计划中,被政府召唤参加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科学家,不仅他们的言行受到严格的保密制度的束缚和限制,每个科学家只知晓自己所负担的研究任务,而不知道研究工作的实际目的,而且在是否对日本侵略者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他们也没有实质性的发言权,虽然他们被看作是能够提供新思想、新发明的“智囊人物”。(戈德史密斯和马凯,第32页)这两方面缺陷的存在,致使职任自由状态下的科学家不能真正地担当起科学求真和造福于人类的责任,因而,随着科学事业的发展,职任自由必然被一种新的高一级的自由形态所取代。
三、国家目标与责任自由
科学家个人自由的性质与科学对社会的影响方式是分不开的。爱因斯坦指出:“科学对于人类事务的影响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大家都熟悉的:科学直接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间接地生产出完全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工具。第二种方式是教育性质的——它作用于心灵。”(《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第135页)这就是说,科学服务于社会有两种基本途径,一是物质性的,它以技术为中介,为生产的进步开辟道路;一是精神性的,它直接作用于人的理智和心灵。科学的这两种价值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一个社会只有把这两种作用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予以同样的重视,才能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主动创造性,有效地实现科学的真正价值。只有此时,科学家的个人自由才可能获得完善的形态。
无待自由因过分强调了科学研究对于人类心灵的精神价值,而贬斥了科学的功利价值,所以它主要实现了人的内在意志的自由;职任自由提升了科学的功利价值,但却忽视了科学的重要精神价值,致使内在自由在很大程度上缺失,因此,它主要实现的是人的外在自由。随着国际竞争在创新能力方面的日益增强和激烈化,科学的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必然日益同时受到重视,因而,国家目标和个人研究自由的统一已经成为一个必然趋势,对科学家的自由探索和首创精神的保护已经成为国家目标实现的前提。这一状况催生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科学家在成功地获得资源以实现科学自身目的的同时,自觉地把对社会进步的贡献和国家的公共利益作为一种学术使命引入到研究活动中去。于是,研究自由与社会责任便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过去那种把研究自由与社会责任二者对立起来的观点将受到否定。我们把这一状况下科学家所享有的自由,称作“责任自由”。
所谓责任自由,是指社会建制中的科学家从事科学知识探索及其与之相关的活动而享有的权利和义务。从英文词源上看,责任" responsibility" 一词来自拉丁文" responaeo" ,意味着有能力履行义务、可以承担、使人满意等。在现代汉语中,责任有两个基本含义:第一,份内的工作或应有的使命;第二,由于失职而应当接受的处罚或承担的道义。虽然职任与责任都含有义务、任务和职责之义,但与职任相比,责任主要强调了“应该”承担的任务,它既包括份内的工作安排所承担的任务,又包括知识分子出于使命感而承担的义务和任务,即作为一个社会公民应主动担当起关注社会发展和人类整体利益的使命,同时包括对自己行为的过失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责任主要被理解为人的生存理念、生存境界、生存智慧以及生存的理性自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般都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他们求知的至上目的。责任自由是一种以社会责任为核心的自由形态。这里的社会责任是科学家的一种理性自觉,是科学家把追求真理并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内化为社会公共关怀的一种自觉意识。责任自由是一种内在自由和外在自由相统一的自由形态。具体地说,责任自由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责任自由作为一种内在自由和外在自由相统一的自由形态,其研究自由与社会责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责任自由强调科学家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应担负相应的社会责任。在责任自由状态下,科学家自觉地把科学的求真目的与国家利益、人类整体利益结合起来,将自己的创造活动纳入到社会财富资源的洪流之中,让社会责任内在地置于研究自由之中。科学家不同于政治家,他的职责就是“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顿悟的世界图像;于是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cosmos)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同上,第1卷,第101页)。因此,为了捍卫个人探索真理的独立性并对其造成的社会后果负责,科学家就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维护社会正义,以真理的尺度对事关社会安危的重大问题客观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保证科学成果造福于人类而不是相反。另一方面,责任自由把“为求知而研究”视为最基本的价值,让追求真理本身成为研究的目的,从而确立了科学求真的责任。责任自由强调科学家承担社会责任,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屈从于权力意志,“由政治权力来左右知识分子的人格和知识”(许纪霖,1991年,第237页)。相反,它是在强调科学有其独立存在价值的前提下,将社会责任与求真责任内在地统一起来,变原来外在于研究自由的社会责任为科学家的一种内在自觉。“为求知而研究”的全部精神底蕴在于求真。在科学技术推动着社会变化的步伐和发展方向的现时代,科学家对真理的追求不能只是满足于在自己狭隘的专业领域里求索:完整意义上的求真不仅是对自然世界的无穷奥秘的探索,同时还包括了对社会的合理性以及人生意义的不懈追求。(参见同上,2003年,第23页)责任自由否定了过去那种脱离现实的极其狭隘的利己主义的专业追求,惟其如此,才能为人类进步事业和社会发展而创新,才能成为社会良知和人类价值的维护者,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第二,责任自由是无待自由和“有待”的职任自由的统一。无待自由强调“为自由而科学”,漠视科学的社会责任;职任自由强调科学的功利价值,排斥科学研究的自由,把社会责任变成了约束人们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的外在力量。因此,尽管二者的自由取向相反,但都将研究自由与社会责任二者对立起来。责任自由则是对无待自由和职任自由的扬弃。作为国家目标下的科学家个人自由形态,它一方面抛弃了无待自由脱离社会的消极因素,批判地继承了它的“为求知而研究”的合理内核,将科学求真与国家的现实需要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又批判地汲取了职任自由强调社会责任的积极成分,变原来由外部设定的、被动的社会责任为科学家个人的自觉意识。
由此可见,责任自由将求真责任与社会责任内在地统一起来,实现了无待自由和职任自由的辩证结合,在社会责任的基础上完成内在自由和外在自由的统一。这样,科学家个人自由从无待自由演变到职任自由,再演变到责任自由,中间经过两次否定,构成一个完整的否定之否定过程,最终实现了内在自由和外在自由的高度统一,从而把科学家个人自由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和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