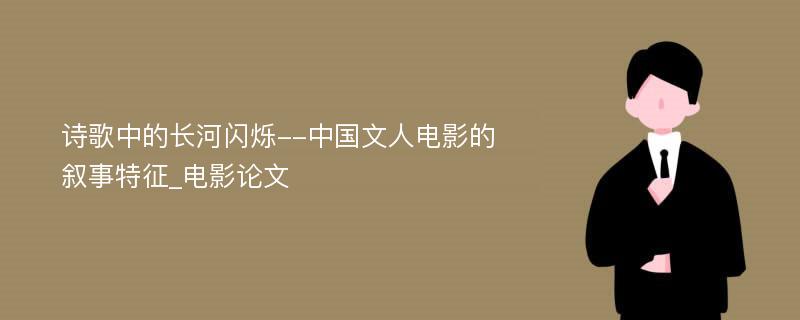
闪烁在诗意的长河——中国文人电影的叙事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河论文,文人论文,诗意论文,中国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中期,陈犀禾先生对20年代一本被时间湮灭与遗忘的电影著作——《影戏剧作 法》给予了崭新研究视角的切入,提出了“影戏”是中国电影美学的核心概念,以此富 于开拓性与启示性地论证了中国自己的电影美学理论体系——影戏观。[1]同一时期, 钟大丰先生以更为丰富翔实的资料进一步展开了“影戏”理论历史溯源的研究,并于90 年代中期,以“再论‘影戏’”探讨了中国电影的历史及其根源。[2]应该说,“影戏 ”理论的提出与逐步完善,为我们开凿了认识中国电影理论与中国电影创作的重要通道 ,为我们认清中国电影叙事肌理及其表征提供了可供参考的重要维度与视角。
但笼统以“影戏”概括整体中国电影美学观,显然不够全面。实际上,在“影戏”— —这一重要且强势的轨迹之外,中国电影一直有着另一重要的创作传统,并形成了特定 的风格,这就是与“影戏”相对应的——“影诗”美学体系。
一、史传传统——影戏——戏人电影
世界电影诞生于1895年。当年,在巴黎的一家地下咖啡馆,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工 厂大门》、《水浇园丁》、《火车进站》等原始纪录片。银幕上活动起来的黑白光影比 起游乐场中投进几角硬币就可观看的“窥镜”,更加逼真地映现出各种事物。在黑黢黢 的地下室里,市民阶层带着巨大的刺激与惊异,获得了超过游乐场所有娱乐项目的愉悦 与满足。这就是电影的诞生——放给市民阶层看的、带着游戏杂耍性质,暂时没有人 会 妄想将她称作艺术。
几年之后,这个新鲜事物就飘洋过海来到了中国。一些外国文化商人开始在北京的市 井繁华地段放映这些原始纪录片,同样的惊异反映同样发生在翘首引颈看“新鲜罕儿” 的中国人身上。守旧者将其称为“西人搜集人眼精华之法”,而更多的市民把这样舶来 品称为“西洋影戏”。
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庆泰主持拍摄了中国自己的第一部影片——谭鑫培 主演的京剧《定军山》。西洋影戏与民族文化精粹的结合,极大调动与符合了市民阶层 的欣赏趣味,一时间万人空巷、观之如潮。这一现象同时也表明了一个事实:中国电影 自诞生开始,就是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的,并在影片的选材与经营中,注重 了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即,它的拍摄不是用以实验探索影像,也不是纪录原初状态的 现实生活,而是纪录了市民阶层所喜欢的某种艺术形式,表现出了清醒的观众立场与经 营理性。
一场不明起因的大火使丰泰照相馆日趋败落,也使得影戏的拍摄由北京转向了近代经 济和文化的中心——上海。对于中国民族电影来说,丰泰的落幕其实只是序幕的完结, 当电影作为一种崭新的“叙事媒介”登上上海的都市舞台,并逐渐走上前景时,辉煌灿 烂的民族电影才开始真正闪耀出熠熠的光彩。
上海是一个市民阶层比较集中的繁华都市,民族制片在上海获得重新起步有着得天独 厚的经济基础、文化精神气候和比较广泛的观众层。当胶片不仅仅作为一种“纪录媒介 ”,而开始作为一种“叙事媒介”,即开始用以虚构与讲述“故事”时,中国市民阶层 对于叙事作品的审美心理定势和欣赏口味,就成为了影片创作人员的首要考虑。
陈平原先生曾以“史传传统”,即作为历史散文总称的“史传”与“诗骚传统”,即 《诗经》、《离骚》所开创的抒情诗传统,来概括中国两大强劲的文化传统与美学品格 [3]。前者集中着《春秋》、《国语》、《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 、宋代话本小说、明清章回小说、戏曲及各种民间说唱文艺形式,后者则有《诗经》、 楚辞、汉赋、乐府诗歌、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等。不难发现,史传传统长于叙 事,注重再现,而诗骚传统长于抒情,注重表现。史传传统中许多叙事观念与技巧都与 民间智慧及其人生观、价值观相结合,粗俗却又清新,与市民阶层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 系;而诗骚传统注重表现、注重主观抒情言志,与文人阶层的文化精神、心灵情感息息 相通,成为文人文化的载体。
本世纪初,电影这个刚刚扎下根来的文化舶来品,面对的就是中国市民阶层受到长期 熏染、几已浸入骨髓的叙事审美定势,即史传传统影响下的叙事法则。具体特征表现在 :对叙事作品注重情节,故事要一波三折、峰回路转、引人入胜,表现出对戏剧性情节 的迷醉;故事的讲述要有头有尾、明白晓畅,一般是顺时性讲述,很少倒叙、插叙,便 于文化层次不高的大众百姓的理解与接受;喜欢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看到人物鲜明的性 格特征,讲究善善恶恶的人物塑造,人物性格善恶分明、棱角突出;讲求文以载道,道 德教化自然流布于故事之中,故事的讲述要有一定的社会功能目的。这也就是说,电影 ——这个崭新的叙事媒介,面对的是中国丰厚强大的史传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叙事的积淀 与陈酿。
中国民族电影的创始人,从创作伊始就敏锐地捕捉到了以上市民审美心理及欣赏趣味 的存在,并自觉地实践着一条注重故事情节、注重写实与再现现实生活的创作道路。张 石川曾说:“有人问我,我的电影为什么好看,无他,剧情见胜耳。”郑正秋则认为“ 先决的问题还在有没有好的情节,要是想出好情节,不论什么顾虑都是杞人忧天;要是 想不出好情节,那什么好处都是镜花水月”。牢牢抓住故事/情节——这一市民趣味与 审美心理的核心,才能牢牢抓住观众。因而,当市民阶层亲切而轻松地说“看影戏去” 时,观众审美的心理被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欣赏与创作的默契也已经潜移默化地被 建立起来——看影戏,不是看文明戏,不是看京戏,虽然艺术表现的媒介形式不一样了 ,但其欣赏与观看的核心实质是不变的——看的还是“戏”、是“故事”。
以上可以说是早期中国电影一开始就以“影戏”的创作手法作为创作主流的民族文化 审美原因。再有,是“历史性”的选择。本世纪初,在好莱坞电影大行其道、占据市场 绝大多数份额的空间中,稚嫩的中国民族电影要想在夹缝中保本、赢利、生存、发展, 迎面撞来的“商业性”特征使得中国电影艺术道路的选择,一开始就不得不把自己抛入 了市场运行的高速列车。在这样的情形下,电影人几乎无暇顾及个人艺术才情在胶片上 的求新探索与自由挥洒,如果有,也是将焦点对准观众与市场的需要的。
因而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国第一部故事短片《难夫难妻》(1913)到后来的《脚踏车闯 祸》、《一夜不安》、《店伙失票》等,再到短故事片创作经验的集大成之作《劳工之 爱情》(也叫《掷果缘》,1922),这些早期默片的创作所反映的多是市民阶层的现实生 活,市井里弄、家常里短,但叙事上大量运用偶然性、巧合性,充满了妙趣横生的情节 ,令人忍俊不禁。镜语表现上,虽然舞台化痕迹比较重,但在调度、景别、取景、剪辑 等方面也显示出了一定的灵活性与想象力。这些影片多在对社会不良现象及世俗偏见的 揶揄嘲讽中,表现了小人物的辛酸与悲欢,它们不承载深刻的思想内涵,镜语风格拙朴 ,以完满清晰地讲述一个故事为主要目的。应该看到,早期电影人在创作中,比较现实 地实践与体现了“影戏论”的本末观,即,“影戏是戏剧中之一种”,“戏”是影片之 根本,“影”是完成“戏”的手段[4]。
到了1923年,郑正秋在积累了大量文明戏及电影创作经验后,提出“电影不单是娱乐 ,电影应当有教育意义”,“应该在营业主义上加一点良心的主张”。这样,他编导了 影片《孤儿救祖记》。这是中国第一部在商业和艺术上同时获得成功的影片。据当时的 报道:“未二日,声誉便传遍海上,莫不一睹为快,”“营业之盛,首屈一指,舆论之 佳,亦一时无两。”这部影片在一个曲折动人的、家庭悲欢离合的故事之外,传达了清 晰的道德伦理观,有着中华民族深切体认的伦理情感与价值判断。女主人公坚韧、忠贞 、孝敬、善良的品格,继承了中国史传传统叙事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正面塑造,符合了 大多数中国观众对女性形象的理解,因而,赢得了观众的无限同情与认同。影片的悲剧 演绎、人物的悲情命运及影片最终的惩恶扬善、大团圆结局,都极大地符合与满足了观 众的欣赏审美心理。同时,这部影片的出现也标志着一种受到中国观众真诚欢迎的民族 电影叙事方法的确立,并在其后的几十年中百试不爽、发扬光大。这就是:
社会良心(影片的功能目的)+悲剧性或传奇性剧情及人物命运(通常以家庭为背景依托) +牺牲奉献坚韧的女性形象+几年至几十年的故事发生时间跨度=中国电影影戏叙事基本 构成法以这样的方法拍摄的影片,在《孤儿救祖记》之后,重要代表作有:《姊妹花 》(1931)、《渔光曲》(1934)、《一江春水向东流》(1945)、《八千里路云和月》(194 7)、《红色娘子军》(1960)、《天云山传奇》(1980)、《芙蓉镇》(1986)、《活着》(1 994)、《益西卓玛》(1999)、《生死抉择》(2000)、《英雄无语》(2001)等。
这一方法几乎纵跨中国电影创作的百年,独领风骚,形成了一条绵延不绝、奇峰叠现 的创作昆仑。这些作品与时代背景、现实生存状态紧密结合,其中曲折的故事、人物的 悲欢离合往往包涵着“家/国同构”关系,见微知著、深刻而锐利地折射出时代与社会 的风云变迁。
也就是说,对应于中国的影戏观,这些影片从外层来看是一个带有浓厚戏剧化色彩的 技巧理论体系,深层则是包含着一种从功能目的论出发的电影叙事法,随着实践的成熟 与完善,逐渐发展为一种有明确的社会政治功能目的,以对叙事内容的戏剧性要求为核 心,以叙事蒙太奇为主要特征的理论体系[5]。与这一理论体系相对应,及符合上述概 括的影戏叙事基本构成法的影片,一般就被称作为“戏人电影”[6]。
二、诗骚传统——影诗——文人电影
在中国民族电影创作的沃野上,除开激流奔涌着的、影戏创作美学观影响下的“戏人 电影”之外,我们可以发现,若隐若现地闪烁着一条涓涓的细流,她别具韵味、生生不 息,蕴涵着浓浓的深情,散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这些影片的叙事方法明显区别于“影戏”,其镜语独特,表现人物情感层次丰富、细 腻,抒情意味浓郁。
30年代文人画家但杜宇创建的“上海影业公司”的出品,可以视作这一美学风格影片 的滥觞。当时就有敏锐的影评家指出了上海影业公司影片的与众不同——“虽然不能像 人家一般地风行,但艺术价值实在是高人一等”。接下来,又有吴永刚、费穆等人拍出 《大路》、《神女》、《浪淘沙》、《天伦》等作品,其意蕴悠远、从容淡定的叙事风 格与清新别致的美学气质,令影坛为之侧目。到40年代,费穆拍出了《小城之春》,今 天看来,这部影片是一座令人仰慕不已的高峰。当80年代初,这部影片被当作“文物” 重新发掘出来时,拂去时光的烟尘,其璀灿的艺术品格震惊了无数中外影人,被公认为 是中国民族电影经典中的经典,其魅力启迪与影响了包括第五代导演在内的许多中国电 影创作者,成为民族电影汲取创作灵感与认识中国民族电影美学理论的又一源泉[7]。 至50年代又有影片《林家铺子》,60年代有《早春二月》,以及80年代的《城南旧事》 、《乡音》、《青春祭》、《黄土地》,90年代的《心香》、《我的父亲母亲》、《那 山、那人、那狗》等。这些影片都一脉相承地保持了一种有别于影戏的、民族电影特有 的美学意蕴,这条线索就构成了中国文人电影的经典。对比影戏美学观,我们可以发现 ,影戏观强调再现,注重文以载道的社会功用,力求以故事和情节动人,影片叙事继承 的是文学性的叙事手段和技巧,所以有“戏”是影片之根本,“影”是完成“戏”的手 段的本末观。因而,影片在引人入胜的、含有了商业性因素的故事外套之下,包裹的是 社会意识强烈、载道色彩浓厚的核心。所以,受到史传传统文化影响的“戏人电影”更 多契合于大众文化与主导文化。
而之所以肯定地把上述涓涓细流的美学风格的影片冠之以“影诗”,或称作“文人电 影”,因为显而易见,这样的影片注重表现,注重抒情言志,影片不是以情节和故事动 人,而是以浓浓的情绪情感表现动人。在叙事风格上,它们有自己独特的特征,多以散 淡、简约的故事及人物关系,承载和传达浓郁内敛、回味悠长的心绪、情愫。影片在镜 语的运用上,更为丰富,也更加倚重镜语的表现力来传递精神及情感气质。影戏的本末 观造成对“影”的轻视,镜头多带有戏剧、舞台剧特征,多中近景,让观众看清人物对 白关系的镜头比较多,再就是大量运用缝合体系、让观众“入戏”的蒙太奇剪辑法,目 的是给出一个强化与合法化了的固定思维,让观众被动地接受[8]。而抒情意蕴的影片 镜语风格多以长镜头[9]和远景镜头为主,便于营造出某种风物氛围、令人难忘的某种 情调,渲染与凝聚某种情思状态。长镜头中时间的绵长往往让观众“出戏”,去产生自 己的思考与联想及调动自己的情感,并体味到情感的蕴积与升华。这里,镜语就体现出 从影像和镜头来把握电影风格及参与叙事的可能性。因而,“戏”不再是本,“影”也 不再是末,影片充分体现出诗骚传统影响下的文人文化的自觉意识和文化情趣——着重 抒发个人意识、传达主观情感,在严肃认真的社会责任感之外,传达出文人性的深沉哲 思与心绪感怀,并强调对个体情感的独特人性分析及人文关怀。因而,这样的影片诗意 诗化色彩强烈,文人士大夫话语特征浓厚,所以被称为“影诗”或“文人电影”。同时 ,这样的电影也具有了几分“作者电影”的气质,体现出了某种探索先锋与实验的特征 ,因而与精英文化密切相连。
但应该看到,文人电影这条线索的创作是被压抑与局限了的。由于前文所分析过的商 业性及民族文化性的特定规约,决定了电影在中国很难成为某个艺术家个性释放、情感 舒展的工具。但我们可以发现,只要在文化氛围适当、艺术创作土壤适合的环境中,就 会有导演出于文化本能的文人电影被创作出来。而这些默默滋生出的一朵朵文人电影的 奇葩,已经成为了中国电影创作的重要一脉,充分体现出了民族电影特有的美学品格。 下面,笔者将着重分析中国文人电影在叙事上的主要特征。
三、诗情叙事的中国文人电影
在进入具体的叙事特征分析之前,有必要就戏人电影与文人电影在叙事本质,或者说 在叙事基本构成上的区别再作一次强调与重申。即,戏人电影通常有一个完满自足的叙 事的因果链,依照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顺序,推进情节逻辑线索,并依靠 这环环相扣的故事情节吸引与打动观众,叙事的核心在于“情节”。文人电影叙事结构 总体较为松散,往往打乱、延缓或者根本不组织情节链,不注重“情节”的推衍,而着 重于“情感”的抒发、心境氛围的营造,是一种非情节化的叙事。古人云:“有所记叙 谓之文,吟咏情性谓之诗”,诗骚传统中,诗的本质就是抒情,文人电影的主旨就是要 像一首隽永的抒情诗一样,去抒发情志、吟咏情性与哲思,并依靠这些浓郁的情感抑或 淡淡的忧伤来抚动观众心湖的波澜,表现出文人气质的对周遭世界及人生际遇的某种感 性的审美体语。因而,文人电影的叙事特征散发着独特的叙事魅力。
(一)、重章复沓的抒情叙事
在文人电影中,常常会反复表现某个叙事链上的点(情节或场景),使流畅的故事叙述 就发生了停顿,造成了情节上的延宕与阻塞,此时,影片的情节、故事的直线流程铺展 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了,影片此时要展示与铺排的恰恰是超出情节流程之外的东西。持久 地在某个点上的徘徊、流连,以一种一步三叹式的旋律感,传达出反复吟哦的诗意的力 量。正如诗歌往往以逡巡、流连的重章复沓表现抒情效果一样,影片情节或场景的重复 也同样地表现出了情感与韵律的和谐,蕴积与升华出情绪、情感的魅力。
影片《我的父亲母亲》[10],整体叙事情节简约,却有着大量情节点上的重复:母亲 一次次在路边等父亲;一次次到井台边去打水;一次次在教室的窗外倾听……这样反复 流连、一步三沓式的场景情节的重复,“多次讲述一次发生的事情”,就使得被重复和 停顿的这个叙事点被“放大”与“化开”,这里反复渲染和累积起的就是一种情绪。影 片不急于按故事流程推进叙事,其实已经将下面用以叙事的时间搬挪过来,在这里进行 着折叠式的重复,目的是加深这种情绪情感的抒发。于是,这个点上的情感蕴积就越来 越浓,观众在这样的情节重复中渐渐体味到一种情感的深深雕刻,母亲对父亲淳朴真挚 的情感被浓郁地抒发出来,同时也真切地打动与感染着观众。
文人电影情节重复的魅力有时会被运用到极致。第五代导演的重要作品《黄土地》中 ,有反复表现翠巧去黄河边打水的场景:缓缓流淌的黄河水、一根扁担两只木桶、孤单 的少女的身影,在这些场景中,构图、景别、选取的景致,以至人物的动作都几乎完全 一致。陈凯歌曾说他“不太满足局限于某个人物具体命运的描写”,“翠巧是翠巧,翠 巧非翠巧,她是具体的,又是升华的,从她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民族的希望”。于是, 那远景中汤汤而去的黄河水,作为流水的意象,缠绵婉致又是最为恰当地表达了含蓄蕴 藉的情感,蕴涵了一种亘古不变、岁月悠悠的状态,同时,宽展、舒缓的流水意象又反 映并强化了华夏民族柔韧、沉稳的文化精神。翠巧伫立河边打水更是与这一精神诗意地 融合起来,在反复表现的场景中,她打水时的剪影、她在这里情感的抒发、心曲的吟唱 ,都使意蕴更加悠长。影片极致的重复,使得这一场景加深了郁郁而怅惘的抒情效果, 使影片获得了气韵连贯的诗意情感的渗透力量。文人电影情节场景上的重复正体现出影 片不满足于某个故事具体情节的描述或不局限于某个人物具体命运的描写的审美品格, 它以一种超乎情节之外的逡巡、复沓,表现了在叙事时间上的“滞泊”,从而以文人抒 情言志的视角真切传达出某种人生感、历史感,引人沉思、流连,为影片营造了诗情线 索与诗性结构。
(二)、叙事链条上刻意的“空白”
戏人电影首先是作为一种“叙事”的艺术,重情节故事性、强化剧情的戏剧性,因而 ,戏人电影的核心要素是要有一条结实的情节链,充满在时间向度,完整而有节奏地被 次第展开,这条链是严谨的,环环相扣的。
分析考察文人电影可以发现,影片常常会有刻意的叙事上的空白,坚决回避和省略掉 了戏人电影中常用的叙事“桥段”。《我的父亲母亲》的叙事就很典型。张艺谋删去了 诸如“井台边幽会”、“教室旁絮语”等对于戏人电影来说必不可少的情节,取的是“ 删繁就简”的情节效果。再比如动作——反动作体系(戏人电影中常见的二元对立关系) 设置也很虚弱,诸如“我姥姥”的反对、给“父亲”戴右派帽子等。这些本是构成戏剧 冲突、衍化情节矛盾必不可少的因素,却被有意地弱化或空掉了,留下一段段情节点上 的空白。影片的叙事就专心致志地围绕着“等”、“看”、“追”等几个叙事点来展开 抒情,纯净的情节线上,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母亲”透明的眼神、执著的身影、优美如 画的风景,诗意的情境表现使影片连成了一条抒情的河流。因而,影片在简单叙事情节 的框架中充盈起的是浓郁的情感,它的整体是建筑在抒情表意的心理基础上,而不是戏 剧型的情节基础上。
说到用叙事的空白来成就文人电影诗情风范的影片,不能不提到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 的《悲情城市》。这部影片讲述的是台湾一家人从1945——1949年的家庭变故,从而来 折射和反映时代变动的故事。本来,这样一个故事,很自然而然就能按戏人电影的叙事 套路来拍,而且,这样的故事内核与主题、立意,也很容易被拍成戏人电影。但侯孝贤 却把它拍成了文人电影,所运用的一个重要的叙事方法,就是打散戏剧性因果链,形成 情节上的片断,而片断内部或段落与段落之间是大量的叙事上的“空白”。
具体分析一下影片最后四场戏:
倒数第四场:文清(以照相为生的哑巴,男主人公)和宽美(女主人公)接到一封信,二 人看信后开始悲伤。镜头闪回:宽荣(宽美哥哥,政治激进分子,参与“二二八事件”) 被捕,生死不知。
倒数第三场:文清夫妇连同他们的小孩子在火车站台上。夫妻俩望着远去的列车久久 地伫立。
倒数第二场:文清调好自拍器,神情庄重地与妻儿合影。
最后一场:侄女阿雪看信后与文清年迈的老父、被黑社会打成白痴的文良、守寡的兄
嫂等老老少少一家人平静地端饭、吃饭。画外音传来宽美的声音:文清也被捉走,下落 不明。儿子已经开始长牙……
镜头最后定格于目睹了林家几十年沧桑的老屋厅堂。
这几场戏每一场都是一个片断或场景,每一场都单独给出一个信息。上下段落间叙事 是不连贯的,段落与段落中间被叙事的空白阻隔。对一般情节剧而言,这样的“空白地 带”,如果不加以省略,正是展开情节的铺陈、渲染,设置悬念,引发冲突高潮的关键 场所,也就是“有戏”的地方。比如倒数第四、三场之间,可以表现文清夫妇接信后, 如何商量逃走;倒数三、二场之间表现他们为何又决定不走了;而倒数一、二场之间可 以作为全剧的重点高潮场次,刻画文清被捕与妻儿之间的骨肉分离、生离死别,这是一 个煽情性的戏剧高潮段落。但是,影片却将这些情节全都隐去了,并且是在尽量回避着 情节高潮段落的展现。在沉郁、内敛的“侯式风格”的“定镜长拍”的镜头里,展现的 是带着鲜活的生活毛边感的平淡细节。这些细节按戏人电影的拍摄法,多会是中、近景 ,并且会很快地被切换掉,但侯孝贤却以一种悲悯的情怀与视角,以长时间的全景镜头 ,置远旁观,传达着超出镜头信息内容之外的冷静哲思,在这样的镜头里渐渐蕴积与被 体悟到的也是超出情节表述的情感意蕴。同时,刻意的情节空白,说明它不想让观众接 受到激烈的、情节上的矛盾与刺激,而是沉着大气地展现生离死别的巨大悲痛与急剧的 社会变动中,人物平静、澹泊的生活片断,让观众体悟到的是一种深沉的、饱含着压抑 却又顽强地生活着的悲情。
对一般叙事作品而言,“省略”越大,叙事速度就越快,即,省略对叙事会起到“提 速”的作用。但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文人电影中,叙事上的空白与省略带给我们的感 受,不是影片叙事上速度的加快,而是情感韵味的蕴积与召唤。因而,这种叙事上的空 白不是“真空”,而是具有了“空筐”的作用,是一个多层面、未完成的“召唤结构”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讲,观众是参与叙事的,在这个结构中,观众可以注入自己的联想 到“空白”里,从而将叙事的链条整合、接续起来,同时,也注入了自己的情感,使情 绪情感得以超脱于叙事局限之外,在银幕弥漫的人生感、历史感、人伦温情感中唤起心 灵的记忆与联想,使影片获得诗意的光辉。
因而,这里观众赋予影片的意义就“溢出”了影片本身银幕符号的框架,“空白”成 为了情感的升华与回味的必要“留白”。试想,如果故事的讲述陷入繁复的情节编织中 去,则会重落戏人电影的窠臼,影片就无法成就文人电影的气息与风范了。所以,叙事 上的空白正是文人电影诗情意蕴表达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
(三)、叙事上不构成戏剧性高潮段落
只要是以剧情见胜的影片,往往要形成戏剧性高潮段落。
在叙事推动情节发展的源动力上,比如好莱坞类型片叙事的推动常常依靠主人公在目 标明确、目的性鲜明的动作完成过程中,不断克服困难、克服一次次敌人的阻挠,以此 来形成明显的情节递进关系。中国戏人电影则主要依靠史传传统影响下的文学性叙事技 巧,其中,大量采用的是情节组织上的偶然性与传奇性。中国传统叙事技巧讲究“无巧 不成书”,“非奇不传”。偶然性和带有传奇色彩的段落,往往成为叙事的环扣,成为 推动情节一波三折的重要因素。在戏人电影的叙事构成上,开山鼻祖郑正秋拍默片时就 追求情节组织的奇和巧,后来,蔡楚生更是说“影片要不怕奇、不怕巧,只要合理、有 分寸”。中国戏人电影正是靠着偶然性、巧合性带动情节、并引发冲突的高潮,造成情 节上的起起伏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形成柳暗花明、峰回路转的故事魅力。
那么,类型片中英雄主人公一次次克服困难的行为的带动与推进,其结果,就是形成 动作情境下的情节高潮。特别是经典西部片、强盗片、动作片中,都会形成全片最为精 彩的、也是观众期待已久的,英雄与敌人最终决一雌雄的精彩打斗镜头,这是全片的压 轴大戏。这场决斗可以在荒野大漠、雪域高原,可以在无限的海洋、遥远的太空……可 以拔枪怒射、爆炸成一片火海,也可以拳脚相加、上天入地,穿梭于骏马、快艇、汽车 、飞机……总之,好莱坞的“重度能指”加上高“悦目度”的画面表现,酣畅淋漓地营 造出一幕幕最富惊险刺激的场景,充分展示着“视觉奇观”的银幕震撼力量。
与好莱坞电影形成的动作型高潮不同,中国戏人电影由偶然性、传奇性带动,各条线 索不断地在叙事中铺垫与系扣,最后推向的是一个具有巨大人伦情感张力的、矛盾纠结 爆发型的冲突高潮。这个高潮是人物情感、命运的归宿,也是人物情感抒发、宣泄的段 落,表现在戏人电影中,最典型的特征是以大段大段的台词来诉说、释放、渲染情感, 并引起观众强烈的心理认同与情感投射,形成经典煽情“苦情戏”段落,而“生离、死 别、重逢、落难”又往往成为苦情戏最基本的核心情境。因而,这个由偶然性、巧合性 、传奇性形成的高潮段落往往裹挟着悲剧型的情感倾向。于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中 ,忠良母亲声泪俱下的控诉、素芬委屈的恸泣,引得“普天下同声一哭,似乎本片能使 受过八年苦难的人们得到宣泄”。谢晋电影苦戏手法更进一步,除了台词的力量,更调 动电影造型、蒙太奇技巧等进行全面的渲染与烘托。《天云山传奇》中的“风雪拉车” ,配之以抒情的歌声;伟大坚韧、牺牲奉献的冯晴兰死后,镜头缓缓拉开;咸菜、破棉 袄、呕心沥血的书稿、见证其苦乐年华的山路与水车……此处无声胜有声,更加情绪化 地调动和感染着观众。应该说,这种高潮段落的煽情手法,中国电影一直沿袭、借鉴至 今,成为一种最基本与模式化的创作手段。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注重情节与故事的好莱坞经典类型片与中国戏人电影,不论是 动作型,还是矛盾线索纠结爆发型,都会形成戏剧性的情节高潮段落,而文人电影与之 相比则没有明显的戏剧性高潮冲突段落。
文人电影在整体叙事平缓、散淡的构成形态下,形成的是两种情绪样态,第一种,我 把它称之为情感蕴积型。
这样的影片不展现大起大伏的戏剧性情节,没有情绪上跳跃性的大悲大喜。在整体叙 事上经常会有游离于主线之外的细节,与常规电影细节是为情节的铺垫不同,文人电影 中这些看似漫不经心的细节就像中国画中“皴”的笔法一样,一点点渲染出氛围、蕴积 起情感。因而,影片在情绪表达上充盈起水到渠成的氤氲之感,观众沉浸于这种情绪的 感染之中,往往是被影片情绪的熏染而动情,而不是为情节的发展而揪心。同时,文人 电影场景、段落间的转换也并不严格按照情节因果的必然性,而是依据情绪情感的潜流 ,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散点透视”的意味。这是一种用心灵的眼睛来体悟人生状态的 叙事,散发着幽兰般的馨香。
《小城之春》中,花草零乱的院落、雕花的窗棂、月光下朦胧的小道、主人公迷惘却 又执著的眼神,女主人公精心替换的衣饰、细微的手部动作、情思悠悠的内心独白…… 这些精致、细腻、繁复的细节,配合舒缓的长镜头,镂刻出内敛却又浓郁的情愫。
《城南旧事》中,小英子纯真的视点下,春天的指甲花、满地跑的小油鸡、送水骆驼 嚼着草、“我们看海去”的童谣、如泣如诉的《骊歌》……这些散漫于故事之外的片断 却成为印刻在观众心中最为清晰的画面,渲染出一个无邪的童年、几许成长的忧伤与多 少对往事的留恋与怀念。
《那山、那人、那狗》中,一段段平静而又从容的山路、一个个途中相逢的质朴乡人 ,幽静的山谷、洁白飞翔的折纸飞机、父子间无言而又默契的心灵的交流……一切都烘 托起温馨暖人的人间真爱与亲情。
这类影片自始至终波澜不惊的情节,传达出电影“作者”充满文人气质的对客观现实 生活细腻诗意的凝望,影片是他们精神沉湎与心灵体验的畛域,而要理解这样的影片更 是需要一把多么婉转的钥匙,才能打开这幽曲的通向心绪与理想的锁。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文人电影中大量优美抒情的画面与好莱坞及部分欧洲电影营建绚 丽而震慑人心的影像,呈现出“景观电影”的风格并不相同。后者是以画面来装饰传统 的情节,强调的是形式感和视觉冲击;而中国文人电影则是为了烘托情调与人物心绪, 是连贯的、一气呵成的情绪的绵延。比如《城南旧事》以沉沉的相思、淡淡的哀愁,宁 静而悠远地感染着观众,在最后一幕“爸爸的花儿也谢了,我的童年结束了”的离别感 伤中,观众看到的是香山满山的红叶六次化入化出,“一切景语皆情语”,明媚的视觉 冲击很快转化为深沉的情绪冲击,浓郁的情感力量既震撼人心又润物无声地烘托与强化 了情感。借景传情、立象尽意,叠化的红叶传达出了无尽的情思与哀痛。
再有,同样是偶然性、巧合性因素的运用,前文分析过,对于戏人电影来说,是为了 进入情节,推动叙事,形成因果关系,并最终推向高潮冲突段落。而文人电影中,偶然 性与巧合性带来的却是非戏剧化的不可知性,往往造成情节的延宕、人物情绪的不稳定 性,即,反而在减缓着叙事的速度,淡化着情节的色彩。在这里,偶然性和巧合性最终 成为了一种机缘、一种深入人物心理活动及影片情绪情感表达的因素。
最典型的还是《小城之春》。志诚偶然来访礼言,却得知礼言之妻竟是自己的初恋情 人玉纹,玉纹恰和礼言陷入情感危机之中,志诚的偶访激起她反反复复的情感波动。不 像戏人电影拿偶然性作文章,会立即进入叙事情境的线性封闭结构“秩序”,文人电影 偶然性因素的运用却通向了叙事焦点有些虚的开放性途径——进入的不是情节,而是人 物情感波动的心理历程的展示。
志诚到来的偶然性,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入戏”的契机。夏衍曾经说“入戏”就是立 即向观众提出问题,构成戏剧性的悬念。志诚的到来,打破了玉纹、礼言、戴秀(礼言 之妹)枯闷的生活,四人之间将会发生怎样的情感变动……然而影片却在引入偶然性因 素之后延宕了叙事,开始进入一种“无事之事”的描写。四个人先是上城墙闲逛,又一 起去划船,再划拳、行令、吃酒,这样的段落竟占去了影片的三分之一还要多。戏人电 影决不会如此拖延,它要紧紧抓住情节、层层递进,快速推动人物之间关系的发展。而 文人电影则以一种重重叠叠的静态描写,不温不火地传达着暧昧的心绪及眉目传情之意 。特别是“划船”一场,“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那温婉的流水、轻柔的划桨、 抒情的歌声,正是玉纹内心情感的恰当写照。因而,不急于叙事的“娓娓道来”的大段 篇幅,就跳出了情节包围的窠臼,此时,人物的行动及目的变得“无时限”了。而注重 情节的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经典叙事,主人公最后行为的完成一定要遵守一个严格的时 间限制,这是自格里菲斯《党同伐异》“最后三分钟营救”所开创的最经典的叙事法则 。“有时限”使得戏剧性冲突高潮到达悬念与惊险的极至,可以完全深入地控制观众对 于情节的迷醉,深陷于故事叙述本身所给予的梦幻之中。此刻,观众来不及跳出情节与 梦境去作独立思考或分析感悟人物的情感心理。而文人电影中,主人公的行为目的变得 无时限,而且很散漫,没有了戏剧性冲突的高潮,而且这也不重要了。于是,重要的就 是情感的展示,是在这个“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故事之外,让观众更多体味到时代环 境变动中,人物渺小、无奈、苦闷、彷徨的心绪,在叙事的滞缓、胶着中,细腻而有层 次地展示着人物的心理与情感的蕴积。
第二种情绪样态可以称之为隐喻型。
文人电影中,本应是戏剧性高潮或苦戏煽情段落,却被代之以具有了隐喻性的象征表 现段落。这种段落与前一种情感蕴积型的不同在于,观众可以感受到情绪上起伏,不像 前一种全篇情感基调均匀、气韵流贯,而是具有了一种情绪上的起伏跳跃感。但情绪的 波动不是影片情节所给予的矛盾高潮冲突,而是隐喻象征的力度所给予的精神情绪上的 震动与感染。
《黄土地》中的腰鼓段落更为典型。电影学院的鲍萧然老师曾真切地谈到他看了“腰 鼓”一场戏后的感受:“看前边,一直很压抑、沉闷,气也上不来,就像梦里被人捆住 了手脚。当腰鼓队猛地打起来时,仿佛一下子从梦中惊醒了,心,跳呀跳的”——这种 情绪感受正是影片所期望的欣赏效果。在这样的段落中,激越昂扬的、有生命感、迸发 感的腰鼓,正是隐喻与传达着对民族或文化来说,一种求精神、求宣泄的渴望;一种对 于活泼泼的生命状态的肯定;一种生命长期缓慢与压抑不变中求挣扎的希寄。
再有像《孩子王》中烧荒的段落,隐喻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忧虑与反思;《青春 祭》中的泥石流段落,隐喻了对青春的埋葬……
这些段落都以比较贴切的隐喻掀起了观众强烈的情感波澜,形成了全片情绪上的高潮 。但我们可以明确,这不是戏剧性的冲突高潮。
也就是说,隐喻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联想,在电影里,如果蒙太奇仅仅作为一种剪辑手 段,不断开发情节组合与速度间的关系,完满而封闭地完成情节组合链上的叙事,这就 是常规电影。而如果选择、利用蒙太奇是来进行诗情、诗意的意象开掘,那么这样的电 影往往通过隐喻来揭示主题,影像含义是丰富的,带给观众的情感与联想也是丰富的, 这样的影片就是非常规电影,这里站着爱森斯坦、塔尔柯夫斯基、帕索里尼、费里尼、 基耶斯洛夫斯基、小津安二郎、费穆……中国文人电影中,富有哲思意味的隐喻段落及 蒙太奇镜头的运用,正体现了文人电影的诗情意蕴及向诗意表现维度的开掘。
(四)、往往通过描画人物的精神状态参与和推动叙事
戏人电影是通过叙事与情节去展现人物命运、刻画人物性格。而文人电影常常反过来 ,以人物的情绪状态、心绪心理去推导、衍化情节。
在文人电影中,人物心理活动的展现往往大于单纯行为目的的活动,曲折的心理历程 会得到寻根究底的表现。人物通常会有情感的困惑,有一系列细腻的内心心理剖析。主 人公呈现出比较强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会和全片的叙事交织在一起。即,叙事的进行 是由人物某种意识的澄清、紊乱、更改来推动与支配。同时,体现在叙事手法中,就是 第一人称旁边白或第一人称视点的运用比较多,呈现出某种“银幕意识流”的韵味。
于是,文人电影也形成了一套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法”:诸如饱含情感寄托的 景致、似有似无的微笑、漫无目的的行走、含情脉脉的窥视、引人相思的小道具、意蕴 深藏的凝思……与好莱坞经典叙事中主人公克服困难、不畏艰险,戏人电影中主人公性 格鲜明、善善恶恶不同,文人电影中主人公的行为与性格往往不是单纯明朗的,他们心 事重重、焦虑彷徨、亦喜亦悲、亦嗔亦怒,充满了不确定性与丰富性。同时,人物又往 往有某种“固置”的心理状态及一系列的“症侯”表现。如果泛泛地用社会学人物性格 分析法往往不能透彻理解人物的情感心绪,现代电影理论通常会借用精神分析法来“读 解”人物,为人物心灵的隐秘洞开一个窗口,并揭示出性格底层的“情结”根源。
结语
如果说,戏人电影更多是通过戏剧性的矛盾冲突来展现社会生活,民众、乡土在影片 中更多以现实主义的方式被加以刻画;那么,文人电影就不是现实生活状貌的再现,社 会与人生是被文人情怀所体悟与想像过的,被心灵的眼睛所笼罩的、是随着情感的迁移 而显现着不同的情绪样态与生活情态——汤汤的流水、郁郁的情思、从容的远镜——带 着一定距离的、悲悯的审视,使影片情绪与情感的韵味远远大于情节的曲折。于是,有 那云絮状温馨的情感蕴积,而不是穿线般联缀流畅的故事;于是,有了一幅幅诗意的风 情画、一段段寄托理想、感悟抒怀的生活片断。
中国文人电影以其自身风韵独具的品格充分体现了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审美情趣与理 想情怀,为摇曳多姿的世界电影之林增添了奇异的光彩。同时,中国文人电影作为中国 精英文化的一部分,体现了特定的情感、哲理,与类型电影及戏人电影起着互相补充与 借鉴的作用,并培养和提升着观众的欣赏审美能力,是民族电影值得挖掘与研究的宝藏 。
当然,客观历史地看,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中国电影的社会功利目的, 常常会形成潜在强大的“场”,来吸纳与纠正创作的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 后,更有“看不见的手”来拨动与调配着文化市场的晴雨冷热。近些年来,中国文人电 影拍得比较少,只有《心香》、《我的父亲母亲》、《那山、那人、那狗》等不多的几 部。这与主导文化的强势、大众文化的冲击有一定关系。虽然,精英文化的探索精神与 启蒙精神已被挤向边缘,但应该承认,文化的多元化特征及不同文化间的包容与渗透正 越来越多地被体现出来,即“多足鼎立”、相互制衡的局面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因而, 中国文人电影必将以自身的文化品格占领一席之地、并将得到进一步的突破与发展。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主要探讨了中国“戏人电影”与“文人电影”,实际上, 戏人电影是“剧电影”、也是常规电影的一部分;文人电影是“诗电影”、也是非常规 电影的一部分。用戏人电影与文人电影的划分远远无法全面涵盖与总结中国电影创作与 美学的全部特征。但是,它们作为两支最重要体系脉络,无疑是中国民族电影的经典。 在世界电影创作风格不断分蘖、叙事越来越纷繁诡谲的状况下,如何保持并弘扬民族电 影叙事的精华、保护和发展中国本民族的电影产业,对民族电影创作轨迹与品格风范的 研究无疑是必要与必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