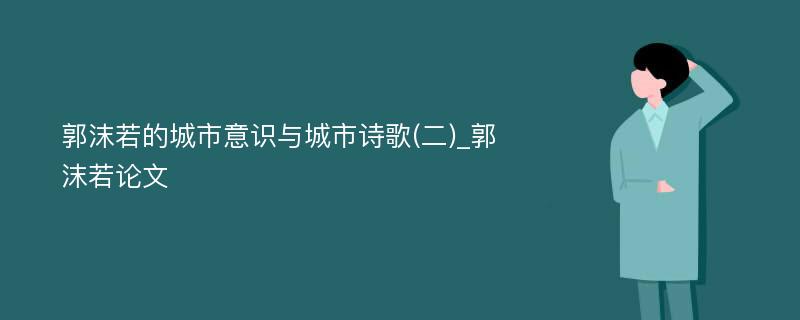
论郭沫若的城市意识与城市诗(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城市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019(2002)03-0024-06
郭沫若的反抗城市的城市诗
诅咒与批判城市的畸形发展造成的污秽、丑陋、罪恶以及由物质文明高度发展而产生 的人的精神异化,始终是与城市诗产生相伴随的现象。19世纪后半叶,波特莱尔的一些 关于巴黎各种丑恶现象的书写,已经显示了都会诗探索“以丑为美”思想的光辉。惠特 曼的《草叶集》里,对于工业进步,自由,健康等大声歌颂,唱着“繁荣吧,城市—— 带着你们和货物,带着你们的产品,广大而富裕的河流”(《横过布鲁克林渡口》)这样 乐观歌声的同时,也对于城市发展所隐藏的“一切无穷无尽的卑劣行为和痛苦”(《我 坐而眺望》),对于“隐藏”在城市繁荣背后的更深层次的人的精神异化现象,开始了 批判性的思考:
我已看穿了你也不比别人好,/从人们的欢笑,跳舞,飨宴,饮啜,/从衣服和装饰的 里面,从洗洁了的,修整了的面容里,/可以看出一种暗藏的,默默的厌恶和失望。/丈 夫,妻子和朋友之间,对各自内心的一切彼此讳莫如深,/另一个自我,每个人的副本 ,总在闪闪躲躲隐隐藏藏,/无形,无声,通过了城市里的街道,在客厅里殷勤而有礼 ,/在铁道上的火车里,在餐桌上,在寝室中,在无论何处,/穿着盛装,面带笑容,相 貌端庄,在胸膛下面隐藏着死,在头骨里面隐藏着灭亡,……——《大路之歌》
到了卡尔·桑德堡的城市诗里,对于城市的赞美与诅咒,已经构成了一种交织在一起 的高亢声音,如在《芝加哥》一诗里,“他咏支加哥是‘世界的宰猪场’,是‘邪恶’ 的,‘不正’的,‘野蛮’的都市”;“在《嘉莱的市长》诗中,用了强烈的对比法, 写出了资产阶级的官吏怎样苛求于他们的劳工”。[16]这些诗里充满了“直觉地感到的 他的怒恨的申斥与痛快的咒骂”[2]。《芝加哥》一诗里这样写道:
世界的宰猪场/器具制造所,小麦的堆积地/纵横之铁道的玩弄者与国家的运输所:/骚 乱的,嘎声的,喧嚣的,逞卖膂力的都市:/他们告诉我,你是邪恶的都市,我相信他 们,因为我曾看见你底涂脂抹粉的女人在瓦斯灯下勾引田舍间出来的少年。/他们又告 诉我你是不正的都市,我回说,是的,我曾真实地看见强盗杀人,自由地逃走了,再去 杀人。/他们又告诉我你是野蛮的都市,我底回答是:在妇人与孩子底脸上我曾看见了 饥馑的颜色。/这样回答了之后,我又向那些嘲笑我这都市的人们,我也报之以嘲笑, 对他们说:来,给我看看那昂然奏着凯歌,骄矜着有生气的,粗野的,强健的,狡狯的 别的都市。/在堆叠职业的劳作中间投放着强烈的咒诅,这里是一个高大的重击手与那 些柔和的小城市作着鲜明的对照;/凶猛得像一条舔着舌头预备开始战斗的狗,狡狯得 像一个与荒原搏斗的蛮人,……/——施蛰存译,载《现代》第3卷第1期
许多这样的创作现象说明,反抗与诅咒城市的罪恶,以批判的视角描写城市,观照城 市,已经成为世界城市诗发展潮流所形成的艺术传统中一个重要侧面。郭沫若归国后生 活的现实处境的转变,使得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了由赞美物质文明到诅咒物质文明, 由歌颂城市到批判城市的转变。他这方面的实绩开辟了新诗创作中反抗城市的城市诗的 艺术传统。
1921年4月,郭沫若从日本短暂回国。为倡导文学和完成医学学业,后来,他又多次往 来于福冈与上海之间。在他的感觉中,那种初归国时渴望看见祖国“向着太阳飞跑”般 “新生”的欢快,短暂地消失了。中国都会现实生活带来的幻灭与失望,驱动郭沫若城 市诗创造的一个走向:诅咒城市。他所乘海舟上的烟囱,已经不再是20世纪“名花”的 “黑色的牡丹”,而变成了“黑汹汹的煤烟/恶魔一样”(《海舟中望日出》)。他眼中 的大上海,并非呼唤中的“和平之乡哟!我的父母之邦!”(《黄浦江口》)他感到的是一 片“幻灭”:“我从梦中惊醒了!/Disllusion的悲哀哟!//游闲的尸,/浮嚣的肉,/长 的男袍,/短的女袖,/满目都是骷髅,/满街都是灵柩,/乱闯,/乱走。/我的眼儿流泪 ,/我的心儿作呕。/我从梦中惊醒了。/Disillusion的悲哀哟!”(《上海印象》)他在 火车上所看到的,只是一群同胞麻木的景象:“哦!我怪可怜的同胞们哟!/你们有的只 拼命赌钱,/有的只拼命吸烟,/有的连倾啤酒几杯,/有的连翻番菜几盘,/有的只顾酣 笑,/有的只顾乱谈。……啊!我的眼睛痛呀!痛呀!/要被百度以上的泪泉涨破了!”(《 西湖纪游·沪杭车中》)看到都会生活现实的景象,飞奔火车中的人群,一个充满美丽 憧憬归来的海外游子,唱出了发自内心深处的愤怒诅咒与“幻灭的悲哀”。面对大都会 的“血海”,他甚至发出了“世界末日”到来的愤激。
一道长堤/隔就了两个世界。/堤内是中世纪的风光,/堤外是未来派的血海。/可怕的 血海,/混沌的血海,/白骨翻澜的血海,/鬼哭神号的血海,/惨黄的太阳照临着在。/ 这是世界末日的光景,/大陆,陆沉了吗!/——《吴淞堤上》
“血海”是一个城市诗人心境幻化的“图景”。浸透主观爱憎情绪的这幅“图景”和 诗末发出的愤怒质疑,在并非具体物质文明而是情绪化的感觉景象描写中,为反抗城市 的城市诗由物境化到心境化批判的探索,尝试了一种新的创造的可能性。
都市现实引起的失望,是郭沫若产生反城市诗一个方面的原因;另一个方面的原因, 是他对城市生活各个方面黑暗丑恶的具体感受和认识。这样的认识与实感,使得郭沫若 收入《前茅》中写于1922年至1923年的几首城市诗,《恢复》中的一些诗作,浸透了更 为实在的城市处境与“革命情绪”。这里有一个情感与理智的转变。传统的自然赞美转 为现代的城市礼赞,是诗歌现代意识的一种进步,但当面对城市文化所给予的负面刺激 的时候,自然本身又承担着反抗者的皈依与再度反叛的双重角色。郭沫若有时以返归“ 自然”美的追求反抗城市,说“我本是“自然”的儿,/我要向我母怀中飞去!”(《西 湖纪游·沪杭车中》)说“污浊的上海市头,/干净的存在/只有那青青的天海!//污浊了 的我的灵魂!/你看那天海中的银涛,/流逝得那么愉快!”(《仰望》)有时又努力摆脱自 然美的沉醉,进入关注下层社会艰难的人生与世间苦:“你厚颜无耻的自然哟,/你只 是在谄媚富豪!/我从前对于你的赞美,/我如今要一笔勾消”(《歌笑在富儿们的园里》 );“矛盾万端的自然,/我如今不再迷恋你的冷脸。/人世间的难疗的怆恼,/将为我今 日后酿酒的葡萄”(《怆恼的葡萄》);“我的眼中已经没有自然,/我老早就感觉着我 的变迁”(《对月》)。前一种情感是以自然美否定城市,后一种情感是以人间苦难否定 沉醉自然美的情绪。自然美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诗人对待自然美的情绪。这改变的实 质,是从放弃浪漫情怀而向关注现实社会苦难的清醒的转变。
《上海的清晨》就是这样的从“人间的怆恼”酿造出来的一首典型的反抗城市的城市 诗。在一个大都会的清晨,一个还不曾被汽油的毒味窒息的清晨,诗人赤脚蓬头地在大 街上行走,与纷乱赴工的男女工人们分外相亲。“坐汽车的富儿们在中道驱驰,/伸手 求食的乞儿们在路旁徙倚。”我们可以把伸着的手互相紧握,自然的道路可以任我们走 遍,而富儿们的汽车“只能在马路上盘旋”。诗由现实层面贫富对立的描写,转而引向 对城市人民命运的追问:
马路上,面的不是水门汀,/面的是劳苦人民的血汗与生命!/血惨惨的生命呀,血惨惨 的生命/在富儿们的汽车轮下……滚,滚,滚,……/兄弟们哟,我相信,/就在这静安 寺路的马路中央,/终会有剧烈的火山爆喷!
为了这“火山爆喷”期待的实现,郭沫若将目光投向城市底层的不幸者们。他写给城 市失业的友人,激励他们“不用悲哀”,要振作精神,“把这万恶的魔宫打坏!”(《励 失业友人》)他决意告别“低回的情趣”和“虚无的幻想”,要超越精神上的“纤巧” 和“否定”,“左手拿着《可兰经》,右手拿着剑刀一柄”,走向粗暴的力的抗争(《 力的追求者》)。他感到拥挤不堪的“上海市上的赁家”,都像怆聚在“囚牢”里一样 ,看不见树的青影,听不见鸟的叫声,大家过的都是“囚在惨毒的魔宫”里的“囚徒的 生涯”(《朋友们怆聚在囚牢里》)。他同情于印刷房里排字工人如“苍白的黑影蠕动” ,好像都是“中铅毒而死的未来的新鬼”,为自己的“不成其为诗的诗”的付排,表示 忏悔与请求“宽恕”(《黑魆魆的文字窟中》)。他期盼着黎明的到来,寄望 于“含着满腔的热诚要把万汇苏活”的太阳:“轰轰的龙车之音/已离黎明不远,/太阳 哟,我们的师哟,/我们在赤光中相见!”
郭沫若说:“我的歌要变换情调”,“我要保持着我的花瓣永远新鲜”(《述怀》)。 这些写在“火狱中的上海”的诅咒之歌,抗争之歌,和他写于大革命失败后的20年代末 期的《传闻》、《电车复了工》等诗篇,都根植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都市社会,反映 了诗人由现实生活激发的真实情感转变的轨迹。关于这种思想感情的转变,当时评论说 ,“《女神》以后的作者,对于物质文明,渐有鲜明的不满。这个我们在《女神》中还 找不出来。……到了《仰望》、《吴淞堤上》、《上海的清晨》、《励失业的友人》、 《朋友们怆聚在囚牢》里,直到十四期周报上的《诗二首》,才逐渐显露。记得沫若有 一次来信说,上海除了天的清洁,便是最令人可爱的儿童,在上海的也只有令人生厌, ——这是多么沉痛的话呀!这个可以说是作者‘对于畸形的物质文明之反抗’。”[19] “以先在赞美物质文明的他,现在是诅咒物质文明了。在《笔立山头展望》中,他感到 ‘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朵黑色的牡丹呀!’而在《海舟中望日出》诗中,他唱的却 是‘黑汹汹的煤烟,恶魔一样’了。”到《伯夷这样歌唱》里边,他“彻底地主张出了 ‘回到自然’”,“高揭起他的独善主义来。他号召说:
可怜无告的人们哟!快醒醒!/我在这自然之中,在这独善的大道之中,/高唱着人性的 凯旋之歌,表示欢迎!”[7]
这种转变给郭沫若提供了这样的艺术空间:从城市生活中吸取反抗城市文化的题材, 于情调的转换中保持艺术“花瓣永远新鲜”,将日常生活的抒情纳入反抗城市的城市诗 创造的轨道。郭沫若的实践为新诗在这方面的探索,展示了具有开放性的启示。
郭沫若城市诗审美观念的转变
城市生活带给新诗的,不仅是书写题材的扩大,更是审美感受的差异。与以自然为中 心的传统生活带给人们的感觉不同,以物化生活为中心的现代都会生活的杂沓、喧闹、 繁复、深层精神异化等,给予人们许多新的感觉,使诗人艺术创造的探索获得了许多城 市诗所拥有的新的审美特征。郭沫若的城市诗意识里,就包含了他这方面美学认识的自 觉。
郭沫若阐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的观点,即艺术的黄金时代和社会一 般的不相应,例如希腊艺术在现在的社会里绝对产生不出来,是因为产生希腊艺术的那 个希腊的神话世界,“那是希腊的自然和社会关系透过了希腊人的幻想所点染出的世界 ,和现代的自动机器、铁路、蒸汽机、电信等不能两立。社会发展的结果把对于自然界 的观感上,所有一切的神话的关系,神话化的关系都排除了,我们对于艺术家所要求的 是脱离神话的另一种空想,……譬如我们住在上海的中心——中国的所谓文坛现在是建 设在这儿的——或者更是睡在东亚酒楼或远东饭店的钢丝床上,你听见的只是汽车的咆 哮,或者是黄浦滩头的轮船拔锚,你能听出甚么河洲上的‘关关雎鸠’吗?有自鸣钟挂 在你的壁上,遇必要时你可以把闹钟放在你的床头,你和你的爱人可以安安稳稳的睡到 你所规定的时候,那里还会闹到‘女曰鸡鸣’的使你在半夜里起床?在避雷针之前那里 还会有丰隆?在有无线电和飞机的交通存在面前那里还会希望要‘前望舒使先驱,后飞 廉使奔属’?……所以整个的一部《国风》,整个的一部《楚辞》在现代是不能产生出 的”[20](P.109)。喧闹的上海是“中国所谓文坛”发展的重地,以这样地方生活为描 写对象的城市文学所产生的审美感觉,与以自然为中心的传统文学所具有的感觉,已经 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由以自然为中心,到以城市日常生活为中心,诗歌题材选择的背 后,隐藏着诗人审美观念由传统到郭沫若所说的“现代”的移动。郭沫若城市诗实践的 探索,反映了他这种审美感觉转变的观念。
郭沫若自觉地引入现代科学的观念、词语,来概括和描写现代的感觉与情绪,并在城 市日常平凡的事物中,努力发掘新的感觉,创造诗意的意象。眺望博多海滨的一片松林 ,给予他的是“高擎着他们的手儿沉默着在赞美天宇”这样新的感觉:“他们一枝枝的 手儿在空中战栗,/我的一枝枝的神经纤维在身中战栗。”(《夜步十里松原》)太宰府 迸放的梅花,激发他引吭高歌,唱出:“我要把我的声带唱破。”(《梅花树下醉歌》) 他用司汤达的名言“轮船要煤烧,我的脑筋中每天至少要三四立方的新思潮”,说读了 这句警策的名言,“便是我今天装进了脑的无烟煤了!”(《无烟煤》)都用的是现代科 学观念和词语。《女神》序诗里,谈到自己作品与读者共鸣的关系,这样说:“《女神 》哟!/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 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把他们的心弦拨动,/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 !”他向众多雄伟的自然景物和伟大的或富有创造精神的人物,都道一声“晨安”。提 到文艺复兴的画家达·芬奇的时候,他说:“啊啊!你在一个炸弹上飞行的D’annunzio 呀!”(《晨安》)这样大胆怪诞的想象所传达的感觉,是超越经验世界限度的,但又符 合他的浪漫情绪运转的轨道。他这样写春天在大自然的孕育中蓬勃发生:“远远一带海 水呈着雌虹般的彩色,/俄而带紫,俄而深蓝,俄而嫩绿。//暗影与明辉在黄色的草原 头交互浮动,/如像有探海灯转换着的一般。”(《春之胎动》)海水细腻的彩色的变幻 ,黄色的草原头明暗的交辉浮动,如探海灯光影的转换,这些对于自然景物的感觉,没 有现代人的眼光和经验,是无法获得和体味得的。
有时,日常生活中带有或粗俗或丑陋特性的事物,本来不可能进入诗的形象,郭沫若 的想象却逆世俗美学观念而行,将其引入诗中:
我这瘟颈子的头颅/好像那火葬场里的火炉;/我的灵魂呀,早已被你烧死了!/哦,你 是哪儿来的凉风?/你在这火葬场中/也吹出了一株——春草。
禁锢的头脑中生出一缕新意的感觉,他竟用“火葬场”这样城市“丑”性的意象传递 给读者!以城市“丑”的日常生活意象,传达独特的感觉,获得了一种具有美感的诗意 ,这种由波特莱尔创造的“以丑为美”的现代性诗学,因为要进入没有诗意的城市世俗 生活的层面,努力在没有诗意的物象中发现诗,需要有一种“穿透熟悉的表面向着未经 人到的底里去”的“敏锐的感觉”,以发现“未发现的诗”(朱自清语)。事实上,在这 些事物中,这种诗意美并不存在。在某种意义上看,与其说这是一种诗的美的发现,还 不如说是诗的美的被创造。郭沫若的诗就是以他独特的感觉和想象力,在城市枯燥、繁 复、机械、肮脏与丑恶的事物中,巧妙地组合和构造出一种富有诗意的境界来。事物的 机械性与丑恶性已经被忽略了。用火葬场与一株春草的组合来隐喻死寂灵魂中的新生, 以黑色的牡丹来形容大轮船烟囱上的黑烟,以摩托车前的明灯来形容日出时太阳的旭光 ,……这些现代经典性意象所带有的现代美的产生,根源于诗人诗歌的眼光与感觉由传 统向现代性的转变。这是一种“内在的科学精神”,“在他眼里机械已不是一些无生的 物具,是有意识有生机如同人神一样。机械底丑恶性已被忽略了;在幻象与感情的魔术 之下他已穿上美丽的衣裳了呢”。[8](P.114)
郭沫若根据自己的一次生活经历与艺术感觉的体验,曾经这样说:“在火车中观察自 然是个近代人底脑筋。”[11](P.124)我的理解,这里说的“近代人的脑筋”,就是现 代人的思维和感觉。这段话的具体内涵,也可以这样理解:即使是传统的自然和历史的 题材,如果用现代眼光和思维,也可以发现和写出一些现代性的东西来。例如,在一些 历史题材的作品里,郭沫若能在传统性的意象里,呼唤一种富有现代性的意识和情感。 被郭沫若称为“实际上就是‘夫子自道’”的《湘累》里的屈原,就这样慨叹道:“从 早起来,我的脑袋便成了一个灶头;我的眼耳口鼻就好像一些烟筒的出口,都在冒起烟 雾,飞起火星,我的耳孔里还烘烘地只听着火在叫;灶下挂着一个土瓶——我的心脏— —里面的血水沸腾着好像干了的一般,只进得我的土瓶不住地跳跳跳。”这样的一些感 觉,这里的一些比喻,显然都是属于现代人所有的。对于自然,也因感觉者的观念不同 ,呈现的意象的美感内涵就不尽一样。郭沫若在异国中的夕阳西下的景象是:“远远的 海天之交涌起蔷薇花色的紫霞,/中有黑雾如烟,仿佛是战争的图画。/太阳哟!你便是 颗热烈的榴弹哟!/我要看你‘自我’的爆裂,开出血红的花朵。”(《新阳关三叠》)这 样的感觉,想象,明显带着一个诗人的现代眼光与个性色彩。郭沫若留学期间,为投身 文学事业,初归上海,在由博多往门司的途中,满怀喜悦和兴奋的心情下写《新生》一 诗,里面所书写的,就更属于现代人眼光与感觉中的自然:
紫罗兰的,/圆锥。/乳白色的,/雾帏。/黄黄地,/青青地,/地球大大地,/呼吸着朝 气。/火车/高笑/向……向……/向……向……/向着黄……/向着黄……/向着黄金的太 阳/飞……飞……飞……/飞跑,/飞跑,/飞跑。/好!好!好!……
这首诗写于1921年4月1日,属于《归国吟》的首篇。诗人明显受了立体派诗的影响, 用特别短促与快速的节奏,将自己乘火车时瞬间的感觉和印象,与自己充满憧憬与乐观 的情绪,凝定在诗句中。它叫出了“郭君心里那种压不平的活动之欲”(闻一多语),为 诗人渴望祖国新生的急切欢快的心境,留下了形象的写照,也显示了一个城市诗人审美 观念变异的痕迹。这种以“近代人的脑筋”观察自然的诗,与他《女神》中其他一些歌 咏自然的诗相比较,可以说完成了由浪漫到现代,由传统诗到城市诗的审美意识的蜕变 。
这里所说的新的感觉,与郭沫若对未来派诗歌的接受有关。20年代初创作《女神》时 期和稍后,郭沫若接近未来派诗歌,对它的理论主张和诗歌探索,并没有表示赞许和肯 定。他甚至认为,未来派只是“彻底的自然主义”,是“没有精神的照相机、留音机、 极端的物质主义的畸形儿”,未来派的诗“我敢断言它没有长久的生命”。他说马利奈 蒂的《战争》一诗,除了在形式上做到了宣言里的追求,“它始终不是诗”。我的感觉 ,郭沫若所注重的,只是未来派的“求新”精神。“它的精神只消用一句话便可以表达 ,便是新的印象应该用新的表现”,“新的感觉要用新的表现”。[11](P.248-250)正 是这种追求新的感觉和新的表现形式的审美趣味,使郭沫若接近了未来派的诗。郭沫若 拥有一种在“不拒新”的时代里“吸收新思潮而不伤食”的精神品格。[14](P.77)他总 是“努力去寻找别人所不曾经验过的感觉,以作他的诗材”[21]。机械文明社会快节奏 的现实生活与未来派、立体派艺术的接受,在郭沫若心灵中的融合,使他对现代社会飞 动的速度,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和愉悦的共鸣。他在现代机械文明的生活中,努力去发现 ,去体验一种全新的诗的感觉,甚至在他投身大自然中的时候,也不会忘记去寻找和体 味各种新的感觉。他向宗白华叙述自己和田汉两人从博多往二日市、太宰府乘火车时的 感觉说:
我们现在正在火车当中呀!我们是要往太宰府去的。太宰府离此处还远,由博多驿车行 至二日市,可十英里。由二日市至太宰府尚有二英里的光景。今天天气甚好,火车在青 翠的田畴中急行,好像个勇猛忱毅的少年向着希望涨满的前途努力奋迈的一般。飞!飞! 一切青翠的生命灿烂的光波在我们眼前飞舞。飞!飞!飞!我的“自我”融化在这个磅礴 雄浑的Rhythm中去了!我同火车全体,大自然全体,完全合而为一了!我凭着车窗望着旋 回飞舞着的自然,听着车轮靬鞑的进行调,痛快!痛快!我念着立体派诗人Max Weber底 The Eye Moment(瞬间)一诗……。
郭沫若当时用英文读着美国立体派诗人麦克司·韦伯的这首《瞬间》诗,他说,“此 诗在火车中诵着才知道它的妙味。它是时间底纪录,动底律吕。”他当时就翻译了这首 未来派诗:
立体,立体,立体,立体,/高,低,高,更高,更高,/远,远在天际,天际,天际 ,远,/平面,平面,平面,/彩色,光辉,记号,汽笛声,钟声,哨声,彩色,/平面 ,平面,平面,/眼,眼,窗眼,眼,眼,/鼻孔,鼻孔,烟筒底鼻孔,/呼吸着在,燃 烧着在,吹喷着在,/叫喊着在,吹喷着在,呼吹着在,吹喷着在,/几百万底物相相重 叠,/几千万底物相相重叠。/眼中作如是观,实体底眼中作如实现,/黑达森江畔,/无 穷地流泻,无疆地奋涌,/涌,涌,涌,涌……
然后郭沫若说:“最后一句借河流自然音律表示全宇宙之无时无刻无昼无夜都在流徙 创化,最妙,最妙,不可译,不可译。飞!飞!飞!飞!我正在车中做着我的立体诗时,火 车在一个小车驿上停止了。车掌来检票,我把车票握在手中,同寿昌兄从窗眼中望出去 。我还念着飞!飞!……哦哈!车票从我手中飞去了!车已发,尚缓缓前进。我迫不及思索 ,便也从窗眼中飞了出去。”[11](P.121~124)
这段早已为大家很熟悉的材料,今天重读起来,似乎可以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考:它体 现了郭沫若自身孕育的诗歌审美现代性追求的特征。郭沫若很兴奋于这次新的体验和感 觉。他自己说:在火车中观察自然是“近代人底脑筋”,在火车中诵读《瞬间》这首诗 才能知道它的妙味。郭沫若无意中揭示了一个重要发现:除了火车这个机械文明的物质 因素带来的兴奋之外,在现代科学与机械文明提供给人的新的特定环境中,人的生命渴 望与追求,人与自然的融合,可以找到一种与往昔生活情绪与音律表现来说都是全新的 感觉与形式。立体派诗《瞬间》的诵读与翻译,在这里已经是郭沫若接受新的感觉与形 式的一个象征符号。几个月后在往门司火车上所写的《新生》,就是以立体派形式书写 自己新的感觉的一个尝试。
这种新的感觉与表现形式,是属于现代城市诗所特有的,也是只有“近代人”所特有 的。郭沫若介绍的未来派的“宣言”里说,“自从伟大的科学的发见出世以来,人的感 觉已完全更新,未来派的基础便建设在这上面。”[11](P.242)由重视情感的表现,到 重视感觉的发现,特别是重视新的感觉和经验的开掘,重视用“近代人的脑筋”对于新 的感觉与经验的发现与捕捉,这不仅仅是未来派、立体派,也是整个世界诗歌发展走向 现代性美学嬗变的趋势。郭沫若对于诗的新的感觉与经验的发掘和表现,正是这种美学 嬗变趋势的一种体现。他的《女神》及其他诗集里一些初期形态的城市诗的探索与实践 ,在诗歌美学上的突进,根本处就在这里。忽略了郭沫若城市诗这种新的感觉的发现, 也就看不到他诗歌中的美学转折与突进。朱湘说:“郭君虽然没有发现到什么新的感觉 ,但他在题材的搜求上,有一点与柯罗勒立相吻合,便是从超经验世界中寻求题材。” [21]这话的后半句是说对了的,但前半句就值得讨论了。他说,英国浪漫派诗人科罗律 治,“为要发现一些别人所向未经验过的感觉”,于是他就去吸鸦片烟,居然从中发现 了两种感觉:一种精神与躯壳解体的奇异感觉,一种灰心的感觉。[21]其实如前面所论 述的,郭沫若的城市诗,无论在日常生活题材中,或想象中的超验世界的题材中,都有 新的感觉的寻求和发现。这种新的感觉,不应只限于个人的生理体验,而是与现代社会 的发展进步密切关联的新的诗的经验,诗情或诗意。40年代初期,朱自清在介绍金赫罗 (Harold King)的《现代史诗——一个悬想》一文里,提出了在“现代商工业的加速的 大规模的发展”中建设“建国诗”的理想。他说,建国的主要目标,是现代化,也就是 工业化;“我们迫切的需要建国的歌手。我们需要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诗。……我们也需 要中国诗的现代化,新诗的现代化;这将使新诗更富厚一些”。[22](P.351~352)这里 隐约提出了城市诗建设与新诗现代化关系问题,可惜这个问题后来没有多少回响。郭沫 若的“雏形”期城市诗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仅提供了新的感觉与现代性审美转变的信息 ,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新诗实现自身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收稿日期:2002-0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