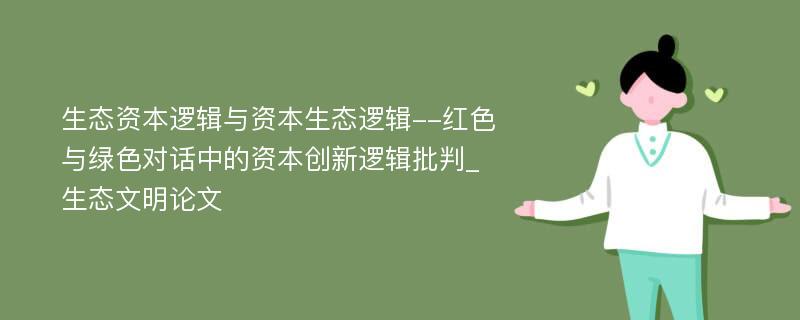
生态的资本逻辑与资本的生态逻辑——“红绿对话”中的资本创新逻辑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论文,资本论文,生态论文,红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将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列为五大建设的重要环节,并贯穿于其他四大建设之中,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然而,无论是就生态文明概念本身还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实践都无可回避地需要回答一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就全球范围而言,我们如何看待生态文明与资本逻辑的相互关系?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全球学界“红绿对话”所阐释的林林总总的话语资源需要有一个深度梳理,而其中涉及的问题硬核需要有一个科学解剖。换言之,深度反思生态发展与资本逻辑的关系,需要全面梳理生态资本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需要基于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加以科学辨识。 近年来,学界十分重视对国外“红绿对话”中的红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介绍与评价。总的来说,以奥康纳、高兹、阿格尔、佩珀等为代表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最先发现了生态破坏与资本逻辑的本质关联即“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深刻批判了资本过度生产和消费导致生态破坏,深刻阐明了超越资本是解决生态问题根本出路的观点,以及对真正的基层民主、生产资料共同所有、面向社会需要的生产、结果的平等、社会与环境公正、相互支持的社会与自然关系等原则的强调,这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无疑具有重要启迪意义。①然而,生态社会主义提出的一个绝对化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内在地‘对环境不友好’”,在日益加剧的增长和竞争的背景下,“一个人道的、社会公正的和有利于环境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幻想”。②生态与资本绝对对立,生态是资本无法逾越的天然屏障,似乎生态建设就成为排斥资本的超然领域。生态文明一定是超越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的。这就有失偏颇。生态主义(深绿)也将资本当作传统工业文明的在场而加以拒斥。在生态与资本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看到:在以大工业资本为主导地位的旧全球化时代,资本逻辑无疑曾经是反生态的,资本疯狂逐利曾经是造就生态破坏的主要原因。然而,以后工业文明为主导的新全球化时代,资本创新以各种节约型、高科技、生态化产业为主导,表现为一种生态资本主义。生态领域决不是阻挡资本逻辑深度进入的天然屏障。只要有利可图,资本必将成为推动生态建设的强大历史力量;生态产业是资本创新逻辑的必然产物。绿色资本主义不仅完全可能,而且已开始成为全球现实。但是,生态发展的最终目的与资本的生态逻辑之间依然存在着内在的巨大对立。传统生态社会主义预言“生态是资本主义天然屏障”的观点是有偏颇的。③我们需要重新反思生态文明与资本创新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资本的生态化逻辑批判:生态领域决非阻挡资本深度进入的天然屏障 关于生态文明的研究,从国外的红绿对话到国内的研究,存在着两个似乎难以动摇的神话:第一,生态是资本主义天然屏障,生态文明是一种超越资本存在方式的先进文明;第二,生态文明是一种可以修正马克思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缺陷的高级文明,应当将马克思主义提升到生态文明的水平。生态文明是不受马克思主义批判的。两个问题涉及生态文明、工业文明、资本、马克思主义四者关系,核心问题是生态文明与资本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资本的批判者,没有资本当然就无须马克思主义的在场;而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的必然替代,成为今日文明的主要形态。因此全部问题在于要以生态文明与资本的关系为准建立一个理论的坐标轴,可以将四者按照他们各自的定位在坐标轴上恰当标出,就可以准确地评判它们的相互关系。 虽然“红绿对话”双方关于生态破坏根源的认识有差异,但是双方都难以否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大工业资本主义存在着内在的生态矛盾,现存的为了追逐利润而无限制地扩大再生产、盲目再生产、盲目消费甚至对不可再生资源采取掠夺性再生产的资本主义是造就生态破坏的原因。差别在于,生态主义着力将破坏生态的原因笼统归结为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内的“工业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并仅视为一种认识态度和价值观。在生态主义者戈德史密斯看来,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传统自由主义,也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基于追求不断满足大众需要的物质财富增长为前提的,因而是“工业主义”的。④生态主义整体超越了工业主义、生产主义逻辑、消费逻辑和物质财富增长逻辑。与之不同,生态社会主义明确将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奥康纳认为:第一,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冲动不断造就无限扩大的生产主义逻辑,背离了真正的需求,不仅造就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而且也造就了“第二种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的自然物质前提的生态恶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与生态的矛盾。第二,为了摆脱区域内的危机,资本不断扩展全球化空间,扩大市场、转嫁危机,从而也破坏了生态的地方性或社群主导原则。第三,资本主义生产为了牟取暴利,不断滥伐森林植被,改变自然空间,造就各种污染,破坏环境,成为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的主要推手。 其实,红绿双方都没有意识到:工业主义和与之相伴的“人类中心主义”,都是资本在特定历史中的外在表象。资本作为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其本性就是无限地追逐利润。为了逐利,资本必然不断采用最先进的生产力。当年,大工业是最先进生产力,因而是资本赢利的最主要路径。资本出场的工业化路径立即造就了三个相关的衍生后果:第一,资本的启蒙效应。人们借助资本化的机器大工业,初步完成了人对自然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本在一百多年间创造的生产力比以往历史上的总和还要多。资本借助大工业手段,迅速扭转了前资本时代物质普遍匮乏的状态,使之转变为相对于市场购买力而言的过剩经济。人的智力不断被资本挖掘出来,充当战胜自然的武器。自然地位从高高在上的神灵变成匍匐在人的脚下被支配的奴隶。大自然的统一性和完整性被各种资本化的大工业撕成分门别类的原料碎片,成为被任意奴役的对象。人真正成为万物的尺度,“人类中心主义”在资本条件下成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启蒙意识形态。第二,资本的城市效应。后现代生态主义批判视野中的所谓“中心性”,不仅体现在人类中心主义,更体现在为了大工业的集聚效应,按照生产集中、市场集中、居住集中的“城市三要素”,造就了一个又一个资本大工业城市,取得了对乡村的绝对统治权力,造就了城乡二元的现代分割与城市中心地位。资本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人口拥挤、资源破坏的严重后果。第三,资本的全球化效应。全球化是流动的资本现代性。资本因不断扩大资源、廉价劳力和销路而在世界到处生产,到处销售,到处扎根,因而成为全球化的。因此,生态社会主义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工业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正是资本在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 当年马克思面对的就是资本大工业崛起并扩展为资本全球化的时代。如果说大工业生产方式造就了“人类帝国主义”、城市对乡村的统治、西方对东方的统治,那么这无非是资本在特定历史时代的在场方式。在造就生态破坏问题上,我们既不能因为看到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外壳作用就断然否认资本的灵魂作用,像生态主义(深绿)那样,也不能同意生态社会主义的观点,即因为洞见资本灵魂的作用因而就否认大工业生产方式外壳的历史作用。进而言之,资本的大工业化,也是资本周期性危机的阶段性根源。资本危机爆发表现出的不可持续性不仅表现在社会内部,而且表现在社会与自然之间。资本的本性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冲突不仅表现在疯狂扩大的产能与相对不足的购买力之间的脱节矛盾,更表现在疯狂的生产主义逻辑迅速破坏了再生产的自然前提,造就人的存在自然基础和无机身体的退场。不仅如此,大工业文化与人的自主形态还是资本意识形态的抽象化表现。越是表现为超阶级、超历史的意识,越是资本的物化意识。 工业资本造就了不断疯狂扩大再生产的“生产逻辑”,不是为了满足人的真正需要而是满足资本逐利的本性。从物质匮乏时代到产能过剩时代,资本都在不断挖掘潜力扩大再生产,追逐利润,因而无限榨取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造就人与自然的全面对立。为了降低成本获得利润最大化,如果能够因减少防治污染而节约成本、增加1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如果无序砍伐和榨取资源能够带来20%的利润,资本就会趋之若鹜;如果竭泽而渔地榨干所有地球上不可再生资源而能挣到30%的利润,那么,资本就会不顾一切;如果能够带来300%的利润,资本就会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和涉及生态的一切良知。资本化大工业无序生产带来了人与自然的尖锐冲突,即“资本主义生态矛盾”,造成了发展前提的崩溃。 资本的工业主义外壳的崩溃和被炸毁基于多个标志性事件。从著名的英国伦敦的“毒雾”,到核爆发和核泄漏引发的世界恐慌;从日本企业排放超量汞等重金属所造成的“水俣病”到世界雨林被大量砍伐和大气中工业污染粒子的超量排放造成的“温室效应”、南极上空的臭氧空洞等等,这些环境生态事件严重破坏着人类生存的自然基础,成为资本大工业反人类的标志,不仅遭遇全世界公共舆论的强烈抗议,也遭遇各国有良知的企业家的抵制。从资本中率先分化瓦解出来的“自觉资本主义”,就成为反思和摆脱粗鄙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通过技术创新和资本创新来实现“绿色资本主义”的先驱。上个世纪60年代卡逊《寂静的春天》就是这一反思的奠基作,由此引发了绿色反思的巨大浪潮。在这一意义上,生态主义对工业主义的反思批判,是对资本一个特定时期出场路径、方式和形态的表象批判。这一批判也在某种程度上加速摧毁了资本的工业主义外壳。 而随着西方国家工业主义外壳被逐渐抛弃和炸毁,资本并不甘心就此永恒退场。为了适应新的人类绿色需要,获得新的利润,资本必须要创新。在资本与社会激烈冲突、大工业外壳已经被西方社会抛弃、资本不创新在西方社会就无以立足的情况下,资本一方面将污染企业与高耗企业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另一方面部分资本加速创新进程,走向自觉资本主义,融入绿色社会,发展绿色产业,通过新的产业形态和在场方式使自己重新获得创利空间。因此,绿色运动、生态主义和生态文明背后依然可能隐藏着资本创新的故事。 资本创新逻辑通过三大路径进入绿色领域、转换绿色外壳。第一,通过技术创新和环境保护,倡导绿色生产、洁净生产,表达“自觉资本主义”的产业意志。当年造就“水俣病”的日本重水公司一方面对事件表示深刻反省并承诺分期赔偿损失,另一方面则运用一切手段在新建企业中倡导绿色理念、推进洁净生产和循环经济。第二,利用资本创新扩大生态产业,为市场和大众提供更多优质的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第三,在文化上,倡导从浅绿到深绿的文化。所谓浅绿,就是依然站在“人类中心论”立场上,用“人类发展为主轴+环境保护”,一切出发点和归宿点依然是财富的增长和人类消费指数的增长;认为人类总是实践的主体,总是以自身利益为价值尺度来规范、控制、调节与自然客体的关系。所谓深绿,主要是生态伦理学,主张地球及其生物都有自己的主体性、权利和价值,人类应当以平等态度对待它们,而不能以一己之私利而无端侵害之。环境保护与生态主义,都是自觉资本主义创新逻辑的必然出场形态。资本的生态化何以可能?资本之所以从毁绿到浅绿再到深绿,其根源在于谋求一种新的自由创利空间。 因此,正如启蒙的抽象人本主义思想本质上就是资本的意识形态一样,生态主义也是资本创新逻辑的意识形态的抽象表达。对于资本创新逻辑来说,并不存在着天然的绿色壁垒。资本创新逻辑也存在着走向生态领域的内在通道。 二、生态的资本化逻辑批判:当代绿色产业背后可能隐藏着资本故事 红绿双方无可回避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对于生态文明建设,资本能否有为?绿色的生态主义当然将资本主义仅仅当作是大工业主义的典型代表而加以拒绝。生态主义反对资本化的大工业文明,将生态文明视为是高于、不同于大工业文明的一种新型文明,颇有道理。但是据此就认为资本永恒被定格在大工业文明的历史外壳上而无法进入生态领域,未免有失偏颇。生态社会主义从本质上将资本看作是生态正义的破坏者,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就此将资本放逐于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之外,根本否定资本对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的历史作用,未免失之抽象。 其实,在生态正义完全实现之前,生态文明建设依然甚至必然要重新经历资本化历史进程。如果说生态正义着力强调生态权益(包括生态环境的占有、使用和生态产品的生产、分配、消费等)的公平性,那么对生态的生产供给能力问题的追问肯定成为强调公平分配的基本前提。没有生态,当然就没有生态正义。没有生态产品和服务的物质基础,生态正义就无法实现。生态生产的正义显然高于分配的正义。也许我们难以仰仗生态资本去完全实现一个正义的生态文明社会,但是利用生态的资本化去推动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确实是一个必要的阶段。 所谓生态文明,是超越了生态与文明对立的新型文明。以往人类文明都是建立在对自然荒野的征服、驾驭和改造基础上的,文明意味着远离荒野。生态则是荒野的自在,维系着生物圈、岩石圈和大气圈存在的系统。文明与生态两种在场始终是保持着著名的“人与自然的对立”状态。在资本大工业对自然破坏性掠夺开采状况下,文明与生态冲突日趋尖锐化。那么,文明与生态两者统一何以可能?这不仅是一个观念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无论是沿用传统资本大工业文明对待自然奴役的“人类中心主义”实践态度或撇开人类实践主体地位的生态主义态度都无法达到。在人类种族的生态足迹遍布全球的时代,要实行生态主义主张的那样,完全隔绝人与自然或驱赶人类生活圈而让自然自发修复已有创伤,虽然听起来很美,局部也能做到,但是在全局和整体上却难以做到。人类与自然深度交融、彼此共享同一生存空间,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唯一的可行的选择只能是:生态支持。这不是割断人与自然的联系而单纯让自然生态封闭修复,不是排除人类作用而消极地仅仅采取“环境保护”而等待自然的自发修复,而是要通过弘扬人类主体性的积极实践,增进生态建设效益,增加生态修复和完善值,人类在增进生态发展过程中得到更多的生态效益和生产、生活品质的改善,人类与生态同向、同态、同构地共进共赢,既保持环境友好,又增进人类利益,这就是“环境支持”。 生态支持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人的主体性责任和改变世界的实践态度,因而与生态中心主义有原则的区别。虽然生态中心主义也强调与呼唤人在呵护生态文明中的责任,但是前提是生态的自主性、独立性和内生价值,主张生态自主修复,反对人为干预。这是一种消极的生态保护观念和自发的生态修复主张。生态支持则将人的生态主体责任与实践干预行动合一,强调通过人的积极实践和生态建设来大力推进生态修复和生态发展,由此而获得生态的整体效益回报。生态支持也体现了生态原则,因而与传统的奴役自然、破坏生态的人类中心主义相区别。它尊重生态规律,按照生态规律来实现生态建设。因此,生态支持是人的主体性与生态的统一,因而也构成生态文明的基础。生态支持支撑着人们将自己纳入一个与自然生态良性互动的完整绿色生产—生活体系中,让绿进沙退,使荒漠改善;以大量繁殖濒危物种来抵御物种消失的厄运,维系生物的多样性;按照生态规律改善生活环境,使天蓝地绿水净气清;利用基因工程,复活千万年前灭绝的物种,再现大自然所不能的过程;在所有生态化的实践中发展人类事业,并让人类得到最好的享受,成就新的幸福生活。 生态支持的回报就是生态服务。我们需要一个越来越大的生态支持和服务。这一支持和服务不仅是宜居、审美的,也是产业和经济的。但是越来越大的生态支持和服务也只有在积极的生态投入基础上才能获得。投入与回报良性循环,产生生态、审美、健康效益,也形成经济价值和创造经济剩余,不断获得积累,形成绿色产业。因此,这就必然需要资本,也无可回避地产生资本。只要我们还不具备为全球人类不断增长的生态需求提供无限的生态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那么生态产业的资本化就是不可避免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就依然需要依赖资本形式的支持。 生态的资本化具有积极的历史作用。第一,有利于改造资本,尽快摧毁资本旧外壳,促进资本创新。只有资本转向绿色的通道畅通无阻,旧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资本外壳才能不仅被外部社会打破,而且也会被资本从内部通过创新而自我否定。资本内部自我否定的力量往往表现为一种资本的自觉和自律,其否定和批判破坏生态的资本旧形式的能力大于外部的压力所产生的效应。我们对自觉资本主义的生态转向或资本的自我创新应当表示谨慎的欢迎而不是全盘拒绝。第二,有利于加速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生态的资本化将会引发更强烈的冲动,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动力。生态建设过程需要借助资本创新驱动,淘汰落后产能,提升和优化产业结构。只要有政府公共政策扶持,有市场需求,有利可图,资本就乐意从事生态建设,成为“生态自觉的资本”。第三,有利于大量积累生态成果和生态财富,为最终完成生态文明建设奠定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生态的资本化在创新逐利的同时就会以强力冲动来积累和增加生态成果、生态财富。这些成果和财富的积累为未来超越资本的局限、走向真正的生态正义提供物质基础。 因此,生态的资本化趋势并不如生态社会主义所言,其结果都是消极的。在其生态产业化语境中,我们依然可以读出具有资本创新逻辑意义的新故事。 生态文明构筑了一个人类全新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社会生存方式和价值形态。它至少涉及四个维度:技术(科学与认识论)、经济(资本批判和产业再造)、制度(公共治理体系和社会组织形态变革)以及生活需要—价值观变革。在这四个方面,我们都将遭遇生态资本化的历史形式。没有生态的资本化,我们就没有强大的生态产业和生态服务,就不可能在技术上形成生态支持;没有生态的资本化,我们就不可能加速推动资本旧外壳的批判改造,完成生态文明建设工程;没有生态的资本化,我们在生态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上就难以提供一套与历史和市场相匹配的可行的公共政策;没有生态的资本化,我们就没有用生态消费价值取代旧的消费社会、转变生活方式的可能。生态产业与消费的资本化,在新的历史基础上依然起着推动世界历史进步的杠杆作用。 三、生态资本批判逻辑:两重作用与辩证视阈 超越“红绿对话”的各自偏颇,我们需要审慎地看待资本创新逻辑的历史作用。资本的生态化与生态的资本化遵循着资本创新逻辑,对于传统的大工业文明形式的资本外壳是一种否定和超越,但是绝没有从根本上完全摆脱资本的逐利本性。生态资本尽管是不断生产生态产品的资本,成为社会生态产品的供给者,与大众社会生态需求具有领域的一致性。但是,只要仍然是资本,其最终目的和根本目的必然与大众不尽一致。在保持赢利这一点上或在此范围内,资本可以起推动生态建设的积极历史作用。当生态破坏严重、生态产品稀缺时,由于市场价值的调节,生态资本的投入甚至是非常高的。然而一旦资本为了逐利而导致某种类别的生态产品大量过剩而无利可图,那么资本就会立即抽逃,甚至导致新的生态产业危机,而与大众之间有关生态目的性矛盾就会立即暴露。 因此,资本创新逻辑的历史作用依然是双重的,我们必须要坚持马克思当年对于资本两重性作用评价的辩证视阈。 一方面,资本创新逻辑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当年所指出的“具有非常革命的作用”和“伟大的文明作用”的特征。为了摆脱危机与更多获利,资本创新是其本性的必然选择。资本创新或通过更新技术、管理、市场,或转换主导产业与资本外壳,来实现自己灵魂的生命再生,同时就开辟出一个新的产业领域、新的生产发展的形式、新的利润扩展的空间。周期性的创新体现出资本的革命性,从而成为推动世界历史进步的杠杆。一旦资本形成生态化逻辑,就必然摆脱大工业外壳而转换为生态产业外壳,成为生态产业、生态建设的强大动力。为此,我们不可能避免利用资本来发展生态产业,促进生态事业,推动生态建设。尤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在生产力仍很不发达的条件下,自觉引入和利用资本,走环境支持的生态建设之路,应当是无可置疑的路径。生态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的发展与克服资本造就的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另一方面,资本创新逻辑尽管穿上生态产业外衣,有了绿色的外壳,但是既然逐利本性没有变,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没有变,生态资本与生态正义之间的矛盾一定会不时地爆发,最终导致对生态正义和生态文明本质的偏离和异化。周期性的扩张使资本创新获利更大,也在更新的层级上孕育着剧烈的固有矛盾。我们一定要警惕资本为了逐利而偏离生态建设道路,甚至重新回到破坏生态以图利的老路;也一定要防止资本为了逐利拼命扩大生态产业,造成生产过剩。即便是所谓生态产品和生态消费,一旦被资本利用,都有可能出现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问题。一旦过度,就从根本上偏离了生态文明的轨道。资本创新可能会成为生态产业和生态消费发展的强大动源。只要将生态建设道路变成是有利可图的,资本就一定会被吸引。资本会按照有利可图和生态建设同轨线路强力推进生态建设,而且一定有将生态产品和消费不断扩大的冲动,一直到无利可图为止。利用和驾驭得当,资本可能成为生态建设的同路人。资本仿佛是生态建设圆周边沿上的切线。我们既要看到两者同路并被资本强烈推动的可能性,积极吸纳并巧妙利用好资本的推动力量,又要驾驭和制约资本,防止资本为了逐利而脱离生态建设正常轨道而变成渐行渐远的直线。利用和驾驭资本需要有政治和制度等一系列刚性边界条件制约。 因此,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一场持久战。其必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制度框架制约下充分利用生态资本发展生态产业和事业,满足人民群众越来越增长的生态需求的过程。“与狼共舞”是一个长期的现象。我们需要自觉充分地利用生态资本的作用,但是又要在观念和制度上限制资本的消极作用,防止被其另类牵引。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坚定地走中国生态文明的建设道路。 注释: ①[英]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②[英]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第3页。 ③参见[美]奥康纳:《可持续的资本主义是可能的吗?》,载《詹姆斯·奥康纳会议论文集》,桑塔克鲁兹生态社会主义研究中心1991年版第27页。 ④参见[英]戈德史密斯:《生存的蓝图》,王新名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标签:生态文明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生态产业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人类文明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时代资本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社会资本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环境保护论文; 经济论文; 逻辑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