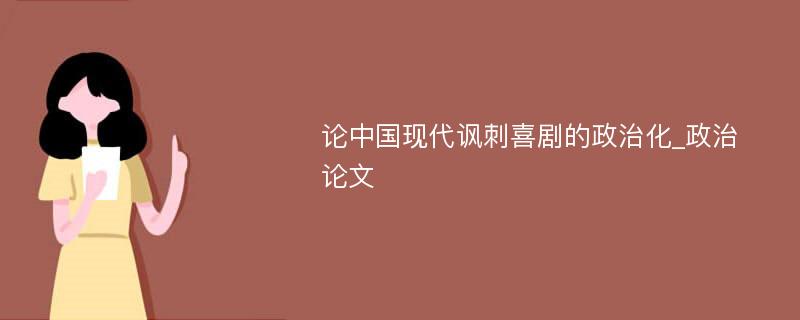
论中国现代讽刺喜剧的政治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喜剧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3)02-0110-06
“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上海事变之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 的生死存亡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抗日救国成了摆在每一位真正中国人面前的最大的政 治问题。战争,以一种强力的方式不仅改变了中国现代喜剧的生存空间,而且也改变了 其创作本身。这种“改变”最突出的体现,就是讽刺喜剧普遍而迅速的政治化。
作为这种急剧政治化的艺术成果,自1938年起,一大批具有特色的战时政治讽刺喜剧 开始应运而生,并且很快成为抗战期间五音交汇的喜剧大合唱中的高音部。当然,政治 讽刺喜剧绝对不会是20世纪40年代讽刺喜剧的惟一样式,事实上,它的兴起和发展不可 能完全取代其他类型讽刺喜剧的存在。但是必须指出,它却是此期讽刺喜剧的主导类型 。正是由于它的出现,社会讽刺喜剧才会发生如此深刻而明显的变化。中国现代讽刺喜 剧的政治化实际是由政治讽刺剧的崛起和社会讽刺剧政治性的不断强化这两个主要方面 构成的。
本文着重考察的是,这种政治化为现代讽刺喜剧的发展所带来的实际影响。
一
政治化给中国现代讽刺喜剧带来的最明显因素是它对社会重大主题的表现。20世纪40
年代讽刺喜剧的基本主题是抗日和民主,无庸赘言,这是两个足以决定中华民族历史命 运的政治性主题。将讽刺喜剧同这样的主题连接在一起,不能不反映出人们在喜剧合法 性问题上认识的普遍深入。这里所说的合法性实际也就是喜剧的社会意义问题。
应当承认,中国的现代喜剧作为新文学的组成部分,从产生的第一天开始就没有忽视 笑的社会意义。即便像熊佛西那样被人认为比较注重艺术趣味的戏剧家也一再在理论著 述中强调着喜剧在启发向上的生活意志、培养合作精神方面的积极作用;即便是带有非 现实色彩的寓言讽刺剧,人们也不难感受到其中明显的现实社会指向[1](p181-195)。 但是,由于多数喜剧作者长期生活在比较狭小的圈子里,和实际政治问题保持着相当的 距离,再加上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他们的讽刺喜剧往往局限 在一般社会问题和伦理问题的表现上,极少涉及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矛盾。这种情况很难 适应“五四”以来中国社会大动荡的现实要求,长此以往,喜剧难免面临流入“小摆设 ”的危险。传统的喜剧观念加上现实的创作实践,使不少人都爱把喜剧仅仅当作一种令 人解颐叫人轻松的戏剧样式,怀疑其在表现重大社会主题和政治主题方面的可能性。这 也正是许多左翼人士时常在喜剧创作面前望而却步或游移不定的主要原因。
上述情况到20世纪30年代下半期开始有了明显改变。这固然与当时的社会情势有关, 同时也是深受以果戈理为代表的俄罗斯讽刺传统影响所致。《钦差大臣》正是这种具有 明显政治色彩的积极传统的生动体现。如果说,它在俄国的演出给贵族社会和政府机构 带来的巨大的震撼、难堪和恼羞成怒曾使它的作者不由地感到痛苦和恐惧的话,那么,
它在中国的演出却为正处于激烈政治斗争形势下的中国进步的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提示了 这样一种可能性:喜剧固然和笑有着不解之缘,它在生活的反映上固然有着自己独特的 审美观照和艺术表现的方式,但它丝毫不必推诿自己对于社会人生的责任,在表现重大 社会冲突的课题面前,它有着与悲剧和正剧同样的机会和权利。喜剧之笑,特别是讽刺 喜剧之笑并不必然地削弱社会矛盾的严重性和严肃性,相反,它完全有可能从一个特殊 的角度突出它们、强化它们,从而使自己成为一种具有高度倾向性的笑,成为打击社会 邪恶、挑破政治疮疽的笑。
正是在认识深化的基础上,中国现代剧坛出现了一批如《县长》、《恭喜发财》、《 魔窟》、《乱世男女》、《升官图》、《狂欢之夜》这样在《钦差大臣》直接启迪之下 问世的作品,出现了一批如《汪精卫现形记》、《两面人》、《草木皆兵》、《群猴》 、《捉鬼传》、《裙带风》、《无独有偶》这样敢于直面重大社会政治人生的作品。它 们在社会上所获得的不同程度的成功以及它们所产生的轰动效应,表明它们已将喜剧在 社会政治批判功能方面所具有的潜在可能性变成了现实。困扰人们已久的喜剧合法性问 题至此似乎已经得到了初步的解决。正是由于有了对社会政治重大主题的表现,20世纪 40年代的讽刺喜剧才得以纵横捭阖,汇聚成雄奇的景观。
或许是因为需要反映重大社会政治主题的缘故,20世纪40年代的讽刺喜剧表现出前所 未有的高度的概括力。较之前此时期的寓言讽刺剧,此期的讽刺喜剧在概括性方面亦显 示出明显的不同。前者的概括基本属于一种伦理的或是哲理的性质,而后者则尤其注重 概括的社会性和政治性。
《抓壮丁》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一出幕表戏的基础上做出重大修改后而取得的可喜成 果。从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政治化时期讽刺喜剧概括性的运行轨迹。该剧底本的主 旨在于宣传识字的重要性,其中概括性的总结也只在不识字的人等于“睁眼瞎”这样一 个浅显的道理,并无明显的社会性内容。但到《抓壮丁》,情况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关于识字重要性的潜在认识或许仍旧存在,但其早已被压缩改作成刻画王保长的诡诈、 李老拴的愚昧和推进情节发展的一种细节性因素,至于整个作品则已成为透过兵役问题 揭露社会黑暗和政治腐败的政治讽刺性的喜剧。表面上看,剧本主要描写的是王保长和 卢队长等人在征兵过程中的舞弊行径,但作品的真正意蕴却远不止于此。作品通过王、 卢两人的沆瀣一气以及后来同李家大娃子的快速勾结,把他们联成一体,从而说明剧中 恶棍们的罪行并不单纯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一种集团犯罪。不仅如此,作品还将这样 一个犯罪集团同“国民党”以及他们的“蒋总裁”联系在一起,从而暗示出一个更大的 犯罪集团的存在,并将讽刺提升到了更高的层位。此外,作品通过李二娃子躲避兵役的 逃而复回,表明这种腐败的兵役制度在各地造成的普遍黑暗。最后,剧本通过姜国富一 家的悲惨遭遇,说明人民大众才是政治黑暗的真正受害者。这样,正是在概括性的基础 上,一个意义重大的社会政治主题被准确无误地表现出来了。
《抓壮丁》当中的概括性主要依赖的是一种社会分析和政治分析。而《群猴》当中的 概括则更多地借重于否定人物的代表性和群体性。和《抓壮丁》差不多,《群猴》也是 重修30年代旧作的产物。在旧作《平步登天》里,贿选丑剧的受贿者是位普通的村长, 同时兼任小学校长,生活窘迫。就其代表性来说,他充其量代表着小市民的某些特征。 其妻也无非是位一般的乡间蛮妇,刁泼外加无知。在两位施贿者当中,一位是上海的开 业律师,另一位是本县的富豪。就重大主题的表现而论,以上四人都不具备真正的代表 性。而在《群猴》中,受贿者变成大都会中的一对“政治”夫妇。先生从日伪时期就是 镇长,昔日的汉奸如今成了民“主”。太太是位颇具“政治”眼光的女性“外交家”, 不仅知道“国际路线”和“中美机会均等”,而且深谙“民主”的底里。施贿者由两人 一变而为四人,并且个个都具备了极为鲜明的政治背景。其中,一位是三青团的少壮派 书记长,一位是中统特务,一位是孔祥熙的下属,最后一位是“新运派”的妇女运动者 。这六位施贿者和受贿者合演了一出“群猴”狂争“乱咬”的丑剧。作家通过这种群体 性和他们各自的代表性以及不同派系之间的相互攻讦,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倒行逆施 进行了广泛的抨击和讽刺。从而体现出作家对于重大社会政治主题令人绝倒的整体把握 力和艺术表现力。
20世纪40年代讽刺喜剧对于概括性社会政治内容的热切关注,在作品的人物类型方面 也导致了明显的变化。一批正面形象不断进入此期的讽刺喜剧中。从《魔窟》中的游击 队员、《乱世男女》中的秦凡、《学校风光》中的爱国师生,到《雾重庆》中的林家棣 、《归去来兮》中的老画家、《美国总统号》中的曾古柏、《满庭芳》中的戴华明,再 到《升官图》中的民众、《捉鬼传》中的钟馗、《裙带风》中的陈建南等,无一不体现 了这样一种总体的趋势。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作家们对于社会政治 概括性内容的自觉追求显然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正如曾古柏在《美国总统号》中所说:
你瞧这个船上,没几个中国人,可倒是咱们国家社会的一个缩影。你瞧,一边是热血 满膛的青年,一边是脑满肠肥的蛀虫。
要想达到全面概括的“缩影”效果,正面形象似乎是一种不可漠视的存在。在人们看 来,只有在正反双方人物同时上场的情况下,作品才有更多的机会去全面、准确并且富 有希望地表达出社会政治主题的重大性。对于讽刺喜剧来说,这种认识本身是值得商榷 的,并且在多数情况中这些正面形象艺术上的完美程度也值得怀疑,但它无疑向中国的 现代喜剧作家提出了一个令人饶有兴趣的课题。应当说,问题提出的本身就包含了民族 与时代的丰富内涵。
二
政治化为20世纪40年代讽刺喜剧带来的又一明显影响是其在艺术表现上的多样化。当 然,这里所说的多样化显然是有条件的,符合政治化的总体要求是其根本性的前提。
政治,在我看来,是理性与激情的宁馨儿。一方面,它是高瞻远瞩、运筹帷幄,表现 出一种清醒透彻的理性精神;而另一方面,它又可能是一种火热炽烈的激情,人们时常 将它同热情乃至狂热相联,或许正是这个缘故。政治本身具有的这两种质素,使得在它 催发下崛起的讽刺喜剧呈现出与之相应的两种基本的创作模式:写实的和浪漫的。
和20世纪30年代一样,40年代的讽刺喜剧仍然以写实主义作为自己的主导创作模式。 同此前时期相比,它除明显加强了社会政治色彩之外;艺术上变得更加圆熟,同时剧本 体制一般较大。其代表性作品有《禁止小便》、《两面人》、《抓壮丁》、《美国总统 号》、《裙带风》和《南下列车》等。一般来说,现代讽刺喜剧通常具有四种功能:批 判、审美、认知和宣泄。其中的前两项是写实型讽刺喜剧和浪漫型讽刺喜剧共同具有的 ,真正能构成两者区别的地方在于:前者相对而言更注重认知功能,后者更倚重宣泄功 能。写实型作品更喜欢以一种客观描绘的方式剥脱丑恶的假面,从而导致对丑恶本质的 清醒的理性认识。对丑恶的深刻认识必然会引发创作和欣赏主体的憎恶之情,但是这种 情感的传达在典型的写实作品中绝不会绕过客观描绘的中介。
《禁止小便》中,作家对于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的批判,是通过某行政机关在视察委 员到来之前的一组近乎白描与速写式的镜头实现的。其中,刘树诚是最重要的揭发者, 但他并不是作家主观的代言人。刘树诚极具情感的揭发完全符合作为一个工作了18年而 未得升迁的老科员的特定境遇,完全是生活实有的样子。在这个机关中,上层人员及其 亲信终日花天酒地无所事事,胡科长的一夜麻将“抗战”就输掉500元,相当于一个小 录事一年有余的工资。而下层人员则在随时可能被解职的阴云之下战战兢兢整天劳苦, 难得喘息的机会。只有位于这两者之间的刘树诚因为绝了晋升之望,加上又有上司不得 不借重的地方,于是日子过得倒也洒脱。正是这种若即若离的特殊地位,使得他的揭发 不仅真实可信,而且入骨三分。刘树诚对于两种为“官”“秘诀”的归纳,固然是对国 民党官僚机构的讽刺,同时显然又包含着自嘲的成分,从中可以看出作家对于这位“刘 同志”本身的清醒认识。也即是说,作家在通过他批判政府机构的时候,并没有超出这 一人物自身的本质规定,从而满足了写实性基本的美学要求。《禁止小便》以刘树诚为 中心,通过部分是由他导演的一出“牌子”闹剧,一方面客观而生动地揭示出国民党政 府“革命化”、“行动化”的虚假本质,另一方面又从中几乎是不露声色地推导出了一 个合乎逻辑的理性认识:靠这样的政府是不可能领导抗战走向最后胜利的。
20世纪40年代浪漫型的讽刺喜剧最典型的代表是《捉鬼传》。作品中,作家以钟馗捉 鬼的传奇故事构成了一种整体性的象征意象,从而明显表达出自己的浪漫主义美学追求 。写实型艺术当然也可以运用象征的方法,但这里的象征至多也只会具有一种局部意义 ,而不大可能发展到统摄全局的程度。《捉鬼传》中的象征世界显然为作家姿肆汪洋的 笔力提供了一个任其驰骋的广阔天地。在这个充满着一连串奇思妙想的天地中,阴间的 阎王可以来到阳间兼差,钟馗酒醉可以变成化石,而在千年之后,化石又可复生,人物 亦会轮回,于是乎,当年的卢宰相变成了如今的卢总理,当年的易根毛成了如今的易总 长,当年的冒牌货变成了如今的真将军,当年的牛魔王成了如今的牛镇长。在这里,生 活本身固有的样态至少在表层的意义上被彻底摧毁,生活真实的规定性受到了公然的挑 战。
然而,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人们并不以此为忤,他们最终接受了这样一种艺术的事 实。这是因为他们在剧中不仅认识了这个鬼狐横行的世界的本质,而且深刻体验到了一 种情绪上的真实。这是主体在目睹世界的丑恶之后必然会生发出来的一种极度愤怒与轻 蔑的强烈感情。正是在这种情感的宣泄中,一切善良的人必然会产生共鸣,达成共识, 并且从中孕育出改造现实的巨大力量。事实证明,这种注重情感宣泄的浪漫型讽刺喜剧 在宣传民众教育民众方面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浪漫主义在度过了20世纪30年代 的反省时期之后,其在40年代的回潮,对此期的讽刺喜剧不能不说是一种可喜的丰富和 突破。
在20世纪40年代的讽刺喜剧中,还有一种常见的创作类型,它的代表作品是著名的《 升官图》。《升官图》的成功,充分说明了那种写实与浪漫兼济的创作模式的生命力。 理性认知与情感宣泄并重的结果,使得这部作品相对全面地满足了前述四大基本功能的 需要,剧本之所以能在当时引起巨大的轰动,并在民众中间获得普遍的赞扬,显然同这 一点紧密相关。
政治化时期的讽刺喜剧在讽刺的样态上也明显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就存在的实际样态而言,我将讽刺区分为三种基本的类型,它们分别是时间型、空间 型和时/空型。应当说明的是,这样的划分当然是相对的。绝对地把时间和空间切割开 ,事实上在创作中并不可能,但在实际作品中,我们的确又可以感觉得到那种孰轻孰重 的区别。这说明上述类型的区分自有它们的根据。
时间型的讽刺剧主要给人的是一种线性的感觉。造成这种感觉的主要因素有二:其一 是讽刺对象的单一性;其二是讽刺主要以前后矛盾的方式实现。这里所谓的前后矛盾具 体可以表现为言行之间的矛盾或是动机与结果之间的矛盾。显而易见,对于这类矛盾的 揭示主要要依靠一种时间的形式才能展开。因此,这类讽刺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过程性 ,而这种过程性特点又使它不能不较多地依赖于作品中的情节因素。属于这一类型的作 品有《出征》、《两面人》、《裙带风》等。《出征》主要的讽刺对象是陈平仙,这是 位把抗日宣传当作一种时髦看待的知识女性。她可以劝说别人的丈夫去参军卫国,但到 同样的事发生在自己的头上,她又用各种名目去拖丈夫的后腿。作品以一种前后不一的 情节讽刺了陈平仙那类口头抗日派。比起《出征》,《两面人》和《裙带风》似乎要复 杂得多,但剔除了那些非讽刺的戏剧性成分以后,人们会不难发现作品的核心,实际是 在因果律的基础上以一种动机与结果相互矛盾的方式对祝茗斋和邓同所分别做出的讽刺 。祝茗斋的两面行径差点将自己推上了绝路;而邓同的换妻提议让自己大丢其丑。从某 种动机出发,人物采取了一定的行动,但产生的结果却是异己的,这种时间向度上的情 节展开,使我们最终有理由将上述两剧归入时间型讽刺剧一类。
空间型讽刺剧主要给人的是一种空间感,其构成要素亦有两种:一是讽刺对象的群体 性;二为讽刺喜剧的场面性。对于这一类型的大型作品而言,则通常表现为多种群体性 场面的连接。属于这一类型的代表作有《乱世男女》、《美国总统号》、《满庭芳》等 。这些作品的讽刺对象明显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作家们以火车车厢、跳舞场、旅 馆、客轮的休息间、文艺演出时的后台等特殊场所为背景,利用一种近似碰头会式的结 构,将他们所要讽刺的那群人召之即来,在那些人做出了充分表演之后又挥之即去,从 而给读者以一种横向的场面性的感觉。不能说这其中没有时间性的因素和情节性的成分 ,但它们毕竟处于从属的地位,一切让路给群体形象的刻画和描写。在我们提到的这三 部作品中,群体性特征并未压倒人物的个别性,这说明空间类型本身并不必然导致人物 塑造的类型化。在《乱世男女》中,紫波女士的做作与虚荣,蒲是今的猥琐与逢迎,王 浩然的领导风范,苗轶欧的绅士风流,李曼姝的玩世,科长太太的陋俗,吴秋萍更像是 个文化特务,所有这些都证明他们的个性并不雷同,尽管他们在抗战问题上都是语言的 巨人和行动的矮子。由于情节因素作用的减弱,空间型讽刺剧的兴奋中枢转向了人物形 象的创造,尤其对人物的语言给与了更多的关注。
时/空型讽刺剧最重要的代表作品是《魔窟》、《升官图》、《雾重庆》等。这一类型 的作品往往兼收前两者的优长,巧妙地把群体性的场面同整个情节的进展比较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升官图》第一幕第二场的县府紧急会议是一个典型的群体性场面,它不仅 意味着两个闯入者“公职”生活的正式开始,而且也是各局局长的公开亮相,其中最重 要的是它种下了假秘书长和财政局艾局长之间矛盾的种子。这时,艾局长通过县长太太 的字条已经清楚了假县长和假秘书长的底细,但又隐而不发,只是旁敲侧击,意在威胁 这两个人以便为其所用。假秘书长深知其意,但又偏偏不予理睬,会议结束时,又故意 将罚金断给了警察局,表现出不甘示弱的姿态。这些描写不仅有利于两个政客形象的塑 造,而且也为他们之间矛盾的日后展开埋下了伏笔。而这两人间的矛盾纠葛也正是推动 全剧整个情节进行的首要线索。时/空型讽刺剧一方面适应了中国普通观众注重故事情 节的审美心理,另一方面又引导着人们对于场面与人物的审美新需求。为了达到兼顾场 面、人物和情节的艺术佳境,不能不需要有一种高超的艺术驾驭力。如果说对挑战的应 战很可能带来艺术水平的提高,那么,20世纪40年代中有不少成功之作都出自这一类型 ,则不会是偶然的。
20世纪20~30年代的讽刺喜剧就讽刺的样态而言,主要是些时间型的作品,对情节的 倚重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物的扁平化。到了40年代,空间型和时/空型作品的明显增 加,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时代对喜剧社会性和政治化的客观要求,而且体现了作家们 对于人物的类本质与个性特征的重视。就此看来,讽刺存在样态的多样化是值得我们充 分肯定的。
三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所钟爱的戏剧类型,每一种戏剧类型都会有独属于自己的东西。在
时代和历史赋予它的独特性当中,人们往往可以发现存在的合理性与存在的局限性之间 那种惊人的组合。就此而论,我们丝毫不必讳言政治性讽刺喜剧作为20世纪40年代讽刺 喜剧主导类型本身所具有的局限。事实上,任何一种艺术类型都会具有自身的弱点,我 们没有理由单单地去苛求政治性的讽刺喜剧。当人们以一种戏剧样式之所长去评判另一 种戏剧样式之所短的时候,问题表现得如此明显,以致使我不想单就政治性讽刺喜剧这 一类型本身的特征去谈论40年代讽刺喜剧的历史局限问题。这一类型不管具有怎样的局 限,它在艺术的大千世界中都有着其他类型无法替代的意义。在这里,我要着重考察的 是政治化时期讽刺喜剧创作中出现的一元化趋向。造成这种趋向的真正原因,显然不在 政治性讽刺喜剧自身,而在孕育和催动其生成发展的那种独特的思想力量。
具体言之,这种思想力量包括两个主要的方面:其一是大一统的思维定势,其二是将 喜剧工具化的认识。
不少论者正确地指出:追求大一统,是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之一。这种大一 统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西周时代。到了孟子生活的年代,已有 了“定于一”(《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的说法。“大一统”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始 见于汉初的《公羊传》,其最初的涵义似乎仅就统一历法而言。在董仲舒那里,它开始 具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其内涵由历法的统一扩展到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一。中国古代的 “政”与“治”,说到底,就是对“一”的追求。这里的“一”既是“正”(政),也是 “治”,换言之,也就是政治上的大一统。思想上的大一统在汉代产生了经学,后来又 通过包括科举考试在内的多种途径进一步弥散到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文学艺术领 域自然也不会例外。这种大一统的思维方式在历史上所起到的作用是复杂的,难以简单 的臧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它培养了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根深蒂固的求同性和趋同 性。而这种求同和趋同的意识又很容易派生出对于异己思想的强烈的拒斥性。反映到文 艺创作上,则体现为主流文学对于非主流文学的明显抑制。具体到20世纪40年代的讽刺 喜剧创作领域,则表现为政治讽刺喜剧的排它性。人们往往以政治讽刺喜剧的美学原则 去要求其他类型的喜剧,政治性成了判断所有作品优劣高下的首要价值标准。20世纪40 年代对于夏衍《芳草天涯》“非政治化”的批判,就是对这一点很好的说明。《芳草天 涯》不是喜剧,但由于批判它所造成的实际影响不会不影响到喜剧创作领域。
几乎从20世纪初开始,进步的文化界就在喜剧合法性问题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困惑。中 国的现代喜剧逐渐走向繁荣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正是人们不断克服这种困惑的 过程。到了20世纪40年代,这一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的解决应主要视为一种“喜剧工具化 ”的胜利。喜剧从思想启蒙的工具,到分析社会的工具,而今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升官图》和《捉鬼传》在社会上引发的轰动效应,雄辩地证明了讽刺喜剧在政治斗争中 所能发挥的重大影响。政治的核心显然是政权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中, 专制主义的国家机器更是政治进步和革命的首要对立物。喜剧既已成为一种战斗的武器 ,其第一位的任务当然应是集中全力去揭露专制政权的虚假、丑恶和反人民的本质。对 照这样一种历史要求,陈白尘的《乱世男女》和宋之的的《雾重庆》尽管本身已经具备 了明显的政治色彩,但仍然难免受到人们的批评。批评者不无道理地指出:这两部作品 对于知识者的讽刺在客观上放过了阴霾真正的制造者。批评尽管给这两位作家带来了一 时的痛苦,但他们毕竟是幸运的,在稍事调整之后,他们都在“刺官”之作方面表现出 自己卓异的才华,在中国现代喜剧史上赢得了长久的声名。但是,如果承认作家在创作 个性上必然会存在着种种差别的话,那么我们势必就要承认:并非所有的喜剧作者都能 沿着这条道路达到自己创作的顶峰。
这种由于大一统的思维方式和喜剧工具论所形成的一元化创作趋向,在20世纪40年代 ,一方面有力推动了政治性讽刺喜剧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明显抑制了相当一批喜剧 作者的创造积极性。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艺术品类的上达都不能脱离它存在其间的艺 术的生态环境。当这种生态环境严重失衡的时候,这种失衡现象必然要反作用于具体的 艺术品类,限制它们在艺术上的进一步发展。40年代讽刺喜剧在人性深度上整体性的薄 弱、对于文化反省主题的漠视以及某些创作雷同化的倾向,都莫不与此有关。
当政治性原则逐渐被认为是所有讽刺喜剧应当遵奉的首要原则的时候,它必然也会影 响到人们对于喜剧本身的看法。在这种愈来愈纯化的喜剧本体观看来,喜剧不仅仅是“ 能够”表现重大的社会政治主题,而且是“必须”表现这样的主题。在政治性讽刺喜剧 为中国现代喜剧艺术赢得了一系列成功和荣耀的时候,这种观念的局限性是不大会引起 人们重视的,但是一旦中国社会进入了政治清明的新的历史时期,它却很可能给喜剧的 发展带来足以致命的损伤。喜剧既然被理解为政治斗争的一种工具,它在一个人民国家 中必然会失去昔日的用武之地。1949年以后27年间中国喜剧艺术的曲折历程清楚地说明
了这一点。
政治性讽刺喜剧的出现和发展有着充分的历史依据,在一个社会矛盾需要政治总解决 的时代情况尤其如此。但是,政治性讽刺喜剧存在的合理性不应该、事实上也不可能取 代其他类型喜剧存在的合理性。喜剧艺术固然不应推诿自己在推动社会政治进步方面的 高尚使命,同样它也没有任何理由放弃自身在全面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和使生命畅达方面 的神圣责任。中国喜剧艺术的繁荣始终呼唤着那种多元互补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