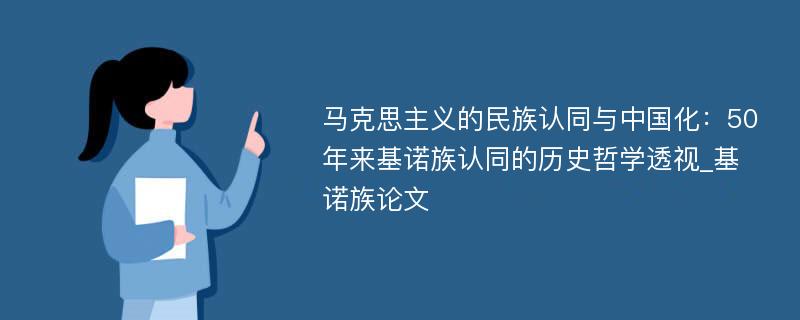
民族识别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诺人识别50年的历史哲学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视角论文,哲学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09)06—0005—04
笔者识别基诺人始于1958年,至今半个世纪,不断反思其学理,最终归结为一点:民族识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例。
一、基诺人识别过程的回顾与识别后的学理认知
拙作《基诺人识别40年回识——中国民族识别的宏观思考》[1](以下简称《40年回识》),其中有对基诺人识别过程的详细说明。这里再做以下概述。
1958年10月,笔者因编写《彝族简史》的需要对基诺人进行民族识别,时任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暨云南省少数民族历史研究所领导的侯方岳所长对此十分重视,行前谆谆告诫:多民族云南存在多种社会形态,独有彝族同时存在奴隶制与农奴制,加上有很大可能是彝族一个支系的基诺人属原始社会,那么,他一个民族中就同时存在着完整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这不仅可使彝族历史大为丰富,更对中央某领导提出的写一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的“续编”大有好处。换言之,此行的成果与马列经典有关。当时本人深感任务重大,难以胜任,侯所长则多方勉励,并指示笔者到西双版纳后多向民族识别的专家林耀华先生求教。林先生是学界前辈,1953年就曾率队对云南族籍未定的少数民族进行大量的识别工作。故笔者到西双版纳后曾恳请并得到林先生多方指点,其要点是:必须以斯大林的民族构成四特征为依据。笔者据此开始了第一次识别工作,并收集回了部分资料。但当时在景洪主持编写《傣族简史》的林耀华(时为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与方国瑜(时为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二位先生听了我第一次调查汇报后,认为没有在识别问题上提出倾向性意见,建议再进行第二次识别。为此我又背着行李登上了基诺山,调查时间是1958年11月至12月间,结果写了题为《社会主义改造前后攸乐(基诺人的音译异字)山的攸乐人》的调查报告,近3万字,但仍没有明确回答基诺人是否属于彝族支系的问题。尽管此次仍未能完成识别基诺人的任务,然其文化特点却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1964年完成《彝族简史》二次铅印送审稿后,我返回北京本单位——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接着是两次“四清运动”与文化大革命,自无识别基诺人的可能。但粉碎“四人帮”不久后就时来运转,1977年四川民族研究所李绍明同志(绍明兄1958年编写《彝族简史》时就与笔者友好相处,可谓无话不说,近已仙逝,特此悼念)邀我参编《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一书,当包括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等领域近20位学人的编写组来昆时,我随即提出基诺人的识别问题,得到认同并经云南省有关方面认准,编写组改为基诺人识别组,并立即实施。结果,识别组认定基诺人具备了单一民族的条件,决定由我写出识别报告上报。由此便有1979年国家对该报告的确认,基诺人随之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第56个兄弟。
1958年是全国“大跃进”的时代,对于当时进行的基诺人民族识别,笔者也就自然认为,它是属于“大跃进”的一部分。其实,本人那两次的整个调研,也体现了那一个时代的特有精神。如果把这一工作再具体化,正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民族识别”条开宗定义所说:“指民族成分与民族名称的辨别。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贯彻民族政策而进行的一项工作。”[2]笔者对民族识别的这一基本认识,一直维持了大约30年。
至改革开放10年后的1988年,我才发现民族识别中的一些新问题,再经10年的学识积累,1997年终于发表了《40年回识》一文。它发表不久即被10余家丛书转载,其中授予“特等奖”的一家还概括了其4点新意:一是民族识别可以分为两个过程,先是识别学人调研后写出识别报告,此为研究行为,后是国家主管方对识别报告的确认,此为决策行为。二是偶然性机遇与学人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基诺人的识别即可为例。三是提出“刚性理论”向“柔性理论”转化的建议,如不宜把“人”与“民族”这两个在个性与共性上互通的概念以法规形式刚性区别等。四是提出异于前人的民族识别定义:“它是20世纪50至70年代完成的一项民族工作方面的政治性学术任务。”[1]以上观点,已以不同形式被社会采纳。
《40年回识》发表至今已12年,借助50年的宏观视角,笔者又有了如下新知:民族识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例。
二、民族识别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例的缘由
其一,中国的民族识别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依据,但在实践中又对它进行了根本性修正。
民族识别以马列主义理论为依据,这从上述笔者1958年奉命识别基诺人时的领导交代,民族识别专家林耀华先生的指导,以及笔者识别基诺人的全过程中,已可见其一斑。前引《百科全书》“民族识别”条更明确地指出:中国民族识别“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为依据。”对于这一点,在20年前有关民族识别的论述中,并无异议。而其理论依据的基本著作,是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的以下名言:“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3](P294)此作1912年开始发表,曾得到列宁的高度评价,在20世纪中期的中国被视为民族定义的马列主义经典。这一点,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的民族识别报告中有明确的体现。即使在1977年笔者代表识别组写的基诺人识别报告中也有如下以下结论:“基诺人有自己的共同语言、共同居住地域,在经济和文化习俗上有一定特点,也有自己的共同心理状态。”也足以证明,它仍然是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一种研究性仿制。
但中国民族识别中并没有硬套“民族四特征”,包括民族识别方法的许多特点,如名从主人、尊重少数民族意愿等,论述多多,此不复述。以下应着重指出的是:中国在民族识别中,曾对斯大林民族定义进行了根本性修正。其明显的事实,是斯大林在上述《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的另一断言:“民族不是普通的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3](P300~301)显而易见,这一论断无疑是为民族设立的门槛,没有进入这一门槛的人们,自然就不具备民族的基本条件。如果根据这一论断,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并无资本主义上升期,因此,不仅我国的少数民族达不到民族的条件,就是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汉族也不够条件。但值得称赞的是,中国民族识别中没有固守经典而是径直跨越,使处于封建制、奴隶制甚至原始村社的人们,皆可被识别为民族。这应是对马列主义经典的根本性修正,也可称之为否定性超越。
上世纪50至80年代的民族学人对马列经典的重视,是今之年轻学人难以想象的。即使基诺人被国家确认为单一民族后,笔者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并未停止,因为它既然是一个民族,必有民族形成的时限,因此就有了拙文《基诺族族源问题试探——兼论族源和民族形成的上限》[4]。还因为此文将基诺族史实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相结合,认定基诺族形成的上限在“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这就与牙含章先生的民族形成上限于蒙昧时代“高级阶段说”发生了矛盾。由此便有发表于《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四期的《关于民族形成的上限问题的两封来信》,其中一封是牙含章先生致该刊编辑部并笔者的信,一封是笔者的复函。正是这两封信,涉及了马列经典作家的许多具体论述,称得上是民族形成上限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辩论。牙先生是“中国当代民族问题理论家和宗教学家”[2](P486),他明确且严肃地指出了拙文的理论缺失,认为它“涉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形成的一个带有原则性的理论问题”,“不符合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基本观点”。由于经典作家在民族形成上限问题上并无系统确切的论述,我又联系基诺族资源对某些经典论断相解说,亦言之有据,加上基诺族已被国家确认,故牙先生也就高抬贵手,基诺民族形成上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便随之顺利解决。而笔者在《基诺人的民族识别报告》中还认为,基诺人社会属于原始农村公社,这显然又是对民族形成经典门槛的一种否定。由此可见,既以马列主义理论为依据又根据国情对它进行根本性修正,是民族识别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例的首要原因,也是它的首要基本特征。
其二,历史意义巨大而深远。
习惯认为民族识别仅限于少数民族,其实也不尽然,因为对于多民族的中国来说,首先需要超越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期经典门槛的,是作为国家主体民族的汉族。为了完成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人文社科界展开了一场汉民族形成问题大讨论,有关文字数不胜数,观点与角度也多种多样,其中最符合经典的观点是:汉族是“部族”而非民族。至1954年,具有一定权威性的中共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研究》,1954年第三期)一文发表,不仅以丰富的史实与经典论断相结合,且具有一个巧妙的角度,说明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此后虽仍有异议,但“范说”逐渐成为学界的主流。这就是汉民族形成问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从50年的宏观视角而言,这一争论本身,也是经典学理层面上的一种民族识别。汉族形成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尚且如此,中国少数民族形成问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就更可想而知。直到1962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牙含章先生《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翻译情况》、《“民族”一词的译名统一问题的讨论》两文,提出“民族最初是由部落发展成的”、蒙昧时代高级阶段的“蒙昧民族”等系统观点,中国少数民族形成问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基本解决。
此间还需说明的是,民族识别与当时的世界历史大背景密切相关。20世纪50至70年代的中国民族识别,正处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冷战时期,因此,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有民族识别,资本主义阵营绝无民族识别,其根源就在于此,这正是中国民族识别体现的特有本色。至于民族识别的重要性,首在它的政治意义,因为新中国建立后面临400多个自报族称,不难设想,对其族属的妥善识别,事关国家的安定团结。为此,中国民族识别的参与学人具有全国性规模,如果加上汉民族形成问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讨论,则涵盖了整个中国的人文社科界。而以民族识别的时间而言,从新中国建立之初至基诺族最后被确认为单一民族的1979年,长达30年。故无论从其参与者的规模,还是从其时间延续之长而言,都可以称得上是空前绝后。
民族识别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可分为短期与长期两种。短期指民族识别30年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人文社会理念方面的巨大影响,因为“民族”这一泛化词语经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等的方方面面。其长期的影响,指由民族识别确认的56个民族构成的中国,其历史的影响将延伸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甚至更远。
总之,这两大特征虽出于基诺族识别的个性实践,但它的个性中又具有共性。笔者认为,凡具有这两大特征的实例都可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
三、民族识别范例的理论价值与历史哲学视角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基本理论命题,但成熟的理论常常落后于客观实际,故这两个明确的概念至近几年才开始出现。这两个概念有所区别,然要明确二者的关系,也不那么简单。而本题的中国民族识别,正好为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实例。
从今天的认识角度来讲,以本文的以上具体论述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指的是在民族识别,如基诺人识别过程中,既运用又否定了经典。但尽管笔者在实践中否定了经典设定的门槛,此后却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因故缺乏理论的自觉。直到近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后,又经过一个实践联系理论的过程,才将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联系起来。换言之,笔者50年间在民族识别上的理论联系实际,或在修正马列经典中解决基诺族识别的实际问题,皆可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与认识过程。
不仅如此,笔者还认为它已具备了进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条件。其原因是,本文上一部分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基本特征的具体论证,解决了民族识别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理论联系实际问题,且其个性中具有共性,实践上升到了理论的层次。因此,民族识别犹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桥梁,最终联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并构成了它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正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例的民族识别的宝贵理论价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在理论联系实际中的突破与创新,是一个复杂的实践与认识过程,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近于成熟的宏观理论体系,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上升至理论层次才能与它相连接。作为理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西学,也由此转变为东方中国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不同点。至于它们的共同点,只有一个,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如果从史学的角度分期,以笔者的基诺族识别来讲,可以将它分为两个时段,第一阶段是1958年至1979年,是在既以马列理论为依据又对它进行修正中完成基诺人识别的过程,基诺人识别报告被国家确认就是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成的标志。第二阶段是1979年至今30年,是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演进的探索过程,可谓基诺族识别史的学理完善期。从全国的民族识别讲,1979年前的30年是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成期,1979年至今30年是中国民族识别史的学理完善期。
最后,因与本题密切相关,还需特别说明的是,近20年来有一种否定民族识别以马列主义理论为依据的倾向(以下简称“否定说”),其中的观点之一是:中国“经过识别的56个民族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本质上都是自然形成的人们共同体,我国的民族识别只是对这种共同体存在的一种辨析和确认,而不是在政治上人为地制造民族”[5]。此言在否定人为制造民族说的同时,又过犹不及,将中国民族识别与美国、泰国等世界上一切民族识别之间画等号。因此,它的必然结果就是:既忽略了中国民族识别过程的举世仅有的基本特征,更抹杀了中国民族识别的一个基本事实——以马列主义理论为依据,因为没有这一理论依据就不会有20世纪50至70年代的中国民族识别。此外,“否定说”中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就是否定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其否定的角度也多种多样,以至上溯到沙皇俄国的对外扩张政策,等等,也都是有其学术视角的,故一研究中国民族定义的大作竟感叹:“一个中国历史的局外人,为什么会主宰了他身后几十年的中国的学术?”[6](P23)既然如此,“否定说”谈到中国民族识别时,自不会有对依据马列理论的认同。而其实,斯大林民族定义也是列宁的定义,因为它不但得到列宁的高度赞赏,还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有关,因而它就成为20世纪中国民族识别所使用的基本马列经典。更何况,即使中国民族识别中曾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错误进行修正,它又未尝不是中国民族识别的理论依据呢?尽管几十年后的文章中各有其否定斯大林民族定义的不同视角,但其任何角度都难以与斯大林脱离瓜葛。而笔者拙文的全部论证,都是在说明我国民族识别以马列主义理论为依据这一基本历史事实。
至于对当时作为马列经典的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根本性修正,既有先辈名家们的业绩,更有毛泽东主席1953年的决策性指示与认准。这一切都可以证明,20世纪50至70年代完成的民族识别,就是在既以马列理论为依据又据中国国情对它进行否定性超越中,实践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史事实。今之学人可以从各种视角评说中国民族识别史,但不宜用50年后的现代视角取代历史事实。为此,回顾近60年的中国民族识别史,还可以选择历史哲学的另一种视角:正是斯大林民族定义的错误成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它真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真理,那也就不存在民族识别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这一点,也可以说是本文的基本学理倾向。
收稿日期:2009—09—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