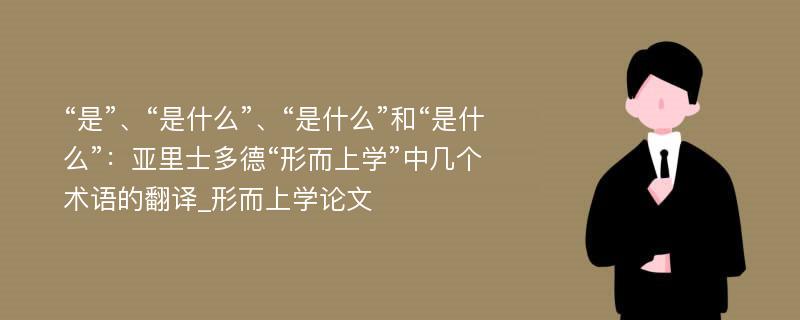
“是”、“所是”、“是其所是”、“所是者”——关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几个术语的翻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里士多德论文,几个论文,形而上学论文,其所论文,术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是由后人编辑而成,经历了中世纪和近现代的翻译和解释。我们自己也有中文翻译著作和研究解释。面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后人的这些研究成果,我感到,若想真正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思想并搞好对它的研究,必须首先注意语言问题。具体地说,我们必须仔细分析和研究其中的einai以及与einai相关的几个概念和短语,因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核心内容主要是围绕着它们形成的。做好这个工作,可以说是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思想的基础。
在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研究中,首先存在着翻译的问题,当然也就涉及到理解和解释的问题。其中最难翻译的是ousia, 它是《形而上学》第七卷(Z卷)主要探讨的问题, 也被认为是《形而上学》主要探讨的问题。与此相关的还有on和to ti en einai,前者是《形而上学》第四卷(Г卷)提出的问题,后者是探讨ousia 时而谈到的问题。 在这几个术语的翻译中, 争议不大的是on , 问题比较多的是ousia和to ti en einai。应该看到,长期以来, 亚里士多德的中译文著作主要是译自英文和德文(当然,近年出版的苗力田先生的译本是译自希腊文),因此,由于在英语和德语翻译中存在着问题,自然给中文的翻译也带来许多问题,因而给我们的理解也就带来许多问题。这里,我想谈一谈几个主要术语的翻译问题。
一
希腊文on是动词不定式einai的单数分词形式, 亚里士多德在使用它时还加上定冠词to。To on 一般被翻译为“being”和“Seiend”,比如:译文1: There is a science which investigates being as being and the attributes which belong to this in virtue of its own nature.(注:The Works of Aristotle,vol.VIII,Metaphysica,ed.by Ross,W.D.,Oxford 1954.)译文2:\Es gibt eine Wissenschaft, welche das Seiende als Seiendes untersucht und das demselben an sich Zukommende.(注:Aristoteles 'Metaphysik,Buecher I-VI,griech.-dt.,in d.Uebers.Von Bonitz,H.; Neu bearb.,mit Einl.U. Kommentar hrsg. VonSeidl,H.,Felix Meiner Verlag 1982,s.123.)英文being是动词不定式to be的分词形式,德文Seiend也是动词不定式Sein的分词形式。因此这些翻译与希腊文是比较接近的。当然,也有例外的翻译。比如科文的翻译如下:译文3:There is a discipline which studies that which is quathing-that-is and those things that hold good of this in itsown right.(注:Aristotle's <Metaphysics>,books г,△,and E,tr.With notes by Kirwan,C.,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p.1.)这里把to on翻译为that which is,与翻译为being显然是不同的。 科文认为,to on是由einai的现在分词加上定冠词组成的。在希腊文中常常有形容词前加定冠词的类似表达,比如the beautiful (字面意思是:那—漂亮的),它可以表示“那个(提到的)漂亮的东西”或“那个是漂亮的的东西”。一般来说,形容词后面要跟名词,而这里的定冠词加形容词的表达却不跟名词,而且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科文认为,“也许是以与这后一种用法相似的方式, 过去一直把亚里士多德的‘ to on’翻译为‘being’(它在单数时一定是一个动名词,即das Sein,而不是分词的名词用法,即不是das Seiende);但是, 尽管希腊文的形容词可以抽象的使用,分词是不是也可以这样使用却是令人怀疑的”(注: Aristotle's <Metaphysics>,books г,△,and E,tr. With notes by Kirwan,C.,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第76页。)。也就是说,一方面,科文认为在being区别不出究竟是动名词用法, 还是分词的名词用法,另一方面,科文怀疑是不是可以在形容词前加定冠词这种用法的意义上理解to on,所以,他要翻译出这里的区别。 这样,他不用being来翻译to on,而且,除了以“that which is ”来翻译“to on”以外,还用“thing-that-is”来翻译不带定冠词的“on”。
应该看到,不论如何翻译,being、das Seiende和that which is至少在字面上都反映出希腊文to on的意思, 因此至少从字面上保持或保留了与它的一种联系。这种字面和意义上的联系对于表达和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中文翻译主要有以下三种:译文4:存在着一种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 以及就自身而言依存于它们的东西的科学。(注:《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译文5:有一门科学,专门研究“有”本身, 以及“有”借自己的本性而具有的那些属性。(注:《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34页。)译文6:有一门学术,它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 以及“实是由于本身所应有的秉赋”。(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56页。)
从这些中译文看,to on被译为“存在”、“实是”或“有”。 我认为,这里的主要差异在于,至少从字面上我们看不出“存在”和“有”与to on的联系,而“实是”毕竟还保持了这种联系。问题是, “存在”的翻译最为普遍,也是我们的一种最主要的理解;“有”的译法虽然不多,但是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也可以看到它的延续;而“实是”这种译法不仅少,在文献中被采用的也少。因此,一个很直观的问题是,中文翻译,比如“存在”和“有”,是不是有助于我们对to on 的理解,特别是,上面这段话一般被认为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形而上学这门学科的性质的说明,如何翻译就显得更为重要。
二
希腊文ousia 是由动词不定式einai 的现在分词的阴性单数形式ousa而形成的。它一般被翻译为“substance”,“Substanz ”(实体),或“essence”,“Wesen”(本质)。这两种翻译都有很长的历史。
据说(注:欧文斯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是的学说》(Owens, J.: The Doctrine of Being in the AristotelianMetaphysics,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57 )是一本重要著作,它系统考察了亚里士多德使用的einai 这个概念以及与此相关的概念,特别是它探讨了这个概念在中世纪时期的用法和发展以及与此相关的思想,阐述了这个概念的发展史。我这里的论述主要就是根据它,参见其中第4章。),substance和essence 这两个英语翻译都来源于拉丁文,而在拉丁文中,与ousia对应的最古老的尝试用语是“essentia ”和“queentia ”。 这两个词都遵循了希腊词中所见的词法形式。
“queentia”似乎是由“queens”形成的,即它依循由queo而来的形式。“essentia”基于一个假定的分词“essens”,而这个分词是由“esse”形成的,就像 patiens是由pati形成的。最终,queentia没有留存下来,而essentia保留下来了,是人们接受的ousia的拉丁语表达。 欧文斯认为,如果记住essentia的词法形成过程,那么它相当准确地表达了希腊文的ousia。
大约在公元4世纪的时候,substantia这个词开始经常出现, 它是essentia的一个同义词。在有些文献中,substantia非常得体地表示它的词源使人想到的东西——某种“处于”性质、名称或偶然特征“之下”的东西。而在另一些文献中,它的意思更近似于事物的本质或永久的特征。这样,substantia和essentia被当作同义词使用,不过,它们还是有区别的。比如在哲学和逻辑著作中,人们使用substantia,而在神学著作中,人们使用essentia。据欧文斯说,波依修斯在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著作的注释中一直用substantia翻译ousia。 通过他的逻辑注释,亚里士多德在中世纪的形成时期变得非常出名。结果,substantia成为经院学者所接受的亚里士多德的ousia这个词的翻译, 由此这个词也转变为现代语言的哲学词汇。
随着亚里士多德著作英文版的问世,“substance ”被牛津译者正式用来翻译ousia,因而成为比较普遍的翻译。 但是在一些不便于使用“substance”的地方,英译者们也常常使用“essence”。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喜欢用“essence”作为正规的翻译。特别是德文译者, 他们似乎更愿意使用与 essentia 相应的“Wesen ”,
而不特别喜欢用Substanz。值得注意的是, 在经院哲学时期, 还出现一个拉丁文术语entitas。这个词的演变是这样的:动词不定式esse的分词形式是ens,由这种分词形式再变成具有抽象名词词尾的名词,就成为entitas。 因此,这个词是以抽象派生的方式产生出来的。欧文斯认为“它与是的直接关系表达得非常清楚”(注:Owens,J.:The Doctrine of Beingin the Aristotelian Metaphysics,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57,p.72.)。
16世纪末发现了使用英语“entity”这个词。它可以既指抽象的是,又指具体的是,并且同样适用于本质和存在。在17世纪上半叶,发现了它表示一个个体和表达一事物的本质性质的用法。它像一般接受的是的范围那样宽泛。 它是一个中性词, 完全是非承诺的。 今天, substance、essence和entity都是本体论讨论中的重要概念,也是亚里士多德思想讨论中的重要概念。但是在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这部著作的讨论中,特别是在关于其中ousia的翻译和讨论中, 用得最多的是substance和essence。当然对这两个概念,人们也是有不同看法的。
欧文斯认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ousia乃是是的首要情况。 所有其他是者都依赖于ousia。所有其他东西都由它命名为是。 它是“事物中是的原因”。它带有对“是乃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此外,ousia又是有歧义的。因此,对它的翻译“必须显示出ousia与是相关的首要作用,然后能够依照正确的比例关系表示由这个希腊词所表示的所有不同事物”(注: Owens,J.:The Doctrine of Being in the Aristotelian Metaphysics,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57,p.66.)。从词法的角度说,ousia 是从表示“是”的希腊动词派生出来的。因此,一方面,它的意思乃是与是这个概念相联系的,另一方面,从ousa到ousia,词尾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起一种作用, 这就是使意思比“是”这个分词用作名词时更加抽象。从这一点考虑 , 应该在tobe的分词being再加一个抽象名词的词尾ness,从而构成英语中与ousia相应的词Beingness。但是,欧文斯认为,ousia常常表示具体的东西,比如一个“动物”或“一个植物”或任何简单物体都是一个ousia; 而且ousia在第一哲学中还总是指高度个体的东西;此外,ousia还表示质料,而在这三种情况,使用Beingness这个英语词都是不合适的。因此,尽管英语Beingness在词法上与ousia 最近, 但是它与《形而上学》中ousia的通常的几种意义一点也不相符,因此不能用来作ousia的翻译(注:Owens,J.:The Doctrine of Being in the
Aristotelian Metaphysics,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57,pp.66—67.)。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substance并不是英语中与ousia最相近的词。
欧文斯还指出,人们发现“substance”这个英文词作为ousia这个希腊词的翻译是不令人满意的。 因为“ substance ”没能表达出与由ousia所表示的是的直接关系。此外,它可能是非常引人误解的。 由于洛克的影响,“substance ”在英语哲学用法中非常强烈地使人恰恰联想到它的词源所表示的东西。它变幻出某物“处于”其他某物“之下”的观念。这样一种看法必然歪曲亚里士多德的ousia, 并且最终像在洛克的著作中那样使偶性具体化。 因此,
在现代哲学的背景下,substantia更容易引起曲解。因为它的词源阻碍它传达希腊文ousia 所表达的概念,而当与一个非亚里士多德、甚至反亚里士多德的参考框架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情况就更为严重。Substance 无法传达亚里士多德使用的ousia这个词的首要意义。
帕兹希与欧文斯的观点大致相同,但是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他认为,当亚里士多德询问ousia的时候, 他的意思常常是询问某种至少在前苏格拉底时期就已经含蓄地被询问过的东西。在帕兹希看来,似乎最迟在柏拉图时期,柏拉图已经把ousia这个表达引入了哲学, 柏拉图的追随者也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正像人们能够看到的那样,亚里士多德把柏拉图的回答看作是与他自己在Z 卷中发展的理论相对抗的看法。这一历史背景是重要的。但是“当人们用Substanz来翻译ousia 并且在亚里士多德的Substanz的意义上理解它时,这一重要的历史背景被搞得模糊不清。因为前苏格拉底时期和柏拉图时期都没有人询问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Substanz ”(注: Frede, M./Patzig, G.,C.H.,Aristoteles'Metaphysik Z',Text,
Uebers.u. Kommentar,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Muenchen 1988,Band I,s.36.)。帕兹希的这一论述基于对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和《形而上学》的研究,他认为,亚里士多德在这两部著作中都论述了ousia, 思想却不同,而使用Substanz这个概念,只适用于在《范畴篇》所涉及到的一种观点,却无法反映《形而上学》Z卷中对这种观点的根本修正。 因此他在翻译和研究中保留了ousia这个词。
关于essence 这个词, 欧文斯认为, 它具有直接来源于动词“tobe”的拉丁文形式的优越性,但是也有缺点。这个词在现代人听来好像表示某种与“存在”(existence)的对立。在《形而上学》中, 在是的用法中没有任何这种对立的痕迹。他指出,einai 既表示“是”(tobe),又表示“存在”(to exist),而且希腊文只有一个动词表示英文的“to be”和“to exist”以及它们的派生形式。 没有任何东西表达出“essence”与“existence”的对立和这样的反差,因此“存在一种危险:‘essence’可能是一个指示错误方向的符号。 在第一哲学中有还是没有‘本质’与‘存在’的区别,必须从文本中确定。在对一个这方面完全中立的希腊术语的翻译中,不应该悄悄引入一个指向这种区别的符号”(注:Owens, J.:The Doctrine of Being in theAristotelian Metaphysics,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57,p.71.)。 鉴于这一点, 有人认为可以不加区别地以“to be”和“toexist”来翻译这个希腊动词和它的派生词,而罗斯则明确地说, 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表示存在的“是”不能与系词相区别,尽管可能有一种逻辑区别。看到这些明显的反对意见,一种隐含着本质与存在之间对立的翻译就会非常有害(注:Owens,J.: The Doctrine of Being in the Aristotelian Metaphysics,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57,pp.70—71。)。
此外,在牛津翻译和其他标准翻译中,“essence ”还被用来表达专门的亚里士多德以einai表示占有者的与格, 以及相应的短语to tien einai。这种用法不必一定与“essence”作为ousia的翻译的意义相冲突。这两个希腊文词组在它们的首要情况下可能表示完全相同的东西。但是它们在次要的情况下肯定是不同的。Ousia 能够表示一事物的质料,而to ti en einai从不这样表示。不应该从一开始就认为这两种意义肯定是同一的。它们可能代表来自两种不同观点的看法,即使它们最终都达到系统的目的。关注亚里士多德的表达形式要求我们在翻译中保留不同的表达方式。即便选择另一种与“essence ”不同的方式来翻译与格的习惯表达,也不能忽视这个词在标准翻译中这种意义上的通常用法。必须假定这个词的意义或多或少是固定的。它为翻译ousia 的其他用法将造成混淆,至少从亚氏的表达形式来看是这样。
在中文翻译中,一般采用的翻译是“实体”,但是也有不同意见。汪子嵩先生认为,“substance这个词,现在通常译为‘实体’, 容易被误解为具体实在存在的物体”,因此他主张把它翻译为“比较抽象的‘本体’”(注:汪子嵩:《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1页注释。)。我认为, 汪先生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不论是“实体”还是“本体”,都比较接近英文的substance,而与ousia的意思还是有不小距离的。
三
希腊文短语to ti en einai是亚里士多德在探讨和论述本体时使用的一个重要表达式。对它的理解和翻译也非常重要。根据史学家的研究,翻译这个短语有两个难点。一个难点是关于这个句子的结构,另一个难点是它的过去未完体(注:讲英语者称它为“philosophical imperfect”,参见Ross,W.D.:Aristotle's Metaphysics, a revisedtext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vol.I Oxford 1924,p.127; 讲德语者称它为“philosophisches Imperfekt ”, 例如参见Frede,M./Patzig,G.,C.H.,Aristoteles'Metaphysik Z',Text,Uebers.u.Kommentar,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Muenchen1988,Band I,s.19。字面的意思是“哲学过去时”或“哲学未完成体”。本书“过去未完体”这一术语是采用苗力田先生的意见,参见苗力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笺注》,《哲学研究》1999年第7 期。)这种时态,即这个短语中使用的en。罗斯认为,ti en einai 是对“是如此这般的乃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 这个短语乃是tienaotoi、to aimati einai这样的短语的概括;而对它的过去时,罗斯认为,按照一般习惯,这里似乎应该是ti estin einai 才对(注:罗斯还谈到人们关于这个问题做出的三种解答。其一,en被说成是“哲学过去时”,指论证中前面陈述的某种东西。其二,可以把这种过去时看作是代表持续性。其三,可以认为这种过去时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形式在其特殊质料中体现之前而存在的学说。参见Ross,W.D.: Aristotle'sMetaphysics,a revised text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vol.I Oxford 1924,p.127.)。塞德尔认为,从语法结构上看, toti en einai 这个概念的完整表达是:to ti en to toi ekastoieinai,它的字面翻译是:“Was war das fuer jedes Einzeldingwesensmaessige Sein? ”(每个个别事物根据本质而是乃(过去)是什么?)他还指出,“严格地说,在希腊文中,由于前面有一个冠词,这个问题被再次名词化, 这在德语中是无法模仿的”。 (注:参见Aristoteles' Metaphysik,Buecher I-VI,griech.- dt.,in d.Uebers.Von Bonitz,H.;Neu bearb.,mit Einl. U. Kommentarhrsg.Von Seidl,H.,Felix Meiner Verlag 1982,s.XXXI.)关于过去时,塞德尔认为,en这个过去时表达了所问的本质性的无时间的持续,它现在是什么,过去就已经总是什么这个问题,即“……(过去)是什么?”, 而且ti en 还使人们回想起苏格拉底一柏拉图式的问题:ti estin,这个问题引向每个事物的普遍什么(Washeit )(注:参见Aristoteles' Metaphysik,Buecher I-VI,griech.- dt.,in
d.Uebers.Von Bonitz,H.;Neu bearb.,mit Einl.U.Kommentar hrsg.Von Seidl,H.,Felix Meiner Verlag 1982,s.XXXI.)。帕兹希认为,to ti en einai 是一个缩短的表达, 完整的表达大概是:ti entoi anthropoi anthropoi einai。他指出, 可以在“哲学过去时”的意义上理解en,然而它在德语中,尤其是在科学语言中没有相应的表达,因此他认为,用“wesenswas”来翻译,似乎是完全无法理解的; 而用“das wesentliche Sein”、“Wesensbegriff”和“Sosein ”等短语来翻译,又“过于普通”,他建议把to ti en einai 翻译为“Was es heisst,dies zu sein”(注:Frede,M./Patzig, G., C.H.,Aristoteles'Metaphysik Z',Text, Uebers. u. Kommentar,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Muenchen 1988,Band I,s.19.)。帕兹希批评的这几种翻译在德语文献中是比较常见的,他提出的翻译的字面意思是“是这,意谓什么”或“什么叫作是这”,通俗地说,它的意思就是:“是什么,就是什么”。
关于to ti en einai,苗力田先生与罗斯的观点差不多,肯定了“这一词组是从日常生活来的,它就是要回答:何以事物是如此如此的样子”(注: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页。),他提出中文应该用“是其所是”来翻译。苗先生也很重视这里的时态的问题,对此亦有论述,他认为“古希腊语重体不重时,这里ti en不在于其过去是, 而在于永完不了的所是”(注:苗力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笺注》,《哲学研究》1999年第7期,第43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翻译《形而上学》时, 苗先生不无遗憾地指出,汉语中没有时态变化,“万难对未完成体和不定式做出区别”(注: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第33页。),而在后来发表的论文《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笺注》中,他却认为,“在对亚里士多德关于ousia的这一原理的转译中, 无时态变化的汉语却独占了优势。其所是的是,过去、现在、永远的将来同样地是”(注:苗力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笺注》,《哲学研究》1999年第7期,第43页。)。苗先生的看法显然是有变化的。 但是不管怎样,我觉得苗先生提出的“是其所是”这个翻译是非常好的,它与帕兹希的翻译也非常接近。所以我建议采纳这个翻译。
四
最后,还应该说一下ti esti(n)。这个短语在亚里士多德的其他著作中也出现, 而在《形而上学》这里, 主要是在第七卷解释和说明ousia的时候,起非常重要的作用。这里, 亚里士多德使用了两个词来说明ousia,一个是ti esti,另一个是tode ti。后者指个体, 相应于《范畴篇》中所说的“第一实体”;而ti esti 大致相应于那里的“第二实体”,它的英文翻译一般是“what a thing is”或“essence”,德文翻译一般是“Was etwas ist”或者“Was”。
罗斯认为,一个ti esti乃是某物的ti esti,即对“这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而且无论这某物是一个个体还是一个普遍的东西,它的本质只能被陈述为一种普遍的东西或一种普遍的东西的组合。在他主编的翻译中,这个短语被翻译为斜体的“what”,由此也说明,它表示的不是个体,而是种和属。 此外, 罗斯还认为, ti esti 与ti eneinai有时候是有区别的, 有时候则是在相同意义上使用的(注:参见Ross,W.D.:Aristotle's Metaphysics, a revised text with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vol.I Oxford 1924,p.159—171。)。帕兹希则认为,把ti esti翻译为“Ein Was”或“Was eines Dinges”“与希腊文本相距太远”(注:Frede,M./Patzig, G.,C.H.,Aristoteles' Metaphysik Z',Text, Uebers. u. Kommentar,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Muenchen 1988,Band I,s.20.),他主张把它翻译为“Was etwas ist”,而当对象已经确定的时候, 把它翻译为“Was es ist”。这里,前一个翻译的意思是“某物之所是”,后一个翻译的意思是“这(东西)之所是”。我认为,帕兹希的观点有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要把这个希腊文短语中的那个“是”(esti)翻译出来,至于它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则可以进一步讨论。比如说,一事物之所是乃是它的本质。而罗斯的翻译则直接突出了“什么”,尽管这“什么”乃是对问题的回答,尽管他还认为ti esti与ti en einai有时候意思是一样的。
在中文翻译中,我们有“什么”和“是什么”这样的翻译。苗力田先生主张后一种翻译。他认为,“这个是什么,既可当作谓词,又可当作所以是的是,当作本质和形式。在作谓词时就是一般。……但在它不单纯是表示是什么,而是表示其所以是什么to ti en einai的时候,这个ousia就是在原理、 认识和时间方面的第一”(注: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笺注》,《哲学译丛》2000年第1期,第78页。)。我觉得,苗力田先生的解释与罗斯的说明大体上是一致的,但是他提出的这个翻译显然比英文的“what”要好,因为它反映出ti esti 这个短语中的“esti”所表达的那个“是”。实际上,“是什么”与帕兹希提出的翻译是一致的。
五
以上我们考察了关于“to on”、“ousia”、“to ti en einai”和“ti esti”这几个希腊文术语的翻译。如果总结一下, 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翻译与希腊文是有距离的!具体地说,“to on”、“ousia”、“to ti en einai”和“ti esti”这几个希腊文短语是不同的,表达的意思也有一些区别,但是无论它们有什么不同,它们的共同点是明显的,即它们都与希腊文动词不定式einai有关, 因为这一点是仅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来的。相比之下,在英文和德文翻译中,有些术语还保留了与动词不定式的联系,即从字面上还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但是有些翻译,比如“substance”、“essence”、“Wesen”、“Wesenheit”、“Was”等等, 这样的联系就不大看得出来了(细看起来,从essence和Wesen等还可以看出这样的联系,但是从substance和Was肯定是看不出来了)。在中文也是同样,比如“存在”、“实体”、“本体”、“本质”等等,我们根本看不出它们与“是”的联系。在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时候,我们固然可以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有这样那样的意思,表达了这样那样的思想,但是对于这些关键而重要的术语的翻译,保留字面的联系与不保留字面的联系,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今天,亚里士多德的研究者们似乎有一种倾向,这就是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保留希腊文的原意,包括其字面的意思,甚至不惜直接使用原文,这一点在帕兹希的著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我想,这样的做法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因为我们使用的语言——汉语属于与印欧语系完全不同的语系,其语言特点本身与印欧语系的语言相距甚远。且不论我们的思想文化传统与西方有什么不同,有多大的差异,这样的语言至少会在我们对思想文化传统的表达方面造成一些差异,至于这差异会有多大,则需要我们在研究中仔细体会。欧文斯在论述关于ousia的翻译时认为, 对这个词的英语翻译应该有四条标准:第一,不隐含有利于任何在亚里士多德以后形成的是之理论的偏见;第二,在形式上比“是”更抽象;第三,能够表示个体,包括具体的和非构成的;第四,在英国人听来表达了一种与是的直接关系(注:参见Owens, J.: The Doctrine of Being in the AristotelianMetaphysics,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57,pp.71—72。 )。不论这四条标准是不是科学,是不是有道理,是不是被广大学者所接受,我认为,至少有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和借鉴的,这就是其中三条都涉及到“是”的问题,都与“是”有关。
关于我们这里讨论的四个术语,余纪元提出如下译名:是(to on),本是(ousia),恒是(to ti en einai),是什么(ti esti)(注:参见余纪元:《亚里士多德论ON》,《哲学研究》1995年第4期, 第72页。)。我认为这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按照我的体会,我们可以如下翻译:to on ousia to ti en einai ti esti是(是者) 所是(所是者)是其所是所是者在我看来,采用“是”,困难主要在于不容易区别对象语言和元语言。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采用“乃”、“所”、“之”等虚词来解决。还有一个困难,这就是外文中有时候“是”不加任何修饰,比如“上帝是”,这样的句子如果翻译成“上帝存在”似乎就不会有问题。但是,是不是真的没有问题?这个问题这里不进行讨论。我只想指出以下几点。首先,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一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他对只使用“是”这个词是有专门说明的,他认为这是“纯粹的是”。其次,关于上帝的大量讨论主要来自中世纪,因此像“上帝是”这样的句子不仅有其自身含义的问题,而且涉及“是”这个词自身的发展演变的问题。第三,不加任何修饰地使用“是”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因此,“上帝是”、“我思故我是”这样的翻译虽然好像怪了一些,其实恰恰也是有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