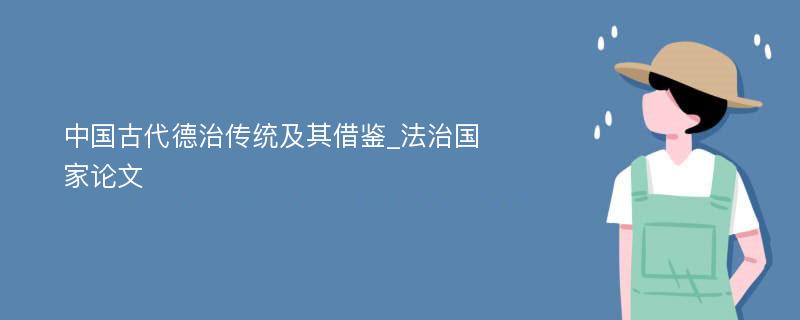
中国古代德治传统及其借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治论文,中国古代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古代德治传统的内容
1.要求统治者以身作则,注意修身和勤政,“以德配天”,“以德服人”,充分发挥道德感化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对“天、地、君、亲、师”的崇拜和敬重,反映着古人对社会秩序化即国泰民安的追求,是中国人传统信仰的最高、最集中的体现。西周统治者从殷鉴中看到“乱罚无罪,杀无辜”的亡国教训,为了走出“王命靡常”的阴影,提出了“以德配天”的思想,即通过“敬德”、“明德”,以争取长久“配天”的资格,最早将德与统治者权力取得的合法性相联系。
儒家经典确定“以修身为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政治纲领,在理论上明确了以建设家族伦理作为实现王道政治的基石和始点的思想。儒家维持“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礼记·大学》云:“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论语·颜渊》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子路》认为,当权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因此“为政在人”,故“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教育广大官吏要克己奉公,成为廉、明、慎、勤的典范,始终是中国古代统治者集团治国的一项基本工作。
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中,秦国统治者要求官吏“廉而毋刖”,“强良不得”,“君怀臣忠,父慈子孝”;以“五善”(“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作为行为准则。
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在盐铁会议上,儒生们针砭盐铁官营政策同时,尖锐地批评了吏治腐败现象,提出了以下思想:首先,强调良吏治国的作用。良吏可贵之处,在于能够通过教化实现犯罪预防,《盐铁论·申韩》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贵良吏者,贵其绝恶于未萌,使之不为非,非贵其拘之囹圄而刑杀之也”。其次,任人唯贤才能事有成效,《盐铁论·刺复》谓:“任能者责成而不劳,任己者事废而无功”。再次,强调高级官吏的表率作用。高官在整肃官风、为民解忧方面负有重大职责,《盐铁论·刺权》云:“夫食万人之力者,蒙其忧,任其劳。一人失职,一官不治,皆公卿之累也”。高官个人是否廉洁,在社会生活中必然开风气之先。《盐铁论·疾贪》认为,“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故贪鄙在率不在下,教训在政不在民也”。
在《贞观政要·论择官第七》中,魏征提出以“六正”、“六邪”向官吏晓之以理,所谓“六正”,即圣臣、良臣、忠臣、智臣、贞臣、直臣。所谓“六邪”,即具臣、谀臣、奸臣、谗臣、贼臣、亡国之臣。唐太宗经常以隋朝灭亡的教训激励自己及百官勤政廉政。在《贞观政要·论贪鄙第二十六》中他还指出,赃官虽未被揭发,却因害怕败露经常忍受精神折磨;而一旦东窗事发,不仅本人丧命,还将给子孙后代留下耻辱:“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
宋朝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颁布了《诫谕百官辞》。根据文、武官员的不同特点,分别规定了“文七条”和“武七条”。与朝廷加强对官员诫谕相呼应,一些官员纷纷撰写官箴,从官员的从政品德和技术两个方面,对官员提出劝诫。
元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纂集的《吏学指南》一书,是流传甚广的一部入仕启蒙教材,其中《吏员三尚》高度集中了古代的德治经验,提出“尚廉”、“尚勤”、“尚能”的思想。
历任县尹、礼部令史、行御史台中丞等职的张养浩在其《牧民忠告》一书中提出了许多值得借鉴的德治思想:首先,其谆谆告诫官吏过好“家庭关”,在《上任第二·禁家人侵渔》中,他提出“居官所以不能清白者,率由家人喜奢好侈使然也”。而一旦东窗事发,昔日为之谋取不法利益的亲友,如“妻妾、子孙、朋友,皆不能我救也,曷若廉勤乃职而自为之为愈也哉”。其次,他提出治吏应严于治民。官吏是皇帝统治的人格化工具,是介于君与民之间的重要一环。皇帝通过庞大的官僚机器实施统治,因而国家及皇帝的治理便首先是对官吏的治理,其次才是对民众的治理,可以说,治民的先决因素是治吏,因而有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政治信条。再次,他认为能否铲除地方恶霸的关键取决于官吏本人的品行,《宣化第五·戢强》云:“夫豪强之所以敢横者,由牧民者有以纵之也。何也?与之交私故也。苟绝其私,可不动声色而使其胆落。”《御下第四·威严》认为,为官只有以身作则,严于律己才能避免奸吏得逞,“欲其有所畏则莫若自严,欲其不为奸则莫若详视其案也。所谓自严者,非厉声色也,绝其馈遗而已矣。所谓详视其案者,非吹毛求疵也,理其纲领而已矣”。第四,他反对不教而诛,提出让高级官吏懂得修身更是首要之事。《庙堂忠告·修身第一》云:“惟善自修者,则能得其所荣;不善自修者,适足速其辱”。所谓“善自修”是“廉以律身,忠以事上,正以处事,恭慎以率百僚,如是则令名随焉,舆论归焉,鬼神福焉,虽欲辞其荣,不可得也”。所谓“不善自修”则是“徇私忘公,贪无纪极,不戒覆车,靡思报国,如是则恶名随焉,众毁归焉,鬼神祸焉,虽欲避其辱,亦不可为也”。
明、清两代同样重视对大臣进行行政伦理教育,在《明太祖实录》中,朱元璋经常劝谕大臣,治人必先自治,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勿徒拥虚位,勿假公济私,应保持晚节。“人处富贵,欲不可纵,纵欲则奢;情不可佚,情佚则淫,忧危来之”。海瑞认为,为官要以“敬”为本,即应当严于自律,保持节操,其基本内容是“廉、明、慎、勤”。在海瑞看来,一个人有志于做官,无非是出于恻隐和义愤,能够出仕做官仅仅是取得了为国尽忠、为民办事的机会。人们如果为了牟利,完全可以选择农、工、商等职业;而做官就应当排除一切利己的动机。[1](P163)在《清圣祖实录》中,康熙皇帝则要求大臣在廉政方面作出榜样:“大臣为小臣之表率,京官为外吏之观型。大法则小廉,源清则流洁,此从来不易之理。大臣果能精自乃心,恪遵法纪,勤修职业,公而忘私,小臣自有顾畏,不敢妄行”。
需要指出的是,忽视常人都有的趋利避害的本性,仅靠道德觉悟解决官吏廉政勤政问题过于理想化。在制度建设上,中国古代强调德治必须以法制为依托,出礼则入法,儒家实际并不否认法的作用,《孟子·离娄上》曰:“徒善不足以为政”,《韩非子·备内》云:“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因此,在古代惩贪立法中,重典治吏是一项贯穿始终的重要方法,对官吏犯罪的法律惩罚重于常人。只要官吏有贪污受贿的行为就构成犯罪,而不论数额的多少和枉法与否。官吏不论以任何方式获得经济利益或所谓好处,都为法律所禁止。量刑上,根据主体区分监临主司和监临势要。根据动机区分为公罪与私罪。根据社会危害结果分为“枉法”和“不枉法”。[2]
2.重视对人民群众的道德教化,“为政以德”,德主刑辅。
周人提倡的“明德”包含了“敬天”、“孝祖”和“保民”三重含义,“保民”是“德”的核心内容,即反对滥施刑罚,应当把犯罪者视为患者,帮助他们弃恶从善(“若有疾,惟民其毕弃咎”);判案要以常法为准,不可轻废(“勿替敬典”)。殷纣王滥用刑罚失掉江山,周文王则反其道而行之“明德慎罚”。“中刑”是“明德慎罚”的核心。所谓中刑,就是要求司法公正、量刑适中、罪刑相适应。否则,就会滥刑无辜引发“民乱”的严重后果。
儒家更是主张道德教化,反对“不教而杀”,反对专任刑罚,《论语·为政》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此要“为政以德”。
经过秦末战火的洗礼,汉代统治者在统治经验上日趋成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非走另一极端,而是“霸王道杂之”,之所以定儒术为一尊,是看好了它以血缘情感为心理基础、以宗法人伦为主要内容的特点。儒家比法家更贴近人性,有很强的亲和力,应当指出的是:汉代的儒学已与先秦儒学有很大差异。它是以儒学思想为基础,吸收了黄老思想、法家思想、阴阳家思想,是一个在更高的阶段上融合了各家思想的发展了的思想体系。它否定了法家强调法治、以吏为师、不要文教德治的片面性,吸收了它的集权专制和注重刑法的思想;否定了黄老消极无为、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片面性,吸收了它的自然观(如养生之道、元气、精气学说)、阴阳刑德思想。它更全面地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对“王道之三纲”的理论根据问题,给予了当时所能给予的适应地主阶级根本需要的答案,因而成为地主阶级在全国确立大一统统治以后第一个占据统治地位的庞大的全面的思想体系。[3](P209)
重视对人民群众的道德教化,“为政以德”贯穿了民本思想。
对“民”的认识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题之一,所谓民本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强调在君民相互依存关系中对君的约束,提醒统治者要对民的社会地位与作用、民的生活状态给予一定的关切,不能饮鸩止渴,竭泽而渔。掠夺式的统治不仅会伤民气,产生民怨,更重要的还会伤及君国社稷的基础。《论语·颜渊》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民本思想要求统治者在态度上不可轻民,《论语·卫灵公》云:“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麻木不仁可致“覆舟”之患;体察民情可使社稷永固。民既不可轻视,如何治民呢?所谓“宽猛相济”,“猛”指刑法强制,“宽”包括取之适度、附加教化两个方面。儒家坚决反对聚敛穷民,反对滥加刑罚。教化的根本目的是使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法律儒家化运动,《唐律疏议》最终确立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并为以后历代所尊崇。
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借用家族伦理关系,辅助其进行道德教育,在实践中颇有成效。
中国古代以家族为本位,家族的利益高于个人;在家族内部,“孝”是维系上下辈之间各种伦理关系的最重要的基本范畴,父母对子女有教令权,违犯教令者应受法律制裁。我国古代有许多利用家庭伦理辅助教化的例子。封建社会所具有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特点,对于加强封建家族伦理关系起着决定性作用。家族成员(包括臣仆)对家族中的官吏进行劝诫,符合包括他们在内的家族的根本利益。我国古代规定有禁锢制度。禁锢包含了政治上的否定和名誉上的污损,多殃及子孙,有时株连整个家族。古人讲求家族观念,古代统治者正是巧妙地利用了家族成员的亲情关系,使道德教育渗入到每个家庭的内部,并且利用家庭或家族实现对职务犯罪的有效预防。
二、中国古代德治传统的借鉴
1.大力提高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和广大公职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充分发挥国家工作人员对全社会的道德感召作用。
领导干部“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在公共行政领域表现为行政伦理观。行政伦理观是国家工作人员在公共行政中关于行政伦理价值追求的总体观念。江泽民同志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把端正党风和反腐败建设联系起来,说明了提高国家工作人员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性。
如前所述,这方面我国古代有着巨大的思想宝库以供借鉴。我们借鉴的尺度是这种传统思想在当前是否“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里涉及到我国行政伦理建设和以德治国的价值目标问题,应当专文论述,这里限于篇幅不作赘述。
2.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建立起以“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三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为落脚点的思想道德体系,重视对人民群众的道德教育,要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予以扬弃。
中国历代统治者对“民惟邦本”的认识对当前具有警世作用,这种思想要求统治者集团在政治上谨慎从事,不能漠视民众的利益和要求,在表面上似乎和我们提出的为人民服务、人民当家作主是一致的。但是民本和民主貌合则神离。因为民主与专制是相互对立的,而民本和专制则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民本所倡导的“重民”“爱民”与神化君主、君权如同硬币的两面,一方面要求君主尊天敬德爱民,一方面要求臣民的驯化、绝对服从,“亲亲尊尊”。把优良的社会生活寄托于圣王明君,对暴君苛政恶之越深,对圣王明主也就爱之越深。[4](P70-72)民本思想的前提是“明主”,本质是人治,而民主思想的前提则是法治。
法治是现代文明进步的基本标志,是全球公认的理想治国方略,关于它的概念和内涵学术界从各种角度出发有各样解说。一般而言,法治是指一种与人治这种治国主张相对的前提下提出的治国方略或被治理的国家所处于的状态。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包括两层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5](P199)人治认为,人类社会群体中有极少数人是圣人贤哲,其智慧超群、品德出众,应当赋予这些人以至上的权力,由他们完全根据其个人的判断来处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法治优越于人治之处在于:第一,法律决策优于一人决策,不受感情等因素影响。第二,能够防止个人专断的腐败。第三,法治是民主的基石,没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民主就没有保障。
3.由于法治包含了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的两层含义,因此当前论及德治与法治关系时,在目的性价值层面应强调法律至上,过分推崇道德,有造成道德化法律最终导致人治的危险。法治和德治只是在工具性价值层面上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普遍的守法),这是法治的工具性价值,要求人们遵守法律这种普遍性的社会规范,法治的工具性价值是由法的工具性派生出的。人类历史上有大量建立在人治基础上的法律制度,法制并不必然排斥人治现象。例如,我国古代法家所谓的“法治”实际是从工具意义上讲的,相当于现代所谓法制的内涵和外延。
良法则是对法治的目的性价值要求,即这种法必须包含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秩序、发展等价值因素。因此,从法治的目的性上来讲,要树立法律至上的权威。法律至上就是指法律的规范作用、强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当权力的运作和法律运行相悖时,权力应让位于法律;当道德、政策规定和法律相悖时,应以法律规范为准;当法有明文规定时,不得违背法律;当法无明文规定时,不得违背法理。从立法上讲,要建立民主、科学、合理的立法程序,充分体现道德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建构一个部门齐全、结构严谨、内部和谐的完备的法律体系。从行政执法上讲,政府要依法行政,尊重民权,接受监督。从司法上讲,要保证司法独立,确保司法公正。从法律文化上讲,要有先进的法学理论,公民要有良好的法律意识。法治的本质是限制公共权力的滥用。
当前论及德治与法治关系时,在目的性价值层面应强调法律至上,过分推崇道德,有造成道德化法律,最终导致人治的危险。所谓道德化法律是指一个社会系统在规范选择中以道德为本位,并将法律纳入基本道德规范系统中的现象。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的特征就是道德化法律,即礼法关系,其基本走向是以礼化法,即法律儒家化。而西方社会法律与道德关系恰恰相反,是法律化道德。[6](P156)即在目的性价值层面强调以法律为准,设计一种和法治精神相适应的道德。市场经济带给中国的必然是社会的交流开放、文化的多元创造、政治的自由民主,因此与之相对应的社会规范只能以法律为本位,这符合当今世界权力多元化与社会化的趋势。中国要在地球村里作平等的村民,不在全球化的巨潮中失去“球籍”,不能回避权力多元化、社会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历史潮流,应当大步革新政治、振兴经济,适应全球化的趋势。法治现代化的过程本质是传统道德价值的扬弃过程,其表现为以法治推动道德价值的重建,每个时代均将该时代至关重要的道德法律化。例如,当前市场经济特定的道德需求要求立法者将有关市场伦理(如诚实信用)、职业伦理和公共道德的内容法律化。
在目的性价值层面强调以法律为准,并不是无视或忽视道德的作用。事实上没有人否认法律中包含着道德价值追求。法必须以道德为价值取向,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势必会蜕变为立法者的专横任意。江泽民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我们理解,这个论断包含了一个前提:当前在探讨法治和德治关系,大都是从法律与道德都作为社会关系调节器(即社会规范)这个前提下进行的,即法治和德治只是在工具性价值层面上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也提到,“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从制度建设角度将德与法相并列,并且在法和德之前用了“依”和“以”两个不同的介词。这是因为,法治和德治作为法学和伦理学中的核心概念各具有多层含义,在工具性价值层面,“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并列,“以法治国”(ruleby law)主要是工具意义上的依法治国(rule of law),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在理论上不是同一层次的,现实中不加区别的相提并论只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