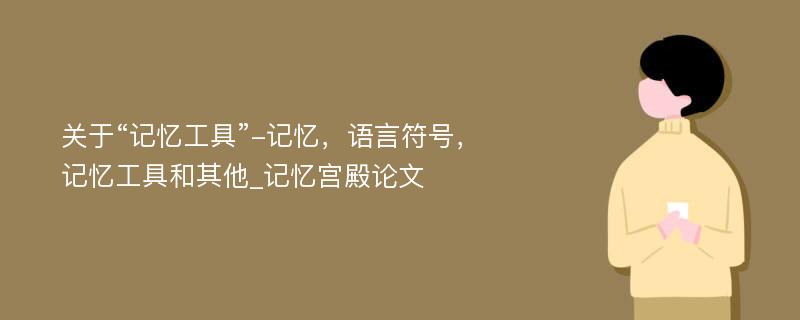
关于“记忆工具”——记忆、语言符号、记忆工具及其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记忆论文,工具论文,符号论文,及其他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记忆
谈“记忆工具”,首先要谈“记忆”。
“记忆”是什么?记忆是物质的产物,是人脑的产物,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客观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而在人脑中留存下的“复写、摄影、反映”。生理学者和心理学者从生理现象和心理现象诸方面,对人的记忆作过许多科学的描述。本文由于作者囿于知识,就不从生理学和心理学诸方面来加以描述,而只是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来谈一点肤浅的看法,归根到底还是和档案相关联着的。
动物也有“记忆”,有些动物还有特定的记忆功能和记忆方式。我们的古人都知道“老马识途”。动物的记忆只不过是一种本能。而人有意识,“他的意识代替了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意识到了的本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36页)因此, 人的记忆不仅是本能的记忆,而更主要的是有意识的记忆。不论是本能的记忆还是有意识的记忆,都要受到制约——人脑物质方面的制约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制约。
二、记忆和语言
人的记忆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受物质的制约。人的记忆,必然要受人的感官(口、眼、耳、鼻、喉、舌、皮肤等)和大脑的制约,人的感官和大脑如果不健全,便不可能有健全的记忆,记下了也很快会消失。每个人大脑的记忆力是有限的。人的记忆也离不开语言和意识。“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35页)语言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 而人的记忆是依存于语言和意识的,记忆是在人和自然、人和社会其他事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归根到底人类是在物质生产和交往中产生了记忆,是在社会生活中留下了记忆。
三、记忆的延伸——记事方式的历史选择
人的记忆,不仅是外界直观形象的记忆。当然客观世界形象的记忆是重要的,或者可以说是人的记忆的基本记忆形态。(空间和时间是客观世界的存在形式,所以人的记忆当然也包括空间和时间)随着人类物质生产和交往的发展,日常生产和交往中,社会生活中,便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必然会发生记事。简单的事比较好记,人脑是可以记住的,复杂的事比较烦琐,人脑也可以记下,但要记住就比较困难了。人类于是寻求在人脑以外采取某种方式方法来辅助人脑的记忆。人脑记忆的延伸,于是便有了人脑以外的记事方式的出现。有些人会说,那种记事方式必定是档案。且慢,并不是的,这样说过于简单化了。有些档案学者乐于希望人类很早以前就有了档案,甚至断定早到原始人类刚开始创造工具从事物质劳动,便开始有了档案。人类尚处于用石器木棒来从事渔猎、茹毛饮血的时代,便有了档案,这是很难想象的,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们最好先不谈论这样的问题,还是继续我们的历史探讨。
人类寻求在人脑以外采取某种方式来辅助人脑的记忆,完全是出于需要——物质生产和交往的需要,社会生活的需要。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历史选择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和人类物质生产和交往的发展,是和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相关联着的。确切地说是依赖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文明的发展的。
人类记忆的延伸,不只是单个人的记事方式。各个人的记事方式,直到现代社会里还会有各个人采用各种不同的记事方式,以辅助各自的记忆。这是由于各个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和文化差异而各自采用的。著名作家赵树理的一篇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轻的农村妇女,她在当年解放区农村搞变工队、互助组以发展农业生产,由于识字不够,不能记账,就采用着色的豆子和布条等等来区别各个劳力的出工,以辅助她自己的记忆。这种记事方法当然只能一时使用的,也只有她自己能弄得清楚,或者她的变工队的成员能识得。而我们所说的记事方式的历史选择,主要是谈社会记事方式。各个人的记事方式当然也是社会行为。人类生产和交往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发展,出现了“治理众人之事”的首领,不论是推举的还是世袭的,要“治下”,便要“记事”。这种记事就不仅是个人的记忆,而成为社会的记忆。记忆的延伸,不只是个人的记事方式,而是社会记事方式了。这当然是历史发展逐步形成的。这样就出现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记忆工具”——社会记忆工具了。
四、语言符号及载体
所谓历史选择,意为选择什么样的记事方式比较适合人们的需要,易于识别、通用、达意,又能传之后世。一代人的记忆,一代人去世后,记忆也就消失了。作为人类的社会记忆,应该是“历史”的。所以中国上古就有专门做记事的人,称之为“史”。“史,记事者也”。我国上古当然没有“记忆工具”之类的说法,但记忆的延伸——记事,则上古就有了。这就是古书上所称的“结绳记事”。而《周易系辞》上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许慎的《说文》序上也只说:“结绳为治,而统其事”,都没有直接说结绳是“记事”。“为治”也好,“统其事”也好,靠人脑的语言意识来记事都不够用了。结绳不只是“为治”,当然是记事,记事才能“为治”。后人为《周易》作的《集解》所引注:“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结,事小小其结,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相考”、“相治”,治和考都需要。
但是,用结绳记事的方法或者八卦符号记事的方法,显然都不能达到人们的要求。用结绳或八卦来作为记忆工具,难于识别、记认,也难于达意。人脑记忆的延伸,要达到辅助记忆的目的,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而人们也就有意识地创造这种物质基础。这就是,记事必须的语言符号、物质载体和刻记在载体上的工具。而要具备这些,人类的物质文明不发展到一定阶段是创造不出来的。而创造这些都是同人类进入文明时期相联系着的。世界各古老的文明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尽管语言符号——文字有所不同,载体也有泥板、纸草、羊皮、兽骨等等的不同,书刻在载体上的工具也有不同,而必须有这三者都是相同的。发展到后来,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都采用纸。在现代社会里,最先进的记忆载体和记忆工具,也必须具备这三者,才能达到人们预期的目的,并且也是这三者发展起来的。即使是声像档案、机读档案也要有语言符号和载体为依托;否则便不能辨认、达意和长久保存。现代科学家制造了电脑,科学家们创造了电脑的语言符号和相应的载体,电脑才能“记忆”,才有“智能”,也才能“人机对话”。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在谈论“无纸办公室”。无纸办公室是可能做到的吗?可能。但直到现在,离真正不用纸的时代还很遥远。而在我国,从结绳记事到甲骨档案,经过使用金石、简牍、绢帛等等直到使用纸作为主要书写载体,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这都是我国古代中华民族祖先有意识创造的,也可以说人们的社会记忆的需要,发展和创造了档案。世界各国皆然。
那么,在还没有形成有文字的档案以前,人们的社会记忆是怎样延续流传下来的呢?只能靠口头语言的流传,而形成古代的“传说”。这种口头“传说”,现代档案学者称之为“口述档案”,而历史学家则称之为“口述历史”。这种“口述档案”或“口述历史”直到现代社会依然存在,作为人们有文字可考的社会记忆的一种补充,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的一种补充。
五、记忆工具和档案
档案,在现代社会里,已经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记忆工具。档案学者为档案下了种种定义,或者论述了档案形成的诸多要素,从诸方面来探索和阐明档案的形成规律、社会特性和社会功能,以及管理的科学技术方法和法律制度。档案是人类社会的记忆工具,人类社会活动的历史记录。它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的记忆工具也是记忆载体。“工具”是就其作用而言的,“载体”是就其物质储存物而言的。工具也好,载体也好,是使用各种物质材料的统称。人类社会活动的历史记录,著录于物质载体上,成为社会长久储存的记忆、记事。人类社会从产生档案到现在,人们对档案的认识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档案作为社会记忆工具、记事载体,是人们继续活动的现实轨迹,人们要继续活动离不开现实轨迹;档案作为人们社会活动的历史记录,是人们世代延续的历史轨迹,人们要了解和延续自己的历史离不开自己的历史轨迹。档案的这种现实的和历史的意义,现实的和历史的客观需要,从人类社会形成档案之时起,便世世代代延续到当今时代。然而,无论古今中外,并不是所有社会记忆工具,并不是人们社会活动的所有历史记录都是档案。从古至今,人们对记忆工具和历史记录有意识地作为档案保存起来,在认识上都有一个界定、一个规定性——约定俗成的和法的界定和规定性。即使是最先进的电脑“记忆”,也不是所有记忆都是档案。直到今天,构成档案的要素,一直是档案工作者和档案学者所要研究的基本问题。我们现在谈论记忆、记忆工具、记忆载体(它是人脑记忆的延伸)为理解和研究这个基本问题提供了又一把最为明快的钥匙。不是要用记忆、记忆工具、记忆载体来替代“档案”,而是用记忆、记忆工具、记忆载体来历史地理解和研究档案的形成规律、社会本质和社会功能。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档案的载体也在发展。记忆工具、记忆载体的新变化,已经引起了档案工作者和档案学者的极大关注。这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档案学者在谈论“电子文件与档案理论”,谈论“重新创造档案”,谈论“虚拟文件”,谈论“后保管模式”等等。记忆工具、记忆载体的现实形态会发生变化吗?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这些可能也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要经过一个社会的历史选择过程。档案工作者必须关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更加自觉地顺应和考察研究这个历史选择过程,以适应社会的需要。打一个比方:一次性塑料用品,顺应社会需要,曾风糜一时,然而曾几何时,都发生了严重的“白色污染”,不得不废止不用,仍改用布质或纸质的,效果如何?还要看社会的选择。但恐怕也不会变回到旧事物,而要用更新的材料来替代它,并且相信,社会一旦需要,人们会创造出新材料来的。记忆工具和记忆载体所引起的新变化,很可能也要经历一个长时期的社会选择和历史选择。
在我国北京召开的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加拿大人T ·库克所作的大会主报告之一:《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在这篇报告的《前言:记忆、档案和档案史》,一开始就回顾了400年前即16世纪末(1596 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提出的一项建造“记忆宫殿”的计划。16世纪末,正是我国明代万历年间,利玛窦的“记忆宫殿”,不会得到重视,他传播的西方天文、数学,经由中国学者徐光启学习译著成书,在中国明清之际的历史上颇有影响,而“记忆宫殿”之说则并无影响。库克在报告中由“记忆宫殿”的启示,而引述了原加拿大国家档案馆长让·皮埃尔·瓦洛所说的“为我们当代的历史建立一个活记忆”,“档案馆是记忆的保管场所”等等。并且由此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回顾自身的发展史,我们的档案人员在建造记忆宫殿时,是如何反映广泛的社会现实的呢?档案人员采用什么样的设想、理论、概念、策略、方法和实践呢?为什么采用它们?他们多年来有何变化?又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我们为什么样的统治政权结构服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影响我们‘智力配方’的是什么社会力量……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记忆的政治功能以便更好地确定未来的方向。”这一系列问题,对于我国档案工作者来说或许也是重要的。“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记忆的政治功能以便更好地确定未来的方向”,或许更是重要的。思考一下这类问题是十分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