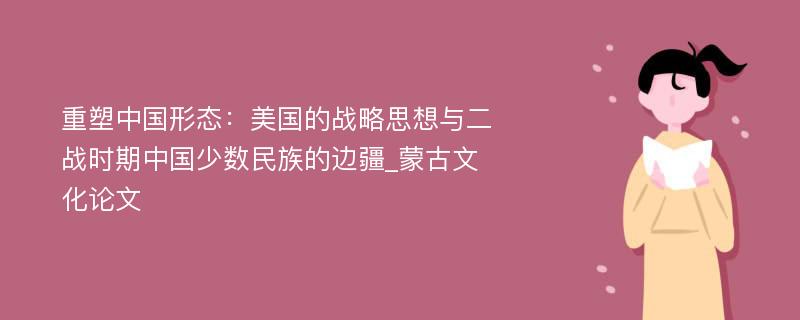
重塑中国形状:二战期间美国战略思维与中国少数民族边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边疆论文,美国论文,少数民族论文,形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72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636(2010)05-0014-09
本文的构思建立在这样一个历史认知之上:十九世纪中叶以降,中国的领土属性,包括领土范围的界定和管理方式,进入了从“帝国”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的漫长过程,这个过程是东亚的国际关系文化现代化亦即西方化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列强、俄国(苏联)、中国中央政权以及中国周边各民族的政治力量,因各自对中国民族国家的“地缘形体”的不同立场,处于一种合作与争斗交织的复杂关系之中①。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当时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给中国加上了一种色彩识别,“红色中国”随之叫响世界。然而,连稚童都知道,学习填充颜色时必须先有形状。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来说,中国的两个地图形象最能使人热血沸腾:一个是海棠叶,另一个是雄鸡。今天中国的地缘形体是在二战期间最终确定的。与此有关的是日本军事帝国在亚洲太平洋的崩溃及战时盟国之间的外交折冲。历史学者们对这些问题都已作过充分的研究②。然而,前此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中国的“失地”和前中华帝国的“进贡国”的地位问题上,诸如中国的东北、台湾,朝鲜,外蒙,琉球,越南等。被忽略的是中国的“灰色地带”,即在“内政”与“外交”问题之间难于拆解的民族边疆地区。无论如何,中国“民族国家”的形状,只是在前中华帝国的各个“藩属”和领地或向中国内倾,或对中国离异以后才能成形。二战期间,由于中美两国的同盟关系,美国对中国周边地区的战略思维对这些地区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欧、亚“少数民族”问题的异同
二战期间,美国国务院在制订战后外交政策计划时,对上次大战的新鲜记忆以及对战后国际关系稳定性的焦虑,使国务院官员再次面对令人头疼的欧洲“少数民族”问题。一些冗长的国务院研究文件给“少数民族”下的定义是“在一国内与大多数人民具有不同的民族意识的群体,这种民族自觉通常通过不同的语言和文化来表现”。在承认少数民族问题“基本上是一个内政问题”的同时,国务院也认定,当一个国家完成“公民权与民族认同的分离,就如其与宗教分离一样,进而成为真正的多民族或无民族国家”之前,少数民族问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不过国务院官员们关注的并非如何在遥远的未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这个问题在战后立刻会产生的国际后果。如果世界上的国家时刻都要担心一个侵略国会以此为借口发动战争,国际上就不会有和平和稳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倡导“民族自决”的原则。解决欧洲民族问题的国际努力也引发许多非西方民族纷纷争取“民族自决”。这些情况造成了历史上短暂的“威尔逊时刻”③。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证明一战后解决民族问题的努力是一次可悲的失败。美国的政治战略家们意识到自己对此失败中承担责任,于是希望能在二战中更好地把握第二次机会。美国国务院的结论是战后应建立一个承担双重责任的国际组织,一是保障能使欧洲国家顺利实施它们对少数民族政策的和平国际环境,二是在任何欧洲国家实行不当的少数民族政策时,出面纠正由此引起的危险局势。国务院坚信,在监督欧洲国家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这个国际组织里,美国必须担当主导作用④。美国在战后欧洲的警察角色,在这种设想里呼之欲出。
相比之下,美国的外交政策计划者从未考虑过用同样的方法应对战后亚洲可能出现的少数民族问题。亚洲到此时为止不过是列强的竞技场,亚洲政治只承认强权。在日本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以后,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进入西方国家权衡亚洲安全的视野。“九一八事变”后,英美驻华外交官一致认为,该事件迫使中国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态度“从漠视变成了焦虑”。一位英国外交官注意到:“蒙古人对于他们曾经是一个伟大民族的事实记忆犹新,总是渴望着新的成吉思汗的出现,以恢复他们昔日的光荣。”因此中国政府最好跟蒙古人达成某种协议,以预防日本人的阴谋。与此同时,对中国北部边疆日益恶化的局势,美英两国都觉得无计可施。尽管苏联在这个地区的利害关系甚于西方国家,对日本也无从钳制,能做的只是切断内外蒙古之间的接触而已⑤。这样,对西方国家来说,1930年代日本在中国的北部边疆是可以为所欲为的。直至1941年末美国与日本在太平洋开战,很多美国人都已准备接受日本对东北和内蒙的统治为既成事实。美国政府内和学术圈子里熟悉东亚形势的人士,对中国在战后能否收回东北和内蒙也都觉得希望渺茫。他们预言,在中日战争结束后,东北很可能留在日本的势力范围内,而内蒙则会成为中国、日本和苏联之间的缓冲地带⑥。换言之,中华民国将不得不承认长城是它的北部国境线。
珍珠港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华盛顿外交决策圈子对战后远东前景的看法。在1942年开始安排外交政策计划时,国务院起草了一份关于战后中国的问卷。在问卷中,内、外蒙古、西藏、新疆及其它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被列为战后中国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国务院官员们预计,战后在中国、日本、苏联和“蒙古人”之间,很可能会因为“构成内蒙的几个中国省份”而发生争执⑦。这样,国务院的政策计划从一开始就把内蒙视为为一个国际问题,而不仅仅是涉及中国政府和内蒙古民族的中国内政。
国务院文件中有意使用了含义模糊的“蒙古人”的概念,原因是这个概念所暗指的外蒙古既非得到国际承认的独立政治实体,也不在中国的控制之下。美国战略情报处(OSS)将外蒙古称为苏联的“实验殖民地”⑧。在国务院官员们看来,这块成问题的领土和新疆、唐努乌梁海、东北都是中苏争夺的地方。国务院当时的立场是,美国政府必须反对任何有损中国对东北主权的举动,但可以接受对于其它三个地区的争端的任何和平解决方案。实际上,华盛顿已经认为中国收复外蒙的愿望是不现实的⑨。
甚至对于东北问题,国务院官员们也曾有过与中国政府截然不同的想法。值得一提的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年多以后,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的一份政策备忘录依然建议以分割东北作为一劳永逸地解决该地区问题的方案。该文件认为东北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成为“冲突的摇篮”的根本原因,是其他四个“种族”,即俄罗斯人、朝鲜人、日本人和蒙古人,从未完全接受中国对东北的主权。而如果按照“族群学的原则”重划东北的东部、西部和北部边界,将来就可以避免麻烦。该文件的起草者认为,在这种安排下中国将得益匪浅,因为不仅东北最肥沃的开垦地区和所有的三千六百万中国居民都会划归中国,而且关东租界和几乎所有外国控制的铁路和矿产权也都将回归中国。那么中国的代价是什么呢?在东部,中国须割让十一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给朝鲜;在北部和西部,十六万五千平方英里的土地以及在那里的蒙古居民将脱离中国⑩。
1943年夏,英国外交部的调究人员也做了类似的演绎,由此产生的备忘录预言,苏联在战后会选择以下两种方式之一来扩张其在东北亚的势力:或者鼓励中共在东北建立一个苏维埃共和国,或者利用蒙古民族主义缔造一个苏蒙集团。根据英国官员的意见,后一种选择对苏联更有利,以支持民族主义为名的政策可以减少对英、美的刺激。在这种选择下,苏联会策动在内蒙和东北受过日本人训练的蒙古武装力量和政治组织与外蒙合成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把所有的蒙古人都纠合在一个统一的“大蒙古国”里。这份备忘录提到,虽然内蒙汉化已经多年,那里的蒙古族人口比外蒙还要多。但在察哈尔北部、东北的西部与西北部,蒙古族实际上是当地的多数民族,可以用“族群人口”的理由宣称对当地的主权。这样一个“大蒙古国”向南可以扩展到长城下,向东扩展到黄海边,从而切断东北与中国其它省份的联系。同时,东北的现代工业和铁路系统可以用来帮助蒙古民族完成内部的统一。这种设想一旦成为现实,就会极大地改变东北亚的国际政治态势,因此该备忘录在英国外交部内部引发很多疑问,诸如苏联政策是否真的具有此种意向,以及无一论情况怎样,中国人是否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11)。
有趣的是,在英美官员为战后东北亚的形势做出种种假定时,他们对民族问题的功用有十分不同的理解。美国国务院对分割东北的可行性信心满满,意在利用民族因素在大局上操控危机四伏的东北地区。而英国外交部则比较冷静,担心在内蒙和东北对民族问题的任何策动只会为苏联火中取栗。总的来说,以民族或族群概念为主的对东亚地区的战后政策设想,无论是在华盛顿还是在伦敦,都没有占主导地位。西方盟国尤其是美国的战时外交,早就打定主意要扶植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而侧重民族政治的发展前景只会分裂中国,非但不能鼓励,而且还应预防。
1943年夏,也就是美中领袖首次在开罗会晤的几个月之前,美国国务院的一次政策计划会议强烈地表达了这种意见:“中国统一的问题是考虑该(东亚)地区安全的关键”(12)。对美国政府来说,中国的统一有三方面的问题应予考虑。第一是中国内部的政治统一,也就是要重新调整国共关系。在是否应该全力支持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的问题上,虽然美国官员们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战时和战后华盛顿的中国政策实际上就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实施的(13)。第二方面是中国从日本手中收复包括台湾和东北在内的失地。在1943年11月至12月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总统正式承诺美国支持中国收复这些领土。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的政策也将美国的商业和战略利益计算在内,指望中国政府在收复台湾以后,会授权美国使用台湾的军事基地。国务院的一些官员甚至建议,美国政府可以用“民族因素”,或台湾东部土著居民与菲律宾山地居民在民族性上的某种相似,作为同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14)。
关于中国统一的第三方面则要复杂得多,涉及诸如蒙古、新疆和西藏一大片地区在内的“灰色地带”。这些地区之所以为“灰色”,是因为有关问题呈“内政”和“外交”的交错状态。在这些地区,争议不仅存在于中国政府和当地边疆民族之间,也存在于中国和战时盟国中的两强——英国和苏联——之间。因此,在这方面中美两国政府极易发生歧见。
中美在这方面的分歧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出现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考虑通过心理战加强中国的对日抵抗时提出,如果美国支持中国不仅恢复1937年以前的领土范围,而且也恢复1894年以前的领土范围,就会大大地提高中国的士气(15)。这里提出的1894年是指中国在甲午战争后到二战时为止失之于日本的权益和领土。也就是说,美国的对华心理战谋略具体考虑的是台湾和东北。美国人似乎没想到,对中国政府来说,1894年的领土就是清王朝在那时的全部领土,不仅包括失之于日本的台湾和东北,也包括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后的蒙古和西藏。
对于中国的这些领土,美国政府充其量采取了一个关切的旁观者的立场。只要中国人、英国人、苏联人能就这些领土问题达成共识,华盛顿对这些地区的国际法律地位并没有特别的主张。与此同时,绝不能让西藏和蒙古问题在中国与英、苏之间引发争执,妨碍同盟国的战时协作。既然把西藏、蒙古分别视为中英、中苏关系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对汉藏、汉蒙关系这类内政性的民族关系便了无一策。换句话说,西藏和蒙古问题在美国战后外交设计的“少数民族问题”的框架里,并没有一席之地。此外,国务院官员在考虑战后如何处理亚洲的“属地问题”时,也没有把西藏和蒙古包括在内。在国务院的观念中,亚洲“属地”问题仅涉及西方列强和日本在亚洲的殖民地(16)。
罗斯福政府的既定政策是扶植中国为四强之一,借此在战后制衡英帝国与苏联。在战时,当中国与其它两强发生争端时,美国往往偏向中国。换言之,华盛顿的战时对华政策一般是怂恿中国“反帝”的民族主义。总的说来,面对中国民族主义敌视外国在华势力的心态,华盛顿表现得比伦敦更善解人意。这种善解人意的另一个表现,是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政府的国内少数民族政策有意不闻不问。美国的战时对华政策从未向中国政府建议,应如何对待国内的少数民族或应如何恢复中国政府在蒙古、西藏、新疆等地的权威。华盛顿视中国为独立主权国家和扶持中国取得强国地位的具体政策,主要是致力于恢复和保护中国政府在中国东部的领土和行政的完整(17)。
国民党政府的民族主义对美国自由主义会偶有冒犯。美国国务院对蒋介石那本著名的《中国之命运》的反应就是一例。这本书在1943年发行以后,国务院的官员们把它看作是中国“民族主义病毒”有可能“变成毒瘤”的证据。他们的批评集中在国民党无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自由主义政治力量的一党专制及书中显示的要成为亚洲领袖的野心。国务院的官员们认为,美国政策必须努力引导中国民族主义向“健康途径”发展(18)。同时,这些批评完全忽略了蒋介石在中国民族政治问题上鼓吹的“一个民族”的信条,即把中国各个少数民族视为“中华民族”的“大小宗支”。
华盛顿对中国边疆的分裂倾向心怀忧虑,担心这种倾向会妨碍美国寻求在东亚与一个强大、稳定的中国结成合作伙伴的努力。如果不考虑国民党政府通常对边疆民族的压制和同化政策,蒋介石的单一民族论或可以理解为一种通过缩小中国各民族间的差别来推动民族平等的努力。实际上这种政策意向能够在美国国务院找到支持者。在考虑欧洲环境下的少数民族问题时,国务院认为若要在战后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唯有尽可能地消除“少数民族”这个标记,并把这个问题置于“保护基本人权这个更广泛的基础之上”(19)。但是美国政府并未向中国政府传递此类有关人权的理念。实际上,整个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与美国国务院从未就中国或其他亚洲国家的“少数民族问题”交换过意见。在中国东部和太平洋赢得对日战争之前,主要存在于中国西、北边疆的中国“内部的”民族政治问题对战时中美之间的伙伴关系来说似乎无关宏旨。
正因为如此,在1941年下半年及1942年,当欧文·拉铁摩尔分几次向蒋介石提出有关民族问题的建议时,他的做法与美国官方政策是大相径庭的。拉铁摩尔是罗斯福总统亲自推荐给蒋介石的政治顾问。他的建议既不是因为蒋介石有所垂询,也不是出于美国政府授意(20)。三十多年以后,当回忆起四十年代前期为蒋介石效力的这段经历,拉铁摩尔表白他在重庆是蒋介石的私人顾问,而不是“罗斯福的人”,所以他“必须忠于职守,把对蒋最有利的考虑置于其他一切之上”。(21) 这种出于情势的忠诚,使拉铁摩尔无法向蒋介石坦承自己的观点。例如,他建议蒋介石在内蒙采取政治措施,以中止中国当局的殖民政策和阻止有关省份官员对蒙古人的暴厉行为,但是他反对在内蒙民众中间得到普遍支持的使内蒙成为一个一体的自治区域的主张。拉铁摩尔为蒋介石出谋划策是为了“促进蒙古人对中国的积极的爱国倾向”,而在他看来内蒙自治的主张是与国民党政府“普遍加强中国政治统一”的意向背道而驰的。拉铁摩尔向蒋介石强调,内蒙问题的解决必须与中国的民主化同步进行。他的理由是,一个民主的内蒙古将有助于中国政府吸引外蒙回归中国。(22)
拉铁摩尔在1942年底回到美国执掌战争信息署太平洋局。他对美国的官方人士们讲的却是另一种论调。1943年拉铁摩尔提交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题为“美国战时与和平时期利益研究”的系列秘密报告准备了一份关于蒙古问题的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指出蒙古在历史上从来不属于中国,当今中国政府也没有机会用武力“归复”“蒙古人民共和国”。至于在内蒙的种种矛盾,拉铁摩尔运用了一种阶级分析的方法,说明那里的形势远比蒙古精英、中国政客和日本侵略者有意煽动的“民族对抗情绪”复杂得多。在蒙古精英鼓动的表面现象之下,另一层次的反抗情绪也存在着,“即蒙、汉普通民众对那些王公、喇嘛、将军和地方官员们操纵他们命运的愤懑而又无计可施的无奈”。(23) 拉铁摩尔的这种立足社会经济角度的观察极为重要,但是它对当时的美国外交政策并不具有明确的相关性。
二、“中国三个角落”的颜色
在中国时,拉铁摩尔不止一次向蒋介石指出中国反对“不平等条约”的百年斗争已经取得胜利,现在该是将注意力转移到中国的“三个角落”的时候了,即东北、西北和西南。他警告说,如果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被中国压制,他们会回头投向俄国和英国。拉铁摩尔特别提醒蒋介石,中国传统的同化政策已被证明无效,而苏联在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上取得了“极大成功”,对中国的少数民族会有巨大的诱惑力。(24)
拉铁摩尔敏锐地察觉到,少数民族问题在战后亚洲的大国关系中将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他对亚洲内陆边疆问题重要性的屡次呼吁,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都是没有引起反响。1942年5月,拉铁摩尔以蒋介石顾问的身份回了一次美国。在给蒋介石的信中他预言,一旦日本和苏联开战,中国在东北、蒙古和新疆的利益将会受到极大影响。他向蒋介石建议,鉴于华盛顿对中国的这些利益一无所知,如果他留在华盛顿便可以更好地帮助中国,用他的学识去防止美国政府方面对内陆亚洲诸多问题产生误解。(25) 拉铁摩尔对于美国政府更确切地说是国务院不了解中国民族边疆问题的看法是中肯的。1942年,他建议华盛顿应该把中亚地缘政治作为对华政策的考虑的重点之一。这个建议虽是未雨绸缪,但对把注意力集中在战争进程上的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来说则是太早了。当时华盛顿一般的看法是,只有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才能顾及莫斯科对中国东北和西北的企图。两年之后,罗斯福总统派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访华,让拉铁摩尔随行。这一安排表明罗斯福总统多多少少开始对亚洲内陆有所关注。
1944年6月华莱士的中国使命是关于罗斯福的许多不解之谜之一,这些谜使他得到和“斯芬克斯”一样深不可测的名声。在华莱士一行到达重庆以后,美国媒体和中国政府还在猜测他访华的真实目的。(26) 本文没有必要对此作进一步揣测。可以了解的是,华莱士此行特别取道苏联远东和中亚地区,而罗斯福总统之所以坚持让拉铁摩尔随行,正是因为他对这些地区具有权威知识。罗斯福希望他可以协助副总统找到一个防止中苏在中亚边境地区发生摩擦的途径。在到达重庆的第一天,华莱士就笼统地向他的东道主建议,应该让那些在远东地区尚未自治的民族建立自治政府。在敏感的中国人听来,他们的美国客人暗指的是蒙古和新疆的穆斯林。(27) 然而随后华莱士在中国的访问很快就被其他更紧迫的问题所湮没,诸如国民党政府面对的军事危机以及与中国共产党的争斗等等。后来华莱士向罗斯福总统汇报他的访华使命时,这些问题成为汇报重点。华莱士的报告只是简短地提到蒙古。他告诉罗斯福总统,战争结束后中国不太可能在外蒙恢复主权,因为苏联在那里有强大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已经延伸到内蒙。至于拉铁摩尔在中国之行中的作用,华莱士声称他主要负责处理“在中国的公关事宜”,而没有提出“任何值得一提的足够重要的政治建议”。(28)
只要美国政府对亚洲政策的出发点是美国在太平洋战略地位,只要华盛顿关注的中心问题是战后东亚地区大国关系的前景,拉铁摩尔对亚洲内陆民族政治的专长对美国政府来说就不具实用价值。1942年8月,国务院曾向拉铁摩尔询问中国政府对战后诸问题的意向。拉铁摩尔向国务院说明了国民党政府对诸如战后处理日本、亚洲殖民地、中共以及中国的工业化等等问题的观点,并借此机会呼吁国务院官员关注中国的“三个角落”。他不无夸张地声称:“未来中国的工业和经济发展将基于云南、新疆和蒙古的三角地带,而不是沿海地区”。(29) 可是美国国务院官员想了解的是莫斯科对中国北部和西北边疆的意图,也就是说这些地区是否会变“红”抑或仍然保持“灰”色。此类信息却非拉铁摩尔所能提供。苏联一直置身于对日战争之外,莫斯科也因此得以避免对战时盟国暴露其在亚太地区的政策意图。华盛顿的政策分析家们对苏联在亚洲的一般政策和对东北亚的具体意图因此一直有神秘之感。在莫斯科自己透露出任何线索之前,国务院的官员们对苏联的亚洲政策只能做众说纷纭的猜测。
1943年8月,国务院远东司就这些疑问向欧洲司求助,因为欧洲司的同僚们至少了解苏联政府在欧洲的战争目的。通过这种内部交换意见,远东司得出的最初结论是,战争结束后莫斯科在东亚会采取类似它在欧洲的策略,即试图在内蒙古、东北、朝鲜和西太平洋其它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30) 然而,两个月后,当国务院的政策计划官员再度考虑这个问题时,却不再认为苏联因素具有太大的危险性。就蒙古问题而言,国务院不认为会有严重的情况发生。苏联不会放弃它对外蒙的控制,这自在意料之中,而中国政府也会采取现实的态度,满足于在外蒙维持名义上的主权。在国务院看来,蒙古问题的另一半即内蒙古问题,麻烦会更少一些。鉴于内蒙地区一直被“周围的汉人省份不断同化”,战后统一了的中国定能有效地控制内蒙古。(31)
虽然国务院不担心中苏边境的民族问题会给美国的外交政策带来严重挑战,但对另一种可能的局面却十分担忧,也就是苏联可能会以中国共产党为工具,利用在中国和亚洲广泛存在的反西方情绪。美国战略情报处的报告表明苏联的这种意图已初见端倪。1944年初,出于类似的担心,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约翰-戴维思敦促华盛顿在苏军对日开战和把华北划入其势力范围之前,就派遣美国军事观察组去延安,与中共建立联系。(32) 当战争进入最后一个年头的时候,美国官员对苏联在远东参战的政治后果的担心也日益加重。国务院远东司认为,一旦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西方盟国将无法阻止苏联红军占领东北亚的很多地区。1945底,国务院已经确信苏联将会在内蒙、东北和新疆有所策动,但认为苏联在这些地区的行动将取决于同中国的全局关系。换言之,“中俄关系的症结不是‘领土’而是政治,即俄国对国共之争的态度”。(33) 至此,美国对战后东亚国际局势的估计已将中苏关系中的“领土”和“政治”问题区分十分清楚。如果未来的争端仅涉及中国的地缘形体,美国不妨袖手旁观,但如果事态表明苏联企图改变中国的政治颜色,美国就不能置身事外。
国民党政府显然对美国政府这种重“色”轻“形”的立场有所了解,因此不断向美国官员提供引导性的“情报”,比如说中共为了使自己的地区和苏联连接,正在鼓动内蒙古脱离中国云云。(34) 此类有关华北政治形势的信息以及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的前景使国务院开始考虑美国有必要采取某种行动。国务院尤感担忧的是,国民党政府会对苏联经过内蒙参加对日作战做出负面反应。1945年1月,国务院起草了一系列关于远东形势的备忘录,以备罗斯福总统在即将召开的美英苏雅尔塔首脑会议上参考。其中第一份文件就提到了内蒙,指出苏联一旦加入对日战争,内蒙的战略位置将使其成为红军进攻的必经路线。国民党政府因为害怕苏联利用这个机会与中共建立联系,已经明言要预先防范。国务院担心这种连锁反应会在远东造成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难堪局面”,因此认为美国应该事先出面干预。国务院建议在苏军进入中国之前,国共的军事力量就应置于统一指挥之下。但是很可能双方不能就此达成协议,此时就应建立“美国对中国军队的全面指挥”。国务院认为第二种情况更为有利,不但可以防止中苏之间在战争中发生政治摩擦,而且可以对战后中国直接产生“稳定作用”。(35)
如果上述任何一种情况在历史上发生,中国战后的历史就会是另一种样子。可是实际上,在国务院起草这些政策方案的时候,这些方案就已经过时了。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已在国共之间进行过毫无成效的调停。罗斯福政府也不可能向中国提出由美国人来指挥中国军队的方案,因为这在1944年的史迪威事件中已被证明行不通。实际上,史迪威事件不仅使国务院在1945年初关于内蒙古的建议徒劳无功,也预示了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会议上即将采取的有关外蒙古的外交方针。史迪威事件标志着美国政府改造蒋介石军队的努力的终结。既然无法使中国政府的军队成为击败日本的有效力量,罗斯福决定转而求助于斯大林,外蒙古也因此成为美国外交的筹码之一。(36)
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罗斯福政府对外蒙古的复杂国际地位似乎毫不知情。只是在1942年初,当罗斯福总统想以外蒙为基地对日军实行空袭时,才从战争部那里了解到外蒙其实不在中国政府的掌握之内,空袭计划因此无从实施。莫斯科可以决定是否让美国空军利用外蒙为基地,可是苏联当时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的中立立场必定也使外蒙古置身战争之外。后来,罗斯福政府意识到莫斯科执意保持外蒙的缓冲国地位,与此针锋相对的是国民党政府恢复中国“固有边疆”和将其治权延伸至所有“边远省份”决心。美国国务院和罗斯福总统都认为,必须避免中苏两国在外蒙问题上发生冲突。1944年春,发生在新疆和外蒙边境的一次武装冲突表明,中苏冲突的危险随时存在。罗斯福十分担心战时同盟因此产生裂痕,打算出面调停中苏矛盾。后来国务院建议谨慎从事,于是罗斯福以一个更超脱的姿态劝诫蒋介石不要贸然行动,以免危及战时同盟。(37)
雅尔塔会议根本改变了美国政府在外蒙问题上对中苏争议所持的不偏不倚的立场。这次会议以后,莫斯科的外蒙方针由于得到了美英的认可而在国际上取得了合法性。华盛顿的支持对苏联后来在外蒙问题上压服中国尤为重要。在这次峰会上,为使斯大林同意参加对日战争,罗斯福和丘吉尔接受斯大林开出的价码。在有关苏联参战的秘密协定里,美英领袖除了同意支持苏联在中国东北和日本北部的领土、权益要求外,还同意外蒙“维持现状”。这个秘密协定成为1945年夏中苏政府在莫斯科谈判双边关系时既定基础。当时蒋介石感到无力推翻这个在三大强国间达成的谅解,于是决定以让出外蒙换取斯大林在中共问题上的合作。(38) 这段历史已经广为人知。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雅尔塔会议上,当斯大林用模糊的“维持现状”的行文来掩饰外蒙的“红色”政治和从中国分离的状态时,罗斯福总统对斯大林这种模糊概念的赞同并非出于对蒙古民族独立的同情。他的出发点是百分之百的大国政治。在雅尔塔会议前后,罗斯福都一直试图使中国政府相信斯大林对外蒙未存野心,而雅尔塔协定却成为西方国家承认苏联在蒙古高原的战略地位的第一个国际文件。美国国务院对此自然是心知肚明。雅尔塔会议结束后,国务院便建议调整美国对华政策中有关中国在外蒙和西藏领土主权的立场。尽管国务院提出这个建议的理由之一是提倡“地方自治”,更重要的理由是在这些地区“容纳英俄利益”。(39)
三、“颜色”和“形体”政治
在罗斯福总统任内,美国外交政策尚未滑向对苏冷战的模式,但是罗斯福总统的战时外交已为美苏各自的势力范围勘定了地缘政治的断层,由此为即将到来的冷战划出了双方最初交手的大致范围。罗斯福的继任者们对他的工作并不满意。甚至在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前,华盛顿的官员们已对苏联在中欧的扩张十分恼火,并开始怀疑雅尔塔会议把外蒙和东北置于苏联控制之下的决定是否明智。(40) 在这种情况下,战后亚洲的国际政治新时期开始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中国领土属性转型的关键时期,对中国地缘形体的定形关系至巨。美国战时外交帮助中国恢复了部分失地,也基本上支持中国政府对前清帝国版图的主权要求。在另一方面,美国战时外交参与了使外蒙脱离中国的过程。鉴于美国政府在战时对苏联和中国的影响的分量,可以毫不过分地说,中国版图由海棠叶形变成公鸡形是与美国的战时外交有重大关系的。尽管美国的外交政策对中国的民族边疆产生了重要影响,二战期间华盛顿的对华政策却极少考虑到中国的民族问题。如果民族问题间或被提及,也只是作为压倒性的大国关系的脚注而已。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取向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没有改变,尽管中国在战后已开始进入一个边疆民族政治激化的时期。
在太平洋战争方酣之时,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斯坦利·赫恩贝克在一个国务院的内部备忘录中提出,如果西方盟国可以和中国、苏联结成集体安全伙伴关系,那么“我们将不仅可以跨越东、西方之间的鸿沟,而且可以超越‘颜色’的差异”。(41) 然而,赫恩贝克所希望的东、西方合璧的集体安全体系并没有在战后亚洲出现,他用“颜色”(不同人种的肤色)差异所暗示的种族、文化冲突也没有成为战后国际政治的主题。“颜色”是以另一种含义进入战后国际政治的。二战在欧洲和亚洲先后结束,随之而来的不仅是和平,也是一种新的国际危机。战后的国际政治确实是带有浓重色彩的,但是这些颜色识别标志区分的是意识形态集团,不是文化分野或种族界限。
当冷战的阴影开始笼罩世界时,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政策制定者们把中国是看作颜色未定的地区之一。然而战后中国是一个拥挤的政治舞台:争霸的美苏强国、重新开战的国共两党、寻求自身政治地位的边疆民族都在这个舞台上各显神通。国民党和中共在各自国际盟友的支持下为决定中国的颜色而苦战,而在中国边疆的蒙、藏、维吾尔、哈萨克各族的政治斗争则关系到中国的形状是否将继续发生变化。中国在冷战时代的历史就这样在着“色”与塑“形”的竞争中展开。
注释:
① 参见Charles S.Maier有关“领土属性”的讨论,“Consign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to History:Alternatives for the Modern Er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5 (3) (June 2000):807-831。关于“地缘形体”的原创见解,见Thongchai Winichakul,Siam Mapped:A History of the Geo- Body of a Naton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
② 有关的重要研究有John W.Dower,War Without Mercy: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tc War (New York:Pantheon,1986),John W.Gar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1937—1945: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Akira lriye,Power and Culture:The Japanese—American War,1941—1945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Xiaoyuan Liu,A Partnership for Disorder:China,the United States,and Their Policies for the Postwar Disposition of the Japanese Empire,1941—1945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W.Roger Louis,Imperialism at Bay: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ecoloniz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Michael Schaller,The U.S.Crusade in China,1938—1945)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Christopher Thorne,Allies of a Kand:The United States,Britain,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1941—1945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
③ Erez Manela,The Wilsonian Moment:Self- 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④ CAC- 250,“The Problem of Minorities in Europe,” 7 October 1944,Harry N.Howard Papers,box 3; ISO- 245,“The Problem of Minorities,” 26 March 1945,同前。
⑤ Dispatch from the British Legation in Peking to the Foreign Office,No.1390,23 October 1933,L/P&S/12/2287; Ingrain to Sir John Simon,17 January 1934,and enclosures,同前;H.M.Military Attache of the Peking Legation to the Foreign Office,28 April 1934,and enclosures,同前。
⑥ “Draft Agenda for Meeting on Inquiry Part IV,” 23 March 1939,and appendix,Philip C.Jessup Papers,box A122,AIPR Annexes No.21-40; Lattimore to Yarnell,29 April 1941,Stanley K.Hornbeck Papers,box 449; Yarnell to Lattimore,29 April 1941,同前。
⑦ “China,” (无日期,1942),Records of Harley A.Notter,box 11。
⑧ Hornbeck to William Langer,15 April 1943,enclosure,“Summary of Outer Mongolia and Tannu Tuva Survey by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February 23,1943,” Hornbeck Papers,box 300。
⑨ PG- 34,“Sino- Russian Problems in the Post- War Settlement,” 4 October 1943,Notter Records,box 119; “Summary Report of Vice President Wallace Visit in China,” 10 July 1944,Franklin D.Roosevelt Papers/PSF,box 27。
⑩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s to Division of Political Studies,“Partition of Manchuria,” 13 March 1943,General Records of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Central Files:China:893.01 Manchuria/1673 (下略为GRDS)。
(11) “The U.S.S.R.and the Possibility of a ‘Greater Mongolia’,” 3 August 1943,FO371/35860。
(12) ST Minutes 21,2 July 1943,Notter Records,box 79。
(13) Davies to Hopkins,31 December 1943,Roosevelt Papers/PSF,box 27; Davies to Hopkins,16 November 1944,同前。在这些信中,美国驻华使馆二秘约翰-戴维思向霍普金斯指出,美国人把蒋介石和中国视为一体是一种以己度人的神话。
(14) CAC- 66a,“Military Government in the Far East,” 5 February 1944,Notter Records,box 109; “Indications of Contact with President on Post- War Matters” (无日期),Notter Records,box 54; ST Minutes 16,7 May 1943,Notter Records,box 79。
(15) JPWC3,“Joint Psychological Warfare Committee:Suggested China Plan,” 16 March 1942,Records of Joint Chiefs of Staff,microfilm reel 13。
(16) P- 241a,“Official Policy and Views Affecting the Post- War Settlement in the Far East,” 30 September 1943,Notter Records,box 58。
(17)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Unconditional Surrender of Japan and Policy toward Liberated Areas in the Far East in Relation to Unconditional Surrender,”29 June 1945,Harry L.Hopkins Papers,box 169-171:Big Three Conference Agenda (Potsdam) July,1945。
(18)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s to Secretary of State,2 September 1943,Hornbeck papers,box 70。
(19) ISO- 245,“The Problem of Minorities,” 26 March 1945,Howard Papers,box 3。
(20) 有关拉提摩尔自1941年至1942年间的任命和他与蒋介石的交往,参见Robert P.Newman,Owen Lattimore and the“"Loss” of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 ),55-96。但是本书完全没有提及拉铁摩尔给蒋介石的有关边疆民族的建议。
(21) Lattimore,“A Memorandum to Chiang Kei- shek,” 30 June 1976,Lattimore Papers,box 28。
(22) Lattimore,“Memorandum on Inner Mongolia”(大致在August 1941),Lattimore Papers,box 28。
(23) No.T- B 63,“Studies of American Interests in the War and the Peace:Territorial Series:Memorandum on Mongolia and the Peace Settlement,prepared by Owen Lattimore,8 June 1943,” Lattimore Papers,box 28。
(24) Lattimore to Lauchlin Currie,27 July 1941,Lattimore Papers,box 27; Lattimore=s note on a conversation with Weng Wen- hao (Wong Wenhao),2 November 1942,同前;Lattimore=s note on a conversation with Chu Chia- hua (Zhu Jiahua),7 November 1942,同前;minutes of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Jiang Jieshi and Owen Lattimore on 31 July 1941,同前;Lattimore=s note on a conversation with Chiang Kai- shek,5 December 1941,同前。
(25)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台北: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3编第1册,第744-745页。
(26)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目抗战时期》,台北: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3编第1册,第859-861页;Newman,Lattimore,115。
(27) Newman,Lattimore,108;王世杰:《王世杰日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4册,第338-339页。
(28) Wallace to Harry Truman,19 September 1951,and enclosure,“Summary Report of Vice President Wallace's Visit in China,” 10 July 1944,Roosevelt Papers/PSF,box 27。
(29) T Document 44,“Principal Points of a Report by Owen Lattimore on China and Chinese Opinion on Postwar Problems,” 21 August 1942,Notter Records,box 60。
(30) FE memo,“U.S.S.R.Aims in the Far East,” 19 August 1943,Hornbeck Papers,box 396。
(31) PG- 28,“Possible Soviet Attitudes towards Far Eastern Questions,” 2 October 1943,Notter Records,box 119。
(32) PG- 28,“Possible Soviet Attitudes towards Far Eastern Questions,” 2 October 1943,Notter Records,box 119; R & A No.2211.1,“Russia and the Far Eastern Settlement,” 22 July 1944,OSS Report,vol.6 (microfilm reel 3); John Davies Jr.to Hopkins,23 January 1944,enclosure,“Observers' Mission to North China,” Hopkins Papers,box 334。
(33) Hornbeck to Secretary of State,18 July 1944,Hornbeck Papers,box 396; State Department to the Officer in charge of the American Mission,Chungking (Chongqing),12 February 1945,Top Secret General Records of Chungking Embassy,China,1943-45,box 1。
(34) Edward Ric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21 May 1945,GRIDS:893.00/5-2145。
(35) Memorandum,“Far East:(1) China:(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ituation if U.S.S.R.Enters War in Far East”(无日期),Hopkins Papers,box 169-171; State Department to the Officer in charge of the American Mission,Chungking,8 February 1945,enclosure 5,“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9 January 1945,Top Secret General Records of Chungking Embassy,China 1945,box 1。
(36) Schaller,The U.S.Crusade in China,147-176。
(37) War Department to President Roosevelt,28 January 1942,Roosevelt Papers/PSF,box 2; T- 325; note by Harry Hopkins on a conversation with Winston Churchill,November 1943,Hopkins Papers,box 331; P-254a,“Chinese War and Peace Aims,” 1 March 1944,Notter Records,box 10; CAC297,“Outer Mongolia,”23 October 1944,Notter Records,box 115;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7 April 1944,Roosevelt Papers/MRF,box 10; FD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7 April 1944,同前;The President to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 shek,8 April 1944,同前。
(38) 参见Garver,Chinese- Soviet Relations,209-228; Liu,A Partnership for Disorder,242-286。
(39) “Formosa,” April 1943,Notter Records,box 63; PWC-195,15 May 1944,Notter Records,box 110; Division of China Affairs memo,“Policy with respect to China,” 18 April 1945,Records of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box 10。
(40) Grew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13 July 1945,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5; Vll (Washington,D.C.:G.P.O.,1969),934-938; Harrim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11 August 1945,同前,152。
(41) Hornbeck to Secretary of State,20 September 1943,Hornbeck Papers,box 378。
标签:蒙古文化论文; 蒙古军队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美国领土论文; 苏联总统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边疆论文; 东北历史论文; 华盛顿论文; 罗斯福论文; 内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