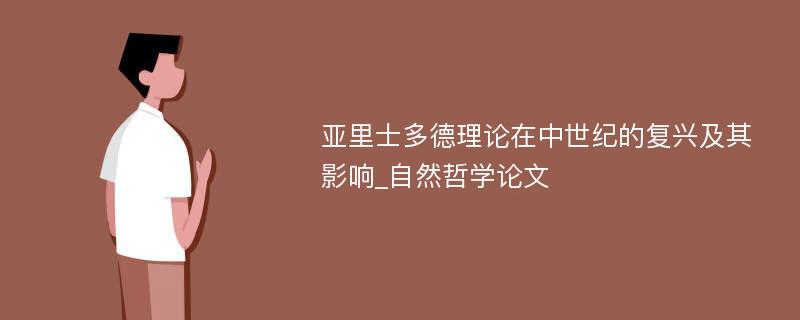
亚里士多德学说在中世纪拉丁世界的复兴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里士多德论文,学说论文,在中论文,世纪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2;B5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0)04-0085-(06)
自西罗马帝国灭亡直到11世纪初期(亦即中世纪早期),古希腊科学与哲学几乎已为拉丁基督教世界的人们所遗忘。公元6世纪末,在拉丁西方世界“几乎所有的希腊原文的希腊学术和文化著作业已失却。甚至有关希腊语本身的知识也几乎毫无例外地消失了”。[1](P15)即便到了加洛林时代,西方人“对希腊著作和哲学、科学思想机体的无知几近一贫如洗的境地”。[2](P87)亚里士多德学说也遭到了大致同样的命运。虽然,在中世纪早期,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部分知识还在波埃修、西塞罗等极少数学者的译著中有所保存,①但从总体来看,亚里士多德学说在中世纪早期几乎完全失落了。那么,亚氏学说是如何在中世纪拉丁基督教世界失而复得的呢?它对中世纪西欧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本文将就此问题略陈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及其传播
尽管中世纪早期的拉丁西方世界历经了各种灾难,但它发展的步伐却是无法阻挡的。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拉丁西方世界历经几个世纪的震荡、重组和积累,从11世纪开始走上了稳步发展的道路。这种发展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它表现在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人口的增长、工商业的兴盛、城市的复兴和基督教新秩序的确立。与此同时,拉丁西方人也迅速走向了扩张的道路,他们通过西班牙的“收复失地运动”、诺曼人对西西里的征服、十字军东征等一系列扩张活动才最终实现了其重新控制地中海的愿望,同时也打开了他们同外部世界联系的大门,从而导致了大规模的同地中海世界各民族的富有成效的交往活动。也正是在这一交往过程中,一场规模宏大的翻译运动在拉丁基督教世界展开了。在此次翻译运动中,亚里士多德的所有著作又被翻译成为拉丁文等西方文字。②
自12世纪20年代中期至13世纪末,在西班牙、西西里、意大利、法国南部等各翻译中心,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修辞学、形而上学、自然科学、伦理学、政治学所有论著的希腊文和阿拉伯文文本被翻译成为了拉丁文。具体而言,在12世纪20年代至该世纪末,除了《范畴篇》、《分析篇》、《政治学》、《修辞学》、《诗学》、《动物志》外,亚氏所有其他的著作被翻译成为了拉丁文,其中最重要的翻译家有:一位无名氏和意大利的两位著名翻译家冈萨里斯与克雷默那的杰勒德(他们都在西班牙的托莱多翻译中心从事翻译工作,而且都是从阿拉伯文翻译为拉丁文的著名翻译家),及威尼斯的詹姆斯(曾经到过君士坦丁堡,是从希腊文翻译为拉丁文的著名翻译家)。在13世纪,除了《正位篇》外,亚里士多德所有其他著作又被重新翻译为拉丁文,其中最重要的翻译家有:苏格兰人迈克尔(他曾经在西班牙托莱多和西西里两个翻译中心工作,是从阿拉伯文翻译为拉丁文的著名翻译家)和莫尔伯克的威廉与(他是佛兰德尔的多米尼克会员,曾多次到过希腊,是从希腊文翻译为拉丁文的著名翻译家)、格罗塞特斯特(牛津大学第一任校长,数学家、天文学家和从希腊文翻译为拉丁文的翻译家)。此外,一些犹太翻译家还将亚里士多德部分著作的阿拉伯文本翻译为希伯来文,以供拉丁世界的犹太人研读,这也是亚里士多德著作在西方传播的一个重要渠道;其中著名的翻译家为13世纪后期的格雷希安。
除了上述翻译渠道之外,亚里士多德学说的传播还有赖于阿拉伯人、拉丁世界的翻译家们和学者对亚氏著作所作的评注。其中被称为阿拉伯哲学中的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著名哲学家伊本·西那(即阿维森那)、伊本·拉希德(即阿维罗伊)等都曾对亚氏的诸多著作作过评注。尤其是伊本·拉希德,其哲学成就便奠定在他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详尽评注上,并被但丁称之为“伟大的注释家”。[3]他曾对亚氏的《范畴篇》、《分析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物理学》、《论天》、《论生灭》、《气象学》、《论灵魂》、《论感觉》、《论记忆》、《论梦》、《论长短》、《动物志》、《形而上学》、《尼各马可伦理学》作过评注。而他的这些评注本也在该时期被翻译成为了拉丁文,从而成为拉丁世界传播亚里士多德学说的重要渠道。而拉丁的翻译家们不仅翻译了大量的亚里士多德著作,有的翻译家还撰写了相关的概论性著作,如格罗塞特斯特不仅翻译了亚氏的《尼各马可伦理学》,还写了一篇有关该书的概论,这也同样成为传播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渠道。
随着亚里士多德著作译介到西方,拉丁世界迅速掀起了研究亚里士多德学说的热潮,而西欧各大学则成为传播亚里士多德学说的重要阵地。为了教学和研究之需,拉丁学者们反复研读翻译过来的亚氏著作,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大量相关评注和概论性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因为这是当时研读亚氏著作的最通常的方法。
面对这股强劲的新思潮的传播,基督教会力图加以抵制。1210年巴黎教区理事会决定,严禁公开或私下阅读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著作及对它们所作的评注,违者将受到革除教籍的处罚。1215年,经教皇特使批准的巴黎大学章程中也明文规定:禁止文学院教师传授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著作。1263年,面对越来越强大的亚氏思潮,教皇乌尔班四世仍重申1210年的禁令。但是,至13世纪中叶,“这些禁令似乎已成了一纸空文。在1255年,文学院的成员实际上都已必须研究他们所知道的所有亚里士多德的著作”。[4](P32)至此,基督教会实际上已经默许或认可了亚里士多德学说的传播。
二、亚里士多德与中世纪西方文化的复兴与繁荣
亚里士多德学说在拉丁世界的广泛传播有力地推动了中世纪西方文化的复兴和繁荣。具体而言,亚里士多德学说对于中世纪西方文化复兴和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满足了12世纪晚期兴起的大学教育的急需,亚氏著作迅速成为大学教育的基本教材,从而填补了大学教育的空白。
中世纪的欧洲大学分为人文、医学、法学和神学四个学院,而人文学院是“其他学院的基础”,③即它所提供的是基础性的教育,其他三个学院则提供专门性的高等教育。因此,所有进入大学的学生都必须在文学院接受基础性的人文教育(一般为两年)之后,方能进入其他学院学习。但在大学出现之前,欧洲学校所提供的课程基本上是从古代继承下来并在中世纪早期广泛采用的“七艺”,其内容相当陈旧和狭窄。随着翻译运动的出现,大量的古希腊、阿拉伯科学和哲学著作被翻译成为了拉丁文,这为刚刚兴起的大学提供了大量新颖的教学资源,人文学院的课程设置由此迅速扩展,教学内容也迅速得以更新。在课程设置方面,虽然各大学通常会保留“七艺”的名称,但至13世纪中叶,人文学院的相关课程设置却已经与之大相径庭了。从一些流传下来的有关中世纪欧洲大学的档案文书中,我们可了解到当时人文学院课程设置的具体情况。自1252年至1452年,经过教会或大学官方多次审定确认的课程设置如下:逻辑学、语法、哲学、自然哲学和科学、心理学、实用哲学。④可见,这一课程设置已经完全突破了旧有的“三科”、“四艺”的分类,并导致了在三种哲学中出现了新的课程分类——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形而上学。其中,1255年3月19日所确立的新课程大纲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所以一些西方学者将之看作是“革命性的课程大纲”。[5](P279)在具体的课程内容方面,新近翻译过来的古希腊、阿拉伯人科学和哲学著作以及据之撰写的概论性著作大量地加入其中。如“三科”中最为显著的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新逻辑”的输入;而在“四艺”中,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托勒密的《天文学集成》及阿拉伯人汇编的托勒密天文学纲要、阿拉伯数学家花拉子密的算术学、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等也成为必修课。医学院、法学院、神学院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此不赘言。⑤
那么,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在中世纪欧洲大学教育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下面我们将作具体的阐述。由于人文学院是为大学中所有的大学生提供必须接受的基础性教育,所以人文学院的课程设置及教材选用情况最能体现亚里士多德在其中的作用及影响程度。根据中世纪各大学有关课程设置的文件,我们得知,逻辑学课程的教材采用了亚里士多德所有的逻辑学著作(包括《范畴篇》、《解释篇》、《辨谬篇》、《命题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哲学教材采用的是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和科学课程的教材采用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论动物的部分》、《论天》、《论生灭》、《气象学》(第1和第4卷),心理学教材采用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论感觉》、《论梦》、《论记忆》、《论精神和灵魂的差异》,实用哲学教材采用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政治学》。据笔者统计,人文学院的课程中大约65%~70%的教材采用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⑥尤其是逻辑学和哲学(包括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形而上学)方面的教材几乎完全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所垄断。即便是在以法学和医学见长的意大利和南部法国各大学,医学院和法学院的学生也都必须学习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哲学著作;如欧洲法学中心博罗尼亚大学的哲学必修课程全部采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而所有大学的医学院和神学院的学生都熟知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⑦
以逻辑学为例,随着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著作的翻译和广泛传播,逻辑学在大学课程中的地位也迅速上升,“从12世纪开始,逻辑分析实际上已经在所有学科中得以施行,不论是人文、法学、神学院的学生,还是医学院的学生,他们都必须将自己训练成为一名合格的逻辑学专业人员”,而“在13世纪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巴黎大学,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哲学还成为人文学科的学生通往学士学位道路上占首要地位的课程”。[6](P150)正是由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迅速和广泛的传播,使得在11和12世纪曾作为教会学校支柱学科的语法和修辞学教育迅速降低到了一个附庸的地位,“在12世纪末和13世纪,对古典拉丁文学的强烈兴趣便让位于对‘新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强调”。[1](P321)
亚里士多德对中世纪大学教育所产生的广泛影响还可从如下事实中得到证实:据统计,自1200年至1650年间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手抄本大约有2000部流传至今,失传的可能也有几千部。[7](P89)正如论者所言:“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构成了中世纪大学教育的基础。实际上所有的学生都学过他的逻辑学、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的著作。由此,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中世纪大学课程中扎下了根,在此它成为所有受过教育的欧洲人的共同知识财富。”[7](P97~98)毫无疑问,在中世纪欧洲大学中“亚里士多德是所有被研究的作家中最有影响的一位”。[7](P89)
其次,亚里士多德学说为中世纪欧洲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人们对哲学、自然科学和神学的研究和讨论。
众所周知,随着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一统地位的确立,古典思想便被看作是异教的东西而遭排斥,由希腊人所确立起来的理性的思维方式也在西方世界逐渐走向衰微。在中世纪早期的西欧,这种状况始终没有得到改观。但是随着古希腊和阿拉伯科学与哲学被大量译介到西方,古典的理性思维方式才得以在中世纪鼎盛期重新复活并蔓延开来,而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广泛传播则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中世纪的拉丁学者热切地采纳了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和探索物质世界的途径和方法。那么,亚里士多德所提供的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是什么呢?那就是理性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正如论者所言:“亚里士多德向其拉丁中世纪读者所传达的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方法……正是亚里士多德研究问题的方法教导中世纪的自然哲学家如何运用逻辑推理去探究物质世界的运转。”[7](P91)笔者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理性思维方式和方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奠定在逻辑推理基础上的理性思维方式和方法,其二则是奠定在感觉和经验基础上的理性主义认识论。
亚里士多德并未将逻辑学归于理论知识的行列,而是把它看作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一门科学的方法论,是人类进行理性探索的基本工具。[8](P182~183)中世纪的人们迅速地接受了他的这一思想,将之作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课程,它也逐渐成为经院哲学的思维方式和论证方法,即所谓的“经院哲学的方法”。所以,这种以逻辑推理为基础的理性思维方法也就成为神学家、哲学家、法学家、自然科学家进行神学、哲学、法学和自然科学研究必备的方法,成为他们思考问题所遵循的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传统的修道院神学强调的是通过人的沉思默想而认识上帝,但现在的经院神学所强调的是通过逻辑推理和辩证法而获得有关上帝的知识;逻辑推理和辩证法也同样成为经院哲学的操作原则;经院哲学的方法也被运用到法学的研究之中;逻辑推理的方法也同样广泛地运用到对自然的探究之中,例如理论医学就得益于亚里士多德的科学观念和科学方法。⑧当然这种理性思维方式的确立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个激烈的斗争过程。但至13世纪中期,它已获得了广泛的认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的出现不仅有力地促进了经院哲学和其他各门学科的繁荣,而且还引发了以蔑视权威、提倡怀疑主义和自由思考的个体自主的理性主义精神的出现,从而为近代哲学和科学精神的兴起发挥了一种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⑨
有意识和系统地将逻辑推理运用到对自然世界的探索之中是走向近代科学的第一步,而试验方法则是通向近代科学的又一重要步骤。后者也导源于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认识论。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将科学知识的归纳奠定在感知的基础之上,并尤其强调经验对于知识的重要意义。正是由于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中世纪的自然哲学家也强调将感知和观察作为知识和科学的基础。翻检中世纪的自然哲学著作,我们发现,中世纪的自然哲学家在研究自然问题时大都遵循亚里士多德在探索自然问题时所采用的路径和方法,因此,中世纪的自然哲学亦根植于感知和经验主义。可以说,奠定在感觉和经验基础上的理性主义认识论已逐渐深入到中世纪自然哲学家的意识当中,并导致间接和直接的观察和试验的出现。西方科学史家A.C·科龙比曾论道,“试验论据和试验操作”确实深入到了大学的环境之中,它是通过那些侧重于数学的科学,如“光学、声学、机械学和天文学,通过运用自然力的奇术和通过医学”而被引入到大学中的。[7](P163)其中,牛津大学的经验主义传统、巴黎大学对自然问题的广泛研究和博罗尼亚大学的人体解剖学最为著名。牛津大学的第一任校长罗伯特·格罗塞特斯特将自然哲学建立在数学与实验的基础上;而罗杰·培根则把推理和试验看作是两种认识的途径,并尤其强调科学试验的重要性,因为在他看来,“在科学研究中,推理是不能证明任何事物的,任何事物都依赖于实验”。[9](P30~311)在巴黎,这种实验主义的倾向也十分强烈。巴黎的一些天文学家如凡尔登的伯纳德和圣克劳德的威廉,“最终开始摆脱经院主义的束缚而对事物采取一种更为独立的和实验主义的观点”。[10](P14)这便导致了14世纪巴黎大学一些学者的重新转向:即专注于自然哲学问题的研究。约翰·布里丹(1300~1358)就是其倡导者。他的学生萨克森的阿尔伯特、尼古拉·奥里斯梅等继续致力于具体的自然问题的研究,从而以巴黎大学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学派。其后,该学派的一些成员则将这种经验科学的精神传播到了海德堡大学、维也纳大学、布拉格大学。自13世纪开始,博罗尼亚大学法学院恢复了对人体的解剖,“在14世纪里,这种直接研究人体解剖学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意大利各个医学流派的习惯”。[11](P468)
当然,在中世纪,这种直接的观察和试验仍然是零星的,人们更多的是依据间接的观察和试验论据去证明其理论。⑩根据西方学者爱德华·格兰特的研究,中世纪的学者所引证的试验例证主要来自于古希腊和阿拉伯人的著作,也来自于他们的拉丁前辈和同代人的著作。在中世纪学者有关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著作的众多评注中,就充斥着此类的观察和试验证据。所以,他将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看作是一种没有观察和测量结果的经验主义。[7](P164,P179)尽管这种经验主义是有缺陷的,但是它的出现却有力地激发了人们对自然界的探索欲望。大阿尔伯特、格罗塞特斯特、罗杰·培根等之所以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所成就,主要就受惠于此。
具体到各门自然科学而言,亚里士多德对中世纪拉丁基督教世界影响最大的当属其动物学和天文学。直到12世纪之前,拉丁西方人对动物学的研究还相当微弱。正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学著作和阿拉伯人伊本·西那对它的评注本被翻译成拉丁文后,新的动物学知识才迅速渗透到拉丁西方世界。同时,西方学者如西班牙的彼得和大阿尔伯特还撰写了有关这些译作的评注。尤其是大阿尔伯特,他在评注中还添加上了自己在欧洲各地游历所见的动物(其中有一些动物是他首次发现的),以及从其他文献资料中所搜集到的动物学知识。拉丁人在地质学方面的知识也主要来源于亚里士多德和伊本·西那。在13世纪之前,他们的有关著作都被翻译成了拉丁文。著名的百科全书学者博韦的温森特(12世纪末~约1264)和大阿尔伯特的地质学思想就主要来源于他们。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他们开始了更加深入的研究。阿尔伯特就曾到现比利时西北部的布吕赫进行实地考察;他还亲自到许多矿井访问。苏格兰人迈克尔曾考察过热硫磺泉和意大利第勒尼安海中的利帕里群岛的火山等。
中世纪拉丁天文学界和哲学界有关宇宙体系的争论,即托勒密主义和比特鲁吉主义之争也间接与亚里士多德有关。在古希腊时代,存在着两种通行的宇宙体系:一为欧多克斯·卡立普斯和亚里士多德的宇宙体系,一为托勒密体系。(11)在阿拉伯世界,托勒密体系相当流行,但反对托勒密理论的学者也存在。比特鲁吉主义实际上就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宇宙体系理论,是亚氏同心圆理论的复活。当比特鲁吉的著作被译介到西方时,有关托勒密主义和比特鲁吉主义之争便出现了。尽管托勒密主义最终取得了统治地位,争论也暂时结束了,但它却为近代的天文学革命埋下了伏笔,正如著名的科学史家萨顿所言:“已安然度过的危机并不是徒然的:它为16、17世纪的天文学革命做了直接的准备。”[12](P18)
众所周知,近代科学思维的两大特征是形式逻辑体系和试验观念。而在中世纪,因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广泛传播所导致的逻辑推理体系的确立及没有观察和测量结果的经验主义无疑为近代科学思维方式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总而言之,中世纪西方文化的复兴和繁荣与亚里士多德学说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典文化作为西方文化之源的重大意义。
收稿日期:2010-05-10
注释:
①波埃修(Boethius,480~525)对古代哲学情有独钟,他曾计划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翻译成拉丁文,但实际上他只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工具篇》、《范畴篇》以及波菲利对其所作的注释。这些译著在中世纪早期被广泛用作逻辑学教材。而他所翻译的《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辩篇》、《正位篇》则一直湮没不彰,直到12世纪才被人发现。参见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第四章第一节,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②有关这次翻译运动的总体情况,参见拙著《东学西渐与西方文化的复兴》第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有关亚里士多德著作翻译的情况,参见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er Medieval Philosophy,ed.by N.Kretzmann,Cambridge,1982,pp.74-78。
③这是1366年发表的巴黎大学章程中的规定,参见Lynn Thorndike,University Records and Life in the Middle Ag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4,87。
④这是综合巴黎大学、博罗尼亚大学、爱尔福特大学、维也纳大学有关课程设置的文件而得出的,具体参见Lynn Thorndike,University Records and Life in the Middle Age,26,28,59,87,107,119。亦参见Olaf Pedersen,The First Universities,translated by Richard Nort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278-279,294。
⑤有关各学院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具体情况,参见Hilde de Ridder-Symoens ed.,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Vol.1,Part Ⅳ。
⑥由于不同时期和不同大学的课程设置有所差别,所以我们只能作出一种约略的统计。当然,有许多概论性的教材也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写成的。
⑦有关这个问题的具体情况,参见Lynn Thorndike,University Records and Life in the Middle Age,107; Nancy Siraisi,"The Faculty of Medicine",in Hilde de Ridder-Symoens ed.,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 Edward Grant,God and Reason in the Middle Ag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184。
⑧有关该问题的详细情况,参见Edward Grant,God and Reason in the Middle Ages,ch.2 and ch.3。
⑨有关这个问题,参见张绪山:《经院哲学与近代科学思维》,载《中国世界中世纪史专业委员会会刊》,第12期。笔者亦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参见拙文《中世纪盛期西方理性主义的盛行及其意义》,载《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
⑩有关经验科学精神在中世纪盛期西欧的发展情况,参见拙著《东学西渐与西方文化的复兴》第二章第三节第一部分。
(11)亚历山大里亚的天文学家曾对亚里士多德宇宙体系存在的缺陷进行了修正,并提出了一个新的体系,而托勒密就是这一新的体系的集大成者。
标签:自然哲学论文; 逻辑学论文; 中世纪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哲学专业论文; 西欧中世纪论文;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论文; 尼各马可伦理学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哲学家论文; 范畴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