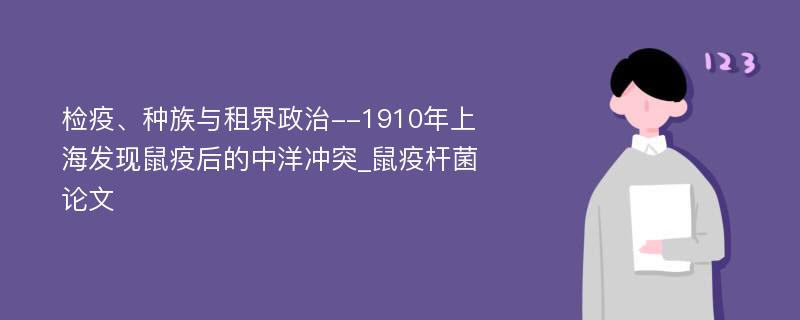
检疫、种族与租界政治——1910年上海鼠疫病例发现后的华洋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鼠疫论文,租界论文,病例论文,上海论文,种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94年香港鼠疫爆发,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和日本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各自成功分离了鼠疫杆菌,在近代细菌学、检疫学新发现的支持下,外人舆论认定危险来自华人的不良习惯和生活环境。当年《美国医学学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刊发的一篇文章声称:鼠疫可以被名之为“野蛮人的疾病”,因为它只在半开化的人群中爆发。① 1905年也是鼠疫继续肆虐香港的年份,当地一份英文报纸写道:“只要有华人在香港,就还会爆发鼠疫。”② 在外人市政当局看来,香港、上海等地与外人毗邻而居的华人社会,人口密集、居住拥挤、乱扔垃圾、随地吐痰,乌烟瘴气的妓院、赌场和鸦片烟馆,以及由于生活贫困,华人苦力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浑身汗臭,均为疾病蔓延的温床。
当疫病爆发之后,将某种特定传染病与某个特定种族联系在一起,并由此对之进行强制性的卫生检疫,其中隐含的种族偏见,自不待言。作为具体检疫法令的实施,1894年香港腺鼠疫病例发现后,殖民政府归咎于华人不良卫生习惯,针对华人采取了诸多违反人道的隔离检疫措施,结果不但引发了华人社会骚动,且至少使10万华人逃离了香港。③ 而在1910年10月底,上海公共租界也发现了腺鼠疫病例,工部局随即宣布在染疫街区实行逐屋检验、消毒染疫房屋、隔离病患及与之密切接触者等强制性检疫、防疫措施。其时,腺鼠疫虽已被认定是通过鼠蚤传染到人,与卫生环境不一定有直接因果关系,但在租界卫生官员的眼里,西式建筑宽敞,多用石头、水泥构建,有较高的台阶;华人房屋低矮、阴暗、潮湿,多用木质材料构建,且四周堆集着秽物垃圾,较容易滋生老鼠——种族范畴仍是外人设定检疫对象的主要考量。④
与租界外人种族偏见相关的,是华人社会的抗争和华洋间的政治角逐。至1910年代前后,租界外人仅有1.3万多(其中英国人4465人),租界华人则超过41万;而且,不同于租界早期华人多为避难寓公、买办、通商、长随,这时不乏投资金融、保险、面粉、缫丝、棉纺业的巨商,以及报人、律师、医生等,在租界的实际影响力不断扩大。⑤ 虽则20世纪初的上海租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英国海外殖民地,但在不平等条约的充分保护之下,作为市政管理机构的工部局由外人居留民自行选出,华人居民被严格排除在租界行政事务之外,在政治权益上与沦为殖民地的印度、香港没有多大区别。不过,就租界华洋相争的历史来看,随着经济实力增长和社会地位提升,华人社会早就提出参政、议政的要求。1873年,《申报》就刊文称:租界之内,华人林立丛居,与西人相较,其数几将百倍。“工部局诸值董,除举立西人而外,若能再添公正殷实之华绅数人,与西人一并聚叙,则上海租界平日之各事务,中外值董会议而后行,彼此必更大有裨益矣。而且捐银供给工部局各费,既系华人与西人一例遵行,则会议一事,亦当令中外一例,公事互相商办,亦所甚宜者耳。”⑥
那么,在1910年针对华人的检疫中,一直谋求参政、议政的华人如何参与,居于统治地位的外人如何回应,权力/权利在不同种族、不同阶级之间进行了怎样的角逐和互动,这些便是本文的基本问题。
以往仅有个别研究简要涉及此次检疫,或只限于对租界统治秩序做出评论,关于检疫、种族和政治的议题尚未充分研究。⑦ 至于租界或通商口岸的研究,尽管这些年来很是不少,但欧美、日本和1980年代以后中国内地的研究,较多关注现代化发展,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影响和示范,很少有人关注政治层面上外人市政当局与华人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更毋论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审视和批判。⑧ 比较而言,中国普通民众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曾是195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主题。不过,在当时“革命史观”的研究框架下,爱国主义的英雄反抗,或流血的暴力革命是最基本的价值预设,介于侵略/反抗间的灰色生存有意或无意地被遗忘或被遮蔽,殖民地的香港、澳门、台湾,半殖民地的租界、铁路附属地,以及1930年代以后的东北和抗战沦陷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反抗史,至今几乎仍是空白。⑨
本文借鉴和参照的理论,是上个世纪90年代非洲、印度、拉美殖民地次属群体的研究。这些学者强调,如果以一种“反抗”排斥另外一些反抗,历史也就只有一种可能性,从而抹煞了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多元性和多样性。这些学者矢志展现殖民统治下次属群体的历史主体性(agency)及多种反抗形式,其中包括在与殖民统治者日常合作中体现出来的日常反抗。⑩ 由此反观上海租界的华人,如果就爱国主义的英雄反抗来看,他们对外人市政当局表面上毕恭毕敬,慎言慎行,肯定不是那个时代热血沸腾的反抗英雄,但从日常生活史的视角进行观察,大量微不足道的细小事件同样可能对外人统治秩序构成严重的冲击和挑战。本文的研究将沿着这样一个思路展开。
一、种族矛盾骤然激化与华人社会的抗争
上海外人对鼠疫检疫的重视,始自1894年5月香港爆发的腺鼠疫。至6月7日降下倾盆大雨之前,香港每天染疫死亡人数超过100人,噩耗通过沪港两地新闻电讯快速传递,让有着欧洲黑死病记忆的上海外人忧心忡忡。6月5日,上海外人商会致信工部局称,如果华界出现疫情,将会迅速蔓延到租界。他们要求当局彻底检查来自香港和广东所有华人旅客的行李。(11) 遵循上海领事团的指令,负责检疫的海关对所有来自疫情口岸旅客的检查持续到9月中旬。工部局除下令清扫租界卫生之外,还在浦东和杨树浦建立了临时性医院和熏蒸消毒站。
1899年4月和1904年春夏,闽、粤、台等地也都爆发了鼠疫,上海海关设在吴淞口外的崇宝沙卫生站,对来自染疫口岸的旅客进行了卫生检疫。尽管其他染疫港口城市,罹患鼠疫死亡之人或数以百计,或数以千计,上海疫情却微乎其微。1904年,海关检疫人员检疫来自染疫港口的442艘船只,12000多名华人和近7000名外国人,只发现1艘染疫船只、2位患者和4位被怀疑感染上了鼠疫的死亡者,以及l位被怀疑为霍乱的患者。被送到崇宝沙检疫站的有8名外国人、143名华人疑似患者,其中3名死亡,11名鼠疫疑似病例和101名与之有接触者安然无恙。(12) 不过,由于人口众多,卫生环境复杂,工部局对鼠疫一直保持高度警觉。1908年11月,工部局卫生处首次在码头附近发现6只染疫老鼠。由于没有发现人群间染疫的病例,工部局只在租界范围内进行了灭鼠动员和大范围卫生清扫,并酝酿将1903年制定、原设想用20年时间逐步实施的“鼠疫预防法”提交纳税人特别会议讨论。(13)
在当时由外人主持的港口检疫中,华人乘客常被作为重点怀疑和查验的对象,故华人早已怨声载道,并将之视为外人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让上海华人直接感受凌辱的,是吴淞口外崇宝沙设立的检疫站。1907年,作为上海国民小学启蒙课本的乡土志称:检疫“以西人主其事。外洋船舶进港,必经此处查验,每于华人多所留难,受其辱者,殊堪发指,而于西人入口,则不加查验,纵之使去,夫验疫处为吾国所设,而犹蔑侮华人,使行旅视为畏途,无怪乎华工华侨之远涉重洋而受彼虐待也。”(14) 就检疫外人生硬、粗暴的态度,一位亲历者痛诉道:检疫人员时用手猛插旅客肘下及股际私处,如站立不牢,几至倾跌,或令含玻璃管以验热度,稍有疑似,即拘至院内监禁。甚至还有检疫人员令旅客鱼贯绕走一二周,以为笑乐。如脚步稍觉滞缓,则被视为有疫之人。无病之人常被查验人员说成有病,强行送到隔离病院。至查验妇女,尤惨不忍言,“曾有及笄少女被其拘去,该女紧牵母衣,呼号欲绝,后经该船买办说情,始准其母随往医院”(15)。
当时检疫被认为是阻断鼠疫传播最有效的手段,1910年10月26日前后,租界发现了染疫死亡的华人患者,当局遂决定在染疫街区对华人进行逐屋查验。27日,工部局董事会主席蓝台尔(David Landale)致信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报告租界发现鼠疫,将准备执行1903年起草的防疫法令。10月30日,英国领事Pelham L.Warren回函同意在租界范围内采取强制性的隔离措施,并告知领事团将向上海道台施压,以配合工部局的检疫、防疫。11月10日,工部局董事会议决“检疫章程”,以法令形式要求检疫包括天花、霍乱、肺结核等一切传染病,并声称要对发现传染病不报、拒绝迁出染疫房屋、阻碍消毒和种痘、超标准聚居在一个房间,以及疫死不报和自行殓葬者等违规行为,处以高额罚款、拘禁和苦役的惩罚。工部局发布通告,称将对发现疫情的华人街区进行逐屋验疫,并讨论颁布相关检疫、防疫法令。(16)
华人社会对检疫早存恐惧,而此次负责之人又都是外国职员。他们大多听不懂中文,不了解华人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平常对华人又习惯于趾高气扬、呼来喊去。当他们来到需要检疫人家时,先使劲砸门,主人稍有拖延、犹豫,立即遭到斥骂;闯入居民家内,不顾华人向有内室不见外人的传统,对所有男女一一检查,致使妇女格外感到羞辱;对居住环境杂乱污秽的华人家庭,又往往不加说明,强行进行隔离和消毒。这些临时抽调而来的查疫之人并非训练有素,一见面黄、或略带病容者,就指为染疫之人,强行送人隔离病院。(17)
更让华人抱怨的是,不法之徒冒充防疫人员,也以检疫为名,讹取钱财。一位华人居民致函工部局,称遇到两位貌似外人的男子,敲门而入,告诉其家眷,说是工部局查疫之人。当他进一步追问时,二人改操西语,随即出门急步而去。作者说:“窃思既系贵局派来查察,亦不应遽行闯入,反手闭门,惊吓妇女,况弟居住上海租界四十余年,安然无事,今因防疫新章,竟有此凭空骚扰。”当局对此似乎又没有办法,不得不颁发告示,称“此等妄为之徒,本局难于禁遏”(18)。谣言于是随之四起,华人人心惶恐,民间风传所谓小儿之身、弱者、及向有夙疫者,将被外籍检疫人员送入隔离医院。11月8、9日两天,城厢内外的茶坊酒肆,无不谈论此事,“于是小儿不敢入学,有旧疾者不敢出外,妇女辈信之尤笃,而愚民又哄传者”(19)。
下层华人民众中的不满引发了街头骚动,并造成大量居民的逃离。据新闻报道,第一起街头骚动发生在11月10日上午9时左右,当外人巡捕一行赴闸北华盛里拘提一拐匿犯人时,民众误以为检查鼠疫,哄动数百人将之围住蜂殴。新闻报道记载的第二起骚动,发生在当天下午,工部局卫生处西员至嘉兴路、哈尔滨路等处调查孩童种痘情形时,民众群起猜疑,一时聚集数百人,欲围攻殴打,该西员寻机脱身而去。翌日(11月11日),见诸于报端的骚动至少有七八起,情节不外工部局西员侦查其他案件,或进行日常卫生消毒,被该地华人民众误以为是进行逐屋查验的检疫、防疫人员,蜂拥而来,不是围攻殴打,就是抛掷石头、灰屑等,洋员和华人助手中不乏受伤者。再就是当街头骚动爆发之时,附近工厂的女工误以为洋人将进来检疫,纷纷停工,四散逃逸。各店铺惊慌异常,一律闭市。菜场各小贩也赶忙收市,街头一片混乱和骚动。不少居民携同小孩及行李,乘车进入法租界或华界,“亦有上轮船起行者,捕房得知,向乘车带孩之人询问,均言英美两界西医查察小孩,暂时避开”。(20)
对于下层华人不满而引发的街头骚动,租界行政当局除加强警力威慑之外,还迅速严惩了所谓聚众滋事之人。在11月10日骚动爆发当天,各捕房捕头,各带手枪,督同西、印各捕,肩荷洋枪,四处稽查,随时准备驰往肇事地点。各处水龙间亦均警备一切,以防不测。11月11日下午,工部局因租界居民误听谣言,酿成暴动,特开临时会议,决议刊印两份华文布告,立即散发给华人民众,“声明谣言之由来,切戒居民勿得轻信”。傍晚,驻沪各国团练暨各捕房西捕排齐队伍,先由各国团练马队开路,中间继以马驾车轮大炮数尊,后殿以各国团练、中国商团步队和各捕房西捕,皆荷枪械,前往英美租界四处巡逻,以张威武。工部局官方文件的记载是:从11月11日至18日,华人社会发生了多起骚动,几乎演变成一场暴乱,巡捕和卫生执法人员受到了攻击,有受重伤之人,致使工部局不得不指示巡捕佩带枪械,并征召了万国商团作为后备。(21)
在街头骚动中,殴打外籍检疫人员和巡捕的滋事嫌犯,被英美各捕房迅速缉拿归案,随即进行审判以作威慑。11月13日上午,捕房将被捕民众装以“香港车”,前后由身材高大、相貌威武的印度巡捕骑马持械守护,押解公堂,进行司法审判。18日,捕房再将这些人用双马车,选派印度巡捕多名,肩荷洋枪,押解到廨,进行讯问。19日,他们又由印度巡捕肩荷洋枪,用双马车押往公共公廨,进行宣判。在会审公廨的大堂上,被捕民众均不承认是骚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只说当时在旁观看和随众起哄。一位名叫王安琴的人犯供称,他年龄31岁,曾在洋人处为厨师,此时已失业,家中有老母、妻子。当天,他往菜市场购买鸡蛋,行经源昌路,见有众人胡闹,未敢随众附和,因为“工部局查验鼠疫,系有益于华人卫生,小的并不反对”。尽管如此,受审民众仍被分别判处拘押西牢半年、一年半、两年,期满之后枷示七天或两个礼拜。在公共公廨上一再声称自己并不反对工部局查验鼠疫的王安琴,也被认定随众附和而被判拘押两个月。(22)
早在租界采行强制性检疫、防疫之初,华人上层已致函租界行政当局,要求暂停外人单方面的查验。及至当下层社会因检疫、防疫群情鼎沸之时,旅沪宁波同乡会绅商乃于11月11日致函工部局,云:检查鼠疫一事,本属慎重卫生起见。然民众以讹传讹,纷起疑惧,因而请求工部局邀集中西商董,会议商讨能够为中外双方都接受的检疫、防疫办法。12日,洋布公会也致函工部局总办,批评工部局先时未经宣布,霎时挨户搜查,妇孺无知,徒致惊恐,若再继续严厉检疫,恐酿成事端,败坏商业不止。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华人与西人体质不同,面黄清瘦者不足为奇,况鼠疫一症,愚者鲜知,即使果有传染,只能令其自赴医院,或中或西,听人自便,庶几人心可定”。13日,商务总会发表公开信,不满西报所登工部局准备提交讨论的检疫章程,呼吁华人各公所领袖集会讨论,婉请工部局只检查鼠疫,其他传染病概不查验,并允许华人自设医院,帮同检查。在他们看来,“租界华民人心惶惶,寝食不安,殊于市面大有关系”。(23)
同一天,还有宁波商会、棉业商会、丝业商会、钱业公所等华人组织,也联名致函工部局总办,称致使民众骚动和社会不安的原因,在于检疫法令不仅为预防鼠疫,且还涉及天花、霍乱在内的所有传染病。这封信最后写道:强制执行防疫措施将会困难重重,华商愿意协助外人市政当局进行宣传和说服,让华人民众理解防疫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不过,前提是必须修改防疫法令,不再冒犯华人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24)
工部局只是一个市政管理机构,租界名义上的主权由中国政府行使,该地的华人民众仍是中国国民,除遵守租界法令之外,还受清地方行政长官上海道台的保护。11月9日,公共公廨华人谳员致函英国驻上海副领事称,请转告工部局,调查疫疾,原为保卫闾阎,法良意美,惟中西习惯不同,前者华人已将吴淞口验疫视为厉阶,此时工部局在上海租界查验鼠疫,诚恐酿成巨衅。11月13日,上海道台刘燕翼致函英国驻沪总领事,强调由于心理气质和生活习惯的不同,来自西方的检疫、防疫措施虽适用于欧洲,但绝对不适用于华人。沪道声称:租界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租界华人是中国国民,按照条约可以不受租界法令管辖,而只遵循他的统辖。如果工部局一意孤行,强迫华人遵照检疫章程行事,华人则无法安居乐业,上海贸易也将受到严重损失,并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民众骚动,工部局总办应负完全责任。鉴于租界颁布的检疫、防疫法令,未得到华界地方行政认可,沪道宣布华官将不参加公共公廨对违背验疫章程案例的审判,并重申:“上海由道台和首席领事共治,不论华人,抑或外国人,都应共享平安。”(25)
二、华人上层对民众的说服及外人不得已的让步
作为主权行使的体现,华界地方行政参与了对租界华人的安抚,并采取措施防止毗邻的华界出现社会波动。11月10日上午,当闸北华盛里民众围殴外人巡捕之时,该处华界岗巡急吹警笛,召集邻岗,并迅速向巡警分局报告。顷刻之间,华界巡警、马队、侦捕队就赶到现场,将被围西人救出。其时,沪道刘燕翼适在洋务局,当听说内虹口、外虹口各店铺因街头骚动而一律闭市之后,用电话立传会审公廨华人官员面询一切,指示他们前往英领事署晤商办法。
由于担心发生焚毁、抢劫、围哄和驱赶外人等排外情事,刘燕翼还紧急派出官员调查街头谣言。当天下午,刘燕翼与英国驻沪总领事紧急会晤。傍晚,刘燕翼出示晓谕,称:工部局连日防避鼠疫,查验户口,原系有益卫生,只以中西医法间有不同,遂致无知愚民自相惊吓。华界地方行政官员将与英国领事竭诚妥商,“允即由中西官绅会同商议和平办法”,总期与卫生有宜,更与我华人相益。(26) 华界采取的治安措施,是当天在华兴坊、公益里、天保南林里等与租界毗连的各岗位上,巡警分局,均派双班,巡官亲率巡弁,长警分头巡逻,无论昼夜,以维治安。翌日,巡警局、上海县也出示禁止谣言,向民众承诺:“租界防检鼠疫,注重大众卫生,华界权在警局,外人并不来侵。”(27)
作为此次抗争的目标,上层华人提出了华人自主验疫和救治,以及只检疫鼠疫一种传染病的要求。11月11日下午,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法政,归国后创办中国红十字会,时任会长的沈敦和(字仲礼)邀同商董邵琴涛、苏葆笙,现场查看被工部局检查鼠疫的居民。面对因房屋消毒,衣物损失而不胜怨苦的居民,沈敦和等郑重承诺:将争取工部局不再来打扰,“惟我们绅董自开医院,派出中国医生前来调查,尔等不必惊慌”(28)。同日,《申报》刊登《沪北同人公函》,以1894年香港腺鼠疫爆发时,港英政府同意将染疫华人送至华人自行开办的东华医院为例,声称华人诸董将与工部局商酌在适中之地,设立医院,“凡我华人患此疫症者,可进所医治,共保平安”。(29)
11月12日,工部局遍贴告示,将于14日下午5点在小菜场召开寓沪各西人特别会议,讨论检疫章程。同日,旅沪宁波同乡会发散传单,号召和平争取自行进行检疫、防疫的权利,并于翌日(13日),邀集各公所、各业、各团体公议对策。沈敦和撰写英文公函,参加会议的80余名商董头面人物签名,即刻送呈工部局总办和两份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泰晤士报》。这份英文公函称:工部局只要顺应舆情,但检鼠疫,华人商会将自设医院,“帮同检查,以尽义务”。自11月初开始,沪北商董连续几天商讨具体实施办法,拟集资5000元,聘请精明中西医理之华员数人,择一相宜之地,创设临时医院,“凡租界华民任其自行设院验视,如果有疫留院医治,无病者给以验单,以后工部局西医,再往查验,即出验单与观,可以免验。惟须妥议办法,商准西官,然后实行。”(30)
14日下午5点,工部局在小菜场召开纳税西人大会,议决是否同意只查鼠疫一门,其余各病一概不提。为了动员更多的外人参与,上海外人中广有影响的英文报纸《泰晤士报》刊发文章,称以选举票585张为定额,由于形势紧张,尤望来者联翩而至,勿以为此事与己无关。作者认为,鉴于华人社会出现了骚动,目前不是宣布此章程的最好时机;如果必欲实行,须由华人帮助或另想聪明之法,始可从事。此时华人丝业、洋货业、银行业、丝厂、宁波会馆、广东会馆、报界等,均要求只查疫症。“故此事似应与华人通力合作,将章程修改妥适,而其余各症俟之以后可也。”(31)
由于检疫涉及自身利害,外人到会者甚众。租界当局特意增派团练一队在四周保护,以防不测。与会代表听取了工部局总办蓝台尔提交的检疫章程,以及草订此章程各款之理由,然后进行了讨论。华文报载,最先发言的是福开生,他提出应考虑加入工部局及领事公会认为危险传染病将流行之时,有权宣布检疫、防疫的条款。此议未得到与会者赞成而被搁置。担文律师随之提出修正条款,略谓工部局所拟章程之内,共列有病症13种之多,范围过广,租界居民必致警扰,应请以鼠疫为限,其他传染病症悉行删去。话音未落,老公茂洋行经理皮亚士起而附和,谓:吾人不能听令疫症亡吾民,亦不能通过能使吾民自亡之章程。除鼠疫之外,其余传染之病症,应该悉行删去。参加会议的外人也纷纷表示意见,称自有租界以来,华人的情绪,从未如此激愤,此事应与上等华人合办,并议决检疫章程“悉心修改之后再行公布”。(32) 当晚7时,工部局代理总办在客利饭店宴饮上海华字报馆六名记者,通报了纳税西人会议议决采取华商公函,“凡检出确系鼠疫,始照所定检疫章程办理”(33)。
华人社会的紧张未因纳税西人会议的这项有利决议而趋稳定。11月15日两点半,工部局召开虹口区居民特别会议,目的在于向民众散发预防鼠疫方法和谴责骚动的传单,附近街区聚集民众达数千人之多,险些酿成又一场骚动。在场新闻记者描述道:本埠华人来者,皆怀一种恶感,喝叱外人,掷击巡捕,“情状汹汹,大有前数日景象”。至会场门开启之后,数百人蜂拥而入,将会场挤得水泄不通。会议开始之后,外人医生摩尔先解说查验鼠疫之理由,甫毕,沈敦和起立发言,不及数语,叱咤之声,此起彼落,禁遏无效,会议不得不在一片喧闹声中即刻结束。翌日(16日),当居民听说工部局移至大马路议事厅续行开议,又有人群聚集,致使周围街道人极拥挤,车马不能往来。“附近老闸捕房恐肇事端,即饬中西探捕到场弹压,旋由解事者告以续议之期尚未最后决定,决定后一定登报,大众始散。”(34)
面对可能爆发的又一波骚乱,华人上层竭力强调文明抗争的重要性,并对普通民众进行了劝戒和说服。在15日下午哄闹的会场上,旅沪宁波同乡会向与会者分发传单,云:工部局议行检疫章程虽本与我居民大为不便,但近来各西商、各西董采取华商舆论,做出了一系列的让步,“务望我华商居民各安生业,勿再迁移为妥”。沈敦和也当场慷慨陈词,日:“我即沈仲礼,宁波人,亦是上海居民,你们心里要说的话,大致同我一样的,我必约同各帮、各业,合开一中国医院,华人有病者,均自己医治。”此时,台下身穿短衣者均脱帽狂呼,表示支持。接着,沈敦和等向民众承诺将向工部局要求不强行给儿童接种牛痘,即普通民众谣传所谓“捉小孩”之事。由于会场喧嚷,为了让后面的听众明白台上的人说什么,老巡捕房书记员邹雅林还在黑板上特意书明,“小孩从此不捉”。最后,沈敦和告诫民众:“工部局西董昨日商议后,以此新章与华人颇为不便,且颇采取华商公函,只查鼠疫一门,其余各普通传染病一概不查,业已由各报明白宣布,我亦有传单交四明同乡会分送,西商既如此明白俯顺舆论,我华人岂可扰乱,作不文明之事。”(35)
针对15日华人大会的混乱,16日《申报》刊发专题文章,曰:“我中国前此屡屡吃亏,皆由我同胞于事前未及深思,莽莽撞撞,轻举妄动,及其究也,卒为外人所藉口。我同胞试思之,今日开会,工部局与华人正合筹治安与卫生兼顾之策。卫生中西亦有关系,治安中西亦有关系。我同胞其思之。慎毋轻举妄动,以蹈前辄,此则,记者愿为我同胞垂涕道也。”(36) 同一天,沪道也发表告示,称:“目前查验鼠疫一事,既经工部局暂停,并仿照吴淞防疫之法,由中国官绅,另在租界外设一医院,遇有租界染疫华人送交华医院医治,较为妥便,所有寓居租界华人务各照常安居,听候中西官董筹办。”(37)
商务总会是被外人市政当局认定能进行合作的唯一华人团体。17日,工部局致函商会,邀请各帮公举董事组建特别委员会,与工部局公举之西董共同会商检疫、防疫事宜。18日下午5时,商务总会代表至工部局与诸董、律师、卫生处医官等协商防疫办法。华商代表希望与外人与会者磋商的,是商务总会11月4日提出的四条建议:(一)一切普通传染病概不查验;(二)华人有患症形似鼠疫之病,即报告中国自设医院,由院中医生前往调查;(三)凡租界华人如有染疫死者,其棺殓等事,悉照中国风俗,由该家属自行殓葬;(四)防疫捕鼠,均由华民自办。总之,华商代表期望通过会商,采取一些在工部局卫生官看来有效,且不会遭致华人居民反对的检疫措施。报载,会议开始后,沈敦和问道:工部局所拟检疫章程七条,是否将查验一切普通传染病一概取消。西董蓝台尔答云:此项已经取消,无庸提议。沈敦和又问道:近闻检查鼠疫拟有新章,不知确否。工部局副总办即将所拟草章交由沈敦和阅读,并声明此系草案,并不马上付诸实行,即使将来付诸实行,亦必先请中西董事联合允准。华董周金箴、邵琴涛接过话头,说:“我们今日来此,并非为租界华民代表,实系欲调停其事,斟酌和平办法,使华人得免警恐,以期俯顺舆情。”(38)
此次会议华洋之间争论十分激烈。讨论到华人能否自主检疫的议题时,一位工部局董事提出:上海租界居民分华人、西人,照华商所议华人自办查验,若不能有效阻止鼠疫传播,则此等办法“但顾华人一面之恐慌,而不顾西人一面之性命,何得谓之和平方法?”另一位工部局代表不满地问道:商务总会四点要求,有三点已被基本认可,惟外人认为华人自行查验鼠疫一项,“须由西医一同前往,且西医只是随往,并无看脉之事,诸公何坚持不能应允?”沈敦和说:“我等所坚持者,不过顺应舆情,人所不愿者,我等是亦不能应允。”话音未落,西董大哗,不少人语气激昂地说:西人特别会议已接受了商务总会的提议,只检疫鼠疫,其余传染病不再检查,此时“又并鼠疫亦请免查,是言而无信,以后再有公函,恐将全无效力,且事近欺骗,旅沪西人势将全力反对。今日会议之一番和平初意,全归水泡,设果闹事,谁执其咎。”沈敦和赶忙声明,说自己并非不同意查验鼠疫,而只是改请华人自查。
工部局代表对四点建议中的第二、三点有较大的异议。具体来说,第二点是华人自行查验,工部局代表认为有欠周妥,还须商酌,理由是上海鼠疫业已发现,此病传染极烈,以前香港、广东发现之后,传染至10万人,若不厉行检疫、防疫,则旅沪中西人士无不人人自危。第三点是华人自办隔离医院,工部局代表认为租界设有华人隔离医院,且装备良好,再设立一所类似医院没有必要。华人代表坚持,首先,港、澳发现鼠疫时即由华人自设医院、自行调治;其次,上海于每年夏秋皆在租界开办时疫医院,6、7、8三个月,医愈人数总有3000以上,为工部局卫生处官员所称赞,表明华人有能力自办医院。工部局代表承认:由于风俗习惯相同,华人医院就医者多于外人主持的西医院。不过,经过四个多小时的商讨,双方商定检查鼠疫归华人自设医院,派出华人之习西医者,和平调查。考虑到对妇女的验疫,检查人员将偕同一女医生同往。
就检查鼠疫地段,华人商董期望缩小范围。双方辩论逾时,始限定南至苏州河北至海宁路,东至北河南路西至北西藏路,其余各处均不调查,并以一个月为期限。西董说:“照此办法,我等可谓极顾民情至矣、尽矣。望诸公担任实力调查,并劝导愚民疑惑,以保治安。”11月20日傍晚,工部局颁发防疫办法,宣布同意华人自设防疫医院,自行调查华人有无疫症者,调查区域限于北河南路、西藏路、海宁路、及新衙门前为限,其余各区毋庸调查;工部局不再开华洋大会,即有患疫而死亡之人,仍听家属自由殓葬,工部局不予检视。(39)
对于检疫、防疫的特殊权益,工部局及领事团不轻言放弃,因为这是不平等条约的一个重要部分。早在11月13日,沪道刘燕翼即在致英国领事的信中谈到,租界华人仍是中国国民,受中国法令保护,可不受工部局检疫章程约束。英国领事将此信转给了工部局董事会。16日,工部局总办蓝台尔回复英国领事,称:道台的信表明他对土地章程和租界卫生管理法的无知,领事团务必向道台郑重指出,工部局即将颁发的检疫法令符合土地章程的规定,在没有得到特别纳税人会议表决通过,以及上海外交使团批准之前,这项法令是不会实施的。然而,如果得到通过和批准,工部局应得到这样的保证,“即有权力让居住在租界的华人和外国人遵守”。12月6日,沪道又致函英国领事,表达对工部局在租界毗邻华界地区进行检疫的不满,要求工部局不要越界干预。8日,工部局总办蓝台尔回复英国领事,说这项检疫工作已经结束。他说,即使继续这项工作,也不能交给华界,因为中国官府会因此开征新的捐税,民众也就可能将不满转移到工部局身上。(40)
外人市政当局所以做出让步,并非出自对中国国家主权和华人基本权益的尊重,而是担心事态如果继续恶化,上海市面及其商业活动将受到严重影响。16日,工部局总办蓝台尔在致英国领事的又一封信中称:12月6日上海道台的信函提出了不要干涉租界以外事务,是老生常谈。他希望英国领事让道台意识到鼠疫的危险性,租界毗邻的华界必须采取更为严厉的预防措施。11月16日,当租界谣言四起,人心浮动,一批民众开始逃离租界时,工部局总办回复会审公廨华界谳员的信中称,其他城市已有先例,毁灭性疫病都曾造成人口惊慌外流和贸易急剧衰落。上海作为远东最重要港口,商业活动不能受到任何干扰。“面对迫在眉睫的危险,工部局和外人社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当务之急是避免灾难的发生。”(41) 11月18日,中西人士会商防疫办法时,华人代表陈述华人自行检疫的理由,也提及市面因验疫风潮大受影响,若再行检查,人心一乱,商业必致损害。山东同乡会的王姓代表称,北帮号客因闻有检疫七条章程各款,束装归去,商品无人过问。西董不得不同意“目前总请先定人心为先”(42)。
外人舆论对华人也向来不信任,认为华人的文化和生活习性保守、落后。早在1895年,舆论谈及工部局卫生署的官方报告时就称华人都是宿命论者,无论官员抑或民众,很少有人相信欧洲预防传染病的方法。一篇评论认为:正是由于华人的愚昧和保守,即使当广东、香港鼠疫来袭之时,上海的大部分华人街区仍没有及时清扫卫生,患有传染病的华人也没有送到隔离病院,对来自南方的船舶和华人旅客并非都进行了严格验疫。让作者担心的是,检疫、防疫仅是欧洲人的关注,“作为形式上的法令,只是礼貌性地向部分华人进行了宣布”(43)。
不过,当此次检疫、防疫过程中出现街头骚动后,外人舆论意识到如果没有华人上层的合作,租界当局采取的检疫、防疫不可能取得实效。一些外人认为:虽然上海华人比封闭的内地开化许多,但他们中大多数人仍相信鼠疫是外人为奴役华人而炮制出来的,很多无稽之谈在民众中盛行,纷传查出的染疫之人将被送到隔离病院,必死无疑。此外,还有那个根深蒂固的神话,即小孩眼睛将被制成药丸,都无非想说明外人正对华人进行一场狡猾的战争。虽则卫生处官员准备针对华人无知进行宣传,请里弄派代表参观隔离病院,并向民众分发宣传防疫必要性的传单,但只要是外人主持,这样的行动就不会产生多少功效。外人的舆论普遍认为:最好从华人行会和当地有声望的人中遴选代表,利用有影响的华人报纸,成立附设于工部局的华人委员会。让这些人到茶馆和其他华人聚集的场所进行宣传。他们不会受到华人的怀疑,“一旦与华人进行了合作,租界卫生署将无后顾之忧地采取更为全面的防疫措施”。(44)
三、华人自主检疫的展开和外人的刮目相看
将瘟疫视为神鬼作祟,是当时租界下层华人社会的普遍认知。对此,华人上层需要首先进行广泛宣传,以使普通民众在西方近代防疫学意义上了解鼠疫的传染危险,以配合即将展开的华人自主进行的逐屋检疫和消毒隔离措施。11月12日,由知识精英组成的慎食卫生会召开第五次会议,“研究鼠疫之酷烈及防范办法,以备布告居民,使知利害,庶日后续行查验,不再致有阻挠之举”。同一天,《申报》刊载《敬告住居租界之华人》一文,称:吾同胞对于公众卫生,向未措意。故一闻有人代为强迫疗治,则徒起惊疑,指为骚扰。“其实狃于旧习,昧而不自知耳。记者以为与其将来至疫气盛行,死亡相藉,始叹防维之不早,何如乘今日鼠疫发见之始,稍费一手足之势,以荡除疫气而宁我室家乎?智者,虑患于未形,愿我住居租界之华人一图之。”(45)
由于长期以来深受外人的蔑视,华人上层希望通过此次检疫、防疫的成效,洗刷华人愚昧落后的恶名。11月20日,当工部局宣布同意华人自主检疫后,华人舆论特别针对华人民众云:“第一,勿以为查验鼠疫事,工部局已允通融而任意秽污,不加修治,第二,当知自立医院亦当随时查验防疫,如防水火盗贼,此乃公共卫生。”(46) 接着,华人报刊以《授人口实之可恨》、《授人口实之可忧》、《华人竟自愿放弃主权乎?》为题,报道某些街区的华人居民不注重卫生而被西人查处的消息。(47) 相关评论呼吁民众须知华董所能争回检查权者,实藉口于俯顺舆情之一语,“毋使人顺我之情,而我转拂人之意”。(48) 再至24日,上海租界华人中最有影响的宁波旅沪同乡会发表告华界同胞书,云:对于华人的自主检疫,如果民众能争先恐后,扶老携幼,惟恐不及早检查而致贻害,则“非特我华人自行检查实较胜于西人,工部局将自此深信矣,工部局将自此敬礼矣,即我租界华人亦自此可自由矣。否则一落千丈,真有不堪设想之势。”(49)
华人社会着手筹办隔离病院,以便患者或疑似患者接受隔离救治,是自主检疫的第一步。作为华人自办隔离病院成功的范例,是早在1904年商务总会诸董以设在崇宝沙的隔离医院孤悬海际,风涛汹恶,院中饮食、治疗均为西式,华人诸多不便,特意禀请南洋大臣指拨巨款,在吴淞口里之浦东北港咀地方自行捐建的华人自办的中国公立医院。让华人社会能够接受的是,进口轮船旅客经外人医生验明有病的华人,即可到该医院隔离治疗,一切起居服食医药等事悉遵循华人习俗。该医院年经费“约二万三千金”,计有正屋6间,平房5间,病房12间,三叉港停柩所3间,冢地4亩3毫,悉由在沪官商捐输集事,所差常年经费,来自广东善后局每年捐助的1000两和上海地方政府每月下拨的1000两银子。(59)
此时,为筹集创办隔离病院的资金,华人精英进行了广泛的动员。11月22日,粤绅张子标将宝山县境北一个有10余间洋房,占地11亩7分的庭院捐出,上海道台禀准拨给官款银1万两,再加上商务总董虞洽卿、沈敦和、朱葆三等人捐助的数千金,大部分资金有了着落。同时,在一般市民中的募捐也紧锣密鼓地进行。11月26日,沪上颇有名望的新式戏剧社——雅歌集,决定周六午刻合集会员,假三马路文明大舞台演唱改良新剧,并宣布除开销之外,所得看资皆拨充医院经费。(51)
接下来的逐屋检疫,华人精英认真负责,一丝不苟。11月23日,是工部局与商务总会议定华人自主查疫的第一天,先由外人医生考克司及其学生负责的病房做好了接收患者的准备,四名精于西医的华人、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女医生黄琼仙和一位西人女医生负责逐屋检疫。与此前外人主持的验疫不同,华人验疫人员和蔼耐心地对患者进行甄别。12月6日城内石皮弄各居民致函医学研究所,谓该处四十三号门牌陈家发现数名传染病人,有头面肿胀者,不知是否鼠疫,请即检查。“该所董立即会同西医暨司查员前往查明,系一小儿偶患天花,传染于二十余岁之男子头面俱肿,势颇危险,惟实非鼠疫,该所董嘱令善为医治,并清洁屋舍,以除秽气,一面即布告邻人,毋庸疑惧。”(52)
此外,华人检疫人员不仅检疫,且对患者还表示关爱和抚恤。12月3日,对于此前被工部局检查鼠疫,薰洗房屋,给各铺户造成财产损失的华人家庭,诸商董出面与房东们交涉,代恳免付租金一个月,并恳请工部局免付本季巡捕捐。报载,诸商董最终说服泰安里一位房东宁波叶氏,同意免房租一个半月,至巡捕捐一项,因工部局收捐处系独立部分,未便通融,诸君于是商之卫生局医官,允各抚恤洋二元,按户发给。鉴于瞽人徐安银因其子恒生惨遭疫死,“终日号哭,公立医院特给抚恤洋五十元,杨信之君又给洋二十元。尚有好善人士募捐款项,存于四明银行,生息以赡其家。”(53)
华人验疫人员对被查出罹患疫病,或疑似患者及家庭,和颜悦色,耐心说服,报刊有多篇报道。11月29日,验疫人员在阿拉白司脱路美华里30号发现身患热症,形似鼠疫一人。当由医士劝令人院调治,经取身上血点,交由红十字会外人医生用显微镜检查,“并无疫毒所患,实系冬温,是以仍用橡皮卧车,嘱该氏之夫陪送回家。其夫以家寒,无力延医为言,董事沈观察(沈敦和)允请张骧云医士每日亲至其家诊视药饵,一切均归医院代备,概不取资,李某遂感谢而去。”再如12月7日早上,公立医院接卫生局电话,谓阿拉巴司德路美华里第39号屋内先有疫鼠发现,继有老妪女子二人病故,当经总理派出两位医生驰往该处检查,查得该女子已亡,同榻幼弟腿脚已有小核,幸未发热。“即经王培元君商明,卫生局将女尸验毕,免其送人验尸所,以求体恤,一面将其孩遍种防疫苗,以免传染,办法甚为和平,附近居民毫不惊诧。”(54)
华人社会情绪稳定的原因是,在验疫展开之前,公立医院、商务总会各帮董即已刊发传单,派人挨户分送。验疫当天,董事祝某先派书记曹某向居民和平开导,居民咸称只要保证外人不来,一定积极配合华人医生查验。“惟再三叮嘱千万不可失信,再派外人来查等语”。翌日,中国公立医院派出三名华医和三名女西医检查北福建路及北山西路、开封路、阿拉巴司脱路等处,并请宁波同乡施嵋青、应季审、徐其相三人随同。民众任从检查,并无他语。“间有一二处迟疑者,一经施君等开导,无不乐从。”对于民众反应,时人写道:初办时居户亦颇疑虑,每往查时,非一番开导,不得入门,“今则不然,虽未经开导,华医生亦能通名而入。检查极为迅速。五日来已查门牌八百余,计居民千余家。虽稍有反对者,无非下流社会。其余中上等人家,一经红柬投入,即许登堂入室,足见华人渐能开通,从此得免外人口实,洵可喜也。”(55)
随着租界华人获得自主检疫权,华界行政当局和社会团体也行动起来。11月21日,上海道台在致英国领事的信件中通报了华界巡警局将关注卫生防疫,督促居民采取防疫措施和保持清洁。警察局受命检查,并由地方自治公所设立隔离医院。翌日,上海道台发布告示,一改以前以为上海秋冬不会有鼠疫蔓延的认识,告诫华人民众日:工部局查检鼠疫一事,本属卫生上必要之举,只因中西医法不同,风俗各异,居民纷纷警恐,“尔等须知鼠疫之害,甚烈且速,现由华医分段投验,无非为慎重生命,兼顺舆情起见,切勿再行误会”。(56) 11月25日,即租界华人自主检疫展开后第三天,《申报》称:防疫为警察卫生要政,尤为地方主权所在,关系甚大,亟应由华人设法自办,以免外人藉口干涉,并呼吁:“现在租界中既暄传此项瘟疫,业已发现,闸北界址毗连,自应预为之防,以重生命。”(57)
华界慈善团体和知识精英也进行了针对鼠疫的宣传和救助。位于药局弄95号,成立于清嘉庆五年(1800年)的同仁辅元堂,除日常的施医、施药和对病逝患者的施棺、掩埋之外,也开始按照近代西方检疫、防疫理念刊发防疫揭贴,称:西人防御此疫,如防盗贼刀兵。未病施种核苗,已病注射血清,审知鼠能生疫,捕鼠之法惟精。“一事更为要紧,即系清洁家门,污秽最酿疫病,实属有碍卫生,垃圾万勿堆积,洒扫务必加勤。”(58) 统计数字表明:从11月10日上海街头骚动的爆发,至11月16日的一周时间里,租界各种死亡人数不足40人。工部局卫生处在租界搜寻所得染疫之鼠不过3头,沿黄浦外海轮码头则寻获50余头染疫之鼠,专业人士认为上海本无鼠疫,偶而有之,亦由外埠传来(在此次疫情流行期间,除两例疑似之外,真正确诊病例为8例)。(59)
至12月4日,华人自主查验宣告完成,华人精英考虑到中国公立医院设在租界之外,不便于租界居民之贫病者就近诊治,将租界内的天津路80号时疫医院改设为公立医院的分院。司役薪工并房租由红十字会每月承担200两,以沪上最有名望的中医张骧云等20余人轮流义务施诊,所用中药由苏存德堂慷慨捐助。自1910年12月26日至1911年3月的四个月时间里,计施医药1566号,住院诊治33人。此外,按照近代医院的管理模式,该医院立有诊病号簿,以备号董随时考查。筹办者说:惟以筹捐非易,院中一切布置仅较西人医院具体而微,未敢过求精美以壮观瞻,并于开支尤力事撙节。总医院虽占地11亩,花园原址树木亭池居其大半,经防疫会中外官商公议,必规模完备,合于防疫医院之程度,“乃添购毗连空地十亩,增建病房,并造自来水池水塔,现已敷五十人住院”。(60)
华人自主检疫的有序进行,没有引发任何社会动荡,多少让外人对华人社会刮目相看。1910年度工部局的官方报告写道:此次检疫、防疫得到了华人的尽力合作,中国公立医院为患者提供免费救治的便利,华人的护理得到了相当的改善。1911年2月10日,东北肺鼠疫传播至京、津、山东等地,上海面临疫情南下蔓延的威胁,工部局颁布的检疫、防疫公告中,明确宣布华人患疫,查验、隔离、诊治,概归华人医院自行办理;种痘、治霍乱等症,亦归华人自理。就此,曾在此次检疫、防疫过程中作为与工部局进行交涉的主要人物沈敦和说:“鄙人苦心孤诣,往复磋磨,得以还租界华人自立之目的。”(61)
再至1911年6月1日,上海公立医院举行对此次检疫纪念碑的揭牌仪式,有谣传说上海2400户家庭受到鼠疫威胁,工部局准备第二天开始新的检疫。出席揭牌仪式的工部局卫生处医官史丹来博士(Dr.Stanley)发表讲演称:以往疫情蔓延期间,华人不愿意接受外国大夫的检疫和救治,让他记忆犹新。在他看来,中国公立医院的建立,是医学史上一个新中国的开始。出席会议的一位伍姓华人医官预言即将进行的检疫不会再受到民众的阻挠。(62) 果然,1911年8月初,闸北热河路天何里连日内死人甚多,中国公立医院闻讯即派数名医士前往检验,并随即进行挨户严查,发现海宁路、甘肃路、北公益路(今蒙古路)、南川虹路(今新疆路)一带均有患者,速以橡皮马车送往公立医院救治。就此,外人评论道:从第一例患者送到病院,到华人检疫机构和人员努力工作,又发现了新的病例,让人无可挑剔。“正是由于他们的高度警惕,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两例病案很早就被披露,促使其他地区的主管部门及时采取了必要的公共预防措施。”(63)
四、结论
19世纪至20世纪初,在欧美那些接受了大量外来移民的城市,以及殖民地一些重要港口城市,每当鼠疫爆发之时,市政当局都采取了带有种族偏见的强制性检疫措施。1897—1898年印度孟买等地爆发鼠疫时,强制性的检疫措施也引发了印度民众的反抗,并遭到殖民当局的严厉镇压。华人社会除1894年香港爆发鼠疫之外,1900年3月6日,旧金山市唐人街发现鼠疫病例,白人市政卫生当局也只对华人进行了强制性检疫,引发了华人社会的不满。由于只是零星病例,西人医生中也颇有怀疑是否为鼠疫爆发,白人房东和加州官员则担心验疫影响该市的商贸活动,遂与华人商董、清驻美外交官员联手通过法律诉讼,迫使检疫当局停止对华人的检疫。比较而言,在白人当政的地方,不论在欧美接受大量外来移民的都市,抑或在殖民地,少数族裔和次属群体(subaltern group)从未取得自主检疫权,只有上海租界的华人是个例外,这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并颇具世界史意义。(64)
究其原因,或在于上海租界是英帝国殖民体系最边缘,或控制最脆弱的地区。比如,同样作为华人社会的反抗,1894年香港腺鼠疫爆发后,香港东华医院董事会曾与港英殖民政府进行了多次交涉,华人民众也通过罢工、关闭店铺和向验疫人员扔石块,要求停止外人主持的逐屋检疫、隔离病患、焚烧染疫房屋,及将华人患者送入政府医院船(Hygeia)留医。结果是港英殖民政府强调香港乃女王的海外领地,华人必须遵守殖民地法律,并命令Tweed号炮艇停泊在“东华医院和太平山对面”。东华医院只在后来被殖民政府允许收治查验出来的华人病患。对此,当时上海外人评论道:不应忘记,在香港的华人尽管是土著,但他们是外国人,欧洲人则像在英格兰一样;而在上海他们则是在中国。如果在上海采取这些措施,将可能出现“不清楚由谁负责实施,以及由谁处罚哪些违法之人”的情况。所以,此次上海租界爆发华人反抗时,工部局总董不敢效法当年港英殖民政府的强硬和蛮横,因为他们意识到:“除非领事团如前几次那样部署军队进驻,否则租界没有力量违背华人官员和绅士的意愿而实施严格的防疫措施。”(65)
帝国统治赖以维系的威严,不只是依赖于军队、巡捕及不平等条约等各种刚性的法律制度,且还通过刻意营造的征服者、统治者的种族和文化优越——这些柔性的身份等级支撑着英帝国。上海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殖民地,但当时作为租界统治者的英国人,在抵达上海之前多曾在印度、海峡殖民地和香港工作和生活,习惯于对当地人颐指气使,种族偏见和文化歧视普遍存在于日常行为的各个方面。体现在私领域,每一位新到上海的英国人,首先得到的告诫是勿与华人交往,因为不论华人,抑或外国社群对此都不鼓励。接下来他还会被人经常提醒:“别忘了你是英国人”,须在社交、性关系,乃至中餐和汉语方面,保持与华人的距离。(66) 体现在公领域里,则是在租界外人商业楼里工作的华人不能与外人同乘一个电梯;在法租界的有轨电车上,华人不得乘坐头等车厢;除非被外人邀请,华人禁止进入外人的俱乐部;此外,华人被拒绝进入公园和外人娱乐场所——尽管华人纳税为这些设施的修建和维护提供了55%以上的费用。鉴于此,华人通过抗争而取得自主检疫权,不仅挑战了租界外人的政治秩序,且也松动了大英帝国赖以维系统治威严的种族区隔和文化设定。
问题的复杂性自然还在于:华人成功获得自主检疫权,不只是简单意义上统治/反抗的二元对立,且还在于华人精英接受了来自近代西方细菌学理论,将之作为“文明”与“落后”的边界,同样将下层民众的抗争视为愚昧排外或落后迷信。精英们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内在化了西人对华人落后、愚昧的指责,承担了对华人社会缺陷的拯救和教育的责任,并体现在他们言论中不乏所谓彼下流之人及妇女等,“方以生命委任于天及神,若语以微生虫寄生于鼠身,又能传及人身,血轮蕃滋极速,可以致死之理,即此已视为可怪之论,再进与语西医之治法及药水之消毒,皆属茫然”。(67)
不过,就中国现代性的形成来看,尽管出现了这样的分化,但华人精英竭力将来自近代西方的理念转换成与租界外人“竞争的知识”,通过更为人道和更为通情达理的检疫形式,以争取和捍卫自己的权力。在此次抗争展开之初,华人舆论呼吁道:租界居民,工商居多,皆颇存暂时居留之心,视所居之地位如传舍,一旦得志,则捆载而归耳。“故于一切自治、教育、卫生各事宜,凡足以开民智而扩权利者,均不甚措意。呜呼,常此悠悠,听命于人,无奋然自立之念,则此后之租界将不堪复问矣。亟愿租界居民力铲此暂居二字之心理。”(68) 再比较以往被视为爱国主义的英雄反抗,如义和团运动、改革精英的反侵略宣传,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发动的抵制美货、日货等抗议风潮,此次上海检疫过程中的华人精英更多揭橥争取个人权利的自由精神,而非抵御异族侵略的单纯民族主义理念。他们强调华人既然承担了租界纳税之义务,即有代议之权利,无论何国何地方均持此义,所谓“租界华人与西人同一纳税,断无不能与议之理。此皆我华人自放弃权利之故,我愿嗣后租界上凡有所兴革,我租界居住之华人皆宜举代表列席,不独检查鼠疫一事而已也。”(69)
作为连锁反应和事态的后续发展,在此次华人争取自主检疫的当月,商民代表致函工部局,称租界应采取措施降低外人房东的高额房租。此外,当工部局准备设立调查教育部,由工部局总办推举西董15人,华董2人,调查租界内中西人士所办学堂之宗旨、教法、经费等项,并研究改良之方法,又遭到华人社会的反对。减租的理由是近来工部局偶然发现一二家传染鼠疫,即全力扑救,深恐居民一人受害,影响全体。“商民等为租界大局安危起见,预料贵局素敦睦谊,必表同情,且久在中国,早与商民休戚相关,必能俯准商民多数之请求,立赐会议劝减,并乞将如何实行,即日宣布,以安众心,而维商业大局。”(70) 对办学一事,华人则认定:“敝学堂等设学宗旨,悉遵照本国钦定章程办理,亦从未有所隐秘,惟是以华人自筹之经费,设立学堂,教育自己之子弟,乃华人自有名分,不敢劳贵局尽代谋改良之义务。”(71)
为了进一步扩大抗争声势,形成凝聚力,12月11日,这些华人在育贤女学堂会议,公决草定简章,以新闸路三育学堂为联合会事务所,并推举职员11人担任会务。(72) 对此,华人舆论满怀信心,颇多憧憬地说:“向来租界上公共之事,悉由外人掌握,华人全不关意。自华人自办查疫医院,而今又有华人学校联合之事,于是租界上之华人,渐有自治之基,试再进而能与各国商人共列工部局议事之列,自后华人之幸福,当不止此。”(73) 果然,1920年代初,工部局董事会不得不接纳五名华籍顾问,1929年又不得不接纳三名华人成为工部局董事,再至1930年英国人终在工部局董事会不占多数。在这个意义上,此次上海租界华人争取自主检疫,应是大英帝国在上海统治最终趋于崩溃之重要一环。(74)
注释:
① Carol Benedict,Bubonic Plague in Ninetieth-Century China(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40;相关研究还请参见胡成《“不卫生”的华人形象:中外之间的不同讲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6期,2007年6月。
② “Plague is Present in Epidemic form at Hongkong”,The Hongkong Weekly Press,June 3,1905,p.504.
③ 关于此次香港腺鼠疫的蔓延,以及殖民政府采取的检疫、防疫措施和华人社会的骚动的记述和研究文献,请参见伍连德著,郭佐国译《中国之瘟疫与陪斯忒》,《公共卫生月刊》第1卷第10期,1936年4月1日,第3页;“The Plague”,The North China Herald,May,25,1894,p.794;Elizabeth Sinn,Power and Charity,The Early History of Tung Wah Hospital(Hong Kong,East Asian Historical Monograph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159—166;Carol Benedict,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pp.140—147;胡成《东华故事与香港历史的书写》,《读书》2003年第6期,第115—121页。
④ “Health Officer's Report”,Annual Report of the Shanghai Council,1910,p.120,上海市档案馆藏,U1/16/4740。
⑤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0、115页;Robert Bickers,Britain in China:Community,Culture and Colonialism 1900~1949(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9),p.125;相关的研究,请参见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页;蒯世勋编著《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02页。
⑥ 《拟上海租界仿照香港延请华绅会议地方应办事宜议》,1873年8月27日《申报》,第1页。
⑦ 日本学者饭岛涉曾简要提及了此次检疫、防疫过程中公共卫生的制度化发展,中国内地学者傅怀锋以评论的方式,谈到了租界的统治秩序,请参见饭岛涉《ぺストと近代中国——卫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变容》,东京:研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164页;傅怀锋《清末上海公共租界的鼠疫风潮》,香港《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第118—120页。
⑧ 早在1990年代初一些接受后殖民、后现代理论的美国学者就曾批评西方学术界将近代中国视为“非殖民地”,致使研究“置换”(displacing)了对殖民主义的审视。请参见Barlow,Tani,Editor's introduction and“Colonialism's Career in Postwar China Studies”,Positions 1(1),Spring 1993,pp.224—267;Gail Hershatter,“The Subaltern Talks Back:Reflections on Subaltern Theory and Chinese History”,Positions 1(1),Spring 1993,pp.103—130;Shu-Mei Shih,“Gender,Race,and Semi Colonialism:Liu Na'ou's Urban Shanghai Landscape”,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5,No.4,November 1996,pp.934—956。
⑨ 相关评论,请参见胡成《全球化语境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问题的历史叙述》,《中国学术》2003年第1期,第144—170页。
⑩ Frederick Cooper,“Conflict and Connection,Rethinking Colonial History”,American History Review,December 1994.pp.1527—1539;相关的研究请参见James Scott,Weapons of the Weak: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Louise Young:Japan's Total Empire: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1998;Parks M.Coble,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n's New Order:The Occupied Lower Yangzi,1937—1945(Ba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Christian Henriot and Wen-Hsin Yeh(eds.),In the Shadow of the Rising Sun:Shanghai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11) “Precaution against plague”,The North China Herald,June 8,1894.
(12) “Keeping the Plague out of Shanghai”,The North China Herald,July 7,1905,p.10;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海关十年报告译编1882—193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87页。
(13) “Health Officer's Report”,Annual report of the Shanghai Council,1910,pp.90—91,上海市档案馆藏,U1/16/4740。
(14) 《验疫》,李维清:《上海乡土志》,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海著易堂印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9页。
(15) 广肇公所陈维翰:《历数吴淞验疫之惨状——行旅苦之》,1911年4月23日《时报》,第5版。
(16) “Health Officer's Report”,Annual Report of the Shanghai Council,1910,pp.139—140,上海市档案馆藏,U1/16/4740;《上海验疫风潮始未纪》,《东方杂志》第7年第11期,1910年12月16日,第348—349页;《论上海检疫之风潮》、《译工部局卫生员西十月分查疫报告》,《时报》,1910年11月16日,第1版;22日,第4版。
(17) 《育贤女校校长张竹君女医士致工部局函》,1910年11月17日《时报》,第4版。
(18) 《三志租界查验鼠疫之大恐慌》,1910年11月14日《申报》,第2张第3版;《再检查鼠疫风潮之善后事宜》、《唐翘卿致工部局函》,《时报》,1910年11月14日,第4版;18日,第4版。
(19) 《时评三》、《租界查验鼠疫之大风潮》,《时报》,1910年11月10日,第4版;12日,第4版。
(20) 《工部局检查鼠疫之风潮种种》、《西报记查疫事》、《租界查验鼠疫之大风潮》、《工部局检查鼠疫之风潮之续志》、《工部局检查鼠疫之余波》,《时报》,1910年11月12、13、15日,均第4版;《再志租界查验鼠疫之大风潮》、《四志租界查验鼠疫之大恐慌》,《申报》,1910年11月13日,第2张第2版;15日,第2张第4版。
(21) “Health Officer's Report”,Annual Report of the Shanghai Council,1910,pp.106—107,上海市档案馆藏,U1/16/4740。
(22) 《工部局检查鼠疫之风潮种种》、《工部局检查鼠疫之风潮之续志》、《再志租界查验鼠疫之大风潮》、《讯究关于检疫风潮之人犯》、《枷示闹鼠疫之马夫》,《时报》,1910年11月12、13、14、18、22日,均第4版;《八志租界检查鼠疫问题》、《惩办阻挠检疫之华人》,《申报》,1910年11月19日,第2张第3版;20日,第2张第2版。
(23) 《租界查验鼠疫之大风潮》、《再志租界查验鼠疫之大风潮》、《三志租界查验鼠疫之大风潮》,《申报》,1910年11月12、13、14日,均第2张第2版。
(24) “Health Officer's Report”,Annual Report of the Shanghai Council,1910,p.145,上海市档案馆藏,U1/16/4740。
(25) 《公共公廨宝谳员致英康副领事函》,1910年11月10日《时报》,第4版;“Health Officer's Report”,Annual Report of the Shanghai Council,1910,p.143,上海市档案馆藏,U1/16/4740;“Health Officer's Report”,Annual Report of the Shanghai Council,1910,p.146,上海市档案馆藏,U1/16/4740。
(26) 《租界查验鼠疫之大风潮》,1910年11月12日《申报》,第2张第2版。
(27) 《工部局检查鼠疫之风潮种种》、《工部局检查鼠疫之风潮之续志》、《闸北之防患谈》,《时报》,19lo年11月12、14、17日,均第4版;《再志租界查验鼠疫之大风潮》、《六志租界检查鼠疫问题》,《申报》,1910年11月13、17日,均第2张第2版。
(28) 《绅董自行检查鼠疫之先声》,1910年11月13日《时报》,第4版。
(29) 《沪北同人公函》,1910年11月11日《申报》,第2张第4版;《三志租界查验鼠疫之大恐慌》,1910年11月14日《申报》,第2张第2版。
(30) 《沪北同人公函》,1910年11月11日《申报》,第2张第4版;《租界团体会议对付检疫通告》、《中西绅商会议检疫之情形》,《时报》,1910年11月14日,第4版;16日,第4版。
(31) 《论今日特开防疫议会——译自〈泰晤士报〉》,1910年11月15日《时报》,第2版。
(32) 《补记纳税人会议防疫情形》,1910年11月16日《申报》,第2张第3版。
(33) 《工部局总办对于检疫之宣言》,1910年11月15日《时报》,第4版。
(34) 《西报纪检疫会议时滋扰情形》、《中西绅商会议检疫之情形》,1910年11月16日《时报》,第4版;《会议防疫问题之中止》、《六志租界检查鼠疫问题》,《申报》,1910年11月16日,第2张第3版;17日,第2张第2版。
(35) 《中西绅商会议检疫之情形》,1910年11月16日《时报》,第4版;《会议防疫问题之中止》,1910年11月16日《申报》,第2张第2版。
(36) 《为检疫问题敬告沪上同胞》,1910年11月16日《申报》,第1张第2—3版。
(37) 《官绅安慰人心之通告》,1910年11月16日《申报》,第2张第2—3版;《沪道刘观察关于检疫之示谕——为另立医院便人诊治事》,1910年11月16日《时报》,第4版。
(38) 《中西董会议检查鼠疫详情》,1910年11月20日《申报》,第2张第2—3版。
(39) 《中西董会议检查鼠疫详情》,1910年11月20日《申报》,第2张第2—3版;“Health Officer's Report”,Annual Report of the Shanghai Council,1910,pp.150—151,上海市档案馆藏,U1/16/4740;《工部局宣示防疫办法》,1910年11月21日《申报》,第2张第2版。
(40) “Health Officer's Report”,Annual Report of the Shanghai Council,1910,pp.152、153,上海市档案馆藏,U1/16/4740。
(41) “Health Officer's Report”,Annual Report of the Shanghai Council,1910,p.144,上海市档案馆藏,U1/16/4740。
(42) 《中西董会议检查鼠疫详情》,1910年11月20日《申报》,第2张第2版。
(43) “The Health Officer's Report”,The North China Herald,Mar.8,1895,p.341.
(44) “Plague Measures”,The North China Herald,Nov.11,1910,p.317.
(45) 《再志租界查验鼠疫之大风潮》,1910年11月13日《申报》,第2张第2版;《釜底抽薪》,1910年11月17日《时报》,第4版;《敬告住居租界之华人》,1910年11月16日《申报》,第2张第4版。
(46) 《时评》,1910年11月23日《时报》,第4版。
(47) 《授人口实之可恨》、《华人竞自愿放弃主权乎?》、《授人口实之可忧》,《申报》,1910年11月21日,第2张第2版;22日,第2张第2版;25日,第3张第3版。
(48) 《海上闲谈》,1910年11月21日《申报》,第2张第4版。
(49) 《谨告应受检查鼠疫界内我华人书》,1910年11月24日《时报》,第4版。
(50) 《商务总会请南洋拨款维持防疫医院禀及批》,1905年10月3日《时报》;张允高等修、钱淦纂:《卫生》,民国10年《宝山县续志》卷10,第12页。
(51) 《再志检查鼠疫风潮之善后事宜》,1910年11月14日《时报》,第4版;《中国公立医院成立广告》,1910年11月27日《申报》,第1张第2版;《演剧筹拨验疫医院经费》,1910年11月27日《时报》,第4版。
(52) 《西报纪查疫事》、《中国公立医院查疫之辛勤》,《时报》,1910年11月24日,第4版;30日,第4版;《天花传染之疑惧》,1910年12月7日《申报》,第2张第3版;《天花又见》,1910年12月7日《时报》,第4版。
(53) 《中国公立医院检查鼠疫续志》、《分给因疫受害之抚恤》、《公立医院查疫续志》,《申报》,1910年12月8、5、9日,均第2张第2版。
(54) 《中国公立医院检查鼠疫续志》,1910年12月8日《申报》,第2张第3版。
(55) 《中医检查鼠疫之详情》,1910年11月24日《申报》,第2张第2版;《公立医院检查鼠疫详志》,1910年11月26日《时报》,第4版;《中国公立医院检查鼠疫情形》,1910年11月26日《申报》,第2张第2版;《中国医院检查鼠疫志详》,1910年11月29日《时报》,第4版;《中国医院检查鼠疫志详》,1910年11月29日《申报》,第2张第2版。
(56) “Health Officer's Report”,Annual Report of the Shanghai Council,1910,p.152,上海市档案馆藏,U1/16/4740;《沪道宣示检查鼠疫之界限》,1910年11月26日《申报》,第2张第2版。
(57) 《华界防疫尚堪稍懈乎》,1910年11月25日《申报》,第2张第2—3版。
(58) 《刊布捕鼠防疫俚言》,1910年12月14日《申报》,第2张第2—3版;《沪道宣示检查鼠疫之界限》,1910年11月26日《申报》,第2张第2版。
(59) 《六志租界检查鼠疫问题》,1910年11月17日《申报》,第2张第2版;《中国公立医院查疫报告》,1910年12月3日《时报》,第4版;伍连德:《中国之瘟疫与陪斯忒》,《中华民国廿四年海港检疫管理处报告书》第5册,第16—18页。
(60) 《公立医院董事会纪事》,1910年12月15日《时报》,第4版;《公立医院董事会纪事》,1910年12月15日《申报》,第2张第2版。
(61) “Chinese Isolation Hospital”,The North China Herald,June 3,1911l;p.597;“Health Officer's Report”,Annual Report of the Shanghai Council,1910,p.116,上海市档案馆藏,U1/16/4740;《大清红十字会中国公立医院分医院开幕总理沈敦和报告》,1911年3月21日《时报》,第5版。
(62) “Chinese Medical Science”,The North China Herald,June 3,1911,p.391.
(63) “The Plague”,The North China Herald,August 12,1911,p.391.
(64) 请参见Nayan Shah,Contagious Divides:Epidemics and Race in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pp.110—155;关于印度的检疫,请参见David Arnold,Colonizing Body:State Medicine and Epidemic Disease in Nineteenth-Century India(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p.200—240。
(65) 《1910年11月18日特别会议》,载《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95—696页;“The Plague in Hongkong”,The North China Herald,May 31,1894,p.771;Elizabeth Sinn,Power and Charity,the Early History of Tung Wah Hospital,pp.168—171;Carol Benedict,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pp.139—141。
(66) Robert Bickers,Britain in China:Community,Culture and Colonialism 1900—1949(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9),pp.77—78;请参见Arthur Ransome,The Chinese Puzzle (Boston and Now York:Houghton Mifflin1927),pp.142—149;Chen Jerome,China and West:Society and Culture,1815—1937(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9),pp.232—233。
(67) 《论上海检疫之风潮》,1910年11月16日《时报》,第1版。请参见Buth Rogaski,Hygienic Modernity:Meaning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pp.251—252;胡成《不敢轻慢执着理想之人》,《读书》2005年第12期,第145—152页。
(68) 《租界非传舍也》,1910年11月13日《申报》,第2张第4版。
(69) 《时评三》,1911年11月14日《时报》,第4版。
(70) 《请求工部局劝减房租》,1910年11月11日《申报》,第2张第2版。
(71) 《租界学堂致工部局总董函》,1910年11月16日《时报》,第4版。
(72) 《补志租界华人自设各学堂联合会》,1910年12月14日《时报》,第4版。
(73) 《时评三》、《租界华人之渐有活气》,《时报》,1910年12月3、14日,均第4版。
(74) 请参见Robert Bickers,Britain in China:Community,Culture and Colonialism 1900—1949,pp.116—1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