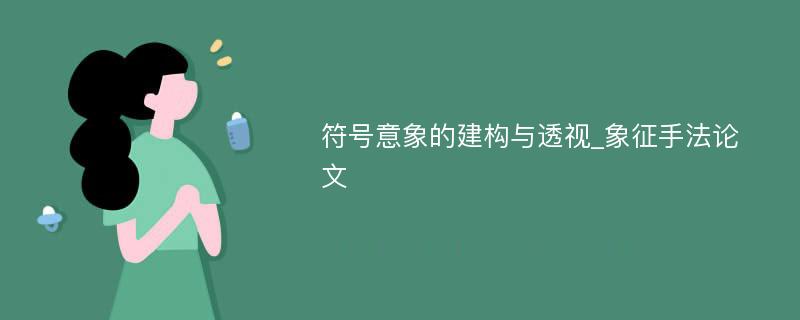
象征形象的营构与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透视论文,象征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象征形象的创造,是为了能够传达出某种象征寓意服务的。这决定了象征形象的本身,要具备透射这种象征寓意的功能。不过,象征形象之所以区别于典型形象的,是其传达寓意的方法是暗示和隐指的,不能也不应该直接体现出它的寓意。这构成了象征形象创造的特有本质与重要标志之一。因此,有意地保持象征形象的暗示性,乃至难解性,成了象征创造的自觉追求。马拉美肯定象征的晦涩与神秘,把象征形象看作“难解之谜”,就把象征创造不求全面展览其寓意的特点揭示出来了。受法国象征诗派影响甚深的中国现代诗人王独清,也有类似的看法。他甚至认为:“不但诗是最忌说明,诗人也是最忌求人了解!求人了解的诗人,只是一种迎合妇孺的卖唱者,不能算是纯粹的诗人!”①崛起于七十年代末的中国当代朦胧诗派,由朦胧而获名,正把象征创造中的暗示性和难解性,作为一种美学原则进行了有效的实践。由此可知,象征创造中的“造谜”倾向,是对艺术创造方式的独特理解所形成的特有文学现象。
然而,决不能把马拉美、王独清和朦胧诗派的观点作片面的引申,以为他们的观点,就是切断文学与一般欣赏者的关系。象征形象创造者们虽有造谜之意图,却不一定都有创造“死谜”、“笨谜”之心愿。象征形象的创造,仍然带有与社会对话,与读者对话的社会色彩。区别只在于:它比写实创造的对话交流更多一点深奥性与抽象性。象征形象的创造保持其暗示性,只不过是在人们走向理解的途径上,设置一些必要的障碍,以激起人们跨越这些障碍的更大自信心和更大探索力,从而培养人们在跨越这些障碍时对生活的更高层次的观察力和思考力。恰如卞之琳所言:“不管您含蓄如何艰深,如何复杂的意思,一点窗子,或一点线索总应当给人家,如果您并非不愿意他理解或意会或正确的反应。”②象征的创造,是把一个谜给读者,是把读者带进一片迷蒙,但又不是仅仅只把一个无解之谜给读者,让读者在无解之谜中沉沦,得不到作品的内蕴。其实,象征形象在其营构之初,就应留下让人进入它的内层的通道,在它所留下的“窗口”中窥探它的隐藏之奥秘。对于高明的创造者和高明的欣赏者来讲,象征形象不仅仅只是一个谜,而且应当是一个有着很多提示和标志的可解之谜。理解象征创造,没有什么通衢大道可循,但可以曲径通幽,应当说,也是堪称满意的。
我们发现,象征形象的营构,往往是按照象征寓意的透射需要设置的。因此,象征形象的营构虽以成为谜而作为成功之一种评估标准,同时,它也以如何才能更好地破译出这一谜底作为其营构之目的。象征形象的创造,实际包含两个过程:一个是谜底的建构过程,一个是谜底的解构过程。建构过程是谜的意义的隐蔽过程;解构过程是谜的意义的敞亮过程。能建构又解构,能隐蔽又敞亮,正好造成了象征形象那特有的含蓄隐晦之美,却又让人能够领略其奇巧之处。这就是象征形象的营构特点,也是象征形象可以顺利透射其内涵的内在机制。
就总的思路而言,为了实现透射寓意之目的,象征的营构,必须做到如下几方面的其中一点:或者离开实在而至超越,从而使读者不被作品的实在的社会关系与内涵所束缚,能在超越实在的情况下,去思索作品之意义;或者脱离具体而入抽象,面对具体,只能得出很具体的思想成果,进入抽象,就能包括具体、消解具体而得到有关人生的抽象思考之哲理成果;或者从此岸到彼岸,不能让读者只观照眼前之物,要安排必要的途径,让读者明白通达彼岸,才达到了理解作品的目的,此时,读者身在此岸,看到的是眼前生活,心却在彼岸,想的是那遥远的东西。有了这样的营构,读者的想象力不是被作品桎梏了,而是被作品激活了,这就必然产生象征形象的创造者们所希望的阅读局面:读者积极参与作品,去探寻作品背后的奥秘。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象征之谜都可轻而易举地被揭破,但揭破象征之谜,领略象征之美,应当说是有了充分的条件和可能性。象征形象的意义,是在其营构之中就被奇妙地悄然地释放过的。这是象征形象营构的匠心所在,也是象征理解的关键所在。
二
借助音乐而升腾,是象征形象营构中实现寓意透射的重要手段之一。作为唯美而又象征的追求者,美国作家爱伦·坡对于诗歌有这样的界定:“语言的诗是美的有韵律的创造。”按照他的理解,诗对音乐的借用,正是诗向自己审美极限发展的必要一步。他说:“我只想先肯定音乐中的节拍、节奏、韵律等要素在诗中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加以抛弃是极不明智的……也许只有在音乐中灵魂才最接近崇高的目的──在诗情激发下力争达到的崇高的目的,即神圣的美的创造。”③整个的法国象征派都对音乐寄予厚望,马拉美对此曾有这样的概括:年轻的诗人们都直接向音乐去吸取他们灵感。音乐成为象征创造中改变诗艺的重要手法。于是,执拗、呆板、生硬减少了,自由、新颖、轻灵增加了。无怪乎瓦雷里主张引进瓦格纳的主导主题的音乐创作手段,因为代表主导主题的某种“特定的旋律,不仅或多或少地暗示一般的形象,它还表明和象征一种特定的思想、概念和人物。”④中国现代诗人穆木天把诗称作是“数学的而又音乐的东西”,可见他重视音乐在象征诗创造中的作用。他曾想写出一首月光曲,就是按照交响曲的方式构思的:月光的波动,草原林木农田房屋的浮动,以及水声风声的响动,与月在轻纱般的云中的律动的幻影,构成了诗,构成了那如音乐般的诗。⑤由此可知,试图“把真正属于他们的东西从音乐中收回来”,⑥是象征主义作家进行创造的自觉追求,象征形象因而具有音乐般的魔力,是象征主义作家们可能达到的一种境界。
为什么象征形象的创造,会对音乐如此倾心呢?原因在于音乐的介入,使得象征形象变得虚无飘缈和空灵悠远了。一方面是:虚无飘缈和空灵悠远,淡化了象征形象的实在性;另一方面,虚无飘缈和空灵悠远,提供了读者理解象征形象时展开更大想象的可能性。象征形象对于音乐的借用,正是对于音乐的抽象性、不实在性和非确定性的借用。德国美学家玛克斯·德索在分析音乐时曾提出:“正因为音乐追求的是象征多于真实,所感受的内在多于外在,所激起的不确定多于所暴露的确定,”所以,音乐深入到世界的精髓之中,揭示了事物的本质。⑦美国音乐理论家伦纳德·迈尔认为音乐不能指明和详述它所唤起的内涵,是其优点,这“使音乐能够表现那些可能被叫作超现实的神话的本质,以及在人类生存中主要的和充满生命力的经验的本质。”⑧结果是,象征形象的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言,它与音乐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起码可以说,是趋向一致的。象征形象的创造,亦会随着它对音乐特性之借用的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对音乐借用多者,其象征性也相当高,象征意义的透射亦相当顺利;对音乐借用少者,亦有从音乐那里承继下来的象征性,音乐依然助成其象征的实现。音乐只要是被象征创造者有意地巧妙地植入文学象征的,象征创造,从音乐那里获得的就是强化其象征特性的美学力量。
爱伦·坡的象征诗《乌鸦》就是诗与音乐结合的典范。诗作意在表达人的忧郁情思。而诗人采取忧郁的句调和低徊的旋律,正好为其特定的内涵找到了恰切的载体,烘托着作品中的忧郁情思去打动了人心。艾略特的名诗《空心人》以其特定的节奏创造出了空虚的失望感,这对引发作品的象征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诗评家就曾有过十分精到的分析:“这首诗的主题是失去人类的生命力──行善或作恶的生命力──的放逐感。那种毫无意义的处于中性地位的情形,正是在最后两行不押韵的诗里引发的。这首诗没有指向某种目的的节奏,它的语言就象其感情一样平淡无奇,消极乏力。作者在开始的几行诗里,通过微弱的、心跳一般的节奏,用诗行中安排的不对称的重音表现出空心人的无生命感。”⑨因此,不以音调的悦耳、悠扬和流畅为其音乐性的特点,看来正是诗人所追求的特殊艺术效果:既然生命已经疲乏,破碎和不完整,那么,表现生命的音乐,又怎么能够不以同样的形态出现呢?其实,艾略特对诗中音乐性之见解,正好佐证了他的诗中音乐性之实践。他说:“我认为诗人可以通过研究音乐学到许多东西……一首诗或者诗中的一节往往首先以一种特定的节奏出现,而后才用文字表达出来,而且这种节奏可能帮助产生诗的意念和形象。”艾略特在《空心人》中的音乐选择无疑是独特的,它证实了诗人所说:“不谐和音,甚至噪音都有其存在的位置。”⑩
穆木天的《苍白的钟声》尤为出奇制胜。其诗行排列与钟声飘荡有机合一,全诗如此设计:“苍白的 钟声 衰腐的 朦胧”一直延至最后两行:“荒唐 茫茫 败废的 永远的 故乡/ 之 钟声 听 黄昏之深谷中”。此诗由于模拟钟声,创造出了钟声的律动,消除了诗中词语和意象造成的视觉感,给人一种听觉的印象。这是一首由词语构成的音乐诗。看起来,它很空虚,空虚得只有钟声或在山谷回响,或在云中游荡,或在树梢流连,或在水中幽咽。然而,这首诗已成音乐,意欲激起的已是人的音乐感,故其把意义交给了节奏,因此,当人们被诗作的音乐带往灰黄的山谷、迢遥的云山和苍茫的故乡时,已心入空谷,或身在云山和故乡,感染上了那种不可言说之荒凉感、寂辽感和悠远感。这首诗不是没有意义,而是借助于音乐表达了它的意义─一一种情绪。其基调是忧郁,是对永恒所产生的瞬间感,对自然的萧瑟所产生的疲倦感。诗人从钟声中听到了这个启示,也就利用钟声的苍白的律动,无力的旋律,驱散不尽的余韵,表现了这种情绪。这首诗的成功,正是把音乐的朦胧、抽象与不确定性的美学特质发挥至某种极致而造成的。
象征性的叙事体裁对音乐的借用,虽然不及象征性的抒情体裁那样广泛,妥贴,有机,但在一些有意者的创造中,亦能达到极高的境地。英国作家伍尔芙在进行小说革新时,曾把象征引进她的小说,音乐对其象征形象的营构与透射,同样不容忽视。伍尔芙的象征小说《到灯塔去》,采用的就是西方音乐曲式学中的所谓A——B——A'结构形式。A——第一主题;B-第二主题(与第一主题形成对比);A'——第一主题的再现(往往是第一主题的变奏。)“第一部以拉姆齐夫人为主题(第一主题);第二部以时间的流逝为主题(第二主题);第三部以对于拉姆齐夫人的回忆为主题(第一主题的再现和变奏)。这样的结构安排,在对比和匀称的基础之上,给人以美的感受。”(11)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到灯塔去》所选择的音乐形式,除了给人以美感以外,与作品象征义的传达关系密切。A——B——A'曲式,富于变化而又主题突出。第一部确立主题,第二部掀起波澜,这看似是第一部之主题的消失,实则是第一部之主题的间歇与重新聚积力量。到第三部再以第一部的曲意复演至结束时,第一部的主题已被强化而显得强劲有力。因此,这种曲式,对于突出某种主题或某种印象,是有很大作用的。伍尔芙选用这一曲式,恰恰出自她的象征创造之需要。《到灯塔去》要表现的是爱对死的胜利,进取对流逝的超越,有序对无序的校正。它以拉姆齐夫人为主要人物统摄作品,实现这一象征义。在第一部分,作品就先声夺人,确立了拉姆齐夫人的主导地位;在第二部分,写的是拉姆齐夫人的死,让其精神接受时间的侵蚀与考验;第三部分表现拉姆齐夫人精神之不灭,在她的感召下,人们完成了应当完成的业绩。对于《到灯塔去》而言,A——B——A'曲式的选用,是带有构思之根本性质的,是其形象存在的模式,而非构思时使用的小技巧,仅仅只是给形象加上的小装饰。
这一切说明,寻思象征寓意,不注意音乐的作用,不愿意从音乐的角度去感受它,都可能是一种失误。音乐与象征太接近了。从音乐角度去感受象征的效果,势不可免。不过,我们也想提请人们注意:非象征的创作中同样也有音乐的成分,但那主要是对音乐美感的借用,音乐只是它的外在装饰,或者,只是它的局部要素,这种借用,不是对音乐本质的借用。所以,非象征创作兼有音乐成分以后,它还是文学,它还保持着语词的硬性与触角。象征的创作一旦与音乐结合,它就与音乐本质化一,它是文学,却已是音乐化的文学;它有语词,而语词已被音乐软化,更象音符。因此,在研究文学与音乐关系时,不能忘却这条原则:只有当文学对音乐的借用,不仅是出自美感的需要,而且也是出自意义的需要,这时的借用,才具有象征的色彩。反之,只有美感的需要,没有意义的需要,这种借用,只有手段的作用。音乐是能够带着象征寓意而升腾的,人们从音乐那里完全有可能谛听到来自象征形象核心的那股意义的强劲震荡,领略到那深藏不露之精深内涵的微妙启示。关键在于人们会不会谛听,会不会领略,总之,音乐已把一切告诉了人们。
三
意象在象征形象的营构与寓意的透射上,也是不可忽略的一种方式。因为“意象真正的功用是:它可作为抽象之物,可作为象征,即思想的荷载物。”(12)这就是说,意象对于稳定地凝聚象征寓意与呈示象征寓意,都是行之有效的。所以,一个创造象征意象的作家总是不忘用其笔下的意象来为他的作品说话,而作为读者,从意象入手理解作品的寓意,似乎也是曲径通幽的正确入口处。
就意象对象征寓意透射的特点来看,反映在意象的营构上,有四种设置方式值得注意:
(一)主导意象的设置。主导意象是指处于作品中心的意象,它对全篇起统摄作用,若把作品看作是一串珍珠,主导意象就是贯串珍珠的红线。作家把自己欲表达的寓意赋予主导意象,正是这位作家由自我走向作品,又由作品走向读者的途径之一。
鲁迅的小说《长明灯》是这样的作品。在作品中,不同人之间的矛盾就因长明灯而起。老一辈的人把它视作神明之光,大多数的人加以附和,只有一个“疯子”要将其熄灭。然而由于寡不敌众,少不敌老,疯人终被囚禁,而长明灯照得更分明和更远大了。长明灯与老年人的结合,与封建势力的结合,与习惯力量的结合,与传统的结合,说明长明灯正是封建主义正统思想的象征。在广大的人民还没有觉醒的情况下,虽有少数先觉者意欲摧毁它,可它仍然是人民的灵魂之光,必将受到人民的崇奉。鲁迅实际借长明灯这一意象,表现与传导出封建主义思想的顽强延续性。
应当注意的是,作品的主导意象之象征寓意的透射,不是单一的,不变的。围绕着主导意象的衍变,可以展开多方面的意义延伸。这样,主导意象的意义透射不仅没有丧失,并且它还可以处于多种意义的中心,构成一种意义之网。在契诃夫的《海鸥》中,“海鸥”之主导意象就有这种综合特点。“海鸥”本是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象征,是自由和成功的象征。作家以“海鸥”命题,并以“海鸥”的命运与人物的命运相映照,就是要用这一意象来透射作品的主调:只有不断地追求自由和胜利,克服一切困难,才能到达生命创造的顶点,完成自身价值的实现。但对于不同人物来讲,“海鸥”的不同变形,透射出来的意义也不同。在妮娜身上,这象征的是一只高飞的海鸥形象。家庭的阻力,婚姻的悲剧,从艺的艰辛,都没有摧毁她对艺术的信心。所以,妮娜是一个胜利的精灵,创造的精灵,是驾驭生活的强者。对特里波列夫言,他是被射杀的“海鸥”形象。他追求纯粹艺术,虽小有成功,却难以大功告成。他在创作苦恼与无爱的苦恼中走上了自杀的道路,这是生活失败者和艺术失败者的代表。特里果林曾将被射杀的海鸥制成一个标本,他自己难道不正是这样一只标本海鸥吗?他有一定创作才能。可并不一心一意去追求艺术的完成;他在生活中产生了爱情,可他并不珍惜它,他虽然也会被人视作翱翔云天的海鸥,实际上只是没有真实血肉和情感的平庸之辈。契诃夫“海鸥”意象之设置,可为一石三鸟,一象三用,不仅透射了海鸥的基本象征义,而且透射了海鸥意象可能有的三种不同寓意:真正的海鸥、死亡的海鸥和无生命的海鸥所对应的胜利者、失败者和平庸者这三种状态。这是象征作品中对主导意象透射功能的一种很大的拓展与充实。
当然,主导意象的选用,还可以主导一个作家的艺术风格,透射作家的基本意旨。屈原与“香草美人”,戴望舒与“雨巷”,艾青与“太阳”和“火把”,艾略特与“荒原”,麦尔维尔与“白鲸”,海明威与“力”,都是证明。一个作家拥有他的主导意象,他就变得清晰一些,易于理解一些。因为这些主导意象透射了作家隐秘的内在情思,成了作家所特有的象征标志。
(二)重复意象的设置。它不象主导意象那么突出,那么引人注目。可是,通过重复的作用,把人们的视线引导到这些意象之中以体悟其中蕴藏之玄机,还是作用不少的。虽然它不能象主导意象那样统摄作品。却能有力地支撑作品。若其与题旨的关系十分密切,对主要人物或事件的阐释至关重要,它所产生的透射强度往往与主导意象的透射强度相近。
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毛猿》在利用“笼子”意象进行寓意透射方面,堪称典范。笼子意象在作品中共出现三次:
第一次笼子意象出现在第一场,用于对邮船前舱的描写。一排排的铺位与支柱互相交叉,象笼子一样,使置身其间的工人无法站直。但主人公扬克洋溢着自豪感与自信心,反对自卑与自轻,自称是原动力,是蒸气,是石油,是钢。他清楚他和同伴的处境,但他感到自己有力量打破这个笼子。所以,扬克是笼中之人,却有不被笼限之感觉,个体的生命力依然是十分强旺的。这样,第一次笼子意象的出现,与主人公发生了关系,却因主人公的藐视而未见其威力。
第二次笼子意象的出现,已使情况有所改观,笼子的意象初露锋芒。扬克因寻衅闹事被捕入狱。牢房就是一个铁笼子。此时扬克感到自己真的关在笼中,但他想到的是辩解,是报复,这使其身陷囹圄,心却未被笼子关死。因此,笼子已发挥了较大的威慑作用,只是由于扬克的反抗,这种威慑作用并未达到顶点。而扬克寻求世界产联帮助之想法的落空,终于使他走投无路,陷入了深深的精神危机之中:“本来我是钢铁,我管世界。现在我不是钢铁啦,世界管我啦。”
第三次笼子意象是在扬克步入动物园时出现的。面对猴房的笼中关着的大猩猩,扬克触景伤情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身在笼外,却正是身在笼中。他想放出大猩猩一道遛遛马路,反被猩猩推进笼中。彻底的失望支配着扬克,他最终死于笼中。
三次笼子意象的重复出现,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不论扬克多么有决心,他都无法战胜笼子而获得自由。所以,笼子意象在剧作中的重复出现,把社会对于个体的挤压暴露无遗;也把人失去自我的孤独感展览殆尽。如果说,一开始“笼子”还不是人的属性,紧接的两次重复,让人无以摆脱笼子的桎梏,人的笼子属性已显得确凿无疑。扬克在笼中死去,正是人无以摆脱异化力量对其控制的准确象征。笼子意象之重复使用,把作家对人的困境的思考很尖锐很突出地告诉了读者。在象征性作品中,《毛猿》不是一部难解之作,与其成功地重复运用了笼子意象不无关系。
从结构特征考虑,重复意象是一种穿插性的意象设置。从意象的这一次出现到意象的再次出现之间,可能留有很大的非重复意象的艺术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作品会展开各色描写。但只要意象的重复出现是适时的,有强度的,在其重复中,就会包容非重复意象的内容,建立起全部作品内容的相互之间的联系与共振。重复意象本身,如果是足以表现寓意的,那么,它在象征的透射中所起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三)逆变意象的设置。逆变意象是对意象进行反处理:由某一意象之日常的预定的性质及意义,转向它的非一般的特殊性质及意义的揭示。逆变意象带有创造者之极强的主体色彩与技巧性。它总是显得不实在,使人们从其怪异中探询其间隐藏的独特寓意。在高晓声《鱼钓》中,这表现为不是人钓鱼,而是鱼钓人;在史铁生《驼背的竹乡》中,这体现为竹的挺拔与人以驼背为荣的巨大反差;在王蒙《杂色》中,这反映在一匹遍体鳞伤的老马,竟然成为出色的千里马的描写上。对于象征形象的营构来讲,逆变意象成为作家超常性象征思维的一部分,通过对事物原有性质的破坏,从而达到赋予事物以超常之象征义的目的。
逆变意象可以分为两种:半逆变意象和全逆变意象。
半逆变意象是指意象之原有性质和内涵受到干扰,因而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意义逆变,但新增性质和意义并未完全取代原有性质和意义,而是新增性质和意义与原有性质和意义共同占有这一意象。半逆变意象就其已逆变部分言,是对原性质和意义的破坏与挑战,所以,这逆变部分同样显得咄咄逼人,使人一见而深感此中的奥义,成为审美注意所无法回避的一个灼热的光点。
作为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思考,诗人公刘的《哎,大森林》中的“大森林”显然就是一个半逆变意象。诗人深深地挚爱它,可也十分痛心地看着它所上演的一幕幕悲剧。因此,诗人在把自己内心深处对其挚爱之情吐露出来之际,也十分自然地吐露了他自己的迷惑不解。诗人把大森林看作是“希望的摇篮”,又把大森林比作“记忆的棺材”,将大森林的富有弹性、饱含养份的枝叶与大森林的枯朽、腐败并置,就不仅仅只是进行艺术上的对照,而是意在揭示大森林在某种程度上所产生的质变。从摇篮到棺材,从充满活力的枝叶到这些枝叶的枯朽腐败,诗中大森林意象的半逆变处理,透射与传导出的,是对某种习惯性认同的否定,这种习惯性认同总是盲目地、过于乐观地只看到社会的光明面,并夸大它。大森林意象的半逆变则告诉人们:他们生存的社会和时代只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与时代,有希望,也有痛苦,有生命的创造,也有生命的毁灭。它不是世外桃园,而是善与恶、美与丑相交织的人寰。
全逆变意象是原有意象之性质与意义被新增性质与意义完全否定和取代。这种艺术处理,用以说明事物的突变。由于突变总是给人以突兀之感,因而也就收到了奇谲的艺术效果,引发人们去思索产生突变的原因,以及突变本身的寓意。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白鲸》就相当出色地使用了这种意象设置方式。在《白鲸》中,除了白鲸这个主导意象以外,土著人魁魁格所制造的棺材与美国木头所制造的大船,是众多意象之中引人注目的两个。它们各自发生的逆变,就把作品的寓意透射出来了。棺材本是魁魁格因病而为自己准备的灵床,而美国大船则是用来追捕白鲸的坚固器具。但在追捕白鲸的最后关头,这两个意象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美国大船被白鲸撞翻,而落水的那只棺材,则成为唯一幸存者的“救生圈”。这告诉读者什么样的思想呢?实际是说,所谓的白人文明正在衰亡。美国大船的被毁,正是白人文明无以自救的证明。魁魁格的棺材挽救了一个白人的生命,正是试图说明白人文明只有依靠与吸收土著人的野蛮精神才能重生。麦尔维尔对于白人文明的严峻思考,对于土著文明的一腔热情与向往,可谓借这两个逆变意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四)随伴意象的设置。所谓的随伴意象,是从主要人物或主要事件之某一特定的内涵出发,对这一内涵起演示作用的营构。它对作品寓意的透射,是比较直接与清晰的。曹禺的《北京人》把这种设置运用得恰到好处。作品意在表现一个封建大家庭的衰朽,为了把它的寄生性、没落性传导给人们,就选用了三个特别的意象来说明曾氏三代的无用与无力。曾皓是曾家的老太爷,关心的只是他的楠木棺材。这不能简单地看作是老年人对死亡的安排,它反映曾皓的本质:除了从封建制度那里继承了繁文缛节的礼仪外,并未获得生存的实践操作能力。作者用棺材作为曾皓的标志,可谓入木三分地刻划了旧制度的末路人的可悲性与腐朽性。曾文清是曾皓之子,成家却未立业。他的随伴意象是“笼中的鸽子”。这位少爷,不乏聪慧,下棋,赋诗,作画,品茗,成为生活的主要内容。富余的是懒散清闲,缺少的是经世致用的本领。即使迫于外在的压力还有些许自谋生路的希冀,这希冀也会因其毫无能力去实现而成为泡影。这就注定了他“精神上的瘫痪”,只能接受遗产,不能创造财富;只有软弱的性格,没有坚强的谋求。家庭的牢笼,或者说传统的生活方式已经软化了曾文清的双翅,使其不能自由飞翔了。曾文清最后吞食鸦片而自杀,不是对人生的对抗,而是他对自我生存疲乏所作出的一种自然的认同。他早就是一只不能飞的笼中之鸽,在笼中死去,不正是合情合理的吗?
曾霆是曾家的第三代。他的现状不容乐观。十七岁的小小年纪就被无爱的婚姻关系束缚着。爷爷期望于他的是早抱重孙,熟读古文,传递书香门第的“圣火”。母亲只知要用他来拴住儿媳,总是用成人的标准来要求这个生理、心理均未成年的大孩子。曾霆实际是一个没有自己独立性格,不能支配自己命运的“可怜虫”。他仍然象其父亲一样,只能过过寄生的生活,根本没有接受过独立谋生的教育。所以,作品给予他的随伴意象是“可怜的小耗子”这一称谓。这预示着曾家的后继无人,也预示着曾家的必将全面朽坏,在其走向衰亡的途中,决没有人能够起死回生。封建主义的腐朽本质,被作者所使用的这样几个独特意象展示得一清二楚。而其随伴意象的安排,则如高明的服装设计师量体裁衣而收到了人衣合一的效果。此时,观衣犹如观人,观人而又离不开观衣了。因此,理解曾皓、曾文清或曾霆,离不开理解“棺材”、“笼中的鸽子”或“可怜的小耗子”这些意象。
四
如果说,意象的透射比起音乐的透射来,要清晰一些的话,那么,以有效的导引产生映照力来透射象征寓意,应当说是一种更为清晰的透射活动。所谓有效的导引是作者通过有意的安排点破作品的题旨。但是,这种导引不应被看作是对作品的非审美性的介入与破坏。就其原则言,这一窥测作品题旨的窗口,应当开得恰到好处。只有这样,导引帮助人们理解了作品,又不显得是对作品艺术性的消解。
运用导引透射象征寓意的最简洁的方法是借用旁观者的解说来实现。这大都出现于象征物自身失去了自我评价能力的时候,而作者又不愿意让读者去苦苦揣摩象征寓意,故作者通过作品中其他人物之口对象征形象进行某种巧妙的阐释。我们认为,茅盾《子夜》中“吴老太爷之死”本是一个象征设置,作者在稍后的篇幅里就借诗人之口对这种速死进行了评价:“老太爷在乡下已经是古老的僵尸,但乡下实际上就等于幽暗的坟墓,僵尸在坟墓里是不会风化的。现在既到了现代大都市的上海,自然立刻就要风化。”(13)这解析了吴老太爷的死因,他不是死于生理的衰老与疾病,而是死于文化属性的衰老与痼疾。乡村是吴老太爷的精神故乡,因此,在乡村中,尽管他老朽不堪,精神的依托没有失去,故其可以延续。一旦他进入城市,他的精神之源泉被割断,他之生命的结束也就势在必然了。所以,吴老太爷之死,蕴涵深义,这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种生存方式的结束,一类精神生命的结束,也就是代表着封建主义的退位和资本主义的崛起。整个《子夜》讲的是资产阶级的故事,这一切发生在吴老太爷速死之后,正是承接了这种历史的逻辑性。吴老太爷不再能够影响吴荪甫,正是封建主义不再能够支配历史的象征,借用其他人物对作品的意蕴进行说明,对理解作品的寓意来讲,真的犹如拨云见日,未说明之前,读者是雾中看花,朦朦胧胧,既说明之后,读者豁然开朗,一清二楚。
比借用人物之口点破作品意蕴要稍显隐蔽的应是“卒章显其志”的导引方式。其特点是作品的大部分篇幅都用于象征体的创造,此时的寓意秘而不泄。然而,在作品的结尾部分,作者又对寓意有所释放,让读者由此线索生发开去,获得对作品意蕴的体认。尽管此时作者给予读者的线索,并不一定是明言直语,可是一个成熟的读者,有了这根线索,也就有了走出象征寓意理解之迷宫的机会。卒章显其志的创造构设,总是象征形象创造者们不愿放弃的手段之一。
波特莱尔可谓善用这种手段的大师。表面看来,他的《黄昏的谐调》,只是写景之作,但至最后一行,诗人把回忆过去爱情之体验给了读者,这就改变了诗中所出现的诸多意象的性质,使落日、花香和小提琴都成为美好事物的象征。同样的,他的《忧郁》(四首中第一首)亦如此,直至诗作的最后词语“逝去的爱情”,人们才明白诗在诉说死神夺去了诗人和他的情妇的爱情而造成的忧伤。所以,“这首诗远远不是仅仅描绘了一幅悲惨凄凉的景象,而是以独持的方式把一些象征聚集起来,在读者心中把诗人的体验重新创造出来。”(14)从波特莱尔的诗作来看,其诗艺的一个特点应作这样的归纳:他能不断地累积意象,同时,亦不急于点破这些意象的寓指,直至作品的最后部分,才把这些意象的总的寓指揭破,这使作品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并凭借这一力量,穿透作品诸多意象的外壳,使作品之寓意进入读者之心灵。
在这方面,最能体现波特莱尔这一手法的是其名诗《腐尸》。它的构思出人意料。在前九节里,描写腐尸之龌龊,令人不堪目睹。尤其是这具腐尸横陈在一个美丽的早晨,被一个美人所见,更增加了诗所传导的那种腐烂恶臭之气息的浓烈程度。但是,诗人一点也没有说明他的用意,他也根本没有向他最亲爱的“爱人”作某些暗示。这时,诗象自然主义的记录,诗人之职责好象只在尽其手段之高明,把这个记录弄得完整全面些,使人产生身临其境之感觉。只是到了后三节,诗人才笔锋突转,由腐尸意象收回,直指他的爱人,在爱人的辉煌中看到了她的没落,美丽中看到了她的丑陋,充满热情的生命中看到了她的死亡。腐尸在今日,是他人的腐尸;腐尸在明天,也许就是爱人的腐尸了。至此,诗作对腐尸的详备描写,已非简单的记录,这里渲染的是死亡的可怕景象,诗作的象征暗示之深意在于说明死亡不仅吞噬丑陋、邪恶,也将吞噬美丽、善良。生命终归要死亡,美与丑,善与恶都会烟消云散。唯一令人欣慰的仅仅是人们可以保持对美好的回忆,把美的形态、美的精髓藏于心底。波特莱尔是一位乐于把读者领进诗作寓意之暗夜的诗人,也是一位最终举起烛照这暗夜之电光、让读者寻找到理解之方向的诗人。在象征诗的创造中,波特莱尔不太晦涩,大概与这种卒章显其志的象征透射不无关系吧!
不过,就象征导引的营构范围来立论,“作品中的作品”更能反映导引透射的艺术魅力。作品中的作品,是指在大作品里安排一个小作品,用这个小作品所讲述的小故事来对大作品所演示的大故事,进行必要的诠释。这是小作品、小故事与大作品、大故事的对话交流,在对话与交流中,小作品、小故事把大作品、大故事的内涵披露出来。创造出凝练精粹的小作品小故事,往往是象征创造中的一项必要设计;而理解象征,同样不能忽略这些小作品小故事的存在。因为这能从小见大,从微见巨。
前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提供了此例。这部篇幅不长的作品相当复杂,说其批判现实,作品又大量描写了动物;说其是动物性寓言,它又把贩毒者刻划得很逼肖;牧区的改革,它写了,基督的受难,它也写了;有对神学的探讨,也有对国内战争的表现。进入该作品的途径何在呢?这虽然难以确定回答,可作者在作品中安排的两则小故事,应是点题之笔。一则故事为“六人与第七人”,写潜伏于反革命队伍之中的肃反人员,趁余下六人举行最后的告别晚宴之际,谋杀了他们,他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可是,这位肃反人员在绕着六人默默地走完一圈以后,开枪自杀了。另一则故事是耶稣受难前的对话。在这个故事中,罗马总督把耶稣当作一个疯子、欺骗者。他只相信皇权,尊尚武力,并拥有决定耶稣生死的权利。只要耶稣答应忏悔,放弃对正义天国的追求,这位总督就释放他。耶稣放弃了生命,坚信着真理。耶稣这样表达了他对人类与生存的观点:“人存在的意义,在于使自己的精神得到自我完善──人世间没有比这更高的目的。”(15)在他看来,人类的末日审判过去发生过,现在也正在发生着,决定人类命运的是人类自己。耶稣死了,只有一只怪鸟追随他。从这两则故事的中心意旨来看,它所倡导的是仁爱、宽恕、理解,从仁爱、宽恕、理解的高度去否定丑恶、仇恨、贪婪。这实际是作品象征寓意的两次相对集中的透射:当人类不能从爱的高度来处理它的生存时,它所面临的必将是世界的末日。因此,当人类大肆进行着捕杀动物、毁坏森林、贩卖毒品的罪恶勾当时,他们为此受到的惩罚是“人之子”的丧失,并且是“人之父”亲自射杀了人之子。(16)这应验了耶稣的话:是人在毁灭人自己。从这两则故事来看《断头台》,这是一部具有十分明显的宗教精神的作品,探索的是人类的自审意识,由此而引申的思想应当是,解决当代人类困境的方法,不是战争式的,不是掠夺式的,不是征服式的,应是人类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完善,是人类的爱,并用爱来统摄一切,才能解决人类的不幸。这两则小故事如同作品的两只熠熠生辉的“眼睛”,从这心灵的窗口中,你尽可领略作品所蕴藏的那深邃的无尽秘密。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导引是有效的,依靠导引读者进入作品思想核心的可能性大大增强了,可这同时并不排斥读者在其解读作品时,会与作品的导引有所分歧。原因在于:其一,作品的导引大都含而不露,其点题方式由于带有形象性、间接性和有限性的特点,仍然给读者理解作品留下了广泛的自由度;其二,读者解读作品时是从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出发的,故其解读有着接受者的自主特点,往往越过作品的导引而直接以自己的理解作为作品的寓意。茅盾对曹禺《北京人》中“北京人”意象的理解就与作者很不一致。在曹禺那里,北京人是一种力量的象征,是对所谓的现代文明人之软弱的否定。因此,他以“机器工匠”的身份出现,实际上,他之被创造又不受“机器工匠”之社会角色的限制,这正是象征思维的抽象性所规定的。茅盾则从具体的社会问题出发来看北京人,当其直接把北京人看作是一位劳动人民的代表时,他就必然发现这一形象对于劳动人民本质的某些背离,从而否定作者的创作构思,否定北京人形象的艺术真实性。(17)曹禺的导引,对茅盾的作用是不大的。这与其看作是导引的失败,不如说正是导引的常态。出现这些分歧符合艺术理解必将伴随歧义这一恒古常存的规律。设若经过导引的作用,解读结果与其完全一致,那才是艺术的悲剧呢。所以,承认象征创造中导引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象征的寓意透射仅此一途,并且已被这条通道所限制而不能从其他方式获得象征寓意之解析。同时,也应看到,即使接受者的理解与作者的导引有着很大的差别,也不要轻易否定导引之某种程度的准确性,因为导引来自创造者的有意为之,与作者的整体思维不可分,由此而看作品,总是能够有所收获的。
我们在以上的分析中讨论了象征形象的营构与透射的几种主要方式,从这一角度可知,象征的创作不是一种处于作者思维之混乱状态的创造活动,它之所以是一种难解的形象模式,是因为作者想以这种模式创造出一定的审美效果。了解这一点,象征形象之理解决不是一种无迹可循的精神探险,而是一种充满机智,并凭借这种机智寻找作品的内在透射方式的解读活动。成功的象征解读不排除读者的想象与创造,但应是对作品之透射的最有效的把握。因此,对象征形象的创作者来说,有没有透射,会不会透射,能不能透射,确实是其营构形象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方式,拥有这种方式,就是架起了与读者进行对话的桥梁,就能更为顺利地实现象征创造的既定意图。而缺少它,不仅是象征营构的缺陷,也是象征理解的缺陷,这是不符合艺术必须与社会进行对话交流之需要的。象征的营构与透射对于象征的创造,就是这样一个必不可少的一环,因而,认识这一象征创造中的重要现象,也就成为象征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了。
注释:
①王独清《再谭诗》,《中国现代诗论》上,花城出版社,1991,5。
②卞之琳《关于〈鱼目集〉》,见《李健吾文学评论选》,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③爱伦·坡《诗歌原理》,《美国十九世纪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
④⑧伦纳德·迈尔《音乐的情感与意义》P.30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⑤穆木天《谭诗》,《中国现代诗论》上。
⑥瓦雷里语,见查尔斯·查德维克《象征主义》P.9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
⑦玛克斯·德索《美学与艺术理论》P·28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⑨伊丽莎白·朱《当代英美诗歌鉴赏指南》P·52.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⑩《诗的音乐性》,《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
(11)瞿世镜《意识流小说家伍尔芙》P·127.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
(12)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P·5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13)《子夜》P·3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14)此处参阅查尔斯·查德维克《象征主义·波特莱尔的“感应”》。
(15)《断头台》(冯加译)P·198.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
(16)在《断头台》中,鲍斯顿为从狼嘴中救下自己的儿子,不得不开枪射击,结果,射中了自己的儿子。
(17)参见茅盾《读〈北京人〉》,《茅盾文艺杂论集》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