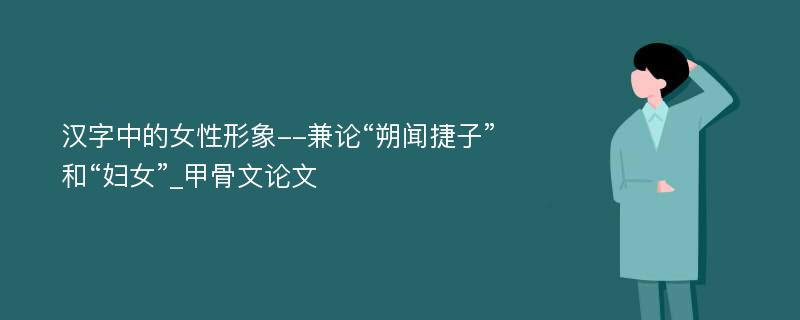
汉字所反映的妇女形象——浅谈《说文解字》“女”部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字论文,浅谈论文,说文论文,妇女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3)专-0017-10
东汉许慎(54-150?)在他《说文解字》——中国第一部以“部首”来分类解说汉字的字典——第十二篇下“女”部收录了238个字(注:许慎生卒年采用顿嵩元《许慎生平事迹考辨》说。论文见中国训诂学会《许慎与“说文”研究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218-246页。本文采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说文解字注》。“女”部字见612-626页。)。这238个字占全书正文总数(9353字)的2.54%,是《说文解字》540个部首中收字较多的部首之一(注:《说文》与人有关而录字较多之部首为“口”部(180字)、“女”部(238字)、“人”部(245字)、“言”部(247字)、“心”部(263字)、“手”部(266字)。)。清段玉裁注《说文》增补了一个“妥”字,加上收入于第七篇下(“宀”部)的“安”与第三篇上(“辛”部)的“妾”,一共是241个带有“女”旁的汉字(注:“妾”字见《说文解字注》102页,“安”字见339页。)。
通过《说文》的后“叙”,许慎清楚地交待了他对文字功能的理解,编辑《说文》的目的与方法,释字的原则,以及《说文》一书的体例。他说;
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也。万物咸睹,靡不兼载[1](P763-764)。
接着他列出《说文》的540个部首,并说明序列编排这些部首(以及各部首下所属的单字)的原则及标准:
其建首也,立一为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毕终于亥,知化穷冥[1](P781-782)。
从这两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许慎对“文字”或“字书”所下的定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工具”或“手段”这些常用词的范围。段玉裁在《说文》“一”部所收之五字后注称:
凡部之先后以形之相近为次。凡每部中字之先后,以义之相引为次……说文每部自首至尾,次第井井,如一篇文字。
进一步说明《说文解字》是一部有整体性、连贯性,对文字本身(即“形”、“音”、“义”三方面)以及产生这个文字体系的文化传统同样关心的著作。
现代学者对许慎以“经艺”论“文字”的态度取向虽持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与评论。但一般都同意,作为文化载体的文字是离不开它特定的时空与社会环境的。正因为这样,文字才能达到“垂后”及“识古”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说文》,我们将发现,《说文》“女”部的两百多个汉字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研究由两汉至清末传统理想妇女形象的途径。
据“同条牵属,共理相贯”的原则,《说文》“女”部字的排列先后基本是按照段玉裁所说的“以义之相引为次”。也就是说把意思相近的字排在一起。因此,“女”部238(或241)字可以再按字义归纳为以下六大类。
部首:女
1.姓及“女字”(31)
2.婚姻与生育(12)
3.称谓(31):包括亲属关系及社会身份之各种称谓词
4.容颜体貌(42):概分为带有正面意义及反面意义两类
5.神情举止与行为(118):概分为含有褒义、含有贬义及中性三类
6.其它(9):妇女病痛及与女性无直接关系之字词
除了部首“女”字外,在这六大类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第四类“容颜体貌”及第五类“神情举止与行为”所包括的160字。这160个字占“女”部所有字的66%。这些字在讨论女性形象时为我们透露了些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们根据许慎《说文解字》中的定义把这两类字再细分一下。《说文》“女”部表示女性“容颜体貌”的字一共有42个。带有正面意义的字有33个,是带有反面意义9个字的3.7倍。
正面意义:
1.美或美女:5字
2.好或好看:22字。其中泛指的有16个,特指的有6个。
3.直、轻、孅长、柔弱:6字(指女性的身型体态)
反面意义:
带有反面意义,表示女性“容颜体貌”的9个字几乎可以看成是带有正面意义那些字的“反义字”。它们所代表的形象包括“丑陋”、“不好看”、“肥大”及“色黑”。
《说文》最能反映汉儒对妇女的看法——也就是最能体现许慎以“经艺”来论“文字”的——恐怕就是第五类“神情举止与行为”中的118个字了。在“附录一”,我把这些字按《说文》定义分成了“褒义字”、“贬义字”及“中性字”三类。所谓“中性字”包括表示情爱、妆饰、以及那些既不含褒义也不含贬义的表示动作或神情的字。必须说明的一点是“中性字”有一些恐怕是见仁见智,可以归到“褒义字”类也可以归到“贬义字”类的。比方说,表示女性神情动态的“媱”、“嬛”,“姽”等也可以说含有褒义,而“姡”、“媿”等表示羞愧的字也许可以算是贬义字。还有,“始”字《说文》定义为“女之初也”,似乎与女性的形象无关,也可以放在“其它”类。
在表示女性“神情举止与行为”的汉字中,“贬义字”(56个)几乎是“褒义字”(34个)的1.75倍。按《说文》对这些字所下的定义,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地把这些字分成几个小类:
褒义字
1.“顺也”:5字
2.表示“服”、“伏”、“随”、“从”:7字
3.表示“庄敬”、“小心”、“谨慎”、“安静”、“专一”:20字(加上“妥”与“安”则为22字)
贬义字
1.不顺从:4字
2.不恭敬、不安分、“狎侮”:7字
3.嫉妒、嫌疑、贪婪:8字
4.愤怒、烦恼、不悦:8字
5.多话、诽谤、争讼:6字
6.轻薄、懒散、迟钝:11字
7.放纵、淫乱、骄傲得意:12字
总的来说,《说文》显示女性神情举止与行为的118个字中,含有褒义的字似乎比含有贬义的字更能为我们勾画出两汉以来传统社会中理想妇女的形象。这些形象基本是与许慎所能看到的先秦两汉文献中的妇女形象平行一致的。
下面我就用比较能全面而具体描绘出两汉至晚清理想妇女形象的《女诫》来跟《说文》“女部”的第五类字作一个比较[2](P1-6)。《女诫》作者班昭(?-116)是许慎同时代的人。《女诫》全文不过1600多字,唐宋以来逐渐成为妇女必读之书。明朝王相把当时流行的四部教诲女子的书籍编成一套,称之为“女四书”,《女诫》就成了“女四书”的第一部[2](P1-6,15-21,22-35,36-53)。
在《女诫》的序言中,班昭自述她写书的原由:“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为了以“妇礼”来“训诲”家中快要成年出嫁的年轻女子,她系统地把五经所载有关妇女言行道德的理论思想,综合编写成了她的《女诫》七章: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
《女诫》从头到尾,引经据典。由《诗经·小雅》“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弄之瓦”说起,表明女子天生卑弱(第一章)。接着便以阴阳之道来解释夫妇之间“驭”及“事”的关系(第二章)。因为“阴阳殊性,男女异行”所以“女以弱为美”,所以“敬顺之道,妇人之大礼也”(第三章)。再下去更详细分析妇女的“四行”:即“妇德”、“妇言”、“妇容”及“妇功”(第四章)。第五章“专心”解释《礼记》“夫有再娶”而“妇无二适”的道理。第六及第七两章分别教导女子如何获取“舅姑之心”及“叔妹之心”(对前者应该“曲从”,对后者应该“谦顺”)。
短短七章,班昭精简而具体地列出了年轻妇女在日常生活中所应该遵守或避免的行为。《女诫》不仅代表了班昭的“妇女观”及她简练的文笔和叙述风格,同时也成为后世“训女”书的典范。从以下引文(见第四章“妇行”)我们几乎可以在形式及内容两方面窥视到中国古代妇女生活史的片断:
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
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
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
专心纺织,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2](P3)。
将许慎《说文》“女”部第五类“神情举止与行为”的一百多字与班昭的《女诫》相比,不难看出这两部著作是同一个文化背景的产物。它们所描绘的妇女形象代表了在那个特定的文化环境中人们所追求的共同理想。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许能理解为什么对某些文字的解释,《说文》会有在今天看来极不合理的说法。
自1899年殷墟甲骨发现以来,古文字学家一方面据《说文》小篆来推认研究甲骨文,同时也借助甲骨文来考订《说文》对字形字义的训释。“女”部字中,讨论较多的可以举部首字“女”及称谓词“妇”为例。
“女”,许慎引王育说认为是象形字。《说文》原文是:
女,妇人也。象形,王育说。凡女之属皆从女[1](P612)。
但“女”到底是“象”什么“形”呢?两汉以降,众说纷纭。所以董作宾在他《从么些文字看甲骨文》中有这样的说法[3](P667-668):
“近取诸身”的象形文字中,最难寻求字根的是一个“女”字。在《说文》中解释小篆的“女”字是:“妇人也。象形,王育说。”从小篆里看象形字,和商代又差了一千多年,因而更不容易找出原始的意义。许叔重知道“女”是妇人,有人说它是象形,又讲不出所象何形,只好注是“王育说”的。于是费了后人的许多揣测(注:根据字形结构,董作宾认为“女”的原始意义是“女俘”,与作为“男俘”解的“如”字相对。)[3](P670-673)。
许慎《说文》虽引用了王育的说法,但并没有穿凿附会,只泛释“女”为“妇人”。那么,“妇”字《说文》又是怎么解释的呢?
妇,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
“服”是释义,“从女持帚”是析形。所以“洒扫”是妇女本分的职务。段玉裁引《大戴礼》“本命”篇,对许慎的说解又作了如下的阐释:
大戴礼本命曰: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者也。故谓之妇人。妇人,伏于人也[1](P614)。
无论是“服”(有“服从”与“服侍”两义)或“伏”,许慎对“妇”字的理解显然是根据现实生活中妇女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先秦两汉以来逐渐定型的男尊女卑的观念。这与班昭《女诫》所宣扬的道理是一样的。班昭在《女诫》的序言中谈到她十四岁嫁入曹家为妇时说:“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执箕帚”成了“妇”或“为人妇”的代词,后世沿用(注:“箕帚”作为“妇”义用在汉代可能非常普遍。《汉书·高祖纪》当吕公将女儿许配给刘邦(即后来之高祖)时就用了这个词:“臣有息女,愿为箕帚妾”。)。
对许慎以“持帚”释“妇”字字形,直到二十世纪甲骨学与甲骨文的研究有了一定成果后才有人提出疑问。首先,是对“妇”字所指的对象。在甲骨文中“妇”是有特定身份的女性。胡厚宣在他《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列出了64个武丁时期的“妇”[4](P9)。1976年“妇好”墓出土,引起了许多学者专家的瞩目(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为全面性论述“妇好墓”之专著,198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通过对甲骨文中有关诸“妇”的卜辞以及“妇好”墓随葬品的研究,使我们对殷商贵族妇女的生活有了比较具体的认识。殷商诸“妇”可以领兵出征、参与祭祀、整治甲骨、负责农事……跟东汉许慎或班昭笔下“持帚洒扫”的“妇”有很大的差异(注:妇好墓出土以来,探讨商代妇女之论文颇多,包括王宇信、张永山、杨升南《试论殷墟五号墓的“妇好”》见《考古学报》1977年第二期1-22页;张政烺《妇好略说》见《考古学报》1983年第六期537-541页;郑慧生《卜辞中贵妇的社会地位考述》见《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亦见郑慧生《甲骨卜辞研究》151-161页)。齐文心、王贵民《商西周文化志》(199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在讨论商代社会结构时有“诸妇”一节(38-41页)。)。
齐文心《“妇”字本义试探》根据甲骨文字对殷商诸“妇”的记载,认为许慎以“持帚”释“妇”是不合于历史事实的。通过对甲骨文字本身的比较,她认为甲骨文“妇”(见“附录二”第七字)是“一种发式的象形,像是将美发规在一处束紧,上部散开的发式。这种发式可能是王妃贵妇所特有的发型。”(注:齐文心《妇字本义试探》,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尚未发表),1999年8月,河南安阳。)但单从个别字形及字义着眼,甲骨文字传递给我们的有关殷商妇女形象的信息非常有限。《说文》“女”部字在字形上可以追溯到殷商甲骨文的大约有37个(见“附录二”)(注:参看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1990年四川辞书出版社。“附录二”主要根据卷十二目录(78-79页)编制。),其中绝大多数在甲骨刻辞中是专有名词,包括人名(“附录二”1,2,3,5,7,8,9,10,14,15,16,17,19,20,21,22,23,24,25,26,28,29,30,34,35,37)、地名(1,11,37)、方国名(6,14,29)、神祇名(1,4,19)、祭名(4,28)以及女性人牲(3,18,31,36);称谓词有六(1,6,7,12,13,36)。在这37个字中只有五个字(1,14,16,27,37)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作为普通名词、形容词或动词看待。值得一提的是有一部分甲骨文中作为专有名词的女性人名到了许慎《说文》都已转变成了形容词,含有美好、柔弱、安静、随从的意思(16,17,21,22,23,24,25,26,29)。在此我们可以举武丁配偶“妇好”之“好”字为例。
“妇好”墓随葬器物中有“妇好”(或“好”)字铭文的铜器共有109件[5](P95)。铭文“好”大致有三种写法(见“附录三”):从“女”从“子”(两个组成部分皆可左可右),左右二“女”中一“子”,上“子”下“女”。三种字形以第二种(左右二“女”中一“子”)最为普遍(注:《殷墟妇好墓》编著者认为第二种写法是一种“艺术字”。)。这三种不同的写法指出了汉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早在殷商时期,汉字构成部件在意义上的独立性已经为使用这种文字的人们所普遍认知。在“好”字形成的当时,它所代表的意思也许只是“子方”(即“子国”)之女,[6](P)但构成“好”字的两个独立部件(即“女”与“子”)却暗示着许慎《说文》为“好”字所下的与“子方之女”完全不同的定义:“好,美也。从女、子”。其实“好”字在先秦的典籍中已经拥有了它的两个最基本和最常见的意思:当形容词“美善”(音“hǎo”)及动词“喜爱”(音“hào”)解。《诗经》中有不少这两种“好”的例句: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南·关雎》,“好”音“hǎo”,形容词)
我有嘉宾,中心好之;钟鼓既设,一朝酬之。(《小雅·彤弓》,“好”音“hǎo”,动词)
两义连用则见《礼记·大学》: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
按许慎对“六书”的解释,“好”字无论是“子方之女”(“子”为方国名)或“美也”(“子”乃“孩子”),都是“比类合谊”的“会意字”。但甲骨卜辞中的“妇好”若确为“子方之女”那么“妇好”的“好”字字音就应该是“zǐ”(而不是“hǎo”),是一个“会意兼形声”的字。
从女从井的“妌”字(“附录二”第25字)在甲骨文中也是人名。“妇妌”跟“妇好”一样,也是武丁诸妇中曾经率军出征的一员女将(见《甲骨文合集》6344、6585正)。但原是专有名词的“妌”到了许慎的《说文》却成了“静也,从女井声”。以“静”训“妌”与以“服”训“妇”,或以“如”训“女”一方面固然显示出两汉语言文字学家对汉字形、音、义三方面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的认识与重视,再方面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价值观、社会观、生活观及字宙观对他们治学态度的影响。
《说文》“女”部五十六个贬义字在字形上可以上溯到甲骨文的只有三个(31、32、34),28个中性字中只有两个(30、33)。这五个字在甲骨文中有两个是人名(30、34)一个是“人牲”(31),还有两个则字义不明(32、33)。另外还有三个字(9、10、11)在甲骨文中原是人名或地名,到了《说文》都变成了妇女孕育的专用词。
甲骨刻辞对我们研究殷商妇女真正有所启示的乃是刻辞中关于诸“妇”的记载。这些记载为我们研究殷商王妃贵妇的生活提供了一定的资料。根据这批资料,我们知道商朝妇女的活动空间,要比自周朝至二十世纪辛女革命之后传统妇女的世界广阔得多。在后世纯为男性领域的军事、田猎、宗教各方面,卜辞中都有殷商诸“妇”参与的记载(注:见上引齐文心《妇字本义试探》及郑慧生《卜辞中贵妇的社会地位考述》。)。但从有关诸“妇”的刻辞中,我们也可以推知早在公元前十二、三世纪,重男轻女的观念已经存在了(注:卜辞以生女为“不嘉”。自胡厚宣提出“不嘉”为殷人“重男轻女”之佐证后,甲骨文学者多同意此说。参看上引王宇信、张永山、杨升南《试论殷墟五号墓的“妇好”》11-12页,郑慧生《卜辞中贵妇的社会地位考述》153-154页。)。
近半个世纪以来,因受女权运动影响,中外学者对中国妇女问题的研究成果相当可观。除了从家庭、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来探讨妇女的地位之外,语言文字也成了研究观察妇女问题的材料[7]。但语言文字上的材料往往只是用来作为中国传统或现代妇女地位低落的佐证,鲜有全面客观而系统的讨论(注:David Keightley在其“At the Beginning:The Status of Women in Neolithic and Shang China”(Men,Wome,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Vol.1,No.1,pages 1-63,Brill:Leiden/Boston/Koln,1999)一文中从墓葬、出土器物、甲骨刻辞等各方面来探讨新石器时代及商朝妇女的地位,为近年英文著作中关于中国上古时代妇女问题比较客观而全面的论述。)。因此,当引用《说文》“女”部字采探索妇女形象时,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大量的贬义字(注:这一类的讨论很多,请参看Dress,Ser and Text in Chinese Culture(《中国文化:衣着、女性与文字》Monash Asia Institute,Monash University,Austalia,1999),第五、六两章:“Writing the female Radical:The Encoding of Women in the Writing System”及“Gender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两章作者都极力主张取消“女”字部首,原因是“女”部字贬义字太多,容易造成对女性人格的误解及对女性的歧视。)。我们忽略了这些贬义字后面所隐藏的理想与追求。尽管这些理想与追求早已成为历史,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的糟粕,却也是中华文化发展中极为重要的一段过程。
文字是离不开人们特定的生活环境与文化的。人们手头上常用的字典辞书就是最好的证明。翻开1998年修订版的《新华字典》,第141页上的“妇”字有三个定义:
1.已经结婚的女子。女性的通称(引申义)
2.妻,跟“夫”相对
3.儿媳
在“女性的通称”下有两个例词:“妇科”、“妇女翻身”。
第366页上的“女”字也有三个定义:
1.女子,女人,妇女
2.女儿
3.星名,二十八宿之一
在“女子,女人,妇女”下有三个例词:“女士”、“女工”,“男女平等”。
“妇女翻身”、“男女平等”,从某个角度看来与许慎或班昭笔下所宣扬的“男尊女卑”的道理是一样的,都代表了在一个特定时空、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人们共同的向往与追求。
(本文初稿曾由作者宣读于2002年3月香港大学主办之“第一届中国语言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上)
收稿日期:2003-0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