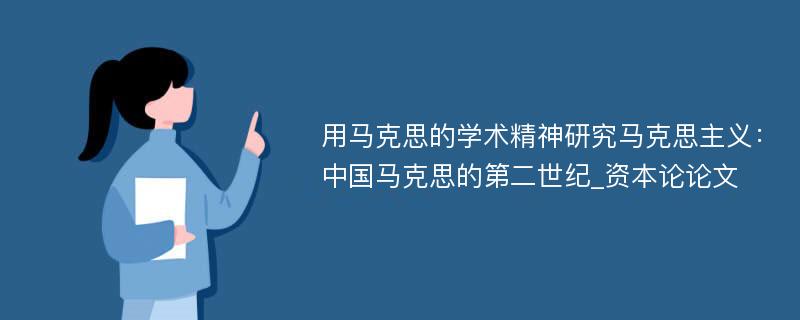
以马克思的学术精神研究马克思主义——致汉语马克思的第二个世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汉语论文,第二个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00(2005)01-011-07
(一)
1899年2月,《万国公报》卷121刊载了由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纂述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其中用一百余字的篇幅介绍了马克思及其关于资本的学说。文中写道:“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这段概述除称马克思为“英人”有误外,堪称言简意赅。有意思的是,马克思姓名的翻译就用的“马克思”三个汉字。(参见《万国公报》卷121第13页)这可能是马克思及其学说第一次出现在汉语文献中。1902年10月16日,《新民丛报》出了第18号,其中发表了梁启超的文章《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该文介绍了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被译作“麦喀士”。(参见《新民丛报》18号,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五日)这可能是中国人自己在用汉语写作的文章中第一次谈到马克思及其学说。从那时算起,马克思在汉语中存在的历史已超过了一 个世纪。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前半个世纪,人们最在意马克思主义的是它作为救世之道、救国之策的意义。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头30年,马克思主义被严格定位为国家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解说主要起调整意识形态的作用。所有这些都以突出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科学性、在功能上的革命性为共同特征,人们很少谈论马克思主 义的学术性。进入21世纪后,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思想环境的改善,学术地研究马克思主 义成为可能,从而马克思的学术精神、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学术性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 学术维度作为一个问题便浮现了出来。
这里的所谓学术性,主要指学术研究这种“天下公器”作为一种专业活动的正当性,涉及学养、工夫、规范、水准等能够被行业认可和接受的诸多因素。学术性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资质,是学术观点参与行业竞争的准入条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影响当代人类命运的理论学说,无疑是具有学术性的,它是马克思等人从事学术研究的成果。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如果不是满足于政治表态或政策宣示,也应该具有学术性,即应该在学养、工夫、规范和水准等方面跟其他学术研究一视同仁。
由于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所内在包含的学术性被揭示得不够,因而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只要有坚定的信仰、能够跟当下的政治取向保持一致就是合格的,学术上马虎一点没有关系。甚至还有一种奇怪的议论:似乎一强调学术性,就是搞“经院哲学”,就是不要政治性或冲击政治性,就是不关心现实,从而把学术性看成政治性的反面。殊不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巨大而深远的政治影响,其学术性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马克思本人的工作情况就是最好的说明。
(二)
人们习惯于称马克思为革命家、思想家,但很少有人称他为学者,即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实际上,马克思应当首先被看成一个学者,在此基础上,他才是一个思想家,进而才是一个革命家。换句话说,马克思作为学者的深厚素养和卓绝工夫,是其取得一流思想成果并将其付诸实行的必要条件。只不过马克思跟一般学者不同,他不仅仅是一个学者,而且是一个思想家和革命家。
马克思上过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后者是黑格尔任过校长的学府,而黑格尔哲学是当时世界哲学的制高点。马克思本科学的是法律专业,受业于黑格尔的门人,毕业时又以关于希腊哲学的论文申请到耶拿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在大学期间,除了学习各种规定课程以及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外,他还读过亚里士多德以及有关德谟克利特和晚期希腊哲学的许多著作,并翻译过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读过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休 谟等人的著作,读过历史、艺术、法、自然科学方面的一些书籍。这些学术训练特别是 哲学方面的训练使他能够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从事学术研究和思想创造。
除德文外,马克思大学期间就熟练掌握了拉丁文和法文,后来又掌握了英文,并留下了用这四种文字所写的著作。马克思在大学时学过意大利语,能够读希腊文著作、西班牙文著作,“能轻松自如地用日尔曼语系和罗曼语系的各种语言阅读,他还研究古代斯 拉夫语、俄语和塞尔维亚语”,[3](P620)以及古代弗里西安语[4](P580)他在外语上的 这种工夫对他的研究至关重要。比如,他的法语能力对他继承法国思想遗产,他的英语 能力对他学习和研究英国政治经济学,他的俄语能力对他了解和思考俄国社会的特殊发 展道路,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为学者,最重要的工夫就是读书,特别是研读学术著作。按照阅读的主题,可以把 马克思的读书生涯大致分为如下八个阶段。
首先,大学阶段可以称为“法学—哲学”阶段。法学是他的专业,哲学是他的兴趣所在。情况已如前述。
其次是“哲学—历史”阶段,大约从大学毕业到1844年3月。1841年7月,马克思读了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同年9月至1842年5月,马克思着手研究宗教史和艺术史,读了梅涅尔斯、巴尔贝拉克、德布罗斯、伯提格尔、鲁莫尔、格龙德等人的著作。1842年冬,马克思首次接触社会主义文献,读了蒲鲁东、德萨米、勒鲁、孔西得朗等人的 著作。1843年夏,马克思读了一系列的历史和哲学著作,包括路德维希、瓦克斯穆特、 兰克、汉密尔顿、卢梭、孟德斯鸠、马基雅弗利等。1843年底至1844年春,马克思读了 勃朗、路韦、罗兰夫人、蒙格亚尔、德穆兰、勒瓦瑟尔等人的著作。
第三个阶段是“经济学—哲学”阶段,大约从1844年3月到1846年底。此间,马克思的阅读兴奋点和重心开始移向政治经济学。一些考证认为马克思读政治经济学著作可以前溯到1843年10月。不过大规模的集中阅读还是在《德法年鉴》出版后的1844年3—8月,马克思读了斯密、李嘉图、萨伊、西斯蒙第、毕莱、佩克尔、斯卡尔培克、穆勒、舒尔茨、麦克库洛赫等人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以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等。阅读的成果凝结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9—11月,马克思认真研究了17和18世纪英 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者。12月,读了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2—3月, 马克思读了毕莱、麦克库洛赫、罗西、布朗基、佩基奥等人的著作。5—8月,马克思读 了萨伊、西斯蒙第、西尼尔、施托尔希、倍倍日、尤尔、加尼耳、维尔加尔德尔、瓦茨 、配第、图克、库伯、科贝特等人的著作。1846年9—12月,马克思读了欧文、魁奈、 布雷、蒲鲁东等人的著作。这些基本上都是政治经济学著作。
此后两三年间,马克思主要忙于革命活动。
第四个阶段几乎是纯“经济学”阶段,大约从1850年6月至1851年底。这一年半时间是马克思读书的黄金时期,读得最集中、最系统、最有成效,并且所读基本上都是政治经济学著作。1849年8月24日,马克思定居伦敦,一直住到逝世。在此间的三十多年里,当时世界上资料条件最好的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实际上就成了马克思的工作“单位”。他 是1850年6月中旬获准进入该图书馆看书的。到1851年12月,他都在那里“上班”,通 常从早上9点坐到晚上7点。这期间他读了穆勒、富拉顿、托伦斯、图克、布莱克、吉尔 巴特、加尔涅、西尼尔、倍克、赖特迈耶尔、李嘉图、杰科布、贝利、劳埃德、凯里、 休谟、洛克、格雷、博赞克特、斯密、丹尼尔斯、塞拉、蒙达纳里、马尔萨斯、莱文斯 顿、霍吉斯金、琼斯、拉姆赛、欧文、菲尔登、兰格、盖斯克尔、安德森、萨默斯、李 比西、托伦顿、艾利生、约翰斯顿、普莱斯科特、伯克斯顿、豪伊特、威克菲尔德、塞 姆佩霄、蒲鲁东、马尔、尤利乌斯、哈德卡斯尔、波佩、贝克曼、尤尔等人的著作以及 大量其他相关资料。1851这一年,他光摘录就写了14厚本。
第五阶段可称为“经济学—历史”阶段,大约从1852年6月到1958年初。该阶段的阅读是间断性的。在中断了一段时间之后,1852年6月,马克思重新获得了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的阅览证,并在1853年初恢复了政治经济学研究,读了奥普戴克、班菲尔德和斯宾塞 等人的著作,但不久后再度中断。1854—1856年,马克思读了一大批历史特别是国别史 方面的著作。1857年,马克思读了一批政治经济学、美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1858年初 ,马克思重读黑格尔《逻辑学》,此后还读了巴师夏、拉萨尔、拜比吉等人的著作。
上述三个阶段的经济学研读结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成果,马克思对拉萨尔说:“它是我十五年的、即我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10](P546)
第六阶段从1859年10月到1867年,为“经济学—多学科”阶段。1859年10—12月,马 克思读了维里、贝卡里亚、奥特斯、琼斯、马尔萨斯、贝尔、范德林特、霍普金斯等人 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1860年初,马克思重读了恩格斯早期、李嘉图、斯密、马尔 萨斯的一系列著作,还重读了孟德斯鸠、洛克、霍布士、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人的一 些著作。这一年晚些时候,马克思还研究数学,作为一种心理调节。年底,读了达尔文 的《物种起源》。1861年春,马克思读了阿庇安《罗马内战史》的希腊文原本,读了洛 贝尔图斯、罗雪尔等人的政治经济学著作。5月,重读修昔底德。1862—1867年,马克 思忙于《资本论》的写作,此间读过一批有关波兰的著作,还有勒南、雷尼奥、李比希 、申拜因、孔德、罗杰斯等人的著作,并在数学、天文学方面投入了一定精力。
第七阶段从1868年春到1879年,阅读主题为“经济学—东方社会”。《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1868年春,马克思读了弗拉斯、杜宁、摩尔顿、杜林、毛勒等人的著作,自述在图书馆头疼很厉害。5—6月,重读斯密、杜尔哥、图克等人的著作。10月底,马克思开始研究俄国村社问题。1869年,马克思读了福斯特、卡斯蒂、韦莫雷尔、克列姆、凯里、约翰斯顿等人的著作,以及一批有关爱尔兰、俄罗斯的著作。1870—1873年,马克思阅读了许多有关爱尔兰和俄罗斯的文献资料。1874—1877年,围绕《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写作,马克思研究大量材料,包括官方资料,还研究数学、植物生理学等问题,并继续大量阅读关于俄国问题和斯拉夫问题的著作和资料。1878年,马克思读了英格列姆、考夫曼、加西奥、许尔曼、曼、普尔、罗塔、汉森、亚契尼、恩舒特、达贝尔、邦纳、雷等人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还读了科佩、赫鲁贝克、朱克斯、豪威耳、梅林、阿韦奈尔、卡斯帕里、雷蒙等人的多学科的著作,还读了莱布尼茨和笛卡儿的自然史和数学著作,并且对东方问题的阅读兴趣和阅读量进一步加大。1879年,马克思读了雷德格雷夫、赖特迈耶尔、罗塞尔、赫希伯格、盖得、鲁·迈耶尔、卡尔顿、耶林、朗格、弗里德兰德、布赫尔等人的著作,并继续阅读有关俄罗斯的各种文献。
第八个阶段从1880年到1883年初,阅读兴趣又调整为“东方社会—古代社会”。1880-1881年,马克思读了贝奈特、艾尔温、奥勃莱恩、勒图尔诺、洛利亚、乔治、摩尔根、 梅因、菲尔、佐姆、道金斯、龚普洛维奇、劳埃德、豪斯、巴罗、布朗、格罗曼、莱斯 利等人的诸多方面的著作和文章,并在继续阅读有关俄罗斯问题的资料的同时开始关注 古代社会问题,尤其重视摩尔根的《原始社会》。1882—1883年,马克思读了一些有关 埃及和俄国的著作,还读了洛利亚的经济学新著、奥斯皮塔利埃的电学著作等。[4]
尽管上述材料不可能反映马克思读书情况的全貌,但也足以让我们窥见马克思从事学术研究的扎实工作基础。
在读书的同时,马克思还形成了一套包括做笔记在内的积累资料和心得的好方法。1837年初,马克思到柏林大学不久,就养成了做读书笔记的终生习惯。这些笔记主要包括:7本《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1839年)、8本《柏林笔记》(1840—1841年)、5本 《波恩笔记》(1842年)、5本《克罗茨纳赫笔记》(1843年)、《1844—1847年记事本笔 记》、7本《巴黎笔记》(1844年)、7本《布鲁塞尔笔记》(1845年)、9本《曼彻斯特笔 记》(1845年)、24本《1850—1853年伦敦笔记》,以及中晚期大量有关经济学、历史、 人类学、自然科学和技术史等方面的笔记。其中,1843年以前的笔记主要关于哲学和艺 术方面,而1843年以后,90%以上都是经济学笔记。[5](P14、PP701—702)[4](P6)这些 笔记既是马克思扎实工作的见证,也是他确保工作质量的有效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MEGA2)拟出114卷。其中,第一部分共32卷,包括《资本论》系列著作之外的著作;第二部分共15卷,为《资本论》系列著作。其余两部分共67卷,为书信、笔记等。在这些卷帙浩繁的著述中,马克思生前出版的大部头学术著作只有4部,它们是:《神圣家族》(与恩格斯合著,1844—1845年)、《哲学 的贫困》(184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资本论》第一卷(1867 年)。其中,前两部属于论战性著作,后两部才是正面而系统地阐述自己理论体系的原 创性著作。马克思一辈子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学,阅读和摘录过的他人著作汗牛充栋,写 下的准备性文字也数量惊人,可自己亲自拿出手的原创性著作也就这两部。这种摄取量 、加工量和出品量之间的巨大反差,恰是马克思研究成果的学术品质的最好说明。
(三)
不过,在作为学者的马克思身上,最令人钦佩的还是浸透在他学养和工夫中的那种精神。
马克思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正式”工作,一生饱受贫病的煎熬。他的经济状况已是众所周知。他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后,没有钱将稿子邮走,完成《资本论》第一卷后,没有盘缠去送稿子,后来都是恩格斯出的钱。他身患多种疾病,31岁就患上肝病,以后经常复发,他夫人就死于肝癌。他还患有眼病、支气管炎、风湿痛、胆囊 炎、痈病,并长期失眠,最后死于肺脓肿。他和燕妮生有七个孩子,只有三个长大成人 ,小女儿弗兰契斯卡一岁就病死了,连棺材钱都是向人要的。
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说过:不应该为谋生而写作,而应该为写作而谋生。尽管如此,为了生计,从1852年8月起,马克思也不得不替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写文章,每篇挣一两个英镑,持续了近8年。此间,马克思渴望能有几个月的空闲时间来进行他的学术研究,他说:“但是,显然我是得不到这种空闲的。不断地为报纸乱写凑数文章已使我厌烦。不管你怎样力图独立不倚地写作,你总归要受到报纸和它的读者的约束,特别是像我这样一个靠领取现款维持生活的人。纯学术工作就完全不同了……”。几年后, 马克思对那帮办报的人一肚子抱怨,说:“跟这号人为伍,还不得不认为是件幸事,这真是令人厌恶。”[3](P289、P290)
尽管有这些耽误,一回到纯粹学术的领域,马克思便一丝不苟。1851年初,恩格斯催 促马克思赶紧完成并出版他的经济学著作。恩格斯劝说道:“对你自己的著作哪怕就马 虎一次也好。对于那些糟糕的读者来说,它已经是太好了。重要的是把这部东西写成并 出版;你自己所看到的那些缺点,蠢材们是不会发现的。”但马克思不肯听从。其实, 恩格斯也知道,马克思只要有一本他认为是重要的书还没有念,他是不会动笔的。[3]( P289、P290、P327)正是这种“过分慎重的态度”使这部1851年就拟议完成并出版的著 作直到1859年才有了结果。当我们今天把马克思正式出版的经济学著作和手稿一起阅读 时,实际上已很难分出高下,有时甚至觉得手稿中的许多论述似乎更有吸引力。这至少 表明恩格斯的劝说不无道理,而马克思对待自己学术成果的严谨程度则远远超过了我们 庸常的察知能力。这种外在条件极差情况下的学术自律令人感佩。
马克思参加革命活动、撰写政论性著作也花去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尽管《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著作跟他的《资本论》系列著作同样重要。不管怎样,马克思毕竟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不因为献身革命活动而降低或牺牲其学术研究的质量,尤其是这种研究直接关乎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命运,以致他必须在学术上高度负责。成果可以出得少一些、慢一些,但在水准和质量上要问心无愧。这也是马克思高于其他革命家、政论家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政论性著作才具有超乎寻常的巨大冲击力。早期共产主义者魏特林跟马克思决裂,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只关心直接的思想结论和实际行动,而马克思则一定要将合理的思想置于牢固的学术论证的基础之上,否则就视之为对人民的欺骗。为此,魏特林曾讥讽马克思的东西是“书斋里的分析”,而马克思则以“无知从来不会使人得到教益”相回敬。[3](PP.45—46)巴枯宁也指责马克思为“空谈理论”的“理论狂”。[3](P189)拉萨尔的著 作除《赫拉克利特》外,也都以实际效果为目的,但事实证明,实际效果最大的还是马 克思经过学术锤炼的思想。在马克思面前,甚至连恩格斯都不免自嘲“在理论方面一贯 的懒惰”[3](P328)。本来,马克思是受恩格斯早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影响 才进入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后来还不止一次重读这篇文章,但最后在该领域卓然成 家的则是马克思,他们二人在这方面的差别显然不在思想观点上,而在学术投入上。
跟绝大多数学者一样,马克思也希望自己的学术成果被人重视和认可,为此,他也找人写书评,作宣传。晚年看到英国的杂志上载文称赞自己,他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然而,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马克思决不炒作自己,更不沽名钓誉。《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也曾通过恩格斯让库格曼“制造轰动”,但当得知他们准备在《凉亭》杂志刊登自己的传记和肖像后,马克思则请求他们不要开这样的“玩笑”。他说:“我认为这种作法有弊而无利,并且有损科学工作者的尊严。”[3](P480)从这里,我们不难瞥见马克思的学术人格。
马克思自己的有些话最能反映他的学术精神。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自己这部呕心沥血的著作,马克思最突出强调的是:这“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在《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序言和跋中,马克思讲了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套用诗人但丁的话说:“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让我们再看看经济学说史家熊彼特是怎样评说马克思的。他写道:“作为一个经济学 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博学的人。马克思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称他为天才和预言家, ……天才和预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专门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为他们不是某方面的专家 ,因而具有独创性。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没有什么能说明他缺少作为学者的素质, 或缺少理论分析技术方面的训练。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 少遗漏重要文献。他消化他读过的所有东西,深入思考每个事实,怀着热情争论不寻常 的问题的细节。他习惯于透视包含整个人类文明和延续发展的历史。或批评,或反对, 或采纳,或综合,他对每一个问题总是要探索透彻。最突出的证明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理 论,这是理论方面的里程碑。他不间断地为武装自己而学习,努力掌握一切应该掌握的 知识,从而避免使自己形成偏见、形成非科学的其他目标,虽然他是在为达到一个确定 的目标而工作着。由于他的聪明才智,他不由自主地把对问题的兴趣本身看得最为重要 ,而不管他在多大程度上把注意力集中在最终结果上。在工作时他主要关心的是用他那 个时代的科学来使分析工具变得锋利,关心如何使逻辑困难得到解决,关心建立一个理 论基础,以获得一个在性质上、目的上完全科学的理论,不论他可能有什么缺点。”[7 ](PP19—20)这简直就是一幅典型的学者肖像!这番对马克思学术精神的评说不能不说非 常内行,十分到位。
(四)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学术性无疑是一个基础性原因。马克思所做出的学术成果远远超出了他那个时代的平均学术水准。盘点19世纪的学术作品,《资本论》第一卷无疑是首屈一指的顶尖级代表作。没有行政力量的扶持,没有学术机构的依托,没有金钱势力的帮衬,没有新闻媒体的鼓吹,马克思的学说起于青萍之末,而终成影响人类历史的雄风巨响,如果不是因为它抢占了时代的学术制高点,是很难解释得通的。在那个时代,社会主义流派纷呈,先知豪杰层出不穷,为什么偏偏是马克思主义独领风骚,众多原因中至少有这条:因为其他社会主义派别中 无人写出在学术上够得上《资本论》水准的理论作品。其实,马克思早就说过:“理论 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 ,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8](P460)尽管马克思没有随即告 诉大家如何才能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他用毕生的学术研究示范了这一点。
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汉语世界的研究,普遍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对学术性的忽视。人们讲立场,讲观点,讲方法,讲大众化,讲联系实际,就是不讲学术水准,甚至习惯于纵容水准低下的言说。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能够延及今天,很大程度上不是靠众人的政治态度,而是靠马克思主义原初的学术力量;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当代的顿挫,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许多传人以政治态度代替了学术研 究,没有再像马克思那样花工夫做诚实的学问,没有再像马克思那样拿出能代表自己时 代学术水准的理论成果来。一种学术水准很高的学说是无须非学术的力量来庇护的,一 种低于平均学术水准的学说也不会给它的庇护者带来真正的益处,无论如何,没有比将 一种事关大局的政治主张和一种水平低下的理论学说捆绑在一起更危险的事情了。
在我们这个时代,要做一个思想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容易的,只要懂得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然后举手赞同即可。在我们这个时代,要做一个实践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难,哪怕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要信仰它,照本本上的说法去做就行。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要做一个学术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却难之又难,因为我们至少必须像马克思 那样读书,读马克思的书,读马克思读过的书,读马克思没有读过的书,读马克思之前 的书,读马克思之后的书,因为我们只有这样去读了,才谈得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创新 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去世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在汉语马克思的一个世纪中,思想上和 实践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固然很多,但真正学术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太少,至于能够代 表所处时代学术水准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可谓凤毛麟角。
同理,在我们这个时代,要做一个思想上的非马克思主义者或反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容 易的,只要对之不予理睬或不以为然即可。在我们这个时代,要做一个实践上的非马克 思主义者或反马克思主义者也很简单,不必说资本主义世界,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那些 口头马克思主义者在其实际行为中不都早就做到了吗?然而,要做一个学术上的非马克 思主义者或反马克思主义者谈何容易!没有比马克思更好的学养,更扎实的工夫,或更 独到的眼光,你怎么可能从学理上驳得倒马克思主义呢?又怎么可能在一个马克思的问 题尚未得到真正解决的时代从学术上绕得过或超越得了马克思主义呢?在马克思去世后 的一个多世纪里,在汉语马克思的一个世纪中,思想上和实践上的非马克思主义者或反 马克思主义者确实不少,但真正学术上够格的非马克思主义者或反马克思主义者其实不 多,至于能够像马克思那样代表一个时代之学术水准的非马克思主义者或反马克思主义 者则屈指可数。
以马克思的学术精神研究马克思主义,这在今天是最不应该存在争议的。不论对马克 思主义持什么观点,都应该争取在一个接近于马克思的学术水准上讨论问题,这对马克 思主义研究有百利而无一害。强调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维度,丝毫无损于马克思主义 的任何积极属性的发挥。也只有建立在严密学术论证基础之上的科学性才经得住追问, 才可能具有实践的合理性。
在写作本文时,我碰巧跟一位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讨论问题,我问他:中国学者知道许多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及其观点,德国学者对中国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否了解?他很干脆地说:没有。我问:为什么?他给了一些理由,其中透露出对中国学者的研究的不感兴趣和缺乏信任。他最后说道:总之他觉得不可能有德国学者为了了解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学习汉语。这个回答令人触动,不禁让我想到:但愿汉语马克思在他的第二个百年能够现出其学者的真身,即现身为学者马克思,或者说成为一个学者本色的思想家兼革命家,但愿马克思主义在汉语世界的第二个世纪是一个学术的世纪,或者说是一个由学术来支撑思想并引导行动的世纪。我想,这也应是马克思博士所愿 意看到的。
标签:资本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政治经济学批判论文; 马克思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读书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学术研究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