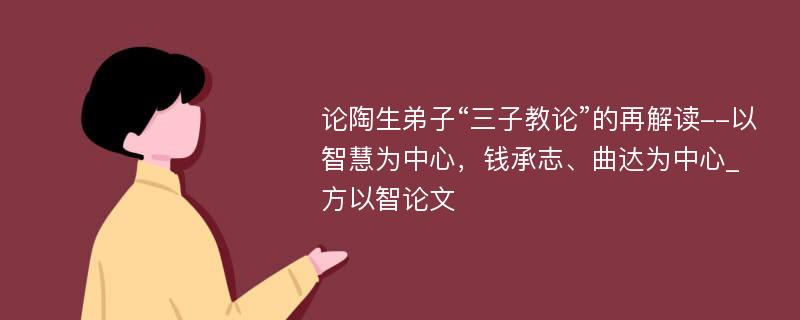
论道盛弟子对《三子会宗论》的再阐释——以方以智、钱澄之、屈大均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均为论文,弟子论文,三子论文,中心论文,会宗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0)01-0115-05
觉浪道盛在《三子会宗论》中指出,孟子、庄子与屈原共同承担着复兴儒宗的重任。由于在行文中,道盛更多地以孟子为标准,弥合庄、屈之间的界限,这样,所谓的“三子会宗”就演变为会宗庄、屈二子[1]32-43。为此,道盛设立了三个论题:一是“怨与怒”,即“夫(三子)固各自潜行以泯其亢变,各以怨怒戒惧而致中和,其相忘于无言也。”二是“天与人”,即“庄子者,道心惟微之孽子也,天之徒也,先天而天不违其人也。屈子者,人心惟危之孤臣也,人之徒也,先人而能奉其天也。此二子者,岂不交相参合天人于微危之独乎!”三是“生与死”,即庄子与孟子皆能自全而不陷于死,善于居亢而能无悔;屈子能自尽而不陷于生,尤善于居亢而能无所憾[2]。道盛享有江南明遗民导师的盛誉,其人格与著述都极具影响力。他的三位弟子——方以智、钱澄之、屈大均,从不同角度继承和阐发了会宗庄、屈的论题。
一、方以智的“怨怒致中和”说
道盛在《三子会宗论》末尾作自评,曰:“世不绝贤庸,讵知此后无有若而人,读吾此论,不大为赏鉴倡同心者,建一祠庙,貌三子之像,以孟居中,而左右庄、屈,同堂共席,相视莫逆,以配享千古。使景仰此天人不二之宗,岂不为甚盛事哉!”嫡传弟子方以智在道盛圆寂后,依师命修建了三一堂,曰:“因与诸子举杖人孟、庄、屈《三子会宗论》,欲以一堂享之。”[3]又作《鼎新闲语》追述杖人遗意:“杖人尝欲建鼎新堂祀孟、庄、屈,以三子同时不相识,特置一堂,作《会宗论》,谓屈以怨致中和,惟危尽人者也;庄以怒致中和,惟微得天者也;孟以惧致中和,合天人者也。”(《青原志略》卷十三)道盛对“怨怒致中和”的诠释,在于以兼善怨怒的孟子,会宗各善怨怒的庄、屈,并强调由怨及怒、一怒安天下的自我激励的心理过程。对此,方以智也是非常认同的:“生于忧患,以死养生;因惧以制其喜,因喜以神其惧。闻足以戒,激怒亦中和也;孤孽哀鸣,怨兴亦温厚也。声气风力,心光相续,塞乎天地”[4];“一以怨而自逼,写其不言之渔父焉;一以怒而自逼,写其藐姑之逍遥焉。以怨怒致中和,而声臭更冥矣”[5]。但方以智对“怨怒致中和”的阐释,运用了家传易学的“公因反因”说,较之道盛更具理论特色。
所谓“公因”就是支配万物运转而恒久不息的最高真理,属于本体,具有普遍性;“反因”则是世界上相反相成、交错代行的一切事物,属于现象,具有特殊性,所以说“公因在反因中”。方以智又化用佛教思想中的“伊字三点”——“∴”,来说明“公因”、“反因”的内涵与关系。《东西均·三徵》云:“圆∴三点,举一明三,即是两端用中,一以贯之。盖千万不出于奇偶之二者,而奇一偶二即参两之原也。”[6]三点中最上面的一点,所谓的“无对待、不落四句之太极”,指的是支配万物运转的至理,即公因;下面两点“相对待、交轮太极之两仪”,则为相互对立且又相互依存的反因。从中可知,“∴”中上面一点和下面两点为公因与反因的关系,恰如太极与两仪一样,太极为万物之源统摄着世界,正所谓“举一明三,即是两端用中,一以贯之”;而世界又是相反相成的形式存在的,太极必须通过一阴一阳的交轮替换而体现出来,即是“公因在反因”中也。
至于“怨怒”与“中和”的关系,方以智说:“举其半而用其余,用余之半皆其半,则所谓相反相因者,相救相胜而相成也。昼夜、水火、生死、男女、……博约之类,无非二端。参即是两,举一明三,用中一贯。千万尽于奇偶,而对待圆于流行。夫对待者,即相反者也。……受天下克,能克天下。欲取姑与,有后而先。”(《东西均·反因》)他认为世界由昼夜、水火、生死等一系列相互对立的因素组成,这些对立因素之间是相反相因的关系,即“相救相胜而相成”。所以,“危之乃安,亡之乃存,劳之乃逸,屈之乃伸。怨怒可致中和,奋迅本于伏忍”。可知,“怨怒”与“中和”构成了一对相反相成的“反因”。那么,统贯这对“反因”的至理“公因”又是什么呢?《东西均·三徵》云:“子思辟天荒以千古相传、不可言之‘中’,恐堕滉洋,忽创‘喜怒哀乐之未发’一语当之,而又创出中和之‘节’,则明示未发之中即和合于已发中矣。中非无过不及之说也,前后俱非,前后相续,时时此中,乃庸其中,适得而几,成毁通一。中非无过不及之说,而又岂废无过不及之中乎?明明上天之载,而无声无臭,是不落有无者也。”文中“喜怒哀乐之未发”的“中”,派生出“中和之节”,来调和“未发之和”与“已发之中”之间的关系。“未发之和”指中和,“已发之中”指怨怒。由此可知,公因乃是“和”,它统贯调节着“中和”与“怨怒”;又因为“公因在反因中”,所以中和是“未发之和”、怨怒是“已发之中”。用“∴”字来表示,即:
中
怨怒 中和
在方以智“公因反因”说的解析下,庄子所善之怒与屈原所善之怨,最终归复于中和。
道盛认为“怨怒”不仅是情绪的表达,更具有极大的社会功效,他大量列举古代圣贤借怨怒以平定天下的事例。那么,所谓的“中和”之境实乃安天下之功[7]。方以智不仅在学理上阐述了道盛的观点,更积极付诸实践。他素怀经世之志,却屡遭劫难,父亲被陷害入狱、自己遭阉党追捕,家仇国恨积郁在胸,未尝不有怨怒。但他从未消沉气馁,即使在明亡之后,仍四处奔走挽救败局。方以智含怨怒以尽忠孝,力图兴救亡之功业,此亦当致于中和吧。不过,他以“怨怒”论庄、屈,则有将二子简单化、类型化之嫌。
二、钱澄之的“庄、屈无二道”说
钱澄之与方以智相交甚厚,对道盛亦执弟子礼。他在《庄屈合诂自序》中强调著此书的目的,是通过“以《庄》继《易》,以《屈》继《诗》”的方式,发明《易》、《诗》二经的宗旨,最终使世人知晓“庄、屈无二道”和“《易学》、《诗学》无二义”[8]。
首先,“以《庄》继《易》”。钱澄之指出《易》之道在于“因”,而庄子正遵循此道:“夫《易》之道,惟其时而已。庄子以自然为宗,而诋仁义,斥礼乐,訾毁先王之法者,此矫枉过正之言也。彼盖以遵其迹者,未能得其意;泥于古者,不能适于今。名为治之,适以乱之。因其自然,惟变所适,而《易》之道在是矣。”[9]230文中认为,庄子看似诋斥仁义礼乐、訾毁先王之法,实乃因时而变之举。就本质而言,庄子所效法的“自然”就是“惟变所适”,也与《易》之道相通。同样,钱澄之对《庄子》内七篇的诂解,也始终贯穿着因时而变的主旨:他认为《逍遥游》讲出世法,与《易》的入世法是彼此为一的,无论出世入世,都因时而定;《齐物论》中成毁治乱是受《易》“穷则变,变则通”规律支配的结果;《养生主》中“善刀而藏之”是为了待时而动;《人间世》说心斋之法要“物来顺应,自然而然”;《德充符》言日夜相待皆有定数;《大宗师》论圣人之学乃是安时处顺、无所不因;《应帝王》意为因时而应居帝王之尊。这样,钱澄之得出结论:《庄子》自然之宗,本乎《易》因时之道。
其次,“以屈继《诗》”。钱澄之认为二者相继的关键在于“感”,即诗歌所具有的发人至深的情感。屈骚之所以能够承继《诗》,就是因为发自内心的深情,“屈子忠于君,以谗见疏,忧君念国,发而为词,反复缠绵,不能自胜。至于沉湘以死,此其性情深至,岂直与凡伯、家父同日语哉!”(《庄屈合诂自序》)“感”不仅是《诗》、屈相承的关键,也是钱澄之对所有诗歌的要求:“彼无所感而吟者,无情之音,不足听也。是以论诗者当论其世也,论其地也,亦曰观其所感而已。吾不知世所为温厚和平者何情也?悲从中来,郁而不摅,必遘奇疾,何则?违吾和尔。风也者,所以导和而宣郁也,吾极悲而情始和也。吾宁诗不传尔,其悲者不可删也。”(《田间集自序》)《楚辞诂》中也贯穿着以“感”论诗的思路:如《离骚诂》:“骚为遭,骚为扰动。扰者,屈原以忠被谗,志不忘君,心烦意乱,去住不宁,故曰骚也。”《九歌诂》:“《九歌》只是祀神之词,原忠君爱国之意,随处感发,不必有心寓托,而自然情见乎词耳。”《天问诂》:“屈子满腔疑情,凡人世相习而安之事,皆不可解。”这样,钱澄之就以“感”将《诗》、《骚》连缀为一。
虽然,钱澄之完成了“以《庄》继《易》,以《屈》继《诗》”的立论,但庄、屈之间仍存在很大隔阂。或许有鉴于此,钱澄之后来又对《庄屈合诂自序》的结论部分做了改动,文曰:“岂惟庄子本于《易》?屈子亦《易》也。《易》之时乘六龙,有潜有亢,庄处其潜而屈当其亢,时为之也。吾以屈子续《诗》,庄子亦诗人也。诗可以群,可以怨,屈子其善于怨,庄子其善于群者乎?吾合诂之,使学者知庄、屈无二道,则益知吾之《易学》、《诗学》无二义也。”[9]232钱澄之认为庄、屈皆本于《易》,乾卦六爻如同六条龙,有乾有亢,“庄处其潜而屈当其亢”。对此,道盛也有近似的看法。不同之处在于,道盛认为庄、屈皆善于居亢而无悔憾,各守生死而不失其正。钱澄之则认为“庄处其潜而屈当其亢”,并借“因时而变”来阐述庄、屈之道皆本于《易》的道理,即庄子藏身于世,惟时之不至;屈子伏清白以死直,乃时之所至。之后,钱澄之又提出庄、屈都是诗人的观点:“诗可以群,可以怨,屈子其善于怨,庄子其善于群者乎?”道盛认为庄子善于怒而屈子善于怨,方以智亦承此论。然而,钱澄之却从诗学的视角出发,认为屈子善于怨而庄子善于群。钱澄之采取了朱熹对“群”的解释,即“和而不流”[10]。近于孔子所言的“和而不同”,即顺应外物而又不失本己之意,也与《庄子·外物》中“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的意思相通。这样,在诗学的背景下,庄、屈也得到了会宗。
综上所述,钱澄之提出“《易》无体,以感为体;《诗》有音,感而成音”的观点,由此得出“《诗》通于《易》”的结论(《系辞上传》右第十章,《田间易学》卷四)。进而,又认为庄子、屈子因时而动,是顺乎《易》之道。这样,在易学理论的阐释下,庄、屈合而为一。钱澄之又以庄子善于群,而屈子善于怨,将二子会宗于诗学的背景下。对此,有研究者借图形做出生动而形象的概括:
诗 易
屈 庄
纵向上,表达了“以《庄》继《易》,以《屈》继《诗》”的观点,是经学与诸子学的会通;横行上,《易》、《庄》代表哲理,《诗》、《骚》代表诗歌,是哲学与文学的会通[11]186-187。如此一来,《易》、《诗》、《庄》、《骚》便彼此会通为一,钱澄之也完成了他合诂庄、屈的学术夙愿。
钱澄之“庄、屈无二道”的结论,实源自《三子会宗论》中“生与死”的论题。他巧妙地运用家传易学和诗学,弥合了庄、屈之间的隔阂。《庄屈合诂》作于钱澄之晚年,当时清王朝的统治渐趋稳定,很多前朝士人纷纷出世做官。钱澄之固守遗民志节,藏复明之心而潜居,以相时而动。他合诂庄、屈的目的,其实就是在为自己寻找理论上的支柱和心灵上的安慰。对此,清人也洞察明晰:“盖澄之丁明末造,发愤著书,以《离骚》寓其幽忧,而以《庄子》寓其解脱,不欲明言,托于翼经焉耳。”[12]当然,钱澄之也有将庄、屈儒家化的不足。他将庄、屈视为《易》、《诗》的后学,无疑是取消了庄、屈的独特价值,把二者看作儒学的附庸。
三、屈大均的“天人一贯”说
屈大均在《读庄子》中认为,大鹏之所以抟扶摇直上,去以六月息者,是因为“龙以六月而潜,故鹏以六月而息也。九为阳,六为阴,鹏之上以九万里,飞于阳之终也。息以六月,息于阴之始也。此庄生自喻其变化之用也。”[13]177屈大均以九六之数解读《逍遥游》,当受宋人以《易》解《庄》思路的影响。然而,屈大均更看重大鹏一飞冲天的结果,不像宋人旨在讨论阴阳循环的过程。因为在屈大均看来,大鹏与天有着紧密的联系:“鹏之在天,亦犹野马尘埃之在空。下视天,一苍苍也,天视下,亦一苍苍也,皆一气絪缊之所为。天以息吹下,下以息吹天,下以天为野马,天以下为尘埃,相消相息,无时而止,而万物化醇于其中,莫知所以,此造化之所以为妙也。”以为大鹏与天为伍,抟扶摇直上九万里,自上视下一片苍苍之色,使得《庄子》极具天放的特征。[13]178
同样,屈原《天问》亦如庄子之狂放:“三闾之《天问》,亦犹庄子之放言也。不必有其人,不必有其事,不必有其言,怨愤、无聊、不平,呵而问之,佯狂而道之,不可以情理而求之。《南华》、《离骚》二书,可合为一,《南华》天放,《离骚》人放,皆言之不得已者也。”相比于庄子的天放,屈原之放乃在人世间,故被称为人放。由于庄子的天放和屈原的人放都是不得已而发,所以可合而为一。但庄、屈之间仍悬隔天人,因此屈大均进而论之:“《嗟来桑户》之歌,《招魂》之祖也。反其真,则人而天矣。生而为人,死而为天。为人不如为天,而又何悲焉?虽然,人之生而已为天矣,天下人知其为人,而不知其为天,故有生死之说。惟生而知其为天,而以天为人,则死而知其未尝为人,而以人为天。于是乎,而天与人为一,生与死而不二矣。”[13]179《嗟来桑户》出自《庄子·大宗师》,认为人之死只是反其真,即由人而天;《招魂》将天上游魂招回人间,即天而人。如果《嗟来桑户》是《招魂》之祖,那么天与人之间就不存在差别,生与死亦可贯通为一,即“天与人为一,生与死而不二”。
显然,屈大均“庄子天放、屈原人放”的观点,融汇了《三子会宗论》中“天与人”、“生与死”两个论题。不同的是,道盛确立孟子为标准会宗庄、屈,屈大均则没有通过中间环节,直接将庄子之天放与屈原之人放会宗为一。但总体上,屈大均所论并没有超出道盛的思路。然而,屈大均在《三闾书院倡和集序》中,虽然也论及孟、庄、屈三子,但结论不但异于道盛的观点,与他自己的《读庄子》也有所不同。他说:“《离骚》二十有五篇,中多言学,与圣人之旨相合,其有功《风》《雅》,视《卜序》、《毛笺》为最。惜孟氏与之同时,知《诗》亡而《春秋》作,不知《诗》亡而《离骚》作。一邹一楚,彼此竟未同堂讲论也。庄生有骚之才,而未及为,亦其所遇不同。然庄生知尊孔子而不知所以尊,有愧于三闾多矣。……朱子笺注六经四子,即为《离骚》作传,非徒爱其辞能兼《风》《雅》,与其志争光日月,亦以其学之正,有非庄老所及焉耳。”[14]284文中慨叹孟子、屈原同时而不能同堂讲论,与之类似的观点亦出现在《孟屈二子论》[15]。虽然,屈大均叹惜孟、屈不得同堂而论,颇似道盛的心意,但是他却把庄子排斥在外,认为庄子“知尊孔子而不知所以尊”,远不如《离骚》得圣学之正。这就与道盛对庄子的看法大相径庭,道盛以庄子为儒家教外别传,“五经四子,互相发明其天人之归趣”(《三子会宗论》)。
屈大均对庄、屈关系的认识,尤其是对庄子的态度,为何出现如此大的前后反差呢?首先,《读庄子》的理路明显受道盛影响,屈大均于顺治十六年拜于道盛门下,该文当作于本年或此后不久;另据邬庆时《屈大均年谱》记载,《三闾书院倡和集序》作于康熙二十三年,《翁山诗外自序》则作于康熙二十五年[16]196、215。道盛圆寂于顺治十六年,故屈大均师从道盛的时间极短,故所受启发与影响,较之方以智等人要少得多,也就更容易在思想上保持原貌。所以二十多年后,屈大均再次论及庄、屈的时候,就更多地以个人看法为主。
其次,学养上的差异,也使得屈大均对庄、屈的理解与其他同门迥异。屈氏一族多工于诗作[17]1852,大均本人亦富诗名,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大家,生前诗集已流播甚广。在学术著作方面,《广东新语》、《皇明四朝成仁录》极具史学价值。《翁山易外》为屈大均的易学代表作,但是以《诗》解《易》的阐释方式,与方以智《周易时论汇编》、钱澄之《田间易学》相比,在理论深度上稍显不足。比较而言,同样为清廷封杀禁毁,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时,收录了方以智的《通雅》、《物理小识》和钱澄之的《田间诗学》、《田间易学》,著述颇多的屈大均却无一入选,或许说明他在学术研究上的缺憾。也正因为方、钱在理论上更具系统性,所以对《三子会宗论》的再阐释,能够自立角度、别有新论。反观屈大均,除了从天人一贯的角度转述道盛观点外,再无新的诠释。
另外,无论是觉浪道盛,还是方以智、钱澄之,都对《庄子》有过专门的阐释,道盛曾全评《庄子》,方以智作《药地炮庄》,钱澄之著有《庄子诂》。他们对庄、屈关系的论述思路,基本上是由庄及屈或是庄、屈并重的。而屈大均一向以屈原苗裔自居[18],又取“骚余”为字,还以“骚屑”为词集名。更认为《离骚》与《易》相通,合于圣人之旨[19]。相比之下,庄子就显得不得其正了。对庄、屈的厚此薄彼,使屈大均失去了深入理解二者关系的可能。
道盛享有江南明遗民导师的盛誉,著述与人格都颇具威信。《三子会宗论》的著成,在遗民中产生了强烈反响。该书眉批中保存了大量时人的批语,表达了对道盛观点的赞同。三位弟子方以智、钱澄之、屈大均各自选取不同的角度,对《三子会宗论》进行再阐释。由于家学渊源和人生经历的差异,使他们的观点在立论角度和演进方向上有所不同。这不仅体现了学术思想的传承,更流露出明遗民在特殊时代的生存困境。易代之际,他们试图通过会宗庄子之生与屈原之忠,来为自己选择做遗民而非死节寻求合理性。
然而,遗民终究是短暂的历史现象,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给后代[20]373-401。出仕清廷的唐甄认为,庄子不以卿相自污,有违君臣人伦,当以屈原之忠调和其荡;屈原悲泣自沉属于妇人行为,应该以庄子之达冲淡其愚。庄、屈之间如同桂热檗寒,性质正好相反,应该如用药一样,相互调剂,才不至于偏颇[21]。由于唐甄不是遗民,因此不需要像遗民那样通过泯灭庄、屈之间的差异,来为生存寻求理论支持。可见,处境和心态的变化会导致某些观念的改变。胡文英亦曰:“庄子最是深情,人弟知三闾之哀怨,而不知漆园之哀怨有甚于三闾也。盖三闾之哀怨在一国,而漆园之哀怨在天下;三闾之哀怨在一时,而漆园之哀怨在万世。”[22]诚如所论,庄子确实比屈原更加深刻和理性。而刘熙载更是道出了庄、屈各自处境的巨大差异,他说:“有路可走,卒归于无路可走,如屈子所谓登高吾不说,入下吾不能是也。无路可走,卒归于有路可走,如庄子所谓‘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今子有大树,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是也。而二子之书之全旨,亦可以此概之。”[23]8屈原固然可以为他国所用,或随波逐流,看似有多种人生选择,但以其狷介的性格,最终只能投水殉节。庄子穷困潦倒,不肯闻达于诸侯,似处绝境。然而,树之于无何有之乡,以无用为大用,最终可以悠游自得。庄子与屈原不同的性格与处世态度,导致了彼此不同的人生结局。由于清人没有明遗民的身份与心态,因而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庄、屈之间似同实异的关系。
收稿日期:2009-0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