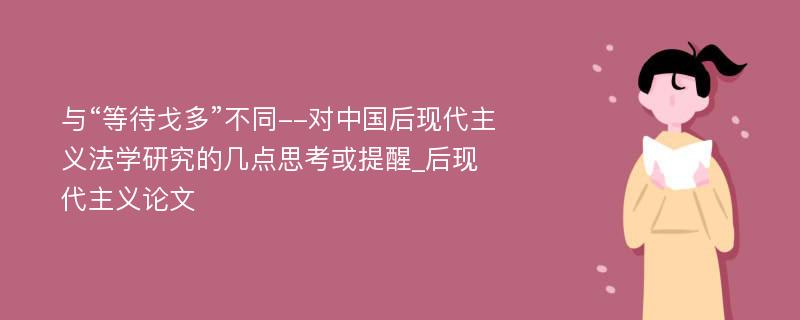
可别成了“等待戈多”——关于中国“后现代主义法学研究”的一点感想或提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了论文,后现代主义论文,可别论文,中国论文,感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今真是一个商品社会了,甚至语词也有了卖点。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乃至在中国法学界也逐渐兴盛起来了。在中国法学界,最早大约是我在1994年的一篇评论波斯纳的书评中提到了并分析了后现代主义的一些思想来源和特点。(注:“什么是法理学?”《中国书评》,1995年9月,创刊号。)随后,在1996年,在同季卫东到一个学术讨论中,我对后现代主义及其法学提出了一种看法。(注:“后现代思潮与中国的法治和法学”,《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我的基本观点是,后现代主义是当代西方的一个重要思潮,对法学也有一定的影响;不应当对后现代作“时代化”的理解,从而简单认为后现代主义与被认为尚未或正在现代化的当代中国无关;应当努力从学理上理解后现代主义,但不是按照现代主义的进路隔靴搔痒简单地予以理解甚或批评;我同时还分析证明,由于制度的因素,后现代主义很难在法学上有太大的市场;最后,我认为,当代中国的这一代法学家包括我自己都是现代主义者。很快,大约由于我在文章中表现了对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宽容”,以及我的一系列文章与传统的法理学研究不同,不喜欢唱高调、跟风;而且不仅论证方式不同,甚至叙述风格也与当时的主流不同;对一些当时或至今为学界视为神圣的概念、原则从经验上予以验证、考察和反思;因此我也很快被一些法学界人士指责为后现代主义或后学。尽管其中至少有一些人大约是从我的文章中才第一次了解甚或听到的这个词。
这之后,后现代主义法学就随着这个名词的引入逐渐就蓬勃起来了。但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其之所以蓬勃,原因并不是法学内思想学术的发展,而更多是法学内的政治经济的发展。这个名词具有一种分类的社会功能。首先,它可以作为一种贬低争论对手的武器,变成了一种拒绝思考对方提出的问题的标签,可以很便利地将一切非我族类的人或/和研究结果排除在视野之外。其次,这个标签的另一种社会政治功能就是自我标榜、标新立异,可以跑马占地。更有甚者,大约看出如今是一个符号的世界,是注意力经济,有概念股,新名词也有其卖点,因此,一些学者开始把大量的与传统法学不完全相同或与自己的理解力有差距的法学派别或研究成果都称之为后现代法学。尤其在中国,这一点格外明显。一些学者把法律经济学、批判法学、法律与文学、女权主义法学、批判种族理论等都称之为后现代主义。(包括这次会议)简直是,凡是与传统法学研究或诠释法学不一致的都可以称之为后现代主义。
这种现象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误解是难免的,任何理解之前都必定有一个误解。误解本身是理解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我们只能即希望经由时间来形成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共识。如果考虑到学术中的政治经济利益,这种相互之间难以交流理解的状况是一定会存在的,或者由于前设的不同(道不同),我看也无法通过理性交流来消除,只能通过法律学术和法律实践的发展逐步消解或遗忘。而且如果从学术上看,这种偏好就如同给人起名字一样,叫阿狗阿猫都没关系,都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标记而已。
我所关心是后果。这种现象带来了一种混乱,在学术界会造成了一种理解的困难,造成一种标签化的阅读和理解,拒绝认真理解被阅读的研究成果,并可能造成一种虚假的学术繁荣,并不有利于中国法学的发展。
如同我先前讨论过的,后现代反对的就是一种“时代化”,即用时间作为一个组织社会现象或学术研究的基本框架。(注:“后现代思潮与中国的法治和法学”,《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而现在绝大多数对后现代的使用,都是一种“时代化”,即把发生在当代的种种法学新发展都用“后现代”这个词统一起来了。这种用法不仅混淆了当代不同法学之间的差别,而且夸大了时下的法学与先前的法学之间的差别。它一方面强调了时间的断裂,另一方面又把时间维度本身当成一种有神奇魔力的组织框架。它把时代或所谓的时代精神本质化了。
事实上,现在一些被标签为后现代法学的学术流派很难称之为后现代的。不仅其内部差别很大,而且它们与先前到法学流派差别就理论思路而言并不那么大。让我们来做一点简单地分析。
例如,目前在美国最流行的、影响最大法律经济学,(注:关于其影响,可参看这一学派之对手的评价,Anthony T.Kronman,The Lost Lawyer:Failing Ideal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166-167,226.)显然延续了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和科学精神,并且这一传统可以更早追溯到古希腊,例如毕达哥拉斯就即希望用科学、数学来解释世界。近代的法律经济学的先驱也许是边沁,(注:关于边沁与法律经济学的关系,请看,Richard A.Posner,"Utilitarianism,Economics,and Social Theory",in The Economics of Justi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但边沁从政治上看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理性主义者。至于法律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以及卡拉布霍西无论如何也不能算后现代主义者。
批判法学当然是受到了后现代思潮的某些影响,但是其主要来源也仍然是现代主义的,理性主义的。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有比较多的怀疑主义的因素,但也受到其他学派思想的影响。例如霍维茨、特鲁贝克、图希内特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的著作都有很深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影子。(注:例如,Mortton J.Horwitz,The Tran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1780-1860,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甚至怀疑主义也并非后现代的特征,而是一切力求创新的研究者(而不是“常规科学”的研究者)的特点。只要看一看霍姆斯书信中所流露的怀疑主义,(注:Richard A.Posner,ed.The Essential Holmes,Selections from the Letters,Speeches,Judicial Opinions,and Other Writingsof Oliver Wendell Holmes,Jr.,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只要听一听汉德的名言“自由的精神就是对任何都不那么确信其正确”,(注:转引自,Gerald Gunther,Learnd Hand,The Man and the Ju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xiii。)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至于批判法学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命题:法律即政治,(注:David Kairys ed.,The Politics of Law:A Progressive Critique,Pantheon Books,1982;又请参看,Richard A.Posner,The Problems of Jurispruden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pp.153ff.)也不过是在重复着古希腊的强权即真理的命题。(注:在《理想国》中,色拉西马克就曾说:“如果一个人推理正确,他就会同意,正义[dikaion]无论在何处都一样,都是强者[kreittonos]的利益或好处[sumpheron]。”Platonis Opera,vol.4,p.339a(Ioannes Burnet ed.,1902)(Politeia,Bk I,11.2-4),转引自,Posner,The Problems of Jurisprudence,p.9n.12。)而这个命题在圣奥古斯丁那里,在马基雅维里、霍布斯那里都一直存在,并且是这些思想家的思想主线或之一。
法律与文学是一个以研究领域或材料而勉强组合的法学学派,其内部其实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纲领,或核心命题,因此它也就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派”。(注:可参看,冯象:“法律与文学(代序)”,《木腿正义》,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女权主义、批判种族理论也大致如此,其内部没有统一的理论纲领,而是一个依赖特定的研究群体,强调这一特定群体的独特视角之存在,并以特定问题为中心而组合的学派,甚至其中许多观点是自相矛盾的。比方说,从怀特的《法律的想象》,(注:James Boyd White,The Legal Imagination:Studies in the Nature of Legal Thought and Expression,Little,Brown,and Company,1973.)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全新的理论命题,他不过是用比较传统的案例教科书的编撰方式将一些经典的文学文本编撰起来,其分析也基本是普通法的案例教学法。此后的法律文学运动参与者更是在意识形态上,在理论进路上,包括对法律文学运动的基本态度上都有很大差异。例如法律文学运动的一位重要人物,波斯纳,就是以经济学家闻名,在他的影响重大的法律与文学(第一版)中,就称两者是“一场误会”。该书的第二版尽管删去了这一副标题,但是如果仔细读此书,我们仍可以发现,不仅波斯纳对法律与文学的进路持有很大的保留态度,而且他的分析进路基本上仍然是经济学的。(注:Richard A.Posner,Law and Literature,A Misunderstood Relationship,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Law and Literature,2nd and enlarged e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另一位学者韦斯特则是一位重要的女权主义法学家。因此,法律与文学作为一个理论来说,还是一个到处游荡的无家可归的人。它并非一个学派。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学派中的人物或著作就没有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确实受到了相当的影响。例如,法律经济学中关于理性人之真实与否与理论的关系问题上,波斯纳就认为作为经济学之前提假设的理性人尽管不存在,但这并不影响法律经济学的有用性。理性人虽然只是一个假定,但它仍然是有效的,解释力很强,因此经济学得以成立并不必须其起始假定是真的。(注:"Ronald Coase and Methodology",in Overcoming Law,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406ff。应当注意,这种工具主义的经济学反基础论(或基础论?)为不少经济学家所分享。请看,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9年。)这是一种罗蒂式的反基础主义的论证,(注:Richard Rorty,Objectivity,Relativism,and Truth,Philosophical Papers vol.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and Contingency,Irony,and Solidar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同时也是一种工具主义后果主义的真理观。又比如,批判法学的一些命题,法律与文学中斯坦利·费希的研究,都有强烈的后现代主义倾向。(注:Stanley Fish,The Trouble with Principl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and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应当注意,这两本书是两本文集,讨论的问题也并不仅仅是法律,甚至主要不是法律问题。)
即使如此,我在其他地方也指出过,受这种影响的也并非上述学派的学者,而是其他学派的学者也受到影响。例如罗尔斯为自己正义理论的基础所作的辩解,(注:John Rawls,"Kantian Constructivism in Moral Theory",and "Justice as Fairness:Political not Metaphysical",in John Rawls,Collected Papers,ed.By Samuel Freema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306.393-394.)尽管他自己也许不意识到这一点。
如果追究起来,一些被认为是后现代的学者,甚至是领军人物,就公开拒绝后现代主义,并对其他后现代主义者表示批评。最典型的也许是波斯纳,当然不是法律经济学的波斯纳,而是新实用主义法学的波斯纳。波斯纳不仅在《超越法律》中拒绝承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注:Overcoming Law,p.317。“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位后现代思想者”。)又在《法律与道德理论的疑问》一书中公开且明确界定了自己与肯尼迪(批判法学)和费希(法律文学)的区别,(注:The Problematics of Legal and Moral Theo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265-280.)尽管波斯纳被有的学者界定为美国后现代法学两个领军人物之一。(注:Gary Minda,Postmodern Legal Movements,Law and Jurisprudence at Century's End,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5,页208以下。敏达的判断主要基于波斯纳主张“一种没有基础的法理学”(《法理学问题》),这是一种反基础主义的立场,与罗蒂的反基础主义(《自然之镜》)有明显的血缘关系。但是敏达的断言过于简单,如果否认基础就足以构成后现代主义,那么科斯因为他反对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假说,也足以称之为后现代主义者了。)
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的主要来源是传统人文学科中的怀疑主义,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这一点非常重要。只要看一看当代后现代主义的一些主要思想家,他们都不是经验科学的信仰者,例如德里达、福柯、利奥塔、罗蒂、费希等,有些甚至是反对者。尽管他们中的某些人(例如福柯)也进行了一些从广义上属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但是他们的倾向从总体说来还是哲学的,人文的。
还有一些被标签为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他们则更倾向于强调实证的社会科学,他们的一些结论可能同后现代的一些命题相近。但是他们得出这种结论是从具体的实证研究获得的结果。例如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研究,使得“哲学死了”;例如波斯纳的经济学和法学研究,使得他主张“超越法律”。但是,他们提出的命题都是有更强的学科针对性,而不是一般的普遍的断言,更不是将这一断言作为他们实际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他们反对从原则出发,主张“不要想,而要看”,(注: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汤潮、范光棣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45页。)反对太多的形而上学的玄思,认为逻辑是批判的武器,而不是行动的武器,是破坏者而不是创造者。(注:Posner,The Problems of Jurisprudence,p.55。)因此,要将这两类尽管在某些结论上有相似之处的学者归为一类,实在是一种混淆视听,有可能误人子弟。这种习惯性归类之偏好反映出一部分学者在阅读学术著作时过分注重结论、断言,而对学术著作获得结论的理路缺乏关注,对这些后一类学者研究的问题本身缺乏关注和理解。或者说,关心话语超过了被话语说的那个东西。
上面的简单梳理并不是反对当代中国法学界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用法。我的要点是,如同我先前的观点一致,我们不应当过于看重将某一个学者或某一部著作归为哪一类。这种工作对于思想史、学术史研究也许有一定的意义,便于分类理解和全面把握;对于自己的思想清理也许也有点用处;对于教学、传授知识也许也有点意义;但是对于法学界、甚至对于法理学界的思想发展,在我看来,则没有什么意义。正如一位学者也许有点过于辛辣的因此有点后现代的挖苦,什么东西一落进“屎”(史)坑里,就完了;特别是法学。
为什么?因为法学和法律的特点,也因为学术思想发展的特点。就法学和法律而言,它们都是世俗导向的,最重要是要解决社会中的问题。而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并非理论在前,实践在后;而更可能是相反,请想一想“理论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才起飞”。理论对实践有某些指导作用,至少可能在某些时候如此。但是,即使理论上通了,在实践上也未必能做好。即使在这一事件问题上做好了,也未必能在另一个问题上做好。从理论到实践之间有一个很难跨越的鸿沟。“懂得如何做”与“做”不仅并不相等,而且两者还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知行合一的问题一直是人类的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法学思想的发展而言,也具有这样的问题。一般原则既并不能规定具体案件的结果,(注:Lochner v.New York,198 U.S.(1905),Holmes,J.,dissenting,in The Mind and Faith of Justice Holmes,His Speeches,Essays,Letters and Judicial Opinion,sel.and ed.by Max Lerner,The Modern Library,1943,p.149.又请看霍姆斯的另一名言,“人的主要目的就是提出一些一般性命题,而——我要说——这些命题都狗屁不值(wortha damn)”。见,同上,p.444。)也不可能包打天下。法学研究能力的培养不是通过了解他人的思想、给它们分类或排座次能获得的,而是在仔细研究他人研究的问题(而不是结论)并不断练习中获得的。(注:请参看苏力:“语境论——一种法律制度研究方的进路”,《中外法学》,2000年第1期。)
因此,在我看来,还是如同胡适所言,应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阅读学术研究成果时,首先不关心作者属于哪个流派,哪个主义,而是要和作者一起进入作者关心的那个问题。看作者的问题是否读者自己关心的问题?作者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其论证是否有道理?道理有多大?能否说服我自己?与自己的经验和信念是否吻合?如果不相吻合,问题是在作者身上还是在自己身上?自己能有什么样的补充和论证?用阐释学的话来说,读者一定要进入作者通过其文本展示给我们的那个视野。如果发现作者的说服力很强,那么,读者就可以而且也应当运用这种进路和理路来分析相似的问题,通过这种举一反三的反复练习,熟练掌握这种研究的“工具”,而不是注重研究的结论性命题。通过这样一个过程,逐步的,人的实际运用理论工具分析解决处理问题的能力就获得了,就扩展了。否则,如果仅仅关注主义、流派,他人的研究成果最多也只能成为你的一种谈资,一种话语的材料。你永远会和这些研究材料格格不入。
应当多多掌握这种工具。因此,学者或读者不应当轻易接受仅仅某一种工具,某一个学派,而是应当反复坚持上述的过程,不断扩展自己的视野和增多自己工具箱内的工具,使自己的工具箱内样样货色齐备,不仅各有各的用处,而且在某些时候用在一处。这样,当遇到新问题时,你会很自然地懂得该用什么样的工具来处理这些问题。这就意味着,各种理论都有其短处和长处,没有一种可以包打天下的工具,没有一种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并保证成功的理论。所有的理论都是人们的备用工具,都是为了出现问题而准备的。而人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言,重要的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1,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原有的着重号)。)所有的理论都只是人们理解、改造自己的生存世界的工具。理论对于人类来说并不具有神圣意味,其全部意义仅仅在于能够帮助我们生活得更好。因此,“我们想的应当是事而不是词”。(注:Holmes,Jr.,"Law and the Court",in The Mind and Faith of Justice Holmes:His Speeches,Essays,Letters and Judicial Opinions,p.389。)
也许我的这种态度太贬低了理论?其实,我的这种态度是具有包容性的。也许对于某些学者来说,理论完美本身就是他生活更好的一部分,甚至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因此,理论之所以对于他或她是神圣的仍然是因为理论对于他或她的效用。
我的这种观点也许还太实用主义了。其实也不是。即使对于法学家来说,重要的问题也在于获得理论,而不是谈论理论。获得理论的真正标志是思想和能力的发展,而仅仅谈论一些理论命题、一些人物的主义归属并不增加人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这种实用主义的观点又并不那么实用主义,它是以能力增长为导向的,而不是以谈资增加为导向的;它是以未来(解决新问题)为导向,而不是往昔(总结以往的观点)为导向;它是以参与者身份进入的,而不是以旁观者进入的。
也正因此,我可以这样说,我并不在一般意义上关心后现代主义。在我看来,究竟是什么主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学派、一个研究成果、一个学者在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上的研究是否出色,论证是否令人心悦诚服,是否给我启发,令我激动,使得我可以在其他问题上借助类似的进路和论证,推进我对世界的理解和我在世界上的行动。
其实,过分关心主义,在中国除了有排除异己、标新立异、跑马占地等嫌疑外,在智识上一个更深的潜在预设或意图是:有某种“主义”可能是通向真理的专列;一旦你搭乘上了这一专列,那么自己就比他人拥有更多的话语霸权,就可以至少在学术上(但不限于此)更多地教育或指教他人,就可以在真理之途上领先于他人一步。每个知识人或许或多或少都有这一点心态。有点也许并无太碍。但问题在于,是否真的存在着这样一种通向真理的专列?而即使有这样的专列,是否搭乘了这一专列,就保证了你可以对一切问题都做出正确的回答?有人可以这样相信;但我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这样的专利。法律的生命还是而且也只能在于经验。最后,就算是有这样的专列,那么对于“专列”的选择也只能在你的路途中,哪怕是需要倒车。你不能总是在月台上观看、分析那一趟是通向真理的专列吧?
一不小心,你可就成了“等待戈多”——也许这也是一种后现代?。
标签:后现代主义论文; 波斯纳论文; 法律学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等待戈多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法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