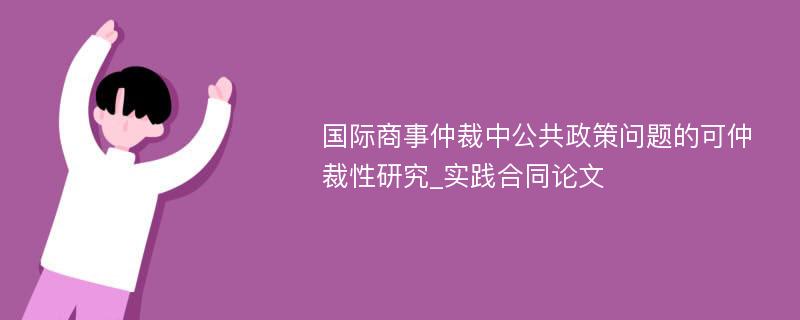
国际商事仲裁中公共政策事项的可仲裁性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共政策论文,商事论文,性问题论文,事项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公共政策与可仲裁性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虽然《纽约公约》第5条第2款把可仲裁性和公共政策作为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两项理由加以规定,但是,这两项抗辩事由之关系十分紧密,以致于二者在仲裁实践中通常是重合的,因为一国法律关于特定争议事项不能交付仲裁解决的规定,往住正是一国公共政策的组成部分或重要内容。在许多国家,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问题被认为属于一国公共政策的范畴。例如,荷兰司法部在“1986年仲裁法案解释报告”中明确指出,可仲裁性问题属于公共政策范围。① 仲裁实践中,争议事项亦往往与公共政策问题有关,通常会涉及到一国的公法,如证券法、反垄断法、知识产权法、破产法、反贿赂与反腐败法等。由此引出的问题是,这种涉及公共政策的公法争议或公法诉求(statutory claims)本身是否具有可仲裁性?这是国际商事仲裁中一个引人关注而又颇具争论的问题,也是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加以澄清和解决的问题。本文以此为题,拟对国际商事仲裁中公共政策事项的可仲裁性问题作一分析和探讨,以期能对我国仲裁的理论与实践有所裨益。
二、公共政策事项可仲裁性的法理分析
由于各国国情的不同,各国立法者对公共政策所持的观念和态度存在很大的差异、对争议事项可仲裁性所反映的公共利益的衡量互不相同,因而在立法上对可仲裁事项的划分标准也各有所异。不过总体而言,从历史上看,各国均不同程度地对仲裁采取了敌视或不信任的态度,不少国家的传统做法均以公共政策作为衡量争议事项可仲裁性的标准,因而可仲裁事项的范围十分狭窄,凡是涉及公共政策的争议事项或公法争议事项,各国通常不允许通过具有民间性的仲裁方式解决,而交由国家司法机关专属管辖。在美国,法院对公共政策事项的可仲裁性过去曾一直持否定态度,并通过若干案例判定与商业相关的公法争议,如证券法争议、反托拉斯法争议、专利法争议、破产法争议以及惩罚性赔偿争议等,不能提交仲裁解决。1953年的Wilko。案和1968年的American Safety案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在Wilko案中,②美国最高法院指出.尽管联邦政策支持仲裁的态度在美国仲裁法中得到体现,但是支持司法途径解决证券争议的公共政策足以压倒可仲裁性的推断(the presumption of arbitrability)。在American Safety 案中,③ 城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了数个促使其判定反托拉斯争议不具有可仲裁性的关键因素,其中之一就是“涉及反托拉斯法的争议不单纯是一个私人问题”,它包含了很强的国家利益,“违反反托拉斯法的行为会影响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的人,会造成难以置信的经济破坏。我们相信,国会并不希望此种争议通过非司法方式解决”。上述判决实际上反映了美国法院对商事仲裁的不信任态度,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美国“不可仲裁案件中的中心问题,是担心社会将由于公法争议事项提交仲裁而遭到损害。法院担心,公法问题对仲裁员而言太复杂,仲裁程序太不正规,仲裁员如同守护鸡笼的狐狸,其‘亲商业的偏见’(a pro-business bias)将导致旨在保护公众的法律得不到执行。”④ 欧洲国家的早期实践也是如此。以法国为例,法国传统上将不可仲裁性视为保护公共利益的一道安全阀。在立法上,《法国民法典》第2060条规定,任何关涉公共政策的事项均不能成为仲裁协议的标的。而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根据该条规定把仲裁限制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如果一项争议需要解释或适用公共政策规则,则这一争议是不可仲裁的。⑤
实际上,以公共政策判定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具有明显的不合理性。一方面,由于公共政策具有地域上的差异性和时间上的可变性,因而适用于可仲裁性的公共政策概念是相当模糊的,要描述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多数国家并没有对此作出立法规定,以确定哪些争议事项属于公共政策范畴哪些不属于公共政策范畴。一些重要的国际条约和文件也因此没有对公共政策提供进一步的定义或说明,《欧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的起草者甚至有意将“裁决违反公共政策”排除在撤销仲裁裁决的条件之外,理由就是公共政策作为一个弹性条款,各国法院均可根据当地的情况作出不同的解释。⑥ 另一方面,如果把与公共政策有关的问题不具有可仲裁性看做是一项原则并作广义解释的话,则意味着几乎所有的事项都是不可仲裁的,因为,争议不涉及公共政策的情况十分罕见。⑦
值得注意的是,晚近以来,各国对商事仲裁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放松了对仲裁的司法限制。事实上,这种转变不仅体现了各国对仲裁的支持,更表明了各国对仲裁的信任。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各国对提交仲裁的争议事项采取了更为包容和信任的态度,仲裁不再被认为是对政府在司法审判上的垄断的一种可以容忍的侵犯,而被视为一种能够公平解决争议的机制,一个能向参与国际交易的当事人提供法律保障的平台,其水平即使不高于也至少等同于国家法院所提供的保护。在此种情况下,当事人应当享有选择中立而公正的裁判庭的自由,而对可仲裁事项施加更为严格的限制将会给当事人设置不必要的障碍。⑧ 在Westacre案中,国际商会在日内瓦适用瑞士法裁定被告败诉,但被告提出争议,称案中咨询合约涉及当事人向科威特官员行贿以取得军售合同,故如果承认和执行这一裁决,将违背科威特法律和公共政策。瑞士联邦法院拒绝了被告的诉求;后者又向英国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裁决,称在英国执行该裁决有违英国的公共政策。但英国法院认为,在本案中尽量尊重裁决的终局性和不鼓励重新诉讼的公共政策显然压倒了防止国际交易中贪污受贿的公共政策,从而再次拒绝被告请求。法官特别强调指出,本案判决并不是对某些行贿行为视而不见,而是表明法庭对国际商会仲裁庭的信心:如果他们发现有这种问题肯定会作出判断。如果依据《纽约公约》让被申请执行裁决的法院以公共政策为由重新审理案件则是不适当的。⑨ 美国最高法院在Mitsubishi案中也同样表明了对仲裁的信任态度:“任何对可仲裁性范围的怀疑都应以有利于仲裁的方式解决。”⑩
上述各国对仲裁态度的转变反映在立法上,就是意思自治原则适用范围的扩大,使得仲裁的范围得以进一步拓宽。众所周知,当事人意思自治是仲裁的基石,是商事仲裁法中的首要原则。(11) 但是这一原则要受到公共政策的限制,当事人约定的争议事项能否提交仲裁往往要受到公共政策的制约。然而,这种制约的范围和力度是有限的。既然仲裁在本质上是当事人通过仲裁协议解决彼此间争议的一种契约性安排,一旦当事人双方决定将争议提交仲裁,当事人的这种选择就应得到充分尊重,就应当尽量减少公共政策对当事人合意的限制。正因为如此,公共政策的适用如今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限制,而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范围却在进一步扩大。这种变化在立法实践中的反映,就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自由处分性或可和解性作为认定争议事项是否可以仲裁的标准。例如,2003年《西班牙仲裁法》第2条第1款规定,“凡当事人依法能够自由处分的事项均可以仲裁。”(12) 又如,按照《瑞典仲裁法》第1条的规定,对于可和解的争议,当事人可以协议的方式交付仲裁解决。(13) 据此,可以认为,在当今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中,意思自治原则已成为判定争议事项能否仲裁的理论基础,当事人对争议所涉的权利及其处理方式可以自主决定,对于那些仅涉及当事人双方利益的争议事项,对于当事人能够自由处分的争议事项,或者对于当事人可以自己通过和解方式解决的争议事项,国家一般都不予干涉而允许双方当事人约定交付仲裁。因此,照此说来,以自由处分性和可和解性为标准,凡与当事人个人利益有关而又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公共政策事项或公法事项,均可以通过仲裁解决。例如,在反垄断法方面,对于因合同而产生的反垄断争议或横向的反垄断争议,只要双方当事人有约定,其可仲裁性就应当得到肯定。在市场竞争中,如果具有优势地位的供应商采取一定的经济补偿或者扶助手段,使得它的同行业对手不至于丧失竞争地位,也不至于损害国家和公众的利益,那么这种争议在私底下解决也未尝不可。毕竟,反垄断的最终目的还是维护竞争者的经济利益,只要是经济利益,就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于是就存在自由处分或和解的余地,(14) 就可以提交仲裁加以解决。
与此相关联的是公法诉权的强制性与当事人自由处分权的冲突问题。在一些国家,法律规定某些公法争议事项只能寻求司法救济,这是当事人的一项权利,不能放弃。例如,按照美国以往的司法实践,因证券交易引起的争议属联邦法院专属管辖范围,当事人不能自行放弃寻求法院救济的权利。在前述Wilko案中,最高法院指出,证券法禁止放弃该法所规定的法院专属管辖权.违反这一规定的仲裁协议属于无效。因此,法院适用了“证券交易案不得排除诉讼管辖权”这一联邦证券法中的公共政策,判定仲裁机制不适于解决证券争议。(15)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公法与私法的界限逐渐模糊和淡化,公法与私法相结合已成为国际商事仲裁发展的一个趋势。实践中,各国司法机构更加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并不完全排除公法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作为公力救济象征的国家司法权设立的根本目的在于解决纠纷,保护当事人私权。因此,如果当事人在权衡利弊后台意放弃了自己的诉权,在不浪费公共资源或者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下选择由他们自己设立的私人法官来定纷止争,司法权就应当尊重当事人的这一愿望,将纠纷交由仲裁解决。另一方面,虽然仲裁协议同时处分了民事程序权利和民事实体权利,并涉及国家的司法管辖权,但从根本上讲,当事人处分的是自己的权利,在不侵犯国家和他人权益的情况下,无论当事人以何种形式对自己的私权进行处分,国家都应当予以尊重。(16)
这样,也就不能断然否定公共政策事项或公法事项的可仲裁性了。随着人们对仲裁认识的转变以及自由处分性或可和解性标准的确立,那种以为只要争议涉及公共政策即不可仲裁的观点和做法逐渐遭到摒弃。(17) 在今天,普遍的观点是,凡涉及证券、反垄断、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公法争议或公共政策争议事项,只要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且争议事项是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或可自行和解的,就可以提交仲裁解决。即便是关涉贿赂的违法合同争议,尽管仲裁员不是公共政策的守护人,无权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但是,如果当事人已商定了仲裁条款,则应由仲裁员决定违法性的后果,即裁定合同的有效与否。所以,没有理由否认把公共利益作为其主要目标的公法问题的可仲裁性。(18)
三、公共政策事项可仲裁性扩大化趋势的体现
正是基于各国对仲裁态度的转变以及对仲裁所持的信任态度,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范围得以进一步扩大,支持涉及公共政策的争议事项提交仲裁已成为现代国际商事仲裁的一种发展趋势。从各国的立法与实践来看,公共政策事项可仲裁性所呈现出的扩大化倾向主要通过下述方式体现出来。
(一)区分国内仲裁与国际仲裁
晚近以来,出于国际商事一致性和可预见性的考虑,世界上不少国家把仲裁区分为国内仲裁与国际仲裁。与此相适应,在可仲裁性问题上,公法争议就有了国内争议事项与国际争议事项之分。相比之下,各国对国际仲裁的态度更为宽松,国际仲裁因公共政策而受阻的情况十分少见。(19) 对于国际争议事项,各国一般不适用国内公共政策,只要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就不轻易地援用公共政策来否定国际性公法争议的可仲裁性。
美国的实践在此方面最为典型。美国最高法院在一系列案件中,改变了其对国际仲裁的敌对和猜疑态度,放弃了其公法事项不可仲裁的观点,主张在国际争议领域中适用国际礼让原则,不能把国内不可仲裁的观念机械地适用到国际性争议事项,认为狭隘的国家利益应当服从于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的广泛利益,任何具有国际商事性质的仲裁协议或裁决都可以得到执行,而不管其是否与传统的可仲裁性标准或公共政策标准相一致。(20) 从而确立了“国际考虑优于国家公共政策”的原则,打破了仲裁与公法争议之间的障碍。Scherk案、Mitsubishi案和Shearson案是美国法院将争议事项区分为国内和国际争议事项并确认国际性公法争议事项可以仲裁的三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判例。
在Scherk案中,美国最高法院非常清楚地阐述了国际和国内仲裁的区别对公共政策事项可仲裁性的影响。该案中,由于联邦法律禁止当事人在国内有价证券交易案件中放弃诉讼权,故伊利诺斯地区法院和第七巡回上诉法院判定,仲裁协议不能排除证券购买者因受欺诈而寻求司法救济。但最高法院最终推翻了一、二审法院的判决。最高法院认为,与Wilko案仅涉及国内证券交易不同的是,本案存在一份“真正的国际协议”,国际协议的仲裁条款即使在涉及法院地公共政策的争议中也是有效的。因此,有关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国际性争议可以提交仲裁。(21)
Mitsubishi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涉及公共政策的反托拉斯争议是否具有可仲裁性。经过审理,美国最高法院指出,不存在公共政策上的原因而禁止将国际反托拉斯争议交付仲裁。法院总结道:“我们的结论是,出于国际礼让的考虑,对外国和跨国仲裁庭能力的尊重,以及在国际体制中当事人对解决争议可预测性的迫切需要,都要求我们执行当事人的协议,即使在国内反托拉斯争议中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22) 这一判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其他国家的仲裁立法与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国际商会仲裁院(简称ICC仲裁院)第8423号案件中,仲裁员在判断一份限制竞争的合同的有效性时,援引了美国最高法院在Mitsubishi案的判决,以支持其公法争议可以仲裁的主张。(23) 新西兰高等法院在一个案件中指出,尽管Mitsubishi原则所反映的是美国的司法政策,但对其他国家也是适用的。(24)
在Mitsubishi案两年以后的Shearson案中,(25) 最高法院同样出于国际礼让以及平衡当地利益与国际考虑的需要而判定,如果当事人有约定,由证券法和《反欺诈与合谋法》引起的公法争议均可提交仲裁。
国际利益的相互承认及国际礼让原则的适用,为允许国内公法争议提交仲裁铺平了道路。上述三个案件后,美国一些判决进一步将这三个案件的裁定扩大到国内争议,判定公法争议在国内情况下也可仲裁。(26)
美国并非惟一区分国内仲裁与国际仲裁而判定国际性公法争议可以提交仲裁的国家。在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20世纪70、80年代后,国际主义以及扩大仲裁范围的愿望逐渐取代了反对仲裁解决公法争议的公共政策考虑,国际性的公共政策事项在这些国家已逐渐被允许提交仲裁。例如,法国于1981年对其民诉法典作了修改,区分了国内与国际仲裁。(27) 在一个类似于Mitsubishi案的案件中,巴黎上诉法院判定,欧共体竞争法支配的争议事项可以提交国际仲裁庭解决。这一判决得到了最高法院的确认。(28) 又如,按照1985年修订的比利时《司法法典》,法院不得对国际仲裁进行司法干预,无论仲裁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29)
(二)要求仲裁员适用公共政策规则
目前,在仲裁员与公共政策的关系上,欧美国家的主流观点是,仲裁员应当适用公共政策规则。在一些案件中,法院并没有因为仲裁涉及公共政策问题而简单地宣告仲裁庭无管辖权或仲裁裁决无效,而是认为仲裁庭有能力甚至有义务适用公共政策规则,从而默许了仲裁庭对于与合同相关的公法问题的管辖权,以间接的方式肯定了公共政策事项的可仲裁性。概括而言,主张仲裁员适用公共政策的观点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首先,仲裁员作为法官的替代者(substitute),与内国法院处于同等的地位,不应忽视本来在同样情况下由法官来保护的公共利益,而应当裁定公共政策规则在何时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介入或者帮助国际商事争议的解决。(30) 学者们认为,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统一和全球化,要回到以前那种仲裁员纯属代表当事人的私方利益而法官则代表公共利益的简单模式中去,已经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了。相反,公共政策规则的正确适用却要求一种复杂的模式,即仲裁员和法官在复杂的裁判程序中和适用公共政策规则方面应当相互支持与协调。(31) 从长期来看,仲裁的合法性取决于仲裁员是否愿意尊重相关国家的公共政策,因为国家允许公共政策事项提交仲裁,是基于相信仲裁员会适用与争议有实质联系的国家的公共政策。如果仲裁员不断忽视这些公共政策规则或对其置之不理,或者断然拒绝适用这些规则,则国家和法院就会对仲裁员裁断涉及公共政策的争议失去信任,进而会危害公共政策事项的可仲裁性。反过来,这将限制当事人利用仲裁优势的可能性,减少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的有效性,从而动摇现代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基础,危及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重要性。因此,仲裁员必须实施保护公共利益的法律,以获得国家对国际仲裁的支持。(32)
其次,基于裁决有效性的考虑,仲裁员应当适用相关国家(通常是仲裁地国和裁决执行地国)的公共政策。法院对公共政策争议事项可仲裁性的承认,通常伴随着所谓的“二审”理论(“second look”doctrine)。(33) 目前,欧美法院在Mitsubishi案、Eco Swiss案等一些著名的国际案件中,确认了“二审”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国内法院在裁决撤销或执行程序中保留对仲裁员适用公共政策规则进行审查的权利。因此,为了保证仲裁不被当事人用来规避有关国家的公共政策,为了保证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即使当事人已经选择了可适用的法律,仲裁员也不能忽视公共政策对合同关系的影响,应当考虑仲裁进行地国和裁决执行地国的公共政策。诚如Catherine Kessedjian教授所指出的:“在仲裁员决定是否适用强制性规则的问题上,每一个仲裁员最应关心的就是他的产品——即裁决能否得到执行。”(34) 否则,倘若仲裁庭不对违法合同或违反公共政策的合同进行审查,它就要冒裁决可能被撤销或得不到承认和执行的风险。
欧美国家的实践亦清楚地表明,仲裁庭有权且有义务适用公共政策规则。美国最高法院在Mitsubishi案中确定了仲裁员适用公共政策的义务,判定仲裁员应当按瑞士法的公共政策审查合同的有效性,即使这样做会与当事人的法律选择相冲突。法院还警告,如果仲裁员拒绝对反托拉斯争议作出裁定,其仲裁裁决将被拒绝承认和执行。(35) 在著名的Eco Swiss案中,(36) 欧洲法院指出,欧盟条约第81条构成了共同体的公共政策.因此,仲裁员在断案时应注意这一问题,仲裁员与法官都负有依职权适用共同体竞争法的义务,必须对竞争法事项进行仲裁,如果没有这样做,则其裁定将得不到支持。可见,欧洲法院并没有因仲裁涉及被视为欧盟公共政策的竞争法而宣布仲裁庭无管辖权或者判定竞争法争议不能提交仲裁,而是要求仲裁庭必须适用欧盟竞争法。1992年在瑞士日内瓦审理的一个有关比利时和意大利两家公司的合同争议仲裁案中,仲裁庭以合同准据法为比利时法为由,拒绝按一方当事人的请求对合同是否符合欧共体竞争法进行裁判。但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否定了这一做法,认为仲裁庭应当对协议是否符合欧共体竞争法的问题进行审查,如果不进行这样的审查,其作出的裁决属于无效。(37) ICC仲裁院在其相关案件中阐述道,违反仲裁程序进行地国的公共政策,可以成为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其目的是为了促使仲裁员尊重仲裁进行地国的公共政策。同时,仲裁员也应当尊重承认和执行裁决地国的公共政策规则。正是基于这一理由,ICC仲裁员才有意识地适用欧共体竞争法规则。(37)
一些法院和学者还主张,在当事人没有提出公共政策问题时,仲裁庭应当主动考虑或提出这一问题。假如仲裁员已意识到案件涉及公共政策,例如跨国公共政策规则受到危害或者明显存在对公共政策规则故意欺诈的情况,而一方当事人并没有援引该规则作为抗辩时,仲裁员应当依职权主动适用相关公共政策规则。比如,在仲裁庭怀疑合同违法或存在与合同相关的违法行为(如商业腐败行为)时,那么其可能犯的最严重的错误莫过于对此置之不理。这时仲裁员应该通过询问证人和当事人进行必要的查证。在证实违法事实后,简单的方法就是适用相关国家的公共政策(如反腐败法),根据公共政策宣布合同或交易违法无效;如果相关法律没有提供足够的法律救济,则仲裁庭还可采取进一步的措施。(39) 在美国法支配的情况下,此种措施应当包括提供三倍损害赔偿的救济。
(三)对公共政策的限制性解释与适用
各国立法与实践对公共政策的狭义解释和适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共政策与可仲裁性抗辩理由的适用范围,很少否定涉及公共政策的仲裁裁决的有效性,从而也就间接肯定了公共政策事项的可仲裁性,反映了公共政策事项可仲裁性的扩大化趋势。
公共政策在范围和内容上具有很大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和主观性,因而很容易导致公共政策在司法实践中被滥用,从而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终局性和可执行性构成威胁。正因为如此,有人不无担心地说,“公共政策好比一匹难以驾驭之马(unruly horse),一旦跨上去,就根本不知道它会将你带向何方。”(40) 虽然这一比喻未免有些夸张,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公共政策确实是一个很难把握的问题。所以,为了更好地控制公共政策这匹难以驾驭之马,以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公共政策进行分类,将其区分为国内公共政策和国际公共政策,以限制对公共政策的滥用。一般的观点是,国际公共政策比国内公共政策的范畴要狭窄,它仅指一国的根本原则、基本道德与公正观念。
立法实践中,各国采取了一种宽松的国际公共政策概念,很少规定以外国裁决的准据法本身与本国的国内公共政策不一致为由拒绝予以承认和执行,而仅在承认和执行该裁决将违反国际公共政策的情况下,才否认裁决的可执行性。例如,按照1981年《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498条,如果援引仲裁裁决的当事人证明它存在且承认裁决不明显违反国际公共政策,仲裁裁决应予承认和执行。另外,依照该法典第1502条,法院可以在五种情形下撤销仲裁裁决,其中之一就是承认或执行裁决将构成对国际公共政策的违反。又如,根据《荷兰民事诉讼法典》第1063条,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只有在违反荷兰法律制度的根本原则时,才构成违反荷兰的国际公共秩序而被拒绝承认和执行。与区分国内国际公共政策的情况相联系,不少国家的立法与实践对于公共政策事项可仲裁性的审查采取了所谓的“客观说”,对公共政策进行限制性的解释和适用。(41)
各国大量的判例也直接或间接地作出了国内国际公共政策的区分,正如荷兰范登伯格教授所说,国内与国际公共政策的区分正在不断地得到法院的承认。(42) 执行法院只是在十分有限的场合,才援用公共政策例外,否定公共政策事项的可仲裁性。欧美国家许多判例的观点是,《纽约公约》第5条第2款第2项所指的公共政策实际上是国际公共政策概念。以美国为例,在著名的涉及公共政策的Parsons案中,(43) 美国联邦法院对《纽约公约》的公共政策作了狭义的解释,认为只有裁决的执行违反法院地国最基本的道德和公正观念,法院才能基于公共政策否定外国仲裁裁决的执行效力。如果狭隘地把公共政策解释为保护本国政治利益的工具,则将严重损害公约的作用。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Fotochrome案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立场,承认了当事人破产前所订仲裁条款的有效性,并执行了仲裁裁决。该案判决表明,美国这一“不可仲裁性”的公共政策并不适用于跨国破产案件。(44)
在欧洲,法国、意大利、瑞士等大陆法国家在国际仲裁方面仅允许当事人依据国际公共政策提出可仲裁性问题,而国内公共政策问题被认为太狭窄,因而不能阻止国际商事仲裁程序的进行。(45) 法国法院把国际公共政策当作对可仲裁性的惟一限制,仅在外国仲裁裁决违反国际公共政策的情况下,法院才考虑否定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和裁决的有效性。(46) 荷兰立法虽然没有区分国内公共政策与国际公共政策,但在仲裁实践中却作了这种区分。对于境外仲裁裁决,荷兰法院通常是从狭义上对公共政策予以解释和适用,即根据国际公共政策而非国内公共政策对裁决进行审查。在“伊沙克诉摩西斯和埃斯特拉”一案中,荷兰鹿特丹法院判定,本案仲裁是在以色列依以色列法进行的,按照该国法律,有关犹太宗教的问题可以仲裁,因而该协议并非无效。(47) 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在Westland-Helicopters案中认为,瑞士国际私法第190条第2款第5项所规定的公共秩序仅限于跨国的情况。因此,一项仲裁裁决倘若没有违反根本的法律原则,如契约必守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诚信原则,征用应予补偿原则等,则该裁决不应被撤销或被拒绝承认和执行。(48) 英国司法实践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在Lemenda案中,(49) 英国法官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公共政策,一是“基于普遍道德原则的”公共政策,二是“仅基于纯国内考虑的”公共政策。如果一个合同违反的是前一种公共政策,英国法院将拒绝执行,而不考虑合同的准据法和履行地法的规定;而当一个合同违背的是后一种公共政策时,只在合同既违反了英国国内法上的公共政策,又违反了合同履行地的公共政策,它才会被英国法院拒绝执行。这就是所谓的“双重不可执行性标准”(double unenforceability)。(50)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国家虽然没有严格区分国内国际公共政策,但对于公共政策的适用采取了狭义解释或严格适用的原则,实际上是以国际公共政策的标准判断公共政策事项是否可以仲裁或者公共政策事项的裁决是否具有可执行性。例如,德国法院在多起判决中已确认,在涉及外国仲裁裁决案中,违反德国法强行规定并不必然就构成违反公共政策,“只有极端情形”(extreme cases only)才认为是违反了公共政策。(51)
各国法院对公共政策采取狭义解释和适用的做法表明,除了违背“基于普遍道德原则的”公共政策的情形之外,那些绝大多数只涉及“基于纯国内考虑的”公共政策的案件,其裁决是可以得到执行的,这也就意味着,此类争议案件是可以仲裁的。所以,公共政策事项的可仲裁范围正在不断扩大,更多的公法争议甚至包括涉及贿赂的争议,现在已经或正在变得可以仲裁。就违法合同而言,英国、美国及瑞士等不少国家的法院都已在判例中明确承认,仲裁庭有权接受涉及贿赂的合同当事人的仲裁申请,并应独立地对非法性问题作出裁决。(52) 在Harbor案之后,英国法院已经允许违法合同争议通过仲裁解决。(53) 在Northrop案中,双方当事人的协议规定,由特里德作为代理人向沙特出售战斗机。特里德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向沙特政府官员进行了贿赂。争议发生后,仲裁庭作出了有利于特里德的裁决,裁定诺思罗普公司向特里德支付佣金。根据美国和沙特的法律,支付此种佣金是非法的。诺思罗普遂向法院起诉,认为佣金协议涉及到公共政策而不可仲裁,因而要求撤销该裁决。但美国法院仅取消了部分裁决,而承认因违法合同或违法行为而产生的争议具有可仲裁性。(54) 在Hilmarton案中,(55) 案件涉及贿赂行为,历经两次仲裁和两审法院的裁判,但无论是两次仲裁裁决,还是日内瓦法院和瑞士最高法院的判决,都没有否认仲裁员对案件的管辖权。总之,从上述案件以及其他相关案例来看,无论仲裁员是断定贿赂合同有效还是认定其无效,法院都没有否定仲裁员对案件的管辖权,也没有否定案件的可仲裁性。而从执行法院的情况来看,大多也没有否定此类合同裁决的可执行性。因此,有学者认为,就目前情况来看,涉及贿赂的合同可以仲裁,应由仲裁庭对争议行使管辖权,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已取得了共识。(56)
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内公共政策与国际公共政策的区分也告诉我们,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并非所有公共政策的争议事项都是可以仲裁的,公共政策仍然制约着仲裁的范围,违反国际公共政策的争议事项仍然不能提交仲裁解决。换言之,只有那些不违反一国根本原则的公共政策事项才具有可仲裁性,其裁决才是可执行的。
四、中国的立法与实践
我国《仲裁法》第2条和第3条对可仲裁性问题作了较为明确和具体的规定。该法在确定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时依照仲裁性质采纳了两条原则,其中一条就是从当事人是否有权自由处分争议事项的角度出发,规定凡是当事人无权自由处分的事项都不能通过仲裁解决。(57) 可见,这与国际上的普遍做法是基本一致的。
我国立法中并没有公共政策的提法,而是使用了“社会公共利益”的概念,(58) 因而我国立法也不可能区分国内公共政策与国际公共政策。再者,我国立法上也没有对“社会公共利益”这一概念作出具体解释,最高法院关于《民诉法》和《仲裁法》的司法解释,也同样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涵义保持缄默。因此,这种状况实际上赋予了法院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地方法院在以往的实践中经常对“社会公共利益”作出宽泛的解释,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不予执行的情况时有发生,有的甚至滥用“社会公共利益”的概念,造成了不良影响。(59)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实践中在对待“社会公共利益”概念的问题上基本采取了狭义的立场。最近的“ED&F曼氏(香港)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及执行伦敦糖业协会第158号仲裁裁决案”(简称“第158号仲裁裁决案”)即为一例。(60) 该案中,中国糖业酒类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糖集团)与ED&F曼氏(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曼氏公司)因原糖销售合同的履行产生争议而按合同仲裁条款向伦敦糖业协会提起仲裁。后者作出了有利于曼氏公司的仲裁裁决。2002年1月22日,曼氏公司向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提出了承认和执行该裁决的申请。而中糖集团其后提出了拒绝承认和执行该裁决的申请,认为裁决所承认的是通过非法期货交易合同取得的非法利益,承认和执行该裁决将与我国公共政策相抵触。另外,中糖集团还援引了英国上诉法院在Soleimany一案中的判决:因非法合同取得的非法利益,英国法院可以依据公共政策否定其执行力。(61) 中糖集团认为该案例所反映的原则,对于我国法院在解释和适用公共政策保留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境内企业未经批准不得擅自从事境外期货交易。中糖集团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境外期货交易的行为,依照中国法律无疑应认定为无效。但违反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能完全等同于违反我国的公共政策。因此,本案不存在《纽约公约》第5条第2款规定的承认和执行该判决将违反我国公共政策的情形。依照《民诉法》第269条及《纽约公约》第5条之规定,应当承认和执行本案仲裁裁决。(62) 值得注意的是,该案中法院使用了“公共政策”而非“社会公共利益”的概念,而且,尽管最高法院并没有正式提及和区分国内和国际公共政策,但实际上是以国际公共政策的标准来判定裁决的可执行性的。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最高法院在“第158号仲裁裁决案”中还肯定了公法争议的可仲裁性。本案中,中糖集团认为,涉案合同及其附件是以规避法律为目的,是具有欺诈性的期货交易性质的违法合同。同时,这种期货交易合同关系也不属于我国法律认可的契约或非契约性商事关系。因此,根据《纽约公约》第5条第2款的规定,我国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争议不具有可仲裁性。但最高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因履行期货交易合同产生的纠纷,在性质上属于因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产生的纠纷,依照我国法律规定可以约定提请仲裁。可见,最高法院在本案中实际上是从狭义上对《纽约公约》第5条第2款规定的可仲裁性问题进行了解释,并没有以我国国内公共政策为标准而否定具有规避法律和欺诈之嫌的期货交易合同的可仲裁性,间接肯定了违法合同的可仲裁性。该案将对我国今后有关公共政策事项可仲裁性的实践产生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五、结论
综括上述对公共政策事项可仲裁性的分析以及对各国立法与实践的考察,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两点重要认识。
其一,尽管公共政策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具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对公法争议的可仲裁性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增加和国际商事仲裁的不断发展,各国对仲裁的态度也随之转变,对仲裁持一种更为宽松和信任的态度。因此,以公共政策对当事人意思自治所作的限制已经大为减少,而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范围却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从而使得自由处分性和可和解性成为认定争议事项是否可以仲裁的重要标准。据此可以认为,凡是当事人能够自由处分或者当事人可以自己通过和解方式解决而又不损害他人或国家利益的公共政策争议事项,理应可以通过仲裁方式解决。
其二,各国对国内仲裁和国际仲裁的区分、要求仲裁员对公共政策的适用以及对公共政策的限制性解释与适用,大大限制了公共政策抗辩理由的适用范围。虽然这些国家的立法与实践并没有完整而确切地阐释公共政策的内容和范围,但却直接或间接地显示了公共政策事项可仲裁性的扩大化趋势。这种趋势不仅表明了人们对仲裁认识的不断深化,也反映了国际经济交往的客观需要。正因为如此,美国最高法院在Mitsubishi案中主张在国际争议领域适用国际礼让原则,并且指出,不存在公共政策上的原因而禁止国际反托拉斯争议交付仲裁解决;欧洲法院在Eco Swiss案中要求仲裁员依职权适用被认为是欧盟公共政策的竞争法,而不否认竞争法争议的可仲裁性;而在Westacre案、Harbor案和Northrop案等案件中,英美等国法院肯定了违法合同或与合同有关的违法行为所引起的争议可以仲裁。
一言以蔽之,基于自由处分原则或可和解原则,通过国内与国际争议事项的区分以及国内与国际公共政策的区分,公共政策在可仲裁性问题上的适用已受到很大限制,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公法争议变得可以仲裁,彰显出公共政策事项可仲裁性的扩大化趋势。
就公共政策事项可仲裁性的立法与实践而言,我国在某些方面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随着我国对国际市场竞争的积极参与,涉外经贸争议势必会逐渐增多,而其中公法争议的可仲裁性问题也会日显突出。我国仲裁机构今后很有可能面临是否有权受理涉及反垄断、知识产权、贿赂等公法争议的案件,我国法院也有可能面临更多的是否承认和执行此类争议的外国仲裁裁决的问题。因而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出发,都要求我国在仲裁方面尽可能考虑适用国际上的通行作法,使原有的有关公共政策及其可仲裁性的规定和做法能因势而变,能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而有新的发展。因此,我国从立法上对公法争议的可仲裁性问题作出明确而肯定的规定已是必然趋势。WW黄德明
注释:
① 参见张艾清:《荷兰商事仲裁法律与实践若干问题探究》,载《法学评论》2000年第1期。
② Wilko v.Swan,346 U.S.434(1953).
③ American Safety Equipment Corp.V.J.P..Maguire & Co.,391 F.2d 826(2d.Cir.1968).
④ Jay R.Sever,“The Relaxation of Inarbitrability and Public Policy Checks on U.S.and Foreign Arbitration:Arbitration out of Control?”Tulane Law Review,Vol.65,1991,p.1669.
⑤ See Antoine Kirry,“Arbitrabilily:Current Trend in Europe”,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Vol.12,No.4,1996,pp.374~75;Matthias Lehmann,“A Plea for a Transnational Approach to Arbitrability in Arbitral Practice”,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Vol.42,2004,p.766.
⑥ 参见赵秀文:《从克罗马罗依案看国际仲裁裁决的撤销与执行》,载《法商研究》2002年第5期。
⑦ See Antoine Kirry,supra note ○5.pp.374~378;Eric A.Schwartz,“The Domain of Arbitration and Issues of Arbitrability:The View from the ICC”,ICSID Review-Foreign Investment Law Journal,Vol.9,No.1,1994,p.19.
⑧ See Homayoon Arfazadeh,“In the Shadow of the Unruly Horse: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d the Public Policy Exception”,The Americ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No.13,2002,pp.56~57;Jay R.Sever,supra note ○4,p.1661.
⑨ Westacer Investment Inc.v.Jugoimport-SDPR Holding Co.Ltd.,[1998]2 Lloyd's Report 111.转引自张宪初:《外国商事仲裁裁决司法审查中“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载韩健主编:《涉外仲裁司法审查》,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77页以下。
⑩ Mitsubishi Motors Corp.v.Soler Chrysler-Plymouth,Inc.,473 U.S.614(1985),PP.625—626.
(11) 参见[英]施米托夫著:《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11页。
(12) 采取这一标准的国家还有法国(《法国民法典》第2059条)、荷兰(1986年《荷兰民事诉讼法典》第1020条第3款)、葡萄牙(1986年《葡萄牙仲裁法》第1条)、印度尼西亚(1999年《印度尼西亚民事诉讼法典》第615条)等国。另外,调整国内仲裁的1969年《瑞士各州仲裁协定)第5条也规定了自由处分原则,而主要调整国际仲裁的1989年《瑞士国际私法》第177第1条则采取了更为宽松的“经济利益”标准,规定所有涉及经济利益的争议都是可以仲裁的。
(13) 采纳这一标准的国家包括奥地利(1983年《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577条第1款)、澳大利亚、比利时(1972年《比利时司法法典》第1676条)、德国(1998年《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030条第1款)、埃及(1988年《埃及国际商事仲裁法案》第9条)、阿根廷(阿根廷《国家民商事诉讼法典》第736条)等国。关于澳大利亚的情况,可参见Michael C.Pryles,“National Report:Australia”,Intl.Handbook on Comm.Arb.,Suppl.13,September 1992,P.8。需要指出的是,按照1998年《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030条第1款的规定,德国是以“经济利益”标准为主,以可和解标准为辅。
(14) 参见钱字宏,马伯娟:《从可仲裁性的发展看司法权的让渡》,载《仲裁与法律》第93辑。
(15) Wilko,346 U.S.(1953),pp.434~35.
(16) 参见侯登华:《可仲裁性问题探析》,载韩健主编:《涉外仲裁司法审查》,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49页以下。
(17) 参见郭玉军、裴洋:《论国际商事仲裁中涉及贿赂的合同的仲裁》,载《法学评论》2005年第2期。
(18) See Nathalie Voser,“Mandatory Rules of Law as a Limitp.ion on the Law Applicavble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The Americ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No.7,1996.pp.330—331.
(19) See Jay R.Sever,supra note④,P.1667.
(20) See Jay R.Sever,supra note④,P.1661.
(21) Scherk v.Alberto Culver Co.,417 U.S.506(1974),P.520.
(22) Mitsubishi,473 U.S 614(1985),P.629.
(23) ICC Case No.8423(1994),reprinted in 26 J.du droit int 1 153(2001).有关该案的案情,可参见Matthias Lehmann,supra note⑤,P.761。
(24) Attorney General v.Mobil Oil N.Z.Ltd.,[1987]4 ICSID Reports 117,139(N.Z.H.C.1997).转引自Matthias Lehmann,supra note⑤,P.770。
(25) Shearson/American Express Inc.v.McMahon,482 U.S.220(1987).
(26) 这方面的案例可参见Rodriguez de Quijas v.Shearson/American Express,Inc.,490 U.S.477,481(1989);Kowalski v.Chicago Tribune Co.,854 F.2d 186(7th Cir.,1988)。在最近的JLM Industries v.Stolt-Nielsen SA(387 F.3d 163,2nd Cir,2004)案中,联邦第2巡回上诉法院判定,所有因谢尔曼法而产生的反托拉斯争议均可提交仲裁。参见ADR News,“2nd Cir:All Antitrst Claims Arbitrable”,Dispute Resolution Journal,Nov.2004—Jan.2005,Vol.59,Issue 4,P.5。
(27) 该法典第1442至1491条是有关国内仲裁的规定,而第1492至1507条则对国际仲裁作了规定。
(28) Court of Appeal of Paris,Societe Labinal v.societe Mors et societe Westland Aerospace,120 J.du droit int 1957(1993).See Matthias Lehmann,supra note⑤,P.766.
(29) See Jay R.Sever,supra note④,p.1686.
(30) See Homayoon Arfazaden,supra note⑧,PP.51—52;Eric Schwartz,supra note⑦,PP,17 and 24;P.Mayer,“Mandatory Rules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No.4,1986,P.285.
(31) See Homayoon Arfazadeh,supra note⑧,p.52.
(32) See Matthias Lehmann,supra note⑤,P.772.
(33) 这一理论也被称为“咬第二口”理论(“second bite”doctrine)。
(34) Marc Blessing,“Mandatory Rules of Law versus Party Autonomy”,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No.4,1997,p.31,footnote 17.转引自侯宁:《论国际商事仲裁中强行法对意思自治的影响》,载《国际经济法网》http://www.intereconomiclaw.com/article/default.asp?id=478,2006年4月1日访问。
(35) Mitsubishi,473 U.S.,PP.636—637.另参见张艾清:《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研究——兼论欧美国家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
(36) Eco Swiss Chian Time Ltd v Benetton International NV,1126/97,[1999]E.C.R.I—3055.关于该案的基本情况,参见前注(35),张艾清文。
(37) G.SA v.SpA,reported in 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 XVIII,1993.pp.143—49.
(38) See ICC Bulletin,November 1994,P.44;ICC Bulletin,May 1995,P.51.Also see Andrej Bolfek,“Arbitration and Public Policy:Application of European Community Competition Law in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from the Aspect of Public Policy”,Croatian Arbitration Yearbook,No.7.2000,P.144.
(39) ICC Case No.7664(1996).See Abdulhay Sayed,Corrup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ommercial Arbitration,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4,P.426;Bernardo M.Cremades and David J A.Cairns,“Corruption,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 and Duties of Arbitrators”,Dispute Resolution Journal,Nov.2003/Jan.2004,P.83.转引自前引⑨,张宪初文,第391页以下。
(40) Homayoon Affazadeh,supra note⑧,P.43.
(41) 在解释和适用公共政策的条件问题上,国际上历来存在两种学说,即“主观说”与“客观说”。主观说认为,只要仲裁裁决所适用的法律与法院地国的公共政策相抵触,即可撤销或拒绝承认和执行该外国仲裁裁决,而不考虑承认和执行该裁决的结果如何。而客观说则强调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决的结果与影响,只有在承认和执行裁决的结果会危害撤销地国或承认和执行地国利益的情况下,才能以公共政策为由撤销或拒绝承认和执行该裁决。
(42) See Albert Jan vail den Berg,“Court Decisions on the New York Convention”,ASA Special Series,No.9,1996,P.91.
(43) Parsons T Whitkmore Oversea Co.v.Societe General(Rakta),508 F.2D 969(2D Cir.1974).
(44) Fotochrome Inc.v.Copal Co.,517 F.2d 512(2nd Cir.1975),reported in 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1,1976,PP.202—203.孙南申:《中国内地与港澳之间区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保留问题》,载孙南申、杜涛主编:《当代国际私法研究——21世纪的中国与国际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以下。
(45) See“Editorial”of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Vol.12,No.4,1996.
(46) See Court of Appeal of Paris,Societe Ganz et al.v.societe nationale des Chemins de fer tunisiens,Rev.Arb.478 (1991):Societe Aplix v.societe Velcro,Rev.Arb.164(1994).See Matthias Lehmann,supra note⑤,P.766;Jay R.Sever,supra note ④,P.1685.
(47) 参见前引①,张艾清文。
(48) The decision of the Federal Supreme Court dated April 19,1994.BGE 120 II 155.634.
(49) Lemenda Trading Co,Ltd v.Afican Middle East Pet roleum Co,[1988]Q.B.448.
(50) See Nelson Enonchong,“The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Based on Illegal Contracts”.Lloyd's Maritime and Commercial Law Quarterly,Part 4,November 2000,P.498.转引自前注(17),郭玉军文。
(51) 韩健著:《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法的理论与实践》(修订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48页。
(52) Audley Sheppard and Joachim Delaney,“Corruption and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Essay of the 10th International Anti-Corruption Conference,http://www.10iacc.org/content.phtml?documents=106 &art=167.转引自前注(17),郭玉军文。
(53) Harbor Assurance Co(UK)Ltd.v.Kansa General International Insurance Co Ltd.(1993)1 Lloyd's Rep.455.参见Philip Yang,“Aribtator's Jurisdiction & Arbitrability”,载韩健主编:《涉外仲裁司法审查》,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页。
(54) Northrop Corp.v.Triad,593 F.Supp.928(1984).See Nathalie Voser,supra note 22,P.351;朱克鹏著:《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适用》,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页。
(55) Omnium de Traitement et de Valorisation SA(OTV)v.Hilmarton Ltd,ICC case No.5622(1988 & 1992).
(56) Audley Sheppard and Joachim Delaney,supra note(52),转引自前注(17),郭玉军文。另外,有关贿赂争议可以仲裁的案件,还可参见赵秀文著:《国际商事仲裁及其适用法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以下;前引⑨,张宪初文,第379页以下。
(57)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顾昂然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草案)〉的说明》。
(58) 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立法,程序法方面,可参见《民事诉讼法》第217条、第260条、第269条以及《仲裁法》第58条;实体法方面,可参见《民法通则》第150条、《海商法》第276条、《民用航空法》第190条、《合同法》第7条、《外资企业法》第4条、2006年《企业破产法》第5条。
(59) “开封市东风服装厂和香港泰初(音)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诉河南服装进出口集团公司案”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有关该案的案情,参见前注(56),赵秀文书,第309页以下。
(60) 有关该案的案情,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对ED&F曼氏(香港)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及执行伦敦糖业协会第158号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京高法[2003]7号。
(61) Soleimany v.Soleimany.31[1999] Q.B.785.
(62)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ED&F曼氏(香港)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伦敦糖业协会仲裁裁决案的复函”,[2003]民四他字第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