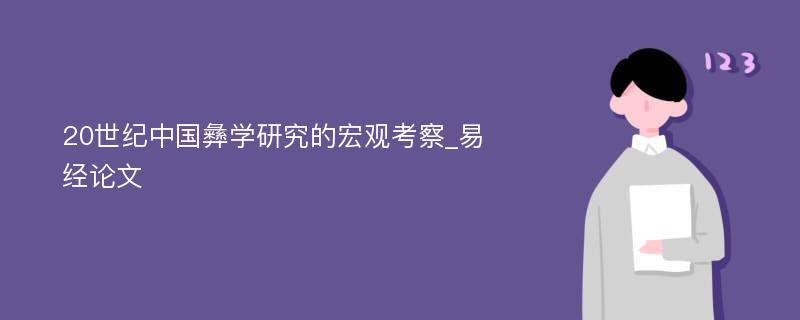
二十世纪中国易学研究的宏观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易学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易》是中国封建时代的学术——经学的核心,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史中,作为五经之首,它始终是人们研究和关注的焦点。回顾和总结其在本世纪的研究现状,既可反映出传统文化在本世纪的际遇,又可以为它在下一世纪的发展提供借鉴。而它本身的特殊性,又能使我们透过百年来的易学研究,透视出本世纪中国学术研究的方法论特征。我们选择“二十世纪的中国易学”作为研究对象,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一
那么,如何把握二十世纪的中国易学研究呢?
二十世纪的中国易学研究,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变革的历程密不可分。在这百来年中,中国先后发生了辛亥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次改朝换代造成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变革,都对易学研究造成了影响。但由于辛亥革命发生在本世纪初,此前的十来年不足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时期。所以,我们以1949年为限,将本世纪的易学研究分为两大发展阶段,49年之前为第一大阶段,49年之后为第二大阶段。在第二大阶段中,又分为大陆和台湾两部分。
就第一阶段来说,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为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划上了句号。但封建时代的学术思想以及传承这种学术思想的方法和手段——经学,却没有因此而马上退出历史的舞台。直到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些接受了新思想的学者,特别是历史研究领域的古史辨派的学者,以史学的观点重新看待传统经典,才真正打破了传统经学的僵局,动摇了传统经学的根基。因此,这一时期的易学研究,呈现出新旧并存、对垒和除旧布新的复杂局面:既有站在经学的立场,用经学的方法和观念摭理《周易》的经学家的研究,又有站在史学家的立场,用文献学的方法整理《周易》的古史辨派的研究,又有站在社会学和文化学的立场,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读解《周易》的唯物史观派的研究,还有既继承传统易学研究中的合理因素,又认肯新史学观念的新探索者的研究。当然,四种研究倾向并非绝然分途,而是既交互进行,又相继发展。而新旧、中西之间的互动和会通则构成了这一阶段易学研究的基本特征。
与流派纷呈的第一阶段不同,第二阶段大陆的易学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大背景中进行的。具体地说,又可以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30年代古史辨派和唯物史观派讨论问题的继续和深入,如讨论主要集中在《周易》经传的成书、著作年代、性质、哲学思想等方面。不过,由于这一时期的易学研究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讨论交叉进行,所以,这次讨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一次尝试。1978年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化讨论的兴起与深入,易学研究又呈现出多学科、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格局。关于《周易》经传的研究,关于《周易》系统典籍的研究,关于易学史的研究,关于易学哲学的研究,关于易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关于易学与科学的研究,乃至于利用出土文物对《周易》进行的研究等等,都一时成为热点。而且,研究者都自觉地继承并超越了前一时期唯心、唯物,辩证法、形而上学绝然对立的狭隘的思维模式,而把探讨易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易学与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等作为研究的目的。因此可以说,既有理智的剖解,又有情感的认同,为下一世纪的易学研究开启了一个多元的方向。
1949年后,台湾的易学研究,经历了与大陆不同的发展历程。大体说来,他们仍然沿袭了民国时期的学术作风和思维路向,如49年以前便已具有一定影响的一些易学家,这一时期仍很活跃。他们多执教于台湾各高等院校,从学者众。所以,台岛“易学的薪传与后续的研究甚为活络”。(注:黄沛荣:《近十年来海峡两岸易学研究的比较》,《周易研究》1989年第1期。 )而由于他们“没有经历过对儒学和唯心主义哲学的猛烈的批判,在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扬方面阻力较小”(注:方克立:《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年第5期。),因此传统色彩较浓。 既有类似于清代汉学的辑佚、考注,又有类似于宋代义理之学的哲学研究,还有颇具特色的易学史研究。而传统的象数与义理之争,则偶尔以科学易与义理易的面目重现于学术论坛。媚世的心态和利益的驱使,也常常使占卜迷信堂而皇之地在易学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但总体而言,台湾学者在易学文献的辑佚、考注、易学史研究和易学思想的研究方面成绩颇佳。
二
二十世纪的中国易学研究,概括起来说,前一发展阶段,尤其是本世纪初,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意在打破封建传统文化——经学的僵局,树立本世纪学术研究的范式。所以,易学研究中的破旧和开新(不同于立新)较为突出;后一发展阶段,尤其是本世纪末,为了重新建立新文化,开启下一世纪学术研究的方向,总结与创新的势头比较明显。当然,事实上的问题远比我们的这种概括要复杂。但如果放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大背景中审视,不难发现,前后两个复杂的发展阶段中,大都体现了本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主流特征——理性精神。
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学术的变迁十分壮观。学术的变迁以思想的解放为背景,以观念的更新为前提,又以方法的重建为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易学研究,与传统易学研究的最大不同之点,恰恰就在于观念的不同和方法的差异。就观念说,传统经学向来视《周易》为“事历三古”,“四圣同揆”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后学只有领悟、卫护和发扬其中的圣人之道。……不允许质疑和批评”(注:朱伯崑:《朱伯崑论著》第832页,沈阳出版社,1998年版。)。而本世纪的易学研究,首先就是以打破它的这种神圣性和神秘性为起点的。视它为卜筮之书也好,视它为博大精深的哲学著作也好,人们基本上都能够从观念上摆脱经学模式的束缚,站在一个较为客观的立场上探讨易学中的诸问题。而这无疑得益于研究方法的推陈出新。
传统易学,虽然有两派六宗之分(注:说见《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提要》。),但就方法论的意义说,不过象数、义理两种。象数学的方法以象、数为《周易》经传之基础,注重探求卦爻象和卦爻数与卦爻辞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善于以《周易》六十四卦为框架结构,建构天人同构的复杂而庞大的宇宙生成体系。义理学的方法以舍象取义、得意忘象为特征,注重阐发《周易》经义名理,哲学思想,以及宇宙中的普遍常存之道。这些方法在易学发展史上,都曾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既是传统易学的研究方法,又是传统易学的核心内容。但是,进入本世纪以后,这些方法几乎随着经学观念的衰落而渐渐地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与新史学思潮颇相符合的一些新的研究方法。
纵观本世纪的易学研究,有三种方法颇值得注意:一是实证主义的方法,一是唯物史观的方法,一是逻辑分析的方法。(注:参见朱伯崑:《易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朱伯崑论著》第831页。)这三种方法被相继用到易学领域的研究之中,大体表现了本世纪易学研究的三个发展时期的主流特征。实证主义的方法在本世纪初的二、三十年代颇为盛行,唯物史观的方法在五、六十年代最为独尊,逻辑分析的方法则在本世纪的后二十年最有特色。当然,这种分疏,仅仅是就其“主流特征”而言。实际上,在许多学者那里,这几种方法往往是同时并用的。另外,传统经学的研究方法虽然式微,但也还没有中断。尤其是在本世纪末,随着回归元典的呼声的日渐高涨,有些学者自觉地用“改造”了的经学方法和经学观念重新审视易学,使易学的研究真正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大体说来,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是随着新史学的兴起而崛起的。就易学的研究而言,可以古史辨派为代表。这一派研究易学的目的,用已故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的话说,就是“于《易》则破坏其伏羲神农的圣经的地位而建设其卜筮的地位”,“辨明《易十翼》的不合于《易》上下经”(注: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自序”第1页。)。 换句话说,就是要求还《周易》经传的本来面目。因此,他们更多地是用文献学的研究方法,象老吏断狱一样地打散历代经学家为《周易》经传编制的种种说词,逐个判明它们的真实样象。唯物史观的易学研究方法也与新史学的传播有关。其首倡者和最早的尝试者是已故著名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与古史辨派仅仅把经书还原为古史资料不同,唯物史观派的易学研究则注重于揭示史料背后所隐藏着的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以及史料本身所包含着的哲学思想。六十年代,有学者将此一方法的核心内容概括为“坚持严格的历史性”(注:方蠡:《坚持哲学史中严格的历史性》,《哲学研究》1963年第3期。)。作为一种哲学方法, 逻辑分析的方法虽然在本世纪上半叶就曾被一些学者所运用,但真正用于易学的研究,主要是近二十年的事情。这种方法注意“对经、传、学中的术语、概念、范畴、命题以及理论体系,进行逻辑的分析”(注:方蠡:《坚持哲学史中严格的历史性》,《哲学研究》1963年第3期。), 以揭示出其理论思维的特征及价值。以上这些方法,都是本世纪的易学研究中颇为流行的新方法。说它们新,并不意味着与传统的经学方法毫不相干,如实证的方法,就曾综合了乾嘉之学的求实精神和宋代以来的怀疑精神。
总之,这些方法,在本世纪的易学研究中,各自显示了自己的特殊价值,分别开拓出了一些易学研究的新领域,也都基本切合了本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精神——理性主义精神,因此形成了本世纪易学研究的发展主线。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除此之外,也还有一股易学研究的伏线,值得引起高度重视。本世纪初,在强大的新文化运动的攻势之下,传统经学不唯还手无力,甚且招架乏术。大师如章太炎者,亦不过是以《周易》六十四卦比西方之社会进化观而已。但这种情况在三、四十年代稍有改变,一些学者在有选择地接受了新史学观念的同时,开始重理传统经学的精神脉络,整理被古史辨派打得七零八落的易学。其中尤以著名哲学家熊十力先生最有特性。他由佛归儒,阐释易理,大有“振斯绝学”之势。但这种势头刚刚露出,便适逢时代巨变,而在全国上下学马列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社会背景下变若一缕游丝。直到本世纪末,易学研究的多元格局形成之后,才又被个别学者以“诠释文本”的现代解释学方法重新继起。同时,传统易学中的象数之学也在多半个世纪的遭压之后,发挥其“援易以为说”的特长,与现代科学联姻,而竟一时号称显学。这些都不单纯是传统易学的回归,因此很需要注意加以分析和研究。
三
由于观念和方法的更新,本世纪的易学研究表现出了许多不同于传统经学的新气象,也提出了诸多为本世纪所独有的易学话题。
古史辨派打破经学,使传统经学的种种“不刊之论”均遭到怀疑:八卦是否伏羲所画?六十四卦是否文王所重?卦、爻辞是否文王、周公所系。《周易》究竟成书于何时?孔子是否读过《周易》?《易传》是否孔子所作?《周易》是否如历代经学家所说的那样,包含了深刻的哲理,《周易》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易传》对《周易》的解释是否合乎《周易》的本义,历代易学家为解释《周易》经传所创设的种种体例是否符合经传的精神?等等。这些在传统经学中本来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在本世纪竟都成为了问题。而新史学家的铁面无私的口号:“拿证据来”,使无论站在何种立场上的易学家,都不得不用自己的考证推出自己的见解。而唯物史观派在重视辩证这些问题的同时,又将目光集中转向对文献背后所隐含着的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精神信仰,以及文献本身所包含着的哲学思想的性质的探讨,将易学研究引向了更为广阔的领域。这些都是本世纪易学研究中的新问题,又都是传统经学中所无而为本世纪的学者们所提出、所开拓的新问题。在本世纪初和本世纪中叶,这些问题几乎成为易学研究的核心。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易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哲学上的逻辑分析方法的成功运用,易学研究的领域又有新的拓展。易学理论思维的研究,易学与中国哲学之特征的研究等过去不大注意的问题,这时都被提了出来。与此相关的易学史的研究,易学与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易学与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研究等为过去所忽视的领域,也都蓬蓬勃勃地得以展开。同时,由于大量与易学有关的出土文物的发现,利用地下发掘的材料研究易学,也一时成为热点。这些研究,大多力图遵循严格的历史性原则,在解决上一阶段提出的问题的同时有所创新,因此,表现出了一种成熟地运用本世纪积累起来的研究方法和新材料,总结和反思几千年易学研究的得失和经验教训的倾向。
四
上述新观念、新方法、新话题,也使本世纪的易学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成就。大体说来,有以下一些方面值得注意:
其一、《周易》卦爻辞著作年代的研究。《周易》一书结构特殊,构成成分比较复杂,有卦有辞,卦系何人所画,何人所重,辞系何人所写等从来就有不同的说法。这为人们正确把握《周易》一书的编写年代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学者如顾颉刚先生利用殷墟甲骨的研究成果和其它文献资料,推定《周易》卦爻辞“著作年代当在西周初叶”(注:顾颉刚:《周易卦交辞中的故事》,《燕京学报》第6期。)。 顾先生的这一推论“可以说基本确定了《周易》卦爻辞年代的范围,是极有贡献的。后来有些论著沿着顾文的方向有所补充,但其结论终不能超过顾先生的论断”(注: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第2页,长春出版社,1992年8月版。)。其二、《周易》时代的社会结构及性质的研究。《周易》一书的文字部分虽然由一些类似于卜词的卦爻辞组成,但却与后人编造的谶诀咒语不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为当时的筮占实录,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情况。本世纪三十年代,郭沫若先生利用这些材料中的一些蛛丝马迹,推论了当时的社会结构,生活基础和精神生产(注:郭沫若:《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载《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5月版。)。 郭先生的这种研究虽然还很初步,得出的结论也未必十分正确,但却开拓出了一个新方向。后来有不少人沿着此一方向探讨了《周易》卦爻辞中反映出的当时社会的宗教、婚姻、农业、牲畜等问题,为本世纪的易学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其三、《周易》与中国古代哲学智慧的研究。《周易》卦爻辞,虽然多由只词片语组成,但其中保存了许多该时代或更早的歌谣民谚,从某些侧面反映了我国先民的哲学思想和生命智慧。另外,《周易》卦爻的特殊符号系统及其特殊的排列次序,也都深深地凝聚了古圣先贤的良苦用心。在本世纪的易学研究中,有不少学者,透过这些只词片语和符号排列,钩玄索隐,探讨了卦象与卦序中的逻辑思维,卦爻辞中的世界观。这种探讨既避免了传统经学家的卫护道统的盲目尊古行为,又超越了近人单纯视《周易》为卜筮、迷信之书的简单做法,深化了易学的研究。其四、《易传》哲学的研究。在本世纪的易学研究中,虽然关于《易传》的作者、成书年代等问题,在学者之间存在着诸多分歧。但就《易传》是一部哲学著作这一点来说,人们的看法比较一致。大家探讨了《易传》哲学的性质,《易传》哲学的基本原理,《易传》解经的特殊方法。特别指出了其中所包含的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和有别于西方的而为中国古人所最擅长的辩证思维。这一思维规律的揭示,是本世纪易学研究中的一大贡献。其五、易学史的研究。自汉代尊《周易》为经书以后,历代经学家都把研究《周易》视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大批成就卓著的易学家。这是一笔丰厚的哲学遗产,需要人们作出总结。历史上有不少经学家十分注意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但由于缺乏历史主义的观点,这种总结往往很不系统,很不全面。本世纪初,著名经学家刘师培先生在所著《经学教科书》中,用不小的篇幅介绍了易学发展的历史,但仍十分简略。进入六十年代,开始有人集中精力撰写大部头的易学史专著。到八、九十年代,这一领域的研究已是十分的热烈。通史的研究,断代史的研究,专题史的研究,人物思想的研究等都得以开展,形成了本世纪易学研究的一大景观。其六、易学理论思维的研究。在本世纪的易学研究中,易学哲学的研究一直受到重视。进入八十年代以来,由于传统文化反思的时代要求,易学哲学的研究开始不断超越前一时期的单纯哲学性质(唯心、唯物等)的讨论,而转向易学哲学与中国文化之特征的关系的探讨。有些学者认为:“易学作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庞大的学术思想体系,所以经久不衰,受到历代学人的重视,其关键在于提出一套观察和思考宇宙和人生问题的思维方式。易学文化所以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深刻的影响,说到底,是基于其所提出的思维方式。”(注:朱伯崑:《易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载《朱伯崑论著》第798—799页。)因此,他们在研究易学哲学时,特别注意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分疏易学理论思维,并对传统易学中所体现出的直观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以及象数思维等,进行了颇为深入地探讨,大大推进了易学哲学的研究。这种探讨,把本世纪以来的深沉的民族文化反思引向了一个更为本质的层面,为人们“转换”传统易学的现代意义开辟了科学的理论通道。其七、易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的研究。《周易》“原属于儒家经典,后来又分别为道家和佛家文化所吸收,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影响”。(注:同上。)如何把握易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近二十年来易学研究中的重大课题之一。有些学者从文化精神发生学的角度,透过易学发展的历史,探索了《周易》在中国文化思想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其中所蕴涵着的中国文化的思想精髓和价值理想。这是一种从价值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层面展开的易学研究,对于全面把握易学的实质是颇有意义的。其八、易学与科学的研究。《周易》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元典,不但受到经学家的重视,也常常被历代的“自然科学家”拿来做自己的“科学”研究的理论根据。虽不免“援《易》以为说”的通病,但其中也确有从自然哲学的意义上来理解易学的尝试。特别是传统易学象数派中的一些人,一直在试图利用《周易》特殊的符号系统和天地人三才合一的整体思维模式,探讨与宇宙构成有关的一些问题。在本世纪的易学研究中,有些学者比较重视分析和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也有些学者以此种研究为基础,更进一步,试图在传统易学与现代自然科学之间寻找某种沟通的渠道。这项工作,虽然目前没有取得什么可观的成果,但作为一种易学现代化的新探索,也是值得予以关注的。其九、利用考古材料进行的易学研究。利用地下出土的与易学有关的材料进行易学研究,并非始于本世纪,见于史载的就有两次,但本世纪这方面的研究最为壮观。本世纪初,曾有不少学者以殷墟甲骨卜辞为参照,研究《周易》卦爻辞的构成及性质。七十年代末期,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文物中,有一部分内容与易学有关,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八十年代初期,又有学者用卦爻符号翻译殷周卜骨及铜器上的奇异的数字,发现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也引起了学界的轰动。至此,利用这些出土材料进行的易学研究便蓬蓬勃勃地展开,乃至于成为本世纪末易学研究领域里的一大景观。这种研究对于澄清易学史上的一些问题,弥补易学史上的一些发展环节是十分有价值的,也往往是其它性质的文献研究所不能代替的,因此,应该视之为本世纪易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以上所述,只是就本世纪易学研究中比较容易作出评价的几个方面而言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方面,如关于《易经》性质的研究,关于孔子与《周易》关系的研究,关于《易传》成书年代的研究,以及关于八卦起源的研究等,也都值得一提。这些研究虽一时尚不能得出颇为周延的结论,但却促进了易学的发展,因此,也应当予以积极的评价。
五
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频繁使用了“新”字,所谓“新观念”,“新方法”、“新话题”等等。“新”当然是相对于传统的“旧”而言的,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新”和“旧”,并非价值判断,而是一种“发展史”意义上的评价。换言之,“新”并不意味着正确无误,“旧”也不表明一无是处。这也就是说,“新”与“旧”一样,都是时代发展的产物,都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二十世纪的易学研究,尤其是八、九十年代以前的研究,就其主流而言,可以说贯穿着批判封建旧文化的主线,深印着两次革命(辛亥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烙印。这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这是时代的潮流,历史的际遇。但是,站在世纪之末,总结百年来易学研究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在充分肯定其成绩的同时,也充分反思其局限性之所在。
观念之“新”是相对于经学观念之“旧”而言的。传统经学观念之“旧”,前面已经说及。之所以谓之“旧”,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以《周易》为核心的传统经学,已无法适应以近代知识论为背景的西方文化的挑战。朱伯崑先生在论及清代汉易的复兴时,说过一段非常令人回味的话:“汉易的复兴表明古代易学发展到宋易阶段后,再不能创造新的形态了。因此清代的易学及其哲学,就其理论思维发展的总趋势说,可以说是由高峰走向低坡。”(注: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四卷第5页,华夏出版社,1995年1月版。)《周易》是儒家的第一号经典,易学理论思维的衰落,足以说明传统经学在清代已经失去了其固有的生命活力。所以,当强大的西方近代文明冲击中土文化时,作为封建时代之正统意识形态的儒家经学便显得毫无应付的能力。因此在辛亥革命结束了传统经学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之后,打破经学已是“现在的时势中所应有的产物”了(注: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自序”第79页。)。但打破经学并不意味着要把经学彻底干净地“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换句话说,不是“为破而破”。破是为了立,破旧是为了创新。而在很长一段时间中,由于人们抱持着“唯古是疑,唯疑是尊”的观念,看不到《周易》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更是否定这些元典作为丰富的文化资源,在新文化建设中的价值。结果,号称打破经学,却并不能真正分析它与封建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而“讲《周易》是为了否定《周易》,……把《周易》否掉了,就行了,就算完成任务”(注:金景芳:《周易讲座》第1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版。)。这种连婴儿和洗澡水一块儿泼掉的做法只能导致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因而值得深刻反思。
方法之“新”也是相对于经学旧方法而言的。如前所述,传统易学有两派六宗之分,就其研究方法说,不外乎义理、象数两种。这两种方法虽然在对《周易》的理解上存在着不同,但有一点是比较一致的,就是注重“解释”,不注重实证。这样做的结果是容易混淆或抹杀历史真相,经、传、学不分,乃至把自己对《周易》的理解看作是《周易》本身固有的思想。但是,传统易学研究方法也并非没有其长处。首先,义理和象数两种方法,既是传统易学研究的方法,又是传统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方法与对象浑然一体的模式,对于易学本身的创新和发展是极为有利的。两千年来的易学史之所以内容丰富,花样翻新,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其次,这些方法都是时代的产物,与该时代的时代精神十分吻合,如汉代讲象数,宋人重义理,都与他们那个时代的思想潮流相一致。第三,由于这些方法以特殊的形式反映了时代的精神,所以,也使它们有资格成为该时代人们认识宇宙,发展学术的理论思维基础。如宋儒以儒家的纲常伦理为核心,以易学思维为理论基础,吸收佛教、玄学、道教精于思辨的理论特征而创立的新儒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与传统的易学研究相比,本世纪的易学研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站在易学之外研究易学。这种研究,可以称之为对象性研究,研究者就象一个解剖师,他可以把研究对象条分缕析,详细入微地解剖开来。如对文献的辨伪和整理,对文献背后的历史背景、社会结构、思想渊源的探索,对文献内容的逻辑结构的分析等。这些方法,可以弥补传统经学方法中经、传、学不分的不足,把经的还给经,把传的还给传,把学的还给学。一句话,可以还历史以真实面目。就这一点说,这些方法之“新”是有其价值的,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站在易学之外研究易学的,方法与对象二分的模式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那就是往往容易造成分析批判有余,继承创新不足的后果。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拿乾嘉之学作比较。乾嘉之学,辨伪求实,被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誉之为“精”。从学术史的角度说,他们的贡献是勿庸置疑的,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从思想史的角度说,这种“精”对于理论思维的发展却没有作出什么贡献,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本世纪的易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乾嘉求实精神的翻版。与乾嘉诸老相比,本世纪的诸多学者,考证的工夫非不高也,分析批判的力度非不够也,但对于传统易学理论思维的发展却没有起到什么推进作用。非但没有什么推进,甚且连可以继承的东西也找不到。因此,也就没有产生真正意义的“现代新易学”。这是很值得深思的。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高举“批判继承”的旗帜,而收效甚微,应该说与这些方法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不无关系。文化的批判继承不象用刀子削苹果,剃去斑点就可以成为下肚的美味。继承是伴随着创新进行的,没有哪一个古代易学家的思想,经过一番批判之后就能成为可以继承的东西。要想继承它,还必须把它与新的东西相融合,还必须赋予它一些新的、为它原来所没有的内容。近些年来,有学者提倡研究易学中的理论思维,提倡“创新”,大概就是由于看到了这些方法的局限性。如朱伯崑教授说:“所谓创新,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更新。所谓更新,不只是用现代人习惯使用的哲学语言,诠释中国古典哲学著作,便于现代人理解,更为重要的是,运用现代科学的治学方法,阐述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并以西方传统的思维方式为借鉴,发扬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知灼见,进而创建适合时代需要的,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注:朱伯崑:《中国传统哲学的未来走向》,载《朱伯崑论著》第51页。)我想,如果真正做到了这一点,易学的现代化就不会成为什么问题了。
总之,20世纪的易学研究,有其长处,也有其局限。发扬其长处,克服其局限,就一定能使未来的易学研究焕发出新的光彩。
标签:易经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周易八卦论文; 易经六十四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文化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文献回顾论文; 经学论文; 玄学论文; 科学论文;
